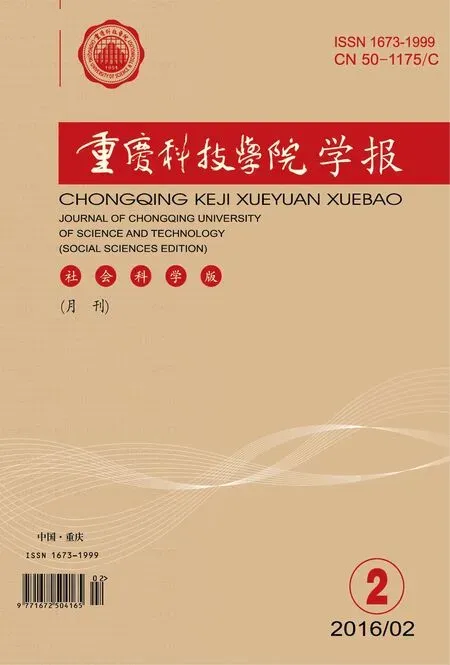论佛教与儒家的会通于善
代训锋
论佛教与儒家的会通于善
代训锋
摘要:佛教传入中土初期,在道德观念上与传统儒家存在严重分歧。为了获得与中国本土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致性,佛教“援儒入佛”,把“五戒”比附为儒家的“五常”,向人们灌输修善止恶的道德意识,强调佛教并不违背世俗道德。佛教与儒家会通于“善”,且相资互补。儒家重在治世、修身,佛教重在出世、治心,对社会教化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关键词:佛教;儒家;道德观念;劝善惩恶;五戒;五常
佛教对古代中国来说是一种外来思想。在一个本身有着成熟思想体系的国度里,外来思想一般很难融入并改变既有的思想格局。然而,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荡中,不但逐渐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而且与儒家和道家思想一样,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是如何做到的呢?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问题,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笔者拟从伦理学角度,通过比较佛、儒的修善思想,探讨佛教是如何结合与吸收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从而融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之中的。
一、佛法初传时的儒佛对立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底蕴,这种历史和底蕴带来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中国人以“我已有之”或“古已有之”的心态,轻视、贬抑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然是困难重重的。佛法东传初期遭遇的阻力,首先是当权者的取舍态度,其次是传统文化的排斥。
早期的统治者对佛教有压有提。由于佛教与传统伦理规范的冲突,废佛事件也时有发生。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就是由统治者发动的4次大规模的废佛事件。北魏太武宗、北周武帝、唐代武宗发动的废佛运动,采取毁寺、杀僧、焚经、烧像等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毁灭佛教;五代后周的世宗则是通过敕令严格管控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统治者限制、打击佛教,主要是从政治得失方面考虑的。佛教徒号称“方外”之士,不从王化、不事生产,被视为社会的寄生者。僧侣人数越多,对社会越不利,甚至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构成威胁。《魏书·释老》记载: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后,“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1]1775。如果这些属实,可见当时的佛教徒在国家总人口中已经占据相当比例。这样一大批不事生产却耗费大量社会产品的僧侣的存在,必然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因此,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绝不会听任佛教无限发展。
除了政治原因,还具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上述发动废佛运动的几位君主,要么崇儒,要么尊道,都把佛教视为夷狄之法。北魏太武帝信任道士寇谦之和司徒崔浩,以为佛教“夸诞大言,不本人情”,下诏毁佛,并声称“承天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1]1766。其实,太武帝的毁佛也是佛道斗争的结果。唐武宗的废佛敕书中写道:“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并认为废除佛教乃“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2],是他当仁不让的职责。
历经几次劫难,佛教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佛教要想在中国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回应本土文化对佛教的批判和挑战,避免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对立,尽量使自己的伦理道德适合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需要,从而进一步获得民众的认同、社会的认可和当权者的支持。
从根本上说,在中国儒佛的斗争和对立主要不是在政治层面,而是在伦理思想和道德生活层面。一般而言,佛教和儒家的区别是出世和入世的对立。佛教认为人生皆苦,现实生活皆为虚幻,不可执著,因而要出世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儒家则秉持《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以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来对待现实人生。佛教追求精神解脱,追求不死不生的“涅槃”境界,这就必须放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责任。而儒家则志在家国天下,强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目标。
在道德观念上,佛教和儒家的对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行善作恶、因果报应问题上的对立。佛教主张业报轮回说,认为有因必有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之间是生死相继、因果相依,生命就是在如车轮般的因果轮回中承受自己前世种下的业报。中国传统观念中虽然也有报应一说,但这种善恶报应是建立在家族、家庭、血亲关系的基础上,反映的是小农经济社会的特征。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秧”,说的是一个人行善积德定会荫及子孙,而一个人如作恶多端必会殃及后代。
二是在身体发肤、服饰衣冠问题上的矛盾。佛教要求出家修行者抛弃世俗生活,这首先就涉及发肤、衣冠。佛教戒律要求修行者剁发毁服,以“偏袒右肩”为证,这在儒家看来简直是无法接受的。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自己无权随意处置,剃发就是对父母的大不孝、大不敬;服饰则是区别上下尊卑的重要标志,毁服则打乱了礼法章程。
三是在对待现实政权态度上的矛盾。按照佛教仪规,世间最尊者不是皇帝或者王者,而是佛教的最高精神象征——佛陀。在僧侣看来,人间的统治者在地位上根本无法与佛陀相提并论。佛教规定,僧侣出家修行,成为彻底的方外之人,就不可再理会世俗生活中的尊卑和长幼。除了礼拜佛陀之外,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君王,都不可行礼跪拜。这在以礼拜“天地君亲师”为天经地义的儒家看来,绝对是不可忍受的。儒家伦理尤其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关系,忠君、孝亲是人生的不二法则。因此,所谓“沙门不敬王者”,在儒家看来是绝对的不忠不孝。
四是在出家问题上的矛盾。这一矛盾最为深刻,不可调和。佛教出于对世俗生活的彻底否定,要求修行者出家弃亲,脱离现实的家庭和社会生活。这直接触动了儒家伦理纲常的根基。儒家讲求的孝道首先是延续香火,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出家弃亲在儒家看来简直是尽毁人伦。
佛教与儒家在道德观念上存在那么多的分歧与对立之处,要获得与中国本土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致性,得到民众的认同和统治者的认可,这如何可能?换言之,二者如何会通?
二、劝善惩恶的出处之道
佛教最基本的伦理主张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道德观念一是处世之德,二是出世之道。在佛教看来,二者并不相悖。东晋安帝时,桓玄总理朝政,重提沙门敬上旧事。认为沙门沾受国恩,应守国制,不宜废其敬王之制,并以其书示于庐山慧远。慧远以佛教界权威的身份回答桓玄,于是有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慧远阐述了佛法与世教之间小异大同的关系。他说:“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3]慧远强调,佛教的处俗之德与王化之制即社会道德纲常并不矛盾,事君有礼、侍亲有敬,忠孝之义亦为佛教所许。佛教在涉及现实生活时所执的善恶价值观念,与世俗道德确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佛教要得到当权者的支持和民众的认同,在伦理道德上就必须向现实生活靠拢。慧远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3]就出世之道而言,佛教伦理具有超迈性。但这种超迈并非脱离或违背生活,而是把握了生活的本质,是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领悟。佛教认为,人生充满烦恼和痛苦,而其根源在于有“我”。要根除烦恼和痛苦,就必须“无我”。因此,对于有利于“我”生存的一切东西,都不觉得珍贵。它觉悟到生命源于自然之化,但并不主张复归于自然。在出家领域,佛教的价值观念与世俗思想出现了分歧。但是,佛教向人们宣示的并非生活的道路,不是教人如何去生活,而是教人如何完善。出家之道与世俗之德的差别是两种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差别,并不是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
慧远认为二者在修善方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说:“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3]出家修道者其礼仪虽与世俗不同,但形乖而实同,不失孝敬之义,且有助治之功。在他看来,按出世之道修行,不仅可以实现个人自我的超越与完善,而且能够极大地利益众生、德泽天下。佛教徒既要保持佛教的独立性,又要依附王权,与传统礼教保持一致,慧远说清了这个理。
为了取得当权者的支持,获得民众的认同,佛教一再调和教义与世俗道德之间的对立,强调佛教道德观念与世俗道德之间在修善方向上的一致性。佛教学者经常以“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比附“五常”(仁、义、礼、智、信),认为不杀是仁,不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瞰肉,神气清洁,益于智也。如唐僧宗密说:“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4]。宋僧契嵩说:不杀指应当珍爱一切生命,不能残害任何生命,故可称为“仁”;不盗指不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实质是不义不取,故可称为“义”;不妄语指说话诚实,言行一致,不以言欺人,故可称为“信”;不邪淫指在两性关系上节制有礼,对非配偶的异性不作非分之想和非分之举,故可称为“礼”;酒会使人头脑昏沉、思想混乱,不饮酒则可保持头脑清醒、思维明晰,故可称为“智”。因此,佛家“五戒”与儒之“五常”乃“异号而一体耳”。“夫仁义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于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5]。其实,以“五戒”比附“五常”,除“不杀生”与“仁”基本相合,其他的都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在教化民众方面,它们都具有劝善惩恶的作用。契嵩强调指出:“不杀必仁,不盗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乱,不绮语必诚,不两舌不谗,不恶口不辱,不恚不仇,不嫉不争,不痴不昧。有一如此,足以诚于身而加于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5]这即是说,修持佛教的五戒十善,就能做到道德高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心怀仁义慈悲,自信信人,兴廉正,息纷争,使人己融洽,社会和乐。既然有这种社会功用,统治者自当给予扶持。
佛教认为其教义与忠君、孝亲的道德规范并不相违。“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3]。宋初僧人延寿详细阐述了佛教教化民众、利乐社会的功能。他说:“佛法众善,普润无边,力济存亡,道含真俗。于国有善则国霸,于家有善则家肥,所利弘多,为益不少……夫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陛下所谓坐致太平也。是以包罗法界,遍满虚空,一善所行,无往不利,则是立身辅化,匡国保家之要轨矣。若以此立身,身无不立;以此匡国,国无不匡。近福人天,远结佛果。”[6]在延寿看来,佛法教人修持五戒十善,有益于修身、齐家、治国。如果一个国家大兴佛教之善,则国家必定强盛;一个家庭能行佛教之善,则家庭必定兴旺。佛教之善利国利民。忠以治国,孝以齐家,这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援儒入佛”,佛教将忠孝之善也纳入其精神理念之中。
佛教通过僧侣的传道,把其伦理道德观念广泛地传播到民间,对民众产生了其他学说不可替代的独特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佛教劝善惩恶的功能与其报应轮回学说密切相关。它告诉人们,行善必然会得到福报,作恶必然会遭致罪报。行善者来生享福,甚至进入天堂,享受净土的极乐;作恶者来生受罪,甚至堕入地狱,遭受惨酷的折磨。佛教对行善者作了幸福的许诺,引诱人们行善;对作恶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使人畏惧罪报而不敢作恶。尽管它无法在生活中予以证实,但也无法证伪。面向未来,人们有两种选择:要么为善得福,要么作恶受罪,未来的生活完全取决于自己现在的作为。佛教的这种劝善止恶说教,利诱与威胁并用,很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
三、相资互补,儒佛相彰
佛教“援儒入佛”,寻求佛与儒在劝善止恶上的会通,实质是强调佛与儒在伦理道德上是一致的,都有助于教化民众,有助于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和乐。佛与儒毕竟存在许多差异。为了说明这些差异是表层的,而非根本的,佛教学者调和儒佛分歧,提出了儒佛相资理论,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伦理道德虽然总体上一致,但各有其特点,相互补充,二者不可偏废。
不少儒家学者也积极肯定佛教的社会功能,承认儒佛相资互补,华梵相得益彰。元代刘谧就在其《三教平心论》中阐释了儒与佛的一致性。他说:“释氏设教,非与儒教相背驰,故释氏化人,亦与儒者无差等。儒者阐诗书礼义之教,而辅之以刑政威福之权,不过欲天下迁善而远罪耳。然固有赏之而不劝,罚之而不惩,耳提面命,而终不率教者。及闻佛说为善有福,为恶有罪,则莫不舍恶而趋于善,是释者之教,亦何殊于儒者之教哉?”[7]在刘谧看来,儒佛劝善止恶,不仅均有益于社会教化、治理,而且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比儒学更有效。利益往往是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利益驱使人们行善或者作恶。善,所以是应该的,不仅由于它在价值上具有正当性,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符合自己和他人的根本利益。恬不知耻、大胆妄为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知道作恶是不对的。为什么有人明知此理,仍然冒着遭受惩罚的危险去作恶?这是因为利益的驱动。利益越大,人们越是敢于冒险,因为如果能侥幸逃脱惩罚,其作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会远远超过行善的好处。因此,尽管社会教化民众行善止恶,但总有人会不服教化。佛教的善恶报应论摧毁了人们的侥幸心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善必将给自己带来利益,作恶必将遭致相应的罪苦。把善恶因果报应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契合普通民众趋利避害的行为心理,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靠儒家的纲常名教难以做到的。“小人不畏刑狱,而畏地狱。若使天下之人,事无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无侵陵争夺之风,则岂不刑措而为极治之世乎?”[7]可见,劝善止恶,教化民众,仅有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不够的,佛教的伦理道德是儒家纲常名教的重要补充,二者各有其特殊功能,不可或缺。
当然,佛教与儒学教化民众,劝善止恶的功用虽同,但其道德观念毕竟存在一定差异。清僧智旭指出:“儒以忠恕为一贯之传,佛以直心为入道之本。直心者,正念真如也。真如无虚伪相,亦名至诚心。真如生佛体同,亦名深心。真如遍一切事,亦名回向发愿心。此三心者,即一心也。一心泯绝内外谓之忠,一心等一切心谓之恕。故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8]52智旭认为,儒家把推己及人谓之忠恕,而佛教则以无己谓之忠,将平等谓之恕,其实质是对真如本体的彻悟。所谓“真如”(或“如如”),指遍布于宇宙中的真实本体,它是诸法之实性,超越一切差别,不可言说,不可思议。据此本体为心,对待众生能无我、平等,就是至诚之忠,至平之恕。
也正因为佛教与儒学在伦理道德上存在一定差异,它们才能相资互补,相得益彰,也才是不可替代的。佛教把二者的不可替代性,从两个方面作了阐释和强调。
第一,在社会教化方面,儒佛有不同的分工。儒学主要追求治世,佛教着重追求出世,这种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有区别,但又是可以调和圆融的。明僧袜宏认为,“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儒佛二教圣人,其设化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则自应如《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足矣,而过于高深,则纲常伦理不成安立。出世,则自应穷高极深,方成解脱,而于家国天下不无梢疏。盖理势自然,无足怪者。”[8]42儒佛二者的关系,其教化各有侧重。儒家主治世,以天下为己任,更关注现实社会、现实人生,因而现实感极强。佛教主出世,其追求不在现实生活中,要超越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因而其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似乎远远不如儒家。其实,佛教并不是不关心现实人生,只是与儒家关注的方式不同而已。佛教正是出于对充满痛苦的现实人生的强烈关怀,才去追求对人本身的超越。
第二,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学重修身,佛教重治心。宋代僧人智圆,自号“中庸子”,以示其对儒佛的折中。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8]19他认为,佛与儒虽言说不同,但在教化民众上则道理一致。儒学是修身之教,佛教乃治心之教。身心有内外之别,但人之为人,岂能越乎身心之外?二者实则互为表里。
儒家追求治世,重修身,是从现实的人的存在出发,追求的是人的存在的完善。佛教追求出世,重治心,是从超越人的现实存在出发,追求的是人的本质的完善。修身与治心,二者不可或缺。不治身,人为欲望、妄见所累,固执于我,困于无明,根本不可能觉悟人的真实本质。不能把握人的真实本质,停留在修身的层面,则只能强行压制私欲邪见,无法保证它们不重新泛滥。因此,只有儒佛相携,才能使人得以真正完善圆满。正如现代大德印光所说:“尽性学佛,方能尽伦学孔;尽伦学孔,方能尽性学佛。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无不深钻佛经,潜修密证也。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具此伦常心性,而以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尽性,以去其幻妄之烦惑,以复其本具之佛性,非但体一,即用亦非有二也。”[8]218儒学安伦常,佛教治心性。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于特定的道德关系之中,其存在与完善都与所处伦常密切相关,而佛教的伦理道德有助于完善儒家倡导的人际道德关系。完善的伦常与人的本性并不矛盾,它有助于人们把握宇宙和人生的真实,断除一切妄惑,觉悟自己的本性。
佛教与传统儒家思想从对立渐趋会通的过程,正应了宋儒张载所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释老[M].钟伟民,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2]刘咰.旧唐书:第18卷[M].廉湘民,等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86.
[3]任继俞.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2-844.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72.
[5]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81-482.
[6]韩凤鸣.解脱轮:禅宗解脱哲学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444.
[7]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册[G].北京:中华书局,1983:512-513.
[8]李远杰.近现代以佛摄儒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
(编辑:米盛)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忻州师范学院专项课题“五台山佛教伦理思想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5-11-24
作者简介:代训锋(1969-),男,忻州师范学院(山西忻州034000)思政部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2-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