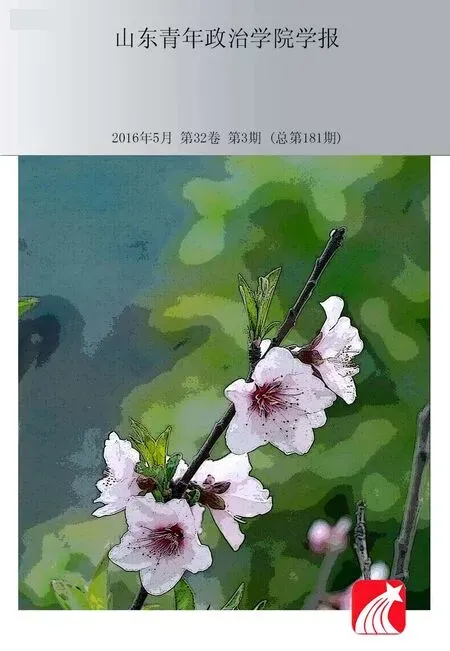论我国农民的法律信仰危机
——以山东某村庄发生的侵权案为实例
韩振文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论我国农民的法律信仰危机
——以山东某村庄发生的侵权案为实例
韩振文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广大农村地区的法治化实践。然而,通过真实案例的分析透视可发现,由于关系网过于强大、权力寻租与不当交换、个别执法司法人员素质偏低、普法宣传未达到应有效果、“权大于法”观念强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过低等多种因素的阻碍,使得农民对法律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仰危机。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采取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建立普法长效机制;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升司法执法能力;依法治官,农村基层干部自觉树立遵纪守法理念等措施,可作为消除农民法律信仰危机的可行对策。
关键词:农民; 法律信仰危机;司法为民;法律权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依法治国的理念更是逐步深入人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与近来司法改革浪潮的双向推动下,国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得到很大提升,不仅懂法守法而且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可否认,目前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仍改变不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现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就笔者的切身体会而言,农民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对法律的真诚信仰,甚至对法律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仰危机。法律人常提到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的一句格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学术界一般认为法律信仰指的是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法的神圣性的意识和观念,对法的宗教情怀和信仰,是全部法治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保障;甚至可以说,公众的法律情感和法的神圣性的观念,是法本身之存在及其具有效力的“合法性”根据。[2]而法律信仰危机则指一个社会缺少法律的信念、理想和精神,公民失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信任,对法律表现出冷漠、厌恶、规避和拒斥,从而使法律规定不能实现,不能由纸上文化产品而内化成社会公众的内在精神。[3]这又突出表现在法律在公众中缺乏足够的权威,许多公民不信任、不尊重、不服从法律,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当自己合法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其他包括非法行为在内的解决办法; 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能严格依法办事,执法犯法、徇私枉法;社会上缺乏将法律视为一切行为之根本准则的环境和氛围,等等。[4]那么,具体到农民对法律产生了何种信仰危机?发生的原因为何?又如何消除呢?本文从一起农村发生的真实案例入手,试图分析农民对法律信仰危机的以上问题,以期为我国社会转型期法治中国建设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根基。
二、从案件中透视农民对法律信仰的认知
2013年底在山东省滨州市的县级所属的一村庄,发生了一起人身损害的民事赔偿案。老赵是此案的原告,与被告的丈夫是亲兄弟。两家因为相邻关系问题发生纠纷,被告打伤了原告的鼻子并扬言不支付任何赔偿,为此老赵一纸诉状将弟弟的妻子告上了法庭。他希望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为自己讨回公道,然而没想到救济之路上遇到重重困阻。
首先是开庭到判决的过程。2014年1月份老赵向山东省滨州市某基层法院起诉并于当天立案,5月份法官告知老赵开庭,7月底才下发判决书判决被告赔偿老赵20072元,在这期间老赵多次询问何时才能发判决书。法官通过律师告知,如果原告拿出800元钱,判决书可以很快拿到。无奈之下,老赵通过律师给予法官此数额金钱。
其次是申请强制执行阶段。老赵如愿拿到判决书,上诉期满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而被告在规定履行期满后也没有履行,因此老赵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时却被告知要求他在一两个月之后再申请,老赵百思不得其解:判决书上明明写明履行期满不履行,原告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何要等一两个月后呢?最后在律师的帮助下,法官终于出具了法律生效证明书,使得执行申请得以立案。
最后是强制执行阶段。2014年8月25日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老赵积极向法院提供被告的财产线索,直到2014年11月份在老赵的不断催促下,执行法官才告知原告刚轮到此案的执行,之后却没有进行财产调查,只在2014年年底对被告拘留15天。因为拘留一事执行法官极尽拖沓始终不执行,老赵遂与执行法官闹僵,执行法官退回老赵先前给他的800元钱,从此对此案不再做任何执行行为。直到2015年4月份,被告伐树卖树,老赵打了多次电话告知执行法官此事,执行法官答复不能执行卖树的价款。结果被告将卖树所得4万多元借此机会成功转让于第三方。
总的来看,从开庭到执行,老赵经历了十分艰辛的过程。在老赵准备起诉的时候,村子里就有很多人对他讲起诉没有用的,没有关系根本赢不了,现在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即使赢了也拿不到钱。但是老赵不相信,坚持古人常说的“有理走遍天下”,现在是法治文明社会了,法律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他要用行动证明法律是公平公正的。然而,这一路走来他遇到的种种困难却让他心灰意冷,开始不信任法律了,开始觉得原来法律的实施还是抵不过人情、关系与钱势。从案件发生起,笔者基本参与了整个过程,对老赵的经历深表同情,同时也感到遗憾。这件事情对在高校法学院任教的笔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震撼与打击。窥一斑可见全貌。它不仅使得老赵丧失了对法律的信赖,连笔者在经历之后也对我国广大农村法治建设现状产生了担忧。那么在此进一步要追问的是,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产生危机的原因在哪里呢?
三、农民存在法律信仰危机的缘由
从以上这则侵权案例分析发现,老赵有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但是由于现实的无奈困阻,让老赵对通过此途径来保护权益发生了强烈怀疑,基于朴素正义对法律的信任也产生了动摇,因而法律的权威与公信力也受到了挑战。笔者通过观察与反思,认为农民产生法律信仰危机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关系网过于强大。县城、农村主要还是熟人社会,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到处是自己的熟人,一切都纠缠于关系网络之中。行政与司法工作人员更像是“一家人”在办公,尤其对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律师来说,他们不愿也不敢得罪这些官方司法行政人员,因为他们还要在这里谋生并扩大案源。比如老赵因担心派出所改口供,曾在笔者的建议下要求代理律师去派出所调阅卷宗,但律师没有答应,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敢得罪这些人。而对于被告来说,其背后是金钱与行政关系的力量。从案件发生到执行,期间,被告通过强大的关系网进行运作,使派出所与法院执行人员通过某种方式达成了“共识”:派出所不及时对被告作出应有的治安处罚,并私自修改了案件笔录,而法院执法人员则拖延开庭、拖延下发判决书,并在执行过程中百般拖延不采取执行措施,对应予以强制执行的财产不予执行。而被告关系网强大的背后则是权力的寻租与利益的交换。
第二,权力寻租与不当交换。案件发生地是一个从现任村委书记上台开始就一直被评为文明村的村庄,零诉讼案件的发生率是作为基层人大代表的村委书记的骄傲,也是他当选人大代表的一个重要竞争指标。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生却打破了村里“和为贵”与书记心中所持的治理权衡之道。他曾多次阻止劝导老赵不要起诉,却又没有给老赵一个公道说法与合理解决方式。他认为老赵的“疯狂”行为损害了他潜在的政绩利益,而被告的哥哥与他同是村委会成员,为此他决定帮助被告为他协调了多方关系,并动用村委的钱物请客送礼,如此以权谋私、以案谋利。而老赵作为弱势群体的一方,如何能在这场官司之战中获胜呢?农民在亲身体验中又如何感受到法之公正呢?
第三,个别执法司法人员的职业素质偏低。据笔者走访了解,乡镇派出所的民警大部分都是从民间招聘的协警员或者是退伍军人,受过专业警察教育的人寥寥无几。他们获取的法律知识大多依赖经验或老警察的言传身教。一般情况下在处理案件时虽无大的差错,但若接受了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财物、宴请或者其他利益的,则不管案件当事人是否有过错而自动偏袒于一方。而基层法院的法官大多也是以前部队转业人员,虽然现在要求法院的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但是在贯彻实施起来总不如预期来得好。受理老赵这个案件的法院法官特别是执行庭的法官对法律认知应用更是很不专业,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有的执行法官以前甚至是在法院开车的,过了几年后调任执行庭做起了执行法官。派出所的部分民警与执行法官“衙门”作风较重,在处理案件之时大都会采用恐吓吓唬的方法,以为老百姓不懂法而诈唬,直到对方“识时务”送礼了,态度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老赵就曾经一度被办案民警与执行法官吼叫过,他表示很受委屈。他试图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执法人员却用自认为很懂的法律去反驳教育他,为此老赵一度害怕再跟他们打交道。司法廉洁与司法为民本应是司法工作者的职业本色,体现其浩然正气,而透过本案看实然的层面却并不乐观。
第四,农民对法律了解较少,普法宣传并未达到应有的效果。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习得培育过程。虽然我国正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5]为此政府曾多次组织普及法治教育(2015年是“六五”普法验收之年)及设立“12.4”国家宪法日,但却过于运动化、形式化,因而未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笔者在法院实习期间也曾跟随法官“送法下乡”进行多次普法宣传,但作为弱势群体农民们的法律意识仍比较淡薄,对法律的认识、精神的理解少之又少,他们中更多的是只知道大概内容及部门法名称,却不知道其中细节及规则关联。因此经常会因为自身不了解法律而作出对己不利的行为或没有及时保存应有的证据,更有甚者相信民警与法官们不合法不合理的说辞。也因如此,他们不知如何采取正确途径与正当程序来捍卫权利,而经常选择涉法上访、“找关系”或“私了”等方法来维护权益。
第五,“权大于法”观念的强化。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思想在国民中根深蒂固,这在农民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作为受害人的农民在心中难舍“青天”观念,对于问题的解决总是寄希望于“青天”主持公道,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维权,而是更喜欢用上访的方式表达诉求,从而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6]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崇尚法律、保障人权的精神基因。农民们认为只有将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诉诸政府部门,并相信明察秋毫的官员能很好地帮他们解决问题,而老赵的案例就证实了这一说法。就老赵的案件来说,老赵在派出所不给及时处理,法院应执行而不予执行时,他选择了去公安局信访办与法院信访办信访,他还想过去找市长信访,认为如果要让市长知道此案,这样就能很好解决了。为此采取此救济方式后,案件果真发生了转机:派出所迅速处罚了被告,基层法院将案件的执行由派出法庭提到了执行局来执行。这给了老赵巨大信心,老赵甚至打算,如果法院还不给及时执行,他就准备去市中院信访。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2条等相关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执行案件(包括受委托执行的案件)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执行结案的,应当作出裁定、决定、通知而不制作的,或应当依法实施具体执行行为而不实施的,应当督促下级法院限期执行,及时作出有关裁定等法律文书,或采取相应措施。对下级法院长期未能执结的案件,确有必要的,上级法院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与下级法院共同执行,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法院执行。那么老赵为何不走向上级法院申请执行途径而坚持选择上访呢?这是因为上访能够引起某些“青天官员”的重视而采取领导批示使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而且要比通过法律途径迅速快捷。由此可以看出,农民们更多的是“信权不信法”、“权大于法”,而政府官员的处事作风更是助长了这一观念的深入,这样必然进一步损害农民对法律的信仰。
第六,法院等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过低。当事人选择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权利,主要是因为相信法律适用最终能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答复,而这种答复来得越快他们对法律的信仰度就会越高。然而,现实中法院的做法却让当事人失望甚至绝望了。前面提到过,老赵于2014年1月份起诉,法院5月份开庭,7月底发放判决书,8月份申请强制执行,11月份被告知案件开始执行。此案从受理到执行的两年期间内,本有很多次可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的机会,但却因法院不作为而错过,而法院对自身怠于行使职权的行为却没有丝毫愧疚与焦虑,执行难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长期难以破解的问题。对于执行难的原因一般认为主要是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所致,殊不知法院的职权配置不科学不便民导致办案效率低下也是重要原因。因而当前司法改革强调,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据笔者调研所了解,并不是法院没有时间处理案件而是由于职权配置不合理形成了一个习以为常的惯例:每天下午一般不安排工作,每周五基本没有新的工作事项。这就导致案件积压越来越多,诉讼过程则变得冗长,本可避免的“案多人少”压力超过法官裁判思维的流畅度,引发办案人员更大的怨愤蛮横态度。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农民们没心情与自信走进法院寻求救济,司法的权威也会逐渐式微。
老赵的案子虽是个案,但这其中反映的问题却可能是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恰恰因为以上这些缘由的存在,使农民们对法律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危机。农民们遇到纠纷不采取正常法律途径化解,即使选择法律途径也会持有尽量托关系送礼的心态。本来“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做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是司法人员的本职工作,现在却成了农民们祈求着才去做的事情。弱者权利的司法保护体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取向,而现实救助的困窘使农民逐渐丧失对法律正义的热情期待。当法律成了索取私利的工具,又何谈农民对法律的信仰。
四、消除农民法律信仰危机的举措
农民对法律的真诚信仰,会为我国社会转型期司法权威的树立提供广泛的社会根基。探求农民法律信仰危机的消除之道,一来并非易事,二来也许过于宏大,但若回顾以上农民侵权案,就可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当然笔者提出的以下对策建议,仅提供一些可行的参考,至于顶层的制度设计仍需从国家建构视角来渐进改革。
首先,继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建立普法长效机制。“普法中国”首先应做好“普法农村”,这是普法宣传的重点。在普法教育的过程中要有针对性、长效性,定期组织送法下乡的活动,多普及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用法律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及参与法治建设的主动性,懂得权益被侵害时的有效救济方式。与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是“国法”(国家制定的法),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等法律文本,这样为每个家庭提供一本常用法律手册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加强农村文化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纷纷开展新农村建设,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文化生活需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建设农村文化阵地,建成了风格各异的农村文化广场。完全可以因势利导,在广场上利用宣传栏、电子滚动屏等工具,加大法律常识、法律原理的普及力度。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丰富了农民文化生活,而且作为一种普法媒介,更具长效性、生动性。此外,由于农民接受的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低,确实存在一些蛮不讲理而漠视法律规则之人,在损害他人利益后却不积极采取补偿措施。在普法过程中强调精神文化素养与法律的道德基础,更易于他们明事理学法律,并从内心深处接受、尊重法律,从而在出现纠纷后也就容易得到化解。
其次,加强司法执法队伍建设,提升司法执法能力。很多农民是在观察或体验法的适用活动中感受到法的公正价值的,而这种感知又直接影响到他们法意识的形成。司法执法人员职业能力的提升,能够拓宽农村法律服务渠道,营造良好的法的运行环境,为农民现代法意识的生成提供观念养料。乡村的司法队伍建设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具体到它如何满足农民基本法律服务需求的问题,那就要充分发挥乡镇司法所及派出法庭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等方面的职能优势,使农民们能够便捷地行使诉讼权利,减轻农民群众的讼累,共建共享法治文明成果,享受到法律阳光的同等关爱。特别是派出法庭直接面向农村,作为农村平安建设的“前哨站”,担负着大量农民纠纷案件的审理任务,就须不断完善有关便民、利民的具体措施,以此提升司法适用的能力,不仅要为农民提供实用的查询、投诉、诉讼导引、风险告知等服务,而且要进行诉讼风险提示,引导农民形成合理的诉讼预期。
最后,要依法治官,农村基层干部自觉树立遵纪守法理念。在农村直接跟农民接触的是农村党员干部(主要是村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书记,村民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主任),他们主要肩负着组织与领导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在解决具体民事纠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他们采取民事纠纷的民间调解方式具有乡土性与亲和力,在调解方式、调解结果上都易于为人们所接受、遵守以及履行。[7]因而他们能否依法办事、带头守法直接关涉到农民对法律功能的认识与评价。有特权阶级思想的农村干部从事违法乱纪行为,不仅会破坏农村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必然会对农民的法律感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对农村干部队伍的法制宣传与法律技能培养必不可少。这就一方面要对农村干部进行选拔培训,提高其法律素养,带动全民守法;另一方面科学化、规范化农村干部的小微权力,建立顺畅的民意表达机制,重点是加大村民对其依法行政活动的监督力度,在考核时不仅要看工作业绩也要认真倾听农民意见,从而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总之,现代法治真正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8]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它的生命却在于具体实施。司法执法人员与农村的基层干部则是实施法律、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公仆,他们依法办事的良好形象能使农民们切实体会到法律的公正,农民才会对法律产生感情与依赖,内化为自身的生活方式,法律的权威才能得到树立。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J·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M]. 北京:梁治平,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2]姚建宗. 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2):6.
[3]黄春.中国农村法律信仰危机的表现、成因与解决途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5):63.
[4]段睿.法律信仰危机探析[J].山东审判,2004,(5):82.
[5]李哲. 传承与升华:法治中国建设探析[J]. 兰州学刊,2015,(2):134.
[6]李先波,杨志仁. 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和出路[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1) :13.
[7]李哲. 当前我国农村民事纠纷的特点及其解决对策[J]. 兰州学刊,2010,(4):101.
[8]姚建宗. 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2):12.
(责任编辑:杜婕)
On the Legal Belief Crisis of Farmers in China
HAN Zhen-wen
(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49, China )
Abstract: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hich cannot do without law practice in rural areas. Howe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al case, we can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is too powerful, along with the power of rent-seeking and improper exchange, the low quality of the individual law enforcement, the popularization propaganda of law failing to achieve the satisfactory effect,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concept "Power Overshadowing Law" , as well as the poor work efficiency of the judicial organs and other barriers , which produce inimical emotion to law for the farmers, even the belief crisis of law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law belief is a complicated system. Taking the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popularization propaganda of law,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the popularization propaganda of law; together with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personnel, promoting the judicial enforcement ability, as well as managing the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law can be used as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to eliminate law belief crisis for farmers.
Key words:Farmers; Crisis of Law Belief; Justice for the People; Authority of Law
收稿日期:2016-02-08
作者简介:韩振文(1987-),男,山东滨州人,法学博士,讲师、浙江大学法学博士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法律方法、司法的认知科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3-0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