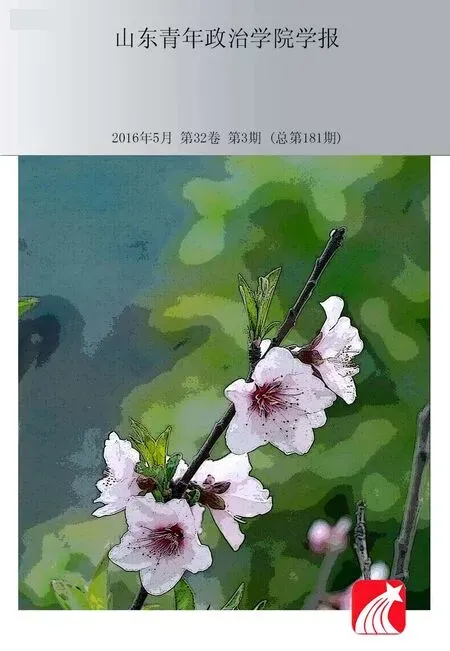论郭沫若建国后“官员型学者”的身份特质
逯 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济南 250103)
论郭沫若建国后“官员型学者”的身份特质
逯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济南 250103)
摘要:建国后,郭沫若作为新中国人文学界的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他不仅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来及时关注国内文艺的动态,而且还积极宣传文学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正能量,要有效地发挥这种正面力量来抵御世界范围内的反动力量。尽管学界已经对建国后郭沫若这种具有官职的学者身份有过研究,但对这种身份特质尚未明确界定,因此文章尝试从“公共人物”这一视角,用“官员型学者”这一身份特质对建国后郭沫若的“职务写作”进行研究,而这种身份特质鉴定也将为同时期同类作家的研究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郭沫若;建国后;官员型学者;职务写作;公共人物
建国后,郭沫若作为新中国人文学界的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都有体现也都被肯定过。比如秦川在《郭沫若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9月版)中认为:“郭沫若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和学者,还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郭沫若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大体上与中国革命同步。”[1]卜庆华在编著的《郭沫若研究新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中认为:“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建国后的郭沫若与解放前的郭沫若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作为一名文化人,他深深懂得文化乃民族之根……郭沫若都是民族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他在努力探索,企图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2]黄淳浩在论著《郭沫若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3月版)中认为:“综观一生,可以看出,郭沫若既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又是一个学者和科学家,还是一个战士和革命家。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文化巨人。”[3]也就是说,建国后郭沫若不仅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及时关注国内文艺的动态,而且还积极宣传文学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正能量,要有效地发挥这种正面力量来抵御世界范围内的反动力量。不管是在文化圈还是学术界,建国后的郭沫若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官员型学者”气质。
一、何为“官员型学者”?
所谓“学者”,是指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受过相当程度的文化教育,从事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的工作;学有专攻并且富有实际成效;具有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求真精神和以理念世界批判现实世界的社会使命感。[4]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许多人身兼作家与学者两种身份。这种特殊的、双重的身份给文学写作带来丰富性和思想深度的同时,也因为理性介入和思想阐发过多而对文学写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5]之所以用“官员型学者”来界定郭沫若,是因为建国后的郭沫若不仅是简单层面的“学者”,他在具有“学者”气质的同时,还因为显要的人文学界官职,散发出一种官员型的风范,这种风范又和郭沫若作为“学者”所具有的文化气质不无关联,所以这就合力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官员型学者”气质。
建国后,郭沫若作为中国人文学界的领导人,在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事业中充当着文化引领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就决定了郭沫若建国后的职务写作不仅潜藏着意义丰富的社会功利性,而且在以“公共人物”身份干预社会时,对中国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郭沫若此时期看似驳杂无序的人文性质的作品文本,不仅有规律可寻,更不缺乏文化层面的丰富意义。对这些意义进行深挖,不但可以显露郭沫若作为中国知名学者的文化气质和世界眼光,同时更能对丰富郭沫若建国后的文化形象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要对这些意义进行展示,必须首先对郭沫若建国后这种独特的“官员型学者”气质进行综合考察,只有把握了这一气质的诸种表现,才能顺理成章地挖掘更为深层的复杂用意。
“人具有各种意向和天资,而每个人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一切天资。尤其是人有向往社会的意向。这一意向使人能从社会中得到新的、特别的教养,这种教养又以为社会服务的最终指向。”[6]也就是说,“学者”不仅仅代表一种职业身份,这种身份的本质是通过知识与文化的互动方式,在学术领域进行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的工作。同时通过这一工作,对关注社会、服务社会、引导社会和造福社会的理念加以践行和运用。[7]一言以蔽之,即“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并为社会而存在。”[8]既然“学者”担负着服务社会的使命,那么,如何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就应该是“学者”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具体到郭沫若身上,他不仅是“学者”,还因为他是人文学界的领导人,他的学者气质又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所以他的这种学者气质应该用“官员型学者”来界定。作为一名“官员型学者”,郭沫若又该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为社会服务的使命呢?
1956年10月1日《文汇报》刊登了郭沫若就墨西哥文学杂志社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提问,有下面这段陈述:
文学是社会现象经过创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过程的反映;反过来,社会要受到文学的创造性的影响而被塑造。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把素材转化为规范是作家的创造性活动。
……
文学和作家可以起很深刻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作用是用形象化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它的影响十分深刻,足以促进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产生。……这种形象化的教育方式往往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
作家对于人类生活应该有他的批判,从而加以分析、提炼、综合而转入创造过程。具有正确的批判性和高度的创造性,然后才具有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而发挥出高度的社会效果。[9]
以上文字传递出的信息有这么几个层次:第一,郭沫若将“文学与社会”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对象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牵强的,请特别注意第一段第一句话中的“创造”。也就是说,郭沫若认为“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被动性的,而是“创造性”的,这就突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第二,“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创造性”关联,必须借助“作家”这一媒介。第三,对“作家”代表的“学者”的强调,其目的是为了引出作家的“创造性”,也就是用“形象化的方式”发挥“教育”作用。第四,作家的“形象化的方式”要借助“文学作品”来表现。第五,“作家”要发挥“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必须“对于人类生活应该有他的批判,从而加以分析、提炼、综合而转入创造过程。”[10]这种“批判性”和“创造性”才是干预社会的前提。换句话说,学者只有自己首先掌握并精通知识才能将其传授给社会民众,才能在社会范围内激活知识作用社会的效能,即“传授技能总是学者所必需具备的,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11]但是,作为学者,“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12]郭沫若同时还身为“公共人物”,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对社会公共道德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引导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力也随之变得巨大。[13]郭沫若这个“官员型学者”又该如何发挥“球形天才”的才能来实现“为社会”的目标?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教育作用”和影响力呢?如果能回答这么问题,那么郭沫若“官员型学者”的气质和风范也就随之被展示出来。
二、用“文学”为世界和平维权
作家和艺术家是脑力劳动者,不管他们的思想立场如何,流派和成就怎样,他们总有一个相互接近的理想,那便是想美化社会并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
凡是认真努力于文学和艺术的写作的人,在这种理想的扩大、深入和具体化上,便有了共同的语言。因而,他们也就必然成为统一战线的战友,凡是反对这种理想,既反对美化社会或损害人类幸福,那样的人和事便不能不成为作家和艺术家的敌对存在。
……
作家和艺术家通过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经验,可以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可以使和平的敌人失去造谣捏诬、挑拨离间的机会,可以使和平得到保障、文学和艺术得到共同的繁荣。[14]
之所以开篇首先引用这段文字,是因为这段话中传递出的信息对下文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承启作用。这段文字出自1957年4月13日《文汇报》“答捷克斯洛伐克文化艺术周刊《文化1957》问”一文。文中传达出这么几个层次的用意:
其一,“作家和艺术家是脑力劳动者,不管他们的思想立场如何,流派和成就怎样,他们总有一个相互接近的理想,那便是想美化社会并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这句话的意思是,“相互接近的理想”是各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共通点,而这一共性又指向“美化社会并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那么,反过来理解就是,但凡以“美化社会并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为“理想”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可以因为这一共性达成一致,联合并团结起来,而这种观点也正是1952年5月4日, 郭沫若在《为了和平民主与进步的事业——纪念雨果、达·芬奇、果戈理和阿维森纳》一文所要传达的意思:
在纪念雨果、达·芬奇、果戈理、阿维森纳时,我们看到一方面他们各各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造就;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着某些共同的东西。……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对人类的合理前途的希望和信心,当我们展开人类文化进步史时,在一切文化先驱者的身上所表现着的最使人感动的共同点,难道不正是这些么? ……文化交流的促进而必然加强的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保证着人类的前途有无限的光明。[15]
类似的意思继续出现在1953年9月27日的《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一文中。文章是郭沫若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五个团体为纪念屈原、尼古劳斯·哥白尼、弗郎索瓦·拉伯雷和何塞·马蒂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举行的大会上的发言:
这四位伟大的人类文化的贡献者和拥护者,虽然各自出生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他们却共同为着人类的正义和进步奋斗了一生……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斗争,是和当时当地的人民的利益相联系的,从他们一生的特定的历史意义来考察,也是和世界人民当前的利益相联系的。……以同样的追求真理、服务人民和牺牲自我的精神,为实现全人类的人民友谊、自由生活与持久和平而斗争。[16]
带着这种理解来看《报告》这首诗,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拉丁美洲的今天,就是咱们中国的昨天。咱们中国的今天,就是拉丁美洲的明天。”[17]这种具有共通性质的诗句了。
其二,既然“凡是认真努力于文学和艺术的写作的人,在这种理想的扩大、深入和具体化上,便有了共同的语言。因而,他们也就必然成为统一战线的战友。”那么也就是说,“凡是反对这种理想,既反对美化社会或损害人类幸福,那样的人和事便不能不成为作家和艺术家的敌对存在。”这里所要传递的意思是,要看到因为“相近的理想”而结成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必须对反对这种理想的“敌对”力量时刻防范和抵抗。这种防范意识早在1952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季洛姆的入狱》一文中有所展现。文章指出季洛姆的罪行是“在疯狂的战争叫嚣当中,反对了战争,为和平与进步作了由衷的呼吁。”[18]对于这一“罪状”,郭沫若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关于季洛姆先生的入狱,想说几句话。但我的话并不准备以美国政府和它的后台老板美国百万富翁们为对象,希望他们会自动放弃罪行。不,不是的。我的话是准备以全世界理智清明、心境善良的人们为对象,希望他们通过了季洛姆的遭遇,重新认识一遍美国政府和它们后台老板们的真相。”[19]这也正如郭沫若在《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一文中强调的: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今天,和平的敌人到处挑拨战争,破坏和平运动,而且无耻地阻挠各民族的自由发展和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它们仇恨人类的进步和自由,迫害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良心,践踏和毁灭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正遭受着战争挑拨者的严重的挑战。[20]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郭沫若此时期的很多人文性质的诗作中会出现“对立性”的表述了。以《题赠日本文化代表团》为代表:
劳心劳力同劳动,
不许寄生再有虫。
创造自由天地出,
万人携手舞东风。[21]
其三,在理解以上两个意思之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也即最后一层意思。“作家和艺术家通过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经验,可以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可以使和平的敌人失去造谣捏诬、挑拨离间的机会,可以使和平得到保障、文学和艺术得到共同的繁荣。”也就是说,要实现维护世界和平和抵御敌对势力侵犯的双重目的,加强作家和艺术家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用文学和艺术的武器来共同抵制敌对力量,这才是郭沫若整个表述最核心的意思。这种和平文化力量的集结,具体到建国之初的特定国情,就是开展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大团结,而这也正是1957年11月3日《向苏联文艺看齐》一文的主旨。该文系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答《文艺报》记者问。因为“如果中苏两国之间的文学艺术的交流能够成为宏流对宏流,那我们对世界文化的共同贡献必然会进一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22]为此,“请让我们拿出一切潜在的力量,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端正我们自己的立场,贯彻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出来,向苏联的文艺工作者们看齐。”[23]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郭沫若在1958年8月27日,就苏联《现代东方》杂志关于“文学在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中应该占什么地位”的提问,会写《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来回答: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和批判。它必须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 ……既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那么作家就必须以人民的爱憎,以人民的感情为感情,表达人民的愿望。……这样才可以使作品具有丰富的、崇高的教育意义,因而可以教育人民,教育人类。
各国人民的爱憎大体上是相同的。凡是深刻地体验了本民族的人民感情的文学,它就具有共同性、国际性,同时也能深刻地感动别的民族的人民。通过这样的作品,就能使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相互尊重,达到和平共处,共同进步的目标。[24]
透过这段话,我们能看到郭沫若强调“学者”服务和“教育人民”的意义具有十分明显的开阔视野。诗歌《亚非作家会议在东京开会》,用文学的形式对这种观念进行了诗体表述:
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到处劫抢,
我们要保卫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平、唱出人民的愿望。
……
我们高举起火炬,把受压迫者的心房照亮;
我们横扫着铁帚,把殖民主义的魔影扫光。
要用我们的笔,我们的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脏,
使友谊的鲜花到处开放,使和平的白鸽普天翱翔![25]
对以上三重意义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再看作为“官员型学者”的郭沫若,为了实现国际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做过哪些努力。他认为:“我努力追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实践来为人民服务。我也努力向别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学习,尽可能接近他们的作品并加以翻译和介绍。我努力遵守我国的和平政策,尽量争取世界各国的文化工作者来访问我国。凡有出国的机会,我便尽力寻求国际朋友。数年来,我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26]这种是以全世界各国人民为服务教育对象的开阔眼界,正展示出郭沫若作为建国后人文学界领导人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
三、借“榜样”的力量实施全民教化
德国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中围绕“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不相信别人的诚实和才能,社会就不能存在,因而这种信任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里;单凭自然界赐予的特别恩惠,我们具有的信任永远不会到达我们最迫切需要别人的诚实和才能时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当学者获得他应有的信任时,他才能指望这种对其诚实和才能的信任。”[27]其实这里所说的“信任”和“公共人物”具备的社会影响力具有相同的指向:学者应有的信任是针对社会公众而言的概念,而作为“公共人物”本身具备的社会影响力其实正是作为“公共人物”的个体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后作用于社会的表现。正如前文所述,建国后的郭沫若借助他在人文学界的写作,透过为人类和平和人民利益为内容的“理想”的强调,在世界文学艺术界传递他对全世界进步作家和文艺家“诚实和才能”的迫切需要,以实现正义力量的广泛团结,达到文学为世界和平维权的目的。如果说上文是从国际角度对郭沫若的“官员型学者”风范进行展现的,那么具体到中国国内社会又有何种表现呢?在展开这一维度的意义探寻前,我们先来看下面一首诗:
鲁迅先生,你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我差不多随时随地都看见了你,看见你在笑。
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幻想,
而是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实感。
我仿佛听见你在说:“我们应该笑了,
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应该用全生命来
保障着我们的笑,笑到大同世界的出现。[28]
以上诗作题为《鲁迅笑了》,作于1949年10月19日鲁迅纪念大会之后。郭沫若在这次会议任执行主席,曾有这样的致词:“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学习鲁迅的精神,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建设好。”[29]之所以首先分析这首诗,是因为其中包含着这么几层具有承上启下性质的意义指向。
第一,联系这首诗作的写作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毛泽东”,这也就能明显地表现出郭沫若作为建国后人文学界的领导人,同时又是中国官方文化言论发言人的身份。而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政界领导高层对鲁迅有过最具权威的界定:“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0]由此,作为“公共人物”的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指向自然不可能脱离这一最高评价。从这一层面上说,郭沫若借助中国政治领袖“毛泽东”的社会威慑力和权威性,势必会在文化界强化“鲁迅”的重要性。借此也能发现,郭沫若正是深谙鲁迅所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巧妙地借用这一榜样力量,可以对国内人文学界进行有效的引导,实现进一步实施全民性质的教化目的。
第二,诗中提到“人民大众”,其实这正和前文提到,以“为社会”为最终目的的学者使命相衔接,这就不难理解郭沫若为何会在1950年10月19日举行的鲁迅 逝世十四周年纪念会上,作为全国文联主席会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的爱憎分明,强烈地爱祖国、爱人民,也强烈地仇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精神。”[31]这一致词在隔年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被重提:“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去反对帝国主义,并肃清我们内部的买办思想、封建思想的残余;也要学习他对人民、对革命、对祖国的热爱,献身于祖国的建设,使我们的祖国成为像苏联一样强大的世界和平堡垒。”[32]致词中所提及的“祖国”和“人民”,都是需要被“热爱”、被“献身”的对象,这正是国内所有文艺工作者要着力学习的。
第三,诗中的“我们的笑”和“大同世界”,作为奋斗目标的不同表现形式,正是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实现的,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共同“理想”呢?郭沫若在诗中给出了答案,即“用生命来保障”。这就不难理解第二个层次中提到的“战斗”和“献身”精神。这在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郭沫若作的题为《体现自我牺牲的精神》文章中有集中体现。文章指出今天纪念鲁迅就是“要以鲁迅为榜样,以自我牺牲精神创造性地从事一切活动。我们要继承祖国的优良遗传,同时也要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人民幸福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为人类进步服务。”[33]作为“革命的新文艺的创始人和奠基人”[34],鲁迅这种牺牲精神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郭沫若借助鲁迅杂文《坟》的一句话:“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勉励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们“要用经过洗炼的人民语言来从事写作,要写出杰出的小说、诗歌、剧本、杂文,自然也还是要费献身的努力。”[35]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在创造过程中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要“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创造性地从事写作,从事研究,从事教育,从事哺育新生代”。[36]
到这一层,可以说郭沫若之所以要在建国后,在国内掀起学习“鲁迅”热潮,有心要做的不仅仅是对鲁迅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的官方表彰和强调,并有借助这一契机来调动国内广大文艺者的主观能动性的意图。因为只有发挥“学者”的文学“创造性”,才能有效地实现全民教化。正如在郭沫若文章《孺子牛的变质》中说的:“齐景公之为孺子牛是很陈腐的典故,袁枚、钱季重辈之使用这个典故也是很陈腐的用法。但这一典故,一落到鲁迅的手里,却完全变了质。在这里,真正是腐朽出神奇了。”[37]这里的“腐朽出神奇”正是鲁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典故“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所以在之后的文章中,郭沫若不仅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在宏观上学习鲁迅的“自我牺牲”精神,同时更要从微观上切实学到点子上。这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郭沫若会在后期的作品中细化学习鲁迅的方法。比如为鲁迅纪念馆题词时,他这样写:“革命热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应该说就是鲁迅的作风。他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而却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38]到了1961年9月25日鲁迅八十诞辰纪念大会上,郭沫若又有这样的开幕词:“我们首先要学习鲁迅的精神。学习他的明辨大是大非,坚忍不拔;学习他的实事求是,发奋忘我,学习他不在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面前低头,而是冷静地对付它们,克服它们;学习他为正义事业不断鞭策自己,并有决心牺牲自己。”[39]相比之前文章中“爱祖国”、“爱人民”、“献身”等广义上的表述,这里的“实事求是”、“明辨是非”、‘“坚忍不拔”、“发奋忘我”等都显得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
至此,顺着这三个层次的意义指向,我们才能发现,郭沫若作为“公共人物”,在履行作为建国后人文学界领导人的职责时,借助这一要职和话语权,所要真正传递的深意正是第三个层次,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层次被政治性的表象遮掩得过于严实,所以很容易被忽略掉。对以上三个层面的意义指向有所理解以后,再来看1961年9月18郭沫若为《鲁迅诗稿》作的序言时,就不难理解他要说“鲁迅先生,人之所好也,请更好其诗,好其书,而日益近之。”[40]的良苦用心和深层用意了。
综上所述,透过“公共人物”这一视角,对郭沫若建国后人文主题的作品文本进行深入研究,不难看出郭沫若具有的独特气质和“官员型学者”风范,同时他建国后看似庞杂无序的职务写作不仅有章可循,而且还能彰显他的“球形天才”,更为揭示郭沫若建国后的复杂性特质提供了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秦川.郭沫若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410.
[2]曾加荣.从尊个性到重群体看郭沫若的文化选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6).
[3]黄淳浩.郭沫若自叙[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5.
[4]喻大翔.知识分子·学者·学者散文[J].当代文坛,1999,(6).
[5]夏一雪.学者写作:打通文学与学术——新时期学者写作研究述评[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4).
[6][8][11][12][27][德]费希特,著.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7,42,42,44,43.
[7]夏一雪.“文”“学”会通——现代学者型女作家研究[D].山东大学,2010.
[9][10]郭沫若.文学与社会[N].文汇报,1956-10-01.
[13]洪波,李秩.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类型及其名誉权的限制——以媒体侵害公众人物名誉权为中心[J].当代法学,2006,(7).
[14][26][33][34][35][3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52,133,102,98,99,100.
[15]郭沫若.为了和平民主与进步的事业——纪念雨果、达·芬奇、果戈理和阿维森纳[N].人民日报,1952-05-05.
[16][20]郭沫若.争取世界和平的胜利与人民文化的繁荣[N].人民日报,1953-09-28.
[17]郭沫若.新华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72.
[18][19]郭沫若.关于季洛姆的入狱[N].人民日报,1952-06-16.
[21]郭沫若.题赠日本文化代表团[N].光明日报,1949-10-28.
[22][23]郭沫若.向苏联文艺看齐[N].文艺报,1957-11-03.
[24]郭沫若.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J].文艺报,1954,(17).
[25]郭沫若.亚非作家会议在东京开会[N].人民日报,1961-03-28.
[28]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
[29]郭沫若.学习先生伟大精神 首都庄严纪念鲁迅[N].人民日报,1949-10-20.
[30]郭沫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N].人民日报,1966-11-01.
[31]郭沫若.首都文化界昨集会纪念鲁迅[N].人民日报,1950-10-20.
[32]郭沫若.首都各界人士千余人举行大会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 华北局等机关及上海等地亦集会纪念[N].人民日报,1951-10-20.
[37]郭沫若.孺子牛的变质[N].人民日报,1962-01-16.
[38]周国伟.中国已新生,方向更光明[A].纪念与研究[M].上海:上海鲁迅纪念馆,1979.
[39]郭沫若.继续发扬鲁迅的精神和本领[N].光明日报,1961-09-26.
[40]郭沫若.《鲁迅诗稿》序[N].人民日报,1961-09-18.
(责任编辑:翟瑞青)
On Scholar-official Identity of GUO Mo-ruo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U Yan
(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250103,China )
Abstract: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GUO Mo-ruo, a leader in Humanities of China, played a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ese literary arts and humanities academic career, which c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He was not only aware of the domestic literature dynamics timely through his own literary writings, but also actively promoted the positive energy from literary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justice, as well as effectively played this force to resist the reactionary forces worldwide. Although his scholar identity with some official position has been studied, but not clearly defined. For this purpo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eople ", regarding GUO Mo-ruo's identity as scholar-official,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udy his " duties writing "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is identification can also be of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f his similar contemporaries.
Key words:GUO Mo-ruo;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cholar-official; Duties Writing; Public People
收稿日期:2016-03-26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青年项目:建国后郭沫若“职务写作”研究(项目号GY2015C02);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博士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建国后郭沫若“复杂性”新论(项目号2014A002)
作者简介:逯艳(1983-),女,山东淄博沂源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3-01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