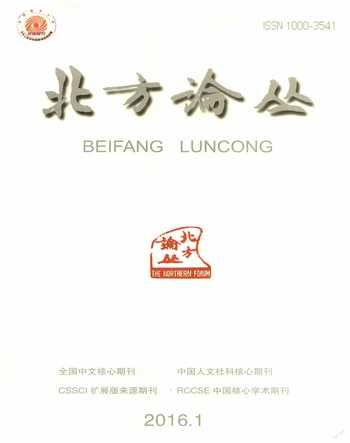命、性、才
王智汪
[摘 要]戴震论性、论才、论命,都是针对人性的不同侧面来说的,实质都是来源于他得“气化”思想。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命、性、才三者本为“一事三说”:命说的是人的自然规定和限制;性说的是人的本性、本质;才说的是表现出来的形体气质。他们分而言之为性,为才,为命,合而言之就是性,戴震以此建构出他的人性学说。
[关键词]命;性;才;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B24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90-04
性、才、命构成了戴震自然人性论的结构模式。命说的是人的自然规定和限制;性说的是人的本性、本质;才说的是表现出来的形体气质。可见,命、性、才三者本为“一事三说”:“命”指自然的赋予,是授方;“性”指生物的禀受,性源于命,是受方;“才”,性之所呈,即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指人与百物在各自本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材质。这其中的“命”“才”与“性”分别从不同侧面说明人的自然特征,“别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谓天性”[1](p160)。这就是“性”的生成过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才性与玄理是人性论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戴震通过对《周易》这段话的诠释,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2]。
一、“命”——人事尽处
“命”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观念物质形式,人性中的“命”,是指人物禀赋阴阳五行之气的多少、厚薄、清浊等种种限制。在戴震人性论视野中,人和其他动物一样,不过是一种自然实体。无论是人的感官活动(即耳聪目明、口言鼻嗅)还是意识与情感活动(喜怒、哀乐、好恶)都是“生于六气”,“人的思虑与情感等皆‘生于六气,则‘气亦与人的心理状态或精神面貌水乳交融、一体不分。”“气统摄着人的一切生命与精神活动,而人的一切生命与精神活动皆是气在人身上的表现”[3](p680)这种似乎很简单的形神观,其实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肉体上说,气在人身上表现为“血气”,并决定着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与相应的生命活动[3](p69)。“命”反映了人从气化流行过程中所获得的带有必然性的特征,即自然界给予人的物质规定性,诸如男女、高矮等差别,耳聋、失明、失聪等缺憾。它既是对人的行为的客观限制,又是对人的行为和发展趋向的引导,使人的自然之性归于中正无失,以成就性善的特性。因此,“命”作为人能知能善的保证,也是人性善的表现。如戴震所说:“命者非他,就性之自然,察之精明之尽,归于必然,为一定之限制,是乃自然之极则。”[4](p370)《中庸》曰:“天命之谓性。”以生而限于天,故曰天命。《大戴礼记》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分于道者,分于阴阳五行也。一言乎分,则其限之于始,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之不齐,各随所分而形于一,各成其性也。人物分于阴阳以成性,由于所分得的阴阳五行不尽不同,所以,形成的“性”也各有区别,如“凡言命者,受以为限制之称,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故理义以为之限制而不敢蹄,谓之命;气数以为之限制而不能蹄,亦谓之命”[1](p149)。“命”是人得之于天者,在对待命的态度上,王阳明在《再与徐子直》中写道:“我命虽在天,造命却我。”朱熹更是表现出儒者的超然:“圣人更不问命,只看义如何,贫富贵贱,惟义所在,谓安于所遇也。”[5](卷三十四)但朱熹又认为,所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个却须由我,不由他了”[5](卷九十八)。
戴震论“命”既异于孔孟,也不同于程朱,他对“命”的理解为人得于天者,有时又把人的这种规定性训释为“分”。他说:“譬天地于大树,有华、有实、有叶之不同,而华、实、叶皆分于树。形之巨细、色臭之浓淡,味之厚薄,又华与华不同,实与实不同。一言乎分,则各限于所分。”在知命、顺命的同时,戴震则汲取了朱熹的积极因素,将“命”融进人生实践中,以自觉的人生实践为命之实现。“人事尽处便是命”,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为钱?为情?为爱?为名?只有冷静地想想,仅仅是要实践人性而已,因为没有人性的人就会被物欲蒙蔽双眼、迷了心窍,渐渐失去人性。“若谓其有命,却去岩墙之下立,万一倒覆压处,却是专言命不得”[5](卷九十七)。人能在实践中通过扩充心智,实现自身性善的特征,这既是可能的又是必然的。
二、“性”——天地之化
在戴震看来,人性绝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理”,而是宇宙大化的生生流行。所谓“生生”乃是万物秉承各自之性,成其自身,如《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表示生不是一次性的,生而又生,生生不已。《系辞上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大传》肯定了变化的实在性与普遍性。这种观点即是过程观点,认为一切存在都是过程,存在即是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过程。“即使是动物,也由于性别具有一种牺牲的爱。自然之一切尊严、威力、智哲和深邃,都集中于和个体化于性别之中”[6](p123)。人性是人的类本质,是人存在的根本属性,也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涉及“性”的有:
天道,五行阴阳而已,分而有之以成性。
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
分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
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有实体,故可分;惟分也,故不齐。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
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为品物者也。限于所分曰命;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而秀发于心,征于貌色声曰才。
戴震认为:“一阴一阳,盖言乎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有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7](p28)天地何谓顺?“言乎自然之谓顺”[7](p28)。因为天地之顺是阴阳气化流行不已,也是血气心知之人性之和谐的初始。戴震认为:“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条理之秩然,礼至著也;条者之截然,义至著也;以是见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继之者善也。”[7](p28)何谓常?他说:“言乎必然之谓常。”[7](p28)“性”是自然,也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了,故天地之常态就是性的常态。这种常态一般用“权”来概括。“权”是“心之明”的最高表现,是性之常的保证。“凡此重彼轻,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则显然共见其千古不易之重轻;而重者于是乎轻,轻者于是乎重,变也,变则非智之尽,能辨罕事情而准,不足以知之”[8]。以达到天地之德,是人性最完美的境界,是天人合一,随心所欲的状态。
三、“才”——尽性即尽才
关于“才”,戴震归之为性的表现的完成形态:“由成性各殊,故才亦各殊。才质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质安睹所谓性哉!”性即是气质之性,它是人“性之所呈”,即人的特性,通过才质来表现,没有才质也就没有性,故尽才才能尽性。戴震说:“才者,人与百物各如其性以为形质。”人的形质即为才,才与命、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人若为不善,非才之罪,而是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所致。性是善的,才也是美的,两者基本一致。“人之性善,故才亦美,”才如果有不美,是因为有是非陷溺其心使然,“非天之降才尔殊。”比如,桃杏的性在桃杏的仁中,并且不可见,只有等到它发芽、生长及开花,结果时,桃与杏的区别也就显而易见,这也就是“才”的表现。因此,“才”本身的美恶对“性”没有影响。关于二者之间的联系,戴震指出“性”与“才”是相互联系的,“言才则性见,言性则才见”[4](pp309-310)。故,“才”是“性”的表现,而“性”是“才”根据,二者不可相离。戴震又在人之性皆善的基础上指出,天下古今之人的才质虽各有所异,但亦有所相近之处,或纯正或清明,皆才之美者。才的美恶,于性无所增,也无所损。
“性”由“才”呈。程朱将“性”分别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且将二者相对待的做法戴震在理论上予以否定。戴震说:所谓的“性”指的就是“气质之性”,在宋儒之前,从未有所谓的“天地之性”之说,无论是孔、孟,还是荀、扬,他们所说的“性”都是“气质之性”。既然万物之“性”乃为“气质之性”,则万物之“性”皆是就其“气质”或“气类”之别。因此,“舍气类,更无性之名”[1](p190)。这里所说的“气类”,是指向人们俗语中的万物之“才”,是人物在分有阴阳五行之气时有偏全、厚薄、清浊、昏明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形体、本性,所以,人与物的本性的区别就是气类的区别。比如:“鱼相忘于水,其非生于水者不能相忘水也,则觉不觉亦有殊致矣。闻虫鸟以为候,闻鸡鸣以为辰,彼之感而觉,觉而声应之,又觉之殊致有然矣。”[1](p183)而这些“知觉运动”之差异无非是性的使然。“只有用生的强烈感受去体察阴阳五行之气,才能容物于己,缘心感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9]。
四、性善才美
“心知”的扩充,仍然是以“血气”为基础,心知不能离开血气而单独存在。故张立文说:“心以一仁而言尽,这就把心理解狭隘了。生理的欲望、心理的欲望、道德的欲望,都可以包括在心内。”[10]道德常常是内在矛盾的,道德成为目的,就会成为人追求的目标,人们就会为道德而毁灭道德。“夷齐饿死,盗跖寿终”,这些都是人性之疑案。如果从真实的人性来看,世间其实根本就没有善人或恶人,只有觉悟的人和迷茫的人。因此,要达到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必须要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步骤,学习、讨论、反思、分析、抉择、践行,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知到行、由愚到智、由困乏到充实的过程,“人心唯危,道心惟微”。也许是休谟说的好:“对人性的终极原因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一种明智的哲学对问题的追究要适可而止。”如果社会主流是称赞“大义灭亲”的美德,并赋予感天动地的内涵,那么只能使人性更加困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之间基于血缘与亲情而自然存在的人之常情,是人性的体现,而那种基于降低执法成本、提高破案率的大义灭亲可能会因为维护法律的正义而伤害了正常的人性。由于这种“心知”的能力而“感知”各种伦理关系、“安排”相应的“社会生活”,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于是又因之而生。所以,人的“情”和“欲”皆是生于“性之自然”的,而且相应的“情”和“欲”之满足也都应该为“人道”所必备:
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者也。有血气,则所资以养其血气者,声、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伦,相亲相治,则随感而应为喜、怒、哀、乐。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1](p193)
人既然有“血气之欲”,则必求口、目、耳、鼻等欲望之满足,这是“气命”的表现,但君子不能因此“欲”而“纵其欲”;同时,尽管同样是限于“气命”导致人们之间的“才质”不一,但君子不因拘泥于“命之所限”而“不尽其材”。人徒知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就是人性。心之于理义,亦犹耳目鼻口之于声色臭味也,“盖就其所知以证明其所不知,举声色臭味之欲归之耳目鼻口,举理义之好归之心,皆内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俘晓然无疑于理义之为性,害道之言庶几可以息矣”[1](p157)。
在“才”上,孟子并不反对告子的“食色,性也”之说,因为“食色之性”,以及相应的“食色之才”也是天然合理性,合理但不合“性”,故不赋予“食色之性”及其“才”以道德属性。只有“四端之心”及其所体现之“性”方为人所独有并以之别于禽兽的根本依据。孟子认为,说人性善,并非意味着每个人天然地在现实中就是一个善人,而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因其先天之“善才”而具有成为善人、成为尧舜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于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即使人具有“四端”之“才”,然若不对此“才”进行“思”及“求”的话,则此先天之“才”也将失去,即“舍则失之”,而“才”之失就是“不尽其才也”。甚至有的人不但不反思、扩充自己的先天之“才”,而且还因其利欲之心而戕害这些“良知”“良能”之“才”。于是,久而久之,人的天赋之善情善意便被扼杀殆尽,同时人的本来用于道德判断的“是非之心”也就成为欺诈、算计、蒙骗的代名词了。“孟子曰‘非天之降才尔殊,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惟据才质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1](p18)。
在知与善的关系问题上,戴震走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儒学的道路。传统儒学把“知”作为达善的手段,“知”只具有工具的意义。戴震则把道德问题放在认识论中解决,因为道德产生于生活实际中,“人伦日用”是它们产生的根源。戴震还将“人伦日用”视为“心知”具体而实在的内容,一反理学以“心悟”求知的路径。发于情,合于礼,是文明之欲,是对善的追求,美的享受,所以人欲趋善,故人性乃善。“智,人也;不智,禽兽也”[11](p390)。戴震将道德问题变成知识问题,将成德变成纯粹的知识追求,性善才美,戴震说:
才可以始美而终于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谓性始善而终于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体质言也。体质戕坏,究非体质之罪,又安可咎其本始哉!倘如宋儒言“性即理”,言“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以孟子言性于陷溺梏亡之后,人见其不善,犹曰“非才之罪”者,宋儒于“天之降才”,即罪才也。[4](p310)
在《原善》中,戴震开宗明义地说道:“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显之为天之明谓之命。实之为化之顺谓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谓之理。”这里,戴震明确指出,“善”的内容包括仁礼义三方面,此三者是“天下之大本”。何谓“天下之大本”?这就在于:“善”显示为上天的智慧和意志时,就是“命”;“善”显示为自然界事物发展的秩序时,就是“道”;人们遵循“善”的要求去处理日常事务而有常规时,此常规就是“理”。即是说,“善”集“命”“道”“理”(即天、地、人)于一身。显然,此外所言之“善”已不单纯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而是一个包罗万有的精神实体,也就是说,戴震已用“善”代替原来的“道”作为万物的本体。
在古人心目中,人的身体及其器官被赋予了伦理的内容,以一种“即器显道”的方式成为人的道德品行的象征。孟子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地之间身为贵,无论穷达,身体都是我立命之所,都是我唯一不可让渡不可予夺的尊严,故把在理学中受压抑的人的欲望,情感,从天命之性中解放出来,正如明人张琦在《衡曲尘谭·情痴寐言》一文中说:“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从此以后,人应该尽情尽性地发挥才能,为人的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而奋斗。”[12](p62)
戴震坚持“其归于必然者也,命也,善也”[4](p373)。作为人的先天“良知”、“良能”的“亲亲”与“尊尊”等情感和行为本质上就是其仁、义之性的呈现。且依孟子之话语,“良知”、“良能”与“良心”、“本心”等亦为同义,而皆可统称曰“才”,即:无论是先天的道德判断能力,还是道德感情皆是人的天赋之才。因为,性不可见,而作为其萌发的各种“才”却是时时呈现的,性是因才而得以显的;同时,性之善恶与否亦是因才之显善显恶而得以确定的。于是,孟子性善论的主要致思理路便为:“以才论性”且“因情定性”也。如果才之形质遭到戕害,并不是才自身之过,更不是性之过。对于现实世界中的恶,孟子早已有“非才之罪”的定论。既然如此,那么“才失其才”,才之形质遭到戕害的原因是什么呢?戴震指出:“所谓性,所谓才,皆言乎气禀而已矣。其禀受之至,则性也;其体质之全,则才也。”[1](p196)
科学使人们相信人是自然的主宰,但如果把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把进化论引入到人性领域,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能毁灭人性,使人们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自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了真理,竞争也就成了社会的准则。人性被弱化,就会导致社会强调个性的发展,让人们相信越进化结果就越好,会导致人类对自然进行更加贪婪的掠夺和破坏,为所欲为、只为自己、不计后果的放纵进化,使得社会畸形发展,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等,失去了幸福的真正含义。社会就会失控,私欲盛行,赫胥黎说:“人类的天资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身体都有贪图享乐和逃避生活上痛苦的天赋欲望。”人们一面放纵地“进化”着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一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这会使得道德沦丧、心理畸变、物欲膨胀。
[参 考 文 献]
[1][清]戴震.戴震全书:第6册[M].合肥:黄山出版社,1995.
[2]李志林.戴震自然观的特色[J].江淮论坛,1990(1).
[3]陈徽.“性与天道”——戴东原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4][清]戴震,汤志钧校点.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宋]朱熹,[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振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清]戴震.戴震全集:第1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8][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61.
[9]张立文.戴震对自然生命的关怀[J].孔子研究,1993(4).
[10]张立文.戴震的心知论[J].船山学刊,1992(1).
[11][清]焦循.孟子正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2]王国良.孔孟·朱熹·戴震——中国生存论哲学传统的建构[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