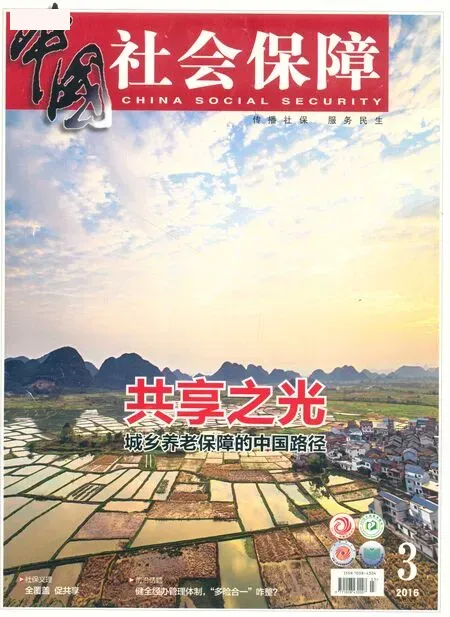教师篮球场病亡之工伤构成与判定
■文/向春华
教师篮球场病亡之工伤构成与判定
■文/向春华
一名普通教师,在篮球场打篮球时猝死,学校和家属认为是在等待工作期间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条件,应属于工伤。此种观点的错误在哪里?是否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要求?对工伤范围的确定和工伤保险制度会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屡败诉屡否定的工伤认定
王某系湖南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教师。2014年5月15日,王某在学校篮球场上猝亡。王某的妻子谢某申请工伤认定后,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决定。谢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历经两轮诉讼、四次审判,长沙市人社局均被判败诉,其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都被撤销,并被要求重新作出认定。
对于本案的基本事实,法院确认为:2014年5月15日下午王某下课后,在学校篮球场等候接受其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期间,自行在篮球场打篮球。当日下午3时40分左右突发疾病,经送医院抢救无效后于48小时内死亡。
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王某当时是否在工作岗位。王某一方认为,王某是在等候学生进行毕业论文指导的间隙出事的,和他的本职工作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并且指导毕业论文的形式和场地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不局限于教室或教研室等场合,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就可以认定为工作岗位或工作场所。而长沙市人社局一方则认为,王某发病时在打篮球,他不是体育老师,学校当时也没有安排篮球比赛等相关活动,打篮球完全是他自己的娱乐行为,不属于在岗状态,不应视同工伤。法院的判定其实是扩大了《工伤保险条例》的工伤范围。
本案表面上看是工伤判定个案问题,但是深层次上则涉及疾病视同工伤的条件认定,对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大影响,需要深入剖析以明晰是非。
法院“认定”工伤理由及其错误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该条款强调,无论作为突发疾病结果的当场死亡还是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该突发疾病必须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书[(2014)芙行初字第140号]认为,王某作为在校老师,在校授课以及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均是王某的职责范围。老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一般由指导老师与学生自行确定,并无固定时间、地点,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王某在与学生约定的时间和地点等候该学生时打篮球,其间突发疾病死亡,该时间和地点应为王某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其在该时间、地点突发疾病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同为工伤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死亡。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于法无据,应予撤销。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行政判决书[(2014)长中行终字第00377号]认为,王某到达篮球场这一事发地点系以为学生指导论文为目的,是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因而事发地点应认定为工作岗位。王某到达事发地点后,因学生未到而在事发地点就地参与篮球活动,边打篮球边等学生,并未中止为学生指导论文的进程,不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属于人之常情,可以认定其在发病时仍在工作岗位的事实。市人社局以王某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为由,否认其事发时在工作岗位,没有法律依据,且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支持。因此,王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规定。市人社局认为王某发病时不在工作岗位,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笔者认为,法院的第一个观点,即“老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一般由指导老师与学生自行确定,并无固定时间、地点,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成立。(1)一审法院使用“地点”一词明显违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无论是从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还是从工伤认定的实践来看,条例是严格区分工作场所(地点)和工作岗位的。二审法院更多地采用“工作岗位”表述,更符合条例要求。(2)事实上,并不仅仅是教师以及教师指导论文工作,任何一项工作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教师的一般工作岗位是教室,但如果由于特殊原因,教师在自己的家中从事教学活动,该特定区域自然也就成为工作岗位;纺织工人的工作岗位是纺织车间,如果领导要求某纺织工人陪同出纳去银行取钱,那么在银行取钱的特定区域也就是工作岗位。(3)虽然工作岗位是可以变动的,但并不意味着具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不宜完全由教师和学生自由确定。例如,教师和学生约定在洗浴中心讨论论文修改,洗浴中心也算教师的工作岗位吗?恐怕没几个人会认同。那么,同样是双方商定的地点,为什么一种地点就是工作岗位,而另一个地点就不是工作岗位呢?根据法院的逻辑是无法区分的。
法院的第二个观点认为,王某按照约定在等待学生时打篮球的时间和地点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长沙市人社局一方则强调,王某打篮球完全是他自己的娱乐行为,不属于工作岗位。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王某的行为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打篮球的行为,这是实行行为,具有外在客观表现的行为;另一个是等候学生进行论文指导。等待行为可以成为独立的行为,比如行为人无其他行为而较长时间立于路边,客观上表现出系在等候某人,则属于等待行为。行为人虽然有等待的内心意思,但客观上并无等待的行为特征,特别是有明确的实行行为时,这时并不存在等待行为,不能认为行为人实施了等待的身体举动。法院将等候的内心意思和打篮球的实行行为混合在一起,而在结论中采纳了等候的内心意思而有意忽略了打篮球这一实行行为,使其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社部门则强调了打篮球的客观行为,而未对等候的内心意思对工伤认定的影响予以分析,因而无法有力地驳倒法院的观点。
法院的第三个观点认为,王某到达篮球场这一事发地点系以为学生指导论文为目的,是其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因而事发地点应认定为工作岗位。该观点的错误在于,根据行为目的直接确定行为性质。例如,在民事法律制度中并不存在预备行为理论,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实行行为,就不能把行为人的身体动静认定为实行行为本身。以本案来说,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论文指导行为,其他任何行为——即便是完全站立于篮球场边,也不能认定为是在实施论文指导行为。在本案中,根本不存在“为学生指导论文”这一行为,更谈不上“未中止为学生指导论文的进程”,不存在正在实施的工作任务、正在履行的职务行为。
玩耍、娱乐与工作有关联,会有利于工作,但除了特定职业外,不存在将玩耍、娱乐确定工作的“人之常情”或“常理”。
工作岗位的泛化及其危害
在本案中,法官实际是通过对工作、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的泛化作出裁判的。一是将“等候”确定为工作本身,即劳动者只要是在等候进行工作,该时间和地点也就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二是根据行为的目的将行为确定为工作,即只要劳动者的行为目的是为了工作,那么该行为就属于工作。这样的逻辑推论必将导致极其荒谬的结论。例如,行为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从事散步、吃饭、消遣娱乐、聊天,如果都是为了在等候“对学生进行论文指导”,到达该地点“系以为学生指导论文为目的,是其履行工作职务的行为,因而事发地点应认定为工作岗位”,那么在这些活动中突发疾病死亡或抢救无效在48小时内死亡的,都应当视同工伤;基于同样的逻辑,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从事任何活动,只要有这样的等候意图和目的,遭受的伤害都应当认定为工伤。
如果贯彻这样的逻辑推论,将会导致凡不能排除属于工伤的都必须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这样一来,工伤保险将不再是工伤保险,而成了“意外伤害保险+疾病保险”。只要用人单位或者同事(工作关联人员)出具证明表明存在工作目的和意图,那么劳动者只要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在48小时内死亡,全部都可以视同工伤;任何事故伤害,也都可能成为工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