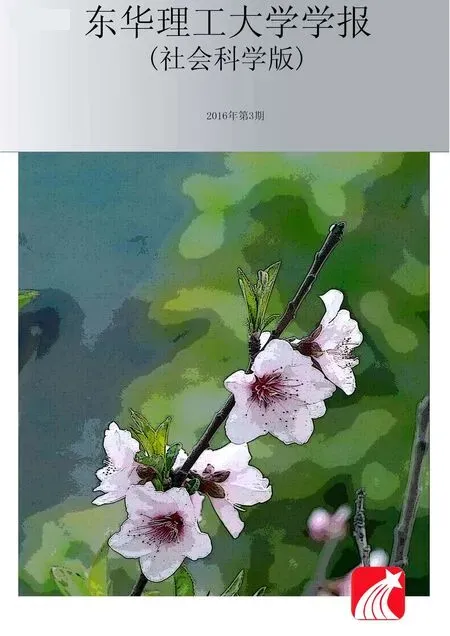《牡丹亭》春香传奇
黄振林
(东华理工大学 抚州师范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
《牡丹亭》春香传奇
黄振林
(东华理工大学 抚州师范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
通过对《牡丹亭》的文本细读,重新审视春香这一形象在杜丽娘性萌动与觉醒这一青春转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明清和近代《牡丹亭》改编和演出中春香形象的变化,深入分析和研究了曲师和伶工对春香形象认识存在的习惯性误区,旨在推动春香形象研究的原始回归。
汤显祖;《牡丹亭》;春香;性觉醒;冯梦龙
黄振林.《牡丹亭》春香传奇[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38-244.
Huang Zhen-lin.The legend of Chunxiang in the Peony Pavilion[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3):238-244.
1 一部情缘,源于春香

《牡丹亭》素材来源是作于明代弘治(1488—1505)到嘉靖(1522—1566)初年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特别是话本前半部分为传奇提供了基本的故事框架,我们看看话本中给春香的定位:丽娘十六岁,有一胞弟,名唤兴文,另“带一侍婢,名唤春香,年十岁,同往本府后花园游赏”。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有关这个人物的语言行为描写。汤显祖《牡丹亭》改杜丽娘为独生女,年方十六,依话本年龄未变。但春香的年龄由十岁改为十三四岁。第九出《肃苑》春香自吟诗上场:“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省人事。终须等着个助情花,处处相随步步觑”。这首诗改写自唐代诗人刘禹锡《寄赠小樊》:“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花面,指如花的面容,也有人理解为少女用花朵粉饰面容。汤显祖在这里有两处重要的修改:“省人事”、“助情花”。前者指明白人事;后者喻指情人。这两条对春香形象的定位有奠基作用。刘禹锡《寄赠小樊》中的小樊,指白居易姬妾樊素,“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是传统诗文中少见的性感少女的象征。古人称少女十二岁为金钗之年,开始带钗梳妆,南朝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中有“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十三四岁则称豆蔻年华,杜牧《赠别》有“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十五岁为及笄之年,绾发插簪,表示成年;十六岁称破瓜之年,暗喻可以出嫁成婚。汤显祖将春香的年龄从话本的十岁提升到十三四岁,按当时女性的社会身份,是性朦胧觉醒的年龄。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1918—2000)用英文写成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中,说到明代万历六年(1578)万历皇帝大婚时,“当时皇帝年仅十四,皇后年仅十三”;另说到当时皇宫宫女情况时说,“这些女孩子的年龄在九岁至十四岁之间”[1]。可见当时女性这个年龄,在官府和民间都认为是可以婚配的年纪。
春香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性觉醒意识。风姿柔美,善于打扮,且身材苗条。第九出《肃苑》春香上场唱【一江风】:“小春香,一种在人奴上。画阁里从娇养,侍娘行。弄粉调朱,贴翠拈花,惯向妆台傍。陪他理绣床,陪他夜烧香。小苗条吃的是夫人杖”。虽然身列奴婢行列,但“在人奴上”,即和一般的粗鄙使唤丫头不同,可以和小姐一样“弄粉调朱,贴翠拈花”,日常的功课是读书、绣花。近代昆曲表演艺术家徐凌云理解“陪他理绣床”,绣床即是刺绣的棚子[2]。唯一受委屈的是,小姐犯错,她要替小姐受过,被夫人杖责。第五出《延师》杜宝明确对陈最良说,小姐读书,“有不臻的所在,打丫头”。春香的成熟、调皮、老练,在《闺塾》一出有精彩表现。此出在历代折子戏均名为《春香闹学》。清代《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三妇之一陈同评点曰:“春香憨劣,处处发笑”[3]。所谓“憨劣”,即顽劣、贪玩、机灵。她借口出恭,实去花园。回来告诉丽娘“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正是因为春香先于丽娘游园,并启迪怂恿丽娘到后花园“耍”去的,才成就了丽娘的“惊梦”。这是“游园惊梦”这段情缘的最原初动力。《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中三妇之一陈同慧眼识金,她评点曰:“此处大有关目,非科诨也。盖春香不瞧园,丽娘何以游春?不游春,那得感梦?一部情缘,隐隐从微处逗起”[3]。清代妇人凭借敏锐的感知力,准确抓住了促使杜丽娘青春觉醒的重要动因是春香的游园挑逗。
《闺塾》中,当春香说到“大花园好耍子哩”时,连自矜“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个伤春”的陈最良,马上警觉并恐吓:“哎也,不攻书,花园去,待俺取荆条来”。面对腐儒荆条施压,春香并不畏惧。且突然借此对女儿家“习经诵文”提出强烈“抗议”:“【前腔】女郎行,那里应文科判衙?只不过识字儿书涂嫩鸦”。明确主张:女儿家不需要应科考,坐公堂,略通文墨即可。甚至说,你陈最良“悬梁刺股,有甚光华”?可谓戳痛陈最良最隐秘脆弱的神经。明末天启年间刻本王思任《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在此处批到:“正是文章凌空起峭处,绝妙绝妙!”更放肆的是,门外传来卖花声,春香即刻叫到:“小姐,你听一声声卖花声,把读书声差”。此处“差”同“岔”。这次在劫难逃,春香引来陈最良真实的荆条抽打。
与在闺塾闹学不同,《肃苑》一出,更表现了十三、四岁的春香的成熟。因为日夜跟随和陪侍小姐,对小姐的性情了熟于心。她评价丽娘“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持重”。这几乎是两对有褒有贬的评语。有远播门外的美貌,却恪守闺阁不出;看起来娇嫩青葱,但处世拘谨本分。一句话,谨守闺训,绝不逾矩。不逾矩,是传统家训对闺女要求的底线。春香的评价褒贬各半,可见她对小姐的表现是有所“保留”的。当她看见小姐读《毛诗》表现出倦怠和乏味时,又怂恿到“后花园走走”。而受到小姐委托先行去请花郎肃扫花苑时,她表现得十分开心放肆,甚至和花郎调情。当花郎恭维她“春姐花沁的水洸浪”,即说春香姐像花香播洒使人神魂摇荡时,春香异常粗俗地讽刺花郎还未成熟、性能力还未达到男儿应有水准。可见,春香“扮演”的是先于丽娘的性觉醒者。
从戏文中主婢对话中可知,游园那天老爷下乡劝农,正好是立春节气。因为在装扮时,春香有一句“你侧着宜春髻子,恰凭栏”。《荆楚岁时记》曾载:立春那天,妇女把彩色织物剪成燕子形状,贴上“宜春”二字,戴在发髻上,以示迎春。从游园前的梳妆过程和丽娘的心情看,丽娘平常的梳妆打扮绝对没有今天这般隆重。今天在春香的安排下,丽娘可谓是“盛装游园”。她有点犹豫和矜持:“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她反复端详自己,特别是面对镜子的羞怯,让观众感觉丽娘是个十分青涩的闺秀。难道丽娘小姐是第一次面对菱花吗?肯定不是。但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的打扮过于漂亮和隆重了。宝石镶簪,晶莹透亮;翠裙红衫,光彩照人。连她自己都“惊艳”了。她对这种装束微微表示不满,微嗔春香:“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对这句曲文的解释存在很大差异。香港中文大学的华玮教授认为,这句唱词“对于理解她的性格至关重要。但这句曲文常被误解。将‘爱好’解作今天通用的‘喜欢’。故将全句的意思当成:我喜欢天然。事实上,‘好’即是‘美’,应该作三声,意同‘那牡丹虽好’之‘好’。全句是丽娘承认自己一生爱美是天性使然”[4]。其实,“好”应该理解为“美”。临川方言中,“长得好”即是“长得美”。意思是:我一生爱美的是我天然的相貌,不需要这样刻意雕琢打扮。在游园的过程中,姹紫嫣红的确让丽娘惊叹。当她无端感伤和幽怨竟让牡丹占得百花之先时,春香再次文不对题地接句:“成对儿莺燕呵”,诱导丽娘感慨:莺燕都成双成对了,我十六岁了,还未出阁嫁人啊!压抑不住的春情春困,直接导致惊梦的发生。到此为止,春香实际上完成了从性觉醒者到性引导者的角色转变。
2 “梅香”队里添新人

3 何以安排春香出家
明清文人曲家王思任(1574—1646)、沈际飞(生卒年不详)、臧懋循(1550—1620)等对《牡丹亭》人物塑造均作出过深入评论。王思任在《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序》中这样概括:“杜丽娘之夭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基本准确地说明了曲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冯梦龙(1574—1646)非常赞赏这段话,他在改编《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传奇》“小引”中全文引述上段话,并说:“此数语直为本传点睛”[9]。王思任还赞赏春香:“眨眼即知,锥心必尽,亦文亦史,亦败亦成”。沈际飞在吸收王思任概括基础上,为《牡丹亭》题词时这样概括:“柳生呆绝、杜女妖绝、杜翁方绝、陈老迂绝、甄母愁绝、春香韵绝”。从舞台表演的角度看,春香作为丽娘的陪衬,其实对丽娘形象起到重要的互补作用。清代宫谱《审音鉴古录》在《牡丹亭·离魂》一出旁眉批到:“春香最难陪衬。(表演中)或与小旦揉背拭泪,或倚椅瞌睡,或胡答胡应,或剪烛支分,依宾衬主法,方为合适”。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谈到《牡丹亭》中春香与杜丽娘的陪衬表演时,也说到两个人端庄和活泼的互补关系。他自己搬演《牡丹亭》,也是首选《春香闹学》。那是1916年1月23日,在北京吉祥园初演春香[10]。1916年的11月,又到上海天蟾舞台演《春香闹学》。当时,11月17日的《申报》,还有《春香闹学》的广告。内云:“此剧梅君兰芳饰春香,天然身材,韶秀绝伦,丰姿出色。兼以姚君(姚玉芙,引者注)之小姐,配合熟手,玉树珊瑚,雅妙超群”。1920年5月,梅兰芳主演的《春香闹学》被拍成电影,这也是汤显祖的剧作首次搬上银幕。
对春香认识的不足,始于冯梦龙。《三会亲风流梦传奇》第四折《官舍延师》和第五折《传经习字》首先将春香性格定位在极其抵触杜丽娘延师闺塾的丫环。当家院传话丽娘拜见师父时,春香说:“小姐,拜了师父,便受他拘管,怎得自在?莫去吧”。春香上场自报家门云:“俺春香自小伏侍小姐,朝暮不离。可喜小姐性格温柔,绝无嗔责。昨日没来由,拜了个师父,那师父景象,好不古板。老爷又对他说,倘有不臻的所在,只打这丫头。哎哟,丫头可是与他出气的?却不是春香晦气!”渐渐地淡化春香身上原有的知性和闺门气息。由于改得活泼俚俗,后来的台本基本袭用了冯梦龙的套路。而在汤显祖原稿中,春香对丽娘春情萌动的含蓄表达,在冯梦龙改本中也变得直白。第六折《春香肃苑》中,对丽娘的介绍,原作是“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持重”,改为:“名为国色,实守家声。一眯娇羞,十分尊重”。春香说;“只因老爷延师教授,讲《毛诗》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知触动了什么念头?忽然废书而叹。春香那时早猜着了八九分,他到关雎小鸟,尚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因而进言,劝小姐后花园消遣”。按照冯梦龙改本中的台词,丽娘称春香是“我知心的侍儿”,自然关系非同一般。但冯梦龙却没有把握好丽娘小姐与春香丫环之间应有的分寸和距离。
《牡丹亭》“游园”一出十分细腻含蓄。春香的精明成熟本来在汤显祖笔下相当精彩地被展示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游园前后的表现。但是在冯梦龙的改本中却被稀释了。第七折“梦感春情”蹈袭《牡丹亭》第十出“惊梦”。原作开篇是旦唱【绕池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描述莺声婉啭,惊醒春梦,丽娘立于小庭深院,隐隐感觉到春光对少女之心的撩拨。并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游园略感忐忑和充满期许。但冯梦龙却改得很直接:“(旦)花娇柳颤,乱煞年华遍。逗芳心小庭深院。(贴)莺啼梦转,向栏杆立倦,恁今春关情胜去年[9]”。台湾文化学者郑培凯批评到:“小姐一上场就看到花柳争春,到处乱煞了春光,在小庭深院里,还没完全清醒,就已春心大动。然后丫头唱,形容小姐春眠辗转,听到莺雀啼声,起来后就靠着栏杆发懒”[11]。郑培凯说,已经不是大家闺秀,倒像青楼佳丽了[11]。在汤显祖原作中,由于春香深知丽娘小姐的脾气:“我一生爱好是天然”。所以面对丽娘的第一次“盛装”,春香只是有分寸地说一句:“今日穿插的好”。而冯梦龙则安排春香道白:“小姐,你今日装扮得更好,试与山色共争春,管春山不逮蛾眉远”。这些都说明,冯梦龙偏离了汤显祖《牡丹亭》中对丽娘和春香两个女性形象的深刻定位。而且,这种偏离,在清代台本中继续作惯性运动。
乾嘉时期的剧唱台本选集《缀白裘》是影响最大的昆曲演出本。《闺塾》更名为《学堂》,像《西厢记》中的《拷红》一样,是舞台上经典的丫环戏。贴扮春香,是名副其实的“闹学”主角。台本把《牡丹亭》原作第九出《肃苑》春香出场的自我介绍和对杜丽娘的评价放在最前面,基本延续了冯梦龙《风流梦》第五折“传经习字”的情节安排。对丽娘的介绍,《缀白裘》改为“名为国色,实守家声。杏脸娇羞,老成持重”,把“嫩脸”改为“杏脸”。杏脸形容女性脸蛋的圆润,对比原作中的“嫩脸”,以及《西厢记》中孙飞虎眼中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香”的典雅描写,逐步地将春香的眼光由典雅变得俚俗。她的身份也似乎由官府家的上等丫头,变成有钱人家狡黠俗气的丫环,真是“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特别是民间演剧迎合市民层审美期待,放大了春香性格中调皮滑头的成分,逐渐由玲珑温雅变成泼辣甚至油滑。说起老爷交代的“倘有不到的所在,只打这丫头”,春香不是原作中还未打就“哎哟”,而是“呀啐!可不是我的晦气(笑),想我春香可是于他出气的么”,简直快要“直唾其面”了。而面对老实迂腐的陈最良,春香竟敢主动“挑事”。先生未责怪时,竟说“先生休怪”;先生说“哪个怪你?”春香回答:“不是小姐来迟了些?”后来竟“抬杠”说,“今夜我同小姐竟不要睡,等到三更时分,就请先生上书”。接着先生发问,本一句都背不出,竟然回答:“烂熟了”。在延续原作最经典的“关关雎鸠,在何知州”的“高论”后,借口出恭到桃红柳绿的大花园“耍子”。又是骂先生“老遭瘟”, 又是夺先生的戒尺掷于地上,“装嫩”说:“我是个嫩娃娃,怎生禁受恁般毒打”。小姐要她下跪向先生认错,她却跪对小姐。小姐打她,她又是装疼,又是做鬼脸。气得先生胡子都白了:“这等可恶,我要辞馆了”。而先生下课用膳,她竟在背后粗俗骂道:“呀啐!老白毛!老不死!好个不知趣的老村牛”。
冯梦龙在《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传奇》“总评”中谈到传奇结构安排应该紧凑时说;“凡传奇最忌支离,一贴旦而又翻小姑姑,不赘甚乎!今改春香出家,即以代小姑姑,且为认真容张本,省却葛藤几许”[9]。尽管这种改动减少了人物和头绪,让人物更加集中,但是并不符合《牡丹亭》的曲意,更不符合人物性格成长和发展的必然。根据汤显祖原作安排,杜丽娘殇殒之后,春香跟随公相夫人到扬州。三年之后的丽娘生忌之日,两人上香祭典,见物思人,黯然情伤。老夫人一直未走出爱女夭折的阴影,而“受恩无尽,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的唱词,也表达了春香对丽娘终身的感恩。所以,安排春香出家没有性格基础,非常突兀。第二十五出《忆女》除了表达上述曲意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因为丽娘夭折,杜宝有娶妾生子续香火之念。当老夫人表达庶出不如亲生的忧虑时,春香现身说法,说自己尚非亲生,蒙夫人收养。《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三妇之一 陈同评点说:“春香现身说法,俨有自媒之意”[3]。可见春香在丽娘夭折后一直侍候老夫人身边,形同子女。春香此番安抚,也有希望老夫人正式收养自己为养女之意。而冯梦龙改本第十六折《谋厝殇女》,安葬丽娘并起梅花观时,春香跪哭到:“春香有言禀上,贱婢蒙小姐数年抬举,一旦抛离,老爷奶奶既为王事驱驰,盼什么人间结果?情愿跟随道侣,共事焚修。一来可以伴小姐之幽灵,二来可以慰老爷奶奶之悬念,三来老道姑有个帮助,香火可以永久”。冯梦龙自己眉批到:“春香出家,可谓义婢,便伏小姑姑及认画张本,后来小姐重生,依旧作伴。原稿葛藤,一笔都尽矣”[12]。看似得意之笔,只不过是冯梦龙自我陶醉罢了。本质上的差距是,汤显祖心中,春香是杜丽娘性觉醒的诱导者、甚至启蒙者,而在冯梦龙眼中,竟然变成削去灵根慧命、人间情种的道姑。第二十二折《石姑阻欢》实际是搬写汤显祖原作第二十九出《旁疑》,只是将原稿中游方小道姑换成出家的春香。当石道姑听到柳梦梅屋子有女人唧唧哝哝话语声,便怀疑春香潜入房中与梦梅有私。说春香“年轻貌美,打熬不过,况是丫鬟出身,偷汉手段,是即溜的”。而春香气愤填膺:“我少小相依绣阁居,调脂侍粉见人疏。为怜雨打中秋夜,愿弃尘凡读道书”。不仅把自己出家人“凡心已灭”的现状捧出,还说自打小就是很少见男人的侍儿。可惜的是,冯梦龙在改编时,忘了《牡丹亭》第九出“肃苑”中春香与小花郎调情的细节。
《审音鉴古录》中“离魂”,在舞台上有意渲染杜丽娘临死前的恐怖氛围,给人阴森压抑之感,甚至春香不敢近前。本来情同姐妹、相依为命的主婢,竟然在小姐还未亡故时就生分了。
“[贴] 老夫人住在此。[老旦] 为什么?[贴] 春香有些害怕。[老旦] 自家小姐,怕他则甚?我去就来。儿啊,银蟾谩捣君臣药,纸马重烧子母钱。[下] [贴] 哎呀,老夫人多着几个人来啊!哎呀,老夫人住在此嚜还好吔。[小旦低头科] 母亲。[贴先张内,作怕走进去科] 老夫人去了。[小旦] 啊,夫人去了?[贴作进内应] 正是。[小旦略变抖声,谩提起上身,抬头,无光眼看贴,身一矬,下磕搁右臂上] [贴看怕科] 啊哟![小旦睁目即闭,无神状] 来。[对贴的头] [贴作走一步退三步,怕状] 在这里。[小旦右手抖拍桌云] 站到这里来。[贴] 哎呀,在这里吔。[小旦皱眉,照前拍科] 这里来呵。[贴] 哎呀,偏是今夜的灯昏暗的紧。”
于是,《牡丹亭》在明清代的传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众多文人特别是闺阁女性在案头阅读《牡丹亭》时,引发强烈共鸣。出现了俞二娘、商小玲、金凤钿、冯小青、冯三妇等痴情文本的女子[13]。“日夕把卷,吟玩不辍”,并在各种评点中独抒性灵,充满卓见;而在所谓曲家眼中,《牡丹亭》却不合律,屡遭沈璟、吕玉绳、臧懋循、冯梦龙等文人和伶师窜改,逐渐偏离汤显祖“曲意”。而春香形象的逐渐偏离是《牡丹亭》改编中最突出的现象。清代龚自珍(1792—1841)在《己亥杂诗》云:“梨园串本募谁修,亦是风花一代愁。我替尊前深惋惜,文人珠玉女儿喉[14]”。龚自珍为汤显祖鸣不平,是有道理的。
[1]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增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2007:22,24.
[2]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27.
[3] 陈同,谈则,钱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
[4] 华玮.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牡丹亭·惊梦的诠释及演出[M] //走近汤显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8.
[5] 王季思.西厢记叙说[J] .人民文学,1955(9):66-68.
[6] 黄季鸿.西厢记研究史:元明卷[M] .北京:中华书局,2013:421.
[7] 王实甫.西厢记[M] .王季思,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5.
[8]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
[9] 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下[M] //冯梦龙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047,1066,1049.
[10] 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152.
[11] 郑培凯.从案头之书到筵上之曲:“游园惊梦”的演出文本[M] //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03.
[12] 冯梦龙.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M] //冯梦龙全集:第13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093.
[13] 黄文锡.突破传统启先河——论“临川四梦”的人物塑造[J] .抚州师专学报,2000(3):1-6.
[14] 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9.
The Legend of Chunxiang in the Peony Pavilion
HUANG Zhen-lin
(FuzhouNormalCollege,East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Fuzhou344000,China)
Through a close study of the Peony Pavilion,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reevaluate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Chunxiang played in Du Liniang’s initial sex awareness and arousal in her adolescent turning process.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regression to the study of Chunxiang’s image by sorting out the changes of Chunxiang’s images in adaptations and performances of the Peony Pavil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by analyzing the musicians and performers’ habitual misunderstandings of Chunxiang’s images.
Tang Xianzu; the Peony Pavilion; Chunxiang; sex arousal; Feng Menglong
2016-08-10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元明清曲谱与南戏传奇关系研究》(14YJA751008)的阶段性成果。
黄振林(1958—),男,江西临川人,东华理工大学江西戏剧资源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戏曲史研究。
J805
A
1674-3512(2016)03-02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