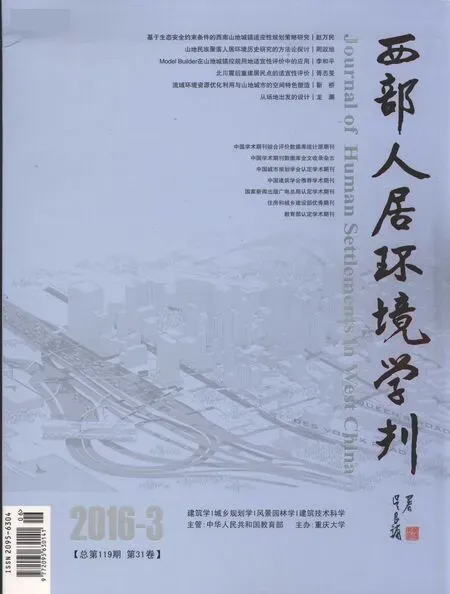大地“渊薮”*——地形要素在乡土建筑中的建构学解读
寿 焘 张 彤 弗兰卡·特鲁比亚诺
◎建筑设计与理论
大地“渊薮”*——地形要素在乡土建筑中的建构学解读
寿 焘张 彤弗兰卡·特鲁比亚诺
从“建构”理论中所涉及的“地形”因素的回溯及纵深辨析开始,围绕森佩尔建筑四要素中“基台”与其他三要素的关系展开探讨,通过对中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乡土建筑案例的类型学归纳与理论探析,阐释了在自然地形、基台塑造以及其影响下的建筑内部空间这三个递进层级中,地形要素在实践和精神层面的现象学转移及其在建构视角下的多重解读可能性,试图建立面向地形的乡土建构体系研究视角与方法。
地形;乡土建筑;建构学;乡土建构体系;基台;建造;生活模式
“建筑不应仅仅通过风格化图片被阐述,因为其本身是建筑形象之外的产物,而地点、围合以及材料应该在风格之前被考虑,因此,在图像和地点的关系中,建筑将变得更加清晰。”[1]——大卫·莱瑟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
“乡土建筑作为民间生活方式的有形表达,并非仅是建筑艺术,他们低调谦逊间或奇异的成就值得思考和学习,那些针对人们生活而不是对抗人们生活的建筑,在我看来,没有哪一个是过时的。”[2]——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
1 在“建构”与“地形”的关联中拓展“乡土建构”的意义
建筑的基本意义无异于栖息大地并建立人与自然内外的某种关系。而大地,作为建筑的永恒前提,“揣测”着建筑的“重量”,“记录”着建筑的“时间”,并“亲眼目睹”建筑的“生长”、“衍化”和“消亡”。如果说建造是人类的本能,而大地是建造之前提。那么,“建构”(Tectonics)——作为揭示建造的“本体”与“再现”之间逻辑与文化关联的指代,则需要依靠地形要素延伸其所谓“诗意”的内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238011)
寿 焘: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访问学者,beyondshou @126.com
张彤(通 讯作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弗兰卡· 特鲁比亚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系,副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图1 森佩尔对加勒比茅屋的解析图Fig.1 the diagram of Caribbean hut by Semper
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将“基台”(Mound)作为其建筑四要素的基础,在建构关系中,抽取了建筑与地形(Topography)抽象关系的基本原型。而正是另一个要素“炉火”(Hearth)的精神意义,使得地形要素不再静止,转而流动的拉近人与大地的距离(图1)。
肯尼斯·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森佩尔建构观影响下,显然意识到“建构学”潜在的自我矛盾,于是他将“建构与地形”的讨论视为其“建构文化”(Tectonic Culture)首要问题。在引述意大利建筑师维托里奥·格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的话中,他试图引发建构与地形之间的古老寓意:“在人类还没有将支撑转化为柱子、或者将屋顶转化为山花以及用石块进行砌筑之前,人类已经将石块置于大地,在混沌一片的宇宙中认识大地,对它进行思考和修改。”[3](图2)从而,对大地的先验性认知决定了地形将在人造物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前提性角色)。
这个角色随后被莱瑟巴罗定义为地形架构下的六个前提,即“建筑和景观共有的地平线;镶嵌的异质性;并非完全的土地也非完全的材料;不是阳光下的形式游戏;被给予却未显示;浸透着实践的痕迹。”[4]地形通过建造成为一种有待被呈现意义的期许。
显然,此时的“地形”已不再是“如是”的土地,它的内涵已在人类改造自然,建造房屋的实践下所化为的“生活地坪”(Living Terrace)[5]中得以拓展。而“建构”的指向也悄然被“解放”,不再仅仅停留于结构、建造与形式的自我辩证之下(往往更偏向于对结构关系的忠实体现和建造逻辑的清晰表达),更在其与大地的连接状态中获得“现象”的赋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森佩尔、弗兰姆普顿,还是莱瑟巴罗等对建构与地形或地形认知的探讨,似乎都不约而同的将二者的关系引入乡土语境。由此进入的乡土世界,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定位“建构”的坐标。
在乡土建筑领域,英国学者保罗·奥利弗(Paul Oliver)几乎探寻了现存于世界的所有乡土聚落,进而在总结喀麦隆玛雅科比河(Mayo-Kebbi River)流域乡土生活时所作的这张全景图谱(图3)再恰当不过的全面阐述了全景意义上的“地形”之于乡土建筑的影响。在这幅图中,建筑不再如其他剖面所示的那样孤立的自我宣扬,而是与地形一起形成富于垂直向地质规律和水平向自然给予之间的场域特质。它隐藏了一种“扎根”乡土的建构文化,意义便暗含于建筑应对选址、取材,甚至气候和地质风化等多种层面上“驾驭”土地的能力。

图2 史前巨石阵Fig.2 the stonehenge
不可否认,传统建构学视角已在乡土世界中转向,此刻的地形要素被容纳进一个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乡土建构体系中,这个体系由地形“发端”并“闭合”,在气候、时间、文化等客观因素中完成自我呈现。此时,对地形的理解,显然不能仅停留于地面上那薄薄的一层表面,作为一种完备的系统,它更应该隐含着其之上和之下,以及它的中介。乡土建构在其位处和场所意义上便包含了3个地形界面,仿若一个连续剖面,暗喻着自然地形、自然地形与建筑的连接状态及其影响下建筑自身地形与基台的含义。并因此,逐步衍化为乡土建构文化意义上的“地形”视角。
2 地形隐喻与建构启发
2.1地形结构性隐喻
自然地形“潜伏”着某种结构性,揭开乡土建构的“序言”,也是人类理解土地并施加建造的初始。高耸的山崖以及层叠的肌理犹如建筑的结构拟态,而这种结构性关系藏匿在早期绘画艺术中,成为西方建构理论的初始依据。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建筑被消隐在山川河流之中(图4);塞尚(Paul Cezanne)的晚期作品《圣维克多山》中(图5),建筑已经让人辨不清其材料,也难喻其形状,但我们依然可以理清结构性所展示的整个地形层次,柯林·罗(Colin Rowe)更将其定义为“物理透明性”的源头[6]。倘若忽略两幅画表现手法的差异,便可直接感受地形隐喻的象征。此时的建筑,仿佛被包裹进一个巨大的“磁场”,恰恰是山水风土所展现的结构力量。

图3 保罗·奥利弗的玛雅科比河流域地形剖面图Fig.3 the topographical section in the area of Mayo-Kebbi River by Oliver
其实,建构的英文“Tectonics”所具有的“地质与地层构造”这样的地质学基本含义也暗示了它与地形的不可分离[7]。山之延绵,乃地质层挤压使然,水之流淌,也正因为岩石泥流的承载。鲁道夫斯基所展示的镶嵌大地、树上栖息和水上生活等便把无声的地形和有声的人类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生命。
2.2显性与隐性的建构动机
地形时常隐喻着显性的建构动机,伟大的建造者并没有在建筑与雕塑之间划分界限。在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伊朗的坎德文(Kandvan),住宅展现了一种与我们现今所看到的众多具有优秀建构特质的现代建筑如出一辙的呈现方式,由地形结构操作空间,而结构关系又直接体现建筑形式。裸露的火山石灰岩在风化的作用下,形成外硬内实的软体结构(Soft Structure)[8],这种地质特性为居住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开挖并无图纸,但都需经过细致的考察,从下至上,一蹴而就,大空间于下部,逐次递进。内部的岩层依据生活起居的不同需要,进行几何与非几何的互变,墙体也随之形成符合结构逻辑的宽窄变换,完美体现了力学传递的轨迹。与此同时,地形结构操作并未在此终止,其下部具有较硬基质的地质钙化层促发了开挖中所产生的“结构废料”的启示,当地人利用这种天然材料在环绕火山岩周围设置鸽舍、牛棚等辅助用房(图6)。由此,墙体厚度、材料属性、空间需求甚至装饰构造,彼此虽互相叠合,但又相互分化,结构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在地形中的得到统一,一个完整的“社区共同体”诞生了(图7)。它是天空和大地交汇处的洞口艺术,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更是赞颂其为所谓“厚墙模式”[9](第3种墙)回应那些因机械化而陷入标准却毫无人性关怀的冰冷立面。直到如今,这里仍然供给着数万民众,共同构成了直接、真实、自由,且具有“启发性”的地形建构美学。

图4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Fig.4 the “Mountain Meander” by Fan Kuan
然而,地形的隐喻有时却是隐性的。在水域和内陆中,自然地形并未提供直接可供生活的凸出体量,但其原始形态和草木土壤的特性却又进一步在被模仿和深层操作中显现。在内陆旷野之中,对地形结构更深的解读被游牧民族的帐篷这一典型乡土建筑淋漓尽致的体现。其最初形态发自对自然山体结构的模仿和描绘(图8),然而,作为这种基本建构逻辑的表述,具有严格模数机制的杆件成为主要结构系统,划分为不同宽窄度与等级。而帆布、麻布等包裹面,由置入地面下的钉锁斜拉,同时作为围护与表层结构的复合系统,应对了地形中风化和气候的考验,以一种轻触大地的状态语言,展现了其自身和山体之间贴近又疏远的辩证关系,恰又揭示了其中的人的生活状态与大地的关联,重构了一种微地形系统(图9)。正如奥利弗所说,技术的革新实际上产生于地形结构的启示,正如竹子、芦苇等结构性材料进一步在游牧民族中的使用[9]。若干年后,当弗雷·奥拓(Frei Otto)等建筑师对于帐篷结构以及悬索结构的创新时,便不由受此启发。而这一切又是建立在大地深层结构基础上的具体回应与地形结构的再现。

图5 塞尚的《圣维克多山》Fig.5 the “Montagne Sainte-Victoire” by Cezanne

图6 卡帕多西亚住宅的建构体系图示意Fig.6 the tectonic system of Cappadocia dwellings

图7 卡帕多西亚地区全貌Fig.7 the whole view of Cappadocia Area

图8 尼泊尔帐篷地区与山体的关系Fig.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ll and the area of tents in Nepal

图9 帐篷结构的建构逻辑示意Fig.9 the tectonic logic of the structure of tents
3 由地形塑造至垂直向建构诠释
3.1地形/基台塑造
可是地形并未揭示全部,地点并没有成为设计的架构,并非所有的自然地形都如卡帕多西亚,地形只是打开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通过设计和建造得以呈现,这就是“连接”(Articulation)[5]。对于不同自然地形来说,连接的关键,便是基地操作(Site Operation)。如果自然地形物质条件产生“轻”与“重”的分离,这便也暗示了建造体系的区分。正如森佩尔所言的砌体结构(Stereotomic)与构架结构(Skeletonal, Tectonic Form)的思想一样,成就了“基台”和“框架”这一对实体的“分离”,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分离。奥利弗依据乡土聚居的择地特性将乡土地形分为三类原型,即高地(Upland)、水岸(Coastal)和内地/平地(Inland),且以此3类乡土地形来做一次建筑物质构成的基本原型解析。在不同类型的乡土地形作用下,形成自然地形到建筑基台的过渡(图10)。
与其说乡土建筑与不同地形的交接展现的是某种形态,倒不如说展现了某种姿态,即整合土地的给予,而与自身空间的呼应。此时所形成的多个标高,在进一步产生建构关系的时候,对地形则重新定义,有些是“顺从”的,有些则是“抵抗”的。优秀的乡土建筑,便在于架构实体、基台和地形在连接中,产生垂直向度建构表述的完整性和明确性。看似毫无规律的基台塑造,却在由下至上的整个建构表达中阐释着材料建造、自然地形与乡土生活意识的微妙关系。

图10 不同自然地形中“基台”与“架构”的关系原型示意图Fig.10 the different prototyp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und” and “frame” in natural
3.2垂直向的建构诠释
基台和框架这一对要素,它们既可以由清晰的材料分差产生具体的地形回应,从而成为完备的建构体系,也可以随时脱离大地,或者固化在大地中,阐释时间与乡土渊源的恒久。
阿富汗的卡姆代什地区(Masule)(图11),住宅并未选择嵌入且顺从的地形策略,而是通过完整、连续的材料组织体系呈现出清晰的建构逻辑。很显然,努尔斯坦人(Nuristani)并不惧怕危险,这是个有趣的悖论,越是危险却越能彰显地形的可能性和材料建构中的生活意志。平整土地之后,下方的土作重而厚实,由大小石块相互咬合且逐层砌筑。紧接其上,铺设主梁并以石块固定,此时,吻合于生活所需的建造体系进一步被划分出来,砌筑土作转换为层叠式木构架,然而,并非木构架独立承重,而是以粘土填至缝隙中用于混合承重,一方面,土层限定了木头的滑动可能,另一方面,木与土密实连接并与空间内部的木柱形成混合受力的第2层“基台”,在第三层建造体系中,承重木梁转换方向,且变细变密。同时又对应了竖向方位的第3层杆件式围护体系的塑造(图12-13)。不仅如此,这3层材料建造系统在地形条件中分别对应3类等级式生活方式(养殖、贮藏和居住),并完美的反映在立面的开窗逻辑之上(图14)。

图11 卡姆代什地区住宅与地形的关系Fig.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wellings and the topography in Masule

图12 卡姆代什地区住宅建造逻辑Fig.12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dwellings in Masule

图13 卡姆代什地区住宅剖面结构Fig.13 the section of dwellings in Masule

图14 卡姆代什地区住宅立面材料体系Fig.14 the material system of the elevation in Masule
纵观整个由下至上建构体系,石材砌筑系统、木骨泥墙编织系统和木杆件榫卯系统,相互配合,未有掩饰,既反映了建造过程的痕迹和连续性,又紧紧吻合于自然地形系统和架之于不同水平标高的人类生活。
然而,基台也可能是抬升的,并且材料体系甚至是同质的。贝宁的冈维埃地区(Ganvie)水上住宅,并没有隐藏于孤乡僻壤,展现了一种与地形巧妙对抗的姿态(图15)。虽然结构、围护、装饰等要素均严格取自地形中的轻质杆件材料,但并非简单的摆放和堆砌,恰恰其建造和连接无不呼应了地形中的空间方位及所在。垂直层面,架构高出水面旱季标高2~3m,形成夹层空间,应对雨季水面的抬升。当雨季来临时,人们可直接停船入室,而旱季则可将渔船停至夹层之内,以防日晒。由夹层进入上层室内,另一番景象被打开,密制竹栅铺设在架构上,以绳索缠绕固定,四围墙壁形成层叠式三重材料建造体系(外侧木结构、中层竹栅以及内侧棕榈叶),而下层竹材开设细孔洞,与四壁一道,适度隔绝水面湿气并形成内环境风场。由此,结构、材料上的微差与地形的微妙特质相互吻合,进而形成了垂直空间的明晰性(图16-17)。

图15 冈维埃水上住宅Fig.15 the river huts in Ganvie
另一方面,基台和架构这一对实体,则在时间和历史中给予乡土建筑永恒的地形阐述。作为承载不列颠地区沿用至今的长屋(Longhouse)这一基本类型,此种石构建筑系统影响了欧洲乃至美国的大部分地区。从下至上,整个材料体系均由当地花岗岩巨石砌筑而至,似乎已经分不清基台与架构的分别。如果仔细观察,便可发现在整个墙面的不同位置,材料建造都产生于对垂直向建筑要素的不同诠释,角部的厚实砌筑,此时相当于结构部分,而靠近开口位置的石砌形式则被碎石和麻岩所构筑,大、中、小3种开口方式彰显对于石材这种砌筑材料特有属性的描绘。形成由基台部分的厚重至屋顶部分的轻盈所呈现的肌理变化。它仿佛如地形中材料固化后所揭示的某种生活性格,静静的与自然地形中的石块融为一体(图18)。

图16 水上住宅室内Fig.16 the interior of the river huts
当然,可以将此理解为材料的真实与自明。但是反过来想,当地人也可以在表面涂刷或彩饰。这种真实性揭示了一个永恒:当岁月流逝,时间的印记逐步显露在斑驳的石墙上,当崭新退去,只剩遗迹时,方才发现基台固守护着这片与它曾经擦拭而过的土地,在这之后,留下永恒的人类印记(图19)。
4 由自然地形至乡土生活的水平向拓展

图17 水上住宅室内材料Fig.17 the inside materials of river huts
如今,“空间”成了容纳一切的“宝典”。弗兰姆普顿并没有否定空间在建构中的重要性,他意指建构是通过精准的建造再现“空间性”。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从建造的角度定义建筑物,并以“记忆”还原给城市空间[10]。这同样适用于乡村,甚至更加强烈,这是“行为模式”与地形指向的综合空间状态。在卓越的乡土建筑中,这种双重的空间性以人的预谋和需求及时给予意义,地形则随时伴其左右,并准确定位空间的现象存在。19世纪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三角洲(Orinoco Delta)的“空中住宅”为我们展现了这种源自地形艺术的“原始图景”(图20)。此时的结构意义和材料逻辑在建构的作用下,展现了空间中的“地形集结”(Topographical Gathering),空间边界被打破,呈水平状延续,生活与自然并无分野。莱瑟巴罗继续说道:地形给予乡土建构的真正目的应在于使用地形的更高智慧去发掘当地生活的具体化层面,并用空间的多样性和等级性去阐释这种文化在现实中的生活模式。

图18 英格兰长屋住宅Fig.18 the Longhouse in England
4.1地形与生活模式的关联
此时,或许可以想到密斯的吐根哈特住宅和赖特的流水别墅,结构与空间吻合于自身构成逻辑的同时,也呼应地形水平条件的轻与重,带来了生活模式的有机组织。公共部分沿山体外侧,用轻质材料塑造界面敞开的大空间;而私密部分沿山体内侧,并用砖石等砌筑材料形成相对封闭的小空间。这是地形水平延伸给予空间的自我展现,也是在吸收乡土建筑对于地形之中隐含的生活性空间有力的建构回应。然而不同的是,密斯似乎更加直接,那块当时欧洲最大的平板玻璃直接降至地坪,导致室内外关系的决然透明(图21),而赖特则相对委婉,他刻意压低的室内高度和四面伸出的横向平台,有意创造一种模糊未定的中间状态,使人在人工地坪和自然地形间游走(图22)。
这给予一种思考,那就是,乡土建筑依据地形水平向的空间建构中,体现了自然中的物与建筑地点间的某种地形转移。施马索夫(August Schmarsow)将茅屋看作建筑之母。而森佩尔对于“建筑基本动机”的理解延展了他对于人类活动和所谓“功能类型”(Function Types)[1]129的概念。在乡土建构中,这无疑成为联系“炉火”与“基台”的纽带。
森佩尔认为炉火的汇聚同时也是崇拜和亲缘之间联系的“地点”(Place)再现。由此理解下的地形,在结构和材料的物质赋予之后,被激活。此时,地形由自然界引入建筑内部,空间的边界得被模糊。在北非和西非地区,一个丁卡住宅(Dinka Hut)始于一棵树,有趣的是,在这些乡民的语言中,“树”和“房子”是一个意思[2]132。它不过只是一个原型,在逐渐的衍变过程中,经历了茅草顶替代树叶以及木骨泥墙替代树枝,而最后,完整的内院替代了原来的支状结构,家族生活模式变迁,空间分化,地形中的物,化作生活中的抬升与汇聚(图23)。
而这种“空间建构”的概念,在生活尺度上回归于人的精神场所,在水平方向上完成地形结构与材料的统筹。此时,正是“炉火”的引申创造了适合于空间承载的汇聚,节日和事件构成了基本回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具有中心结构的空间形式在世界各地乡土建筑中的普遍存在。而因此,对于院落空间的延展和微观中地形叙述几乎是同时的,并且院落的塑造也和基台的塑造产生同步性。此时,地形再一次转向,在水平向的“生活地坪”中升华了,而以院落为代表的中心空间则成为其象征的核心。

图21 吐根哈特住宅剖面Fig.21 the section of the Tugendhat Villa

图20 奥里诺科三角洲“空中住宅”Fig.20 air dwellings in Orinoco Delta
4.2地形与身体的漫游
人从室外进入室内,往往只注意四壁及屋顶,忽略了脚下。然而人不可能生活在空中,恰恰是忽略了的脚下才构成了地形之于空间建构的“基础”,并由此彰显四壁。此时的地形可被视为材料与表面、结构与隔断、装饰与家具的 “全体集合”(Ensemble)特质的场所。
约翰·伍重(Jorn Utzon)说欧洲的建筑在乎四壁,而东方(中国和日本)的建筑更关注地面。很显然,他指的是基台的塑造。更准确的说,这是一个地形空间的转换和转译,由自然地形至建筑地坪,水平向所展开的综合序列。优秀的乡土建筑总是能够在这种行走关系中准确的阐释乡土建筑的文化根基。

图22 流水别墅剖面Fig.22 the section of Falling Water
回到当代中国,徽州乡土建筑在山水之交的那一丝暧昧中,交汇了空间的奇遇。它常常被视为乡土建筑的“完美标本”,这种建构体系恰恰激活了大地的潜在,并准确回归于人的生活。徽州人对地面/基台的处理显然要比墙面更有力量,且更加到位。在晓起村的老屋中,由外而内,穿过前院,进入室内序列的始端,踏上台基,门槛抬高,地面由外至内微微抬升,此时仪门出现,半隐着室内空间,铺装紧紧跟随,限定每一次步伐所对应的空间状态(图24)。穿过前厅,达到第一个高峰——前天井,地面在天井内降至最低,铺装控制人的进入节奏,铺设吻合四周而呈放射状。由正厅侧门转入后天井,此时空间放大,形成第2个高峰。此时的身体在地形架构中感受空间,并被空间感知。这是结构和材料的跨越,更是吻合于空间中“建造性节奏”(Constructive Rhythm)的平衡。而在阐释地面与序列空间之后,建筑实体又极其丰满的呈现了一个仿佛形式可自成的幻象(图25)。

图23 丁卡住宅由“一棵树”的结构变为合院式布局的演变过程Fig.23 the evolution of Dinka Hut from the tree structure to courtyard
而对于“天井”的理解,更是地形要素的延伸。天井不仅是气候内外调控的节拍,更是地形漫游变奏的关节,恰似一种“扩展了的地形”。在徽州大(公建中的院)、中(中心天井)、小(侧天井)3级天井中(图26-28),空间方位汇集于地面,檐口的侧缘与天井中铺设相吻合,在此处得以扩大,而地形紧随其后,彰显出抬梁结构的轻与青石板路面的重,形成空间中的对比与韵律。此时的二层并没有消隐,但是空间被压缩,檐口压低,日光缓慢的交接在有限的范围内,墙体退后而地形凸显。另一方面,天井空间是物的集结,材料的集结,更是人的集结。它并没有在空间中停止,反而在空间中延展了地形属性。而再现的意义在于,它并不是一些附加于空间中的形状去回应生活中的某种必须,而是在历史和文化中展现地形给予空间的固着与记忆,并以此形成乡土建构的逻辑。人们可以在此看到一线蓝天,也可以在此感受到材料的地形和身体属性的交汇,加之以时间的节奏和天气的变化,地面悄然改变,并成为朝向天空的“立面”。历史穿过了地形,而地形承载了建筑。这种动态与静态的在地交叠,同时汇聚在天井之中,它完美的展现了徽州乡土建构体系的精神内核。
假使森佩尔“饰面”理论的目的在于揭示人类最深的文化情感,那么徽州乡土建筑对于基台及其影响之下的核心序列的塑造则揭示了大地给予他们最深的基因。另一层面,从村落整体来说,乡土建构体系在地形空间维度的展开,也基本是由中心空间从而开启一个个居住单元的建立,而单元又由其“自组织”法则构成了整个有序的村落结构,形成水平与垂直式的综合地形扩展,在这个层面上,构成了具有核心价值的“场所记忆”。
纵观那些典型的乡土建筑,丈量着地形的空间,并且可适时的加快或者放慢空间的“步伐”。此时的空间已经超越了它自身,构成了整个乡土生活的再现。此刻的地形,化作空间的方式存在,浓缩了大地景观的精华。所谓“乡土”的含义,便不言自明了。
5 结语:在乡土建构语境中建立面向“地形”的依托
多年来,学术界对于传统建构学所虚设的“矛盾”一直存在于“建构”到底是在阐释建造中获得自我的表现性收获,还是在承载文化特定内核中建立新的存在秩序。当回到文章开端的两段引文,虚设的建构学似乎缺乏合理的在地依托,“地形”恰是合理的处所与视角之一,甚至有助于建立在“场所”之上真正的乡土关怀。而乡土建构的视野必须准确的定位过去、当下以及预判未来,这一定位需要将“地形”一词进行合理的边界拓展。引申一步,进而探讨何为“乡土建构体系”,它应是在以地形为架构下的核心空间所带来的建造体系的“逻辑呈现”与“文化再现”系统,而材料、工艺、性能、装饰等隐藏在系统背后的第2层在地要素则随时对抗并补充整个体系的闭合性,使其丰满。这个体系既是乡土“建造标本”,更是应对未来“活的建构机制”。它最终指向乡土社会中人的集群,并面向集群中的“身体”。盖瑞特·埃克博(Garrett Eckbo)说道:“人从大地中来,而建筑从人中来”[11]。如此的转换或聚焦,乡土建构的自省性得以彰显,便在于它更倾向于一种态度和意识,修正不加限制的形式与所处特定地区关系的错位,但恰恰肯定人的价值并弘扬生命的诚恳,接纳来自科技与文化的双重给予,建立一个合理而有序的乡土人文环境。

图24 晓起老屋天井序列平面Fig.24 the plan of the Old House in Xiaoqi Village

图25 晓起老屋地形剖面Fig.25 the top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Old House in Xiaoqi Village

图26 潜口曹门厅内院天井Fig.26 the big courtyard of Cao Threshold

图27 呈坎易经馆核心天井Fig.27 the core patio in the Yijing Hall

图28 呈坎易经馆侧院天井Fig.28 the lateral patio in the Yijing Hall
诚然,不能说谨以此乡土世界中这些未经“正统”训练的建造者们的建构文化的匆匆一瞥,便已可能发掘那些逐步陷入快速或矫情中的当代乡村建设之灵感源泉。偶尔回溯,或许更可以看清未来。鲁道夫斯基更是一语中的:“人类的自由,在于他能够以其自身的能力,在地球上选择他想要前往生活的地点。贫困和危险,都无法阻挠人们去选择一个会让他们感到快乐的壮丽景致。”[12]始于地形的乡土建构已经超越建造本身的物态价值,在地形的逐步转向中“延异”着自然与文化的壮美,转而成为记忆和现实美学衡量的尺码,这正是其真正意义所在,它承载了“乡土社会中的人”对于“集体中的土地”的深刻理解。
这就是地形给予乡土建构的潜质,反之,又何尝不是建构驾驭地形的机会呢?特别是在当下所构建基于半工业体系下如火如荼的乡村建筑实践中,或许大有裨益。如果说人类之有形之手在结构、空间、表皮甚至形态上变换着建筑的装束,那么,地形便是那双无形之手,在微差中调节着建筑与人的“分寸”。它默默的潜藏在大地“性格”的深处,随时等待并接纳去唤醒深藏其中那些“人”的文化,激发着留存于乡土气息中永恒的“力”与“美”。
[1] LEATHERBARROW D. The roots of architectural invention: site, enclosure, material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RUDOFSKY B. The Prodigious Builders:notes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ose species that are traditionally neglected downright ignorant[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3] FRAMPTON K.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4] LEATHERBARROW D. Topographical premises[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2004, 57(03): 70-73.
[5] LEATHERBARROW D. Uncommon Ground: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and Topography[M]. Cambrige. The MIT Press, 2001.
[6] 柯林·罗,罗伯特·斯拉茨基. 透明性[M].金秋野, 王又佳,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7] 史永高. 面向身体与地形的建构学[J]. 时代建筑, 2012(02): 70-73.
[8] OLIVER P. Dwellings: The Vernacular House Worldwide[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7.
[9] OLIVER P. Shelter, Sign, and Symbol[M]. New York: Overlook Books 1977.
[10] 阿尔多·罗西. 城市建筑[M]. 黄士钧, 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168.
[11] ECKBO G. The Landscape We See[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9.
[12] RUDOFSKY B.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pedigreed architecture[M]. New York: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69.
图片来源:
图1:引自参考文献[1]
图2,8-9,20,23:RUDOFSKY B. The Prodigious Builders: notes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ose species that are traditionally neglected downright ignorant[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图15-17:Jean-Paul, Trinh T.Minh-ha.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West Africa[M].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图21-22:Werner Blaser. Mies van der Rohe[M]. Germany: Birkhauser Verlag AG, 1997.
图4-5,10-14,23-28:作者绘制、拍摄
(编辑:刘志勇)
The “Aggregation” of the Land—The Tectonic Approach of Topographical Elements in the Field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SHOU Tao, ZHANG Tong, TRUBIANO Franca
From the review and argument of the “Topography” in the “Tectonic” theory, this essa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und” and other three elements in the Gottfried Semper’s theory named “Four Elements”. Then, insofar as the typologic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typical vernacular architectural cases around the world, the research illustrated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nsitions of topographical elements from the practical and spiritual levels and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within tectonic view under the three layers of natural land, mound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interior spaces, trying to establish the research angels and methods of vernacular tectonic system towards the topography.
Topography;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Tectonics; Vernacular Tectonic System; Mound; Construction; Living Norm
TU-021
A
2095-6304(2016)03-0037-08
10.13791/j.cnki.hsfwest.20160306
寿焘, 张彤, 弗兰卡·特鲁比亚诺. 大地“渊薮”——地形要素在乡土建筑中的建构学解读[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31(03): 37-44.
2016-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