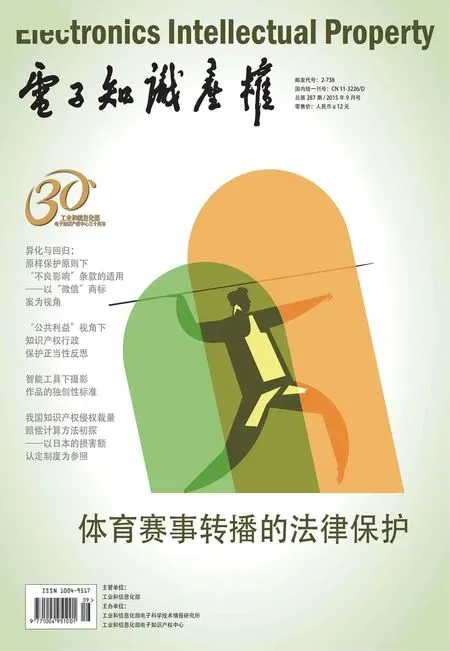版权默示许可的确立与展望——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视角
文/宋戈
版权默示许可的确立与展望——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为视角
文/宋戈
版权默示许可产生于作品委托合同关系之中,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合同关系,受合同规则的规制。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中对作品委托合同中的默示许可予以承认。但随着数字技术性规则的产生及数字行业规则的影响,版权默示许可合同规则的适用面临着困境。对此,应当在合同规则的基础上,探寻与建构新的版权默示许可的适用规则。
版权默示许可;数字环境;合同规则
学术界对于版权默示许可的研究始于2009年,在2011年方正诉宝洁案件中成为热点问题。版权法的发展总是离不开两个问题:一是对多方主体利益进行平衡;二是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前者造就版权默示许可的认定更多依据衡平观念,即公平与正义原则。后者造成版权默示许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与协调。上述两点则决定了我国对于版权默示许可这一命题的立法保守性、司法开拓性、学理谨慎性特征。版权默示许可并非我国著作权法成文的规定,在我国合同法中也难觅踪影,其基础依赖民法的默示行为理论。在2015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送审稿中,版权默示许可在作品委托合同中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
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对默示许可的回应
在2015年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以下简称送审稿)第21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委托作品的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但委托人在约定的使用范围内可以免费使用该作品;当事人没有约定使用范围的,委托人可以在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范围内免费使用该作品。”仔细解读该条款,很难发现其中的许可含义,可是该条将现实中委托合同中未约定的默示许可加以确认,并明确委托合同目的对于版权默示许可的确定的决定性意义。
送审稿对于版权默示许可的规定解决了原有《著作权法》第27条与《合同法》第125条的冲突,将作品委托合同中的默示许可情形予以承认。然而,该条文仅对作品委托合同中的默示许可予以承认,版权许可仍然采取严格的约定主义,缺乏必要的衡平机制对个案公正的补充。依委托合同目的产生的默示许可仅仅是合同对价理论的具体体现,而非合同法衡平精神的完整解读。此外,委托合同固然是版权默示许可认定的基础,然而,数字技术及与其对应的行业规则发展给版权默示许可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
依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7条规定,许可转让合同中未明文记载的权利,合同相对方不得行使。著作权法该强制性规定同我国合同解释规则相冲突,难免会危及个案正义:如《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因此,在我国现有立法框架中,著作权法关于转让与许可的规定多少与合同法解释规则相冲突,也极大限制了版权默示许可规则的构建。应当说《著作权法》第27条重点在于保护版权人的利益,规制版权许可与转让应当采取书面合同,载明许可与转让的权利,以免发生权利冲突。然而从方正字库案件结果中可以看出严格适用该条文会造成个案不公的情形。对于版权许可与转让合同而言,《合同法》第125条包涵的公共利益、公平价值高于片面的著作权保护价值。因此,《著作权法》第27条面临着法益冲突与利益协调的必要。另外,就现阶段而言,尽管著作权法与合同法均为民法单行法,仅就现行《著作权法》第27条而言,其规制内容为版权许可与转让合同,属合同法中应有内容。当其与《合同法》第125条冲突时,著作权法的特殊规定优先于合同法的一般规定。版权独占许可范围严格限于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使用方式也是各国著作权法的普遍立法实践。然而,片面恪守版权法的强制性规定也引起了国外司法界对该实践的反思。在有损个案正义的情况下,合同解释规则成为纠正个案平衡的有益补充。1美国著作权法将版权许可分为独占许可与非独占许可,版权独占许可必须以书面形式做出才具有效力。因此,对于非独占许可,可以默示行为做出。版权默示许可往往是对版权许可合同中推定出的非独占性许可,例如判例Bossey & Hawkes Music Publrs.,Ltd.v.Walt Disney Co.,145 F.3d 481, (2th Cir.1998);Effects Associates.,Inc.v.Cohen,908 F.2d 555, (9th Cir.1990).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行业惯例获得普遍认可,版权默示许可并不一定以合同关系为基础。
二、版权默示许可的确立与合同对价理论
(一)版权默示许可要约承诺规则的误读与澄清
版权默示许可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一种合同行为。默示许可有着深厚的契约法渊源。早在英美古典契约法阶段,合同成立与强制执行需要受诺人行为或明示允诺构成对价为前提,但法律在特定情形中会强加于一种默示义务(Impling an Obligation)来确保一个缺乏双方协商(对价)的债务存在。2刘承韪:《英美契约法的变迁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例如早期的保证行为,双方尽管没有约定保证人替债务人偿还债务后,保证人得以向债务人追偿,但法律会强制附加该默示义务存在。合同说认为:版权默示许可是一种合同义务,即约束权利人不起诉相对方侵权的合同义务。长期以来,受到专利、商标默示许可规则的影响,版权默示许可一直被理解为属合同法范畴之内。早在Effect案中,版权默示许可被认为是法律创制的产物,与其他的默示事实合同(implied-in-fact contract)非常像。根据美国学者Allan Farnsworth的理论:默示事实合同意味着法院查明双方行为构成了生效的要约与承诺,而该要约与承诺效力不以明确存在的表达为必须。3See E.Allan Farnsworth, Contracts 155 & n.2 (2d ed.1990).“经拟制的版权默示非独占许可是一种合同。”4See Lulirama Ltd., Inc.v.Axcess Broadcast Services, Inc.128 F.3d 872,882 C.A.5 (Tex.),1997.因此,在版权默示许可中,尽管双方表达行为缺乏明确的意思表示,但仍可以被理解为要约与承诺。
然而,该说却面临着规则适用的混乱,例如在Effects案中,法院判决并未依照默示事实合同理论中的要约与承诺生效规则进行默示许可认定,而是援引先前的Oddo v.Ries5See Oddo v.Ries,743 F .2d 630,(9th Cir.1984).案的判决规则。而Oddo案却对默示许可如何授权只字未提。Effects案的合同说的解释仍有缺陷之处:此案的混乱之处在于作品载体交付的默示行为产生的默示事实合同与委托合同对价的杂糅,即错误认为交付行为产生了默示合同意义上的要约与承诺。然而事实上该合同的有效对价是委托创作与支付报酬,确保该默示许可可以执行的原因在于双方的委托对价交易。对此,学者Christopher M.Newman指出,脱离合同对价(Consideration)的交付行为构成默示的授权将导致一种荒谬的结果,即使用人没有依照委托合同支付分文,却默示授权他人使用作品,权利人依照委托合同只能请求支付价款,而无法终止(Terminate)该交易。6See Christopher M.Newman,“What Exactly Are You Implying?”: The Elusive Nature Of The Implied Copyright License,32 Cardozo Arts & Ent.L.J.501,510-11.因此,Effects案的版权默示许可脱离了合同法的对价理论。依照合同法对价理论,有效并可强制执行的是作品委托合同中的对价。因此,应当认为在Effects案中,法院是依照合同目的性解释对默示许可进行认定,尽管双方对被告商业性使用未做约定,但被告Cohen对特效镜头的商业性使用与原告获得报酬构成有效对价。因此,尽管原告仅仅获得合同约定一半的报酬,但属于双方变更履行合同,该默示许可仍然成立,并可以执行。相反,如果默示许可认定采取默示行为认定规则,即本案的交付行为,那么在被告严重违约情况下,例如在被告未支付分文的情形下,作品交付给被告,却产生了版权默示许可将造成不公平的后果。因此,交付行为认定的默示许可,排除了权利人因相对方违约而撤销该默示许可的可能性,导致版权默示许可规则的混乱。
也正是上述缘由,在方正诉宝洁案7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终字第5969号。中,法官认为该案的默示许可出自于软件被许可人的合理期待。合理期待本属保险合同中的术语,用以纠正保险格式合同对普通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在本案中,合理期待实质是对价理论的另一种解读。在特定情形下单字的确具有可版权性,然而该案情形又极其特殊,软件的被许可人对于因软件使用产生的字体的正当使用与软件许可费用构成充分的对价。在对价涵盖范围之内的使用行为则视为获得了软件所有人的默示许可。
(二)合同对价理论下的版权默示许可
对价(Consideration)又称约因,为英美契约法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含义为在双方相互交换的允诺构成充分对价的前提下,契约则获得强制执行之效力,亦即,充分有效的对价使得双方的允诺获得法律承认。英美合同法对价理论走过了从英国的获益受损理论到美国的对价交易理论的历程,其理论基础是在双方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保障交易的公平与正义。对价成立的判定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其中主观性决定了对价无须等价,即构成对价的允诺内容在经济价值上无须相等。而客观性则意味着对价须从双方允诺中提取,反映双方缔约时的真实意愿。8王岩川:《英国对价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当代价值》,载《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7月。由此,在英美衡平法中,对价的客观性限制法官对对价的自由裁量的滥用,同时又使得法官拥有足够的权力对双方交易条件的公正性进行判断。对价理论模型从英国损害获益理论到美国对价交易理论发展至今,突破了要约承诺的镜像规则,法院可依据合同关系的具体情况决定合同条款是否公平,从而对个案平衡进行调整。9同注释2,第157-160页。由此,在具体合同案件中,合同条款虽立足于要约承诺规则,却又须接受衡平法公平正义观念的检验。
合同的对价理论对于版权默示许可而言是为了合理分配合同缔约时的预见责任。合理分配合同预见责任是合同自愿原则与公平公正原则相协调的结果。合同法中的公平公正价值与版权法保护作品创作者利益的价值目标是相互平行的,彼此无法取代。对价理论对于版权默示许可的价值在于,对双方当事人缔约时由于理性不足而造成的预见责任分配失衡进行合理纠正。在版权默示许可情形中,合同当事人出于理性不足的状态,合同中的许可范围边界往往无法清晰地界定。若否认该许可范围,则有失个案公正。合同对价范围内的默示许可产生大致如下图所示:

可以说,合同对价范围内的默示许可产生原因是由于双方缔约时未能保持充分的理性,对交易习惯、交易条件等因素未能预见。因合同双方缔约时理性不足无法预见的因素有以下四点:
第一,交易习惯的影响。此处的交易习惯意为传统交易中形成的习惯。例如在委托合同交易中,标的物交付意味着委托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委托人得以自己的意志自由使用该物。作品委托与有体物委托不同,载体交付并不意味着作品著作权变更。在获得广泛接受的交易习惯约束中,作品委托的争议就集中于委托人的使用权限同一般作品接触者权限是否存在区别。作品一般接触者使用作品无疑需要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而作品的委托人由于与作者产生了作品委托的交易,身份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作品接触者。作品委托人以一定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符合交易习惯,也是双方合同对价必备内容之一。同时,为了避免委托人与著作权人的权利冲突,委托人获得的版权默示许可仅仅具有非独占许可的效力。
第二,交易条件的变化。交易条件的变化产生的版权默示许可在Walt Disney案10See Bossey & Hawkes Music Publrs.,Ltd.v.Walt Disney Co.,145 F.3d 481, (2th Cir.1998).中最具代表性。该案中,双方在1939年签订合同,约定迪斯尼公司可以在“motion picture”中以一切方式与媒介使用、发行原告Bossey&Hawkes的音乐作品。90年代之前,双方合同对于“motion picture”中发行的音乐作品仅限于影院表演,而90年代后,CD技术与录像带开始普及。因此,在CD与录像带等视频格式中发行该音乐作品是否需要重新获得原告授权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法院最终认定版权许可合同签订之后,使用人通常会想尽办法来挖掘作品许可利益。因此,使用人有权通过开发新传播技术等新的使用方式拓展作品市场,新技术产生的使用媒介应当属于原合同约定的“一切方式与媒介”,获得原告的默示许可。
第三,变更协议的默许。由于交易属于一种动态过程,版权默示许可往往也会在交易过程中产生变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履行困难、合同条件变化等因素影响,双方常常会就合同的履行发出通知。此时,权利人对通知的沉默表示行为也会使被许可人产生合理期待,因此也可构成默示许可。此类情形大致如下:1.在许可人阻碍合同履行以及被许可人因此采取合理措施挽救损失的情形中,权利人对被许可人的通知的消极沉默产生的默示许可11See McCoy v.Mitsuboshi Cutlery, Inc.67 F.3d 917 (Tex.),1995.在前该案中,原告迟延交货造成被告因货物积压产生的损失,被告向原告多次发出通知提取货物否则即将该货物变卖,而原告始终不予回应,最终被告为合理减少损失而将该货物变卖。法院认为原告对被告多次通知的消极沉默为默示授权被告的变卖行为。;2.权利人对被许可人超出许可合同约定的侵权行为发出通知,未明确阻止被许可人行为的,应视为被许可人取得默示许可。12See De Forest Radio Telephone & Telegraph Co.v.United State,47 S.Ct.367.U.S.(1927).在该案中,原告对被告使用其专利技术的通知,做出通知回应称:尽管使用人侵犯其专利权,但支持(hold)该行为,并表达了与其协商许可条件的意愿。因此,该“不阻止”的通知内容被认为是默示许可被告的使用行为。虽然原告之后将被告起诉至法庭,但法院认为该通知已默示许可原告使用其专利。
合同缔结前,双方应当承担告知、保护等先合同义务,这是合同成立、不被撤销的先决条件。而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应当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合同相对人采取减少损失的版权行使方式应当被认为是可预见的,也是合理的。此类默示许可产生的原因在于,合同的履行包含着双方的期待利益,在一方当事人不适当履行或迟延履行时,另一方发出通知本意为善意地促成交易实现,促进交易效率。当通知人善意勤勉通知之后,相对方未能及时有效回应,此时,将高昂的协商成本强加于通知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因此,出于对交易的保障以及减少损失的目的进行的版权许可也应当视为权利人默许的。
第四,合同约定的许可对价不充分。对价是合同双方为达成交易而彼此交换的允诺。在对价有效、充分的前提下,合同得以获得强制执行的效力。正如传统的交易习惯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在不违背交易目的的前提下,双方对交易条件进行简化,降低交易的协商成本。在合同明确示意的许可范围并未构成充分对价的情形下,应当认为被许可人取得著作权人的默示许可,以纠正合同约定的不足,从而保障交易的公平。合同范畴内的默示许可始终以许可合同为基础,在特殊情形中,如视频分享网站的合同目的即为用户利用运营商的网络服务上传视频,而运营商得以在互联网内非独家传播。数字环境下,除去反映于双方协议中明确约定的对价外,合同中争议的对价应当结合数字行业具体情形,根据双方当事人交易时的主观、客观条件加以确定。
三、版权默示许可的发展与禁止反言规则
随着数字行业的发展,在作品传播效率需求的推动下,版权默示许可所依赖的土壤从合同逐渐转移至数字行业惯例之中。版权默示许可的价值基础也从合理期待转移至合理信赖之上。在此背景下,版权默示许可产生了新的适用基础,即禁止反言规则。禁止反言规则(Estoppel Doctrine)的基本含义是:一方以自己语言或行为做出产生法律意义上的允诺或保证,另一方基于对该允诺的信赖实施某种行为,法院应当禁止允诺方违反先前允诺。禁止反言的正当性在于保护相对方的信赖利益。其最初属于英美证据法范畴,而后,在证据法基础之外产生了衡平禁止反言规则(Equitable Estoppel),它是公平正义的体现,是衡平法与普通法融合的结果,同时也是适用于契约领域中允诺禁止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的雏形。长久以来,英美古典契约法以合同对价(Consideration)作为合同强制执行的效力依据,没有对价,则合同无法强制执行。英美古典契约法重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期待利益。随着缺乏必要对价的无偿允诺的出现,信赖方基于信赖做出行为,允诺方任意反悔而无法强制执行,信赖方因此将遭受损失。为保护受诺人的合理信赖,避免允诺人任意反悔,产生了允诺禁止反言规则(Promissory Estoppel)作为合同对价理论的例外与补充,即对缺乏对价的无偿允诺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以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允诺禁止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在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90条中得以确立,目的在于将“允诺——信赖损失——合同责任”的归责公式作为传统合同中“对价——期待利益损害——合同责任”的补充。13同注释2,第180-181页。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新古典契约法代表人物富勒将合同利益分为:期待利益、信赖利益、履行利益。14See L.L.Fuller, William R.Perdue:The Reliance Interest In Contract Damages(2).46 Yale L.J.373(1936).由此,信赖利益保护的重要性提升。由此,允诺禁止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的适用范围扩大,其涵盖了契约法、侵权法,甚至是侵权法、契约法无法适用的领域。15陈融:《“允诺禁反言”原则研究》,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在普通法中,允诺禁止反言与衡平禁止反言规则逐渐被更具一般性的禁止反言规则(Estoppel Doctrine)所取代。
可以说禁止反言规则是衡平法中公平原则的具体应用,其目的在于保护相对人因默示行为产生的合理信赖利益。因合同条款产生的默示许可,往往还存在合同目的对默示许可范围进行限制,即以满足合同目的实现为限。而在数字环境下,受到行业规则主导,版权默示许可脱离合同束缚。在版权默示许可情形下,禁止反言规则被称为一项激烈的救济途径,它阻却了版权对使用人进行侵权诉讼,同时也导致版权人的权利被摧毁。因此,禁止反言规则应当被谨慎地使用。16See Keane Dealer Services, Inc.v.Harts.968 F.Supp.944,947-48(S.D.N.Y.,1997).这点可从美国司法界公开的数据可以看出,以禁止反言作为案件依据的案件胜诉率不到10%。17同注释2,第188页。因此,禁止反言规则产生的默示许可较合同中的版权默示许可更为苛刻。例如,在谷歌搜索引擎案中,被告方往往需要证明以下事实以获得版权默示许可:
1.原告事先知晓其行为的含义,行为包括特定默示行为、原告的通知、对被告侵权行为默许等;
2.原告有意错误传达其行为的含义,并期待被告依据错误的传递行为实施其他行为;
3.被告因原告默示的行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
4.被告因合理信赖实施行为具备了侵害原告权利的表征。18See Field v.Google Inc.,412 F.Supp.2d 1106(D.Nev.2006).
禁止反言规则适用条件决定了,在满足一定的适用条件下,其仅仅可以作为侵权之诉中获取授权的积极抗辩。因此,在数字环境中,禁止反言规则更加适用于双方并没有合同条款的束缚情况下的版权默示许可。
在版权默示许可与禁止反言规则的关系上,不同法院的认定不同。但多数情况下禁止反言被认为是默示许可认定规则的构成部分,而在某些案件中法院认定默示许可就是依照禁止反言规则形成的许可。19See Minnesota Mining & Mfg.Co.v.Berwick Industries, Inc.532 F.2d 330 (C.A.Pa.,1976);See also General Protecht Group, Inc.v.Leviton Mfg.Co., Inc..651 F.3d 1355,1360(2011).依照美国版权法,独占许可或转让必须依据双方的书面合同。而早期的专利或商标许可也采取书面合同形式。尽管依照传统合同对价理论与合同目的性解释仍然可以解释以Oddo、Cohen案为代表的作品委托创作合同中演绎作品使用的默示许可。但以Field案为代表的数字版权默示许可案中,法院采取的是广义的禁止反言认定,而非合同法中的允诺禁止反言的认定。二者区别在于,广义的禁止反言适用范围更加宽泛,只要一方主体实施法律上的允诺行为,并引起对方的合理信赖,允诺方不得反悔;而允诺禁止反言限定于合同语境之中,以双方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广义禁止反言规则的适用反映了要式书面合同规则对版权默示许可的规制的不足。由此,颁发版权许可无须合同与对价,它完全属权利人的一种单方行为。20See Christopher M.Newman,“What Exactly Are You Implying?”: The Elusive Nature Of The Implied Copyright License,32 Cardozo Arts & Ent.L.J.501,519 (2014).并且允诺禁止反言规则虽然是被作为合同对价责任的例外规定,其本身更是一种对权利人许可行为的举证工具,并且禁止权利人反悔。然而,以Field案为代表的版权默示许可采取禁止反言的四要件证明21(1)原告事先知晓其行为的含义,行为包括特定默示行为、原告的通知、对被告侵权行为默许等;(2)原告有意错误传达其行为的含义,并期待被告依据错误的传递行为实施其他行为;(3)被告因原告默示的行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4)被告因合理信赖实施行为具备了侵害原告权利的表征。,被告得到许可的依据并非基于对原告默示行为的信赖遭受到实际损失。被告在诉讼中往往是面临基于侵权认定的成立,而处于一种不利的法律地位。因此,数字规则下的版权默示许可认定事实上仅仅是采用广义禁止反言(Estoppel)的举证规则,以证明版权人做出许可行为而禁止反悔,适用于数字行业惯例下的版权默示许可。
四、禁止反言规则的版权默示许可适用范围
适用禁止反言规则的版权默示许可一般发生于数字行业之中,受到数字行业惯例的主导,双方对特定行为的含义均拥有足够的共识。在此共识的基础之上,一方的特定行为产生另一方依据行业管例的合理信赖,则产生了版权默示许可。
(一)搜索引擎行业中的默示许可
数字环境下,搜索引擎成为检索海量网络信息的重要工具,因此被喻为“电子信息管理员”。同社交网络相比,搜索引擎行业中的默示许可规则更加隐性一些。这是由于搜索引擎的默示许可是针对网站创始人的,其行业规则相对简单,因此也就没有明确的用户协议加以规制。搜索引擎默示许可的认定是依据权利人未采取排除性技术措施,而将其作品发布至网络。搜索引擎利用机器人在检索网页时候,往往会缓存网页内容或网页缩略图于其服务器中。尽管搜索引擎的缓存构成复制行为,但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合理使用。对于网站创始人而言,其有三种方法避免其网站被搜索引擎检索:
1.使用“非存档元标签代码”限制其网站被搜索的页面范围;
2.采取“Robots排除协议”排除搜索引擎对其整个网站进行搜索;
3.直接请求搜索引擎删除特定内容。
网站创始人若未采取“非存档元标签代码”及“Robots排除协议”等技术措施,则默示许可了搜索引擎对其网站内容进行搜索。因此,搜索引擎的这一默示许可规则也被称为“选择——退出”(Opt-out)机制。
对于搜索引擎而言,既然搜索引擎对网站仅仅是一种信息检索,其必要的缓存虽然构成复制,但是其本身更是一种提升信息浏览速度的技术,其因版权法技术中立原则而免责。22冯晓青、付继存:《著作权法中的复制权研究》,载《法学家》2011年第6期。对于搜索引擎的“缓存”等技术特征,虽然可以合理使用地进行抗辩,但相较于默示许可而言,合理使用的成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合理使用的认定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增加了认定结果的不确定性。以美国Kelly v.Arriba Soft Corp.案23See Kelly v.Arriba Soft Corp.336 F.3d 811.C.A.9 (Cal.), 2003.与Perfect 10 v.Google, Inc.案24See Perfect 10 v.Google, Inc.416 F.Supp.2d 828.C.D.Cal., 2006.为例,对于同样的搜索引擎提供网页图片行为,司法采取了不同的判决态度。Kelly案中搜索引擎缓存复制的低分辨率的转化图片,法院认定缓存图片与原图片具有不同功能,不会对原图片的市场价值产生影响,构成合理使用。而Perfect 10案中认为搜索引擎转换图片的行为构成侵权。原因在于,法院认为谷歌搜索引擎提供缩略图会对Perfect 10版权图片的手机市场产生影响。针对同样搜索引擎的缓存复制行为的侵权认定,在Perfect 10, Inc.v.Amazon.com, Inc.案中又被推翻,因为法院认为搜索引擎转换图片的行为因其让之前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作品,是具有社会价值的。25See Perfect 10, Inc.v.Amazon.com, Inc.508 F.3d 1146,1166.C.A.9 (Cal.), 2007.抛开搜索引擎商是否产生新作品而言,Amazon案的缓存与其说是合理使用,不如说是从保护搜索引擎行业出发而对其缓存正当性的解释。26参见郭威:《版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218页。正是由于合理使用无法为搜索引擎提供完全的免责事由,搜索引擎不尽然是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因此,从默示授权角度来说,搜索引擎行业规则的默示许可构成对合理使用规制之外版权许可的合理解释。
除去对搜索引擎缓存的制度性失灵,合理使用在搜索引擎行业其他方面也面临着不适用的困境。首先,合理使用的认定,受到权利人的主观意图所限。无论是合理使用检验的“三原则”或者美国检验的“四标准”,合理使用均不以权利人主观意图所限。而搜索引擎在网站成立之初即给予权利人“选择——退出”的自由。权利人单纯的沉默则默示许可了搜索引擎对网站内容的检索。因为,默示许可认定的基础是行为人默示行为背后的授权含义。所以,默示许可规则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搜索引擎行业。
其次,数字环境下的信息检索并不是合理使用的事由之一。由于版权法的规定,合理使用被限定在对作品评论、教学科研、新闻报导等,搜索引擎的营利性与合理使用制度相冲突。最后,严格来说合理使用的情形均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因此合理使用的认定需要采取一系列标准,“合理性”的标准是复杂而难以把握的。因此,不同个案的认定存在不同。若采取合理使用作为搜索引擎的积极性抗辩,则与数字行业效率价值目标不符。
(二)社交网络中的默示许可
社交网络(SNS)是数字技术催生的一大新兴行业,包括新浪微博、bbs论坛、facebook、人人网等。社交网络的出现,使得用户可以通过轻松的上传行为,例如上传照片、心情记录等等满足了自己的网络社交需求。社交网络行业的规则类似于链接的默示许可与传播27Eric Schlachter认为:链接并未侵权,因为上传知识产权于互联网的行为授予了对其链接的默示许可;Maureen A.O'Rourke认为:相反在互联网领域,双方是陌生人。此时该默示许可的基础不在于双方任何交流行为,而是被链接方将未加以限制访问的网页上传至网络的行为。,作品上传至“非私密性空间”的默示行为意味着许可被进一步传播。网络作品的访问以网页链接的网址为基础,因此,社交网络的分享实质上是一种链接的分享。Maureen A.O'Rourke认为:网络环境相当于市场,作品上传至网络空间则默示许可他人为私人目的的自由使用。28See Maureen A.O'Rourke“Fencing Cyberspace: Drawing Borders In A Virtual World”82 Minn.L.Rev.609,659-60(1998).社交网络行业默示许可规则主要体现在:用户的上传行为即视为许可免费转载、访问。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作品一经上传至开放性空间,则视为著作权人许可其他用户无限制转载与访问。无论从社交网络运营机制,或是网络用户的主观目的(社交需求)来看,权利人无法就其上传的作品行使著作财产权。权利人仅仅保留了以修改、署名权为代表的著作人身权。由于社交网络低成本的默示许可,许可的类型往往是非独占性的。
社交网络中版权默示许可,其范围与内容应当坚守其依附的社交网络行业惯例,否则案件的处理容易发生偏差。2015年在浙江中院关于郭某与上海茶颜公司、天猫公司的二审案29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浙杭知终字第244号。中,原告郭某在其个人博客中发布其独创性卡通人物歪脖形象,供用户免费下载,并附载声明“供大家免费使用,欢迎关注其微博”等。被告人上海茶颜公司在天猫购物网的客服头像中使用了原告的歪脖形象。被告以版权默示许可进行抗辩,法院审理认为“送给大家使用”以及并未要求报酬的声明使相关公众产生合理信赖,茶颜公司使用行为并不构成版权侵权。此处的合理信赖应当坚守微博行业惯例进行展开,亦即依照微博行业惯例,用户上传作品内容供任何第三人使用是为了获取个人博客的访问量,而非绝对地对其作品版权的放弃。此案中,茶颜公司仅仅将该作品作为客服头像,属于数字网络领域内的使用,可以被微博行业惯例所包容。但假使茶颜公司将该歪脖卡通作品印制成画册进行销售,若脱离数字行业惯例仍然认定该行为取得原告的默示许可,则难免将茶颜公司侵权行为合法化,版权默示许可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也就沦为侵权方剥夺权利人著作权的工具。
五、我国著作权法对版权默示许可的进一步应对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版权默示许可拥有合同与数字行业惯例两个适用前提。因此,我国著作权法的默示许可的进一步应对也应该围绕这两种进路展开。
(一)合同进路规则的应对
首先,明确版权许可的效力类型,并加以区别对待。我国现有著作权法未能明确著作权许可类型的划分,将所有的版权许可类型均“一刀切式”地规定为“合同未经明确约定的使用方式,被许可人不得行使”。该规定严重限制了版权默示许可的存在可能性。因此,应当借鉴美国的做法,将版权许可合同效力划分为独占许可与非独占许可;其次明确版权独占许可的范围应当严格依照书面合同约定的范围确定,而非独占许可不必以书面形式做出。此种立法安排即为非独占性的版权默示许可提供了构建前提,同时也避免了版权许可范围对合同明文约定的僵化固守,危及个案公平。
其次,减少版权合同中约定的强制性与绝对性,引入合同法解释的衡平机制。现有著作权法对于版权许可合同的许可严格限于合同明确约定的范围。这一做法看似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利益,减少著作权侵权行为,而在实际效果中则不适当地阻碍了交易进行或是增加了版权许可合同双方后期发生争议的协商成本。当发生许可范围争议时,原本的交易最终不得不以著作权侵权诉讼而告终。因此,为纠正上述偏差,应当规定:版权许可范围应当依照书面合同确定,当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应当结合合同的对价、目的,或者依照《合同法》第125条处理。
(二)数字行业惯例进路规则的应对
首先,明确版权非独占许可可以数字行业所认可的默示行为做出。正如前述谷歌搜索引擎案中,网站创始人将其网站内容投放至网络未采取任何避免搜索措施则视为对搜索引擎的默示许可。在我国的数字行业中,很多网络服务商均在其服务协议中明确“用户一经上传,则视为许可……非独家使用……”的规则。30如优酷使用协议,参见http://www.youku.com/pub/youku/service/agreement.shtml,2015年5月访问;如新浪微博服务协议,参见http://www.weibo.com/signup/v5/protocol,2015年5月访问。因此,可以考虑将该“上传——版权默示许可”的规则作为一项行业惯例,在网络服务者从事相关类似的网络服务而又无具体使用协议的情形下,作为版权非独占许可的依据。此外,版权默示许可的范围限于该数字行业规则所涵盖的范围,脱离该范围的使用仍需取得权利人的许可。
其次,明确合理的版权默示许可撤销规则。由于版权默示许可在法律制度层面属空白领域。网络行业规则在法律规制不足的前提下可以对版权默示许可做出约束,也应当注意其不合理的条款产生的公平、公正问题。在现行网络行业许可利益分配机制、权利人对运营商使用的控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形下,版权默示许可撤销规则关系到版权默示许可公平公正的关键。数字行业惯例中默示许可属权利人行使其著作财产权的一种方式,而非合同约定的义务。该默示许可有着自身的特点:
第一,授权简便。授权简便是网络行业对传播效率的需求。权利人通过简单的“上传行为”即视为授权服务商广泛的使用、再授权第三方使用的权利。
第二,许可利益分配不明。一方面,行业规则并未对许可利益分配进行规定;另一方面,大多数上传至网络的作品市场价值不高,本身不具有盈利能力或盈利能力有限。而在服务商本身的运营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的现实情况下,针对每一部上传作品建立许可利益分配机制是不可能的。
第三,许可条件不明。行业规则不同于许可合同,许可条件无法进行细化。网络行业是从用户对产品“依赖性”入手,开发衍生产品,从而获取“延迟收益”。衍生产品与服务需要多种方式使用版权作品,其使用结果也带有不可预测性。因此,该默示许可条件也无法进行细化。
考虑其授权方式的上述特点,在原则上不应当对权利人撤销该默示许可做出过多限制。结合数字版权行业默示许可规则前提,该版权默示许可应当遵循任意性撤销为原则,信赖利益保护为例外的规则:
首先,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产生该默示的行业惯例非普遍为行业领域熟知,或权利人有证据证明据以产生默示许可的行为并非权利人本人或经其授权所为,权利人有权单方撤销该默示许可,并通知被许可方;
其次,服务商或第三方已经就默示许可的作品传播、衍生品开发进行额外资金、技术等方面投入的,权利人可与服务商或第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权利人在赔偿运营商损失情况下撤销该默示许可。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spect of Implied License of Copyright under the Third Modification of Copyright Law
The implied license of copyright emerges in the commission contract of copyright works, and is considered as a contract obligation regulated by contract law.The draft of copyright for examination of the third modifi cation confi rmed the existence of implied license of copyright in the commission contract of copyright works.But with the emerging of the digital ru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rules, implied license of copyright under contract law faces some diff i culties.To tackle this problem, we should fi nd some new rules to observe.
Implied license of copyright; Digital environment; Contact rules
宋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