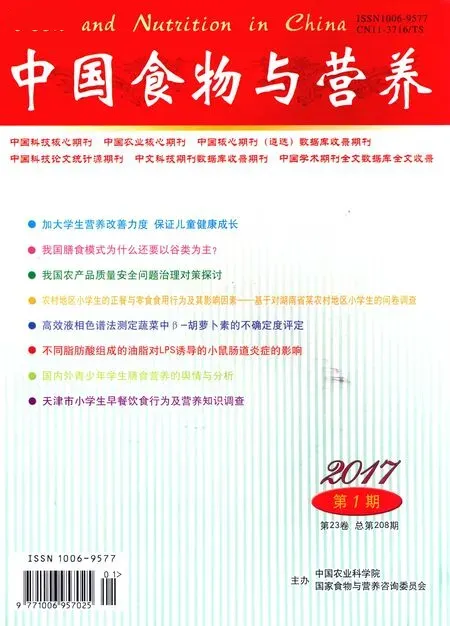贫困县农户食物安全动态变化影响因素研究
程晓宇,张 莉,聂凤英,黄佳琦,毕洁颖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贫困县农户食物安全动态变化影响因素研究
程晓宇,张 莉*,聂凤英*,黄佳琦,毕洁颖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利用陕西、云南、贵州等3省6个贫困县2010年、2015年调研获得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户食物安全的动态变化,结果发现:持续食物不安全农户占6.1%,食物安全水平恶化农户占9.5%;食物不安全更容易出现在患病、户主年龄较大、不积极参与培训、受教育水平偏低的农户中。采用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持续食物不安全以及陷入食物不安全状态的主要原因,结果发现:能力不足、食物营养知识缺乏是导致农户食物不安全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改善农村地区食物安全水平应着力提高精确识别瞄准“精度”,加大教育、培训投入,加大食物营养知识宣传力度。
贫困县;食物安全;动态变化;影响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解决食物不安全问题上取得广泛成功,食物安全总体得到保障,然而,中国仍有许多人口处于贫困和食物不安全中。根据“中国农村食物安全与贫困综合调查”课题组2015年在西部6县的调研,1 368个样本户中,食物不安全农户占比达18.3%,因此解决贫困山区农户食物安全问题仍然是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
研究农户食物安全水平的持续和恶化,能够准确把握其食物不安全的原因。Sen 1981提出的食物权理论认为,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对个体而言,其食物安全水平主要受宏观层面的食物可获得性以及微观层面的食物获取能力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已经基本实现总量上的食物安全,即食物可获得性方面基本得到解决[1],因此食物获取能力不足成为食物不安全的主要原因。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收入是影响农户食物获取能力的关键因素[1-3],其次是家庭规模、农村市场体系、耕地资源、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2、4-5]。此外,有研究发现,对妇女的培训能够显著改善农户的食物安全水平[6]。
以上研究均为静态研究,而贫困地区的食物不安全问题不仅表现为单一年份的食物不安全,许多农户是处于持续的食物不安全中,部分农户甚至由食物安全陷入食物不安全中。因此,基于静态视角来理解与研究食物不安全问题难以准确地界定影响食物安全的因素,不利于制定改善贫困人口食物安全水平的政策。因此,研究食物安全动态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Gundersen 等[7]利用1991—1992年的“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SIPP)数据,分析了影响食物安全的动态因素,发现家庭食物不安全主要是由于收入减少;Ribar and Hamrick[8]基于SIPP数据,采用Logit模型研究了美国食物不安全的原因,发现女性户主、有残疾人的家庭更多陷入食物不安全;高帅[9]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将农村人口食物安全水平划分为食物安全、暂时食物安全、暂时食物不安全和长期食物不安全四类,研究了经济增长、社会地位及生活方式对食物安全的影响。综合来看,目前对贫困地区农户食物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态研究,对于食物安全动态变化的研究较少。
研究贫困地区农户的食物安全动态变化,首先需要界定食物安全的识别方法。Pinstrup-Andersen[10]指出,食物安全意味着在家庭、社区、国家各个层面都拥有足够可利用的食物。因此,食物安全的定义中涵盖食物安全的测量——即什么样的食物水平才是“足够”的。美国农业部[12]认为,食物安全是指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足够的能够保障健康生活的食物。基于此,美国农业部测量食物安全的方法是采用美国“当前人口调查”(CPS)项目问卷中的问题,即通过问卷调查住户的食物数量、食物质量、是否出现紧缺、出现紧缺的应对方法等四个方面判断住户是否处于食物安全状态[11]。基于CPS调查来研究农户的食物安全状态,是一种较为主观的研究方法,可能会由于农户对自身的食物安全状态评价不够准确,导致结果不客观。FCS(Food Consumption Score)法是由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提出的,通过受访者回顾过去一周各种食物的消费频率,计算出家庭的食物消费得分,以此客观地判断家庭的食物安全水平。
为此,本文拟采用FCS法研究食物安全,以更加客观地描述家庭食物安全的动态变化,重点研究持续食物不安全和食物安全状态恶化的原因。基于两时期面板数据,分析贫困地区农户食物安全的动态变化,通过进一步研究贫困地区农户持续食物不安全以及农户陷入食物不安全状态的主要原因,实现对贫困地区食物不安全动因的准确把握,从而为建立更加合理的精准扶贫机制解决贫困地区的食物不安全问题提供借鉴。
1 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食物安全与贫困综合调查”课题组2010、2015年对陕西省镇安县和洛南县、云南省武定县和会泽县、贵州省正安县和盘县进行的入户调研数据。6个样本县从全国592个贫困县中选取1[12],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2010年、2015年分别按比例抽取2,每县19个村、每村12户,样本总量2 736户。本研究对2015年重访的农户食物安全变动状况进行研究,只选择重访的698户,构成两时期面板数据,样本总量为1 396。
样本特征:将农户分为四类:农户2010、2015年均食物不安全的为不安全型,2010年食物不安全但2015食物安全的为改善型,2010年食物安全但2015年食物不安全的为恶化型,2010、2015均食物安全的为安全型。整体来看,698个样本农户中,不安全型农户比重较低,仅占6.1%,安全型农户最多,占74.9%;食物安全发生变化的农户占19.0%,其中恶化型和改善型各占一半(表1)。

表1 贫困县农户食物安全变动状况
Sen[13]的食物权理论认为,家庭的食物获取能力主要表现为家庭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家庭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主要包括家庭特征和家庭所拥有的其他资源。从表2可以看出,食物安全水平低的农户在家庭特征、家庭所拥有的资源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家庭特征方面:(1)户主的年龄较大。安全型农户和改善型农户的户主年龄比恶化型和不安全型农户的年龄小,户主年龄越大其获取食物的能力越差;(2)户主或配偶没有参与培训。户主或配偶积极参与培训,不仅能提升户主或配偶自身的能力,还能帮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提高技能;(3)受教育水平偏低。恶化型农户受教育水平偏低,小学程度占比最高;(4)患病率更高。疾病也是导致食物不安全的主要原因,患慢性病的农户劳动能力受损,食物获取能力下降。资源特征方面:(1)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在许多研究中已经被证明对食物安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3];(2)耕地面积较少。耕地是农户获取食物最主要的资源,食物不安全型农户和恶化型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6、0.095hm2,明显低于改善型和安全型农户。

表2 各类型农户的特征分布
1首先,通过对全国592个贫困县的食物供给能力、食物可获得性、食物利用条件、食物消费与营养的综合分析,挑选出其中食物最不安全的271个贫困县,再从中选出本研究中的6个县,同时兼顾了合作意愿与基础、数据的可获得性[12]。

1.2 变量设定
1.2.1 被解释变量 对贫困农户食物不安全原因的探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因此主要考察农户持续食物不安全及由食物安全陷入食物不安全的原因。以农户的两种食物安全状态“不安全型”和“恶化型”为被解释变量。
1.2.2 解释变量 代表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的变量:主要包括户主基本特征、是否有家庭成员患慢性病、家庭人口规模、是否参加培训、家庭外出务工人数等,这些特征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家庭的食物获取能力。其中,户主基本特征主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户主是家庭中最主要的决策者,户主特征更能反映家庭的食物获取能力。由于本文的食物消费得分分值是由在家的成员回忆过去7天的食物消费情况,因此家庭人口规模只考虑在家成员数。代表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的变量:农户所拥有的资源包括收入、是否借债、是否种植菜园、是否饲养牲畜、是否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等,还包括自然灾害变量,人均耕地面积。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状况;菜园、饲养牲畜能为家庭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食物;贫困山区自然灾害频发,引入了自然灾害变量,考察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食物安全的影响(表3)。

表3 自变量及取值
此外,为研究不同贫困县之间食物安全状况的差异,引入分别代表盘县、正安、武定、会泽、镇安、洛南的虚拟变量,以洛南县为参照组。
1.3 研究方法
从FAO、美国农业部所定义的食物安全来看,食物安全与营养安全之间存在明确的界线[14],食物安全首先是要保证人们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其次才是保证营养。在中国贫困山区,农户的食物安全问题突出表现为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甚至表现为食物消费量不足,因此本研究采用FCS来衡量食物安全状况。
FCS法是根据家庭的食物消费频率,从而计算出家庭的食物消费得分,再根据相应的指标阈值判断家庭的食物安全状况。具体计算公式为式(1):
FCS=∑bi*ai
(1)
式(1)中,FCS表示食物消费得分;bi代表农户过去7天对第i组食物的消费频率;ai代表第i组食物的权重。 食物消费频率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是根据受访者回忆过去7天是否食用过大米、小麦等,若食用过,一天仅食用了一次也按一天计算。权重的设置依据食物的不同类型来定3。FCS>35表示农户食物安全、FCS≤35则表示农户食物不安全。
3其中,谷物和块茎类(大米、玉米、小麦、马铃薯、木薯及各种制品)赋权重为“2”、蔬菜(各种蔬菜)赋权重为“1”、豆类(豆类、豆制品和坚果)赋权重为“3”、水果(各种水果)赋权重为“1”、肉类和水产品(猪肉、牛肉、羊肉、禽肉和水产品)赋权重为“4”、奶类(牛奶及各种奶制品)赋权重为“4”、糖(食糖)赋权重为“0.5”、食用油权重也为“0.5”。
多元Logit模型要求不同被解释变量的取值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而本研究中样本户持续食物不安全与食物安全恶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选用Biprobit模型来估计食物安全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
y2010=x2010β2010+μ2010,y2015=x2015β2015+μ2015
(2)
2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采用Stata14.1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结果显示:rho=0的chi2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相关系数ρ=0的原假设,即两个被解释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关系,表明采用Biprobit较为合理,估计结果见表3。
2.1 恶化型结果
在家成员数、户主婚姻状况、户主或配偶参与培训分别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负向影响,表明在家成员越少、户主未婚、不积极参加培训的农户其食物安全水平更易恶化。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恶化型表现为不显著地负向影响,即外出务工人数越多越能有效改善家庭的食物安全水平。年人均收入对恶化型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年人均收入水平越低,食物安全状况更易恶化。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种菜园都更有可能使家庭的食物安全水平得到改善,而借债、饲养牲畜或家禽、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冲击的农户都更易于陷入食物不安全中。
2.2 不安全型结果
户主年龄对农户持续的食物不安全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年龄大的户主更容易持续食物不安全。在家成员数越多、患慢性病的农户更有可能一直处于食物不安全中。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在家成员更多的是老人、妇女、儿童,其劳动能力较差,食物获取能力较差。相较于未上学,受教育程度达到了大学水平的农户更不易成为不安全型农户。外出务工人数对不安全型表现为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外出务工能够显著地改善家庭的食物安全水平。年人均收入、种菜园的农户对不安全型表现为负向影响,而债务、饲养牲畜、自然灾害表现为正向影响。
2.3 恶化型与安全型综合分析
(1)在恶化型和不安全型估计结果中,参与培训均表现出负向的影响,表明培训能够有效改善家庭的食物安全状况,并且参与培训对恶化型结果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意味着培训能够有效防止家庭由食物安全陷入食物不安全中。通过培训种植、养殖或其他方面的技能,从而提高农民食物获取能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培训,在许多地方已经被证明是改善食物安全状况的有效途径[6]。(2)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食物安全改善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由于在贫困地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还不能通过知识来改善其食物营养状况[2]。这也在不安全型的结果中得到了证明,当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达到大学程度时,持续食物不安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3)外出务工能够有效改善贫困地区的食物安全状况,尤其是对长期处于食物不安全的农户,外出务工人员通过带来外地的饮食习惯、学习城市的食物消费理念,有助于家庭打破长期的食物不安全状况。而对短期内提高家庭食物消费水平的效果不大,意味着外出务工人员并不是通过短期内带回更多的收入,而更可能是带回能够改害家庭食物消费水平的营养知识。(4)低收入是造成家庭食物安全恶化的主要原因,农户可支配收入越低,越缺乏食物获取权[15]。然而,低收入却不是造成家庭持续食物不安全的主要原因,意味着低收入水平对农户食物安全的作用有限[3]。造成贫困地区持续食物不安全的原因更多的是食物消费习惯、营养知识缺乏(表4)。
3 结论及政策含义
3.1 基本结论

表4 各因素对农户食物安全状态变动的影响估计结果
注:*、**、***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并利用Bi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农户食物不安全状态的持续与恶化的原因发现,不积极参与培训、低收入是农户食物安全水平恶化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持续食物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外出务工有利于改善持续食物不安全。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贫困地区食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持续食物不安全农户占6.1%,食物安全水平恶化的农户占9.5%。食物不安全农户往往表现为患病、户主年龄较大、不积极参与培训、受教育水平偏低。第二,能力不足是导致农户食物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培训是改善农民的生产技能,从而提高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而贫困地区培训参与率较低。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制约着农户食物获取能力的提升[2]。第三,食物营养知识缺乏是持续食物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外出务工通过带来城镇的食物消费习惯及食物营养知识,从而能帮助家庭长期改善食物安全水平;而增加收入无法带来食物营养知识,因此收入对改善长期食物安全的作用有限[3]。
3.2 政策含义
第一,农村地区持续食物不安全和食物安全恶化人群占比依然较高,老、弱、病、残等人群食物安全状况较差。解决这部分人群的食物安全问题,一是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时,应切实提高精确识别的瞄准“精度”,综合考虑多个维度贫困状况,制定更加合理的识别政策,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实施精确帮扶;二是应当充分发挥社会救助体系的兜底作用,不仅要充分利用资金救助,还要针对自然灾害、疾病等冲击,采取实物救助和服务救助等多种措施。第二,能力建设是提高食物安全水平的关键。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水平往往较低,缺乏接收信息的能力、生产能力、外出打工技能等,因此一是要继续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的生产能力[11]、认知能力;二是加大贫困地区培训投入,尤其是在精确帮扶过程中,应针对因缺乏能力而贫困的人群实施生产技能培训,实现高效扶贫,并鼓励农民参加多种技能培训,增加收入来源。第三,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食物安全水平,需要从改善其食物营养知识入手。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食物营养知识普遍缺乏,进一步造成食物消费结构水平较为落后。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食物安全营养知识宣传,改善农民膳食结构。◇
[1]朱晶.贫困缺粮地区的粮食消费和食品安全[J].经济学,2003,2(3):701-710.
[2]肖海峰,王祖力.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2):60-75.
[3]王兴稳,樊胜根,陈志钢,等.中国西南贫困山区农户食物安全、健康与公共政策——基于贵州普定县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2(1):43-55.
[4]Guo B. Household assets and food security: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program dynamics[J].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2011,32(1):98-110.
[5]毕洁颖,聂凤英,黄佳琦.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食物安全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6,22(2):5-8.
[6]Wilcox C S,Grutzmacher S,Ramsing R,et al. From the field:Empowering women to improve family food security in Afghanistan[J]. Renew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2015,30(1):15-21.
[7]Gundersen C,Gruber J. The dynamic determinants of food insufficiency[C].Second food security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Food Assistance and Nutrition Research Report,2001,2:11-2.
[8]Ribar D C,Hamrick K S. Dynamics of poverty and food sufficiency. USDA Food Asistance and Nutrition Research Report Number 36.2003.
[9]高帅. 农村人口食物安全测度与动因——基于家庭微观面板数据的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6(2):36-42.
[10]Pinstrup-Andersen P. Food security: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J]. Food Security,2009,1(1):5-7.
[11]Coleman-Jensen A,Gregory C,Singh A.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3[J]. USDA-ERS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2014 (173).
[12]聂凤英,Amit Wadhwa,王蔚菁,等.中国贫困县食物安全与脆弱性分析——基于西部六县的调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10.
[13]Sen A. 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4]Carletto C,et al. Towards better measurement of household food security:Harmonizing indicators and the role of household surveys[J]. Global Food Security,2013,2(1):30-40.
[15]马九杰,张象枢,顾海兵.粮食安全衡量及预警指标体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1(1):154-162.
[16]马晓茹,姜会明. 吉林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2):91-95.
(责任编辑 李婷婷)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ynamics Changes of Food Security in Poor Counties
CHENG Xiao-yu,ZHANG Li,NIE Feng-ying,HUANG Jia-qi,BI Jie-ying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The paper used the rural panel survey data in 2010 and 2015 in six poor counties in Shaanxi,Yun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to analyz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household food securit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ouseholds of continuing food insecurity accounted for 6.1% and the households of food security deterioration accounted for 9.5%.The households’ headers of food insecurity were more likely ill,older,not actively involved in training and low level of education.We applyed Biprobit Model to analyze empirically the factors led to continued food insecurity or food security deterioration of farmers in poor counti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ack of capability and the knowledge of food and nutrition were the main causes of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so we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food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including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pointing “accuracy” of precise identification,increas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vestment and spreading the knowledge of food and nutrition.
poor county;food security;dynamic change;influencing factor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贫困人口粮食安全研究”(项目编号:711732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食品价格波动对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营养安全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71303239);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
程晓宇(1991— ),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食物安全与多维贫困。
*共同通信作者:聂凤英(1963— ),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粮食安全与减贫、畜产品经济、国际情报;张莉(1974— ),女,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信息分析、国际情报。
——以上海市郊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