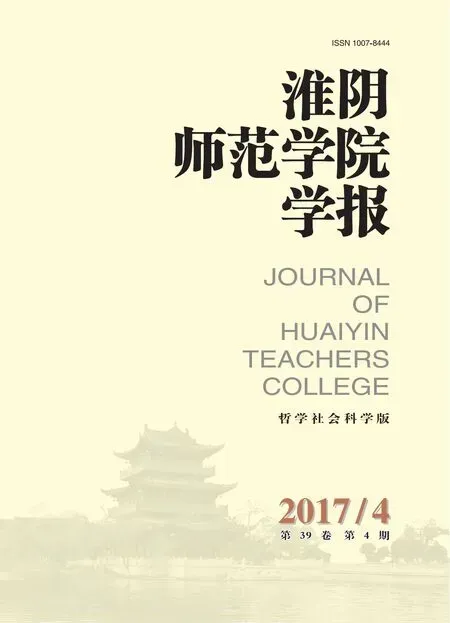《庄子》“重言”辨析
刘 畅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庄子》“重言”辨析
刘 畅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庄子·寓言》篇云“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重言究竟何指,郭象以来,众说纷纭,而以“借重先哲时贤之言”为最常见。依据《庄子》文本,欲准确诠释“重言”,要兼顾三重意涵和四个层面。所谓三重意涵是指:(1)“耆艾,年先”的长者意涵;(2)“明经纬本末”的通达事理意涵;(3)体悟道之本“真”的道本意涵。而这样多重意涵的理解又导致“重言”所倚重、借重的对象有四个维度或层面:一是往圣时贤之言,二是得“道”的普通人之言,三是形残德全之人之言,四是其他借重的对象。虽然这几个层面所借助的对象迥异,但其“重”、其“真”则一。不仅如此,“三重意涵”和“四个层面”的诠释思路还能解释为何要将“重言”读解为“zhong”(重要之重)而非“chong”(重复之重)。据《庄子》本意,重言者,真言也;真言者,体悟道之本真之言也。无论借重的是谁,无论其处于俗世的什么地位,只要他通达了“道之义”,说出了“道之真”,就在“重言十七”的范围之内。
重言;三重意涵;四个层面
一
《庄子》中有两处提到了“重言”: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寓言》)
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
案“重”为多音字,一读为重要之“重”(zhong),一读为重复之“重”(chong)。前者有“所重”“借重”“重要”“德高望重”义涵,后者则有“重复”“反复”之义。在解释何为“重言”的问题上,两种读音均有涉及;而读音不同,则训释各异。
认为应理解为“重”(zhong)言”的,始于郭象,其注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成玄英疏:“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犹十信其七也。”陆德明《经典释文》:“‘重言’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1]830-831曹础基认为:“重言,庄重之言,亦即庄语,是直接论述作者的基本观点的话。……十一与十九对合。九成是借他人之口说的,一成是作者直接论说的。《庄子》一书实际也基本如此。”[2]421陈鼓应先生认为:“重言,就是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3]涂光社先生亦循此说:“所谓‘重言’指德高望重的长者有权威的言论,其论断有分量,可以制止争论。”[4]309-310又:“作者欲借助德高望重先圣时贤有分量的言说来申述思想,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孔子。”[4]634方勇先生也同意:“‘重言’则是借重古代圣贤或是当时名人的话,来止塞天下争辩之言的。”[5]23
认为应理解为“重”(chong)言”的,始于清人,如王夫之《庄子解》云:“乃我所言者,亦重述古人而非己之自立一宗,则虽不喻者无可相谴矣。”清代学者郭庆藩在其《庄子集释》中引用其父郭嵩焘的说法,认为应理解为重复的“重”,其云:“家世父曰:‘重,当为直容切。《广韵》:重,复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郭(指郭象)云世之所重,作柱用切者,误。”近人马叙伦《庄子义证》谓:“重为緟省。《说文》曰:‘緟,增益也’,即‘重复’之‘重’本字。重言者,重说耆老艾之言也。”高亨《庄子今笺》云:“重言者,古人所言我再言之者。”[6]宣英认为“重言”是《庄子》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并说:“‘重言’即引用和反复,是对中国‘记言’传统的承传和创新,是庄子时代理性思维的产物。……对于引用可理解为引用‘重要之言’和‘重要者之言’,也就是指为人所重之言和为人所重者之言两种。笔者认为两者皆可。……按照郭嵩焘、郭庆藩父子的理解,‘重言’应该是‘再三言之’之言,即重复的话语。笔者以为也是非常有道理的。用作‘反复’的‘重言’是为了表达一种强烈的甚至难以言说的感情,或是强调某种观点,庄子使意义或文字完全相同的语句反复地出现,来加深读者的印象,目的是收到一唱三叹的效果。”[5]陈启庆也认为:“我们倾向于把‘重言’作‘重复之言’来理解,当然,所重复的绝非‘古人说过的话’,恰恰重复的是自己说过的话、表达过的意思。只是因为这种重复好比老人说话唠叨重复一般,因此是不带私心成见的,也因此是真诚可信的,而这样的用例在全书中占有十分之七。”[8]
还有一种见解认为应该综合“重(zhong)”言和“重(chong)”言的内涵,涵纳兼容两种说法,如张海就指出:“综上所述,关于‘重言’便有两种说法。一种解释是:‘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及德高望重之人的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一种艺术手法。这种解释以郭象、成玄英等为代表。另一种解释是:‘重言’就是对于某一言辞或思想反复言之,再三强调。这种解释以郭嵩焘父子为代表。通读《庄子》一书,我认为上述两种关于‘重言’的解释都有可取之处。我想,或许‘重言’这种手法本身就包含上述两种解释,用现代修辞手法换言之,则一为‘引用’,二为‘反复’,庄子把这两种修辞手法合二为一,名曰:‘重言’。”[9]
二
除了借重圣贤、倚重权威和重复申论两种解释之外,目前学界对“重言”还有其他几种解释。
一是认为重言是夸张之言。如王运生说:“我以为‘重言’就相当于后来的‘大言’或‘夸张之言’。‘重’有‘增益’的意思,凡是‘增益’语气、‘增益’言语分量、程度的话语就叫‘重言’。亦如今人所谓‘重话’。这样解释应是合乎逻辑、合乎实际的。所谓合乎逻辑,一是字义有据,在义项范围之内,有此字源可凭,是可信的。二是词义切当,把‘重言’看作‘增益语气’的‘夸张之言’理解,与庄子书中对‘重言’的种种说明无不相合。所谓合乎实际,这是指庄子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夸张语言,读者闭目可想,不必举证。此说成立,连‘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比例也就显得自然合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寓言中常常运用夸张语言,这正是庄子文章的特色。”[10]
二是认为重言是引用论证之言。曾昭式说:“其(重言)特征是‘借有见解、有才德之长者或先人的言论来论说’。就其规则而言,即便年长却无才、无德、无做人之道者,其言论亦不能作为论说之论据。……就其作用而言,即如《天下》篇所言‘以重言为真’。此名人名言的论证形式与印度逻辑的‘声量’、‘圣言量’相似;但在形式逻辑里,则犯了‘以人为据’或‘诉诸权威’的错误,因而此‘真’不是形式逻辑之‘真’概念。”并指出了《庄子》“重言”的几种类型:“(1)虚构一个人的言语作为论证之理由;(2)用真人虚构一个事件为论证之理由;(3)用真人真事为论证之理由。”[11]
三是认为重言就是道言。严平说:“重言,是庄子的根本言说方式。重言,以道为本,言道之真,是对道的言说,因此具备使人停止争辩,走出是非迷惑的能力,成为衡量言论的价值标准。荒谬与狂放,是庄子重言的语言风貌,但在这种荒谬之言中,又深深蕴藏着言说者的苦痛。庄子重言,在语言中建构了诗性的精神世界,而这个诗性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从而使庄子重言成为可以栖息心灵的诗性家园。”进而认为庄子用“重言”构建了一种诗性的精神家园——“庄子重言,以道为本,言道之真,是庄子根本的言说方式。庄子重言,以其对自然与生命的深邃回答,以其建构于语言,又只能存在于语言的诗性精神家园,以其荒诞而又深藏痛苦的语言而貌,与寓言、卮言一起,形成了庄子诗性的言说形态,让庄子的哲学通向了生动活泼的诗与艺术的境界”。[12]
四是认为重言是一种“随说随扫”的言说方式。武云清指出:“《庄子》‘重言’的特点和禅宗所说的‘随说随扫’的道理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随说随扫’是禅宗启发人的方法。……佛教和佛学中‘随说随扫’的方法可以自我消解之前陈述的话语,对已有说法进行清扫。这和《庄子》的‘重言’是相通的。能够破除语言的局限性,能够达到‘言无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另外,它否定有固定的、单一的真理,从而使自己不会处于固定的立场,这也是符合庄子表达特点的。”[13]
五是认为重言是由赋中的记言演变而来。徐秀认为:“从众多例证中,我们看到‘赋、比、兴’手法在早于《庄子》的《墨子》《孟子》等诸子的‘重言’篇章中已得到日臻成熟和完善的发展。尤其是《孟子》‘赋’的肆意铺陈,‘比体’‘兴体’的复杂运用已渐成浩大之势,比喻也已发展到它的最高形态——寓言故事。但遗憾的是,《孟子》‘记言’以雄辩显胜,不以铺陈、比兴见长;《墨子》‘记言’抽象晦涩,形象铺写无几。然而在《庄子》之本中,‘重言’不但有了言者的形象,而且所设形象皆是超越现实的,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色彩,言论中采用的‘赋、比、兴’手法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出现了博喻、寓言乃至寓言群,‘重言’几乎完全门!纪实(直笔)演变为艺术虚构(曲笔),真正成为一种以形象阐述抽象哲理的艺术手段。综上所述,‘重言’源于‘赋’中的‘记言’,‘比兴’手法的介入,使‘重言’由不设其他形象的直言陈述演变为形象丰富的婉转言说,因此‘重言’的形成与传统的‘赋、比、兴’紧密相关,有着渊源关系,它的发展对后代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4]王莹也认为“已言”之本意应理解为“记言”,其云:“大多数学者采用‘所以已言也’的说法,即‘已’做‘止,停止’讲,‘用以中止是非之言’。但笔者认同高亨先生的论断,应作‘己言’。‘己’,古纪字。己,正像束丝之绳。乃纪之初文。古者结绳记事,故记谓之纪。此文‘己言’即记言也,通用纪字。’‘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说重言占7/10,是用以记录人言的。形式上近于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所采用的语录体和以师徒、君臣问对为主要形式的《孟子》所采用的对话体。重言与寓言一样,均以‘藉外论之’为手段,是包含在寓言中的一种写法,是指以人物形象为主角的寓言,包括传说历史中的人物及作者虚拟的得道之人和普通百姓。重言借助刻画他人言行而达到‘真实’的效果。”[15]
三
《庄子》为开放、多义的文本,这在上述各家对“重言”的多元解释上也有所表现。应该说,各家训释,均有所本,也均有各自视角,对全面理解《庄子》之“重言”,启发思维,不无助益。本文读音上采取“重(zhong)言”,释义上认为还是应该依据文本,以符庄子“重言”本意。如前,《庄子》中两次提到“重言”,所谓“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寓言》)在此,“耆艾”“年先”“年耆”“先人”等语汇明白无误地将“重言”的语义训释指向了“德高望重”“人重则其言亦重”这一方向,因而,自郭象至陈鼓应诸位先生将其理解为“先哲时贤”是符合庄子原意的。庄子申明倚重或借重先哲时贤的成分占到了全书的十分之七,其目的与多多使用“寓言”是一样的,就是“藉外论之”以“己言”,即倚重权威,以平众议,制止彼此是非的无谓争论。当然,在此“年先”“年耆”并非“重言”的唯一标准,庄子特别提到,重言所依仗的不仅仅是年长,即所谓“耆艾”,而是对揭示事物本质有自己真正独立见解的人,即所谓能明瞭“经纬本末”者,否则就是无用的“陈人”,纵然年长,也不被尊重;顺此逻辑,那么反之,如果确有独见新意,那么年后者也可以发出“重言”。但借重先哲时贤以明己意只是“重言”的第一个层次,庄子在另一处提到“重言”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这里明确说出了“重言”的一个标志:真。据此,也可以理解为“重言”就是“真言”。
于是,根据《庄子》文本提供的信息,“重言”应有三重意涵:一是借重先哲时贤之言。二是能明事物“经纬本末”(即事物本质)之言。三是真言。明于此,则前所引自郭象、成玄英、陆德明乃至于曹础基、陈鼓应等人关于“老人之言”或“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的解释就显得有些单一和欠缺。而且细读《庄子》,单就其第一重意涵(借重先哲时贤之言)而言,也感觉还是有探讨的空间。
如前所述,是否符合“重言”有三重意涵,除第一重“先哲时贤”的意涵之外,还有两个要素:(1)是否有“经纬本末”;(2)是否有“真言”。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是对“重言”的全面理解。
根据“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的文字,庄子明言“重言”的标准不仅局限于“年先”“年耆”者的范围,这是因为虽然是先哲往圣,虽然在时间上先于晚辈,但如果其言无新意,其人就是陈人,其言也就是陈腐而无新意的僵化的语言。而这里判断的标准则是其人是否明瞭于“经纬本末”。曹础基注:“经纬本末,合指道理。”[2]422林希逸注:“无经纬本末:学无所见。”[3]838显然,有“经纬本末”,就是对事物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而不必以年齿、名望、权威为唯一评价标准。
根据“以重言为真”,则“重言”亦可理解为“真言”。但此处之“真”究竟何指,也不无探究余地。有一种解释为“真实”。如成玄英疏:“重,尊老也。……而耆艾之谈,体多真实,寄之他人,其理深广,则鸿蒙、云将、海若之徒是也。”[1]964陈鼓应译“以重言为真”为:“引用重言使人觉得真实。”[3]1018但本书认为,这种解释似有未尽之意。
“真”,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老子》二十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五十四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真,亦是庄子哲学中之重要范畴,在《庄子》中出现66次之多。《齐物论》云:“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达生》云:“不厌其天,不忽其人,民几乎以其真。”《应帝王》云:“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让王》云:“道之真以治身。”等等。
庄子心目中,究竟何为“真”?《渔父》篇提出同样的问题,并给出答案:“孔子瞅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但这种“真”,不仅仅是世俗世界的“真情实感”,更是源于天道自然的根本之真,试看:“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在此,庄子说明了“真”与道的关系——不能“法天”者不知“贵真”,“真”的要义在于“天”。“法天贵真”,简明地揭橥了庄子及道家本体论的宗旨:效法自然,追求本真;真,乃天道的一种表现形态。在此,“真”与“天”,“天”与“真”,浑然一体,难分彼此。曹础基注:“真,真心话。”[2]509颇近庄子之“真”意。效法天道自然,一切以之为准绳,“得道”“知道”,即为真,反之即为假——这就是《庄子》的“真心话”,如《天道》所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与“何谓真?”类似的问句还有“何谓天?”,《秋水》云:“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源于自然,自由自在,天然自放,没有人为的痕迹,就是“天”;反之,人为地去“落马首,穿牛鼻”,束缚自然生物的自由,就是“人”,人为,而在此“人”是违反“天”道的。谨守这一原则而不会违反,就是“反(返)其真”了。于此亦可见“天”“真”之同构、同一的性质。
既然“真”具有与“天”相通的性质,如沉溺于世俗的各种利益、诱惑与欲望之中,就容易迷失方面,“失其本真”,即失去天然、自然的本性。《山木》载: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攫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啐之。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蝉因浓密树叶之利而忘其身,螳螂欲捕蝉而暴露在异鹊的攻击范围内,庄周因贪看上述景观而忘其身,受到“虞人”的责斥……世俗世界中物物相累相害,稍不留意就会“见利而忘其真”也。甚至留恋于人间世的“情”也会迷失,如《大宗师》中庄子与惠子关于人“情”的讨论: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
在此,二人处于“天”与“人”的两种视角。惠子从人(即世俗)的视角出发,认为喜怒哀乐等感情乃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素,而庄子则从“天”(即天道)的视角考察,人的外貌和形体乃源于天,认为过多地流连、牵挂于各种“情”而不能自拔,纯属对于生命本真的损伤和戕害,所谓“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谓“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是也。人的外貌、形体甚至生命都是受之于天,所谓“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生死衰荣,阴晴圆缺,都是天道自然的体现,故不必纠结、沉溺于人间之“情”,于是庄子说了下面的名言:“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还纠结、沉溺在“相濡以沫”的情感中,都是尚未“悟道”“知道”“得道”的表现。
那么,何人可以颖悟大道,效法自然呢?庄子的回答是一系列“真人”,亦称神人、至人、天人、至德者、知道者等,认为他们是最接近“道”之本真或本体者。《秋水》云:“河伯曰: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而所谓“知道者”就是“真人”,这是因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与“何谓真?”“何谓天?”的句式一样,庄子亦有“何谓真人?”之问——对此,《大宗师》答曰:“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忻,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刻意》亦云:“能体纯素,谓之真人。”真人,亦称“至人”。《天下》:“不离于真,谓之至人。”《天运》:“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总之,“真人”系列就是“道”或“自然”的化身,或者说是“道”或“自然”在人身上所体现的最高境界,他们在感官、能力等方面都超越了常人、常识,具有与道同一的性质。
四
通过以上对《庄子》中的“真”及“真人”等范畴的梳理分析,再来看“以重言为真”的意涵,就很好理解了:在此,“真”乃指庄子心目中“道”之本真的境界,甚至,“真”与“道”、与“天”具有同一性。换言之,在此,不妨将“真”理解为“道”或“天”的表现形态。在此,真,即应指“道义”之真。所谓“道义”,即庄子心目中天道之本义,凡是符合其道之本义的,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就是“蔽道”“离道”“悖道”“叛道”的;而“重言”的灵魂就在于“真”,所以才说“重言为真”。如果以“真实”来诠释“真”,也是指“道义”上的“真实”,而不是事实上、物理上、情理上或其他方面的“真实”。所以,重言,就是反映了道之本真的达道之言。
这样来理解“重言”,就可明瞭其意涵但绝不仅仅局限于“借重先哲时贤之言”了。结合《庄子》文本所提到的“耆艾,年先,年耆者”,“经纬本末”,“真(言)”这几个要素,可知所谓“重言”有这样几个层面:
(一)借先哲时贤之言为重,来止塞天下争辩之言。翻阅《庄子》,其中提及黄帝36次、尧64次、舜46次、禹17次,亦可见其“借重”之意。《庄子》中“重言”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其中出现的老聃、黄帝、孔子、颜回之言及一些明贤言论。如《大宗师》所谓的“坐忘”,就是借儒家圣贤孔子和颜回来表达的——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在此,就是借重孔子这位时贤之言,来说明庄子对仁义礼乐的不以为然和批判态度。在此一层面上,要看到:无论庄子借重的对象是谁,其本意都在宣扬道家无为、天道、自然之旨。恰如方勇先生指出的:“但是庄子的实际用意,并不是为了推崇圣哲与名人。虽然庄子有‘齐物论’之心,但却也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借着偶像说自己的话,以避免纠缠于世俗的是非之争。因此,在创作‘重言’时,他时而借重黄帝,时而借重老聃,时而又求助孔子,当然,他们都得披上庄子的外衣,说庄子的话。所以,虚构圣哲与名人的言论在庄子笔下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历史上的人物不够用了,他还会另造出许多“乌有先生”来,让他们谈道说法,互相辩论。例如孔子在《庄子》一书中,就是个形象不定、人格不一的人物:有时被抬得高高在上,满口道家言论,俨然成了另一个庄子;有时又被还原本来面目,让他屡受老聃的教训;而有时又沦落到屡遭痛斥,被冷嘲热讽的地步。”
(二)值得注意的是,庄子所借重的对象并非仅仅局限在先哲时贤的范围内,也常借一些社会中的普通人甚至地位低下之人——如庖丁、木匠、渔父、牧童、佝偻者、畸人,甚至骷髅等——来表达,而这些人的训诫或辩论对象则都是社会上位高权重者,像国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等,粗略浏览,即可列出以下的几组名单:如许由与尧帝(《逍遥游》),庖丁与文惠君(《养生主》),轮扁与齐桓公(《天道》),徐无鬼与武侯(《徐无鬼》),佝偻者与孔子(《达生》),梓庆与鲁候(《达生》),为圃者与子贡(《天地》),渔父与孔子(《渔父》)……在这几组对话关系中,前者都处于社会较低或底层地位,但其所表达的“道”或真理往往使对方——社会地位较高者——一一折服,自愧不如。换言之,在此颇有些“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意味。这种“重言”,充分表现出庄子对于功名利禄、仁义道德的鄙视,及对外在地位低下、形貌丑陋、肢体残缺而内在修养深厚之人的尊重。换言之,其“重”不在于外在的社会地位、权势、财富、形貌,而在于内在的修养及对“至道”之真的体悟。只要达到对“道”的理解和体悟,世俗眼中的至贱至卑者也可以说出“重言”——真实体道、悟道之言。
(三)虚构的身残而德旺之人。《庄子》中还有一种“重言”是借助身体畸形或残缺之人立言,表达对于“道”的理解,此种“重言”集中体现在《德充符》之中。《德充符》共六章,全为身体残缺但内在德性充足之人的训诫之言,如兀者王骀、申屠嘉、叔山无趾、丑人哀骀它等。这些人在庄子笔下,都是形貌有亏但心智道德完善之人,他们都有自己对自然社会的理解,其见解甚至高于孔子及其弟子。孔子,无疑是《庄子》“重言”多次借重的对象,尽管其形象和价值观前后不一。但在《德充符》中,孔子对兀者王骀的评价是:“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如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可见,在庄子笔下,兀者王骀之“重”要在孔子之“重”之上。兀者叔山无趾用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言论一番之后对老聃说:“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皎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认为孔子其人远未达到“至人”的境界,还把桎梏人的名声荣誉等身外无用之物当作宝物,鄙夷贬低之意跃然纸上。又《大宗师》记载子贡向孔子问道,什么是残疾之人(敢问畸人),孔子回答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四)其他借重的对象。由于重言的灵魂在于体道、悟道之“真”,而非年长、声望和文化地位,所以,这种道理由谁说出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言辞的内涵是否触及“道”之真谛。例如在人世间令人恐怖的骷髅,也可以成为“借重”的对象,试看《至乐》的描述: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哓然有形。徼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骷髅,枕而卧。夜半,骷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骷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在此,世俗以生为荣,骷髅以死为乐,因为不再有俗世种种羁绊和困扰,以至于即使有返回人间重生的机会,也被骷髅拒绝了。还有学者认为,于此还可以见出庄子的平等思想:“庄子心目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平等的……在庄子的意识中人们的社会地位无关紧要。个人能达到的精神品味不可限止,超越凡俗精神上获得充分自由的人能‘与造物者游’,‘游于物之初’,‘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品味差别是精神境界的悬隔而非社会等级的区分,体现出一种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人本思想。”[4]706-708
庄子之道,以自然为本,以虚无为宗,明乎此,即使没有语言交流,心灵也会彼此相通,也会说出惊世骇俗的“重言”。《大宗师》描述这样一个故事: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语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求使汝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芄溃痈。夫若然者,又恶乎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子桑户等三人均领悟与“无”为伴,与“无”始终,故心领神会,无须语言沟通。紧接着,子桑户死,孔子派子贡去吊丧,看到完全出乎儒家对丧礼的理解的一幕——孟子反、子琴张二人鼓琴临尸而歌,认为死者已经返璞归真,而我们还滞留于俗世……这就是借助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等人之口所说出的“重言”。子贡不解,复问于孔子,孔子告知:主要是道术不同,他们游于方外,我们还在方内,故难以相互理解。只有忘乎死生、神形等拖累,才能“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这又显然是把孔子道家化,属于以孔子之口来说庄子之语的“重言”了。
要之,纵观《庄子》全书,依据《庄子》文本,欲准确诠释“重言”,需将与其关涉的多重意涵和多层要素综合起来考虑。本文认为,诠释何谓“重言”,要兼顾三重意涵和四个层面。所谓三重意涵是指:(1)“耆艾,年先”的长者要素;(2)“明经纬本末”的通达事理意涵;(3)体悟道之本“真”的道本意涵。只有将其综合考虑,才可窥见“重言”的全貌。其中,第一重意涵给予“重言”借重先哲时贤的依据,第二重意涵给予“重言”辨明事理的特质,而第三重意涵将“重言”所论则聚焦于道之本真的宣扬与辨析。
而这样多重意涵的理解又导致“重言”所倚重、借重的对象有四个维度或层面:一是往圣时贤(如黄帝、老聃、孔子)之言的层面,二是得“道”的普通人(如庖丁、轮扁)之言的层面,三是形残德全之人(如佝偻、兀者)之言的层面,四是其他借重的对象(如骷髅、虚构人物等)的层面。这几个层面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其“重”、其“真”则一,即:无论是谁,无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上,只要领悟了“至道”的妙处,其“德”就高于未领悟者,就在“重言”的范围之内。这样,所谓“重言”就不仅仅局限于自郭象至陈鼓应先生所说的“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的范围之内了。
不仅如此,“三重意涵”和“四个层面”的诠释路径还能解释为何要将“重言”理解为“zhong”(重要之重)而非“chong”(重复之重)。如上述,据《庄子》本意,重言者,真言也;真言者,体悟道之本真之言也。无论借重的是谁,无论借重的对象处于俗世的什么地位乃至于阴间的骷髅,只要他通达了“道之义”,说出了“道之真”,就在“重言十七”的范围之内。而实际上,种种所谓“借重”,如同一个个炫目的木偶,其动作令人眼花缭乱,而其背后的操纵者则是庄子,是庄子借助这一个个“耆艾”“渔父”“兀者”“骷髅”频频立言,“藉外论之”,叙说与申明自己的主张,机锋迭出,新意频现,难见俗见、陈言与重复之语。因而,所谓“重言十七”,只能是“重(zhong)言”,而非“重(chong)言”了。
[1]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涂光社.《庄子》心解[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5] 方勇.庄子学史·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 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J].天中学刊,2007(3).
[7] 宣英.中国“记言”传统的承传与创新:“重言”在庄子中的运用[J].学术交流,2010(10).
[8] 陈启庆.互文见义:《庄子》“重言”新释[J].莆田学院学报,2009(4).
[9] 张海.《庄子》“重言”初探[J].成都师专学报,2000(3).
[10] 王运生.什么是重言、卮言?[J].昆明师专学报,1995(3).
[11] 曾昭式.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J].哲学动态,2015(2).
[12] 严平.道言之真与诗性家园的建构:论庄子的重言言说方式[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6).
[13] 武云清.“随说随扫”与《庄子》的“重言”[J].西北师大学报,2011(6).
[14] 徐秀.解读《庄子》“重言”的诗质语言特色[J].枣庄学院学报,2007(4).
[15] 王莹.关于《庄子》“寓言”“重言”的思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0(4).
责任编辑:刘海宁
地方历史文化
I206.2
A
1007-8444(2017)04-0370-07
2017-02-17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12BZW14)。
刘畅,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