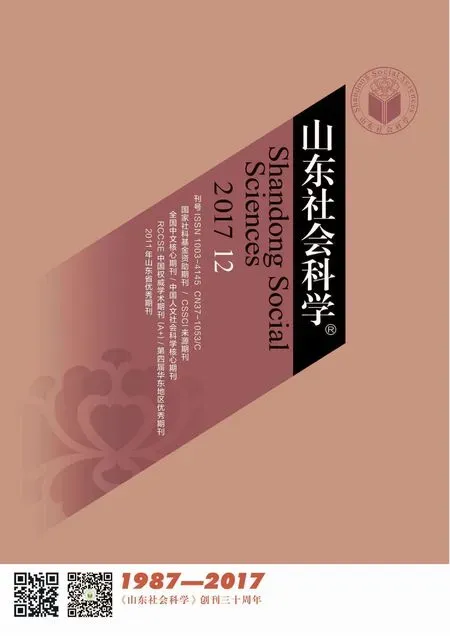自我独白与潜性对话:《伤逝》的叙事话语
王晓恒 姜子华
自我独白与潜性对话:《伤逝》的叙事话语
王晓恒 姜子华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31)
1927年的《伤逝》在现代爱情小说当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鲁迅通过主人公涓生痛苦的追忆和坦诚的心理剖析把爱情悲剧、社会悲剧和女性命运悲剧融合起来思考并同整个时代对话,叙述者涓生的爱情体验和生命体验使得小说极富人性的深刻性与哲理性。《伤逝》中的独白与潜对话是内涵丰富的,涓生的独白中蕴含着三种话语:爱情话语、社会话语和痛苦的自我忏悔的话语,抒情主体与客体、与社会、与自我的潜在对话构成了一种复调性的美学效果,三个层面的意蕴构成对话性文本的召唤结构。尽管在叙述层面涓生是男性独白者,子君是沉默的悲剧女性,但涓生深切的自我反省和灵魂忏悔避免了精英独白式的话语霸权。这种开放性的对话小说正契合了俄国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对话”与“复调”的理论。
《伤逝》;独白;潜对话
《伤逝》因其悲剧之悲与忏悔之痛获得了无数读者的心灵认同。鲁迅带着深刻的社会解放意识与自我反省意识叙述了涓生“谋生”的悲剧和子君“谋爱”的悲剧,使“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爱情叙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我们深思的不仅是唯美主义的爱情主题和深刻的思想,还有它独特的叙述形式及美学意蕴。《伤逝》的叙述方式是没有听众的单向独白,但涓生的痛苦与胆怯分明来自于个体灵魂被道德伦理环境压迫的“他者”处境,他的反省也构成了一个主体的“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对话;而且,爱情回忆虚构了子君形象且形成了两个主体在场的面向“他者”的对话;叙述者的爱情、生命、虚无等等自我否定式的叙述与开放流动的情感也构成了一种可交流的空间情境,读者在这种空间情境中获得感情的潜对话。涓生的幻觉和谋生的艰难都暗示了当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警醒着读者的现实忧患意识,呼唤着他们的思想共鸣。可以说,涓生的这种“丰富的”独白中蕴含着三种话语:爱情话语、社会话语和痛苦的自我忏悔的话语,小说中的抒情主体与客体、与社会、与自我的多重矛盾的言说构成了一种复调性的美学效果。
一、社会话语层面的“生存”艰难与“爱情”反思
首先,小说的独白式叙述中有中国传统伦理意识的时时在场,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气质、精神状态统统纳入涓生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仔细体会,不难发现涓生的个体自我和伦理意识的要求是冲突的。他的生存艰难既是物质性的生存艰难,也是精神性的生存艰难。他和子君追求自由爱情的“叛逆”行为受到旧道德、旧伦理的监督与敌视,一个强大的外在世界使他和她的生存处境、道德处境都十分困窘,“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①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只随文标出页码,不再另注。他们因为自由恋爱被世俗伦理排斥为异类,备受冷眼与讥笑,外在舆论的压迫、伦理的压迫、人群的排斥对涓生所信奉的自由爱情与同居行为的合理性构成了消解,而且陈旧的世俗伦理意识和涓生的自我意识构成了冲突,涓生需要背负的既定的社会角色期待和他的私人情感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文化向来对个人、自由、恋爱持道德贬抑的敌视姿态。在思想的矛盾与痛苦外,更严峻的是物质生活给新家庭造成的窘迫,失业的知识分子如何浪漫?曾经浪漫的爱情在沉闷的家庭中如何维系?社会动荡和个人幸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生存的艰辛和浪漫的理想之间构成冲突,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个体存在困境。这种困境中的孤独感,涓生要比子君更深重。
其次,小说在个人生存的话语之外还有一种普遍的社会关怀,涓生娓娓而谈,痛苦的爱情追忆中透露了知识分子谋生的艰难及其身陷于旧的官僚体制中的精神困境:“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第118页)呆板无趣的工作,如同主人的施舍,不仅不能让他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而且麻痹了他的个性与生命活力,最后就连这样陈腐的工作也因为邻居的暗算而失掉了,涓生日复一日的书信求职都一一落空,经济处境更加窘迫。小说里涓生的生存艰难也暗含了鲁迅深广的社会悲悯,他自己亲身体验了“辛苦恣睢”的生活与人情冷暖,而且也亲眼见证了底层民众在饥荒、疾病和阶级压迫中遭受的摧残,中国苦难的同胞们在死寂而空旷的时空中生死无常、命如草芥,这一切,都给知识分子造成一种国家危机感和生存的焦虑感。涓生在爱情回忆的间隙,幻觉中看到了社会的动荡与民生艰苦:“屋子和读者渐渐消失了,我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子君,——不在近旁。”(第121页)而最后的一句话俨然是在呼唤着精神同盟者的支持。鲁迅对于社会解放的绝望使他想象到了爱情的绝望,对爱人的绝望更衬托了他理性思考后的绝望。他并不相信社会解放理论和人性自由的乌托邦,而且时常质疑“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这种绝望与虚无感时刻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
最后,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消解了当年的爱情神话和“娜拉”解放的神话。“五四”时期的爱情斗争是当年社会解放思潮的主流,觉醒了的青年人以爱情为武器,向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自由和人身自由。自由恋爱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甚至作为人生奋斗的最终目标鼓动了青年人狂热的激情,然而鲁迅却借着涓生的思考,告诉人们爱情需要在实际生存中接受考验。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是涓生说给子君听的,也是鲁迅说给当年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们听的,《伤逝》中的爱情与婚姻脱离了严酷的生活实践,主人公在生存的压力下终于被夺走了精神的自主性,这既是社会时代给个性自由带来的局限,也是人性存在的普遍困境。鲁迅告诫着人们:个体价值并不可以完全拘囿在家庭之中,自由恋爱成功后也要有人生追求,更需要生活伴侣携手同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第121页)涓生的生活难以为继,他连自己都难于保全,如何能为小鸡小狗与妻儿老小负责生计呢?如何能超越现实困境空谈爱情呢?
《伤逝》表达了鲁迅对于女性解放的深刻理解,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解说那位勇敢地冲出丈夫家门的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认为女子要真正地解放,首先要争取到独立的经济权,但当年女性群体在社会上并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伤逝》中的子君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觉悟到要有经济的独立),她的死亡,给被家庭伦理遗弃的女性留下了一个纯洁的结局。涓生和子君的失败,也是对“五四”文学流行一时的爱情神话的一种警示。
作为虚构的文学作品,《伤逝》的读者是不在场的,但是鲁迅的叙述预设了情感宣泄的对象(不仅是追求爱情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包括广大民众),而且成功地传达了自我意识中的社会意识、他者意识和爱情自由的意识。
二、面向“他者”的审美记忆与爱情感受
小说是在审美的情境中完成爱情故事的,开篇到结尾都是以抒情诗一样的语言反复地渲染、沉痛地哀悼,让人感受到单纯而悲怆的情感旋律。涓生的视觉、听觉、幻觉和自述不仅叙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且树立了一个抒情自我形象和一个悲剧女性形象。涓生十分详尽地回忆了恋爱全过程,也袒露了自己的爱情心理:由自由恋爱到同居、由温馨生活到痛苦的谋生、由精神隔膜到最终的“不爱”过程,以及最后子君的死亡……“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第110页)恋爱中的涓生焦急地等待着子君的到来,因为门外的脚步声而感到欣喜,因为自己的错觉而迁怒于邻居:长班的儿子,擦雪花膏的小东西——算什么?涓生持续地追忆曾经的爱情,眼前常常幻化出子君得体的衣着和优美的神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第110页)在涓生真切细腻的叙述中,子君的神态和个性跃然纸上,涓生面前的子君,往往表现出孩子一般的幼稚和向往:“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倾听涓生谈论伊孛生、泰戈尔、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第110页)
子君的爱情给涓生带来安慰与欢欣,如果不是怀着深切的思念,涓生如何把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每一个神态都能记得明明白白?如何能把子君的音容笑貌、思想情感、个性追求描述得如此生动?我们不得不敬佩鲁迅对女性心理与神情的精准描摹,跟随着涓生的回忆,如欣赏电影慢镜头一样看到子君的神态,当涓生把热烈而真诚的爱表达给她的时候,子君的表情十分羞涩而惊异:“但也还仿佛记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第113页)涓生带领着子君反抗封建家庭的阻挠,独自寻觅新居所,终于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温馨的小家庭,子君善良、勤劳的天性也得以施展,她很精心、很热忱地经营着自己并不擅长的家务:“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第116页)子君不顾涓生的劝告,一如既往地忙于家务并乐于温习往事,时而在涓生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中得到快乐,时而在凝神遐想中回味着爱情的欢饮:“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第113页)然而,恰恰是这种一厢情愿的“自修旧课”,让忏悔的涓生感到了自己的薄情寡义。涓生无法忍受日常生活的贫乏与空虚,无法忍受子君失却了“战斗”精神的萎靡状态,在几番徘徊犹豫后终于对她说出自己“不爱”的事实,子君受到打击后悲怆的表情诉说着内心的孤苦无告:“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第124页)子君离开后,涓生并没有真正地轻松自如,也没有走上新的生活道路,面对他们曾经共同居住的破屋,他更加感到人去屋空的破败与凄凉,在得知子君死去的消息后,涓生才意识到爱情在子君生命中的意义,以往那自欺欺人的妄想变成了痛心的醒悟: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子君那为了爱的勇敢和涓生的怯懦构成了对照:“我想到她的死……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第127页)。
在小说的表述层面,涓生是主角、叙述的主体,子君是缺席的、不在场的客体,但子君自始至终在涓生的情感话语中,是曾经与他一同追求爱情的伴侣,是曾经给他带来生命活力的人,叙述过程中主体、客体是相互构成的,缺一不可,因此涓生的爱情回忆中句句都暗含了与子君的对话。最后主人公的自我反省终于回到了故事的起点:子君的离去使破屋里失去了生活的气息,曾经的欢欣变成了现在的阴郁,眼前破旧而黯淡的景象、空空荡荡的屋子、街头人群给亲人送葬的仪式……构成了一个“广大的无爱的人间”的意象。涓生不断地感受到黑夜的幻象和灵魂的悲痛:“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第130页)子君在涓生的记忆中是唯美的、无辜的,美好的事物与美好的生命消逝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叙述者调动了所有的感官体验,通过视觉、听觉、幻觉和回忆营造了悲凉的故事与唯美的情境,这个沉郁悲凉的话语场是开放的,对读者的感情构成了一种召唤结构。
三、虚空的自我体验:生命、爱情与人间的“空虚”
研究《伤逝》的思想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文本中透露的“空虚”意识,作家有意识的灵魂忏悔和爱情回忆透露了哲学的思考和生命存在的感悟,这种自我体验的深度表达更增加了小说的悲剧分量。
涓生一直体验着无处不在的空虚:自由的缺失、爱情的缺失、生存保障的缺失、理想前途的缺失、亲情与友情的断裂和自身文化的虚无。爱情的消逝,不仅是子君的悲哀,也是涓生的悲哀。涓生悲叹于子君背负真实的重担独自前行并在无爱的人间孤独地死去。对文本中的这样一个“他者”,叙述者/鲁迅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空虚体验移植给了子君——子君付出的全部的爱毫无结果;她的爱人弃绝了自己和真挚的爱情;“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变成了空虚,而且诞生在空想中的爱情,脱离了正常的社会情境与物质保障,终究归结为一个空虚;她的亲人——父亲、叔父、涓生对于她是空虚;子君死去了,她的精神和身体都成为了空虚。子君的死,并非出于叙述者的无情,而是一个象征,是一个知识女性精神生命消亡的象征,沉默的子君在沉默中消逝,对整个人间的阴暗和男性文化的冷酷形成了一个控诉,促使涓生反省自己的罪过:“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第127页)通过细读式的文本考察,涓生/鲁迅是在不断地在思索着、质疑着、洞悉着真相,然而这其中的虚妄却包含更忧愤深广、更摄人心魄的个体生命的虚妄和言语的虚妄感。涓生既希望着“新的生路”,又时时预见到“未来”的阴暗与魅惑:新的人生路,像一条灰白的长蛇……《伤逝》中涓生常常使用“虚空”的意象表达痛苦体验,当然也有对未来的幻想,“新生的路”“新生”和“新的希望”等带“新”的词出现了9次,而“虚空”“空虚”的意象有20处之多,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连续地重复使用。这里的空虚感,不仅是由于生存的压迫、物质贫乏的空虚,而且是由于精神于现实无补产生的空虚感,子君沉默的“爱”更使涓生感受到言词的无力,小说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表述:“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即刻发生反响,“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一方面是主人公由于失去了爱情的激励而感到寂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执着的精神探索而产生的心灵孤寂,甚至是心灵孤寂状态中言词表述的空虚。这里的虚空实际上是涓生以面向子君为形式的自我与自我的对话。
叙述者涓生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谎言,由此我们看到鲁迅对社会、人生和生命的执着追问以及这种求索带来的无处不在的矛盾感。涓生的思考,带上了哲学思辨的意味:说谎(对子君重复演习求爱过程)=空虚,真实(停止重复言说对子君的爱)=空虚,说谎+真实(纯粹的爱情解放口号)=空虚!究其实质悲剧的内在原因就是两个人各个层面的爱(无论是单纯热烈的爱、勉强维系的爱,还是悲痛的回忆中的“爱”)都没有建立在正常的生存基础之上,飘移在生活之上的个人主义叛逆和神圣爱情的想象带来的仅仅是短暂的爱情体验,涓生和子君曾经神圣的恋爱同盟终于抵御不过物质的挤压、人群的排斥还有各自性格的弱点而迅速地夭折。这一切,对于依靠着回忆来缓解内心痛苦的当事人无疑也意味着更可怕的精神空虚。
同时,鲁迅的空虚体验中蕴涵着深广的社会悲悯,涓生的孤独落魄和子君生命消逝的悲哀,也被移植到了一切苦难的底层民众身上:“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第128页)死亡成为一种生存状态的暗喻:“死于无爱的人们”是鲁迅面向黑暗的言说、面向死亡的言说,足见其言说的勇气和人间大爱的胸襟。
《伤逝》透露了作者灵魂的自我言说,作者同孤独的自己展开了思想对话,想在悲悼之中确立曾经失落了的自我主体。“谎言,当然也是一个空虚。”小说的结尾竟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表达:“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第130页)这里明确地表达了鲁迅反抗人生绝望与空虚的勇气,因此说,《伤逝》可以成为理解鲁迅思想的一个切入点,“空虚”的思想、“历史中间物”的思想、希望和绝望并存的痛苦体验在《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野草》等同一时期的作品里都有所表达,鲁迅的思想彷徨和对生命的孤独体验使很多作品出现了相似的意境:死亡、欢欣、悲痛、存在、虚无……吕纬甫(《在酒楼上》中的言说者“我”)反省自己的奋斗不过是同“苍蝇”一样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努力寻找弟弟的“尸体”却发现了身体和灵魂的虚无,魏连殳(《孤独者》中的言说者“我”)繁华过后寂寞的死亡也表达了生命的虚无感,这两个孤独者形象也是鲁迅自我的化身,他们和叙述者的对话表达了鲁迅自我批驳的哲学思辩。韩国学者研究《彷徨》集的小说时提出其人物的主体分裂性与对话性,《孤独者》《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篇章中存在明显的对话性质的独白,鲁迅自我否定的意识派生了意识的混乱和颠倒,发展到《伤逝》中竟然出现了独白和独白性质的对话,“看来更为接近于‘自问自答’式的鲁迅自身的‘心思’或‘密语’”①申正浩:《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载《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河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鲁迅自身的“心思”与“密语”给小说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意味。《伤逝》中涓生既痛苦地感受到爱情的可贵,也感受到爱情言论的空虚和自我忏悔的无济于事,而在《野草》(1925—1927)的题辞中鲁迅如此总结自己的生命体验:“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第159页)
鲁迅反省人生,反省自我与爱情,反省生命存在中的一切,《伤逝》这篇沉痛的自我反思之作尤其浸透了丰富的感情内涵,叙述者的自我剖析是勇敢的、冷峻的,简单的爱情故事被蒙上了阴郁的色调,但是鲁迅的阴郁是启示人的阴郁,他的阴郁总是蕴含了广大的人生悲悯。
《伤逝》的叙事性和抒情性结合得十分完美,独白体的形式既完成了叙述故事的功能,也完成了自我抒情的功能,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中它是思想感情内涵最丰富的、最有情绪感染力的。小说中人物心理和叙述的空白给我们一个思考与审视的空间,从叙述姿态上看,《伤逝》比较平和,同当年另一篇比较轰动的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作于1928年)比较可见其差异,后者塑造的“女勇士”莎菲是同涓生相似的个性解放主义者,她傲慢不羁地审视身边的两个求爱者,既追求自己的身体欲望又愤激于男性对女性的玩弄,她的傲慢姿态和意念中的反叛仅仅演变为针对自我的身心斗争,而结果却仅仅是精神上的狂傲,不能改变困窘的女性宿命。①参见王源:《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中的“解构—建构”模式》,《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莎菲过分自我的主体膨胀和叙述的重复单调给读者带来一种威压感,而《伤逝》中涓生的时代苦闷和个性苦闷以及由此生发的伤害弱者的举措引发了深痛的灵魂忏悔,他的忏悔话语也部分地遮蔽了他的过错,使他获得了接受者审美情感上的认同。
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他的对话理论中提倡文学作品内在的对话性和外在的对话性,把文学形象、人物语言、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这些因素同隐含作者的交流看作各自主体性存在的特征,并认为人物的主体性和对话交际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展开的。巴赫金还提出独白体叙述小说中的潜在对话性,即叙述者的独白式陈述中还隐含着另外的叙述主体,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双声语现象”。从文本内部的对话性来看,《伤逝》中的人物独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话;人物反思的内容构成自我的矛盾、自我与他人的矛盾、自我与社会的矛盾,而这种潜在的对话透露的是“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语境,这些互为主体又互相对立的微妙的矛盾关系构成了作品内容丰富、含蓄蕴藉的审美要素。鲁迅并非试图实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但中国文学的诗学传统造就了他的小说潜在的话语意蕴并构成其超越时代的艺术价值。
I206.6
A
1003-4145[2017]12-0079-05
2017-09-19
王晓恒(1975—),女,吉林农安人,文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姜子华(1975—),女,吉林农安人,文学博士,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女性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