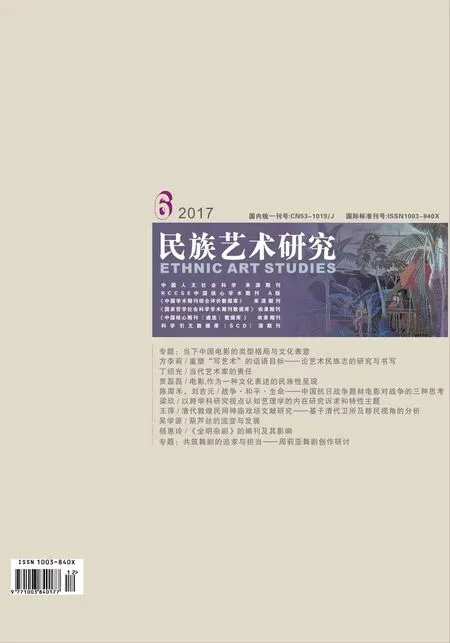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
——论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
方李莉
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
——论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与书写
方李莉
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需要有一系列艺术民族志的撰写,从而提供中国艺术现象所存在的基本事实,以形成共同研究的话题及系列的本土理论,并以此与西方艺术人类学形成平等讨论的话语空间。为此,有关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及书写理论的讨论,就成为当今中国艺术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使命。但由于艺术人类学是一门来自西方的学科,所以,如果要发展中国艺术人类学,还必须要掌握西方艺术人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了解其发展的脉络及其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不同流派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理论。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讨论,我们就很难找到中国艺术人类学在世界艺术人类学领域中的位置及发展坐标。因此,这篇论文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思考中国艺术民族志书写的未来走向,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但文章首先讨论的还是有关来自西方艺术民族志研究的一些相关概念与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找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中有关艺术民族志写作的基准,并以此来讨论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中所遇到的诸种问题。
艺术民族志;艺术人类学;艺术界;后艺术民族志
本文提出的“写艺术”的概念是力图与西方的“写文化”的概念形成相对应的讨论,“写艺术”与“写文化”的不同之处是其聚焦的不是文化而是艺术。 西方“写文化”概念的提出,是力图对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进行反思与批评,但作为中国的研究艺术的人类学者,是否可以站在艺术的角度,对人类学的艺术民族志传统提出一些新的思考,产生一些新的观点,这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而更进一步的思考则是我们如何通过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来展示中国的艺术田野中发生的种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由此讲清楚我们中国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发展的现状。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1](P2)民族志是由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创立的一种关于某个特定民族或文化群体的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对研究对象所在的“田野”知识进行考察、收集,再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知识进行分析、比较与阐释,以获得关于此文化的形态与意义的繁复而细致的知识谱系。[2]而作为艺术民族志也同样如此,只有依据民族志的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有关社会事实中的艺术实践与表达,才有可能勾画出人类艺术的完整风貌。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套中国艺术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与西方对话,或者将中国的艺术历史和发展现状,整体地描述出来贡献给世界的学术界,我们就需要有一系列的艺术民族志的撰写,以提供中国艺术现象所存在的基本事实,形成共同讨论的话题,并涌现出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由此磨炼出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因此,中国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不仅关系到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还关系到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否能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原创性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艺术人类学已形成了一支不小的学术队伍,研究者们分散在各个高校,并涌现了许多艺术民族志的专著与论文。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民族志的理论探讨,以取得共同的话语空间和研究规范,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这也是笔者写这篇论文的初衷。
首先,艺术人类学是一门来自西方的学科,所以,如果要发展中国艺术人类学,首先要掌握西方艺术人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了解其发展的脉络,其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不同流派的主要观点及理论。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讨论,我们就很难找到中国艺术人类学在世界艺术人类学领域中的位置及发展坐标。
因此,虽然这篇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思考中国艺术民族志的未来走向,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但在这之前,笔者首先要讨论的还是有关来自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些相关概念与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找到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者们与西方艺术人类学对话的基准,并以此来讨论中国艺术人类学有关艺术民族志写作中的诸种问题。
一、什么是艺术民族志
(一)有关艺术的概念和定义
人是在概念的定义之中感知这个世界的。[3]因此,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必须要对所要讨论的对象下一个定义,才可以接着往下深入。艺术民族志所要描述的对象是艺术,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艺术下一个定义,才能够讲清楚要研究的相关内容。
当前学界所涉及的最早的,有关艺术的概念是来自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概念是源自于古希腊的艺术模仿论,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再现自然。因此,欧洲最早的艺术史学家瓦萨里在他的著作里认为艺术品的完美性就在于其真实地再现了自然,并认为艺术史的铁律就是从不完善向完善的进化。[4](P33)也就是说,“艺术是现实的模仿”的说法在古希腊就已出现,但再现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则是启蒙思想的产物。从启蒙这个角度出发,康德发展了无功利审美和崇高美学,奠定了西方现代再现艺术理论的基础。[5](P58)进而这种美的艺术(fine art)构成了一个受人尊重的独立学科。[6]同时也使艺术成为脱离日常社会生活的高雅活动,也由此将日常生活中的手艺人的创造性劳动和艺术家们的创造性劳动区分开来,这就是西方现代艺术理论中美学自律和艺术自律的起源。
但是到19世纪,来自人类学家们对不同地域的原住民的考察成果,对西方传统的艺术概念形成了第一次的冲击。在那以前,美学界对艺术的定义是“美的艺术”,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是如何“再现真实的世界”。[5](P16)但当人类学家们从世界不同原始部落收集到的艺术品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大都市的博物馆中得以展示时,西方的艺术家们才领悟到,这种能够逼真再现的艺术与整个世界的艺术相比,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流,艺术不完全是再现,也可以是表现,而且艺术也不仅仅是表现美,还可以表现生活中更多更深刻的文化内涵,有的未必就是美的。
由此,“艺术家们开始向美洲、非洲的原始艺术和东方文明古国的艺术形式学习,美学史家开始重新审定他们老祖宗的言论和著作。”[7](P2)于是,西方学者又开始重新定义什么是艺术,在定义中,美学家们将康德对形式美的论述极力扩展;心理学家则通过艺术形式同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关系中揭示艺术形式的特殊意味,最终,英国学者克莱尔·贝尔得出了“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7]这样的新定义,开启了现代艺术理论的先河。同时,毕加索、马蒂斯、高更等艺术家受到原始部落艺术的影响,创造了现代艺术的新形式。
类似“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样的概念,在人类学里也有,如博厄斯就提出“形式和实践创作的活动是艺术的基本特征。”[8](P4)“艺术的双重源泉:一、仅以形式为基础;二、与形式有关的思维为基础。”[8]克莱尔·贝尔出生于1881年,博厄斯出生于1858年,博厄斯年长贝尔23岁,是否可以认为,人类学界提出的艺术是以形式为基础的理论,对艺术界的新定义也是有所帮助和有所启发的。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及艺术史学家们对艺术的定义,在其从美的艺术进入到形式的艺术,从艺术的再现进入到艺术的表现等新的发展过程中,“不再将艺术视为构造世界的一种方式。”[9](P209)而更多关注的是艺术与心智的关系,这是其与人类学家的最大分歧,也是人类学家始终不敢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目标的原因之一。以下我们可以看看人类学家们是如何定义艺术的。
哈登认为,“艺术(art)可被定义为智力的创造性发挥,顾及实用性或观赏性的制作。”[10](P1)在他的定义里艺术不仅有观赏性还有实用性,实用性就涉及了生活和技术,因此,他认为“研究艺术有两种方法:美学的和科学的。”[10](P257)由此,他认为人类学家是从科学性或人的生物性方面去研究艺术,而把其中表达美的部分和心智的部分,让给艺术史家或美学家去做研究。
莱顿的定义又比哈登的定义更进了一步,他认为“艺术与广义的经济或政治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11](P3)这样的定义不仅使艺术具有实用功能,还具有建构社会秩序和经济制度的功能。面对世界多样性的艺术表达方式,莱顿还认为:“既然现存的艺术传统是如此相异多样,那么关于艺术是什么或艺术不是什么的定义就成了难题。”[11](P5)在这里,莱顿看到了艺术的复杂性,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就能将其概念说清楚。
墨菲的定义就更复杂,他认为,作为一个概念,“艺术”的边界是含混不清的。[12]他还认为,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围绕着艺术观念群,存在着一系列松散而又有关联性的特征或主题。[12]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西方美学界对于艺术的狭隘定义。[12]
由于他提出的对艺术的宽泛定义,以及艺术是一个观念群,甚至是“家族相似”的概念,[12]促使他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即“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艺术生产融入于意义创造过程的整体之中,艺术需要一种形式感,并且艺术与审美经验相关。”[12]他的这一定义非常重要,这里涉及人类学要研究的两个重要的范畴,一个是社会关系,另一个是文化意义。一般来说,欧洲的人类学更注重社会关系的研究,而美国人类学则更注重文化意义的研究,故欧洲常称之为社会人类学,在美国却常称之为文化人类学。而艺术人类学既研究艺术的生产过程及方式,也研究通过艺术生产而表现出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理念,因此,对它的研究可以完整地表达人类学的两个重要方面。也由此,墨菲认为“艺术与知识实体、技术以及表征实践相关,它们可提供对一个社会整体生活的认识。”[13]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艺术,艺术就会很容易地从人类学的边缘性研究领域,进入到中心性的研究领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概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边界,同样,还可以确定我们的研究视角和视野。
当艺术的基本概念确定以后,我们还需要确定艺术的分类,有关这一问题,博厄斯在其原始艺术的专著中,转引了马克斯·弗沃恩的话:“艺术是一种表达感觉过程的功能,这种感觉过程的表达是由艺术家以人们的感官所能看到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他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歌曲、音乐、舞蹈同绘画、雕塑、装饰一样,都是艺术。[8](P5)因此,在他的那本原始艺术的著作里,就包括了这些方面的内容。
传统把绘画、雕塑与音乐、舞蹈、戏曲分开来研究的方法,符合西方艺术史的分类法,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跨文化分析。墨菲认为,视觉艺术*在西方往往把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统称为视觉艺术。常常与其他媒体一样,是一场表演的一个部分,或者,即使视觉艺术是独立出现的,它也就是 (为观众)指引其他媒体中的艺术实践。[13]因此,他认为,人类学必须面向感官世界分类法,虽然这种方法与西方分类并不一致。[13]也因为如此,笔者这篇论文讨论的是广义的艺术概念,其理论可以涵盖以上的所有艺术门类。
(二)有关民族志的概念与定义
当我们讲清楚了人类学范畴中的艺术的概念以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就是:什么是民族志?只有将民族志的概念说清楚了,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讨论什么是艺术民族志的问题。
阿兰·巴纳德认为“田野民族志是关于民族的写作实践。”[14](P4)他的解释是:因为人类学家通常更多地研究异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文化,所以田野民族志常常意味着我们理解其他民族思维模式的方法。[14]民族志学者采用文化维度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行为,并确保这些行为被放置在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中。[15](P1)
这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的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承认不同文化有自己不同的意义正是人类学的可贵之处,人类学之所以要去做田野,要用民族志的形式将自己所理解的异文化以一种知识体系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下来,就是在于其将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为己任,不带任何先见之明,不带任何有色眼镜地去平等地看待任何一个民族和区域的文化,这正是人类学者之所以成为人类学者的基本素养。在西方国家如果你说自己是人类学者,同行一定会问你在什么地方做田野,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唯一标志或关键要素,也正因为如此,做田野、撰写民族志就成了人类学专业的基本训练,也成为每一位人类学者走向成熟的成年礼了。
(三)什么是艺术民族志
当我们确定了人类学有关艺术的定义,同时也理解了人类学民族志的概念以及其对于人类学者的重要性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理解作为艺术人类学者为何要学习撰写艺术民族志,以及回答什么是艺术民族志这样的问题了。顾名思义,所谓的艺术民族志就是撰写“他者”或异文化背景中的艺术现象,艺术行为和艺术作品,以及由这些各种因素形成的社会关系及文化的意义世界。如果说,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1](P8)从而奠定了人类学的研究基石的话,艺术人类学也一样,艺术民族志就是艺术人类学者迈向这一专业研究的起步与入门卷,就像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有自己的田野作为自己研究的试验场一样,艺术人类学家也必须进入一个具体的艺术场域,而获取自己的研究领地。
正因为如此,对于研究艺术理论的学者来说,艺术作品是艺术研究的中心,但对于人类学者来说,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器物本身,而是器物所产生、被看待和被使用的整个语境。[13]并且,必须认识到,艺术是作为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方式而存在的,因此,我们只能在人类行为的各种关系及客观性语境中去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如果我们将围绕着艺术品与生产艺术品相关的纽带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其情感性的属性和意义性的属性就可以和社会的能动性及文化的象征性交叉重合了,也就使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进入了复杂的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了,而艺术民族志则是要将这一系统中的各个部分有效地表现出来。而且要认识到,所有的艺术都内嵌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它们具有文化意义的内容。为了理解这一文化意义的内容,仅仅研究普泛的人类价值和情感是不够的,还需要将艺术置于特定的时空和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16]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田野工作和要撰写艺术民族志的根本原因和理由,因为没有对一个特定文化中的艺术做整体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文化中艺术的根本含义,也不能完全理解在这一文化中艺术所占据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也不能理解在这一文化中,艺术所特有的功能和艺术是以何种形式以及何种方式来表达和象征其文化意义的。
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当代文化中,多数人认为艺术是远离生活的高雅之物,它们是放置于美术馆,出现于音乐、剧场和荧幕上的艺术收藏品或者是艺术的表演曲目、影片等。但在人类学家考察的原始社区中以及偏远的乡村中,艺术是为普通大众所用,是出现于他们的家用器具之上,以及日常的社会集会与各种仪式和节日庆典之中的有用之物。
艺术的有用性,不仅体现在家具、房屋以及各种器具的装饰上,也体现在歌舞、音乐和戏曲中,因为即使歌曲也有不同的功能,如节日婚礼上的欢歌,葬礼上的挽歌,仪式中的舞蹈,以及舞蹈时的伴奏,取悦情人的音乐等等。正如格尔兹指出的:“如果在人们发现的各个地方、各种艺术(如在巴厘人们用钱币来做雕像,在澳大利亚人们在泥土上画画等)确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不能被纳入西方化的艺术程式,即艺术并不是为了诉求于什么普遍的美的感觉。”[17](P155)美国学者丹尼斯·达顿也指出的,“在当下关于跨文化美学的讨论中,一句经常被提到的话是:理解其他民族的艺术可能是困难的、甚或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同于我们的艺术概念’,或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意义上的艺术’。”[18](P278)因此,艺术民族志的撰写就是向人们展示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艺术的特征与差异性,以及由这些差异性所形成的文化整体的表现模式和社会互动的特殊方式。
艺术民族志的撰写意味着人类学不仅可以从宗教、巫术、亲属、性别、法律与经济等问题去考察和描述不同文化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也可以通过艺术的考察从另一个角度去达到这一目的,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在西方世界“艺术人类学已经步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13]而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界也要对此有所反应,因此,讨论如何撰写艺术民族志,也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界目前所需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 西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艺术人类学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因此要讨论艺术民族志就必须要将其放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待,艺术人类学的概念既是一个跨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跨时间的历史产物,因此,要从时间的维度来看待其概念是在如何变化,而且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中国艺术人类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西方艺术人类学不同阶段所解决的问题有哪些重合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我们只有真正读懂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基本研究角度才有可能看清楚今天中国艺术人类学所要走的路、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进行的学科建构是什么?以下笔者将西方艺术人类学分成古典、现代与后现代三个阶段,并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特点。
(一)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艺术作为文化的象征系统很早就被人类学家所关注,但每个时期的人类学家之所以会关注艺术,都是因为艺术可以帮助人类学理解异文化的整体表征问题。不同时期的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式,这些角度和方式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人类学家要解决的宏观问题有关。在古典人类学时代,人类学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是进化的还是传播的?因此,其讨论艺术的问题也是围绕着这两个重大问题来展开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学学科以进化论为范式,当时,达尔文的自然进化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为其提供了解释文化差异性的路径。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些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家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初级”艺术形式是理解西方艺术“复杂性”的可行性开端。持这种观点,并践行这种观点去做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史家是德国的格罗塞,他是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的开山鼻祖之一,也是最早关注到原始艺术,并将艺术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研究的艺术史家。他在其代表性著作《艺术的起源》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艺术科学这样的概念,以示其研究与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的区别,当时没有艺术人类学的概念,今天看起来其探讨的就是最早的艺术人类学所探讨的概念和理论。他在书中提出“艺术科学教给了我们一条看上去似乎没有规律任意的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19](P6)也就是说,艺术科学要研究的是艺术发展过程的法则,而这一研究“要从底层攀起”,[19](P16)也就是说“从野蛮人的许多单调的装饰开始研究。”[19](P16)他认为这一研究,“就等于要解决高等数学问题之前,必须先学会乘法表一样。”[19](P16)他关注到这一问题,是因为他关注到,当时的各大城市都有人种学博物馆,在人种学博物馆里有人类学家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不同的艺术品,是这些艺术品的出现和存在,让西方世界开始了最早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讨论艺术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则是哈登,他认为,“高度文明社会的艺术表现形式非常复杂,要完全理解它,是一项非常困难甚至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10](P1)因此,“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问题简化到最简因子,在研究更复杂的领域之前先研究它的最简因子。”[10](P1)在他看来,艺术中的最简因子就是“蒙昧艺术(savage art)”。[10](P1)但他是一位人类学家,因此,他对原始艺术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是有别于格罗塞的,而且他不仅是一位人类学家,还具有动物学家、海洋学家的身份,这种身份使他更接近科学家,而不是艺术史家。因此,他认为,研究艺术有两种类别:美学的和科学的。艺术的美学研究最好交给专门的艺术评论家,而他追求的是一种物理学和生物学式的科学研究。[20](P306)其次,1898年,由他带领的剑桥托雷斯海峡探险队开系谱学研究方法的先河,摸索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技巧,是最早走向人类学田野考察的一支探险队。如果说,格罗塞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材料是来自当时的人种学博物馆,其研究是没有地域限定的广泛的研究。而哈登则不完全赞成这样的研究方法,他说,“要先简要地描述某个特定地区的装饰艺术,而不是满世界随机抽选装饰样本。”[10](P1)“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同样的图案很有可能在起源上具有某种联系。”[10](P1)即:他认为,如果将艺术放在某个特定的地域来做深入的研究,可以更能有效地研究其生理机制和变化的规律,就像在显微镜下做研究一样,比起那些浮在表面的,大而化之的研究更能说明问题,其在这里凸显了人类学的研究特点。
当然,因为他不关注当时美学界和艺术界的研究,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他所认为的写实的欧洲艺术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层级时,欧洲的艺术家们却开始打破了这一再现的、写实的模式,向抽象的、表现性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发展的最初原动力却是来自于原始艺术的启示。
古典人类学的另一个角度就是从传播论来讨论艺术的起源和分布问题,人类学传播论中最具典型性的学者代表应该是拉策尔、莱奥·弗罗贝纽斯、史密斯等,但继承这一传统并将其运用到原始艺术研究中的代表性人物则是博厄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他所完成的《原始艺术》。他对造型艺术的研究和哈登一样,主要是着眼于装饰纹样和图案的研究,他认为,其研究的任务就是去“努力查明各种纹饰的分布情况和不同部落对于相同的纹饰是如何理解的。”[8](P109)其目的是为了“去探究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及无法用考古学证明其发展的某些民族文化的部分历史发展过程。”[8](P109)同时通过这样的研究,“即可相当准确地探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传播的。”[8](P109)那样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人类学所有的研究都是受自然科学影响的,所以,博厄斯提出,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生物学家研究动、植物分布的逐渐发展的方法极为相似。”[8](P109)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艺术研究不同的文化区域是如何形成和如何分布的,所以,他认为,艺术研究的“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地理的方法。”[8](P9)正因为这样的方法,在人类学的领域里形成了文化类型、文化圈、文化区、文化模式等概念。
另外,博厄斯是历史特殊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为了进行这样的“历史的分析,首先要把具体问题看成是一个单位,然后再逐步弄清楚它在发展为现状以前的来龙去脉。”[8](P8)而这样的来龙去脉,需要有可视性的象征符号来标识,因此,博厄斯研究艺术的目的,主要是研究其中的文化因素,而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正如弗斯所说的,“艺术中包含的文化因素使人类学家进入这一领域。”同时“人类学家将原始艺术视为一种文化材料”[16],当然这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材料。也正因为这样的因素,博厄斯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各个民族在创造的象征符号和对象征符号做出的各种解释。”[8](P9)这些可供解释的象征符号,即艺术品都具有各自的风格,而正是在这种风格的基础之上才促进了各种艺术的发展。因此,研究艺术风格,关注艺术的形式和图案,是传播学派所研究主要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古典主义学派,无论是进化论学派,还是传播论学派,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本身,对于制作作品的人,以及作品与人的互动,还有围绕着作品产生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关注是不多的。
(二) 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如果说,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人类学在时间的节点上,主要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而笔者在这里所提的现代主义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时的人类学界,由于受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结构功能主义和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们想为人类学创立一个空间,使其有别于其他周围学科,为此而创立了以社会组织共时研究和社会结构比较研究为中心的人类学。这样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式使欧洲的人类学界疏离了历史学和心理学。同时,处于某种对美国人类学发展趋势的回应,也使欧洲的人类学界疏离了文化,而产生了社会人类学的概念。同时,艺术至上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形态也严重限制了人类学家对土著艺术的阐释,它反映了西方社会某个特定阶层的普遍见解,而大多数人类学家正属于这一阶层。正因为如此,人类学家仍普遍视艺术为一种人工制品范畴。[8](P9)由于这些诸种原因,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处于一种低潮状态。
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们对艺术的兴趣开始复兴。这种复兴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学研究工作内容的转变;二是西方艺术创作和西方艺术理论潮流更倾向于艺术人类学思想。[13]也就是说,人类学之所以关注艺术,主要是因为其从关注亲属关系、宗教、经济等开始集中于关注地方性意义和价值。
这一转变使得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受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的理念影响很深,涂尔干相信;“民族乃是人群的集合,一伙人很容易被集体情感所支配而充满了每个参与者的情绪,这与‘他’或者‘她’个人单独时的感受很不一样。”[11](P30)这种感受能形成一种集体力量,这种集体力量会强制和命令众多的个体共同产生一种持久意识,也就是一种集体意识。而这种集体意识,往往是通过“象征”来表达的,“这种‘象征’是通过图腾所提供的。”[11](P39)在这里对于土著艺术和图案的认识就不再仅仅是形式和风格,或者文化类型的认识,而是作为一种社群关系的象征物的认识,是集体意识公共符号的表达。如莱顿认为,艺术作品可能代表了若干不同程度的文化的特征。[11](P36)通过这些艺术品所刻画出的表现形式,往往不会超出其群体共有的想象力,而这共有的想象力构成了社群共同体的种种仪式的表达,其中包括了不同类型的艺术表现形式。
有关这一时期的艺术人类学讨论,在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一书中最为深入。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可以说是西方的第一本艺术人类学专著,博厄斯、哈登等人类学家虽然都从人类学的角度讨论艺术,但将艺术人类学作为一种概念,并完成为一本专著的是莱顿的这部《艺术人类学》。这部书成于20世纪80年代,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人类学家完成了艺术民族志的写作,如完成于1966年的贝蒂的《仪式与社会变迁》,完成于1973年的比巴克的《莱加人——艺术、创新与道德哲学》,完成于1960年的W福尔曼的《贝宁艺术》,完成于1965年的J.A.W福吉的《塞皮克地区的艺术与社会》和完成于1967年的《贝兰艺术家》,H.科尔编于1972年的《非洲艺术与领导权》等等,通过这些众多的艺术民族志,莱顿结合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田野考察,完成了其《艺术人类学》的写作。从这样的角度看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发端于古典主义时期,而成熟于现代主义时期,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大量艺术民族志的完成,再就是莱顿的这部《艺术人类学》著作的完成。
在这部著作中,莱顿不再将艺术纳入到科学规律中去研究,在书中,他引用了贝蒂的看法,“神话将宇宙戏剧化,科学分析则宇宙。”[11](P42)从而认为,“宗教前提不是建立在科学可控的假定性试验,而是建立在隐喻和戏剧的基础上。”[11](P43)而这种隐喻和戏剧往往是通过仪式来表达的,因此仪式比宗教提出了更大量的知性问题。其让我们更加容易地鉴赏我们周围世界的意识、道德存在的视觉特征和力量的戏剧性效果,而这些效果都是通过各种艺术符号的呈现和表演才达到的。
在这一阶段对艺术人类学影响较大的还有索绪尔的语言学,其认为,语言是一种集合现象,它是集合体的一种特征,而且只有凭借集合体才能存在。[11](P111)也就是说,索绪尔把语言确定为来自整套符号的选择,并且它们绞合在一起形成信息。人类学家们也倾向将艺术看成是一种语言符号,而这种语言符号构成了一个自身的交流系统,其和语言一样,有自己的各种可以组合的要素,并“以根据各种具体规则排列的相当少的要素表达了非常多的复杂意识。”[11](P115)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人类学家们看到的是,在许多土著民族生活中,文化浸染了用意义制造或使用的每个物体的外表,而这种文化的意义正是通过艺术的语言给不断地表达出来的。列维-斯特劳斯把这看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社会的特点,他写道:“每种人工制品、甚至是最实用的物品都是一种不仅对于制造者,而且对于使用者可理解的具体化的符号。”[11](P125)
人类学家通过研究还看到,人类所有的文化意图,无一不是通过艺术的语言与符号来表达的,甚至人们穿的衣服、人们所用的用具,都在说明人们不同的社会级别、人们所希望遇到的社会条件等等。
特纳通过他对恩登布人仪式的田野考察,提出了一个“情境关系”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他认为,最重要的仪式象征是一些分离的意识的组合,其范围包括从社会秩序的意识的概念到身体功能的感觉概念。而这些概念所形成的交流系统,需要放到一个具体的情境关系中去理解。因为任何其他艺术形式,包括自我装饰,都带有自己特殊的象征符号,传递着不能用其他媒介准确重复的信息。 也就是如德里高斯基所说的“高度程式化的艺术,离开其特殊的文化不可能被理解。”[11](P176)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有其特殊的语言符号,并由此形成了她自己的语言体系,而人类学家去做田野,写艺术民族志的目的,就是去读懂这套语言体系,并建构和理解这套语言体系背后的语法。
尽管有学者认为,在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之前,欧洲人类学界有研究土著民族艺术的传统,但在这之后,欧洲人类学界有关土著艺术的研究被削弱了。但我们又要看到,兴起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艺术民族志田野的写作无一不是受到马氏田野民族志方法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写道,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目标在于“理解土著的观点以及他们与生活的关系,并认识他们对世界的愿景”[21]和这些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学者的目的和想法一样,他们到土著民族去研究当地人的艺术,也是希望将其艺术还原到其具体的社会情境和意义世界中去,理解他们艺术的真正含义。
在这一阶段艺术能够引起不少人类学家关注的原因,还在于其既被“看成是对世界的主题进行编码的意义系统”,又可以看成是“意图改变世界的行为系统,由艺术作品所激起的兴奋之情就存在于二者的交互作用中。”[22](P42-69)也就是说,通过艺术既可以研究其文化所构成的意义世界,也可以研究由于艺术行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其填平了人类学界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之间的沟壑。
(三)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后现代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缘起于20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那样的年代正是全球化概念开始得以风靡学界的年代。长期以来,人类学考察的土著社会,尽管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考察的目标却仍然是按社会被殖民前的样子重建的。长期以来,许多人类学家都在忽视社会的变革, 对于导致社会变革的种种外来因素,许多人类学家“常常是从一个不利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所研究的社会的外生事物,而非社会全面参与的一个过程。”[13]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产生的全球化概念,让当代人类学家就再也无法找到前辈界定的研究主题。人类学家们开始观察到,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场脱离传统文化概念的发展方式,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化不再存在具体的时空边界,许多文化是“通过共同身份、共同‘话语’、共同时间来区分群体。”[23](P7-27)就像是笔者考察过的798、宋庄、景德镇等许多的区域,之所以成为一个社区,是因为里面聚集有许多的艺术家或手艺人,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艺术家或手艺人身份的共同体。
在这样的研究中,有的人类学家发现,艺术品和艺术品销售是土著社会融入全球化经济的主要切入点之一,也是外界人士想象该社会形象时的主要创造渠道之一。[13]于是,在西方有一整代学者都认为,艺术人类学主要就是研究“殖民化挪用”或非西方物品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商品化”等问题的。[24]在这样的背景下,交换理论和符号人类学相互联系,影响了艺术人类学对人类和事物本质的分析。这也成了20世纪80至90年代人类学的一个中心议题。[13]同时,也成为后现代艺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另外,这一研究涉及对社会变革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探讨,它影响到两个主要领域:其一,贸易和交换进程研究;其二,全球化 (包括文化界限概念化 )进程研究。[13]也就是说,艺术和艺术品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土社会和非本土社会间当代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代的土著艺术,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作为文明世界历史的变迁方式,因为艺术品所参与的价值创造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其生产场地和生产年代,而是存在于其所参与的一切相互作用之中。[13](笔者曾用这样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陶瓷艺术的远距离贸易,并希望通过这样的贸易研究来理解陶瓷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和艺术的象征符号是如何参与全球互动的,并促使世界文明的象征体系不断的再生产的。)[25]
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旅游业的发展,世界艺术贸易的日益增长,出现了一个“后现代的艺术界”,这里所谓的“艺术界”就是一个包罗艺术家、经纪人、画廊、媒体等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土著艺术被牵扯进膨胀的国际化艺术市场中,那些曾被“部落或原始艺术”掩盖的群体身份得以重新塑造。[26](P2)这种重塑为传统的土著民族创造了全新的政治,以及新的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也使其原生文化受到挑战。
另外,自20世纪70年代起,情感、性别、人体、空间和时间等论题日益受到关注。宽泛意义上的艺术常常成为这一研究的主要的资料来源。其中,雕塑和绘画为研究表征体系、身体美学、价值创造过程、社会记忆和空间划分提供了深入理解的可能性。同时,歌曲和戏剧为 (研究)文化诗学、情感世界、文化反思和自省向度及例证表述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13]在这样的背景中,艺术成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之一,如果说,在现代主义时期我们谈论的是艺术人类学的复兴,而发展到后现代主义时期,艺术人类学开始步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正如墨菲所说,其正在由一门大多数人类学家鲜有问津的学科转变为人类学研究的一大中心。[13]
“艺术界”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将围绕着艺术而形成的各种相关成分和机构看成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重叠的职业和社会关系、多种艺术话语、围绕着拍卖市场的商业机构构成的。[26](P3)其不仅是一个市场,或一个杂志读者群,甚或一个职业部门,还是一个遍及世界的多层商业、传播的社会网络。
也由此有学者认为,艺术人类学现在已经扩展为艺术界的人类学(然后是后现代艺术界)——这是一个关键而且颇具新意的场景。[26](P305)从这个角度出发,后现代艺术人类学不仅见证、记录、研究了土著历史转变的复杂性,还见证了土著艺术与当代艺术的互动与重构过程。因此,艺术界被定义为“话语建构”,所谓的“话语建构”就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由某一给定时间的具体社会关系构成的,这样的构成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定义。这样的概念使艺术成了一种行动中的艺术,而不再只是理论上和书本上的艺术,以及画廊中、美术馆、剧院、舞台中的艺术,因为其所有的定义和表现形式都是动态的,包括什么是艺术,如何确定其标准也是动态的。也由此,艺术民族志的撰写有了更加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必须要将其放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实践中来理解。这种理解方式涉及更广泛的领地,也涉及如何在复杂社会的变迁中去理解人类学与艺术的关系等问题。
将艺术放在具体的文化空间中去理解,这本来是人类学的观念,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鲍德里亚、詹姆逊、德波、利奥塔、布迪厄和其他一批学者通过对西方消费生活的长期观察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其中也包括了有关艺术方面的理论。而在这些理论中“艺术不再是孤单的、孤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27](P99)在鲍德里亚看来,“一切事务,即使是日常或平庸的现实,都刻意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是审美的。”[27](P99)而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28](P589-612),从不将艺术品视为人类智慧的实在产物,而仅将其看成是社会差异的标志或者仅看到其图像学的意义,[29]由于将艺术重新置于生活空间,包括消费市场中去理解,让学界重新确定了艺术的概念,即:艺术不再是独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之地,而是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这已经成了一种学术界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正是人类学的本来认识,在原始部落那里,鼓乐、歌唱、绘画和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不分离的整体。于是艺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跨界交流,有了更加宽广的通道,包括与当代艺术界的合作,也展示出了许多新的场景。
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艺术界鼓励人类学和艺术之间有效的交流。[26](P2)乔治·E马尔库斯、弗雷德·R迈尔斯主编了《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该书研究的是西方艺术界自身,通过研究反思传统范式,提出应当重新协商艺术与人类学关系的主张。
人类学家之所以把焦点放在当代艺术界,最初并不是处于研究的目的,而是源于自身的经验。如迈尔斯多年来使用创新的理论和传统民族志的方式研究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当这些土著艺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后,他发现自己开始处于艺术评论家、交易商、博物馆长构成的艺术界中。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要重新思考人类学和艺术的关系。另外,施耐德和赖特在其主编的《当代艺术和人类学》一书中,对人类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欠缺合作,以及在艺术和科学之间所制造的巨大差异进行了批判,同时,其也在寻找如何与当代艺术沟通及合作的途径。[30]反之,有不少的艺术家,或艺术史论学者,也开始在人类学研究的“他者”中寻找新的研究资源和视角。
两者都在寻找自身研究的新主题。[26](P2)于是,人类学和艺术界在后现代语境中得以相遇。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艺术逐步成为叙述差异性,赋予行为和思想以意义的主要文化生产场地,人类学也将其的艺术研究视为自身在文化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代艺术家和其他类型的视觉从业者正以一种更新的方式参与到人类学之中。[31](P195-220)而越来越多的艺术界人士介入其中成为准人类学家,共同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使其“步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13]然而,这是一个和传统人类学家所面对的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我们如何重新确定我们的田野范围、研究对象、话语空间,重塑民族志的写作范式,成为一个很棘手,也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写艺术”与“写文化”一样,可能要重新界定或者重新为艺术民族志的写作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和探索的途径。有学者就像提出先锋艺术一样提出了先锋民族志的口号,而这种先锋民族志也可以定义为后现代主义民族志。
三、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
本文中提出的“写艺术”与“写文化”一样,首先是希望对艺术民族志的写作提出一种新的构想,但由于艺术民族志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所以,笔者用了以上大块的篇幅对西方艺术民族志的概念,以及西方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做了一个简述。通过这一简述,我们看到的是,作为人类学研究的艺术田野一方面是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其具有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我们所面对的艺术田野并不是固有的,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停运动不停变化的,甚至是不停重组与重构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促使了全球旅游业的兴盛、全球贸易的迅速流动,还有各种艺术展、拍卖等艺术市场的膨胀,将世界各地的艺术都卷进了一场共同的流通领域中,其中不仅有当代艺术,还有土著艺术和民间艺术等。许多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象征符号都不再具有其原生的意义,在中国也一样。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田野,作为中国的人类学者应该如何去描绘,去记录,去研究,去得出自己的看法,并和西方人类学者一起共同完成一种既能表现新的社会结构,又能体现新的文化价值意义的艺术民族志,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也就是如何去“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
克利福德和马库斯在他们编撰的《写文化》中指出:民族志学者必须把社会想象为一个“整体”,并通过对眼见的地方、耳闻的谈话、遇到的人的描述将他对“整体的想象”传达给读者。[1](P13)按照这样的理论,艺术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在这样的时代如何能够成为人类学家描绘的整体,乔治·E马尔库斯和弗雷德·R迈尔斯提出了一个“后现代艺术界”的概念,在这样的“后现代艺术界”的概念中,不仅包含有当代艺术,也包含有土著艺术、民间艺术、大众艺术等等。因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一种艺术是不受其他艺术和文化所影响的,当代艺术在影响土著艺术,土著艺术也在影响当代艺术。因此所有的文明“都已经变成了间生物”,“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是间生性的,都是文化同化的产物。”[32](P320)也就是说,由于全球化加速了不同文明交换、改变、加工、合并文化元素的速度,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再也不存在“确定类型”或纯粹系统。
在这样的背景中艺术民族志的写作,就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中,“反思的、多声的、多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志具有了实验的正当性。”[1](P13)另外,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中国既不是艺术人类学产生的原生地,也不是人类学产生的原生地,所有的学科定义、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包括学科术语都是来自西方世界,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不是目的,目的是如何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了西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同阶段以后,是否可以思考我们是将其三个阶段的方法都给予尝试,还是直接进入后现代艺术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中?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曾说当时的中国正在面临三级两跳,也就是工业革命还没有完成,后工业文明的阶段就已经到来了。
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也一样,对于古典艺术人类学和现代艺术人类学都还没有完全明白,后现代艺术人类学又出现了,艺术民族志的规范还没有弄清楚,又出现了先锋艺术民族志,后艺术民族志的概念。
这样看来,中国有关艺术民族志写作的探讨是比较滞后的,但有时我们要看到,社会的发展往往会出现后发制人,或者蛙式跳跃,中国的艺术民族志发展也一样。首先中国的艺术资源丰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空间,不仅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点,还呈现出先后不同的发展场景,需要我们用艺术人类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去进行解释和研究。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文化历史是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殊规律的,正是这样的历史特殊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而当代中国虽然有过一百多年学习西方的过程和经历,但其终究还是中国,不仅具有自己的历史特殊性,也有自己当代的特殊性,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所有文明都成了“间生物”的今天,中国的艺术场域仍然有其自身的,与全球文化对应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文化。虽然西方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很重要,但我们仍然要看到,其大多数的经验和理论都是来自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土著社会。这些土著社会基本是部落社会,即使有少量的皇权社会,也是极粗浅的,与根基深厚的中华文明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而且,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还有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这个国家充满活力,几乎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一百年所走的路,但这条路又不完全是西方的路。新的社会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来总结,也需要有新的民族志来记录和研究这一社会事实。
而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西方人类学家所界定的“后现代艺术界”,在中国不仅也一样存在,而且随着农民工进城,随着新的艺术和工艺品市场的出现,许多的农民艺术,少数民族艺术开始出现在城市的商场,甚至画廊、舞台和剧院里;还有一个影响中国艺术发展的,就是以国家意志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及民族情绪所带来的本土艺术的复兴等现象,几乎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艺术生态,也改变了中国的当代艺术,还由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界”。
2017年,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发生了两个大事件,第一件大事是年初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策划的“中华匠作”在北京太庙艺术馆展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工匠的艺术和当代艺术家的艺术放在一起同馆展出,并且由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的评论家做策展人。策展人在前言中写道:“今欣逢盛世,社会创新活力竞放,当重承继传统,倡扬工匠精神。”*范迪安.“文明的回响·系列展览·第二部 中华匠作”1月22日于太庙艺术馆开幕前言http://www.sohu.com/a/124760087_407290第二件大事是著名艺术家邱志杰于2017年2月,代表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其将中国民间艺术纳入“当代艺术航母”,并以“不息”为主题(其摘自《周易·系辞》中的“生生之谓易”),来回应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艺术永生”,所谓的“生生不息”是基于一种中国人对“永生”的特别理解——即:宗族血缘式的代代相传的绵延不断。
这两大事件,让我们看到所谓“间生性”的文化,不仅出现在“全球”与“地方”,也出现在“现代”与“传统”,“精英”与“民间”之间,其代表着中国正在把传统和民间的艺术作为当代艺术创新的资源,走出一条中国原创性当代艺术之路。这是中国式的后艺术民族志值得关心的问题,也是后艺术民族志值得去书写和研究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打造民族志是一件手艺活儿,[1](P34)但笔者认为,其不仅是一件“手艺活”,还必须是一件“理论活”“思考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建构就会出现什么样的艺术民族志的写作范式,艺术民族志不仅是一种社会事实的描述,更是一场话语空间和理论空间的建构。因此,中国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与中国艺术民族志理论的建构紧密相关。
本文主要是想抛砖引玉,希望能在学界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民族志的写作,同时也希望由此能产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文章,以引起大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
(责任编辑 唐白晶)
[1][美]克利福德,[美]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Clifford, in Marcus (ed.),WritingCulture:PoetryandPoliticsofEthnography, trans. by Gao Bingzhong, Wu Xiaoli and Li Xia,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2]向丽.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如何可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意义再生产[J].民族艺术,2017,(3).
Xiang Li, How is it Possible for the Writing of Art Ethnography: the Field and Re-production of Meaning of Art Anthropology,EthnicArts, No 3, 2017.
[3][英]汤姆·杰克逊.大脑的奥秘:人类如何感知世界[M].张远超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Tome Jackson,TheSecretofBrain:HowHumanFeeltheWorld, trans. by Zhang Yuanchao, Beijing: Electronic Industry Press, 2017.
[4] Liana De Girolami Cheney,GiorgioVasari’sPrefaces:ArtandTheory, New York: Peter Lang,2012.
[5]高名潞.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Gao Minglu,WesternArtHistoryConcepts:RepresentationandtheTurnofArtHist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6]雷蒙德·弗思.艺术与人类学[J].王永健译,民族艺术.2013,(6).
Raymond Firth, Arts and Anthropology, trans. by Wang Yongjian,EthnicArts, No 6, 2013.
[7][英]克莱尔·贝尔.艺术[M].王永健译,北京:文联出版社,2015.
Clair Bell,Arts, trans. by Wang Yongjian, Beijing: Literary Feder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5.
[8][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M].王永健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Franz Boas,PrimitiveArts, trans. by Wang Yongjia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89.
[9]M. Johnson,TheMeaningoftheBody:theAestheticsofHumanUnderstan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0][英]哈登.艺术的进化:图案的生命史解析[M].阿嘎佐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Alfred Haddon,EvolutioninArt:asIllustratedbytheLife-HistoriesofDesigns, trans. by Agazuoshi,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美]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M].靳大成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Robert Layton,ArtAnthropology, trans. by Jin Dacheng et al, Beijing: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2][澳]霍华德·墨菲.艺术即行为,艺术即证据[J].李修建译,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1,(2).
Howard Murphy, Art is Act, Art is Evidence, trans. by Li Xiujian,JournalofInnerMongoliaUniversityArtSchool, No 2, 2011.
[13]霍华德·墨菲,摩根·帕金斯.艺术人类学学科史以及当代实践的反思[J].蔡玉琴译,民族艺术,2013,(2).
Howard Murphy and Morgan Perkins, History of Art Anthropology and Rethinking of its Contemporary Practice, trans. by Cai Yuqin,EthnicArts, No 2, 2013.
[14][英]阿兰·巴纳德(Alan Banrnard).人类学历史与理论[M].王建民、刘源、许丹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Alan Banrnard,HistoryandTheoryofAnthropology, trans. by Wang Jianmin, Liu Yuan, Xu Dan, et al,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6.
[15]大卫·M费物曼(David M.Fetterman).民族志:步步深入(第3版)[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David M. Fetterman,Ethnography:StepForward(3rdEditio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英]雷蒙德·弗思.社会组织的诸要素[J].李修建译,民族艺术,2015,(3).
Raymond Firth, Elements in Social Organization, trans. by Li Xiujian,EthnicArts, No 3, 2015.
[17][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Clifford Geertz,LocalKnowledge, trans. by Wang Hailong and Zhang Jiaxua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4.
[18][美] 丹尼斯·达顿.“但他们并没有我们的艺术概念”[A].[美]诺埃尔·卡罗尔编.今日艺术理论[C].殷曼楟、郑从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Denis Dutton, “But They Don’t Have Our Art Concepts”, in Noel Carroll,ContemporaryArtTheories, trans. by Yin Manting and Zheng Congro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9][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rnst Grosse,TheOriginofArts, trans. by Cai Mu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20] Alfred C Haddon,EvolutioninArt:asIllustratedbytheLife-HistoriesofDesigns, London: Walter Scott, Ltd., Paternoster Square,1895.
[21] Malinowski Bronislaw,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1984.
[22]I. Winter, Agency Marked, Agency Ascribed: the Affective Object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Robin Osborne and Jeremy Tanner (eds.),Art’sAgencyandArt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2007.
[23]Abu-Lu Ghod, Lila:“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WomenandPerformance:AJournalofFeministTheory, No 5, 1990.
[24][荷]范·丹姆.风格、文化价值和挪用:西方艺术人类学历史中的三种范式[J].李修建译,江南大学学报,2012,(3).
Wilfried Van Damme, Style, Cultural Values and Appropriation: Three Paradig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thropology of Art in the West, trans. by Li Xiujian,JournalofJiangnanUniversity, No 3, 2012.
[25] 方李莉.丝绸之路上的陶瓷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Fang Lili, The Ceramic Trad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JournalofYunnan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ical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 4, 2016.
[26][美]乔治·E马尔库斯,[美]弗雷德·R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George E. Marcus and Fred R. Myers,CulturalExchange:ReshapingArtsandAnthropolog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27][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Mike Featherstone,ConsumerCultureandPost-modernism, trans. by Liu Jingm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0.
[28]Pie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Art Pei’ception’,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 No 20, Vol 4, 1968.
[29][英]阿尔弗雷德·盖尔.魅惑的技术与技术的魅惑[J].关祎译,民族艺术,2013,(5).
Alfred Gell, The Technology of Enchantment and the Enchantment of Technology, trans. by Guan Wei,EthnicArts, No 5, 2013.
[30]Schneider, Arnd and Christopher Wright, The Challenge of Practice, in A. Schneider and C. Wright (eds.),ContemporaryArtandAnthropology, Oxford, New York: Berg, 2006.
[31] Anna Grimshaw, Art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in M. Westermann (ed.),AnthropologiesofArt, Williamstown, Massachusetts: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 2005.
[32][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费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Nigel Rapport and Joanna Overing,SocialandCulturalAnthropology:theKeyConcepts, trans. by Bao Wenyan and Zhang Yahui,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3.
Re-constructingtheDiscourseObjectivesof“WritingArts”:OntheResearchandWritingofArtEthnography
Fang Lili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requires a series of writings of art ethnography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c facts of Chinese art phenomena, as well as to form the topics and domestic theories that are of common interests. These results then entail a discourse space where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could have equal conversation with its counterpart in the West. Therefore, the writing of art ethnography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of writing become significan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Owing to the fact that art ethnography derives from the West, in order to develop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basic concepts in Western art ethnography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basic methodology, and main perspectives and theories in different schools. Without a deep discussion on these issues,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position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in the world territory of art ethnography. Therefore, with the aim to contempl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writing of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and to re-construct the discourse objectives of “writing culture”,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relevant concepts and issues in relation to Western art ethnography. Based on these, it is possible for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to establish a standard of writing art ethnography, and to discuss various issue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t ethnography.
art ethnography, art anthropology, art circle, post-art ethnography
Abouttheauthor:Fang Lili, Research Fellow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Institute of Artistic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2017-11-15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J0-05
A
1003-840X(2017)06-0047-14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 100029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6.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