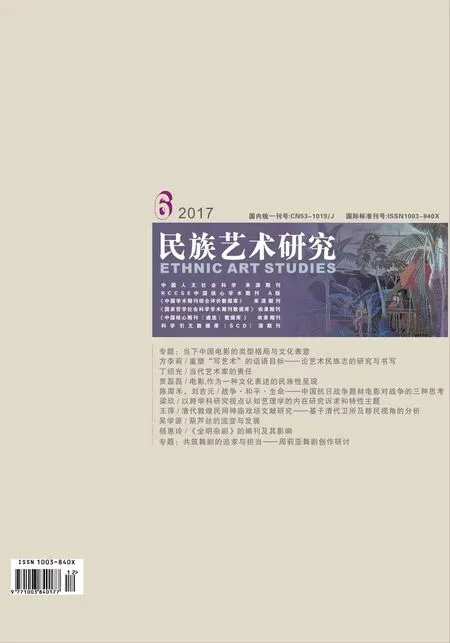战争·和平·生命
——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对战争的三种思考
陈犀禾,刘吉元
战争·和平·生命
——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对战争的三种思考
陈犀禾,刘吉元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拍摄的抗日战争题材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影片所表达的价值观切入并进行分类梳理,可以总结出其反对法西斯战争的三种叙事模式: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以生命和人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以和平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三者分别侧重了战争、生命、和平的价值观表述,之间有差异,也互有交叉。这些价值判断既是编导个人能动选择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影片生产时代大背景的回应。
中国抗日题材电影;反法西斯战争;战争;和平;生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70多年,7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电影人为这一重要题材贡献了无数电影作品,其中有许多堪称伟大的作品。中国的抗日战争题材电影是这一世界性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之前、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电影人创作了许多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据詹庆生统计,仅2000—2014年15年中,拍摄的战争片就有224部,占据15年来电影总产量的5%。在这5%的战争片里,抗日战争题材又有114部,占战争片的51%,远高于早期革命红军题材、解放战争等其他题材影片。市场表现方面,2000—2014年15年来票房最高的10部战争片里,抗日战争题材就有6部。从新世纪返回到战争片一度繁荣的“十七年”时期,我们得到如下数据:“十七年”共摄制了187部战争片,占这一时期电影总量的31%,抗战片在战争片里占到20%的份额。[1]中国抗日战争题材影片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上述沉默的数据中,还体现在其对国人生活、记忆的参与和重塑上:提及“十七年”电影,人们很难不想到《地雷战》《地道战》等经典抗战片;谈起新时期影片,《一个和八个》作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不可能被绕过;更不用说新世纪以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片子因为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而引起的热烈讨论了。
抗日战争题材电影表达了中国人对战争的种种思考,其中包括对战争和民族命运的求索,对战争中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探寻,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量。本文将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所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为对象,研究这一题材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表达中国人对战争和战争相关问题的思考:他们思考的重点在哪儿?表达了何种价值观立场?以及这种思考和时代背景的关联。
总体说来,中国电影反对法西斯战争的镜像语言描述呈现有三种叙事模式。第一种是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这是中国抗战电影的经典模式。这一叙事聚焦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往往用激昂的语调歌颂战斗英雄和事迹,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个体需要为战争胜利牺牲一切个人利益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战争的价值观呈现上,这种叙事模式采取了民族战争观。这种战争观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确立起来,抗战时期拍摄的很多新闻纪录片里,画面一边呈现受害者的惨状,解说词一边这样表述:“我们再不起来反抗,国家就亡了,民族就亡了。”[1]第二种叙事以生命和人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主要描写法西斯战争与生命价值之间的冲突,控诉战争对人类肉体、心灵的戕害,表达编导对战争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思考,彰显的是重视人类生命个体的战争价值观。战争毁灭了个人幸福甚至生命,但是个人又必须为保卫国家尽责,其间流露出的对战争的态度是很纠结的。第三种叙事则以和平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镜头主要对准中日人民和民间的友好交往,控诉法西斯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试图用超越国界的人类情感化解战争的伤痛,反对法西斯战争,追求和平,传达的是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三种叙事在承载着不同价值观的同时,又各自对应了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的三大主题:“战争”“生命”与“和平”。
其分别以“战争”“生命”“和平”作为主题的三种叙事模式在对战争表现的直接性上也有差异。主题是“战争”的第一种叙事直接并且重点描绘战争过程和战士(参战者)的战斗事迹,战场被建构成集保家卫国、自我实现等各项功能于一体的诗意战斗空间。个人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缴获了敌方士兵的武器乃至生命以后,获得我方授予的“英雄”称号,也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第一种叙事模式重点在于歌颂英雄和胜利。主题是“生命”的第二类叙事同样展现战争,但重点已不在对战争的正面描画上,战争成为背景或退居第二位,首先描写的是战争中人(不一定是战士)的命运。就这样,有血有肉的“人”从善恶两分的第一种叙事模式中被拯救出来,观众得以和片中人一起感受战争中普通人的伤痛、恐惧和爱。主题是“和平”的第三种叙事常常不直接表现战争,而是重点表现战时和战争前后中日民间和平交往(战争对立面)的故事,传递出编导希望用超越民族的沟通和理解取代战争中的民族仇恨和伤害的创作意图。
一、歌颂人民战争和抗战英雄
“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是中国抗战题材电影中最先出现的一种叙事模式,也是抗战电影的经典和原型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歌颂保家卫国的正义(抗日)战争和抗战英雄。“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叙事中,战争作为前景出现,战争过程和战斗英雄是重点表现的对象。民族战争观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人物塑造和镜语体系等都围绕民族战争观建立起来,“日本鬼子”大多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我方统帅则是有勇有谋的抗战英雄,片中人物的是非善恶,只需看上一眼就能判断出来。
“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电影作品有很多,《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中华儿女》《赵一曼》《血战台儿庄》《雄魂》《喋血孤城》《遍地狼烟》《太行山上》《夜袭》《百团大战》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根据抗战主力的不同,“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叙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发展出三种略有差异的叙事形态: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的游击队抗战、八路军正规军作战、国民党军队抗日。
(一)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的游击队抗战
中国第一部抗战题材故事片是1932年“联华”二厂出品的《共赴国难》,影片透过华翁一家人的变化,通过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反映了“九·一八”“一·二八”后全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和民族觉悟的提高,也表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和决心。[2](P249)新中国建立后,电影工作者学习吸收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抗日战争和文艺工作的重要观点*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农民抗日”观点:“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的革命,现阶段抗日的实质是农民的抗日”和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出的“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与“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文艺理想。,在此基础上对前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加以改造,由此发展出新中国抗战电影“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叙事的最初形态——“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中华儿女》《赵一曼》《苦菜花》《狼牙山五壮士》《鸡毛信》《小兵张嘎》《兵临城下》《三进山城》《古刹钟声》《永不消逝的电波》《野火春风斗古城》《回民支队》《新儿女英雄传》《南海潮》《吕梁英雄》等即可视为这一形态的典型代表。
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相配合,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势力主要在敌后根据地活动,负责钳制、粉碎日寇的扫荡与进攻。中国共产党的作战方式以游击战为主,作战人数较少,作战方式灵活,群众参与性较好。游击队的作战方式培养出了一批人民(农民)英雄,他们在多部片子里得到表现,《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铁道游击队》的刘洪、《新儿女英雄传》的牛大水、《地雷战》的赵虎、《地道战》的赵传宝等皆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游击队作战英雄。“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是英姿飒爽的,一袭土布衣裤掩饰不了他们高昂的战斗激情和随时随地喷涌而出的智慧。他们对党和国家极度忠诚,对人民群众无比热爱;就算偶尔犯错,也是些无伤大雅的小错误,绝不会影响大局。
英雄人物战斗的对象则是一身黄军装、满口中日混杂词汇*如经常说的“八嘎呀路”“大大的狡猾”“死了死了的”等。的“日本鬼子”。“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影片对“日本鬼子”的呈现实际上是很主观化的,日本侵略者要么被妖魔化为阴险狠毒、无恶不作的杀人狂魔,要么被戏谑成空有一腔坏水、智商却跟不上的“小丑”角色。对“日本鬼子”矮化、丑化的策略与此类电影整体的叙事策略分不开,唯有将日本侵略者塑造成人格、智商上远低于我方抗战英雄模范的人物形象,才能反衬出我方英雄的高大伟岸,达到令观众认同我方、唾弃敌人、增强民族自豪感的目的,是一种典型的胜利者话语言说方式。
“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叙事最重要的一点是其爱国主义主题的弘扬,包括敌我双方(我方战斗英雄和地方日本侵略者)人物形象描绘在内的一切叙事活动都紧紧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在这一类叙事中,“国家”“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三个概念是同构的,爱国就等于爱民族也等于爱党。个人利益轻于国家利益;家国大义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则常常沦为汉奸、叛徒;只有国家、民族有了出路,个人才会有出路。
“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电影在视听语言运用上也凸显了爱国主义的主题。景别方面,这类影片喜欢将大景别与小景别结合使用,英雄人物多被置于人民群众中间,在抗战英雄模范为国家民族做出重大贡献等时,则往往使用近景、特写等小景别镜头表现,摄影机框定他们无所畏惧的面庞,《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作品大致遵循了这样一套运镜方法。此类影片还经常把英雄人物和山川河流等自然意象组合到一起,《狼牙山五壮士》的片头、《中华女儿》的片尾等皆采用了这样的剪辑手法。《中华女儿》中,投江的八位革命女性巍峨的身影分别跟滔滔江水、入云高山、朗朗青天相结合;《狼牙山五壮士》里,泰山日出、黄山云峰、丘壑群山、八达岭长城合力开启了电影的序幕。山川河流本是存在于祖国疆土上的自然景物,此时被用来指代人文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电影镜语运用方式。创作者把英雄为国牺牲的壮烈行为与象征民族、国家的山川河流剪接到一起,是对于英雄至高无上的褒奖礼赞,也是对作品爱国主义叙事主题的阐发升华。此外,“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电影选用的音乐也多与爱国主义的主题紧密相关,乐曲常有激昂明快、回环往复的特点,富有煽情性和鼓动性。为人熟知的《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就兼具抒情和力度之美——前半部分是抒情的男声领唱,给人以抒情倾诉之感;后半部分是铿锵有力的男声合唱,抒发了抗日战士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将煽情性和鼓动性整合到一首乐曲中,《铁道游击队》的音乐创作的确匠心独具,最终指向电影爱国主义的主题。
不管是对人民(农民)英雄和日本侵略者形象的主观化塑造,还是综合运用各种视听手法表达爱国主义的主题,都是电影创作者们按照新政权的政治诉求来构筑抗战历史想象的产物,是在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做注解。“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叙事以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来反对法西斯战争,契合了时代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
(二)八路军正规军作战
“以农民战斗英雄为主角的游击队抗战”叙事是“十七年”抗战题材电影最主要的叙事形态,进入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平原枪声》《东江特遣队》《张思德》《我的母亲赵一曼》等一批主旋律电影相继涌现,巩固了“以正义战争(抗日战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叙事模式。与此同时,《太行山上》《夜袭》《百团大战》等描写八路军正规军作战的影片也被创作出来,发展了这一叙事。
《太行山上》《夜袭》《百团大战》等不再致力于展示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和小规模战斗的景况,而是以正规战役作为电影主要情节,歌颂八路军正规部队的英勇善战。《太行山上》表现了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间,朱德率领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平型关大捷、阳明堡战役、击毙日酋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战役等几次重大战役中的作战情况;《夜袭》讲述了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团长陈锡联率领下,突袭位于山西代县以南的日本侵华军队阳明堡机场的故事;《百团大战》则将目光投向“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4千米、公路1500余千米,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3](P49)的百团大战,讴歌了毛泽东、彭德怀、左权等革命领袖的有勇有谋、周密果断。
(三)国民党军队抗日
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长期冰封的政治局面有所缓和,两党关系由对峙走向对话。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的提出,为解决台湾、澳门问题提供了参照。政治上的“破冰”很快反映到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中,以国军爱国抗战将领为主角的《吉鸿昌》(上下集)、《西安事变》(上下集)、《喋血黑谷》等影片相继上映。
1986年《血战台儿庄》的公映是中国抗战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抗战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影片勾勒出李宗仁、张自忠、池峰城、王铭章等多名热爱国家、精诚抗战、以大局为重的国民党将领形象,结尾处“血肉长城”一段,抗战将士横陈的尸体、战场上未灭的硝烟与死寂般的氛围叠加在一起,突出了《血战台儿庄》“血战”和“爱国”的主题。杨光远、翟俊杰在《<血战台儿庄>导演艺术总结》中写道:“镜头从护城河摇至坍塌的城楼,缓缓地拍下千百具尸体的每一个细部。这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遥渺地传来了,仿佛是从遥远的天空中传来的,又似乎是烈士们的呼喊,轻颤……”[4](P3)《血战台儿庄》奠定了“国民党军队抗日”叙事的整体程式,此后,《雄魂》《兵临绝境》《血誓》《铁血昆仑关》《七七事变》《大捷》《喋血孤城》《遍地狼烟》等多部以国民党军队抗战活动为主要线索、展现国军将士泣血抗战和国民党抗战将领不朽功勋的片子陆续献映,使得抗战电影的创作面貌更加丰富多样。
值得提及的另一点是,新世纪以来国产抗战大片序列里也出现了一些表现国民党军队抗日的影片,较为出名的如以日本士兵为主角的《南京!南京!》和描写青楼女子抗日的《金陵十三钗》等。在上述国产大片中,战斗只是作为次要线索参与叙事,国民党抗日军队被书写成一种官方抗战符号。《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电影里,浓重的硝烟、轰隆的炮声只是历史背景和故事底色,国仇家难情况下流民的惨状才是编导着墨的重点。正是因为官方抗战力量的孱弱,才使个体变成失去国族庇护的“孤儿”,从而为孤立无援处境下人们的人性挣扎提供了动因。
二、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思考
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内迈入和平建设年代。国际上,中国先后跟日本、美国等国家建交,战争阴影日渐被消除。在新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电影界也进入了朝气蓬勃的新时期,掀起多股电影创新浪潮,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处在浪潮之中,亟待新观念、新元素的汇入,“以生命和人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叙事模式由此诞生。苏联在此前也已经出现了《这里黎明静悄悄》等从人类生命价值角度表现“二战”题材的影片。“以生命和人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叙事模式的总主题是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美好,编导在对这一主题进行阐发的过程中,也注入了他们对战争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在这些影片里,战争多作为故事背景出现,具体战斗情节被淡化乃至隐去,叙事重点是描写战争背景下人的故事和命运。这些人里有战士,有受害者,也有侵略者,从主人公的不同身份出发,我们又可将此种叙事划分成“抗日战士的战地青春”“普通平民的惨淡岁月”和“日本士兵的灵魂煎熬”三个子类型。“以生命和人类的名义的反对法西斯战争”叙事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产生以来,出现过许多佳作,《归心似箭》《黄河绝恋》《红樱桃》《避难》《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晚钟》《斗牛》等是其中代表。
(一)抗日战士的战地青春
说到抗战片中的抗日战士,观众很容易便能列举出李向阳、刘洪、董存瑞、赵一曼、刘胡兰等一长串名字,他们都来自于“十七年”时期拍摄的相关影片。这些片子里的抗日战士骁勇善战、思维敏捷、意志坚定、浑身充满党性,没有凡人的七情六欲。新时期以来,《归心似箭》《黄河绝恋》等影片打破了以往作品抗日战士塑造的固定范式,将不食人间烟火的抗战英模还原成心怀国家、敢爱敢恨的普通人。
不同于《地雷战》《地道战》等“十七年”抗战片对“造神”的执着,1979年由李俊执导的《归心似箭》第一次把“神”置换成了“人”。电影前半部分魏得胜仍是一个十足的抗战英模。作为东北抗联连长的他数次落入敌人魔掌,但从未丧失寻找队伍的决心和抗战到底的勇气,他进煤窑背煤,拿野草充饥,历经千难万险只为重回部队和同志们一起抗战。影片前半部分以蓝灰冷色调为主,色彩影调相对低沉凝重,营造出一种客观理性的感觉,烘托出战争的残酷和我方抗日战士的坚定信念。在魏得胜被玉贞救起后,后半部分的摄影基调发生了逆转,整个影调开始向偏暖色调转变,色彩很柔和,气氛也随之变得明快起来,给人一种温暖、舒适的感觉。电影后半部分用大量篇幅抒写魏得胜和玉贞的爱情。当魏得胜说要报答玉贞的恩情时,玉贞回应道:“你这人的嘴还怪甜呢!那你一天就给我挑两趟水,挑到我儿子娶媳妇,挑到我闺女出门子,给我挑一辈子!”聪明的玉贞借用“挑水”行为委婉地表达了对老魏的爱慕之情。听说老魏要走,玉贞心里痛苦万分,老魏去小溪旁挑水时,她抢过他的水倒掉一桶,一个女性又爱又怨、舍不得却必须放手的心情呼之欲出。片子最后,深明大义的玉贞主动劝魏得胜早点出发,以免天气变冷,路上难走,真挚的话语加上“灯下补衣说相思,树下送别暗垂泪”的画面,使影片处处闪耀着人情美、人性美的光芒。
《归心似箭》是“文革”以后第一部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大力描写爱情的作品,它打破了中国抗战电影在题材创作上的多个禁区。1999年冯小宁拍摄的《黄河绝恋》继续描写战火中的珍贵情谊。纯洁美丽的八路军女战士安洁和爱憎分明的男战士黑子奉命护送盟军飞行员欧文前往根据地,途中三人遭遇过日本人的追杀和土匪的拦截等多次险阻,但都被黑子和安洁一一化解。影片最后,安洁和黑子为了掩护欧文顺利渡过黄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安洁和欧文之间的爱情,黑子与安洁、欧文之间的友情是《黄河绝恋》表现的重点。黑子为掩护欧文、安洁渡河献出了生命,让观众领略到友情的伟大;安洁为不拖累欧文,偷偷剪断了连接二人的绳索,沉入黄河的万丈波涛之中,如此深沉的爱情令人动容。安洁初次见到黄河一段是电影的高潮段落。一泻千里的黄河前,美如天使的安洁像芭蕾舞演员一般张开自己的双臂,黄河水在后景奔腾直下,前景中的安洁闭上双眼,微微颔首,后景黄河的动势衬托出前景人物的高雅、纯洁、安静和美好。
颂扬生命可贵,青春、爱情的美好是《黄河绝恋》《归心似箭》等影片的主题所在。在这样的叙事之下,抗日战士变得更加可爱和有人情味。浓郁的人情、勃发的生命和美好的青春一起,赋予了此类电影一种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
(二)被战争摧残的普通民众
在“十七年”和“文革”抗战片的人物形象谱系中,普通平民几乎是缺席的。那个强调“全民皆兵”的年代里,一个人通常有战士(民兵)和汉奸两种身份可供选择,拥护抗战的中国人是战士,反对抗战的则被称作汉奸。“十七年”的经典战争片如《地雷战》《地道战》里,本该是普通人的老乡也担负起了放哨、后勤等战士的职责。新时期后出现了《避难》《红樱桃》《金陵十三钗》等多部以普通人为主角、以揭露战争的反人类性质为主旨的反法西斯战争电影,集中暴露法西斯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其中,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摧残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肉体的伤害,二是精神的折磨。法西斯战争打破了普通人宁静的生活,吞噬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成为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
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是一部关注法西斯战争中个人身体和灵魂创伤的作品。影片改编自朱德之女朱敏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共高干之女楚楚在德国法西斯统治下九死一生的故事。拥有奇怪嗜好的德国纳粹将军看上了楚楚光滑的皮肤,并在她的背上刺下了一大幅纳粹鹰徽,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背上的纳粹纹饰始终像幽灵一样折磨着楚楚。由于创伤面积太大,楚楚的多次植皮手术都宣告失败,身体上的伤害引发了灵魂创痛,楚楚一生未婚,直到去世时也没有走出法西斯战争的阴影。《红樱桃》塑造了一个被法西斯战争毁灭的中国少女形象,使观众真切感受到残酷战争里个体的绝望和生命的力量。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获得1996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在《电影艺术》刊登的1995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 《红樱桃》以1300万元的票房高居榜首。
《红樱桃》是国产电影里比较少见的描写欧洲战场和德国法西斯罪恶行径的作品。同样是描摹普通平民惨淡的战争岁月,《避难》《金陵十三钗》等影片将批判矛头对准日本法西斯。两部影片在主创人员*著名作家严歌苓是《避难》的编剧之一,也是《金陵十三钗》的小说作者。上的交叉使二者在故事讲述上也颇有重合之处,如都以江南名妓作为故事主角,并把她们在国仇家难下的转变作为故事线索。当然,两部作品也有许多不同之处。《金陵十三钗》很重要的一点改动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强调上。与《避难》相比,《金陵十三钗》不仅加重了身体展示的比重,而且赋予玉墨、豆蔻等女性以身体自主权。虽是烟花女子,“十三钗”却誓死不拿身体侍奉日本侵略者*这一点在《避难》里也有所表现。,豆蔻因为反抗日本人的奸污被残忍杀害,玉墨等人也做好随时牺牲生命的准备。慷慨赴死前夜,玉墨将自己的身体给了约翰,她对约翰说:“今晚过后,我的身体就不再属于我,带我回家吧”,身体的归属指引着玉墨心灵的方向。《金陵十三钗》对身体的强调使玉墨等人在战争悲剧中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明知会惨死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之下,却不得不这么做,更加重了悲剧的浓度。
(三)对日本士兵的灵魂拷问
日本侵略者历来是中国抗战片人物形象谱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侵略者阵营里的一员,日本军人在绝大多数抗战片中被描写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恶魔,但偶尔也有例外,如展现日本士兵灵魂被煎熬的《晚钟》《南京!南京!》等。《晚钟》《南京!南京!》等电影从“人”的角度批判战争以及研究战争的责任,重点暴露战争对人性(灵魂)的摧残,表现法西斯对人性的毁灭,探究个人对战争应承担的责任。其中,《晚钟》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日军小分队的受降仪式上,描画出杀人恶魔在得知自身战败时内心所经历的挣扎。片中的日本军人恰似一只只“丧家之犬”,有着最后的疯狂和最多的被可怜之处。《南京!南京!》则借渴望和平的日本军人角川之眼观察中国近代史上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南京大屠杀,目睹了队友的人性尽失后,角川放走了两个中国人,并开枪打死了自己。
《南京!南京!》片尾,角川在漫山遍野的蒲公英花海里死去,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承担起面对战争的责任,完成了自身的救赎。《晚钟》在拍摄前就将“反战”确定为影片的“灵魂”,导演吴子牛表示:“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造成惨痛的伤害。我们以一种本能、一种直觉、一种人类所共具的纯朴善良的道德和情感,诅咒这丑恶的战争!”[5]从某种意义上说,《晚钟》片头、片尾重复出现的砍炮楼意象就是“反战”主题的外化。负责引爆军火的军曹精神崩溃、日军中尉剖腹自杀后,其余日军放下武器投降,也是在这时,木桩才猛然被砍断,炮楼也应声倒塌。
《晚钟》《南京!南京!》关于人对战争责任的探讨极易使人联想到英国电影《生死朗读》,但无比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一部作品对战争、责任等命题的思考可以到达《生死朗读》的深度。故事讲述上,《生死朗读》比《晚钟》平实,姿态也不像《南京!南京!》那般过于高蹈,但《生死朗读》因其对法西斯战争根源的探寻征服了世界。无知令许多民众没有思考的能力,正因如此,他们才像零部件一般被组装进纳粹法西斯的绞肉机器,酿成一个个“平庸之恶”。影片中,意识到自己罪恶的女主角汉娜带着赎罪的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临死前,她脱去所有鞋袜站在书上,并将生前的所有积蓄捐给幸存者。男主角迈克把钱捐给了扫盲机构,希望从根源上遏制“平庸之恶”的发生。他们由此真正担负起反法西斯战争的责任。
“以生命和人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叙事从个体角度关照战争,个人不再是战场上一个个模糊的面孔和胜利的符号,而成为景深深处产生意义的焦点。新时期以来摄制的《归心似箭》《红樱桃》《南京!南京!》等抗战影片叙事重点不在战争,而在生命上。对生命的重视流露出编导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这与《拯救大兵瑞恩》(美国)、《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苏联)等反法西斯战争电影相一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二战片《拯救大兵瑞恩》把对生命的尊重推展到一个近乎极端的境地,为了一个素未谋面母亲的欢颜,米勒上尉带领八人小分队潜入德国兵据守的敌区,执行拯救大兵詹姆斯·瑞恩的任务,自身却随时面临被战争吞没的危险。苏联“二战”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体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影片运用黑白画面与彩色画面交叉对比等视听手法谴责了战争给普通人造成的不幸,烘托出战士们对生活的热爱,讴歌了生命的美好纯粹。导演罗斯托茨基镜头下的女兵丽达、冉妮娅、丽扎、索妮娅和嘉丽娅,兼具普通女性的美丽柔情和反法西斯战士的坚毅勇敢,是一代观众心目中理想女性的代表。
三、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举行会谈,随后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关系状态宣告结束,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6](P128)1978年12月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使中日两国的政府、民间交流陡然增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日关系迎来了所谓的“蜜月期”,电影创作中也涌现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清凉寺的钟声》《将军与孤女》《玉色蝴蝶》等一批强调和平的价值、反对战争,以中国和日本的普通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这些作品关注中日民间交往及其事件,抨击战争的残酷,颂扬和平的美好。战争成为故事展开的一个因素,但没有作直接表现。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由中国导演段吉顺与日本导演佐藤纯弥于1982年合作拍摄。影片反映了中国围棋手况易山一家和日本围棋手松波麟一家在战前、战时和战后的曲折命运,用两个家庭的分离聚合象征两国关系的起落沉浮。影片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诸多不幸,即使这样,况易山最终还是原谅了松波麟,国族之仇、杀子之恨消解在对方的一跪里。影片最后,两位老人登上长城,下完了那盘被战争阻隔多年的棋。被当作中华民族象征、最初作为防御工事建造的万里长城在此处也可视为一个隐喻:况易山和松波麟踏上长城,也将战争踩在了脚下。在长城上对弈的情节设置,表达了编导希望超越战争、共筑和平、共襄繁荣的心愿。
1991年谢晋导演的《清凉寺的钟声》以明镜法师访日为故事线索,引出法师的身世之谜和被中国家庭收养的温暖回忆。在日访问期间,栗原小卷扮演的日本母亲找到明镜法师,一根丝腰带把失散三十年的亲生骨肉系在了一起。《清凉寺的钟声》里明镜法师的“换装”段落耐人寻味。母子相认后,明镜法师脱下袈裟,换上日本父亲的和服,为母亲捏肩捶背,尽了儿子的孝心。突然,远方清凉寺的钟声传来,明镜法师复又换下和服穿上袈裟,其乐融融的母子相处时分宣告结束。“换装”段落前半部分导演将母子二人尽可能安排在一个画面里,二人之间没有嫌隙;后半部分则多是二人各自的单人镜头,就连母子同桌吃饭的场面也被导演拍得很疏离,摄影机远远地凝视着这对母子,镜头不肯做过多推进。“清凉寺的钟声”在片中象征着宗教的大爱,它化解了世间的爱恨情仇,使“和平”弥足珍贵的价值得以凸显。同样摄制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玉色蝴蝶》《将军与孤女》也展现了中日民间的友好交往,用超越国界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来弥合战争的创痛。
中日“蜜月期”结束后,“以和平的名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叙事也渐趋衰落,2009年上映的《拉贝日记》从第三方切入,讲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处于敌对阵营的德国人拉贝等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20万中国平民生命的故事。无论是救助者还是被救助者,都不具有战士的身份。《拉贝日记》宣扬了一种超越国家、种族、阵营的人类之爱,最终指向“和平”的主题,被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主角设定上,《拉贝日记》和《辛德勒的名单》也有共同之处,两位主人公都有纳粹党员的特殊身份,但这一身份没有纵容他们发展成不义战争的刽子手,而是成为法西斯大屠杀中一张庇护生命的通行证。德国人拉贝和辛德勒用一己之力减少战争灾难,以和平的名义反思战争。
其实早在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拍摄《拉贝日记》前,电影大师谢晋就有了创作同题材影片的想法,只是当时迫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体现出大师目光的前瞻性,当其他导演还在关注“战争”和“生命”的时候,谢晋已将自己抽离出来,进行更有高度的关注。他仅有的两部抗战题材电影《清凉寺的钟声》与《拉贝日记》(未能拍摄)都聚焦“和平”的主旨,希望用敌对双方民间的交往化解战争的仇恨。
结 语
中国抗战题材电影发展到今天,形成了“战争”“生命”“和平”三大主题。其中,以“战争”为主题的影片数量最多,是经典和原型模式,在后来的发展中,此类影片在保持基本主题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调整变化,其创作一直延续到当下。以“生命”为主题的抗战电影主要出现在新时期以后,国内进入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国际上中美、中日建交,战争阴影日渐消除的大背景下,其创作也持续到当前。以“和平”为主题的抗战片则主要诞生在新时期,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代表性。在近年来新的世界和中日关系格局中,“战争”和“生命”融合的主题居多,以“和平”为主题的作品鲜有。
其实,作为基本价值,战争与和平、生命之间是存在某种张力关系的,中国辩证法(作为思想方法)里有关于“矛盾”双方的理解,当年杨献珍受中国传统思想启发提出的“合二而一”的观点便是其中代表。杨献珍强调“和”的哲学,认为不应只讲斗争性,忽略掉事物的同一性,这一思想与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产生了重大分歧,并由此招致了严重的批判与迫害。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今天,冷战“铁幕”已然落下,“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这次争论,应该看到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的哲学观是很有价值的,与近期我国在外交上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主张的“利益攸关方”提法颇有共通之处。
反观当下抗战题材作品的创作,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涉及对战争和生命的思考,但是集中探讨战争中敌对双方如何化解的作品数量还是较少,而且屏幕上大量流行的“抗战神剧”仍在用十分刻板化的战争观指导创作,或一味强调民族间的对立和斗争,或只顾娱乐和“圈钱”,缺乏对战争更深层次的关照。说到底,抗日战争题材电影中“战争”“生命”“和平”三种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对其应有不同的侧重。在今天“和平发展”作为国际潮流和基本国策的背景下,三种主题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为人类反思战争、汲取历史教训、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以促进中国和人类社会长久的稳定和繁荣。
(责任编辑 彭慧媛)
[1] 胡克,赵宁宇,李镇,詹庆生,尹鹏飞.国产抗战(反法西斯)电影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当代电影,2015,(8).
Hu Ke, Zhao Ningyu, Li Zhen, Zhan Qingsheng and Yin Pengfei,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of the Domestic Anti-Japanese War (Anti-fascist) Films,ContemporaryFilms, No 8, 2015.
[2]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
Cheng Jihua (ed.),HistoryoftheDevelopmentofChineseFilms, Beijing: China Film Press, 1963.
[3]《中国大百科全书(普及版)》编委会.风林火山 细数二战风云战役[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Editing Committee of China Encyclopedia (Popular Version) (ed.),FenglinShanhuo:OnWarsintheSecondWorldWar, Beijing: China Encyclopedia Press, 2013.
[4]杨光远,翟俊杰.《血战台儿庄》导演艺术总结[A].中国电影年鉴1987[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Yang Guangyuan, Zhai Junjie, Artistic Conclusion of the Director on The Battle of Taierzhuang,AnnalsofChineseFilms1987, Beijing: China Film Press, 1990.
[5]吴子牛.《晚钟》导演阐述[J].影视文化,1990,(3).
Wu Ziniu, Director’s Interpretation on Curfew,FilmandTVCulture, No 3, 1990.
[6]刘守旭,徐萍.大国风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历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
Liu Shouxu and Xu Ping (eds.),DaguoFengfan:TheHistoryofChina'sDiplomacy, Beijing: World 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 2013.
War,PeaceandLife:ThreeThoughtsontheFilmsthemedonChineseAnti-JapaneseWar
Chen Xihe, Liu Jiyuan
Based on the films themed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produc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studied the values of the films. As a result, three narrative modes are found: just war (the Anti-Japanese War) against fascist war, life and humanity against fascist war, and peace against fascist war. These three modes concern the expression of values in terms of war, life and peace, which, although being different,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These value judgments are not only products of the directors and editors but also response to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hen these films are produced.
Chinese films themed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ti-fascist war, war, peace, life
Abouttheauthors:Chen Xihe, Professor of Shanghai Film Institute at Shanghai University; Liu Jiyuan, PhD candidate of Shanghai Film Institute at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
Thepaperisfundedbythefollowing:Results of the Peak Discipline in Film Studi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in 2015-2016.
2017-10-21
[本刊网址]http://www.ynysyj.org.cn
2015-2016年度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成果。
J90-02
A
1003-840X(2017)06-0077-09
陈犀禾,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吉元,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6.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