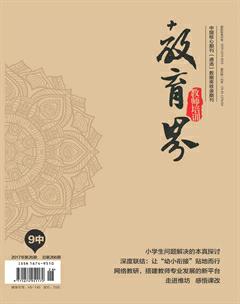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陆嘉明
(续前)
69
出入乱世,剑指天下。是非功过,任由历史评说。
成也好,败也好;舍也好,得也好,淡泊致远而无愧平生之志,从容达观而不失英雄本色。
隆中预言天下三分。力助刘备匡汉顺天应物而据其一,建立西蜀,扶其登基称帝,终遂出山建功立业之愿。
建蜀伊始百废待兴,身为相父辅佐后主刘禅励精图治国力大增,“两川人民,忻乐太平”,终不负先帝托孤遗愿。
时值南蛮犯境边臣作乱之际,毅然亲自率军远征,七擒七纵蛮王孟获,刚柔并举攻心为上,终而平定叛乱,祭水凯旋,消除了外患内乱而国泰民安矣。
戎马倥偬二十年,始终在“隆中对”的蓝图上行走,始终在“三分天下”的梦想中角逐,立下赫赫战功,创出煌煌伟业。
诸葛亮者,功成名就之英雄也。
所成者,时也,势也,机遇也;亦志也,智也,知遇也。
然而,成也于斯,败也于斯。成者于斯,在于得;败者于斯,在于失。
诸葛亮平定南蛮后,于建业五年(227)即上表后主率军北伐中原,直至建业十二年(234),先后六出祁山与曹魏交战,惜乎在数年的双方胜败交错的胶着形势下,终而六战六败,不仅无功而返,竟又命丧征途,从此一生心血皆付之东流矣。
难道诸葛亮真个计穷智竭了吗?
非也,乃失天时失大势失机遇也。
其实,诸葛丞相出征前,自也心中有数,对时势了如指掌。《出师表》一开头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是啊,自彝陵惨败尚未复原;倾力征蛮损耗实力;况又地处僻远国力贫弱;且曾与东吴结怨,巩固盟约还有待时日;而曹魏称雄北方力量最强,虽兵戈未起却始终虎视眈眈于东、西大地……所谓“危急存亡”并非虚言啊。
既然人富我贫,人强我弱,人无安危之虞,我有存亡之忧,贸然出击北征伐魏,时未到,势又未得,机遇更未见端倪,那么,丞相何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情也。用情太专,太深,太重,在日月的流转中固化为一种解不开的心结,一种风雨无憾的执念了。
天地无涯,人寰难测。即如大智大勇者诸葛亮,一旦被情捆绑,也难脱天地人寰的变幻和劫数。
何情之有?历来非常知遇之情,人世难能可贵的感恩之情也。
那也有错?当然没有错。不但没有错,而且知恩图报向来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崇高品德和操守,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标杆。问题在,“知恩”是心,“图报”在行。心不可变,报当合时顺势,得其机遇而以涌泉出之,报则有功有利,有理有节,郁郁乎如高树入云,潺潺乎如活水长流。反之,则往往不合时宜逆势而上,弄不好即如一叶小舟遭遇滔天风浪,难免樯折桅断甚至于遭遇灭顶之灾。
这种浅显的道理,常人也懂,何况智者?
不错,诸葛亮是智者,更是君子,深挚儒家文化,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报效以诚,天地为之感泣。先主曾有遗诏托孤,又留遗志匡扶复汉一统天下,诸葛丞相一一应诺,并在蜀帝病榻前信誓旦旦:“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是的,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铭刻寸心永世不忘,十七年超越尊卑的患难与共的泣血之情,念念于兹,日月可鉴。因之,谨遵先帝遗志出师伐魏,实出乎此种“情”也。这在《出师表》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由此看来,奉受先帝临崩托付,夙夜忧叹不已。忧也者,巴蜀僻处西南一隅,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叹也者,先帝遗志一统天下,迄今依然前程渺茫。自忧自叹自多情,半生沧桑半生担当。
岁月不饶人,心里真个有点急不可待了。原来这出师伐魏攘凶除奸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实为应先帝遗志而报知遇之恩,又为恪守尽忠而报托孤之责。一一皆出乎一个“情”字啊。
这个“情”字,落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便诞出一个“义”字;落在纷纷扰扰的人群中,则可博得一个“和”字;落在温温润润的人的心里,尚能漫出一个“真”字;落在跌跌宕宕的文学畛域中,那当仁不让可得“真、善、美”三个字矣。
《出师表》有别于历朝历代的表章奏疏之文,堂而皇之地跻身于古典美文之列,首在情真意切,寸心毕现。既俱为“父”者的苦口婆心声声叮咛,又闻为臣者的忠心谏言铮铮作响,慈父心肠忠臣肺腑,读来感人至深。
二在大气浑然,理脉可寻。作为相父双重身份的谆谆告诫,无儿女情长的温软柔态,有治国安邦的风云气象;非为谨小慎微的沉郁婉转,却有淋漓痛快的迫烈陈情;也不是忧患无已的芊绵咏叹,却露出征挥戈的纵横豪宕……意在规劝后主立大志,亲贤人,远佞臣,纳雅言,谨自谋,行善道,旨在“深追先帝遗诏”。为君者是,为臣者也是。可见表章叙实情与寄虚灵互为生发,理脉循循可寻,至道郁郁而起,自有理性的力度。
三是文辞朴质,不求自工。作为上奏的表章,重在务实、说理、建言,是非臧否皆依缜密之思逻辑之据情采之敷简约之言循循出之,情理脉动,辞达而尽。《出师表》所奏事之大、理之深、情之真、辞之简出类拔萃于历代奏章,虽说出语平扑无意藻饰,然以特有的文学价值,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美学印记。
说到这里,愚之用笔则要绕个拐角来个大转折了。依然是那个“情”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半生因之成就大业,半生因之失败告终,悲乎抱憾饮恨魂归五丈原;壮哉六出祁山屡败屡战尽显智者风范英雄气概!
真的,他没有倒在失败的脚下,始终有一腔无声血挥洒在中原大地上,有智慧之光闪烁在精神高地上。
乱云飞渡仍从容。是的,他输了,却赢在侠风义胆上,赢在坚韧不拔的骨气上,赢在逸兴壮思的遒烁气势上……
不是嗎?那些个耳熟能详的段子,诸如空城之计、减兵添灶之计、装神弄鬼之计、木牛流马之计、木像惑敌之计、预设锦囊之计……虽一一皆为败退之策,却使同为大智大勇如司马懿之流闻风丧胆,顾盼惊慌进退两难。战事败绩,精气神却依然如故,不减当年!
他还是累倒在那个“情”字上的啊。
为报知遇之恩,为担托孤之责,尽管伐魏时机未到,祁山之外也非有利时区,如前所说,明知不可为仍决然为之也。
《出师表》,是超越阴阳相隔的对先帝遗诏的一个回应,一种倾情的告慰;也是对无能后主的一个深情告诫,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情怀。孤军伐魏,逐鹿中原,无论胜败,都是心的告白,情的倾诉。一段情,既已用一生的心血和智慧来报答了,又何惜用自己的安危乃至生命来偿还呢?
血性男子当如是。
伟伟大丈夫当如是。
有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成也英雄,败也英雄。诸葛先生孔明者英雄情怀如是也。
杜甫曾作诗发豪慨: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是啊,一掬英雄泪,绵延成历史的长河,长流不息感启后人;一腔英雄气,凝结为岁月的沧桑,悉皆由时间来诠释生诠释死。
愚唯感到,人生难得如此,而时惭一己之渺小。
70
天数茫茫,世事纷扰。乱世无统无治也无序,兴衰存亡,既在天,也在人。天人交集处,世间诸事和历史过客,冥冥中果真自有定数?
魏蜀吴三国鼎立,称王称帝各自为政,依然纷争不断怀远天下。但经血腥交锋残酷并吞,蜀先灭于魏,继而魏又亡于晋,鼎立三足,二足先断,唯剩东吴一方孑然而存,虽然艰难竭蹶独足难支,却延以时日,立足最为长久。这不能不说到孙权建吴立国的伟伟功业了。
说起来,论雄才大略,吴主不及魏主曹操,论宽和至仁,也不及蜀主刘备,然其刚柔得兼以及阴阳交合的纵横之道,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尽管在罗氏笔下,吴主戏份不多,但每每挺身于风起云涌惊涛拍岸处,飒飒英气逼人,戎马倥偬激起惊天一鸣;而每每于柳拂残月水起柔波时,则融融暖情怡人,君臣相顾化为春风一缕。
《周易》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位诞生于江南富春山水间的乱世英雄,其人格和性格也许约略合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时或观乎“天文”和“人文”,恰有山之定力,有水之至刚至柔的秉性,剑气凌云和灵动若水的双重性格,果然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不仅稳守父兄开辟的这片广袤的江东大地,而且自19岁从兄长孙策手中接过治吴印绶,直至登基称帝凡51年,而过古稀之年寿终正寝矣。
真不可小觑这位显赫一世的乱世英雄,活,比曹、刘活得潇洒,活得沉稳,活得左右逢源;死,也死得坦然,死得尊严,死在江山维稳功绩昭著之时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