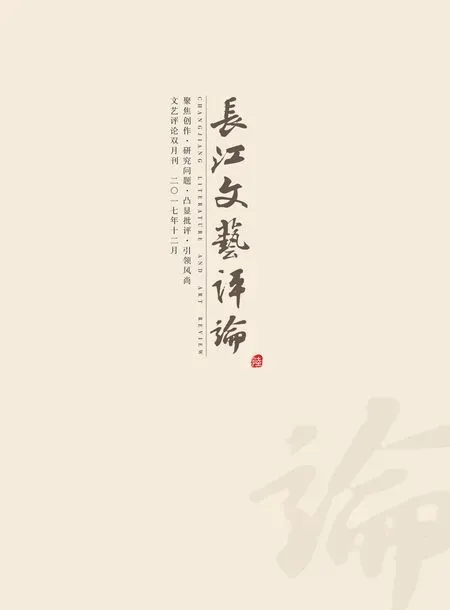走出纸房子
——我的批评观
◎ 李松睿
走出纸房子——我的批评观
◎ 李松睿
写“我的批评观”这样的题目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惶恐。毕竟,这更像是好为人师的批评家在退休后强行向晚辈“推销”所谓成功经验时写下的文章,旁人看了或嗤之以鼻,或随便翻翻,并不会真的当一回事。不过换一个角度想,这样的文章虽然对别人未必有什么价值,但于我自己却又是一个颇为难得的机会。这几年被编校稿件、读书、写作以及开会等各类事务逼得团团转,使得自己只能勉勉强强跟上工作的节奏,几乎没有机会仔细想想,我的批评风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文艺批评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后的学术道路又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那么,借这篇文章停下来想一想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回顾过去、整理思路,让我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意义更加自觉吧。
十多年前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正好赶上陈思和教授担任系主任时主导的教学改革,强调让本科生以新批评的方式精读原典,摒弃各类文艺理论的中介,珍视阅读文学作品时的最初感受。我那时从这一套学术训练中获益匪浅,但同时也误以为批评工作不过是靠着才情与灵感书写阅读文学时的感受,是所谓灵魂在作品中的伟大冒险,根本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学问。因此,虽然我当时觉得与当下生活有着紧密关系的当代文学更有意思,但在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时,还是选择了已经充分经典化、历史化了的现代文学。在导师吴晓东教授的指导下,我一方面“恶补”在批判理论层面的欠缺,集中阅读了一批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书籍,完成了在知识结构上的更新;另一方面则像北大中文系大多数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在图书馆旧报刊阅览室里翻阅那些20世纪20、30年代的报刊,以触摸原始文献的方式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后来和吴老师一起编辑、整理的《太阳社小说选》就是那段时间“泡”图书馆的成果。
当时,我每天一觉醒来就跑到图书馆旧报刊阅览室的一个固定角落里查阅民国期刊,旧报刊阅览室下班后则转移“阵地”到其他阅览室,等到晚上十点图书馆闭馆再回宿舍看两三个小时书,这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不管是否真的为学术做出了贡献,单纯沉浸在这样忙碌的生活状态中,就会使人产生出全身心投身学术事业的幻觉,也让我感到十分充实,没有虚度光阴的遗憾。然而,时间久了,每天坐在旧报刊阅览室那张古旧笨重、漆面斑驳的书桌前,小心翼翼地翻着那些书页发黄、变脆的民国期刊,也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怀疑。将鲜活的生命投入到那些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些报刊上长篇累牍的民国旧事,又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有什么联系?如果学术研究只能进行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生活带给我们的困惑,无法真正回应外部世界普遍关切的问题,那么,它是否只是学术界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只能用来满足学术从业人员的虚荣与幻想?
正是这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使我在选修戴锦华教授开设的选修课“后冷战时代的文学与电影”时格外受到触动。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我惊异于戴锦华那优雅的风度、清晰的思路、雄辩的口才以及华丽繁复的用语方式。特别是她令人信服地从冷战后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变迁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与电影,揭示出文本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脉络,让我一下子明白文学研究还可以以这种方式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发生互动,彻底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如果说吴晓东老师教给我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细致入微地分析文本的能力,那么戴锦华老师则引导我打破封闭自足的文本世界,寻找文学与世界之间的种种交集,并将文学研究当作理解社会生活的途径。由此,我认识到批评工作并不一定是所谓灵魂的冒险,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身处学院的知识分子面对世界、介入现实的一种独特方式。
后来,我之所以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余,抽出时间和精力对当代的文学、影视剧乃至美术等各类作品进行批评,就与获得了这样的认识有关。因为在评论当下流行的文艺作品时,我能真切地感到自己与现实生活发生了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本身可能是虚妄的。我很清楚,某种特定的批评路径在今天非常流行,甚至已经成为俗套。只要是那些在市场上获得广泛影响的文本,评论家就会在讨论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将这些作品与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用诸如“症候”、“张力”、“抚慰”等貌似深刻的术语予以评说,似乎只要不在文章的结尾例行公事似的谈论一下这样的话题,批评就显得没有深度,不够精彩。回过头来重新翻检自己发表的那些批评文章,我发现其中也多少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每每想到这里,就感到十分惭愧。
不过,我仍然认为批评不应把视野完全局限在文本内部,而是要始终带着对时代的思考进入文本。在长年累月的读书与写作中,知识分子往往会将自己禁锢在“纸房子”里,把知识看成力量的源泉,把引用当作学术的传承,把阅读变成生命的意义,把文献视为炫耀的资本。他们陶醉于前辈大师的智慧与成就,热衷于勾连起纸张与纸张之间的内在联系,身处用书籍垒起的囚室而乐此不疲,不愿意“浪费”一点点时间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看上一眼。而注重对当下的文艺作品予以迅速回应的批评,恰恰可以在“纸房子”的墙壁上打开一扇窗,让我们呼吸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新鲜空气。必须承认,批评面对的也仍然是纸张或屏幕上的文本,其实并没有和真正的社会生活相接触。然而,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知识赋予的“特权”使他们可以超越民族、性别、肤色、阶级等一系列身份、差异带来的桎梏,让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多样化的视角以观察时代与社会。如果说普通人只能在社会、文化给定的位置上理解自己的生活,那么知识分子则可以用知识带来的多重视角,超越某一社会位置带来的局限,从整体上反思这个世界。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如果离开文学的中介,直接对现实问题发言,其实并不能提供比普通人更加高明的看法,但面对携带着鲜活经验的当代作品,却能够借助专业训练思考和回答一些让研究者本人感到困惑的现实问题。毕竟,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都生发自研究者的生命经验和现实困惑。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批评的价值所在。
也正是带着这些想法,我从读硕士期间开始“不务正业”,尝试跨越学科壁垒去关注当代的各类文艺作品,并在此后的七八年里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在写作这些或长或短的文字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虽然自己从事批评工作是为了走出“纸房子”,使学术与社会现实发生呼应,但在实际操作时却不能不对某些拙劣的批评套路与窠臼保持警惕。毕竟,所谓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在批评中将文本随意地与某些产生广泛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联系起来,也不是在文章结尾处曲终奏雅般用“压抑—抵抗”或“宣泄—抚慰”模式解释某些作品的流行,而是在深入剖析文本的前提下,分析外部现实如何渗透到文本的内在肌理之中,并由此出发展开批评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你的文章一读就知道是搞现代文学的人写的。甚至有一位老师曾私下透露,当初在盲审一篇论文时,觉得肯定是吴晓东的作品,后来等到文章发表出来,才知道作者是我。之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印象和看法,可能是因为我虽然在写批评文章,但分析文本的方式却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经历了新批评式的训练,后来的导师吴晓东教授又特别强调文本细读,使得我阐释文本、分析问题的切入点,总是包括叙述语言、主题意象、人物形象、景物描写以及情节结构等在内的形式特征,并努力思考这些特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批评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阐释作品,而作品究竟写了什么,其实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能够予以领会。因此,批评的关键并不是呈现作品写了什么,而是说明作品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写作,这种独特的形式背后又蕴藏着哪些东西。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处在文艺作品的内部,仅仅与纯粹的审美有关,社会生活的万事万物其实也与文艺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诸如时代环境、政治立场、阶级地位、生存困境等问题带给艺术家的一系列压力与限制,最终会在作品形式上留下无法磨灭的印痕。因此,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征一边联系着作品的美学特质,一边则与作品所属的时代紧密相连,是批评必须详细考察的中介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艺术家本人并未想清楚,或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问题,也会在不经意间刻印在他创造的艺术形式中。这就使得我们用不着太在意作者的“权威”,也没有必要把作者对作品的阐释奉为圭臬,而要尽量寻找批评家自身的关切与作品形式间的契合之处。只有这样,批评才能摆脱为作品提供注脚的窘境,真正成为思想表达的手段。当然,这么说也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脱离作品随意发挥。在批评中,还是应该尽量让自己像老到细致的侦探那样,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作品形式上的种种印记,分析这些印痕的来龙去脉。或许只有这样,在以批评的方式对外部现实发言时,才能突破粗疏、空洞的惯常套路,把思考真正落实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借着写这篇文章的机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自己这几年写下的各类批评文章,总会发现其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并意识到自己走过了种种“弯路”。当年由于受到戴锦华教授的影响,原本秉持着“精英趣味”,对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毫无兴趣的我,也开始在北京的胡同里寻找各种隐秘的“淘碟”小店,并对镜头语言、场面调度、用光布景等电影形式颇下了一番功夫,这才写了一些与电影相关的评论文章。博士毕业后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机缘巧合地被首先分配至《艺术评论》编辑部工作。那时,领导因翻看我的简历误认为我是“搞电影的”,于是处理了不少与影视相关的稿件,也就顺便继续玩票儿式的做了做电影批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那样的工作环境里,自然会有很多机会与从事各艺术门类研究的学者接触,于是我也就在一些老师的“怂恿”下写了几篇美术方面的评论文章。
不过,虽然我觉得这些电影、美术类的批评文章本身写得并不算太糟糕,也获得了不少肯定,然而自己却多少会感到有些不满,乃至遗憾。批评看似简单,但对批评家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都有着极高的要求。真正出色的批评,不仅要能敏锐地捕捉作品本身的风格特色、艺术手法,还要将它们放置在史的维度上加以考察、辨析。这里所谓史的维度,既是指要将艺术家还原到文学史、电影史或美术史的脉络中予以准确的定位,也意味着要把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形式、风格特征放到艺术发展史上进行考量,判断它们究竟在哪些方面超越、修正、改变了前人的成果,还是在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我在从事电影、美术等领域的评论时,虽然自认为还能够把握批评对象的形式特征,并努力结合时代、思想背景对形式问题进行分析,但由于知识结构、专业训练的不足,始终无法将形式还原到形式自身的历史中予以讨论。对于批评文章的写作来说,当然有很多叙述技巧可以“藏拙”,让读者不把这方面论述的缺失当作一个问题,但批评家本人却应该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白自己的缺陷究竟在哪里。每写完一篇文学批评类的文章,不管写得究竟好或不好,心里总觉得很踏实,而写完一篇电影或美术评论,我的内心深处却会隐隐感到不安。因此,这两年随着自己调至《文艺研究》编辑部负责编校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稿件,我在批评方面也逐渐推掉了一些艺术批评方面的约稿,把工作重心更多地转移在文学批评上。毕竟,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与其去写一些自己也没有十足把握的文章,不如在真正熟悉的领域里把工作做好。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不是要写这篇文章,我其实不会停下来集中思考所谓“我的批评观”,因此,前面谈的其实只是我理想中的批评大致是什么样子,以及今后自己应如何去努力,而不是在总结自己过去几年的批评实践。那种一端扎根于深厚、广大的社会生活,另一端渗透进艺术形式的内在肌理,成为学院知识分子呼应时代、表达思想的手段的批评,是我心向往之却力有不逮的。希望自己能借这篇文章理清自己对批评的理解后,能够在今后的努力中与那理想中的批评更近一步。
【青骑士档案·李松睿】
李松睿,1983年生于北京,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影视剧研究等。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各类文章八十余篇。出版专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文学的时代印痕》。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