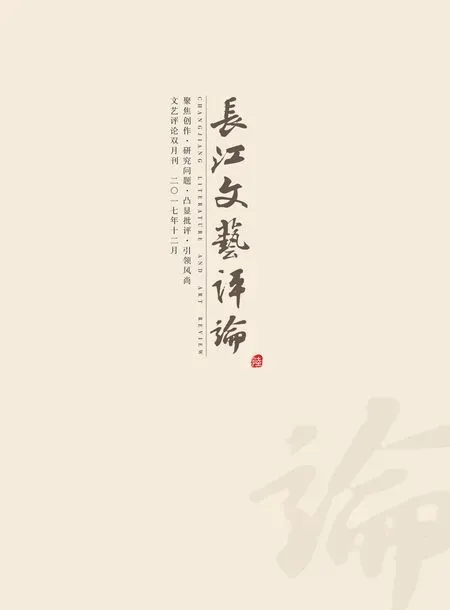好青年李松睿
◎ 鲁太光
好青年李松睿
◎ 鲁太光
跟松睿接触,很容易为他身上那种独特的气息所打动。一张圆脸,白净,帅气,上面总是浮着浅浅的笑意,既不冷淡,也不张扬,让人觉得明亮、踏实、自然。接触久了,你就会发现,这是松睿的标配。即使跟人争论,他也不急不躁的,一边笑笑地倾听,一边从容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在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之前,我就知道,那里的青年学者,朋友之间开玩笑,喜欢以“好青年”相称。这样的称谓,有点儿亲密,有点儿调侃,但更多的,却是对对方为人为文的肯定。
但这只是松睿的一面。在跟松睿交往、交谈时,我注意到,除了明亮、从容、自然,他还有敏锐、犀利、通达的一面。在跟人交流时,他那原本就明亮的眼睛,常常会极快地一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道微小的闪电,从那里一掠而过。这往往意味着他已经领悟你谈话的核心,看透你谈话的指向,或者,干脆抓住了你的破绽。在这个混沌的时代,人人都难得糊涂,难得有清醒的思考者,因而,松睿的敏锐不仅没有影响他的明亮感,反而让他更加明亮,更加“好青年”了。
明亮,从容,敏锐,这就是松睿给我的印象。我以为,这也是解读松睿文章的几个关键词。
随着中国社会大转折,自19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就开始分裂——现在,这种分裂不仅没有得到弥合,反而以一种更加极端乃至病态的方式演进、恶化着——从那个时候开始,知识界就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很多时候,立场排斥思想,偏见取代知识,轻慢压制客观,再加上文人相轻的老病根,知识界可说是乌烟瘴气,攻讦怨怼成为常态,很少见到清醒的文章。评论文章,要么无原则地“表扬”,要么无底线地“批评”,少有通达、客观之作,更不用说明亮、从容之作了。
在这样的氛围中读松睿的文章,无疑是一种幸运,一件乐事。文如其人。正如松睿的明亮、从容一样,他的文章也是那么的明亮、从容。这倒并不是说松睿的文章没有立场,恰恰相反,他的文章有坚定的立场。而是说,他的文章有一种可贵的说理精神,有一种难得的从容气度。即使所谈对象十分敏感、复杂,甚至争议巨大,他也能不急不躁地展开论述,以理服人。他对张承志《心灵史》新旧版进行对读的文章《“自我批评与正义继承的道路”》就很好地展现了这种气度。
我们都知道,张承志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文学界、思想界断裂的象征性人物,文学界、知识界、思想界对张承志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势同水火:认同张承志的人,认为他是鲁迅后中国唯一的作家,是中国的良心;反对张承志的人,认为他无知、傲慢,认为他偏激、极端,认为他鼓吹革命、煽动暴力。在这样的氛围中,研究张承志的文章,大都带着个人好恶乃至偏见,因而情感宣泄往往压制了理性分析。松睿自然知晓张承志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场中的复杂性与重要性,知道围绕着张承志及其《心灵史》所展开的长时间的争论,“使得这部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思想文化界在价值观念、道德立场、知识背景以及情感结构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裂隙”,然而他却没有像诸多研究者一样停留在这个“裂隙”上,而是将其当作一个出发点,当作理解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把“钥匙”,正因为如此,他在文章中没有“意气用事”,而是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心灵史》两个版本进行了字斟句酌的对读,指出相较于旧版,改订版《心灵史》虽然激情有所隐退,但思想却更加开阔,宗教意识也更加超拔。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张承志将哲合忍耶与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风潮、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排斥在外的底层民众放置在同样的结构位置上,形成一条独特的思想脉络,才使得改定版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始终能够在波诡云谲的人物、事件中,辨析出富有与贫穷、压迫与反抗、强权与弱者、主流与少数等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对立关系,从而获得灵活多变的批判立场”,这种灵活多变的批判立场表明,张承志通过其书写,“构成了一条投身底层民众的‘自我批评与正义继承的道路’”。在完成了充分理性的辨析之后,松睿才在文章结尾以极其精练、诗意的文字揭示张承志及其创作之于我们的意义,即他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有繁荣、进步与资本的狂欢,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那些不被人留意的角落还存在着无数苦难,我们或许无法拯救那些被剥夺至一无所有的底层民众,但至少应该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尽可能地向他们伸出援手。”在有了充足的理性铺垫后,这样的感性吁请才格外动人。
看了笔者引述的简短文字,相信读者会发现,松睿的文章不仅有说理精神、从容气度,而且还敏锐、犀利、通透。这也是我欣赏松睿其人其文的另一个原因。我在上文说过,在跟人交流时,松睿原本就很明亮的眼睛经常一眨一眨的,每当这时,就好像有一道微小的闪电从他眼前掠过。这道闪电暗示我们,他已经抓住了你话语中的秘密或者漏洞,只是出于礼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他不愿意直接说出来。
在生活中他是这样的温和、内敛,几乎不露一丝锋芒,可在文章中他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把自己的敏锐与犀利,展现得淋漓尽致。于是,在他的文章中,那些原本无比周全、自洽的事物、现象或道理,都不那么周全、自洽了,甚至变得捉襟见肘、破绽百出。比如,一般的研究者处理在晚清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文学时,“通常只在两个问题上做文章:要么探讨晚清翻译文学是否忠实于原著;要么探讨晚清翻译文学如何影响了清末新小说以及后来的‘五四’新文学。”这两种思路看似不同,实际上却共享同一种思维模式,即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第一种研究思路把翻译文学的最高标准视为与原文相同,因晚清翻译文学与原文之间的差异而视前者为不好的、不成熟的或不那么‘现代’的翻译。第二种研究思路则把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形式要素作为衡量小说是否现代化的标准,因晚清翻译文学不符合西方小说的标准,也就相应的不够现代,只能在从古代到现代的‘过渡’意义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松睿则通过对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TheWaroftheWorlds(今译《星际战争》)与由晚清翻译家心一根据这部小说翻译的《火星与地球之战争》细致对读指出,晚清翻译文学中“那些所谓的错译、误译、曲译,以及有意删改等情况,就不是翻译者的翻译水平、翻译态度问题,也不是某种过渡时代的‘遗迹’;这些‘错误’恰恰就是东方与西方遭遇时发生对抗的战场,晚清一代中国人或许就是通过这些抵抗,展开他们对现代中国、现代世界的想象。”这样的发现,不仅犀利,而且重大,甚至可以挑战晚清文学的研究范式。
在松睿的文章中,这样的发现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在研究《大宅门》系列电视剧的文章中他就指出:“与其说《大宅门》的成功是由于其制作品质,不如说是这部电视剧所蕴涵的某些因素呼应了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审美需求、情感结构,使它能够受到全国观众的热情追捧。在时过境迁之后,当整个社会在近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大宅门》系列电视剧原本所具有的‘灵氛’与魅力消失不见,其被观众抛弃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这样的发现,无异于当头棒喝,将那些沉迷于剧情不能自拔,甚至于把自己当作剧中人的观众惊醒,使其不仅关注“舞台小世界”,而且还要由此反观“天地大舞台”。再比如,在研究热播电视剧《潜伏》的文章中,他通过对官方、制作方、观众对这部电视剧关键词“信仰”的不同认识及其龃龉进行细读指出,“这一现象表明,21世纪的中国观众不再像80、90年代那样选择一种拒斥‘官方’的姿态,也没有完全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而是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定位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职场成功人士。从这个角度来看,《潜伏》中的‘信仰’正像余则成的间谍身份一样多变莫测,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与‘去政治’式的历史表述的失效,似乎暗示着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正在浮出水面。”这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的,是文本内外的巨变,其启发性以及由这启发而带来的新鲜感,刺激人思考,刺激人警醒。
松睿的导师吴晓东老师也格外激赏松睿的敏锐,认为松睿的文章是“形式研究的独异风景”,他还进一步指出,“形式所积聚的‘意味’往往更加内在,形式中所隐含的内容往往更加深刻,形式最终暴露的东西也往往更加彻底,形式更根本地反映了一个作家的思维形态和他认识世界、书写世界的方式。”吴晓东老师的这段话,是对松睿研究特色的总结,但也无意中透露了松睿研究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认识世界,而后,书写世界;或者,书写世界,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世界。我个人以为,正是由于对于现实的执着,才使松睿越来越敏锐、犀利。在一篇研究徐冰的文章中,他干脆引用研究对象的一句话,以“紧紧抓住时代”作为文章的题目,徐冰是为了紧紧抓住时代而创作,松睿又何尝不是为了“紧紧抓住时代”而读书、思考、研究、书写的呢!
抓住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松睿的敏锐了,就会理解松睿文章中犀利的批判意识了,因为,他不过是从文艺这个“形式”出发,探究现实的“内容”,或者说,把为现实所遮蔽的“内容”呈现出来,就像他在文章中盛赞的徐冰的《凤凰》:“当那两只凤凰最终在北京CBD地区‘飞翔’起来的时候,它们用自己布满建筑垃圾的身体在四周由玻璃幕墙组成的现代城市空间中,打开了一个通向‘背后的故事’的缺口。透过这个缺口,我们看到的是无数劳动者为建造现代城市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被盘剥压榨的底层人民的血与泪,是现代大都市隐藏在亮丽外表下的残酷与狰狞……”毋庸讳言,松睿的文章没有“凤凰”那么浩大、醒目,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他一直努力着要撕开这个世界光鲜的形式,让人们看到“背后的故事”。
这无疑是选择与“鸡蛋”站在一起,而非与“石头”站在一起。而这,是需要勇气的。在研究张承志改订版《心灵史》的论文中,松睿这样评价张承志的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张承志的选择无疑是特殊的。毕竟,在权贵与底层、正统与异端、压迫与反抗、强权与弱者以及主流与少数等选项中,如何选择以及抉择背后的不同命运是毫无悬念的。这是一场胜负已定、强弱立判的战斗。选择了前面一组选项,意味着与胜利者站在一起,加入到书写历史的阵营当中,拥有富足、美好、充满希望的生活;而选择后面一组选项,则是不识时务地与失败者为伍,将必然面对着充满坎坷、苦难、不公的悲惨境遇。在形势分明的情况下,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然而,反抗的声音、弱者的呼喊虽然注定是微弱的,但其意义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在面对杀戮、压迫、欺凌、不公的时候,良心尚存的人们或许出于自保而无所行动,但内心世界却多少会泛起一丝波澜。这恰恰是正义与公道尚存人间的铁证。”通过接触松睿的“人”,通过阅读松睿的“文”,我时常能感受到他心中的“波澜”。有这“波澜”在,就证明人心还没有死,正道还没有死,希望还没有死。而只要人心不死,正道不死,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就还有“年轻”的希望与可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松睿是个“好青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自己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好青年”。而我自己,自然愿意加入这“好青年”的队伍,努力呐喊前行。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注释:
[1]李松睿:《“自我批评与正义继承的道路”》(未刊稿)。
[2]李松睿:《文学的时代印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第3页。
[3]李松睿:《社会转型与时代的“灵氛”》,《文化研究》(辑刊),2015年第 1期。
[4]李松睿:《潜伏:以“信仰”的名义》,《粤海风》2012年第2期。
[5]吴晓东:《形式研究的独异风景》,《文学的时代印痕》,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序”第2页。
[6]李松睿:《“紧紧抓住时代”》,《艺术手册》,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