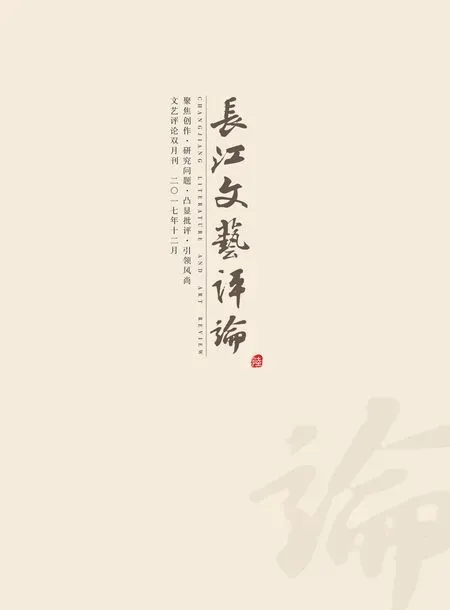当代中国书法“势”的审美崇尚
◎ 王太雄 王子亭
当代中国书法“势”的审美崇尚
◎ 王太雄 王子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特色,与之相应也有各自时代的书法审美崇尚,于是在几千年悠久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中国书法审美崇尚就链接成一条较为明晰凝练的主线或脉络:殷商秦汉之尚象,魏晋之尚韵,隋唐之尚法,宋人之尚意,元明之尚态,清人之尚朴。而现如今已成为一种纯粹视觉抽象造型艺术的当代中国书法,与其现代性本体特征和现代人文环境、展示方式、欣赏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艺术观念相适宜,突显为“势”的时代书法审美崇尚。
首先,当代中国书法的审美崇尚之所以为“势”,是由当代中国书法的两个现代性特征所决定的:一是书法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分离。从现代汉字书写工具的运用到毛笔退出汉字实用性的书写,再到计算机的汉字虚拟的“以敲代写”成为主流书写方式的今天,当代中国书法创作和研究已经具备了不考虑其实用性而纯粹探索其艺术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依康有为的说法:“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基于创新的要求,每个时代都面临自己的“古今”问题。对于当代中国书法来说,古者,书法之实用与艺术“同体而未分”也;今者,则为纯艺术之研究也,其探索的问题是书法艺术审美形象的创造和书法艺术的形式构成。谈形象,谈形式,谈构成,自然会引出时代书法审美崇尚的议题,自然会关注当代中国书法“势”的审美崇尚问题;二是当代中国书法美学发生了重大转型。基于对书法艺术性的强调,对书法形式自律性的探索成为当代中国书法美学的重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对中国书法的深入探索,从书法艺术的本体上予以了定性,澄清了书法艺术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书法意象的审美特征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书法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体两面的统一体,书法的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书法的内容即其形式自身。其形式或内容就是表现各形式要素,诸如点画、结体、字组、行列及章法的笔墨趣味、形式之美与空间关系。强调书法的艺术性和其形式自律性,绕不开书法艺术意象的构筑、形式构成及其“势”的审美崇尚话题。
其次,康有为的“书,形学也”的书艺观念,是当代中国书法“势”的审美崇尚的重要理论基础。其实,对于中国书法“势”的存在,古代书论(法)家早有笼统的感知。东汉蔡邕有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有纵横可象者,方得为之书。”(《笔论》)“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九势》)“南齐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形 ”“ 象 ”“形 势 ”“ 形 质 ”“ 神 采 ”“势 ” 这些 概 念 范畴的内涵都互相渗透交织,边界模糊,都有“势”的蕴涵。尤其是清代康有为在其煌煌书学巨著《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提出了“书,形学也”这一极具学术价值的书法艺术命题。“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曰‘九势’。卫恒曰‘书势’。羲之曰‘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得势便,则已操胜算。”势因形生,形为势存。形是势的表现形式,而势是形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形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势,形和势是统一的。在一定程度上,形即是势,势即是形,形势不可分离,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合二而一的,由形和势的多重集合共同构成书法的视觉艺术形象,这也是中国书法的本质特性。作为书法之形的点画、结体和章法,都是表征生命形式和运动形式的“势”,而非仅仅是形状、样式、线形或轮廓的死板几何线条图形。“势”灌注了书家的情感,反映了书家对宇宙生命形式的感悟和律动态势。正是因为书家充分发挥毛笔书写的特殊功用,才使得书法载体上的点画墨迹不再是原始的点线,而成为富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点画线条墨迹。在点画(笔势)的基础上,书法的结体、章法也因形生“势”,生出体势和气势,具有了生命的形式和意味。
康氏对“形”的觉察,在书艺本体论上是颇具开创性意义的,他非常看重书法的第一形式,即各种汉字体符号的形态,以及书法艺术作品的视觉构成要素形与势(“笔势”、“体势”“气势”)的书法本体意义。其《广艺舟双楫》开篇《原书第一》,对中国书法之本原——汉字进行了推究探求,并仔细地辨析道:“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唯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唯字母略有形耳”。通过中外文字重形与重声的差异比较,从书法审美诉诸感官的途径概括道:“中国用目,外国贵耳”。应该说,这一中外文字差别的比较是符合中外语言文字现象和语言文字学现状的。作为诉诸视觉“形”的艺术,中国书法正是建立在各类汉字体符号原生态质基础之上的。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形式,即各类汉字体原形符号,它应是中国书法艺术发生学的源头,是书法美学的初始范畴,书法美学的其他范畴都是由此起步派生的。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述道:“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汉字的三美均与文学之美密切相关,其中音美、意美与书法之美关系甚微。当然,对于书法作品中所写的文字内容,观赏者也可以口诵其音、心通其义地加以理解接受,但这种音美、意美并不属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本体之美,当属附庸之美。就中国书法艺术的自律性来看,汉字体符号的“形美以感目”才是它升华为书法艺术的重要契机,所以康有为说书法艺术是“形学也”。中国汉字“重形”“用目”的特征,必然导致中国书法艺术意象的创造对“势”的重视、关注和推崇。可以说,康氏的“书,形学也”的书艺思想,是对中国书法艺术及其审美形象特征和本体特性的高度概括。书法艺术的本体定性,通俗地讲,一言以蔽之:中国书法是以各类汉字体符号为原型的视觉抽象造型艺术。这就从书法本体论上为当代中国书法“势”的审美崇尚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资源。
再者,中国书法艺术审美意象的创造或曰书法形式构成的基本形式语言点画、结体、章法的三个层次都是形与势的统一,都有以形造势,因形生势的书法形式构成的艺术语言功能。书法艺术形式构成的最终结果,就是“势”的彰显,对书法的审美观照由形而获得势的美感体验。形和势是点画、结体、章法等中国书法艺术本体内容展开的基础。东汉蔡邕认为书法产生于自然,并印证于自然阴阳和合的法则,这种法则在书法中进一步通过形和势体现出来。形是静态的形象,势是运动的过程。形通过势而生成,是蕴含着势的形;势通过形来呈现,是表现形的势。一个是静,一个是动;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形状,一个是态势;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形势统一,共同构成书法的完美艺术形式,并赋予其丰富的审美内涵。
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观照,最集中的表现在对于其形与势的意象体验上。在古代书论中,蔡邕的《笔论》、崔瑗的《草书势》、成公绥的《隶书体》、萧衍的《草书状》、孙过庭的《书谱》等书法论著都对书法艺术的形势审美意象作过生动的描述,展示了书法形势兼备的生命意象,赋予书法以生命和情感意味。书法艺术的形,不是静止的形状,而是生命跃动的审美意象(势),是生命形象的动态展现,是把势贯注于形之中所呈现出的生命态势,赋予了书法以生命、以情感、以主体精神的生动表达。书法的本质在于形与势的浑然状态,这种状态表面上是形象与势态的关系,而实质上却是书家的主体精神和生命情感融入的结果。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除了表现法、理、道之外,还在于其寄寓了书家的主体精神和生命情感。正是把万事万物的生命态势投射到书法的形象中去,以形、势贯穿于书法形式,才充分实现了书法“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艺术功能。因此,生命与情感的态势或意味才是书法艺术所要真正表现的内容。
由书法形式语言的点画所引发的笔势内涵是“势”的第一要义。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语言层次或要素,即点画、结体、章法的以形造势、因形生势,分别造就和显现出笔势、体势和气势。透过传统书论对书法审美意象“取象其势,仿佛其形”的生动比拟描述,可以感受到书法艺术多样化的形象与态势,而这些诸多的形象和态势,都是在具体的驾驭笔墨书写过程中产生的,所谓“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这种毛笔运动过程中贯穿的势叫笔势,它以书写过程中时间性的展开为线索,由于运笔过程中力量、速度、方向等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点画形态,并生发出通篇点画之间的牵丝、引带、顺承、衔接的关系态势。
对笔势的研究最著名的理论是“永字八法”,“永字八法”理论,表面上是在阐释点画即笔法,实质是形势统一而偏重于势的构成观念,是用势来解释形,落脚点在势。其精髓就是把所有的点画当作一个过程去处理,得出了关于笔势的理论,确立了以形求势,因势生形的书艺形势观。“永字八法”以八种笔势(法)对应于真书的八个基本笔画(点画),即由侧、勒、弩、趯、策、掠、啄、磔,分别对应点、横、竖、钩、挑、长撇、短撇、捺。“永字八法”理论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蓄势生发的运笔过程,通过提按、轻重、快慢等力量和速度上的变化,形成各具态势的点画形象;二是强调前后点画之间笔势的过渡与承顺关系,这种关系超出了点画内部的运动范围,而延伸到点画与点画之间,是保证结体内部筋脉贯通、气势顺畅的基础。进而由“永字八法”扩展开来,在上下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及全篇之间都是以笔势为纽带贯穿始终的。正是由于笔势的贯通,才使得作品成为一个充盈着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
由书法形式语言的结体而引发“势”的第二个层面的体势内涵。体势以书写过程中空间性的关系为线索,是字与字或形与形之间的空间关系所产生的势,主要包括结体内部点画与点画之间俯仰向背关系和篇章之中结体与结体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欹侧呼应关系。点画是形和势的统一体,并具有各自形态和方向上的倾向性,点画与点画之间为了变化协调,就需要在体势上作出配合和承接,以便气息顺畅。点画组合是结体的基本内容,并以构建体势的和谐关系为前提。
倾侧是产生体势的基本方式。它意味着运动的倾向和态势,这种不稳定的态势,会让人产生心理上使其获得平衡的愿望。在结体内部,一个部分的倾侧需要其他部分反方向的倾侧来取得平衡,这样就建立了点画与点画、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左顾右盼、相互依赖的关系,加强了结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有机性。因此,为了营造富有动态和张力的结体,就必须使其内部的点画和部分之间上下腾挪,左右倾侧,生成相向或相背的多种态势,并在相互对抗的关系中达到动态平衡。
由书法形式语言的章法引发“势”的第三个层面的气势内涵。章法的构成是按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展开的,在展开的过程中,由点画的笔势与结体的体势将上下点画和上下字连贯起来,形成时空统一的浑然一体的态势(气势)。笔势不管是以时间线索展开的笔势,还是空间线索展开的体势,势存在于各个造型元素及其相互关系之中。正如朱和羹《临池心解》所云:“凡作一字,上下有承接,左右有呼应,打叠一片,方为尽善尽美。即此推之,数字、数行、数十行,总在精神团结,神不外散。”由此看来,作品中的势是无处不在的,遍布于各个角落。章法中的任何一个点画或任何一个造型元素,特别是每一个有机统一的结构体,都离不开势的作用。点画无势则弱,结体无势则散,通篇无势则阻。章法上下气韵的律动靠笔势的连贯,左右的张力靠体势的呼应。一句话,势是由形入神的催化剂,是形式构成的黏合剂,是由书写上升为书法并具有审美境界的必备条件,是中国书法重要的审美意蕴。
综上所述,章法构成的所有关系都见之于形、势之中,是形、势的组合,并生发三种态势。轻重快慢、离合断续、纵横牵制表现为笔势;上下腾挪、左右倾侧、前后避让表现为体势;笔势和体势统摄于全篇,形成作品的整体态(气)势。笔势与体势贯穿于造型、造型组合以及各种造型关系之中,是赋予造型以生命、以动态、以情感的纽带。经由各种造型元素的丰富变化,章法获得了时间节奏与空间构成、视觉性与抒情性的完美融合,浑然一气,也使得作品具有了生命律动、气韵畅达的整体态(气)势。
还有,中国书法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性质,是时空合一的艺术,体现为形和势的统一,其形式构成(章法)的最终结果是“势”的彰显。中国书法的时空合一性,表现在形式语言上最根本的是形与势的合一,形是空间造型,势是时间节奏,二者构成了章法与时间不断生发的过程。形势合一使书法艺术融时间性(音乐性)和空间性(绘画性)于一体,成为一种形而上的艺术。同宇宙的运行一样,书法的章法也是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合一,空间在时间中流转,时间在空间中延续,时空的统一与推衍构成了章法运动的基本形式。大小长短、方圆藏露、枯湿浓淡为形,是空间的组合关系;轻重快慢、纵横牵制、离合断续为势,是时间的组合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时空合一实际体现为形势合一,形与势以对方的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所有的形都是在运动中完成的,都有一定的势。所有的势都凝固在载体上,依赖一定的形。形必须靠势来激活,势必须靠形来显现。具体来看,作品的形势合一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点画的形势合一。书法作品中点画不仅仅是形状意义上的,而且是形势合一的,它们是笔法与笔势的组合。它们除了具有笔法组合的空间特征之外,还是笔势作用的结果,富有时间性的音乐节奏感。一个好的点画,它必然是形与势的统一,它既有优美的造型(点画形状),同时还有一种来自笔势运动的速度、节奏、韵律美感;二是结体的形势合一。书法作品中结体都是形势兼备的。就结体内部而言,它们是笔势与体势的合一。一方面既要注重笔势的连贯让点画与点画之间成为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在快慢、连带、疾涩中组成充满节奏律动的生命个体。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体势之间的承接对应关系,或俯或仰、或正或侧、或断或连、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有起有应,在对立统一中显现生命体势;三是作品整篇章法(篇章)的形势合一。篇章的构成是按照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展开的。时间主要表现为笔势,通过连续书写时的牵丝映带与上下连绵将上下点画和上下字连贯起来。空间主要表现为体势,通过空间造型(大小、正侧、宽窄、向背)的对比变化与顾盼呼应将上下点画和上下字连贯起来。篇章的形势合一,既要兼顾作品的时间性,强调笔势,将笔势贯穿于点画之中、结体之中、篇章之中,让全篇表现出音乐性的节奏,又要充分挖掘点画、结体、空白、墨色的造型活力,围绕篇章空间关系的构建而千方百计,施展浑身解数,强调体势和空间的变化、丰富与和谐,使整个的篇章构成既具有绘画般的视觉张力,又充盈着饱满的生命气势。
最后,当代书法“势”的审美崇尚,是当代中国书法发展的必然要求。20世纪末以来,中国书法的人文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几乎退出了日常书写的舞台,即使曾经在20世纪获得普及的硬笔书写方式也因计算机的普及运用而虚拟化了,书法的实用性基础至此基本消失,传统上附着于书法的种种他律因素退隐,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长期纠葛也最终得以解决,书法获得了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地位,真正成为一种纯粹的视觉抽象造型艺术。在书法艺术独立的时代语境中,围绕书法艺术形式自律,当代中国书法在本体观念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就历史条件而言,今天的中国书法已经开始摆脱实用性的束缚而进入追求艺术自律为本体目标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当代视觉文化迅猛发展也正在对书法的形式变革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的中国书法首先是作为一种视觉图像而被人们接受、观赏和消费的,由对书法的视觉图像的审美观照而获得“势”的美感体验和精神愉悦。就创作而言,当代书法已经进入了“展厅”“展览”“展示”时代,当代书法是为展示而创作,书法家艺术思考的核心是笔墨形式的审美含义问题,至于文本内容,它是作为人们的阅读惯性而存在于书法的艺术本体之外的,在创作中需要保证的仅仅是文字造型符号的传统合法性。基于对作品文本性的扬弃,当代中国书法在创作观念上体现为对“展厅效应”的追求日益突显。由于展示方式的改变,书法的审美观照方式进入了从阅读到观看的转换期。在古代,书法欣赏一般都与阅读文本内容同步进行的,诸如《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这样的名帖,都具有文本与艺术的双重属性,对文本性内容的创作,以及对文本价值提供某种文学意义上的保证是书法家无法回避的。当今,书法欣赏是“观看”,“观看”的内容是书法点画、结体和各种关系对比,感受其笔势、体势、气势或曰生命情感的意象态势。
当代书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要强化形式构成意识,强调作品的造型性与可视性,以形造势,因形生势。传统书法强调作品的识读性,强调作品艺术感染力在识读过程中逐步展开。而当代书法则强调必须在可视性与可读性的结合中充分突出可视性,认为一件作品的情感图式是通过形式构成来实现的。因而,作品首先是让人观看而不是供人阅读的,对文本内容的阅读已退居其次。只是在视觉美上获得成功后,文本性才作为一个书法欣赏过程中的接受习惯问题被予以考虑。由于当今书法生存环境以及书法欣赏方式的改变,书法作品展厅效应日益突出,创作观念也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丈二、丈八的巨制作品,突出的主要是视觉冲击力、形式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书法的这些艺术张力,是无法通过文本的阅读而获得的,它只能在观看中给人以震撼、给人以共鸣、给人以激动、给人以精神愉悦。强调书法作品的造型性和可视性,实际就是要推崇当代中国书法“势”的审美追求,充分突出和彰显书法“势”的视觉审美价值。
总之,当代中国书法“势”的审美崇尚,是书法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与现代人文环境、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欣赏方式相适宜的审美观照。书法家要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努力创作出能表现时代书法精神气象、气势磅礴、适宜现代人们审美需求的书法作品来。
湖北省襄阳市文艺理论家协会
注释:
[1]胡抗美:《书为形学》,荣宝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2][3][4][5][6][7][10]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第6页,第6页,第62页,第845页,第753页,第736页。
[8]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9][11]胡抗美:《中国书法章法研究》之形势理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中的章法探索等章节,荣宝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