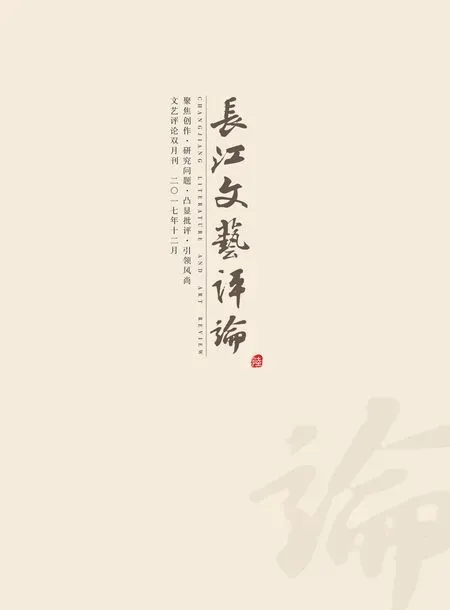任蒙散文的诗化与文化
◎毛 翰
任蒙散文的诗化与文化
◎毛 翰
近二十年来,任蒙的散文在评论界和读者当中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新观察》和《中国散文评论》等报刊相继发表专题论文,对任蒙散文的艺术特色作过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我看来,任蒙散文之所以受到读者首肯,除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有其浓郁的诗化特色,用“诗化+文化”来概括任蒙散文的艺术成就,或许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因此,本文试图从诗化散文和文化散文的认知角度,对任蒙的散文作一次新的解析。
任蒙散文的诗笔
这里,不妨简略回顾一下作家任蒙的创作历程。早年,他是知名诗人,发表过几百首军旅诗歌,继而从事诗歌评论,出版有多部相关理论专集,包括他那部至今还在许多课堂的作文教学中发挥着“品牌效应”的论著《诗廊漫步》。《诗廊漫步》1988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曾经多次再版、重印,曾被有的高等院校用作函授教材或写作参考教材。鉴于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的成就,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劝他重点从事文学评论,但他却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散文创作之路。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任蒙先后出版了《文化旅思》《海天履痕》等多部散文集。一批文字优美的短章相继见于各种散文选刊和选本,关于访欧见闻等一些域外散记,特别是一批历史散文,更受到好评。2005年10月,《任蒙散文选》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三年后又出了第二版,但没过多久,出版社发现淘宝网不少店家销售的《任蒙散文选》都是“复制”的盗版书,为此,他们于2014年推出了《任蒙散文选》第三版。此外,任蒙《走向另一个自己》《假如明天没有阳光》两本散文集也曾经再版。这些年,评论界的一些文学教授和作家诗人纷纷撰文,对任蒙散文予以推介,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少评论家关注任蒙散文的诗性特色。比较来看,著名学者黄曼君教授在论述任蒙的散文艺术时,把握得更为全面而准确。他在《开拓文化散文的多维空间——任蒙散文融合诗、史、思的文学意义》一文中指出:“任蒙的散文有深厚的历史感,又有鲜活的现实意识,显示了不可忽视的创作实力。评论界曾多次提到任蒙对于中国当代散文的贡献,也主要是指他这方面的艺术高度和创作超越。他把史实、学术和散文的抒情几个方面,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任蒙散文的最大成功之处。”黄曼君教授的评论正是围绕这种“融合”展开的。显然,这种富有立体感的“融合”中包含着任蒙散文的诗的品质。
缘于诗人本色,任蒙不少散文给人的直观感觉就富有诗化意味。例如《峡江两赋》之一的《古老的栈道》这样开篇:“峡江从历史深处流来,栈道也从苍茫的世纪中蜿蜒而来。/峡谷有多长,栈道就有多长。/峡江无岸。栈道只能凿在险峭的石壁上。它时高时低,有些路段悬在半空,长长的纤索自身已够沉重的了,还要拽着逆流而行的舟楫。/那不屈的脊梁呵……”如此峡江之赋,文字空灵,读来却很沉重,谓之散文诗,亦不为过。
所谓诗化散文,在中国当代曾经风靡一时,拿散文当诗写,曾是杨朔的标榜。文革结束之后,那种“叙事-抒情-政治象征”三段式的诗化散文模式已告式微。作为新一代充满怀疑和探索精神的散文作家,任蒙不愿意蹈其覆辙,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华中师大主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他就明确表示过,不赞赏杨朔那种为文造情的抒情方式,并举例说,杨朔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之类的笔法,有些牵强,甚至有伪情之嫌。由此,任蒙放下诗笔之后,在已经置换了的文化背景上,在广阔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的时空里,展开了属于他自己的散文意境的营造。
任蒙散文重在诗意的内化
散文的诗化程度,折射出的是作家以诗的眼睛观察世界的能力,以诗的心灵感悟世界的能力,以诗的语言重构世界的能力。在《秘境之旅》这组短章里,任蒙写道:“高原的石头是海的化石,山的化石。光滑的石头上什么也没有写,但它们都是天地的符号,向我们显示着:天是什么,地是什么,时间是什么,人又是什么。”他没有着意于那种独特卵石的外表,而是通过它们“烙着沧海的痕迹”,通过它们经历的亿万年沧桑,来表现这些石头内在的丰盈和内在的美感。
夕照、戈壁、雄关等,是任蒙不多的写景散文所摄取的意象。或许这些场景更能够激起任蒙的诗情,更适宜于任蒙散文那种壮美雄浑的美学追求。比如,他这样描绘沙漠之美:“尖厉的风刀在沙海中忙碌了千万年,雕刻出了浩瀚沙浪,雕刻出了一座座古老城邦的断壁残垣,雕刻出了一个个绿洲王国残露在沙砾中的辉煌幻景,雕刻出了那金樽玉饰、金冠皓腕的歌舞浮影,还有那隐约的佛塔、果园、作坊和夕晖下络绎不绝的远行驼队。”他以其大气而流畅的诗笔,引导我们去想象当初西域王国的盛世景象和一部大漠古史。
散文的诗化,重在诗意的内化,重在作者能够自发地以诗心诗语观察和记录生活。任蒙散文极少吟咏花鸟虫鱼之类,《鸟巢》是他近些年所写的几篇咏物断章之一,但它更像是一篇散文诗。在他的笔下,一具具硕大的鹊巢架在还很细嫩的白杨枝间,迎着寒风不停地摇曳,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但他最后的想象却让读者为之释然:“鸟儿偎依在属于它们的那座温暖的空间里,享受着它们的生活,享受着它们的尊严。哦,这高悬的巢穴原来不在乎天空的表情。”这里,作者通过他的联想,展示了生命面对险恶环境的坚韧、镇定和从容。
在任蒙过去的散文集里,有些记述自己情感经历的短文也写得相当精致、相当感人。比如,《二十九个荷包蛋》写他参军离乡的前一天,乡邻家家户户煮鸡蛋为其送行的情与景,十分生动,很多人都曾经被这篇散文感动过,并留下深刻印象。可他在编《任蒙散文选》时就是不收,并且表示以后如果再版,仍然不收这类散文。他认为,那样的“短小制作”尽管也需要技巧,但很多写作者只要亲身经历过,就有可能写出来,不足以体现散文书写的难度。由此可见,任蒙追求的散文境界和艺术高度。
任蒙散文的哲思光芒
诗化的表达,不是散文唯一的美学要素。特别是文化散文,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思想重量。任蒙的散文创作,注重的是在广阔的调色板上作浓墨重彩的描绘,作大撇大捺的勾画,表现的是广阔的意象和丰富的内涵。如《历史深处的昭君背影》一文,作者想象了昭君出塞的历史场面:“马蹄声,铜铃声,雪地上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以及将士们挥鞭驱马的喝斥声,打破了大漠的宁静。”类似一连串形象化的诗意描写,将读者不知不觉带进遥远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之中,进而对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判断,对昭君出塞之后的匈汉关系表达出自己的见解。他说:“昭君出塞前后的匈汉宁和,主要是几代单于能够从匈奴自身利益的大局考虑,审时度势,明智地处理匈汉关系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历史,不要无限夸大和亲的作用,更不要无限夸大和亲女主角的作用。”这样的认知,正是文化散文所要追求的史识。而这种具有一定深度的思想层面的历史见地,往往比诗意语言更能激活读者的想象,更能产生流动的气韵,使读者获得更多的审美趣味。
任蒙所选取的散文题材本身,也不允许作者运用托物言志的简单方式,去做种种情与景、情与物的肤浅“融合”。他在《凭吊赤壁古战场》里,是这样表现那场殊死大战的:“战争不会选择时年,更不会选择季节。假如那场激战不是在那个严冬,而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到来的这种春意弥漫的时日,自北方而来的曹军参战将士,看到这山,这江,这田野,也许他们战死时会增添一份对人世的留恋。”这里,作品透出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生命意识,更是对世间真善美的深切期待和无言歌赞。
众多研究者关注任蒙的文化散文,称赞其文化和思想品位,称他为“坚守精神家园的独立思想者”。任蒙坚持认为:文化散文就是思想散文。他在宽广的历史时空纵横捭阖,往往追求的是深层思辨的文化批判。
“漫长的时间使腐朽化作了神奇,而我们通过神奇更透彻地看到了腐朽。”这种被论者誉为“神来之笔”的句子,不仅《放映马王堆》里有,其他篇目中也不时可以读到。他写长城:“它像一道高高挥舞的粗大鞭影,千百回抽打过我们的民族,最后沉沉地落在这块土地的脊梁上。”这样的散文语言,不是诗句,却是诗意的丰厚积淀,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哲思的光芒。
由与余氏散文的比较说开去
评论家刘保昌在《体贴人生:实力派散文的突破性意义》一文中指出:“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来研究余秋雨和任蒙这两位文化散文作家的写作,或者在余秋雨文化散文创作的既定背景下,来反思任蒙文化散文写作的突破性意义所在,就不仅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比较学意义上的话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和创作学意义的话题。”他认为“任蒙的这组散文(指任蒙的一批历史题材散文——引者注)在审美性上可能比余氏‘稍逊风骚’,但在思想性上绝对超过了余秋雨。”
还有几位理论家在评析任蒙散文时,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其与余秋雨散文进行比较。我不反对这种比较,只是觉得,进行这种比较研究还须谨慎。关于余秋雨其人其文,如今批评者众多。对人们说到的其人格软肋和作品中的文史硬伤,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再作议论,我所要强调的是余氏散文的模式化、套路化,即所谓匠气,也曾为有识者所诟病。已故诗人黎焕颐晚年就曾著文,对余氏人品和文品作过透彻的解析:“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恰好以其宏观与微观的整合,散发出他特有的文化底蕴,在散文领域苍头突起,这是可喜的。我并不认同对他散文的某些非持平之论。散文最讲究的乃是情与物,理与势,势与气的有机的组合——组合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组合,无空格之格,无定局之局。有如天马神龙的性灵神韵机杼自发。余的文化散文,单篇看,或者抽一二篇来玩味,窃以为庶几近之。但,把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和最近才问世的《霜冷长河》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特别是他的《文化苦旅》从头到尾来审读,则是主题先行的思维定式,外化为他文章手法的老套。这样,就匠气十足了!有人以大家目之,这就失察了!”如此犀利的批评、彻底的解构,想必也引起了余秋雨的反思和警醒。读余氏近作《诗人是什么》,从《诗经》时代的诗国风采,写到屈原《离骚》的绝世风神,但觉文思瑰丽,才情纵横,已不见其惯有的章法套路,不禁为之惊喜。
而任蒙散文早已是一篇一世界,一章一时空,既不重复他人,也很少重复自己。即使同为音乐笔记,《超越语言的语言》一文品评弦乐四重奏《梁祝》,另一篇《一个世界性艺术话题》,则是品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这就构筑了两个风格迥异的“艺术王国”。
前者赞叹《梁祝》低回跌宕的旋律,把我们带到那个没有年代的年代,“那里有寂静的山川和田野,有古老的拱桥和溪水,有高深的宅第和闲恬的园林,有现代和未来不可能再现的生活背景和文化心态。”作者如诗似画的描绘,让我们走进了那个古老的故事,走进了那个为后世孕育了不朽音乐的古老时代。“爱情故事淡化了十年寒窗追寻功名的价值观念,渲染的是封建礼教和门第婚姻的残酷。但音乐使故事的主题得到了再次升华,听者感觉到的不是几千年尘世俗念的困扰,而是空灵,纯洁,缠绵而不忧伤。”文章在倾诉了对音乐的心有灵犀的许多感悟之余,也记叙了文革动乱之后,中国的一道文化景观:当海峡彼岸,邓丽君那圆润甜美的歌声飞来,让整个大陆为之倾倒;海峡此岸,一支《梁祝》飘飞过去,在台湾岛上萦绕不散,也让上至政要下至百姓为之沉醉。从而感叹艺术的魅力,感叹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灵的亲和力。
后者,即《一个世界性艺术话题》及其续篇《还说〈二泉映月〉的话题》,由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竟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跪下去的动人情景,一路洋洋洒洒写下去,从瞎子阿炳个人命运的凄惨,写到中华民族历经的苦难,写到《二泉映月》享誉世界,却一度在自己的祖国被封杀……文思追随音乐旋律,一路流淌而来,所谓行云流水,所谓舒卷自如,不过如此。请看其中的一段文字:“你或许从凄然悱恻、如泣如诉的倾吐中,读到一种苍凉;或许从迷茫幽暗、激昂忧愤的琴声中,读出的是悲怆;或许从顿挫有致、优美晶莹的音符中,读到的是古老的江南水乡;或许从跌宕起伏、苍劲有力的旋律中,读出的是原实的音色……”这样表达对名曲的欣赏感受,犹如音乐一般流畅了。特别是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或许你什么都没有听出,而又什么都能听出。”是思辨,更是诗语。
当人们竞相赞扬任蒙的文化散文时,我忽然生发出一点小小的感想:一位散文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风格、散文疆界,不妨任其朦胧一点,有时不妨诗化,有时不妨文化,有时则不妨随缘走笔,我手写我心,不化而化,是为化境吧。
任蒙散文是不曾固守一种风格和题材,画地为牢的,即便它如何时尚。
归纳、整理、定性、命名,那是史家和论家的事。创作之树常绿,史与论总是灰色的。作家自己完全应该并且可以任由文思信马由缰,纵横驰骋。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说做人的境界。至于作文,只要从心所欲,管它逾矩不逾矩呢!逾矩,也许更意味着超越、突破、别开生面、别见洞天呢!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的文章,纵无诗化的美、文化的雅,信笔写来,素面朝天,亦自有动人可人之处。
任蒙文化散文的时代性特质
审视任蒙的散文,我们也能够进一步坚信:散文的诗化,不是那种没有思想的“纯美文”,更非华丽词藻的堆砌。任蒙曾多次表示过,他不主张刻意求变的散文创作。有人为了追求所谓的变革,将主要精力运用在对表现技艺的把玩上,将好生生的语言折腾得文理不通,一篇散文病句连篇,甚至连标题、书名都是病句,让人不知所云。任蒙曾批评说,这种表面化的求新,容易滑向“反创作”,流于对母语基本法则的反动。
任蒙散文中洋溢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情感色彩,是因为他能够坚守自己的文格,坚守一个作家的精神园地,不断追求作品思想与个性的充盈。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任蒙所要表达的决非是个人悲欢和个人好恶,他是在为一个悠远的历史时空而书写,是在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而书写。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起任蒙的杂文,如《戏说红尘》《世态幽默图》等杂文集。他还是一个为不少读者所熟悉的杂文作家,曾经获过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这里,顺手从网上拎出一篇《农妇与蓝甫》,好像是他二十年前的一篇杂文,文中写道,由红豆集团与《中华诗词》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传统诗词大赛中,名列二等奖榜首的一首绝句:“北国春风路几千,骊歌声里柳含烟;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其作者竟是山东一位农妇。作家于是感叹,朝中贪官胸无点墨,甚至错别字成堆,却能加官进爵,到处题字。乡间农妇,满腹诗书,锦心绣口,却只能“汗滴禾下土”,年复一年。古时科举以诗文取仕,被人批得体无完肤,但时至今日,以厚黑取仕,让诗人耕田,难道就正常吗?
任蒙的文化散文更是充满着对历史的思考,有人说过,任蒙散文强烈的冲击力,主要源于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任蒙作出的种种反思与批判,与其说是对历史的思辨和拷问,不如说作家关注的是未来的社会走向,关注的是我们民族的命运。
思想分量,为任蒙散文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性特质,也为这类散文增添了难以遮蔽的文体光辉。
任蒙之“蒙”,本义是野草。任其散文之中葆有一派野草般的朴素、清新、自然之趣,也很得体,甚至不可或缺。任蒙总在努力超越自我,我们也相信他的散文一定能够走向更加高远的境界。
华侨大学中文系
注释:
[1]黄曼君:《开拓文化散文的多维空间——任蒙散文融合诗、史、思的文学意义》,《文艺报》2007年2月15日。
[2]刘保昌:《体贴人生:实力派散文的突破性意义》,《任蒙散文论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
[3]黎焕颐:《戴厚英和余秋雨》,《书屋》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