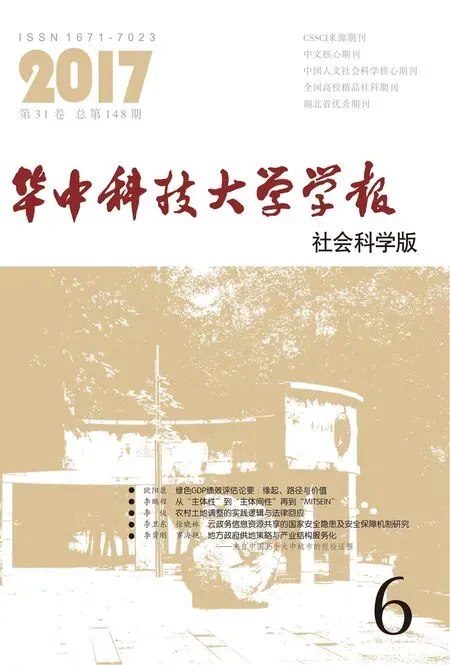我国环境行政命令体系探究
□胡静
我国环境行政命令体系探究
□胡静
我国环境行政命令在法律实践上沦为行政处罚的附属品,在学术研究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结果是其补救性功能被掩盖。基于补救性功能,环境行政命令应分为纠正违法行为和消除环境危害后果,并进一步划分为各种亚类,从而形成其体系。因此,有必要认识环境行政命令体系,推动其立法,充分发挥其补救性功能。
环境行政命令;纠正违法行为;消除环境危害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随着生态损害赔偿和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和实践的发展,司法权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因而引发对于行政权、司法权在环境保护中如何配置分工的思考。司法权介入环境保护是其职责所在,但相比行政权,司法权本身具有谦抑性,司法权固然不能缺位,但其承担的角色是依法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行政权在环境公共事务中应居于主导地位,面对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受到普遍的侵害和破坏的情况,首要的解决措施和第一道防线并不应当是求助于司法机关的个案裁量,而是应当通过加强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法上的制度创新实现规则之治[1]。
环境行政执法主要针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监管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建设项目只有事前符合一定条件才允许开工建设,其监管工具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者只有事前符合一定条件方能投产排污,其监管工具是排污许可制度。这都体现了环境法以预防为主的原则。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要求“排污许可证中明确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浓度、排放量、排放去向等事项,载明污染治理设施、环境管理要求等相关内容”。可见,排污许可证既是企业的环境义务清单,又是环境行政执法的依据,因此,排污许可也是事中监管的工具。对违法排污者的事后监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其监管工具是环境行政处罚;二是对违法行为及其环境危害后果的补救,其监管工具是环境行政命令。我国较为倚重行政处罚,对于责令改正或责令停止行为一类的环境行政命令的补救性制度功能没有充分发掘。
环境行政命令是行政命令的下位概念。我国正式确认行政命令的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发[2004]2号),该文件将行政命令作为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等相并列的行政行为类型。《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明确列举了责令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的具体形式: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试生产、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责令重新安装使用、责令限期拆除、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治理等。该条还强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行为种类和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规定,行政命令不属行政处罚;行政命令不适用于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考虑以上规定和我国实践形成的认知,本文将环境行政命令主要限缩在排污行为导致的对相对人科处的不具有惩罚性的可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
在我国和行政命令纠缠不清的行政处罚在大陆法系行政法理论中不在行政决定之列,而被作为行政保障性措施单列。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行政决定分为基础性行政决定和保障性行政决定。基础性行政决定直接落实法律规定的应有的权利义务。保障性行政决定的特点是以相对人应该履行的义务为必要前提,目的是以责难、惩戒、威慑等直接或间接地付诸于人身、财产或精神的强制力量保障法律明定的义务或是行政决定所设定义务的实现,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2]。基础性行政决定中的命令性行为是以命令或禁令形式要求相对人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行为,包括作为、容忍、不作为义务[3]207。行政命令大体对应于命令性行为。环境行政命令是行政命令工具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运用,和其他领域的行政命令相比较,环境行政命令针对环境违法行为和环境违法行为产生的环境危害后果。这里的环境危害后果指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并不包括环境违法行为经由环境媒介如大气、水、土壤、海洋污染对个人人身或财产造成的损害,后者通过民事诉讼加以救济。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关乎环境公共利益,对其损害的救济主要通过行政机关的执法进行。环境行政处罚为相对人施加新义务,其功能是对违法者进行惩罚;环境行政命令仅仅是要求相对人履行法定义务,矫正没有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及其造成的环境危害后果,其功能是补救。
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有关环境行政命令的判决书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关涉环境行政命令案件中最常见的争议是对某种具体责任形式是应认定为环境行政命令抑或行政处罚,这种认定关系到应适用的行政程序。例如,根据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六行终字第00051号)①该案和本段下文涉及的案件的判决书原文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记载,环保局认为其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中载明的责令停止生产属于行政命令,环保局在作出决定前,无需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但一审和二审法院则将其认定为行政处罚,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此外,巴林左旗林东镇龙泉浴池与巴林左旗环境保护局不服环保行政处罚案、北京楠海印刷厂与北京市平谷区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吴武汉与广州市黄埔区环境保护局不服停止生产处罚案、栾城县新峰锌厂与栾城县环保局行政命令纠纷案等,皆属此类案件。这类争议系对环境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的区别认识不一致所致,凸显了环境行政命令并没有从环境行政处罚中彻底独立出来的困境,其结果必然是环境行政命令的作用受到严重制约。如果行政执法主要停留在对违法者加以制裁而忽视对违法行为本身及其后果的矫正,这显然并不符合《环境保护法》第5条规定的损害担责的基本原则,也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虽然当下环境行政执法力度空前加大,但多以解决“违法成本低”为重点,恢复合法秩序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环境行政实务呈现“重处罚、轻改正”的局面。
“重处罚、轻改正”现象和环境行政命令的立法滞后直接相关。我国早在1996年就出台《行政处罚法》,1999年就制定《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对行政处罚和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及其相应的行政程序进行了规定,在立法上为行政处罚在执法实践中的适用铺平了道路。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行政命令和环境行政命令的立法,有关环境行政命令的种类散见于若干环境立法中,关于其行政程序的规定更是付之阙如。环境行政命令在立法上并没有获得与环境行政处罚并列的地位。
学界对于环境行政命令的研究也较为匮乏,笔者在知网上期刊范围内检索,以“环境行政处罚”为篇名检索到121条结果,以“环境行政命令”为篇名检索到5条结果,以“环境责令改正”为篇名检索到3条结果。纵观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发现:(1)在环境行政命令的定位方面,有的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作为救济罚纳入行政处罚体系[4],模糊了补救性和惩罚性的界限,对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有的主张将环境行政命令作为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5],对其适用和功能有窄化之嫌,不利于充分挖掘其功能潜力。(2)在对具体责任形式的研究方面,有的对某具体责任形式如限期治理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6],有的对具体责任形式如责令停止生产和责令停产进行辨析[7],侧重某具体形式适用的研究,对环境行政命令体系的研究尚待展开。
立法的缺失和学界关注程度的不足,导致环境行政命令恢复合法秩序的补救功能长期被遮蔽和忽视,环境行政命令事实上沦为行政处罚的附属品。因此,有必要制定环境行政命令的专门立法,恰如《行政处罚法》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内容一样,在厘清具体种类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行政程序,将环境行政命令从行政处罚的阴影中彻底解放出来而显性化,从而形成针对违法行为的环境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两相配合的格局。本文首先从环境行政命令的补救功能出发,逐级推演出主要的环境行政命令形式(种类),在推演过程中按照不同具体形式的特点讨论其适用,以期唤起学界对环境行政命令的重视。
二、纠正违法行为
一般行政命令确定的义务往往由相对人以前的行为产生,在某些情形下,即便相对人此前并没有实施某行为或导致某后果,但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行政机关也有必要依法要求相对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行政机关的这类行为应当在行政法体系中加以定位,考虑这类行为以给相对人施加义务为内容,具有可执行性,虽然并不具备行政命令的补救性特征,但在执行上和行政命令并无二致,宜纳入行政命令,可谓“准行政命令”①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6条第1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应急措施。。在多数情况下,相对人违法在先,环境行政主体发出行政命令责令其履行在后,如责令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等;也有相对人虽然此前并无违法行为但已造成危害后果,如合法排污造成土壤污染,环境行政机关会依法要求污染者修复污染场地。据此,环境行政命令可以分为违法行为产生的环境行政命令和合法行为产生的环境行政命令。违法行为产生的行政命令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下,违法行为正在进行中,有必要进行纠正,通常的责任形式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改正等;如有危害后果的,还应责令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第二种情形下,违法行为已经结束,并无纠正行为的必要;如有危害后果,则应责令消除环境危害后果。上述各种情形,通常伴随处以环境行政处罚。基于以上分析,环境行政命令包括两种主要的类型:纠正违法行为、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纠正违法行为适用于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形,消除环境危害后果既适用于违法行为也适用于合法行为。以下分别就这两种类型的具体形式展开探讨。
纠正违法行为的形式多种多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最为常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改正”都属于概括性的表述方式,具体内容可随语境变化而变化[8]。“责令限期改正”实质上是责令改正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主要适用于需要明确改正期限的情形。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责令重新安装使用、责令消除隐患、责令拆除等均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改正在特定情形下的具体化。在有些立法中甚至一并使用,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立法中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的表述。可见,“责令改正”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之间很难有清晰的区别,但在使用习惯上呈现不同的倾向。第一,“责令改正”适用的范围更宽泛,“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在行为人存在法定不作为义务但实施作为的情形下更为常见。第二,“责令改正”在广义上可以涵盖消除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②在本文环境行政命令分类体系中,消除危害后果单列,不在责令改正之列。,停止违法行为则不然,但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是理论上的,环境立法中改正主要还是针对行为;如果涉及危害后果的消除,往往运用“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和“消除污染”等责任形式。第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往往要求即时履行;“责令改正”有即时改正和限期改正之分,限期改正适用于经过一定持续过程方能完成、有必要给予合理期限的行为。第四,“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内容明确,“责令改正”的内容往往需要结合具体情形加以确定。从环境行政命令体系组成的清晰性考虑,结合现有立法可以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适用于不履行、不作为义务的情形,如相对人没有获得排污的批准或许可而擅自排污,这类行为自始违法;责令改正主要适用于违反作为义务,如获得排污的批准或许可但排污行为存在超标等违法行为的情形,在这类情形下,相对人应积极作为,通过“改”而导“正”排污行为。
(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以停止生产为重点
停止违法行为包括停止建设、停止生产、停止使用等多种具体形式,系针对违反法定不作为义务的行为予以适用。如,停止建设针对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擅自开工建设的行为,停止生产或使用针对违反“三同时”③“三同时”指我国环境法规定的环保设施和主体工程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擅自投产的行为。本部分以停止生产为例加以阐述,为凸显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的差异,阐述将贯穿停产停业和停止生产的辨析。对一个具体责任形式判断为行政命令抑或行政处罚,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表达,需要遵循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的功能差异,从责任形式的实质内容对其归属进行判断。某种特定的责任形式是属于行政命令抑或行政处罚,取决于该责任形式和此前义务的比较。如责令行为仅针对违法行为本身,责令行为没有制裁性;如责令行为超过了违法范围,实际给相对人施加新的义务,属于处罚[8]。当然,不排除个别责任形式兼具制裁和补救性质,如针对盗伐林木和滥伐林木的行为责令加倍补种林木,这就属于复合型责任,自然应适用行政处罚的规定。
停产停业和停止生产在表述上接近,但在制度上各有所属。对于停产停业的理解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停产停业只是在一定时间内限制或剥夺相对人的生产经营权,不剥夺相对人的生产经营资格[9]230。第二种观点认为停产停业是永久性的;与之相比,停产整治、停业整治、停产整顿、停产停业整顿重点强调整治或整顿,因此,其间的停产或停业是临时性的,不具有终局性的效力,是要永久停产停业还是恢复正常生产经营,还需要看整治或整顿效果[10]249。在第一种观点看来,停产停业仅仅是督促相对人回归合法状态的手段。我国《行政处罚法》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均将停产停业作为行政处罚,显然并没有采纳第一种观点。关闭和吊销许可证如排污许可证也属于行政处罚。关闭是形式上消灭主体资格,相对人如需要重新获得主体资格,必须另行登记注册;吊销排污许可证在形式上永久性剥夺相对人排放污染物的能力,相对人如需要获取排污许可证,必须另行申请。既然将停产停业和关闭、吊销许可证都纳入行政处罚范畴,停产停业自然具有惩罚性。其惩罚性体现在,停产停业虽然并未在形式上消灭主体资格,也没有在形式上永久性剥夺相对人行为能力,但对相对人行为能力构成实质性剥夺,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主体资格如工商执照和行为能力如排污许可等。只有对停产停业从第二种观点上理解,才能对停产停业属于行政处罚进行合理解释。可以看出,将停产停业纳入处罚是在实质上认定效果的结果,因为停产停业在效果上和关闭、吊销证照别无二致。这无疑体现了从实质效果上对某责任形式的制度归属加以判断的思路。
鉴于《行政处罚法》将责令停产停业作为处罚,而行政处罚的强制性和法定性色彩浓厚,缺乏弹性,有必要限缩其范围,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为更为灵活的环境行政命令腾出更大的发挥空间。责令停产停业应适用于需要获得批准或许可才能从事的活动,如相对人获得批准或许可实施该活动,存在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情形下,方有适用的必要。对于无需批准或许可就当然可以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适用的可能。针对轻微的违法行为,只需要适用临时性限产或停产加以整顿即可,无需适用停产停业这种严厉的责任形式。已经获得批准或许可从事某活动的主体被责令停产停业,从有权从事某种活动的状态变为无权从事该活动的状态,对该主体而言,责令停产停业自然具有惩罚性。对于需要获得批准或许可才能从事的活动,如果相对人没有获得批准或许可而从事该活动,自开始属于非法活动,被责令停止从事该活动,只是恢复法秩序,并非对该主体的惩罚。对这类活动,应该适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不宜适用责令停产停业。
在环境法中,排污者的活动依法需要批准或许可,没有获得批准或许可的相对人有不得从事该活动的不作为义务,如果从事该活动,自开始即是非法,运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即可①在具体形式上可以是停止建设、停止生产或使用,等等。。责令停止生产是对建设项目需配套的环保设施未建成、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而投产的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命令[7],相对人本身并没有获得投产的资格,停止生产是停止违法行为的具体形式。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本无资格排污的企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往往并不具备时间持续性,不需要动态监管②这里的不需要动态监管不宜理解为环保部门没有责任核查是否重新开工生产,而是指并不需要对纠正过程进行监管。,可以责令停止违反行为,一禁了之或一停了之。
综上所述,环境执法中的停产停业的适用情形为:相对人已经获得排污审批或许可,但存在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停止违法行为适用的情形为:相对人未取得从事活动的批准或许可而实施该活动,如停止生产适用于相对人未获得排污的批准或许可而擅自排污。
(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对于已经获得排污的批准或许可、违法并不太严重的相对人,也不宜责令其停产停业,永久性剥夺其行为能力,也不宜简单一禁了之或一停了之,应当给“出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恰当的责令改正形式实现相对人从违法排污到合法排污的转化。这个转化呈现明显的过程性,往往需要动态跟踪监管。
较为常见的责令改正具体形式如下:限制生产、限量排污、限产限排、限期治理、限期整改、停产整顿、停产整治、停业整治、停工整治。其中限制生产、限量排污、限产限排是对生产经营活动的限制,停产整顿、停产整治、停业整治、停工整治则是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禁止,但同属于临时性的行为管制,无非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不关乎行为资格的形式上剥夺或事实上行为能力的永久性剥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旨在令相对人进行整改或整顿后重新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以恢复合法秩序为目的,补救性特征明显。“停产”“停工”“停业”,都是作为手段以激励相对人实现合法排污,这为行政机关和相对人采取合作态度、实施合作治理留下空间。
限期治理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被纳入环境行政命令中,但在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201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则为“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所取代。《环境保护法》第60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限制生产”和“停产整顿”就其内容而言应该属于实现达标排放和符合总量指标排放的过程和手段。“限期治理”中如何“治理”并没有明确要求,实践中企业在关闭前还可以继续超标或超总量排污,限期治理似乎变成了企业继续违法排污的护身符,为违法者违法行为网开一面[11]214。“限制生产”和“停产整顿”相较于“治理”含义更为明确,对违法者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虽然具体要求有待进一步确定,但排除了继续超标和超总量排污的可能性,其进步不言而喻。“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是临时性的、阶段性的,针对的违法行为相对较轻,只要企业经过整顿,排污符合法律要求,经环保部门批准可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5]。《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中的“停产整顿”虽然被纳入行政处罚,但却非《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类型,“停产整顿”应该以“停产”为手段,实现“整顿”效果,恢复合法秩序的目的非常明显,建议在修订时归入行政命令中。
《大气污染防治法》使用了“停工整治”、“停业整治”和“停产整治”。分析条文,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和第117条,停工整治针对施工工地、料堆经营者、码头、矿山、填埋场、消纳场等未依法采取防尘降尘措施的,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第117条及第120条的规定,停业整治主要针对第三产业如餐饮、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停产整治更多针对生产者。
日本的改善和停止使用命令和我国上述责任形式十分近似。《大气污染防止法》第14·1条第1款规定,都道府县知事在烟尘排放者于排放口继续排放烟尘量或烟尘浓度均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危险的情况下,认定因其继续排放会发生与人体健康或生活环境有关的危害时,可以命令该排放者限期改善该烟尘发生设施的结构、使用方法或与该烟尘发生设施有关的烟尘处理方法,或者命令临时停止使用该烟尘发生设施[12]1026。改善命令和停止使用命令,是以防止环境污染、有利于将来的环境保全为目的的,不应把它作为对过去的违法行为的制裁加以运用。例如,有些工厂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超标有害物质,现实上给周围的居民带来了损害,但在改善了其设施、已经遵守排放标准的场合下,不得为对其实施报复而命其停止使用设施等。总之,设施的改善命令、停止使用命令,应该作为为防止将来公害于未然的制度加以运用。改善命令,是为防止公害命令采取必要的设施改善等的手法,命令采取何种改善措施由行政机关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改善命令的内容宽泛地交给了行政机关的裁量判断。被下达的改善命令必须是本来就有实现可能而且能够特定的事项,不能是无限定的事项[13]83-84。改善命令的内容需要明确、措施必须特定化,不能过于笼统。
为避免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被法院认为责令改正的行政命令过于笼统、不具有执行内容而拒绝执行的尴尬,环境执法中有必要在内容上对责令改正加以明确。一切行政行为都具有连接法律规范和现实生活的桥梁作用,行政命令是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科处特定义务的行为,作出过程分为三个步骤:法律规定——命令发布——义务履行。由于行政命令有法定命令和职权命令之分,上述过程分两种情况展开。一种情况是,法律对行政命令作出直接、详细规定,有权主体依法发布命令,相对人履行;另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较为笼统和概括,实际默许有权主体对义务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具体化和明确化,并加以发布,相对人履行义务[2]。当然,具体内容必须具有可行性,相对人经过努力可以履行。适用于不具有排污资格的相对人的停止违法行为属于第一种,适用于具有排污资格但有违法排污行为的相对人的责令改正属于第二种。环保部门作出责令改正的命令时不宜“一刀切”表述为“责令改正”等,也不宜笼统责令相对人限制生产或者停产整顿,而应当为相对人规定履行的期限和方式,在确定具体改正的时限和方式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考虑相对人的实际情况并征求相对人的意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办法规定责令限制生产决定书和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应载明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改正方式、期限。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期限,限制生产的程度、计划或方式,整治计划或方式等,如此方具有可执行性或具有给付内容,法院自然没有理由拒绝执行。
当然,责令改正还包括限期缴纳排污费(环保税)、公开环境信息、如实进行排污申报等责任形式。
三、消除环境危害后果
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的责任形式不是针对行为而是针对行为造成的环境危害后果。
(一)我国现有立法中的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的形式
根据我国相关立法,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的具体形式包括恢复原状、限期拆除、限期清理、消除污染等。
恢复原状适用情形有: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擅自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违反规定造成领海基点及其周围环境被侵蚀、淤积或者损害的;违反规定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海洋工程建设活动的;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非法占用海域的;未经许可,擅自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以外范围、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影视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的等。
限期拆除的适用情形有: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码头的;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未持有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者私设暗管的;未持有经审核和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兴建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等。限期拆除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原状具体形式,有时结合使用,如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
限期清理适用情形有:海洋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海洋排放含油污水,或者将塑料制品、残油、废油、油基泥浆、含油垃圾和其他有毒有害残液残渣直接排放或者弃置入海的。
消除污染适用情形有:企业事业单位违反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将畜禽养殖废弃物用做肥料,超出土地消纳能力,造成环境污染的;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或者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的;对已经非法入境的固体废物,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的;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的;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者容器的;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或者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等。
(二)修复污染场地
上述责任形式都是我国现行环境立法针对违法行为造成环境危害后果对相对人施加的义务。以前瞻性的眼光看待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的具体形式时,会发现正在制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的修复污染场地也是典型的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的具体形式。
各国立法通例将土壤污染修复责任纳入公法责任中。这种责任的定性赋予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污染土壤修复对象识别以及对责任人课以修复义务的决定以公定力,即行政机关可以单方面决定责任人的法律义务或责任,直到被有正当权限的机关取消或者确认其无效为止[14]114。在具有公法和私法分野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都是由行政机关划定需要修复的地块并命令责任人实施修复。如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第7条规定,发现某划定区域特定物质造成的土地污染达到环境部法令规定的标准时,地方行政长官可以根据内阁法令的规定,在防止污染的必要限度内,命令该地块的所有者(包括所有者、管理者或占有者)或者污染行为者采取清理污染、防止污染扩散以及其他必要措施。美国《超级基金法》也授权环保署必要时自行签发行政命令,要求责任主体采取具体措施清理污染设施[15]30-35。为了提高污染场地修复效率,超级基金法第113条(h)款禁止联邦法院审查针对行政机关根据第104条选择的清理行动或修复行动提出的异议,或者审查行政机关根据第106(a)款发布的要求责任主体采取行动的行政命令。虽然在通用电器(GE)诉美国环保署案件中,通用电器公司认为这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但挑战没有成功[16]253-257。可见,联邦法院支持行政机关就污染场地修复发布的行政命令,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污染场地修复责任事实上被定位为公法责任。欧盟《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中找到与我国环境行政命令较为类似的环境行政行为。根据《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必须以“环境责任指令”为基础制定“国家环境责任法”并贯彻实施。“环境责任指令”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环境损害范围,规定政府当局必须以命令的形式责成污染单位修复环境损害,以达到预防和补救的目的。这种“责成”的命令形式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环境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命令行为[17]6。由于土壤污染修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各国大都规定,土壤污染修复计划由专门的土壤污染修复专家负责起草,还需提交给有关主管机关审批之后付诸实施[18]。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也规定,行政机关应责令责任人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此时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土壤污染修复涉及污染地块的调查评估、修复目标的确定、修复方案的编制、修复方案的施工、修复过程的监督、修复结果的验收,行政机关因其专业性优势,较之法院对整个过程更有能力加以监管。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服可以提请司法审查,法院仅仅是对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不触及合理性,因为专业技术性是行政机关而非法院的优势所在,这也是司法权不得侵犯行政权的原则的要求。因此,修复污染场地应纳入环境行政命令范畴。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各国立法例,土壤污染者无论是否具有过错,都有修复污染的责任,合法排污或非法排污并不影响修复责任的成立。
消除环境危害后果呈现明显的过程性和变动性,需要一定的动态过程监管,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形确定行政命令形式、内容和实现手段。这种明确化和具体化既是为相对人提供指引的需要,也是获得法院执行的需要。当然对于履行过程较为持久、存在不确定因素概率较大的情形时,不排除含有弹性和灵活空间,根据情况对义务内容进行调整或变更。如土壤污染修复施工过程中发现污染场地调查不充分、不全面时,有必要重新调查或者补充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调整修复目标和修复方案。消除环境危害的过程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因此,对环保部门的动态监管提出的要求很高。
结 论
综上所述,环境行政命令的体系可以梳理如下。

针对环境违法行为,我国法律实践长期以来偏好适用行政处罚,轻视行政命令的适用。在环境行政命令中,环保部门对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适用又远远多于消除环境危害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原状、限期拆除、限期清理、消除污染等消除环境危害后果的形式被闲置,其结果是 “企业污染、政府买单”常态化,没有充分贯彻损害担责原则。因此,有必要全面梳理、正确认识环境行政命令体系,推动出台规定环境行政命令的种类和程序的《环境行政命令办法》,充分发挥环境行政命令的补救性功能,形成针对违法行为的环境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两相配合的格局。
[1]王明远:《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
[2]曹实:《行政命令地位和功能的分析与重构》,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期。
[3](德)哈特穆忒·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程雨燕:《试论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之制度归属——兼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涂永前:《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行政命令的衔接——从<环境保护法>第60条切入》,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6期。
[6]陈海嵩:《论限期治理的法律属性》,载吕忠梅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8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杨朝霞:《“责令停止生产”与“责令停产”的辨析和适用》,载曾晓东、周珂编:《中国环境法治》(2012年卷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8]曹实:《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的性质界分》,载《学习交流》2016年第2期。
[9]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0]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11]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12]赵国青主编:《外国环境法选编(第一辑下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4](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李冬梅:《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上的环境民事责任研究》,载《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版。
[16]贾峰等编著:《美国超级基金法研究——历史遗留污染问题的美国解决之道》,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
[17]罗怡超:《环境行政命令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版。
[18]梁剑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模式考察》,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
HU Jing,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 is regard as the accessory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n legal practice and is neglect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s a result, its remedial function is concealed in China.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 based on the remedial function should be divided into redress on illegal action and redress on environmental damage result, further, into all kinds of subtypes, and then constitute its system.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system,promote legislation and explore the remedial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order;redress on illegal action;redress on environmental damage result
D922.68
A
1671-7023(2017)06-0082-08
胡静,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科学研究项目(17ZFG82003)和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2017-06-01
责任编辑 胡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