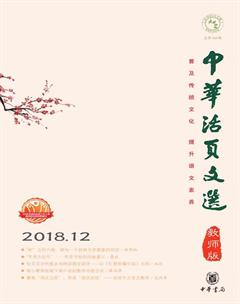经典的误读及其反思
刘红娟
经典是在阅读与传播中生成的,但和经典本身一样,在经典生成的进程中,其阅读史上的见仁见智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共存,洞见与盲视共舞。甚至有些经典,往往是因为阅读进程中的“谬误”与“偏见”而脍炙人口。而这些误读一旦自身固化成为经典,则以讹传讹,这里姑且以《儒林外史》中的典型人物严监生的经典误读为例来谈。
一
说到严监生,“两茎灯草”的细节(《儒林外史》的第五回末与第六回初),人们可谓耳熟能详。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毫无起色。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以后,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
——《儒林外史》第五回《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儒林外史》第六回《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严监生的所有讨论,大多都基于这两段文字。而得出的结论几乎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严监生是个吝啬鬼,与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代表作五幕喜剧《悭吝人》中的阿巴贡共同成为中西文学史上一对典型的吝啬鬼形象。令人不安的是,此类误读的泛滥与陈陈相因,尤其以传播广泛且深远的教材为深重。
对严监生形象管中窥豹式的误读早在基础教育的小学阶段开始。前面所引两段文字被收入了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教材,命名为《临死前的严监生》。讨论基础教学教法的一书指出:“读过文学名著的人一般都知道,文学名著中有‘四大吝啬鬼形象,严监生榜上有名。于是,严监生就不仅仅是小说中的人物了,其文学形象早已超越了文本,进入了日常语言,成了‘吝啬鬼‘守财奴的代名词。”这种观点不仅代表了基础教育层面对严监生形象的判断,也代表了普通大众对严监生形象的经典判断。
如果说作为基础教育的小学阶段的误读不足为虑,那么我们看看高等教育的三套权威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相关叙述和讨论。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这样写的:“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這一形象辨析有所变动,已经注意到艺术不外乎人情的境界,书中写道: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提到“两茎灯芯”的细节:“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不过,也注意到了严监生性格中的复杂性,教材同时指出:“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从游国恩到章培恒再到袁行霈,编撰时间前后相差不到四十年,但三种教材的涵盖面和概括力,基本可以呈现读者对严监生这一人物及其相关细节片段的解读形态,即“被讽刺的本质化的人物”——“有人情味的人物”——“有丰富个性的人物”。但不管如何,三部教材都无法撇开吝啬来谈,以至于总是存在着对于严监生阐释的两难困境,没能在解释这个人物的“人情味”和“性格矛盾”中走出围城。教材如此,学界观点大抵亦如此。
难道承认严监生并不吝啬有那么艰难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在困扰着我们不能、不敢得出这一文本事实很浅显的结论呢?当然是经典的阅读谬误造成的思维传统与结论定式。
二
解读严监生(严致和)的形象,当然要以文本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儒林外史》中对严监生的居家和持家之道有所交待,分正面叙述与侧面交待两种形式,可谓全方位地呈现了严监生的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细读全书,小说里正面叙述来展现严监生性格的文本,约略有三处:
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第五回)
……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第五回)
第三处便是上面所言的经典细节——掐灯茎。
显然,文本中直接写严监生本人生活经济表现的笔墨并不多。当然,除了正面的刻画之外,小说还通过侧面衬托或对比的方式来塑造严监生。一是根据夫唱妇随的逻辑,小说里另有两次借老婆王氏和妾赵氏的话,来呈现严监生生活状态叙述。
一次是妻舅王德和王仁到严监生家里赴席所见:
严致和即迎进厅上。吃过茶,叫小厮进去说了,丫鬟出来请二位舅爷。进到房内,抬头看见他妹子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见他哥哥进来,丢了过来相见。奶妈抱著妾生的小儿子,年方三岁,带著银项圈,穿著红衣服,来叫舅舅。(第五回)
另一次,则是严监生妻子王氏病逝后,原为妾室、后来扶正的赵氏顾念王氏时所言的:
吃了几口酒,严监生掉下泪来,指著一张橱里,向赵氏说道:“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姊姊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给他,我也不管他在那里用。今年又送这银子来,可怜就没人接了!”赵氏道:“你也别说大娘的银子没用处,我是看见的;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他的恩惠?况他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成的,也要把人穿;这些银子够做甚么?再有些也完了!”(第五回)
此外,小说还从其哥哥严贡生及其家庭生活塑造上,对比写了严监生。严监生尽管屡屡受哥哥严贡生的窝囊气,却倒也厚道,从来没有太过贬损哥哥严贡生,只是对哥哥家里人有个评述:
我家嫂也是个糊涂的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也不听教训。
……便是我也不好说。……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第五回)
而严监生的妻舅王仁、王德从亲戚眼光看严贡生,也在呼应着严监生的言下之意并不虚:
王仁道:“老大而今越发离奇了,我们至亲,一年中也要请他几次,却从不曾见他家一杯酒。想起还是前年出贡竖旗杆,在他家里扰过一席酒。”王德愁著眉道:“那时我不曾去。他为出了一个贡,拉人出贺礼,把总甲、地方都派分子,县里狗腿差是不消说,弄了有一二百吊钱。还欠下厨子钱,屠户肉案子上的钱,至今也不肯还。过两个月在家吵一回,成甚么模样!”(第五回)
综上可见,事实上严监生的为人极为勤俭厚道。表现有三:
第一,他于兄弟人伦诚挚笃敬。严监生对贪婪无耻、蛮横无理的兄长,没有恶言相向,反而为其忧心如焚,操心不已。对病重的妻子,也是尽心尽力医治。对于妾室扶正一事,花费也是尽心尽力。
第二,则是夫妻之道令人敬重。严监生固然是节俭,其妻王氏更是勤俭持家。王氏哥哥过来吃饭,她自己“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王氏会如此操持家务,一方面也许是性情贤惠,但另一方面无疑也是夫妻齐心的情感表征。因为严监生对妻子王氏并不苛刻,王氏不但有自己的收入,每年光典当的利息就三百两。王氏还可以自由支配这些钱,做善事做好事,严监生一概不闻不问。相应地,夫唱妇随,王氏也就能想丈夫所想、急丈夫所急,把钱存起来放在吊篮子里,预备家中应急。
第三,则是妾室赵氏的表现。王氏没有子息,赵氏生有一子。按常情常理,王氏病重,赵氏完全可以拥“儿”自重、坐等顺位。赵氏要“扶正”的焦虑,显然是来自严监生的主导,原因当然是因为虑及唯一的儿子继承家业的名分。问题就在于王氏的时间不多了,严监生和赵氏为了抢这个节点,尽善尽美地主动解决这一问题,才有赵氏颇有“心机”的那些表现。
在我看来,通过情感的铺垫,严监生、王氏、赵氏三者达成的共识正确,恰恰是以王德、王仁及其妻子在妹妹去世前后的丑態毕露得到了证明。赵氏居然连扶正仪式头上戴的赤金冠子也被王德王仁的老婆掳走,很难说赵氏哭王氏是假仁假义的。严监生倘若不仁,会有这样的妻和妾么?
反倒唯一让人觉得有些不忍的,却是严监生对自己的苛求,真可谓克己复礼。他对王氏生前恩爱情谊的顾念阑珊,他对妾室赵氏的尊重,他对儿子的爱,表明他并非一个无情刻薄的人。也许有人会觉得严监生在赵氏扶正一事上虚伪,乍一看也确乎如此。但看到后面哥哥严贡生在他去世后的侵夺弟弟家产时的诸多行径,不由得佩服严监生事前的多虑和周密自保的做法。而且妾室赵氏与严贡生、王德王仁的交际,难保就不是严监生生前有所交待的。然即便如此周密小心的经营,严监生按“礼”出牌的精心布局,仍旧难以抵挡哥哥严贡生贪没家财的狼子野心。
如此说来,严监生不但不是什么可笑之人,相反,他是个令人同情的人。他的可怜之处,恰恰是他想自尊自爱、自足自乐而不得的处境。原因自然有他的懦弱,但未必就不是因为他的善良,以及那个满口诗书礼义的虚伪世界的逼迫。可叹可悲的是,那个情境下的严监生,一个仅仅通过独善其身而自保、仅仅想通过勤俭而希望能持家的人,即便做得如此勤俭周全,善始善终也只能是个瑟瑟缩缩的梦想。这才是善的悲剧,才是对那个虚伪礼教世界的批判。
三
既然严监生并非一个多么可笑之人,其勤俭的持家之举即便有些苛刻,无论如何也着实不该将其简单化地定性为吝啬鬼。但长期以来,他已然被定型为中国乃至东方吝啬鬼的经典代表。但是,从来如此便对吗?
严监生究竟是不是个吝啬鬼?为什么他会被阅读成了一个经典的吝啬鬼的典型人物呢?
吝啬的基本含义是“小气,当用而舍不得用,过分爱惜自己的钱财;气量狭小,用度过分减省。”可见,大凡言及吝啬,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过度、过分爱惜,当用不用;一是气量狭小。吝啬是该出不出,该花不花,视钱财如性命,爱财如命,甚至把钱财看得大过命。但前提都是有钱,够用度支配。也就是说,一般说来,大凡吝啬,前提需是有钱,而且是相当余裕的有钱。倘若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富足,吝啬便无从说起。进而言之,达到相当的物质丰富,却不肯坦然承担正常的支出,这才叫吝啬。
相较而言,节俭则无须富足余裕这一前提。节俭不过是积累财富的方式方法,而吝啬不是。节俭往往与勤劳相结合,缺一不可。正因如此,节俭还是某种道德美誉的缩略语。因此,节俭是该出的出,但不多出,而且尽量少出;该花的花,但不乱花,而且尽量省着花。显然,严监生顶多也就是后者。况且,吝啬多指向他人,节俭则更是律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而事实上,严监生充其量也不过是节俭成性而已。至于说他的节俭是否过犹不及,则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但就文本所述,也还属于物理人情的范围。
严监生是否吝啬?应该算不上。严监生的确“家有十多万银子”,尽管原始资本也是分家时所得,和哥哥严贡生一样。只不过严贡生坐吃山空,严监生则开源节流,所以才有越拉越开的差距。虽说严监生有钱,但只是对自己苛刻,对家人也还不至于。夫人王氏生病,用药也是舍得的,人参之类的不缺。哥哥贪婪、好吃懒做,他却不得不要帮哥哥严贡生拆烂污、擦屁股、兜破事。按惯例,他虽有钱,但也没有理由为哥哥的事情包圆善后。这里面或许有怕麻烦的因素,但起码也说明他对钱财这方面并不看得太重。
可悲的是,胆小善良的严监生一家试图用钱财消解烦扰、解除后顾之忧的做法,不但没有获得哥哥严贡生的回报和支持,也没有博得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的真心庇护,更没有得到所在环境中的呵护与理解。相反,他试图自足自乐的生活,始终处在哥哥严贡生虎视眈眈的各种威胁与困扰中。于是在临终之际,他面对满满当当挤了一屋子的看热闹的人,面对五个如生狼一般等待着抢夺其家产的侄儿,严监生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所思所想,无疑只能是绝望。因为这一切对严监生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真真是徒费灯油。
也就是说,严监生要掐灭一根灯茎的含义,固然是他认为其浪费灯油。但为何是浪费?似乎无人往平常心上去试解一二。连一贯懂得丈夫的妾赵氏,也以为他是在忧心费灯油而已。对一个身家不小的临死之人而言,忧心区区一根灯茎浪费灯油,的确是过于苛刻。但细细想想,严监生临终时所处的情景,面对一屋子虎视眈眈图谋家产的虎狼之徒,除了见物不见人的两根灯茎的无奈与嘲弄之举外,还能说什么呢?难道他那执着摇晃的两根手指,不也是一种无声似有声的抗议与嘲弄吗?
善良柔弱的人被欺侮嘲弄,贪婪横行的人反而得美名功利,人世的悲哀莫过于此。严监生对他人常常慷慨解囊,对自己严苛如此,充其量也就是过于节俭。如此说来,严监生仍是吝啬鬼吗?
四
基于文本的证据,可以发现严监生并不吝啬,但应该说严监生的确为人羸弱。小说里没写他欺负别人,都是写他怎么花钱周全各种外来的烦扰。花钱最多的,便是他哥哥严贡生嫁接到他身上的各种麻烦。严监生为何要怕他哥哥呢?原因只是他有两点无法改变的劣势:一是功名,一是伦理。
何以见得?严监生是个明白人,在对两位舅老爷临行托孤时,他说:“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严监生非常清楚老大严贡生公然欺侮自己的底气所在。一是自己功名比严贡生低。监生比贡生低级。严贡生贪赃枉法,却可以和汤知县暗通声气,实在不行可以一走了之。严监生面对来找哥哥严贡生办差的差人,“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最后还请两位舅爷商议,“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才“官司已了”。接着还要“整治一席酒,请二位舅老爷来致谢”。因为这功名差级的原因,严监生怕官,甚至比一般的小老百姓还怕。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严监生就是一个“穿鞋”的“监生”而已。乃至于他的“监生”名分,也不外乎就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鞋”而已,甚至还没有鞋的实际用处。
严监生一生气短,屡屡受哥哥严贡生欺侮,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家族内身份也比严贡生低。严监生说哥哥严贡生是大房出身,他自己则是二房。大房与二房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严监生与哥哥的身份等级差别。以至于严监生在世时,虽然勤俭持家而家业殷实,但仍旧终日要周全哥哥的行动,看严贡生脸色行事。更毋庸说严监生一去世,严贡生便公然觊觎弟弟家产,乃至于自作主张要当弟弟家的家长了,甚而至于威胁要发卖弟媳妇赵氏。
一是功名,一是伦理。严贡生也正是拿捏住自己这两点在封建秩序里的天然优越性,不仅不拿族长当回事,更不拿严监生的妻舅、妾氏的亲戚当回事。有意思的是,严贡生蔑视赵氏为弟弟的妾的出身,在立嗣问题上大包大揽,想法子贪没弟弟家产。严监生的妾赵氏不服上讼,恰好几个环节的主官都是妾生身份,于是严贡生在府、县都告输了,司里又不理。可见,严贡生一旦发现伦理规则不起作用时,就凭自己的功名来施压。当发现功名威力不够时,便层层托关系、勾结官府权利,只得飞奔到京,想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伏。最后还是弄了个三七开的审判结果,轻而易举地侵吞了弟弟的大部分家产。严监生一生谨小慎微、克勤克俭,却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叹息。
显然,《儒林外史》对比着写严监生和严贡生两兄弟,讽刺的是严贡生以及纵容、包庇和衍生这类人事的不合理的社会。对于严监生的胆小、勤俭和克己复礼,以及最终令人扼腕叹息的命运,作者在冷峻的筆墨中,寄寓的应该是同情,传达的无疑是人世冷暖的叹息。长期以来,阅读者仅仅把严监生定格成一个吝啬鬼,这对严监生典型化处理的经典阅读模式,不仅有点混淆黑白,更僵化了对《儒林外史》这一高度浓缩的艺术片段的理解,萎缩了人类天性中应有的对于善良与弱小者的感慨与同情。
五
吴敬梓是对比着写严贡生和严监生两兄弟的,其艺术公心所向绝不仅仅是塑造、讽刺一个吝啬鬼。显然,较之哥哥严贡生的满口仁义道德、标举诗书,实则寡廉鲜耻、巧取豪夺、挥霍无度、贪婪无耻,弟弟严监生的克己复礼、节俭成性、畏缩懦弱无疑更让人同情。因此,仅仅以两根灯茎这一经典细节孤立理解严监生,并将其理解为吴敬梓意在讽刺一个节俭成病态的书生,不仅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儒林外史》的艺术趣味。
重新讨论严监生,目的不是为其翻案喊冤。但对这个人物的重新理解,无疑可以刺激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和估量《儒林外史》的艺术旨趣。众所周知,《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最为显著的特征,大概就是“讽刺”了。诚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毋庸讳言,鲁迅对《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概括异常赅要,如老吏断狱,可谓对经典的经典概括。但是,《儒林外史》写得好,与讽刺与否、讽刺对象并不构成直接的逻辑关系,而是其“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机锋”与“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而”。而所谓“机锋”和“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之间的两个“而”,这不也就是恩格斯的说法——“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本领吗?可见,阅读、理解与欣赏《儒林外史》,要件有二:一是不忘吴敬梓写作的初心和始终,即“公心”;二是不要偏执于“戚”与“能谐”、“婉”与“多讽”的任何一端,而是要辩证理解,即体会作者将它们融于一体的“而”的功夫。前者是内容与思想,后者是艺术才华。如此才能更好地在经典阅读中品味古今同慨的人生共识,而不是仅仅存留些许干枯的文学笑话来慰藉世俗。
事实上,不仅《儒林外史》的阅读需要反思和检讨,许多经典作品,尤其是那些以选择和过滤了的作品片段来广泛传播的经典都存在这个问题。譬如一提到《红楼梦》,林黛玉就成了病态的促狭才女、身体不好的偏激女子代名词,薛宝钗则是八面玲珑、吃得开、会做人的贤德女性代表。贾宝玉自是毫无世俗用处的多情公子,薛蟠简直就是花花大少、空心大萝卜的“富二代”……一提到《儒林外史》,就只想到范进中举时的失心疯、严监生掐灯芯等若干经典片段。这些文本片段被一再作为经典选段进入阅读、传播层面,所涉人物形象的艺术思想内涵也就往往不被深究,反而在大众趣味和世俗压力的双重遇合下,成为非常庸俗的阅读趣味,甚至自然而然地被当作生活与艺术珠联璧合的榜样,以符号化的形式流传于世俗趣味与大众营销共谋的阅读共识谱系之中。多少丰富的艺术形象都是如此滑入大众的、庸俗的阅读共识视野中!
经典作品的经典选本或者选段进入教材,固然极大推广了经典的传播与接受,也弘扬了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化魅力。但与此同时,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片面、浅薄和负面化的理解与阐释。一旦对人物的解读在某一时段内因应着时代语境和社会潮流而出现定式思维一边倒,不仅会将鲜活的文本脱了水、定了轨,更会歪曲、扭曲甚至凋敝了读者活跃丰沛的阅读主动性。
如今,呼吁对经典文本的阅读,旨意恰恰就在于融通古今的人心隔膜,让今人在人生的意味上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慈悲。毫无疑问,在这个意义上,对经典文本展开细读、回读、反读与全读,在曾经和现在都经历过那么多阻断、引导与隔阂的当下中国语境,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选自《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