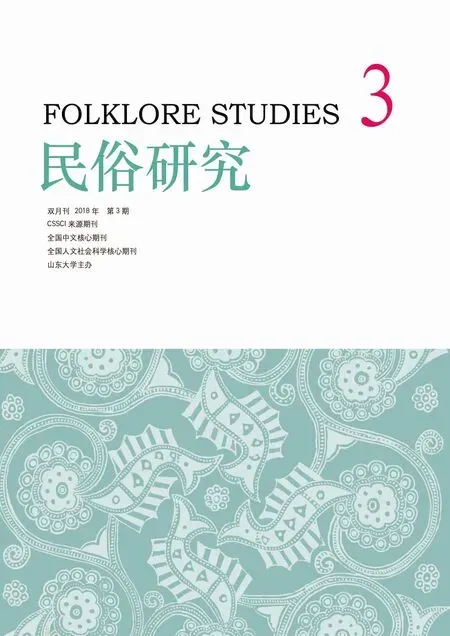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
王杰文
自“实践民俗学”的旗帜被树立以来,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俗学者都对它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部分民俗学者囿于某种被建构起来的学科边界及学术陈见,不肯越雷池一步。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对于“理所当然”的学术传统不加追问,只知道眼前的苟且,不知道还有诗与远方;另一方面,实践民俗学者的关键概念、知识谱系、话语方式、问题意识等迥异于传统民俗学,而他们“传经布道”的通俗化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因此,“实践民俗学”至今仍然没有获得它应得的关注。
从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实践民俗学”是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毅然决然地要与传统民俗学(户晓辉教授称之为“经验民俗学”)相决裂。这种势不两立的决绝态度让少数传统民俗学者深感惊愕;惊愕之余,又不免觉得这些实践民俗学者不过是“21世纪的唐·吉诃德”,既疯狂得可以,又可爱得出奇。这种直觉与印象似乎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户晓辉教授与吕微教授的确有些像唐·吉诃德,比如,他们坚守着某种高度的道德原则,体现着某种无畏的精神,怀抱着高尚的理想,公开表达对自由、平等、正义的信仰,对事业的忠贞(当然,在唐·吉诃德那里,是对爱情的忠贞);但是,他们又与唐·吉诃德截然相反,因为他们并非神志不清,他们的行为既不疯狂更不可笑。相反,他们坚定而忠实地强调“理性”“自由”等启蒙主义的价值理念,向往彻底的民主与法制。因此,准确地说,他们是高扬“理性”价值的唐·吉诃德。反过来,在实践民俗学者看来,实证的经验民俗学似乎总是显得鄙陋不堪,鸡零狗碎,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经常是在从事一些经不起推敲与论证的、可有可无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工作;那些自鸣得意的经验民俗学者仿佛“快乐的小猪”或者“迷途的羔羊”一般,缺乏理性地反思的能力,甚至完全不知道“自由”的价值理念与民俗学可能有什么关系。面对少数固执的反对者与大多数冷漠的沉默者,实践民俗学家大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悲壮感,然而,也许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而自矜的实践民俗学者还应该自问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近来,户晓辉教授的专著《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正式出版了,这是作者与吕微教授努力倡导“实践民俗学”多年以后,努力把它应用于理解家乡、亲友与自我之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项学术实验,也是对“实践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予以更全面、更系统地阐释的一次理论尝试。这种寓理论讨论于经验描述的实验性写作模式,给读者清晰理解“实践民俗学”的哲学基础、核心理论、学术价值及其终极目标提供了方便,也为深入反思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史、理论预设以及未来走向辟出了新途径。
质疑与辩难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实践民俗学”的思想观念正在通过少数民俗学者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而渐渐清晰起来,并在小范围内获得了一些影响。*对于“实践民俗学”的质疑与答难,可参见吕微、户晓辉、王杰文等人在“民俗学论坛”网络上的争辩: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forum/viewthread.php?tid=36968&extra=page%3D1。另可参见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吕微:《理想的共同体:构建日常生活的先验语境——王杰文〈表演研究:口头艺术的诗学与社会学〉的实践民俗学理解》(未刊稿);户晓辉:《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户晓辉:《重识民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答刘宗迪和王杰文两位教授》,《民族艺术》2016年第5期;王杰文:《“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王杰文:《“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民俗研究》2016年第4期。在户晓辉教授的新著出版之际,本文试图对其“实践民俗学”的理性主义主张进行批评,努力说明当前国际范围内的“‘实践’民俗学”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
一、“愤怒的”实践民俗学家
为什么说“实践民俗学家”是愤怒的?因为他们对于国际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历程感到不满,也因为他们对中国民俗学家们“忘记初心,辜负使命”的盲从与沉沦感觉忿恨,根本上则是因为他们对于自由之车的两翼——民主与法制——在中国未能深入贯彻感到痛心。在他们看来,人的本质就是追求自由;生命、自由与幸福是人类不可转让的权利。这些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组成部分被屏蔽于学术研究之外,这难道不是令人愤怒的事情吗?对于“民俗学”这样一门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学问来说,忽视“自由与民主”这样一些先验的伦理问题难道不是不道德的吗?因此,户晓辉教授说,“民俗学家已经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基于自由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哲学理念,实践民俗学家的第一项任务是“正本清源”,要让被埋没已久的“初心”与“使命”重新显现出来,具体来说,就是要批判“经验实证的民俗学传统”与“某些后现代的民俗学倾向”,证明它们“终归是迷妄,不能得究竟”。
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户晓辉教授认为,现在所谓“民俗学”(他认为其本义应是“民学”)的学科称谓其实是一种“误译”,而这一“误译”的灾难性后果是“民”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被作为民俗学实践的主体。在科学化的学术潮流中,“民”只是作为被认识的对象,其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却被忽视了。站在“实践民俗学”的立场来看,那些先设定问题,然后去田野寻找信息和答案的经验民俗学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在逻辑上已经把民众当作了“客体”而不是“主体”,当作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这样的研究并不具有头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77页。。相反,“实践民俗学不仅要看见民、发现民,还要把我们多年来一直未能踢出的临门一脚踢出去——重新还原日常生活的目的条件,并在其中看见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52页。户晓辉教授“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论证从“俗”转向“民”,从“经验实证范式”转向“实践理性范式”的正当性,试图因此返回民俗学实践理性的起点,彰显民俗学“当初”所立下的鸿鹄之志。从更深层的逻辑来讲,“实践民俗学”认为,既然学者与民众都是“人”,那么,民众的不解放和不自由就意味着学者的不解放与不自由。“实践民俗学”要求直接面对学者与民众在交互主体意义上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即“人的自由的问题”。
第二,既然“人”及其自由才是“实践民俗学”的最终目的,那么,“实践民俗学”不仅不能赞同经验民俗学的那种实证的、归纳的研究方法,而且根本不屑于仅仅关注那些已然的、实然的经验事实、行为事实,而是把关注的重心转向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因为“我们提出的实践民俗学,不是指一般的实践,也不是指基于任意意志的实践,而是指基于自由意志的实践。因为基于任意意志的实践仍然是外在于实践理性的、不纯粹的经验性的实践;只有内在于纯粹理性的自由意志的实践才是内在的实践。”*户晓辉:《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基于主体外在的与内在的局限性,已经发生的经验事实、行为事实常常并不是合意的,与实践民俗学家们关心的“自由”的概念不相干,现实中,“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但是,人的自由意志是向往更加完美的、合意的人生的。所以,自由的实现经常并不是在过去的日常生活中,而是在面向当下与朝向未来的理想的生活观念之中。因此,在实践民俗学家眼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第三,基于康德的道德哲学,户晓辉教授坚信:普通人先验地具有行为的道德意识(比如常识感、公平感与正义感),实践民俗学家的工作只是去发现并还原普通人的道德意识,并把这种道德意识的目的条件清楚地还原出来,尤其是要把其中的“理性目的”还原出来。换句话说,“实践民俗学”重新设定(户晓辉教授宁愿说“重新发现”)了民俗学的学术任务。既然“实践民俗学”试图研究的是通过理性就能够认识的实践知识,那么,实践民俗学家有理由强调“理性”而不是“经验”的重要性;既然还原实践行为的目的条件并不必然需要借助田野经验,相反更多的是要借助知识储备、阅历、视阈和判断力等主观条件,以及时间上的契机等,那么,实践民俗学家们就把“田野”转向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验实证意义上的田野不适合实践民俗学。”*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09页。“所以,我天天宅在家里,就已然在田野之中了!”*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93页。
第四,“实践民俗学”是一种伦理学与政治学,它的终极目标是推动中国社会确立以理性公识为基础的道德行为和社会制度。“在中国,无论搞什么研究,都不能对如何让我们过上好生活的那种政治不闻不问”*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可是,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户晓辉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需要努力传播才能进一步深入人心,民主思想与法治观念仍然需要深入彻底的理解与践行。总之,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更需要“实践民俗学”,更需要实践民俗学家强化与彰显日常生活的目的条件与基本前提,更需要民俗学者去努力推动以现代公识为目的条件的日常生活政治制度实践。
当然,最让实践民俗学家“愤怒的”的是中国人向来缺乏理性地思考与辩论的能力这一基本事实,“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学术活动中,我们习惯的是争吵而不是真正的论辩或论证”*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所以,对于他们重新提出的学科使命,实践民俗学家既不能不乐观地相信“未来”与“将来”;又不得不悲观地面对“向来”与“从来”,颇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在里面。
高扬“理性”旗帜的实践民俗学家认为:人们对于他们的问题,至少在原则上,在任何地点与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凭借“理性”来解决;而这些解决的办法因为是“理性”的,因此不可能产生彼此之间的冲突,最终只会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真理将会流行,自由、幸福与不受妨碍的自我选择将向所有人敞开。人类将从蒙昧与野蛮的迷雾中走出来,最终获得自由与解放。总之,实践民俗学家们高唱着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谱写的歌曲,扛着“自由、理性、民主”的大旗迎面走来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理性”之上。
二、实践民俗学家的“自由哲学”批评
无可否认,“实践民俗学”属于我们这个国家与时代。因为它比他们所批评的中国的“经验民俗学”更加关心当下的现实与日常生活的困境。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俗学者仅仅满足于辗转引述国际民俗学界流行的理论成果,“只顾低头拉车,忘了抬头看路”(户晓辉教授如是说),对于一些貌似简单却又是根本性的学科问题(比如民俗学是什么?民俗学的学术任务是什么?)漠不关心,或者只是拿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陈词滥调敷衍了事,自欺欺人,他们不能、不愿也不想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相反,从一开始,实践民俗学家就是直接针对这些基本问题展开研究的,
“实践民俗学本来就是这样一门自由的学问。难道有谁不想让实践民俗学成为一门直抵人心和直达人性的自由学问吗?如果中国民俗学者只是一味步当代德国欧洲民族学或经验文化学之后尘,把从黑格尔到格林兄弟的Volksgeist(人民精神)完全抛到一边而不再重新思考它,民俗学研究的民岂不变成了没有精神的存在者吗?没了精神,那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吗?民俗学者搞再复杂的术语和不断翻新的方法论,除了自娱自乐甚至自欺欺人之外,对普通民众有用吗?什么叫接地气?什么叫走来走去没有根据地?至少是此之谓也。”*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重着号为笔者所加。
户晓辉教授的上述质问,在风平浪静的中国民俗学界不啻于一声振聋发聩的“狮子吼”。他把“实践民俗学”与“自由”“真正意义上的人”等术语关联起来,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把古典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引入民俗学,借以反思、补救民俗学在形而上学层面的缺憾,实则不然,因为他所依据的有关“人的先验本质”的思想不只是对固有的民俗学研究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相反,它转变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任务,甚至彻底地改变了民俗学的学科性质,是要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民俗学奠定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18-579页。因为户晓辉教授所界定的“实践民俗学”本质上是一门思辨的学问,而不是经验的研究。他的“实践民俗学”描述的家乡、亲人以及他们自身的日常生活,是根据他所说的人的永恒利益来描述他们生活的意义,他想象性地进入其他人的经验,并以一种通感的方式表达普遍的道德理解,他坚信:存在着客观、永恒且普遍的道德与社会价值,它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任何一个理性之人的心灵只要选择正视它们,便可以接近它们。
“实践民俗学”立论的第一块基石就是有关“人与自然”的区别:因为人类不是自然物,当然也不应该像其他自然物那样被操纵与控制,而且,人类的根本目的就是摆脱被操纵与控制的命运,尽可能拥有在可能的行动路线间自由选择的机会。户晓辉教授把“自由”定义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他说,
“我们作为公众需要认识到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因为‘公众要启蒙自己,是更为可能的;只要允许公众自由,这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37页。
而且,按照户晓辉教授的意思,自由不仅意味着(主体)能够做他们选择去做的事情,而且意味着不受在他们控制之外的原因的决定去选择他们所选择的。
“所以,说到底,人的自由或不自由状况都是由人自己的选择造成的,由此带来的后果在主观上也是要由人自己负责的。只有那些经过人自己独立选择而做出的行为,才能给人归责。也就是说,只有自由的行为,才能让人负责。从外因来看,正常的社会不仅应该允许并鼓励每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实践,而且应该创造各种条件让每个人学会公开使用并且磨炼自己的理性能力,让人的理性为自己做主,这样才能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72页。
的确,康德说过,没有自由就没有义务,没有原因的独立性就没有责任从而没有应得,因而也就没有称赞与斥责的存在余地。这种说法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它的“令人信服性”只是停留在纯粹理性的层面,一旦当它越界并开始面对日常生活(户晓辉教授的新著就是一项直接面对他的家乡、亲人与他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实践民俗学研究),人们不禁会质问:即使赋予每个人以自由,就一定能够保证他们发展出理性的能力吗?即使具有理性的能力,就一定能确保人们都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吗?即使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就一定可以确保这种理性的选择就是人们想要的结果吗?
按照以赛亚·伯林的精典区分,“自由”这个词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消极的自由”,即“免于……”的自由,就是在虽然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界内不受干涉的自由;另一方面是“积极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就是主体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自我,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的自由。既然“他者”——自然界、他人或者社会、个体自身的内在情感与欲望——都是无法“杀死”的永恒的存在,那么,建立在个体理性基础之上所选择的“自由”,一方面只是主体对自我无法拥有的东西学会不去企求,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自我压抑”,或者甚至是鲁迅所谓“阿Q精神”;另一方面意味着主体主动地接受规则;而主体对一种规则的自我强加或者自愿接受,它就不能算是奴役,相反它是一种对“超我”的深度认同。正像卢梭所说的那样,“自由与权威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它们是一回事;它们是同一块奖章的两面”。*[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5页。在这后一种意义上,教育工作者强迫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就变得合理了。总之,如果自由就是理性的自我导向,那么,这种理性的生活,就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卢梭式的悖论!而且,如果理性的生活是可能的,这种生活如何才能达到呢?如果强迫经验自我符合于正确的模式并不是专制,而是自由,那么,“自由”,不仅不与权威相冲突,而且实际上与它相同一。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如何可能不相矛盾?总之,户晓辉教授有关“自由”的界定只是纯粹理性层面的,当它试图拿来分析日常生活经验时,他的“自由”理论就显得十分粗略。事实上,他所安置在“理性”之上的“自由”,即使在最抽象的层面,似乎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回答有关“自由与社会”的一般性问题。
此外,人们有理由怀疑,人类的所有有价值的信念(当然包括“自由”)并不会像户晓辉教授所断言的那样连贯一致。
“真实的情形却是:你必须灵活务实;你得告诉自己:唉,世上并没有什么永恒的、普适性的东西;大多数的人,在大多数的时候,大都会见机行事、因地制宜的。不过即使这般灵活务实,你也没有丢弃启蒙主义的基本理念。”*[英]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比如,人们会不会在研究中信服自由选择论,而在生活中把它丢在一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户晓辉教授自我批判的那样,
“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在有些场合,我发言了会难受,因为可能会得罪某些人;不发言也难受,因为觉得该说的话没有说,因为自己没有尽职尽责。总是,横竖都是不好受。”*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
如果简单地遵循理性地自由选择的逻辑,人们是不会产生矛盾的情绪的,然而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可见“理性地自由选择”并不能“包你满意地”解决所有人生的困惑。况且,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寻求的并非幸福、自由、公正,而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人天生就是奴隶,被解开锁链后不具备道德与智力资源来负起未来的责任,也无法在太多的可能性间进行选择;因此,在丢掉一副枷锁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另一副,或者自己锻造一副新枷锁”*[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73页。。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是像自由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依赖理性去解决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消除问题本身,使得困扰他们的问题本身变得不再是问题。由此可见,人类追求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尽管“自由”的确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最核心的目的条件之一,但却肯定不是唯一的目的与充要条件,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与仁慈,效率与自发性,真理知识与幸福忠诚等价值标准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类生活理想,它们在本质上可能是无法调和的。如果他们本来相互冲突,那么,人类就无可逃避地要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价值标准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僵硬地把“理性地自由的选择”贯彻到底。
事实上,如果结合哲学史的一般知识来检验户晓辉教授所倡导的“自由论”,其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与“自由论”相对的是“决定论”,它是一种有关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在决定论的框架中,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个体理性地选择的“自由”及其连带的“责任”的观念,最终可能只是一种“错觉”。相反,决定论把历史与社会中的个体比喻为“牵线木偶”,在不可避免的历史与社会过程中,个体不过是被分配了某种角色去扮演的演员而已,“天地是舞台,演不同的戏……剧本不在自己手里,随着剧情改变自己”。对于决定论者来说,那种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能够避免自然或超自然力量对其生命的完全决定的言论,简直是一种前科学的、不值得文明人注意的、幼稚的妄自尊大。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不是常常说,所有事情或至少是大多数事情,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种族、文明或社会结构的作用吗?不是时势造英雄吗?人间能有几个造时势的“英雄”呢?即使是那些造就了时势的英雄,又有谁能把他的“造就”行为简单地归结为他个人“理性的自由选择”?总之,在决定论者看来,所谓“人类能够自由地作出各种不同的选择”的观念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无知之上的结果。真实的情况是:不是个体而是更大的实体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历史后果的最终负责者都不是个体自身。总之,决定论者告诫人们永远不要忘记人的“有限性”这个事实。
三、实践民俗学家的“实践行为”批评
当然,户晓辉教授把自己的论证范围限定在理性的形而上学所要保证的层面,他要强调的是先验的、原则上可以发现的正确而具有结论性的方案,这本身是合理的,也是重要的。他说,
“从学理上说,规范的起源与规范的效用必须分开,正如人权产生自西方文化圈这一事实并不能导致对人权的法律伦理效应加以肯定或否定一样。规范的有效性问题与其起源无关。同样,即便人类达成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之类的规范公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我们不能以古人和不同民族在历史上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公识这一经验事实来否定这些公识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因为过去也好,现在也好,仍然有不少人并没有在这些规范问题上采用逻辑思维,这是经验事实。但是,一旦他们采用了逻辑思维,一旦他们站在实践理论的立场独立思考、选择和判断,他们就能够不约而同地达成这种共识,并且会形成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理性公识。”*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73页。
的确,今天没有人会反对户晓辉教授所强调的那些“共识”(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理性公识),但是,所谓“公识”意味着它是隐藏在一切文化与社会现实底下的“基石”,没有人反对“基石”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要性,但是,它的价值又不能超越它作为“基础”的边界,不能替代建立在它上面的“上层建筑”的地位与价值。以赛亚·柏林说,
“对共享价值的接受,至少对其不能再少的最小部分的接受,进入我们对于正常人的理解之中。共享的价值能将关于人类道德基础的概念与诸如习俗、传统、法律、风俗、风尚、礼仪的概念区分开来。有了这些价值,所有这些广泛的社会历史、民族、地方差异与变化,便不再被视为奇怪或反常的、极端自我中心的、不健全或根本不可取的;更不会被认为在哲学上是有问题的。”*[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户晓辉教授的“实践民俗学”(在这一问题上,吕微教授同样难辞其咎)恰恰是将“人类道德基础的概念”与“习俗、传统、法律、风俗、风尚、礼仪的概念”混为一谈了,他们混淆了“理性实践”与“民俗”以及哲学与民俗学的边界,试图把丰富多彩的民众日常生活还原成干巴巴的几条抽象的实践理性原则,然而,
“既然历史学并不是一门演绎的科学(甚至是社会学,当它失去与其经验基础的关联时,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这些假设作为未被应用的纯粹抽象模型,对于人类生活的研究来说也没有什么用途。因此,虽然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古老争论仍然是神学家与哲学家的真正问题,但没有必要打扰那些关注经验问题,亦即正常时空经验中的人类的现实生活的人的思想。”*[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修订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24页。
与历史学、社会学相类似,民俗学同样不是一门演绎的科学,而是一门经验学科。然而,户晓辉教授却竭力反对这一历史事实,并一再强调现代民俗学研究在其发端时就具有先验的实践理性起点,认为“它本来应该是一门实践科学”*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90页。。可是,无论户晓辉教授多么坚定地相信民俗学“当初”曾有多么自觉地以“民”为本,但是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经验民俗学”占据了国际民俗学的主流。尽管“占主流”或者“从来如此”的确并不一定正确(正如户晓辉教授所批评的那样),但是,比较起来,“从来极少如此”的做法之正确率可能会更低。
非常明显,“实践民俗学”从马丁·布伯有关“我与你”*[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以及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有关“他者性”*[法]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朱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的伦理学思想中获得了巨大的思想灵感,这使他们从根本上排除了通过经验研究来讨论“人的自由”问题的可能性。户晓辉教授给“经验民俗学”贴上一系列本质主义的标签,但是,他同时也承认,“至少半个世纪以来,民俗学的方法论变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悄然出现。简言之,这些变革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物到人;从描述到批判;从客观到主观;从异地到家乡;从家乡民俗学转向日常生活研究。*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56-361页。表面上看起来,上述变革是朝着“实践民俗学”的立场相向而行,但是,按照户晓辉教授的逻辑,一旦它们仍然是以“民”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他者”而不是“你”来看待,那它本质上仍然与“实践民俗学”大异其趣。他说,
“只要我们继续坚持经验实证范式,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就会任你东风唤不回!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验实证范式在把被调查者当作单纯手段(信息提供者)的同时实际上也把自己变成了单纯的手段。……如果继续以经验实证为主导范式,伦理问题、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的问题就仍将继续被我们搁置和遮蔽。……一门本想研究民众日常生活的学问竟然变成一种无动于衷的冷血知识。”*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54页。
如果户晓辉教授所命名的“实证的经验民俗学”只是作为“实践民俗学”的理想模式之对立面(同样也只是一种理想模式),那么,他的做法还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他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民俗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的描述,那么,这就是一种极不公正的、污名化的行为了。首先,户晓辉教授常常把“经验的”与“实证的”两个术语捏合在一起使用,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经验研究并不一定是实证研究。这一点首先应该予以区分,否则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无的放矢。其次,经验研究并不一定会搁置“自由、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的问题,恰恰相反,转向“民”的“经验民俗学”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他者”作为人的权利问题,民俗学家们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民俗学学术伦理的问题,制订了并一再修订着学科的伦理指南。*Bemte Gullveig Alver, Tove Ingeborg Fjell and Orgar Oyen (eds.), Research Ethics in Studies of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Helsinki: Acacemia Scientiarum Fennica.2007.最后,正是基于对近几十年以来“经验民俗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简单化处理,同时怀抱着对自由与民主的狂热信仰,实践民俗学家武断地否定了“经验民俗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历史贡献,另起炉灶另开张。他们坚持认为,“要防止对知性和理性的误用,民俗学就离不开先验逻辑”*户晓辉:《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第7页;。然而,“离不开”先验逻辑不等于“就是”先验逻辑。似乎从来没有哪位民俗学家说过民俗学可以离开先验逻辑,当然似乎也从来没有哪位民俗学家像实践民俗学家一样把民俗学当作先验逻辑哲学来研究。
四、异于“实践民俗学”的民俗学“实践”
在总结与评估国际民俗学的历史与现实时,“实践民俗学”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失误:一方面是固执地认为民俗学“当初”就具有要实现“人的自由”的初衷,这是错把今人的思想安置在古人身上的一种心理投射;因为在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法律概念中,几乎不存在个人权利的概念;“自由”的概念尽管有其宗教根源,但其获得发展绝不会早于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德国民俗学之父格林兄弟的学术实践仅仅是一种浪漫的民族主义行为,其中暗含着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思想,却远没能达到今天户晓辉教授所谓“个体自由”思想的明晰程度;至于英国、芬兰、美国等国家的早期民俗学,根本与户晓辉教授的“自由”思想距离遥远。自由得以广泛传播以至于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生活状态,在人类的历史中还是一种颇为新鲜的事物,而其产生是与现代化及资本主义的出现密不可分的。只有当自由已经具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况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特殊寓意时,它才能够声称具有了普遍性。另一方面,实践民俗学家草率地认为民俗学“当前”的工作与人的自由、权利、尊严、伦理问题不相干。这又是错把自身片面的逻辑推理替代国际同行之实际成绩的一种做法。比如,户晓辉教授说,
“20世纪90年代初,格特鲁德·贝内迪克甚至提出‘告别民俗学’的说法,并且认为换一个名称,民俗学就有三种可能性:它是实践,是实践的理论,是理论的实践。只是这种经验‘实践’与本书的理性‘实践’可能大异其趣,其反启蒙立场与本书的理性启蒙立场也根本对立。”*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58页。
在这里,户晓辉教授区分了贝内迪的“经验实践”与他个人的“理性实践”,称贝内迪的研究持一种“反启蒙的立场”,而他自己则是持一种“理性启蒙的立场”。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彻底“非理性的”“独断论”。
有理由相信,贝内迪提出的所谓“实践”的观念从属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论”转向。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忆一下这一学术思想史的转向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这一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深刻影响今天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走向的三项关键性成果: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1978),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1979),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隐喻与神话现实:桑威奇群岛的早期历史结构》(1981)。它们共享的关键词正是“实践”。三位作者以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使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与“结构”“体系”相对应。众所周知,“结构”“体系”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词汇。尽管这些理论流派的主张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它们都属于某种强调“制约性机制”的理论,它们都认为人类行为是在外部社会、文化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下塑造、形成、排序和确立的,这些社会、文化力量包括文化形态、心理结构、资本主义等等。以布迪厄、吉登斯、萨林斯为代表的理论家们讨论了社会和文化中的“结构”与个体行动者的“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对立关系)。不难看出,他们同时注意到了前述“决定论”与“自由论”的理论思想并给予了必要的辩证统一。经过“实践论”转向之后,“历史创造了人类,人类也创造了历史”这句看起来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陈词滥调,似乎不再相互对立,反而闪烁着“揭示了现实社会生活最深刻的事实”的哲理的光芒。*Sherry B.Ortner,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Culture,Power,and the Acting Subject,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pp.1-18.
换句话说,“实践论”为困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的诸多问题提供了真正的解决方法,它使“行动者”回归到社会结构与进程之中,既不轻视他对制约其社会活动的广大社会结构的认识能力与创造能力,也不否认这些“结构与体系”制约他们并为他们的社会活动得以进行提供前提的条件性限制(其中一些思想可以追溯到功能主义,另一些则产生自20世纪60年代的新理论流派)。总之,“实践理论”将个体能动性、文化进程(话语、表达还有格尔兹所谓“象征体系”)与人类社会关系体系综合在了一起。
上述“实践论”带有深厚的实用主义的哲学色彩,它综合了理性主义的自由意志理论与经验主义引证事实,强调事实,面对事实的踏实作风;与此同时,它完全摒弃了职业哲学家们许多由来已久的空疏的习惯,避开了字面上的解决方式与坏的先验理由,它依靠事实、行动和力量。这意味着经验主义的气质占优势地位,而理性主义的气质却被直率地抛弃了;它丢掉了独断、矫揉造作和狂妄的终极真理,却赢得了开放的气氛和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实用主义的“实践论”强调,
“我们带着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自己已经造成的种种信念投入到新的经验领域;这些信念决定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关注什么决定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又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样由此及彼,陈陈相因,虽然有一个可感的实在之流这个顽强的事实仍然存在,但适合于它、使它为真的,从头至尾,主要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美]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3-144页。
在实用主义的“实践”中,个体将旧的意见与新的事实相融合形成新的真理,这一新的真理是新的经验与旧的真理相结合、互相修改的结果。换句话说,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实践”是历史语境中具体个体的行为过程。在这一行为过程中,主体获得有关“真理”的信念,它在事件与过程中获得证明,它的有效性就是使之生效的活动过程。个体随着其生命历程的展开而积累“真理”;当然,个体的经验是在变化中的,相应地,个体对真理在心理上的确认也在变化中。但是,真理的观念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之所以有责任追求它的唯一理由与动力。显然,实用主义的“实践论”反对理性主义所谓“无条件的有效性”“至上的责任”的真理观;在实用主义者看来,这种真理观尽管绝对正确,却也绝对地无意义。
当然,只要户晓辉教授面向经验的日常生活,他同样会发现“结构”与“实践”的矛盾性存在,比如,至少他强调了“模式化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一种超越个体而存在的文化的与社会的“限制性因素”,他说,
“世代延续甚至不断重复的苦难,甚至成为最坚固、最持久却一直被我们最不愿意看见因而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模式化的日常生活方式!……事实上,这种最不该忽视的生活模式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声称要研究模式化生活的民俗学却根本遗忘了我们最大的模式化生活,这岂非咄咄怪事?”*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31-332页。
遗憾的是户晓辉教授倾力要关注的并不是这种“最大的模式化生活”,而是“诗意地栖居的世界”;也许甚至不是“诗意地栖居的世界”(主体以劳作或创造的方式的栖居,他们的操劳、做事或者庸常的生活),而是他们行为事实背后的“实践理性”。他的“实践民俗学”,从一开始就自我限定在纯粹理性的范围内,他说,
“实践民俗学意义上的实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行为,更非泛泛而谈的行动,而是特指实践理性规范意义上的实践。它既非人的生物和生理活动,也不是人在自然界的生产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80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他所界定的“实践”乃是自由个体“理性选择”的目的条件。他坚持要发展公民的批判或者寻求答案的能力,揭示真理的洞见与直觉的能力,却忽视了经验层面上这种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许多经验证据表明,自由选择的疆域远比许多人假定的要狭窄得多,现在也许还有人错误地相信这个疆域很大。然而,在因果性地决定的系统中,通常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与道德责任观念便不复存在了,至少是没有用了,因此,“实践”的观念也将不得不予以重新考虑。既然民俗学是一门经验研究的学科,那么,在面对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时,人们不难发现,人类可选择的范围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还要狭窄。在个人自由选择与他的自然和社会必然性间划定明确界限的企图,恰恰暴露了那些试图解决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的惊人的失误,以及在事实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们真的有权利对我们的同胞说三道四吗?避免不宽容的判断和自作公正,只是去描述、呈现事实、分析,然后抽身让“事实说话”会不会更可取?
户晓辉教授主要是通过“污名化”“经验民俗学”,并给以“实践”的概念以纯粹哲学式的界定来倡导他的“实践民俗学”的激进主张的,但是,他也无法不承认:
“民俗学的主流一直在谈文化、身份的特殊性与个别性,这固然是学科的本行,但我想在基础问题层面上提醒大家别忘了普遍性和一般性。这两方面谁也离不开谁。民俗学长期以来正确地强调了文化多样性和特殊主义,却有点忘却了普遍价值,应该把这个环节补上,才算完整齐活。经验实证范式下的民俗学与中国社会共同的症结所在,恰恰都是缺乏普遍的理性目的论条件。”*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92页。
在其他地方,他又说,
“民俗学当初立志研究的完整的人及其日常生活,首先是如其已然和实然,然后是如其应然和可然。已然和实然主要是经验事实,应然和可然则是目的条件,这两方面缺一不可。”*户晓辉:《日常生活的苦难与希望——实践民俗学田野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99页。
比较之前他有关“实践民俗学”的论述,上述两种表述要辩证与宽容的多,尽管它们仍然拖着他的“先验哲学”的长长的尾巴。
五、结 语
实践民俗学家说人们先天地具有选择的自由却罔顾人们实际上无所不受限制。他们假设个体通常是其行动的源泉,行动是由行动者的目的和意图决定的,行动者的动机是解释其行动的最终原因。每个个体的自由意志以及独一无二的特性都被视为一种“纯粹的事实”,一种源于本性的产物,而不是特定社会安排的结果。
然而,与社会学一样,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门“不自由的学科”发展起来的。泽格蒙特·鲍曼说,
“让我们回想一下,社会学最初是作为对某种特殊类型社会的反思而出现的,该种社会直到现代才在西方确立起来,并且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生。所以,有人提出一种猜想,即人类作为自由个体的联合是与该种社会所独具的特征密切相关的。如果这种猜想属实,那么,自由个体恰恰就像它所归属的社会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创造物。由于个体自由是随特定类型的社会而产生的(而且也可能随之消失),所以,我们绝不能够、也不应当将其视为当然之物。”*[英]泽格蒙特·鲍曼:《自由》,杨光、蒋焕新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同样,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同样可以表明,我们的实践民俗学家们所谓“天生的”(natural)自由个体不仅是相当稀少的物种,而且不过是存在于一定区域内的现象。自由个体,远远不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状态,而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创造物。
实践民俗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混淆了哲学与民俗学的学术任务,提出了类似于“关公战秦琼”的命题,而且,既然“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必然性优于偶然性”*户晓辉:《民俗学为什么需要先验逻辑》,《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第7-11页;,那么,“秦琼”必然能够战败“关公”,信奉先验逻辑的“实践民俗学”必然优胜于仅仅关注具体的经验现象的“经验民俗学”。殊不知,正是他们所信奉的“唯一正确的”康德早就区分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边界。康德正确地发现,哲学的任务不是为关于事实的经验的问题寻找答案,这种问题只能由具体科学予以解答。因为他知道,
“知识必然具有两种类型:或者它声称是‘必然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它以形式的标准为基础,但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消息;或者它声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超越或然性,也并非永远正确;如果我们的意思是只有通过逻辑或者数学才能得到那种必然性的话,那么这种知识就不能具有必然性。”*[英]以赛亚·伯林:《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孙尚扬、杨深译,韩水法校,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对于民俗学的鼻祖赫尔德(户晓辉教授当然会同意他的重要地位)来说,
“人类学才是理解人类及其世界的关键,而不是形而上学或逻辑,不管它们来自亚里士多德,还是莱布尼茨,还是康德。”*[英]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
此外,实践民俗学家们系于“个体自由”之上的希望也是片面的。不需多说,个体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喜忧参半的恩赐。人类的“实践”正是在自由与限制之间的能动性的选择与创造,他们不会像故事里布里丹的驴子那样无法在两堆距离相等的草料中选择而饿死,而是有差别地在文化与社会提供的资源的基础上依据语境展开实践。从经验的层面来看,他们的实践行为是生成性的、开放式的,民俗学家们没有权利把民众远远地赶入我们为他们圈定的围栏中或者四海皆同的唯一解决方案中。尽管我们“大可认为自己发现了关于道德、历史、绘画和人际关系的真理,但要说偌大世界上任何不接受这些结论的人都是白痴或无赖,这就很荒唐了。”*[英]以赛亚·伯林:《个人印象》,林振义、王洁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