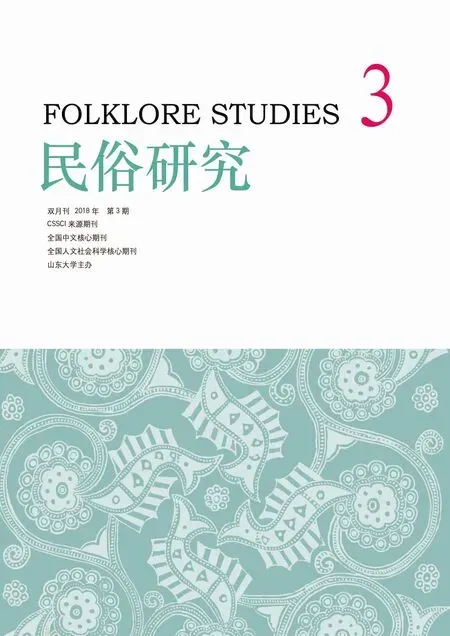儒家政教与汉代风俗理论的演变
曲宁宁 陈晨捷
“风俗”一词先秦已有所见,《管子·法法》《庄子·则阳》《诗·大序》《礼记·乐记》《荀子·王制》等篇章中均有其迹。其中,儒家对于风俗及其引导最为关注并且形成了一套相应的教化体系。《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云“天子省风以作乐”,杜注:“省风俗,作乐以移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424页。其根据为儒家之“乐教”“诗教”理论。*“乐”与“诗”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孔颖达《诗·周南·关雎》“训诂传”中正义“美教化,移风俗”云:“此序言诗能易俗,《孝经》言乐能移风俗者,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也。然则诗、乐相将,无诗则无乐。”(《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汉书·艺文志》亦言《诗》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在儒家看来,“诗”“乐”本生于“风”,“诗”“乐”是“风”之直观呈现,观“诗”“乐”可以知“风”,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言:“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反过来,“诗”“乐”又是移风易俗之不二法门,如《礼记·中庸》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也。然大致而言,先秦儒家之移风易俗理论较为单一,在方式上多侧重于“乐”,易流于空疏。入汉以后,风俗理论逐渐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与可操作的行政技术层面,从而逐步走向成熟。但需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风俗概念及其理论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对此本文将逐一予以展现,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汉初诸家争锋
移风易俗并非儒家特有的专利,事实上,法家、黄老道家也认为应该通过某种手段来引导进而形成一定的社会风俗、习惯。法家也倡导“变易风俗”*黎翔凤:《管子校注》卷六《法法》,中华书局,2004年,第296页。,《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蔡泽曰:“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秦始皇三十年于会稽刻石并发布部分条令以“宣省习俗”,如为“防隔内外,禁止淫泆”,规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61-262页。等。然而秦政之要却在于奖励耕战以图富强,这一政策虽然行之有效,其弊端也相当突出。因而汉初士人的一个重要学术使命就是总结并反思秦片面奉行法家主张之教训,为汉代的长治久安提供理想的治国之术。
西汉建国不久,陆贾即首倡教化之议。在《新语·无为》一文中,他认为秦政之弊在于刑法过于严苛,结果却事与愿违,因而治国当行儒家之教,“尚宽舒”“行中和”,如此才能令百姓从德向道。为此他一再强调“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儒家政治理论之关键,首先在于王者能否正本清流、以身作则,移风易俗亦当如是:“孔子曰:‘移风易俗。’岂家令人视之哉?亦取之于身而已矣。”其次则是要以“乐”移“风”,陆贾建议“调之以管弦丝竹之音,设钟鼓歌舞之乐,以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本行》、卷上《无为》、卷上《道基》,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67、18页。。
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但纲度法纪多仍秦旧,社会风气与秦时相差无几,如逐利不止、侈靡相耀、僭越无度、背本食末等,贾谊认为此乃亡秦余毒:“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4页。对此不能视之为“是时适然”,放任无为。在贾谊看来,秦俗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然而当前“进取之时去矣,并兼之势过矣”*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时变》,中华书局,2000年,第97页。,因而应与时更化,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定制数,劝民归本。与陆贾一脉相承的是,贾谊同样遵循儒家之道,主张治国之根本在于君主的选择及其德性修养,“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九《大政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341页。。同时,要重视吏治、检选贤能,重用儒家士人而非法家术士,如是方能风俗淳美,“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俗激》,中华书局,2000年,第92页。。宰职作为群吏之首,尤应“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五《辅佐》,中华书局,2000年,第204-205页。。此外又有贾山踵继其议,认为只有重视风俗教化才可能奠定万世之基业,云:“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336页。
黄老道家虽然也认同风俗移易的意义,但在方式与目标上却与儒家不同。《淮南子》认为民不仅可化而且易化,云:“人之性无邪,久湛于俗则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在他们看来,儒家所坚守的礼义不过是五帝三王时代的风俗而已,并非不可移易,它只适用于当时而非万世不易之法则。儒家据于末法而不知本统,固守礼乐以抱残守缺,显然是不知道德之真知与本意,因而为治应超越礼义,直指礼义之所以为礼义者,“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以礼义治天下无疑乃“离道德之本”,“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圣人所据以“制礼乐”者不过道德或人情而已,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导致“风俗浊于世,而诽誉萌于朝”,是故圣人废而不用。圣人治国必原人情、因人性,在此基础上变易习俗,此为“养化”或者“神化”:“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治国,太上养化,其次正法……风俗犹此也”。*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卷十三《氾论训》、卷十一《齐俗训》、卷二十《泰族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775、921、796、786、1378页。
董仲舒认为秦“以贪狼为俗”,至汉而流毒不已,“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故而当前务在“更化”。所谓“更化”,即反秦政而“承天意”以行儒家之王道,“任德教而不任刑”,细绎之,则当“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510、2504、2503-2504页。。武帝采纳董仲舒之建策,通过罢所举贤良中治申韩者、举孝廉、置博士弟子员、遣使巡行天下等一系列举措以“化元元,移风易俗”。
然而随着武帝经略四方、穷兵黩武,西汉中后期财政匮乏,百姓疲于兵役与力役,张汤、杜周等酷吏和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贾人”得到重用,国家政策实际上转向“霸王道杂之”,而儒家教化理论及其教化成效则备受质疑。《盐铁论》中,文学贤良认为百姓的善恶取决于风俗,“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治国之关键在于以礼义导民,即应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为遏制当前的“贪鄙之俗”,则当重农抑商、节用尚本。“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而国家的一系列举措,如盐铁官营、买爵赎罪等,无疑是驱民逐利:“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大夫则认为盐铁官营正是为“建本抑末”,而儒家德治却于国无益,孔子“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孟子接驷连骑亦无补于齐,可见“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以当世而论,丞相公孙弘治《春秋》,“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贤良文学更是泥古而不通世务。进而言之,逐利之风不无可取之处,法家之术亦有其所长,“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引文具体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十《大论》、卷一《本议》、卷二《论儒》、卷二《刺复》、卷二《非鞅》,中华书局,1986年,第604、1-3、149、131、94页。
可见,汉初对于如何移风易俗、树立何种风俗可谓众说纷纭,而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确立更是几经波折,事实上一直要到元、成之时,儒家学说才真正得到贯彻,大量儒生受到重用,如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刘向、王褒、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等,既有重臣树标于朝,又有地方官吏宣化于野,儒家之礼制及其主张才有所确立并得到推广,儒家之风俗理论才真正得以施行。
二、风俗理论的政治诉求与功用
汉初的风俗理论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迹,换言之,每一风俗理论都有其背后相应的政治诉求。汉初饱受战争荼毒,民生凋敝,经过六十余年休养生息方由“将相或乘牛车”发展至“海内殷富”,但其间问题也很突出。一些开国功臣心有怏怏不甘屈为人臣,因而汉初的一些异姓王,如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淮阴侯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相国陈豨等相继谋反,而同姓王则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如刘邦死后,吕后与审食其谋划尽诛诸将,郦将军则劝审食其曰:“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史记·高祖本纪》)其后贾谊在《新书》“藩伤”“藩强”“大都”“权重”等篇中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袁盎、晁错等也一再上谏要求抑制地方势力。而作为地方藩王、被告谋反的淮南王刘安却一再倡导道家“无为”之治,其用意昭然若揭。实际上,他希望通过对不同地方风俗各有所宜来论证治国当因循旧制而不宜变常,举例道:“九疑之南”,民人“被发文身”“短绻不绔”“短袂攘卷”,而“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均为顺应当地自然特性而形成的风俗,“是故圣人一度循轨,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故准循绳,曲因其当”。*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38、61页。徐复观先生指出:“强调各地礼俗不同,但皆有同等的价值,不必劳心用力去加以统一,藉以表达他们地方分权的愿望……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是由朝廷所制定的,以达到彻底统一与集权的礼义。”*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所谓“无为”“循天”“随人”,即要求因循此前旧制,毋妄作,以此抵制大一统的政治趋势,对此贾谊批评道:“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汉)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3页。
《盐铁论》中御史、大夫的言论反映的则是统一、专制皇权的意志,其目的在于齐民,其基本政策为崇本绝末、强干弱枝,以此遏止豪强等势力对中央皇权的可能威胁。御史为其铸币、盐铁、榷酤政策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绝并兼之路,令百姓均平,言:“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三《轻重》,中华书局,1986年,第179页。司马迁曾深入分析人的逐利天性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4页。一些成功的商贾则“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6页。武帝时期的诸般政策虽然主要是为解决用度问题,但其附带的一个功能便是“齐民”,以确保君主的无上地位,“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一《错币》,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然而过于推崇君主权威使得朝臣一味阿谀奉承而不能谏诤。大夫以其所理解的“忠孝”之道来事君,所谓“忠孝”即“尽忠顺职”,以保全君主的名声与功德为己任。大夫曰:“君有非,则臣覆盖之……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有司倚于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于文学之谋也”,并讽刺儒生“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未见其为宗庙器,睹其为世戮也”。文学则批评其行为“不忠不信,巧言以乱政,导谀以求合”,“处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邑顺风”,最终恐难逃脱“宜受上戮”的下场。而这一风气的形成大概是从武帝中后期开始的,贤良指出:“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二《忧边》、卷五《讼贤》、卷六《救匮》,中华书局,1986年,第162、284、310、301、401页。
在儒家看来,礼乐是引导、形成公序良俗的不二圭臬:乐因其发诸人之真情而“感人深”“移风易俗[易]”*[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四《乐论》,中华书局,1988年,第381页。;礼则以规范内外亲疏等差、社会上下等级秩序及其相应之言行。但实际上,对儒家而言,风俗理论还承载着一项重要的政治功能——谏议。《诗·周南·关雎》“诂训传”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义风动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汉]毛亨:《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可见儒家强调风俗的一个重要用意就是以此来批判现实、讽谏君主。根据儒家的教化理论,教化的根本在于国君,“风”“草”之喻是也,又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程树德:《论语集解》卷二十六《子路》,中华书局,1990年,第901页。汉初陆贾倡言“正风俗”时就秉持此义,曰:“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者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无为》,中华书局,1986年,第67页。贾谊认为国君应对民之善不善负完全责任,“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九《大政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341页。。董仲舒亦曰:“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1页。与此相应的是,朝廷之上士人应形成坚持是非、犯言直谏的风气。《盐铁论》中,贤良指出:人主“谷之教令,张而不施”,导致“帝王之道,多堕坏而不修”,对此臣子当“触死亡以干主之过”“犯严颜以匡公卿之失”,如此方为“忠臣”“直士”,然而执政的御史、大夫们却“顺流以容身,从风以说上”,“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国君有过,臣下等极力谏诤以格其非,若臣子一味迎合君主,则足以乱化伤俗,“公族不正则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则奸邪兴起”*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相刺》《刺议》《讼贤》,中华书局,1986年,第256、319、285页。。
东汉王充努力辨明俗之忌讳、不祥,订正妖祥鬼神、卜筮祸祟等,归根结底在于其劝人为善、令民立化的现实政治关怀。王充认为俗之忌讳,如讳西益宅、妇人乳子、作斗酱恶闻雷、厉刀井上之类,无非是“教人重慎,勉人为善”罢了,其立论之本旨在于扞格流俗之失:“充既疾俗情……充书违诡于俗……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论衡》一书便是王充模仿古代之“诗”而作的,希冀统治者采纳其观点而使风俗淳美,“《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黄晖:《论衡校释》卷三十《自纪》,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4、1185页。。
东汉后期,王符对社会上道德沦丧、衣食奢侈过制、学巫事神、厚葬破业、游手好闲等陋习深恶痛绝,然而在他看来,国君及其统治集团对此应负最大的责任,“凡诸所讥,皆非民性,而竞务者,乱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统世,观民设教,乃能变风易俗,以致太平”。王符认为“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正己而后能化人,国君为世之表仪,若能躬身敦行仁义,则“羲、农之俗”也有可能“复见于兹”。*(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三《浮侈》、卷八《德化》,中华书局,1985年,第140、380页。汉末政治腐败、民生残弊,社会风气的败坏已然威胁到社稷安危,“世奢服僭”、百姓离本归末、厚葬伤生、官吏仗势巧取豪夺、严刑峻法等,可谓“外溺奢风,内忧穷竭”,“是以风移于诈,俗易于欺”,因而国君当塞绝末、防萌奸。一旦年谷丰稔,便当整治风俗,因为在他看来,“夫风俗,国之诊脉也”,而政之所以败、国之所以亡者,多在于国君不重视风俗。类似的观念在汉末相当盛行,如《后汉书·郎顗列传》云:“风者号令也,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蔡邕列传》亦云:“风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应劭希望通过“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来“匡正时俗”,故作《风俗通义》,实际上是要藉此讽谏国君,所谓“谏有五,风为上”*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卷四《过誉》,中华书局,1981年,第173页。。
三、汉代风俗理论的转变与演进
在汉代移风易俗理论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风俗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在逐渐丰富的同时也在不断调适、转变。
首先,先秦时人认为“乐”或者“诗”是移风易俗最有效与最根本的方式,同时以“风俗”为本,以礼制为末,“风”与“俗”意近;而汉人则认为“风”与“俗”异,“风”本“俗”末,在教化方式上强调以“乐”移“风”、以礼正俗,甚至多论礼而少谈乐。《孝经·广要道》引孔子之言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其中“风”“俗”并列,意义大体相同,与以礼规制的社会秩序、政治格局有所区别。《礼记·乐记》认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正是因为音乐触及最深层的人心、人情,故而“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礼与乐有别,所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因而移风易俗当以乐为本,而礼制为末;治国之道则以“风”为首,以“教”居次。而汉代士人却凸显了“风”与“俗”之间的差异,如班固与应劭均对其重新进行定义,并认为风、俗二者之间当以“风”为本,“俗”为末。班固引用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语并解释道:“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0页。其所谓“本”指的是“风”,“末”则指“俗”,如孔颖达在《诗·周南·关雎》“训诂传”的正义中引用其说并进一步明确指出的那样:“风为本,俗为末,皆谓民情好恶也。”*[汉]毛亨:《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只是如此一来,教化方式也需有所更张,即以乐移风,以礼正俗。
汉人亦多提及以乐移风者,如陆贾、《盐铁论》中的“文学”、董仲舒、班固以及《淮南子》的作者等,然而却多如雪泥鸿爪,其关注的重心绝大多数在“俗”而不在“风”,强调以礼正俗。贾谊在列举汉初诸多“邪俗”之后,认为原因在于“上无制度”,因而他建议张礼义、“定制数”:“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瑰玮》,中华书局,2000年,第104页。《盐铁论》中文学多据古礼以诘责大夫所为、世人所行,主张以礼治国而非以法“乱化伤俗”,“礼所以防淫,乐所以移风,礼兴乐正则刑罚中……故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五《论诽》,中华书局,1986年,第299页。。董仲舒认为若欲为治,“非反之制度不可”,“圣人之道”便是制度、礼节,当世之所以难治便因无度制,“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是世之所以难治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八《度制》,中华书局,1992年,第223页。。礼乐制度是治国的不二法门,“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本”即孝悌、衣食、礼乐,“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六《立元神》,中华书局,1992年,第165页。
其次,先秦儒家对“俗”有所肯定且态度较为包容,而汉人对“俗”则多有否定,视“俗”为“礼”的对立面。孔子云“移风易俗”,《礼记·王制》虽然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的说法*“易俗”或“不易俗”看似对立,其实指向相同。孔颖达以华夷之别来解释“易”或“不易”:“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彼谓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语不通,器械异制,王者就而抚之,不复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其俗’,与此异也。”([汉]毛亨:《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1页)然而“五方”本即包括“中国”在内,“中国”亦有其俗,也需在肯定“俗”的基础上以德同俗。显然“易俗”或“不易俗”的差别不在于夷夏,而在于风俗之善恶。,但却在指出五方之俗差异性之后,主张因地制宜,尔后“兴学”“一道德以同俗”。移风易俗,就是使风俗由恶向善转变,“易俗”或“不易俗”的实质差异便在于对原生性风俗为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到底什么风俗是恶的、什么是善的?王充意识到世俗对“贤洁”“邪污”的判断未必合乎事实,故而对世俗“四讳”、厚葬、妖祥等风俗的辨正、“违诡于俗”的根本目的是要“正时俗嫌疑”,从而“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东汉末年荀悦认为“致政之术”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其中“四患”首为“伪”,因为“伪乱俗”,而“五政”之一则为“审好恶以正其俗”。若欲“正俗”,关键在于“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即厘定何为“好”(善)、何为“丑”(恶),“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悦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059-2060页。。应劭也认为为政最重要的是“辨风正俗”,“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可见“本俗”是与“政教”相悖的,其作《风俗通义》的目的在于“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序”,中华书局,1981年,第4页。。总体上看,汉人对“俗”是持否定态度的,常以“礼”与“俗”相对。董仲舒认为圣人之礼制就是用来规范、引导风俗的,若放弃度制,则民“各从所欲”“俗得自恣”。《盐铁论》中的贤良认为,“三代之盛无乱萌,教也;夏、商之季世无顺民,俗也”*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六《授时》,中华书局,1986年,第422页。,君子之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易其俗”,即以礼变俗而非从俗,“安能变己而从俗化?”*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二《论儒》,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151页。王充更是将从俗之士视为“乡原”:“(士)岂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谤哉?偶俗全身,则乡原也。”*黄晖:《论衡校释》卷一《累害》,中华书局,1990年,第13页。
再次,汉人对“俗”的否定进一步导致对原生性、自然性风俗的先天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质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尽管只从经济层面分析当时的社会风俗,但他对风俗的成因却颇多关注。大体而言,导致风俗呈现各种差异性的原因不外有三: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与当代政教。其中,后两者为“变量”,较为特殊,如关中为周人故土,是以“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中山为纣“淫地余民”,故而“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邹鲁有周公遗泽,“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后受富商邴氏刺激“去文学而趋利”,甚至“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等。地理环境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可谓“定量”,在极大程度上决定当地百姓言行、生计以及价值取向。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谈论风俗成因时,尽管也无法避谈自然环境,但他却把重心放在历史沿革以及当代政教对于风俗的影响上。较之《史记》,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点也体现在班固对于“风俗”概念的定义上。班固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0页。其中包含三层涵义:一、民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只是各有所偏;二、“风”指其自然性、先天性,民受水土风气影响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之不同,此为其自然表现,即不言善,也无涉于恶,可见班固还是认可其合理性的;三、“俗”指其社会性、后天性,民之好恶、动静完全取决于君主的引领与带头作用,完整的“风俗”概念应包含这三者内容,班固对风俗成因的分析基本上与之相符。
但到了《风俗通义》,“风俗”概念又有一重大转变。应劭曰:“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在应劭看来,“风”即自然环境并不是先天合理的,隐含着美恶,需要进行价值判断,而“俗”则是“风”的直观呈现(“像之而生”),同样存在“或直或邪,或善或淫”的问题。“风俗”概念当中并不包括后天教化的因素在内,因而其先天合理性是可疑的,甚至是值得批判的。
最后,汉代风俗理论的演进背后更为深层的逻辑则是对地方地望的否定与对“中国”的崇拜,因为承认风俗的地域性、先天自然性不仅阻碍了教化政策的推行,而且也有悖于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政治需求。两汉社会对风俗的定义与价值判断每况愈下,这种概念转变是汉代儒家移风易俗的教化政策得到充分执行的理论需要与逻辑结果。董仲舒认为治国之道当上体天道以正其元,“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措,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若仅就地望而言,中国为“化四方之本”:“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七《三代改制质文》,中华书局,1992年,第192页。。中国正,则四方正;中国阴阳和合,若欲国治民安当以其中和之气整齐四方。四方是不可与中央同日而语的,《淮南子·地形训》认为“土地以其类生……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中土多圣人”,《盐铁论》中文学也认为“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在他们看来,环境越恶劣,越不为天地所钟爱,其风气也越差,如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三《轻重》、卷七《备胡》,中华书局,1986年,第179、444页。。班固认为水土之风气有刚柔缓急等差异,虽然未曾明言中央的风气如何,但作为王者所居,自然不可能有所偏颇,而移风易俗需“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0页。,言下之意,四方亦需以中央为鹄的,如此方能使风俗淳美。颜师古注“天子省风以作乐”引应劭曰:“风,土地风俗也,省中和之风以作乐,然后可移恶风恶俗也”*(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448页。。《白虎通·王者不臣》论“三不臣”,其中之一为“夷狄”,因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后汉书·鲁恭传》也对四夷风气充满歧视,云:“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认为只要中央王朝修仁行义,则“阴阳和于上,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而至矣”。
四、余 论
在汉人看来,终两汉之世,社会上的恶风恶俗甚嚣尘上,如普通百姓逐利不已、奢靡无度、“生不养,死厚葬”,官吏侵渔盘剥、仗势求利,富人兼并土地、挥霍无节以及东汉末年兴起的谶纬之风等,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因而他们对移风易俗的主张异常重视,并由此带动了风俗概念及其理论的转化。然而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自元狩元年汉武帝遣使巡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考核官吏政绩开始,两汉帝王多次派遣使者“行风俗”“览观风俗”“览风俗”“观览风俗”“班宣风化”“循行风俗”,其人选也多为“博士大夫”甚至“素有威名”或“耆儒知名多历显位”“明达政事,能班风俗”者,但其成效却不尽如人意。从汉初陆贾、贾谊到武帝、昭宣时的董仲舒、司马迁、《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再到两汉之际的桓谭,以及东汉末年的王充、王符、仲长统、荀悦、应劭等,都深刻揭露了当时的社会情势以及各种不良风气。反过来看,似可说明两汉的风俗政策与举措并未取得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