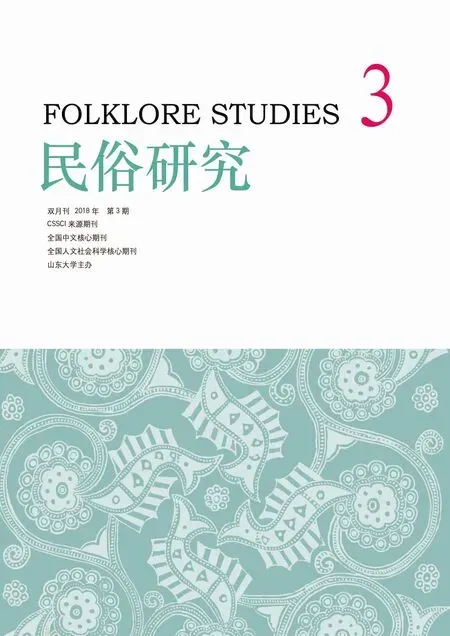变迁作为遗产?城市传统作为“自相矛盾”的范畴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 著 包汉毅 译
论文的题目绝不是要说,城市传统是个自相矛盾的事物,而主要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自相矛盾、我们在文化与传统理解上面的分歧,因为我们已经(早就?)习惯了,对于“遗产与传统”这类现象,仅仅将其视为特定的历史表现形式、封闭的社会架构以及特别的文化表演。文化被定义为持久、静态与同质的事物——当然会有少许的变化与变体,它有着极高的形态与地点稳定性。同时,这些特征主要涉及到乡村“面对面社会”的文化情态,它们是要永久“保留”这些节日、知识和各类共同体活动的。对此,民俗学的先驱们利用“风俗习惯”“仪式”“禁忌”等类概念已经特别进行了整饬。
“自相矛盾”在此处指的是观察者眼中障碍视线的“眼翳”,他们觉得应当固守这种对于“文化遗产”的狭隘性初步理解;他们或者自我实践这种“风俗认知”的观点,或者倒过来,就是将其背后的民俗学界置于“右翼”。
“另外”一种遗产?
不管怎样,由于有关“非物质遗产”的讨论,我们现在面对的一种情形是,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几乎不能成为这种传统认知的“舞台”。它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很难对旧传统有所期待,而想通过旧传统来“读懂”城市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另一方面,城市恰好是彰显变迁的空间与社会,它是通过迁徙与运动而产生的:人、知识、观念、物品的迁移;还因为,社会的、文化的外来性由此就体现了城市社会的基本准则,城市也因而被搅入持续变化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关联之中。
由此,城市的群体、共同体和组织就一直主要是异质性的、多元化的,而非同质性的、规范化的;由此,城市的边界、节奏和空间就一直偏向是“液态”,而非“固态”;由此,那里的行为方式、规则和知识形式就一直展现为动态性进程,而非静态性样式;由此,我们有关“文化遗产”的许多观念、范畴在这里就是有问题的、乃至不可用的。因为,在乡村、小城镇的情境下,传统首先指的是源自持续性和稳定性、也以持续性和稳定性为核心的知识,它们涉及到地方的秩序、规则、“自画像”、价值观,更多的是代表着同一性和集体性,其变迁要经受严格的管控。与此相对,在城市的情境下,正好倒过来,传统在很多方面可以描述为“变迁的传统”:作为持续变化与商讨的经验、知识模式。所以,较老的城市传统也都关涉到运动的情景,比如佣人和工人家庭的“搬迁日”、火车站的告别礼仪,等等,都是一些有关分离、迁移的习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阻挡视线的“眼翳”在大多数情况下遮蔽了如下这些事实,就是:城市的社会互动、文化交际是以“其它的”、流动性的、过程性的、交换性的以及匿名性的形式来加以组织的;经验、知识记忆、沟通、秩序的“其它”模式因而也存在着;传统可以是经由实践而“塑形”的,而且其主体不断变换、形式不断翻新。乡村社会的各类协会、节日世界在这里被公民社会与其日常生活世界取而代之了。
公民社会以及传统、公民社会作为传统?
如果说这一观察视角不是完全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在事实上就必须尝试改换范畴、并对现象重新加以分类整理。其中,需要审视的并非那些诸如城市节日、狂欢游行、射手习俗等类的老的文化形态——它们通常可以类比于乡村情景,因而可以很容易地将其识别、归类为“遗产”;需要聚焦的恰恰是那些新的文化样式,它们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文化化”与“移民化”的过程之中。在此,提醒一下大家:仅仅数十年之前,在很多西方城市都还未能谈及城市文化和地域身份认同。1971年,纽约的一个艺术家团体设计了那件著名的T恤“I love New York”,因为在其时,由于生产和投机、交通和犯罪、贫苦和迁居,纽约这个城市几乎已经变为了一座死城。同一年,德国城市代表会议也提出了要求:“救救我们的城市吧!”因为,在这里,以钢筋混凝土、汽车尾气为标志的城市建设也已经威胁到了都市生活。
对于这场深重危机的拯救是“由上而下”的:首先,市政府实施了各种规划,推行城市文化的节日化、制度化、活动化,通过文学节和音乐节、博物馆建筑和歌剧院建筑、露天音乐会和灯光秀等等而又重新使得市中心变得富有魅力。与此同时,移民群体和外来人口、艺术家和历史追想者、环保人士和街区文化积极分子也一起开始推动公民社会的思维和行动,让公民社会也积极参与塑造城市的空间和文化,并且试图阻止地域的“说一不二”政策以及城市文化的商业化。其间也出现了一些自嘲的形态,比如城市居民可能会对其邻居的“乡村化”加以戏谑;再比如,由于河岸、咖啡一条街、停车场的一揽子沙滩化、棕榈化,城市变得“酷”起来,居民们会调侃地称其为“炎热的地中海地带”。
这样,就产生了我们今日称之为城市公民社会和新城市主义的事物:倡议、文化协会、网络、数字化运动等等。它们既具有“真实性”,又具备“可操作性”,即是说:它们追溯于传统,却又常常是游戏般的;它们既关乎到连续性与持久性,却又适应于短平快的城市节奏;其主体人员主要由不断移动的城市中产阶级组成,他们——用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的话来说——对于市中心提出了“城市权”的诉求,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自身利益想把城市空间加以“私有化”。——在今日,城市公民社会的社会性特征及其认证政策绝对是一个超有趣味的题目……
无论如何,过去这些年发展的成效是卓著的:市中心又成为了富有魅力的生活世界!城市社会变得更为开放,而且结成了各种文化共同体!基于“道德”的立场,城市空间和城市政策被利用、被协商!城市风情自“谋求效率的福特主义”转型为“追求享乐的后福特主义”。简短来说: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城市经历了一场“文化革命”,这场革命早就发展出了自身的形态、结构、意义设定和连续性——即是“传统”。所以,对于这一“遗产”,我们必须在公民社会的架构与模式下重新加以考量。因为,这里所关乎到的是相当特别的知识形式和文化活动,这又涉及到城市的地形地貌、社会空间、社会生态等等维度,涉及到与运动、过程相关的物流,涉及到与工作体系、基础设施、社会氛围相关的移民经验,也还总涉及到与市民利益、协商、倡议相关的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从“文化”上来看,这其中的很多事物绝对是切实的、持久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它们又是流动的、流逝的——这是一种“不一样的”遗产,有着独有的知识、传承与载体。
所以,要谈论的事情很多:城市活动和足球粉丝文化、跨文化协会和体育协会、公民布告牌和服装仓库、音乐节和票友剧场、电脑俱乐部和红灯区协会、饮食文化和每周集市、青年文化和城市花园、艺术倡议和五一节、难民聚会和聊天咖啡吧……当然,如果认真考察的话,其中的一些是不能被视作传统的。但是,即使依循经典的“乡村标尺”,当我们给行为主体——人——穿上紧身连衣裙和皮裤的时候,它们中的一些倒的确还是属于传统的。或者,我们可以倒过来:对已有的范畴加以仔细审视,从浪漫主义、民俗学的“遗产”概念中摆脱出来,把其时间尺度的设定、表现形式的范围适应于城市的情境;那么,“遗产”这个概念就可以牵连到这样的一种文化——日常的知识和实践体系。“传统”也成为一种行为主体自身所选的范畴,他们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地进行论证。而“世代”这个概念也可以牵连到社会中的这样一种经验,基于移民的、移动的、乃至大学生们的视角,它们有的时候只涵括十年、乃至五年的期限。
无论如何,我的“结案陈词”是双重的:一方面,学术界、专家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员会应该加紧致力于对文化遗产的如此这般的再定义,也就是将旧的乡村范式扩展为公民社会的文化范式,而且针对社会的沟通、过渡政策,他们应当担负起主持人和翻译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我们却也要踏上相反的另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对于纲领的辩论、国家和世界的遗产名录制定,我们应当将其塑造为一种众人参与的、(文化)政策的协商过程。应当同行为主体、并且在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商讨,“坚持的力量”和“运动的力量”——请允许我此处引用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的老名词——如何融汇到一起?——其前提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是要有不同的文化传承、文化遗产的路线。那么,我觉得,无论高端的“道德资本”,还是特别的“认证潜能”都能够重新加以商讨、重新加以分配——无疑地,一种关于“文化遗产”的反思性纲领是包含有这种潜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