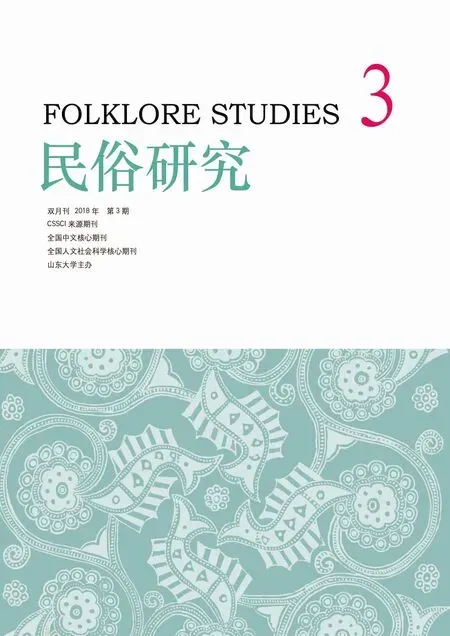日常生活与作为视角的民俗
王立阳
日常生活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民俗学界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受国内外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日常生活转向的影响,以及1990年代以来国内民俗学界研究实践和国际民俗学界相关理论译介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俗学者逐渐接受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带来的范式转换。不过当下的问题是,中国民俗学界对日常生活相关理论视角与本学科定位的认知还存在争议,更重要的问题是曾经以传统/现代二分为学科基础的民俗学要如何面对以后现代姿态进入民俗学的“日常生活”。
一、民俗学的学科定位与危机
2017年初,高丙中教授在《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一文中将他一直以来所关照的民俗学学术路径转向与有关中国社会及民族国家建设问题的思考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更为清晰地将“日常生活”概念放在了民俗学研究和实践路径的核心位置,提出中国民俗学的学科意识单从过去转向当下是不够的,处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和学术生产都致力于“在未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的大局之中,中国民俗学要确定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日常生活概念不仅是伦理概念、方法概念、目的概念,也必须是一个实践概念。民俗学的未来要致力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未来,“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中具有优先地位提供知识的基础、理念的基础和思维方式的基础”*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上述论断集中展现了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属性认知转换的深入以及伴随而至的研究范式转向。近年来,除了关注表演事件和语境的表演理论,还有很多研究更为直接地考虑到日常生活本身的特性。刘铁梁教授在2011年发表的《感受生活的民俗学》一文中提出民俗学应关注生活中富有弹性变化的表达与呈现,提出“感受生活的民俗学”*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刘晓春2013年在《文化本真性:从本质论到建构论——“遗产时代”的观念启蒙》中提出民俗或文化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民俗学应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刘晓春:《文化本真性:从本质论到建构论——“遗产时代”的观念启蒙》,《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吕微、户晓辉、尹虎彬等也提出民俗的价值和意义并非自身赋予,而是来自人们的实践,提出民俗学应回归“实践民俗学”。*吕微:《走向实践民俗学的纯正形式研究》,《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3期;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尹虎彬:《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日常生活的引入为民俗学带来的开放的危机甚至是学科存亡的问题心存疑虑。高丙中教授在《核心传统与民俗学界的自觉意识》中提出在固守传统所造成的学科边缘化的封闭的危机之后,近些年民俗学的危机是开放造成的危机,开放带来新的活力和发展契机,却也有让民俗学湮没自我的危险,迫切需要自觉寻找开放条件下的学科认同基础。*高丙中:《核心传统与民俗学界的自觉意识》,《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对此,赵世瑜教授2011年在《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一文中提出:虽然“日常生活”等概念和提法缓解了“传统民俗”逐渐消失给研究者带来的困境,将民俗学方法提升到新高度,但也有进一步模糊民俗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差异的趋势,使民俗学学科本位问题更为凸显,他认为民俗学要坚持自己是一门“传承”之学的核心传统。*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田兆元教授在2014年发表的《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一文中提出:民俗并非琐碎的日常生活或通俗文化,而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华彩乐章,是精英文化,是文化遗产,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并指出这样的重新定位有助于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发挥民俗对国家和社会的重大职能。*田兆元:《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学者们对引入日常生活视角可能带来的学科危机的担忧都有一定的道理。学科之外新概念的引入需经过一番努力,在不触动学科根基的前提下将其纳入学科传统的序列中,何况是日常生活这样一个对民俗学的历史和研究路径都存在反思和巨大挑战的概念视角。虽然德国、美国、日本等国际民俗学相关研究可资借鉴,但无法完全替代中国民俗学界自身的思考。
民俗学曾经以时间上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衍生的空间上的城乡对立为学科合法性根基,在当下的很多研究和实践中这一逻辑依然延续存在。户晓辉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民俗结束的地方才开始了民俗学的研究”的说法*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action-viewspace-itemid-34561.html。,从民俗学历史来说,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可以说民俗学参与甚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现代”进程。那么民俗学该如何面对以后现代姿态进入的“日常生活”概念,我们也许需要回到历史原点去找到出路。
二、“民俗”及民俗学的“知识考古学”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民俗学自肇始开始,在不同国家展示出不同风貌,这种差异不仅由于各国民俗材料不同,更是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不同国家面对的民族、社会和政治问题不同。民俗学真正发现了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参与现代性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又以不同方式将其推向过去。
追溯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在民俗学发源的欧洲,在“Folklore”出现之前,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通过引用旅行和探险记录中风俗的多样性来强调人类价值的多样性,挑战理性主义。*刘晓春:《文化本真性:从本质论到建构论——“遗产时代”的观念启蒙》,《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出于古风考古的文史兴趣、统治者的政治兴趣或是基督教批判前基督教异端的需要等缘由开始出现有意识收集和记录地方传统的兴趣。18世纪,这种兴趣逐渐发展出学术研究的路径。意大利学者维科的《新科学》被认为是早期民俗研究的先驱,发现了来自下层人民的大众传统的重要性,视民众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维科认为不同民族以不同方式传递关于世界的一致观点,并开创了以实证的比较方法研究不同社会中神话、歌谣、舞蹈、语言、仪式等蕴含和表达的诗性智慧。*Isaiah Berlin,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Vico, Hamann, Herder. Princeton &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这部作品及其思想影响了现代民俗学的肇兴和研究路径。
17世纪末,德国的历史人种志和古文物研究传统已相对成熟,民俗开始被视为特定的、可以认真收集和研究的对象。*Archer Taylor,“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 Folklore Stud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Vol.74,No.294(Oct-Dec 1961),pp. 293-301.而德国现代民俗学的诞生要归功到赫尔德和格林兄弟的身上。德国浪漫主义之父赫尔德受维科《新科学》的影响,提出“自然之诗”的概念,他认为在神话、诗歌、仪式和其他民俗中可以找到跨越语言和民族边界的人类共同体经验,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价值和意义,从中可以找寻和探讨民族精神,建构民族共同历史。*刘晓春:《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他的观点启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
受到赫尔德等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影响,格林兄弟认为所有可以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特征的东西都应该保存,他们视基督教为外来宗教,因为担心德意志生活方式的消逝,将搜集和研究重点放在前基督教时代的过去,放在乡民身上,关注重点是对不同地域民俗异文和相似物的搜集、保存和修复,而不是专题著作和个体的故事讲述。*Archer Taylor,“Characteristics of German Folklore Stud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74, No. 294 (Oct-Dec 1961),pp. 293-301.
而在英国,早期搜集和记录民俗的动力来自于对急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厌恶而产生的对于“英国风格”的追求,人们试图通过再造过去来补偿当下,从而沉浸到一个美丽英格兰的神话中,这是提出“Folklore”这一术语的汤姆斯及其同时代人所抱持的夹杂民族主义和反现代意味的理想。*Gillian Bennett,“The Thomsian Heritage in the Folklore Society(London)”,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Vol.33,No.3(Sep-Dec 1996),pp.212-220.
受德国民俗学的影响,不仅“Folklore”的结构模仿了德语词汇“Volks-kunde”,汤姆斯在研究路径上也仿效了雅各布·格林在《德意志神话学》中对重构的文本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俗所在的社会脉络,而同一时代另一位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关于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成性和未完成性的表述却未受到汤姆斯和当时各国民俗研究者的重视。*Peter Tokofsky,“Folk-Lore and Volks-Kunde:Compounding Compounds”,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Vol.33,No.3 (Sep-Dec 1996),pp.207-211.这是由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学者们的问题意识所决定的。
19世纪70年代,进化论思想兴起,主要的英国民俗学家都迅速转变为进化论者,泰勒等人的进化论思想扩展和修正了汤姆斯为代表的对乡村地区民俗和早期遗留的搜集记录,这些遗存从“英国风格”的象征和内容转变为人类社会历史早期的“文化遗留物”,在实践上造成英国民俗学会将搜集工作作为第一要务。泰勒的“文化”概念也受到了汤姆斯“Folklore”概念的影响,同样注重事象、文本和体系,对他们认为必将消逝的“民”的生活和价值没有关注。*Gillian Bennett,“The Thomsian Heritage in the Folklore Society(London)”,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Vol.33,No.3(Sep-Dec 1996),pp.212-220.
民俗学两大传统虽有直接影响关系,却走上不同路径。德国当时民族国家建设中的要务是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重估并提升自身文化在欧洲文明阶序中的位置和价值,因而对内宣扬民族主义和对外倡导文化多元主义成为其民俗学的突出特征,研究路径上注重从对神话、故事等文本的收集和研究中追寻民族精神。德国民俗学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其最终成为纳粹的帮凶,“民俗”和“民俗学”在二战之后成为德国学术界的禁忌,这是后话。而对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来说,其面临的问题却是巩固工业革命成果,并从文化阶序上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英国殖民秩序的合法性,所以其民俗学对“英国风格”的追求在昙花一现之后就很快被进化论路径所代替。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无法避开现代科学中理性主义主导的影响,造成“学”对“民”和“俗”的辖制。虽然民俗学发现了“民”及其生活,但无论是进化论的英国传统还是倡导民族主义的德国传统,都将当时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民俗从当下推向过去,否定记录者和被观察者的共时性,欧洲民俗学的两大传统经由译介都影响了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民俗学的肇始。
在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之前,中国民俗学具有一段很长的史前史,风俗搜集和记录往往与善治联系在一起,除少数专门文献之外,大部分记录出现在方志中,作为地方善治的证明或靶子。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民俗学的肇兴和发展与其在欧洲的前辈一样,是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精英知识分子们开始关注民谣、故事、庙会或是村社仪式等基本上从没上过台面的下里巴人的生活,这看似琐碎而微不足道,但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宏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关系到新人、新民和新的国家的创立。
关于民俗学对现代中国的贡献,高丙中教授在200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中提出中国民俗学为作为现代中国三个重要时期立国基础的民间、人民和公民三个关键范畴的形成提供了依据,成为中国民俗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立身之本。*高丙中:《民间、人民、公民:民俗学与现代中国的关键范畴》,《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在这三个范畴背后都还隐含另外一个关键范畴“民族”的影子,同时也有进化论观念的在场。
20世纪初的中国,同时面对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设双重任务,因此也出现了颠覆儒家传统之后如何重新形成民族国家自身认同的问题。《歌谣周刊》创刊前的1922年初,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自序》中提出中国长期以儒术统一国家,但西学东渐后,儒家学说无法与之相抗,各地风俗各异的国家如何统一成为问题,而且西方学说不能完全适宜中国不同地域治理,因此需要周知全国风俗,因病施药。*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岳麓书社,2013年。胡朴安整理全国风俗的初衷和最终实践依然更多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风俗与善治的观念以及采风传统。真正将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勾连起来的是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民俗学的肇兴。从梁启超的“新民”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民”的发现和论述之后,“民”的基本风貌通过以民俗学为代表的民众文化研究逐步展现出来,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界定范畴。*徐新建:《“民”的发现与“歌”的采集——民国时期歌谣研究的历史回顾(之一)》,《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二辑),2004年。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民间生活的态度是复杂的,对现代性的追求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诉求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中国民俗学早期在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之间摇摆。因此,如孔迈隆(Myron L. Cohen)所言,包括民俗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失去打造一个有意义的详尽的共同文化架构来表达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机会。*Myron L. Cohen,“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Daedalus,Vol.122,No.2 (Spring 1993),pp.151-170.这个任务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它意图通过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传统的构建来完成。
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来寻求当时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东西方平等,但是仍无法避免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在此发挥了作用,用阶级斗争的策略,以人民传统来重新解释和甄别中国历史。*[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人民的传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阶级和民族的思想同时体现在1949年前后所奠定的文化政策基调中,一方面继承了《歌谣周刊》对作为国民心声的民间文学的积极态度,大力搜集民族民间文学,将其解释塑造为人民反抗和打破阶级枷锁的心声与社会动员工具,另一方面又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精英的反传统思想,众多的民众日常生活事象被视为旧社会和落后阶级的象征受到排斥或摒除。相关的意识形态、文化政策和实践创造出了持续至今的文化和阶层区隔,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断层。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重新回到学科和研究体系中,各地民俗复兴也为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田野。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文史研究路径在民俗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民族主义和现代性两种意涵依然交织在学科研究之中。虽然钟敬文先生等一直强调民俗学作为现实之学,但是掩盖不住学科内外充斥的拯救即将逝去之物的悲情。不过如高丙中教授所言,曾经作为民俗学主流范式的对民俗的文史研究和相关实践,作为民众生活合法话语的呈现,“参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开启了这些被视为遗留物的民众生活重新成为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可能性。*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3期。本世纪初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通过一系列的程序赋予了曾经被贬斥的日常生活事象以合法性地位。民俗学界在此之前多年的努力也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中国民俗学依然面对着学科最初面对的问题。从中国现代民俗学肇始之初,研究者们脑海里都有一个应然的社会的样子,这个社会的主体是民俗学者所重新发现的“民”或者“人”,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就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公民,有着自由、价值和尊严的个体,通过一个公共的文化架构与群体进而与更大的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是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学科传统中的带有强烈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意涵的“民俗”概念和科学的反映论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民俗学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
“民俗”和民俗学的出现,正如托尼·贝内特所说是出于现代之初政治治理和社会运动需要的“现代文化事实的发明”*[英]托尼·贝内特:《现代文化事实的发明 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批判》,王建香译,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俗主义是被以反映论和本质化方式理解的民俗的宿命或本质特征。民俗学两大传统路径无法避免给民众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不幸的命运,一是要将民俗继续作为“遗留物”存在,同时导致它的实践主体——“民”,在整个文化和政治阶序中被贬低;再就是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成为被搬弄的圣物。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民俗”的本质化和神圣性。
当下民俗学研究虽已在检讨文化遗留物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却依然不时带着民族主义的拯救悲情或者英雄情结,特别是在各种遗产保护实践中。遗憾的是这种悲情或者英雄情结背后支撑着的依然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带着这种情结,民俗学者只能像希腊神话里推巨石上山顶的西西弗斯一样徒劳无功。
所幸的是,“民俗”背后交织在一起的两大传统又赋予它另外的力量,民族主义在将民俗推向过去的同时又需要不断地将其拉回现实作为认同标靶,现代性建构将民俗推向过去时也不免有反作用力出现。民俗中蕴含着吉登斯所说的避免现代生活零散化、逃出技术知识的铁笼并发展真实人类生活的机会。*[英]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4页。但要真正完成这一使命,“民俗”和民俗学都需要回到它“结束”或所由来的地方,也就是日常生活。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过去和现在相互交融作用,不再决然对立,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反思和摆脱理性和技术的辖制。
三、民俗学与作为视角和方法的日常生活
当然,日常生活并不是要代替“民俗”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日常生活更应该被视为理解和感受民俗生活的视角。日常生活研究也无法完全替代或排除民俗学传统积淀下来的学科范式,不同方法在面对不同对象和情境时依然有其独特解释力。从学科传统来说,我们没有理由简单讲民俗学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学科,从学科分野来说,我们也无法将日常生活研究这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直接纳入民俗学领地。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而且必须承认,日常生活是民俗的本质属性,也是民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因此,我们不可避免要将日常生活纳入民俗学研究视野,并以民俗学研究参与到更大的跨学科的日常生活研究领域之中。
日常生活视角延续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历史中形成“眼光向下”的独特视角。眼光向下,重新发现不被重视的“民”及其生活,同时又“自下而上”,以大众的生活文化或微观的日常反思精英文化或那些看似宏大的主题。这一视角来自日常生活自身特性所具有的力量。哲学和相关经验研究对作为视角和方法的“日常生活”的思考和研究积累可资借鉴。
讨论作为视角和方法的日常生活,无法避开胡塞尔的现象学和他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将“生活世界”作为其现象学方法的核心概念,并认为启蒙运动后,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唯一指针的科学的数学化实质上抛弃了科学世界所由来的日常生活世界,导致科学只关注事实而忽视意义,造成科学危机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危机,要解决此危机必须回到科学世界所来源的作为“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的生活世界。*[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与胡塞尔同时期,在韦伯、齐美尔等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也隐含着与胡塞尔现象学类似的视角和问题,开启了社会科学对经验和意义的关注。*[英]Harvie Ferguson:《现象学的社会学意味》,陶嘉代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不过真正将现象学视角引入社会科学的是美国学者舒茨。舒茨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引入社会科学,但抛弃了胡塞尔的抽象路径,将胡塞尔注重意识感知的先验现象学发展成为注重现实经验的更为世俗的社会世界现象学,在的不同著作中,舒茨曾用不同的概念来替代“生活世界”,包括“社会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等。*[美]舒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深受舒茨现象学路径的影响,加芬克尔等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提出常人方法论,关注人们在日常社会情境中如何确立、建构、维持和变革社会规则,虽然常人方法论过于注重对话分析而在社会学领域显得离群索居,但它唤起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互动过程的关注,并为“社会如何可能”提供了有意思的答案。*[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
日常生活在20世纪初以来成为西方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思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性的主要概念和场域。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经验教训时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阿格妮丝·赫勒以及法国学者列斐伏尔为代表。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渗透进了日常生活,使无产阶级失去了革命斗志,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改变日常生活,唤醒阶级意识。葛兰西主要通过市民社会实现向日常生活的转向,提出无论是夺取还是维护政权都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获得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体现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诉求,强调对个性的追求而不是阶级解放的追求,她的日常生活革命是为了达到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诉求的启蒙。*赵司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转向及启示——以卢卡奇、葛兰西和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为例》,《哲学分析》2013年第3期。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将这种哲学思考进一步拓展出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致力于从长期被贬斥为琐碎和无足轻重的日常生活的视角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是消极的、批判的,认为要克服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和非反思性,不过他认为日常生活的总体性特征使它保有改变自身的可能性,并力图在日常生活内部寻求能够改变它自身的能量,他的思路逐渐“从一种哲学方法转换到一种更加具体的社会学方法”,集中体现在他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与列斐伏尔等对日常生活及无反思的个体的消极批判态度不同,米歇尔·德-塞托更强调日常生活实践的创造力。德-塞托关注的不是发现新的文化文本,而是聚焦于人们从事日常生活实践的方式,也就是日常生活的诗学。日常生活在德-塞托看来是一个抵制的领域,不仅是强调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实践者的战术对表象的东西或权力的抵制,更强调日常生活是一个不断的生产和创造的过程,关系、空间、社会、政治等等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而不是仅仅应用于日常生活。*[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的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在德-塞托看来,日常生活实践给了我们重新想象权力和政治这些宏大主题的新的方式,一种形成于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应用于日常的政治和权力。
除此之外,在西方主流政治和社会理论界,日常生活本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也被不断提起,以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生活政治和亲密关系变革的研究为例,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或者说高度现代性的世界中,传统的控制放松,日常生活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互动中被重构,个体自我作为反思性主体被迫或主动地显现出来,就生活方式选择进行讨价还价,因此在解放政治之外,生活政治兴起。相对于注重脱离某种束缚状态或群体的解放政治,吉登斯发现或倡导的是“自下而上”、更关注朝向未来的个体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吉登斯提出亲密关系的变革等基于个人生活基础结构的革命,有利于个体生活民主化,进而进入公共领域,可能导致社会制度的革命和转型。*[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从现象学的启发以及社会学、文化研究、政治学及社会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来看,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交融在一起,所呈现出来的是活生生的实践和经验以及多元的声音和叙事,提供了反思那些抽象的命题和理论、单一的叙事以及看似宏大的主题的机会和场域,从中重新发现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价值和意义。正如布朗肖所言,虽然日常生活是逃离的,日常生活属于无意义,却又是所有可能的意义所在。*Maurice Blanchot,“Everyday Speech”,Yale French Studies,No. 73(1987),pp.12-20.无论从哲学还是经验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无论是将日常生活视为批判的对象还是作为潜在的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日常生活研究所具有的“以小见大”“自下而上”的反思的视角与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是契合的,回到日常生活可以重新找回民俗学最初对“民”或“人”的关注。无论从民俗的基本存在方式还是民俗学的学科视角而言,日常生活都是民俗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框架。
四、日常生活的民俗学研究路径
生成性和未完成性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赖立里、张慧:《如何触碰生活的质感: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论的四个面向》,《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我们无法给它一个准确的描述性定义,也无法用反映论的方法来把握,否则只能陷入无穷无尽的资料收集之中,抑或通过抽象概括给出一个貌似正确的社会秩序和结构的框架,这样的做法会丧失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所带来的反思力量。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和不断生成性的把握,必须从与之前的客观描述不同的视角出发,也就是从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人的视角出发,这也与民俗学自肇始以来对民俗之“民”的关注和重视相一致。而主体视角无法避开作为感知主体的身体以及由此而来的实践、情感、记忆等等“不可见”的经验,同时研究者本身在整个的研究过程中同样作为主体的身份也必须时时被纳入反思。
(一)身体与实践
身体是人类实践最自然的也是最基本的工具,从人的外在的生产、生活和仪式等的实践到内在的情感、记忆等等都无法脱离身体的基础存在。正如梅洛-庞蒂所说,身体是我们拥有的世界的总的媒介,人类在保存生命和追寻意义的行动中,身体在自己周围设计出生物性世界和文化世界。*[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但在西方古典哲学追寻人性的过程中,身体却被视为人类动物性的一面,与代表着人性的心灵相对,而被贬斥或漠视。
身心二元对立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存在,柏拉图认为身体和灵魂是两分的,同时还将身体视为人类通向知识、智慧和真理之路的障碍,人类正确认知世界、接近知识的唯一之路就是禁绝与肉体之间的往来。笛卡尔的意识哲学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笛卡尔之前,身体本身作为人性的反面警示被压制,依然不断地醒目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笛卡尔的意识哲学中,知识和理性成为哲学的兴趣中心,身体则在漠视中销声匿迹。*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
20世纪有三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一个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一个是涂尔干、莫斯、布迪厄这一人类学传统的社会实践性身体观,还有一个是尼采、福柯的历史、政治身体观。*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所谓拖出“深渊”就是指将身体从在笛卡尔的意识哲学中达到顶点的“身/心”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核心问题就是超越笛卡尔意识哲学的身心二元论,试图重建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关系,重返个体的身体和作为身体的活生生体验的知觉上,“我就是我的身体”*俞吾金:《问题意识与哲学困境——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探要》,《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虽然梅洛-庞蒂没有真正解决身心二元论,但是却将身体从被漠视的深渊里拖出来,放在与心灵对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提出了身体作为知觉主体的首要性,让现象学更加贴近现实的日常生活。
涂尔干和莫斯等人所关注的身体是在社会层面所谈论的作为象征体系的身体,特别是莫斯,在身体缺席的社会科学中,重新引入了身体的概念。与涂尔干强调集体表征不同,莫斯所讲的社会内在于个体之中,更注重个体实践,身体技术是连接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环节。莫斯所提出的“身体技术”是指人们在各种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和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莫斯还提出了习性(habitus)这个概念,来解释不同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不同的行为方式。*[法]马歇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04页。受莫斯启发,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自然的象征》和T.特纳的《社会的肌肤》都同样表达了身体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思想。而布迪厄则继承了莫斯的“习性”的概念,作为他的实践理论的关键概念之一。*[法]皮耶·布赫迪厄:《实作理论纲要》,宋伟航译,麦田出版社,2012年。
尼采和福柯为代表的传统主要关注身体与历史、社会和权力之间的纠缠。尼采强调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是一切事物的起点,理性只是其上的附着物。在尼采哲学里身体是一个主动的生产者角色,生产社会和历史,而后来到了福柯那里,身体则只是历史和权力关系的铭写对象。*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2页。福柯关注身体与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它上面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这些事件同样在肉体中相互连结、间或倾轧,也会相互解散、相互争斗、相互消解,追逐着不可克服的冲突。”*[法]米歇尔·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152-153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身体转向”也被引入了民俗学,让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主体得以更为鲜活地浮现在人们视野中。彭牧总结了美国民俗学身体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条以福柯的话语分析路径为主,结合玛丽·道格拉斯对身体象征和社会结构与关系的考察,在对身体语言、装扮与服饰、运动、仪式和禁忌等的研究中着重探究社会、历史与文化如何塑造身体,如何刻写于身体之上,身体如何成为权力、话语争夺和角逐的场域和体现;另一条则根植于现象学的传统,强调身体的肉体性和知觉主体的地位,同时引入了从莫斯到布迪厄的“身体技术”和惯习(习性,habitus)的理论脉络,它关注身体的能力、经验、感觉和能动性,探讨“体现(embodiment)”、“体知”(bodily knowing) 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关系。不仅如此,学者对自身身体性的感知和反思也被纳入到认知和把握身体性文化和实践的研究路径中,对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而言更具有方法论意义。*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
受美国民俗学和文化研究等的影响,国内民俗学者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身体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对房山农村劳作模式和春节的个人身体叙事两项研究中,刘铁梁教授将身体视角与他所提出的作为感受生活之学的民俗学的研究路径结合起来,探讨身体经验和个体叙事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和价值。*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刘铁梁:《身体民俗学视角下的个人叙事——以中国春节为例》,《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
身体与实践视角给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路径一个重要的落点,无论是被历史、社会和权力纠缠的作为被规训对象的肉体身体,还是作为感知和实践主体的身体,都更能包容和呈现日常生活复杂多变的过程,有助于让民俗学从反映论的“事象研究”彻底走出来,避免回到描述日常生活形态变化而忽视主体价值和意义的路子上。
(二)情感
在中国民俗学肇始之初,学者们曾将民间文学视为国民心声,慨叹香会所体现的民众的想象力和生活理想,并努力通过调查采风展现“民”的风貌。但在传统的事象研究范式中,具体的生活和情感却被理性排除在外,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一个个抽象出来的社会结构或者民俗文化理想型,如节日、仪式或者经过整理甚至是改编的口头文学的书面文本等,虽然这些理想型背后是丰富的情感表达,却往往被忽视,涉及情感的表述也往往与“国民”“阶级”等抽象的群体概念相关。即使在谈论人情的时候,情感因素也大都在社会和文化钳制当中,学者看到的是礼物交换、姻亲关系等抽象的社会形式。不过,当我们以日常生活视角代替事象的文本描述,将目光从俗转向作为实践主体的民的时候,作为主体性的条件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的情感将是无法避开的话题。
当下西方的情感研究者使用Emotion、Affect或feelings等多个词汇,在汉语学界有“情绪”和“情感”两种不同译法,情感的意涵中既包含个人生理的和心理的反应,也包含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维度,因而可以成为连接身体与心灵、个体与社会的中介。在相关研究领域中由于对两种意涵的不同侧重形成了对待情感的不同态度。
西方哲学界和社会学对情感的态度可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涂尔干等都对情感抱持着消极态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状态的情感变动不居,不利于城邦的稳定,需要完全服从理性统治和引导,才能够对群体利益发挥积极作用。而涂尔干提出了“集体情感”的概念,与“个人情感”相对,他赋予社会以优先于个人的权威,集体情感通过不断重复搬演演化为集体无意识而促成社会团结,个人情感则可能会对社会团结产生威胁。与涂尔干同时代的柏格森同样用情感概念批评了涂尔干的宗教理论,将情感提到与理性同样重要的地位,二者是互相交融的。*宋红娟:《两种情感概念:涂尔干与柏格森的情感理论比较——兼论二者对情感人类学的启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在人类学界,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他的弟子们在“文化与人格”的研究路径上也一直强调文化的情感向度。本尼迪克特的“性情模式”概念以及米德和贝特森的“精神气质”概念都强调个人情感表达是由不同群体文化选择形成和允许的,这一研究路径也影响了格尔茨对巴厘岛的研究。虽然他们“将‘情感’从被理性压制的灰色地带解救了出来,但紧接着就落入了文化建构主义的窠臼”*宋红娟:《情感人类学及其中国研究取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消极的情感观念和文化决定论的反思,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女性研究等领域情感研究勃兴,对情感研究领域产生两大影响,一是本体论的视角,强调人作为社会文化研究的对象或主体,进而凸显了曾经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情绪或情感;第二是反本质论的倾向,在认识论上接受绝对客观的“真实”无法达到,认为包括情感在内所有的理解都是日常实践所建构的。*黄应贵:《关于情绪人类学发展的一些见解:兼评台湾当前有关情绪与文化的研究》,《新史学》2002年第13卷第3期。
中国社会的情感研究也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感情解释为人生理和心理上面对紧张状态的反应,认为感情对社会关系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感情淡漠意味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国家庭被看作事业群体,出于对效率的追求必然讲究纪律,而普通的感情包括夫妇之间的感情就要被排斥。*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44页。这种观点基本上与西方社会古典哲学及经典社会学对情感的消极态度一致,强调理性对情感的统治或排斥。
很多国外人类学者对中国人的情感基本上持类似观点,美国学者Potter夫妇提出中国农民用工作而不是感情来构筑社会关系,而澳大利亚学者Andrew Kipnis虽不同意potter夫妇的观点,但又基于西方社会感情必须通过口头直接表达的规则而提出中国人情感的“非表达原则”,阎云翔认为他们都犯了西方中心主义错误,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社会,假定中国人情感表达有着一成不变的独特方式,并低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迁中的应变潜力。*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对上述论点的进一步反思需从日常生活出发,更为注重个体及其日常互动关系。基于下岬村的个案,阎云翔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语言、工作以及其他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或以外人不易察觉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亲密关系,而且随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变迁,人们的个体自主性得到发展,进而带来情感世界的丰富,家庭也从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向个体情感的私人领地过渡。*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这种研究思路显然受到了吉登斯关于亲密关系变革思路的影响。吴飞在《浮生取义》中更为注意日常生活中情感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张力与复杂性,他认为家庭生活是情感和政治的混合,不是完全按照情感逻辑发展,亲密关系仍然需要政治过程的维护,只不过这种政治过程不再是等级森严的礼教,而是人际关系中微妙的权力游戏,情感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事关家庭中的正义问题,必须通过礼来处理,“缘情制礼,因礼成义”*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宋红娟的《“心上”的日子——关于西和乞巧的情感人类学》通过对甘肃西河的乞巧仪式的民族志描述,展示了在乞巧仪式中仪式神圣性与日常生活、集体情感与个体情感以及信仰与娱乐等多重维度的混融,提出应该恢复被涂尔干等贬低的个体情感和凡俗世界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地位,达到个体和社会的情感自觉,找回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位置,这样才是一个好的社会或文明。*宋红娟:《“心上”的日子:关于西和乞巧的情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三)记忆
记忆在涂尔干、韦伯等古典社会理论家中少有人关注,希尔斯认为这是由于韦伯及其同辈人所怀有的现代与传统二分的“天真的想法”,他们认为现代社会在无传统的道路上前行。*[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社会记忆研究的奠基时期是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集体记忆”概念在此时期为哈布瓦赫、布洛赫等多位学者使用。哈布瓦赫继承了涂尔干对社会的强调,反对记忆研究中对个人和心理的过分强调,提出记忆有社会框架,也就是集体记忆。但哈布瓦赫同时受到柏格森对绵延意识流中个体记忆形成过程的思路的影响,强调记忆是在集体实践中不断被重构的,不仅通过节日等仪式性庆典不断搬演并强化,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以各种叙事、习俗实践和象征继续保持生命力。集体记忆填补了涂尔干所强调的节日集体欢腾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社会整合的空白。*[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作为一股潮流开始兴起,除了民族国家追求自己合法性的需要之外,还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界的转变的影响,首先是多元文化主义者意识到历史编纂是文化支配的根源,开始以受压迫群体的名义挑战主流的历史叙事手法;其次是后现代主义者抨击线性历史性、事实和认同的概念根基,对历史、记忆和权力的关联日益感兴趣;最后,霸权理论为记忆政治提供了分析框架,强调记忆论争、大众记忆和过去的工具化。*[美]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周云水编译,《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记忆研究中权力分析视角、底层视角、社会历史变迁视角等不同的研究路径。
20世纪末以来媒体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也推动了记忆研究的发展。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主要关注超越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周期的由神话、仪式、庆典等传递并由图片、文字等外在媒介保留下来的过去的信息。*[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法国学者诺拉提出“记忆之场”的概念,认为记忆在现代社会已经与日常生活脱节,需要依赖人为的纪念仪式和节日、档案资料、博物馆、纪念碑等一系列外在场所才能加以保存。*钱力成、张翮翾:《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对民俗学来说,记忆并非一个完全新鲜的话题,从欧洲民俗学肇始早期开始,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民俗一直被视为人类或者民族的历史或记忆。在中国民俗学早期,除了文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之外,还有顾颉刚等历史学学者的参与,倡导通过民俗学的记录和研究“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顾颉刚:《民俗发刊辞》,《民俗周刊》1928年第1期。。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里,也正是包括言语在内的习俗系统提供给集体记忆一个最基本和最稳定的社会框架。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历史和记忆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过去的方式,哈布瓦赫认为历史是外在于和超越群体的,与具体的群体已经不再有有机联系。集体记忆却是持续活在群体意识中,而且超越不了群体边界。*Maurice Halbwach,Collective Memory.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0,pp.80-81.从这种区分我们也可以尝试理解中国民俗学对民俗的认知路径的转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对民俗的理解都是历史路径,或是在进化论影响下将中国民俗置于人类历史的阶序中,或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初衷从底层生活中将民众的生活事象抽取出来建构民族历史,或是出于政治目的建构人民的传统和历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方法是这一阶段民俗学的主导范式。在历史或比较的事象研究关照下,民俗脱离所处的民众群体生活,超越了群体边界,并被本质化和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注重“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路径的引入带来民俗事象研究向民俗生活研究的转型,使民俗学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到具体群体的民众生活上,民众的实践和记忆开始在民俗学的研究中浮现出来,对民俗作为一种“传统的发明”及其蕴含的民众记忆的建构性的反思也越来越深入。特别是在民间叙事领域,随着表演理论的引入,杨利慧和巴莫曲布嫫等在神话、史诗等研究领域将传统的对文本的研究延伸到直接影响文本形成的讲述现场乃至更大社会语境的研究。
不过,有意识地将记忆作为民俗学的一种研究路径是本世纪初之后才逐渐出现,一方面是受到2000年以来记忆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兴起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日本等国外民俗学影响。较早的中国民俗学界的记忆研究是郭于华对骥村的研究,郭于华认为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郭于华:《社会记忆与人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0日,转引自http://www.sohu.com/a/161463116_664633。刘铁梁教授也基于当下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提出将村庄记忆作为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刘铁梁:《村庄记忆:民俗学参与文化发展的一种学术路径》,《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日本民俗学相关研究的译介也对中国民俗学的记忆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岩本通弥对作为方法的记忆的思考。岩本通弥提出,记忆为民俗学分析民间传承提供了新的方法,同时也能够与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让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要坚持民俗学对边缘群体的关心,坚持作为最接近底层生活的记忆观察者的角色。*[日]岩本通弥:《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王晓葵译,《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直接受到岩本通弥和日本民俗学记忆研究影响,王晓葵教授关于战争和灾害记忆的研究已经获得不少成果。
中国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的视角也为我们在整个记忆研究领域中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基于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各种节日庆典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叙事以及具体个体的个人生活史的记录分析,彰显他们的经验和记忆,发出底层的声音,显现出社会的变迁或分析各方力量的博弈,记录和分析人们如何在当下社会通过重构自己的集体记忆形成自我和群体认同。正如沃尔夫冈·卡舒巴所说,“搜寻、记录这种对‘自己’历史的看法,然后将其铭刻在人们的头脑里,就是他们/我们的任务”*[德]沃尔夫冈·卡舒巴:《记忆文化的全球化?——记忆政治的视觉偶像、原教旨主义策略及宗教象征》,彭牧译,《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对中国民俗学而言,记忆研究是整个学科范式转向的一部分,也提供了对学科历史反思的路径,从民俗学的学科史我们可以看到民俗学者曾经在记忆政治中的角色,这一位置也给民俗学者研究和反思记忆政治提供了独特的优势。
(四)互为主体性和研究者的位置
日常生活也给民俗学研究带来田野方法和伦理的挑战。如前所述,对总体性的、不断生成中的日常生活的把握,必须从作为主体的人出发,关注作为感知主体的人的身体性和由此而来的实践、情感、记忆等,从很大程度上说,只有做到这些,民俗学才真正成为“人研究人”的学问。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研究者的位置。我们需要承认研究者并非化学试纸、显微镜、摄像机或其他人造的呆板的仪器,研究者同样有血有肉、有着自身的身体性实践、情感和记忆,与我们的“研究对象”处在同一个实践和关系过程之中,这是我们研究展开的前提,也对整个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及其呈现都产生影响,这是研究者必须时刻保持警醒的。
研究者“价值无涉”的客观立场曾经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一直保持的理念,这是社会科学对于自身科学性追求的重要基础,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保持客观立场,将自身的立场、价值、情感等放在一边,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描述和分析所观察到的社会与文化事实,以达到真正的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这种“价值无涉”的客观立场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研究者的身体性的排斥和对理性的信任。正如前文所说,古典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身心二元对立,身体被视为达到真理的障碍,人类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必须并完全可以通过理性的超越来实现。
但缺乏研究者的自我主体在场,被研究者作为主体行动者也无从呈现。在近六十年来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改变这种姿态。在田野和民族志写作中强调学者和被研究者同样作为主体的地位,对新的田野模式的设想,保罗·拉比诺提出要与“关于科学工作的实证主义观念”和“格尔茨所展现的‘精致化的实证主义’”决裂,他认为田野的建构是一个公共的交流过程,最终呈现出来的民族志事实上是通过不同主体交流所建构出来的。*[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田野并不是外在于研究者存在的作为社群或者个人的他者,田野存在于作为主体的我们和他者之间,田野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甚至远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观点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接受。
国内民俗学界对田野作业中的互为主体性或研究者的主体在场的反思在过去二十年内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表演理论引入之后。巴莫曲布嫫在研究彝族史诗时在史诗演述传统、表演事件、受众和史诗演述人之外,还强调了研究者的在场,她认为研究者的在场直接影响史诗演述人和作为表演事件的史诗演述,同时研究者在场也是在研究视界中勾连起整个演述事件诸因素的前提,对研究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他观行为,也是一个内省过程。*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当然,我们研究者的位置不仅在田野作业中,还包括在最终民族志或民俗志呈现中。日常生活的民俗志要摆脱反映论的描述、归纳和抽象,必须将研究者的主体视角纳入其中。无论是实践、情感还是记忆,这些日常生活的不同呈现都时刻处在社会关系之中,包括研究者与田野中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中在理性视野中“不可见”的经验和感觉必须通过研究者的主体视角才能得见,也只有通过研究者与其他主体之间互动实践才能够传达给读者。
五、结 论
如上所述,民俗学回到日常生活,是要重新找回学科肇始之初对于“民”或“人”的关照,回到日常生活是重新赋予我们学科自身这个机会,也延续了学科传统中“眼光向下”的视角。不过民俗学引入日常生活概念,并不是要拷贝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昙花一现的“考现学”,单纯记录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变化。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对于民俗学来说也并非新鲜事物,无非是将民俗记录从过去转向当下而已。日常生活对于未来的民俗学不仅是作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这也是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现象学转向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日常生活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统统纳入其中,将被标签为不同符号的对象还原为鲜活的人,在此基础上平等、深入和实质性地交流,达致互相理解、认同或尊重,从而建立起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勾连,它为民俗学继续完成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提供了新的机会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