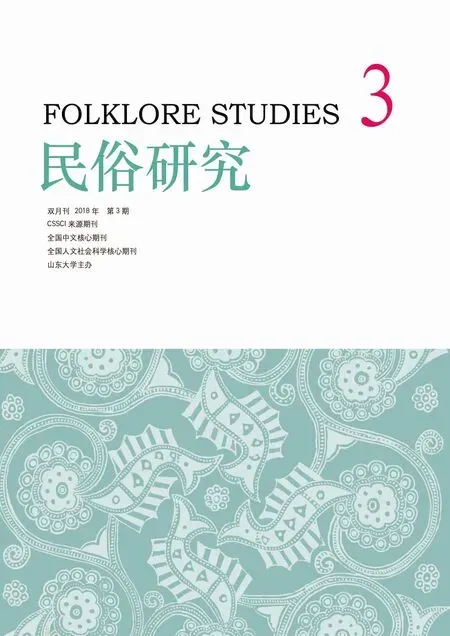女为悦己者容:中国古代女性服饰表征与审美取向
宋金英
对于女性服饰文化研究,首先离不开物态服饰和迎合时政的服饰制度。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女性服饰的研究,虽专门性的论述并不多见,但在涉及古代服饰的相关研究中却有大量涉及。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古代女性服装的形制、色彩、纹样、穿着方式、产生原因等方面都有较详尽的研究与论述,并对影响女性服饰产生、发展、嬗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索。*代表性成果,如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袁仄:《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年;缪良云:《中国衣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赵刚等:《中国服装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华梅:《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等等。但纵而观之,这些研究的出发点多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域、气候、风俗习惯等表象方面入手,鲜少从男权角度论证女性服饰特点和审美思想的。有鉴于此,本文试从男权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梳理古代女性服饰文化的发展脉络,挖掘掩盖在表象因素之下的男权社会对女性服饰的影响,重新理解“重礼求善”的古代女性服饰文化背后所包含的无奈与不甘,以图为“古为今用”的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服装中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定的思想文化上的借鉴。*郑晶、厉莉、刘晓刚:《品牌服装款式系列设计方法》,《纺织学报》2016年第12期。
一、古代男权社会影响下的女性服饰特点
在宗法制度贯穿整个男权社会的背景下,注定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男性通过各种封建义务与整个国家机构形成密不可分的依附关系,家庭的义务只是各种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而男权社会剥夺了女性所有与社会有关联的权利,把她们禁锢在唯一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家庭当中。女性除了与父母、儿女的血亲关系稳定而牢固之外,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丈夫并不会因为婚姻而变得执着和专一,面临着随时离去和被离去的境况,这直接影响到女性一生的幸福与否。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女性服饰上的迎合性、趋同性和规则性的特点实是无奈之举,而古代不同时期所发展产生出的相关思想与观念,也像一把钳子似地牢牢遏制了女性追求个性和表达自我喜好的权利。
(一)迎合男性审美
在封建男权社会制度中,决定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生产结构里并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女性在封建体系中也因此失去了参与生产活动的机会,只有依附男性才能获得生活的基本保障,这也是女性成为男性观赏品和消费品的重要因素之一。*张小萍:《从陶瓷仕女图看古代女性文化》,《中国陶瓷》2006年第2期。因此,在古代男权社会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并不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对待,将女性私有化的婚姻,成为男性与男性之间划分女性所有权的契约,而被软禁在男性权威之下的女性,则必须固守闺阁,与外界断绝所有联系。于是长期在封建礼教熏染下的女性也逐渐接受了这一不平等的约定俗成,并将三从四德当成一种传统理念,甘愿接受男性的奴役。将女性物化和财产化的男性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任意处置身边的女性,苏轼“以妾易马”的黑色历史就是将女性当成私有物品与商品互换的有力证明。
因此,古代女性的私有化社会地位使女性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取悦男性,以此来达到自身价值的体现,这种取悦不仅仅是行为上的,还有投其所好的着装上,整体风貌表达的是男权社会对“美”的理解与要求。同时被私有化的女性也是男性炫耀的“物品”,容貌身姿成为封建社会女性文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服饰作为人外在物化的表现形式,其审美价值与文化寓意也就变得尤为重要,并从不同的角度迎合男性的审美。因此无论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还是“丰腴华贵”的美人,只是满足了不同时期男性对美的要求和标准。这其中既有“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张景贤注译:《晏子春秋》,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的记载,又有南唐李后主因一嫔妃以帛缠足舞于莲花之上而导致的、始于五代延至民国的女性缠足陋习*华梅:《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63页。,而女性为迎合男性“尚小足”,不惜通过自残的形式来取悦男性。还有隋炀帝荒淫无度喜华贵服饰,致使女子专事妆饰的风气盛行*赵刚等:《中国服装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为盛唐服饰的雍容典雅奠定了基础。因此,古代女子服饰是迎合男性观赏和欲望下的产物,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古代女性对自身美的需求。
(二)趋同于礼教要求
婚姻让女性从一个家庭归属于另一个家庭,“妇人因夫而成”的婚姻,其从属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从女者,女子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传生:《说文释例举要》,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可以看出女性一生从父、从夫、从子的附属地位,其活动核心主要是家庭。因此,女性生命本体和情感喜好往往被社会所漠视*罗嘉慧:《古代爱情戏中女性爱欲的生理学解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而男性对女性的种种要求与规范,更加剧了女性在婚姻中依附关系的不稳定*万光治:《古代女性的价值实现及其文学的悲剧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女性只有极力通过改变自身的条件以满足男性的各种要求来巩固其家庭地位。因此,在这种以“尊尊亲亲”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里,人伦秩序变得尤为重要,而中国女性的服饰特点也由此更加注重社会的群体意识和伦理象征*宋炀:《美人之美:中西方古代女性妆饰与审美文化比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7年第3期。,并以此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与妇德休戚相关的妇容礼仪制度来压制女性心理和生理上的欲望,从而追求精神上的洁净与人格上的纯粹。这种审美取向的界定,注定了古代女性服饰具有趋同于礼教要求的特点。无论是秦汉的庄重、魏晋的飘逸、隋唐的雍容、宋明的典雅,还是元清的异族之美,所包含的内在本质都具有中国特色的温润内敛的“美”和女德内容的“善”,是一种服饰审美思想的趋同性,是男权社会男性眼中对“美”的定位,也是中国人文思想的物化表现。
因此,古代不同时期的女子服装形制,虽然朝代更迭跨越几千年历史,但其本质形态和内在审美文化并没有发生突破性改变,整个服饰发展脉络都在“尊礼从善”的框架里演变,服装造型没有刻意的结构线和装饰线来展现女性的性别特征,或上下连属,或连体通裁,所表达的都是遵从祖制中的“规矩”与“中和”,是“礼教”影响下的内敛与包容。这种隐藏性的美,更是对女性“女德”中善的要求。它不仅仅是思想行为上的依附,装扮上也要满足男性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眼光,即思想行为要达到的“三从四德”“温婉贤淑”,服饰上更要满足男性欲望的想象,并通过女性服饰上的嬉戏、游离来疏解社会压力,以此达到男性自身的快乐与满足。*师爽:《古代服装与身体——古代女性服装解读》,《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
(三)遵循社会规则
封建男权社会的女性服饰文化也是伦理政治的附庸。*尹志红:《中国古代服装发展的启示》,《艺术百家》2010年第8期。作为男性附属物的古代女性服饰,所体现出来的依附性是中国人文哲学“礼”的再现,所谓“夫礼,地之义也,民之形也”*(春秋)左丘明:《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第344页。。服饰规制不仅在男装上有所体现,女性服饰也随男性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形成有序、有制望而知贵贱的服饰形态。这种变化是固化的,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具有很强的制约性。如《唐会要·章服品第》对男性服饰等级有详细的规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金带九銙。七品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鍮石带九銙。九品服浅青,鍮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一《章服品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9页。男性服饰的社会规则化是为从事相应社会活动而制定的,它是社会对男性身份的定位,也是对男性行为的限定与规范,而严格的服饰等级划分涉及到与社会完全脱节的女性身上,则是对女性与男性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即“妇人从夫之色”*(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一《章服品第》,中华书局,1995年,第569页。。如在唐代就明确规定,贵妇所穿之服饰,要依其夫、子而分别有定规。五等以上诸亲妇女及五品以上母、妻,通服紫;九品以上母、妻,通服朱。另外,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妻子所穿衣服的领口袖子上,可以使用锦绣,凡间色衣裙不能超过十二破,单色衣裙不能超过六破。*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5页。这种建立在男性地位高低基础上的制度化服饰,服饰的审美性屈从于政治目的的等级划分,具有很强的标识性和隐喻性。又如宋代的袆衣,是王后与命妇的祭服,位居诸服之首,相当于君王的冕服,是皇后最贵重的服饰。这种服饰主要在受皇帝册封和祭祀典礼的时候才会服用,其上下连属的服装形制,代表的是女德的“专一”,深青色的底色上绣有象征“文采昭著”的赤色翟鸟,衣领、袖口、门襟、下裾都用红色的衣料镶缘,上缀具有帝王“应变能力”的云龙,与之配套的是凤冠、青纱中单和深青色的蔽膝并挂白玉双佩及玉绶环的饰物。*赵刚等:《中国服装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3页。政治意蕴显而易见。
(四)隐含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特点,除了男权社会中“礼”的制约以外,还包含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光辉。中国几千年的服饰文化,主要受儒家、道家以及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这些哲学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观、伦理意识的主导,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古代服饰走向。*吕逸华:《中国古代的服饰审美观》,《艺术设计与研究》1994年第2期。对于男性服饰所隐含的哲学思想,更多的是巩固男权地位的“君权”“父权”“夫权”等,男性服饰除却冕服固化的形式外,常服也主要在细节上有些微变化。袍、衫是历代男子服饰中常用的服装款式,主要变化在领与袖的局部方面,整体款式简洁大方,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冕服的上玄下纁,象征未明之天和黄昏之地,上绘下绣的十二章纹代表了照临、稳重、应变、文丽、忠孝、洁净、光明、滋养、决断、明辨,既是对着装者的要求,更是体现着装者的不可替代性。又如始于唐朝的补服,其文禽武兽的朝服形式,是用纹样的象征寓意来划分男性的地位与身份。这些用于男性服装的结构、工艺、色彩、纹样等形式,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功能,而不是取悦和迎合女性的手段,这与女性服饰所体现的、以男权需求为标杆的服饰审美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女性服饰发展的整体风格,与其说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不如理解为是哲学思想影响了男性审美的结果。
儒家提倡的“中庸”,体现在服装中,即是着装的适度与适合。所谓适度即是合理的选择服饰装扮,反对花里胡哨和奇形怪状的着装形式。“服奇志淫”*(明)吴从先:《小窗自纪》,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认为服装不雅,则人必不雅,因此“中和”是儒家服饰装扮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女子服饰的外化视觉效果则是柔顺、含蓄的窄肩、长身、直线条的自由衣褶。道家的“乘道德而浮游”*叶舟编著:《庄子全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意为自由、超脱与自然相融合的哲学思想。“清净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表现在女子的服装中就是减少结构线对人体造型的束缚,如宽博随性的衣身、舒展的袖子、曳地的裙摆等。唐朝更是将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服装形制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兼容并蓄,破除一切束缚局限,成就了一代盛世华服。*吴欣:《“魏晋玄学”和“程朱理学”对古代服饰文化的影响》,《丝绸》2007年第11期。“惟物洁净,不可异众”*(宋)袁采:《袁氏世范》,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的审美定位,摒弃有悖于传统的奇装异服,审美取向似乎又重新回归到了儒家“服奇志淫”的“中和”,“温柔居中,以理节情,以理节乐”的审美观中暗透了“灭人欲”的观点,使宋、明女子服饰文化走向素雅、细腻,女性特征被进一步压制,溜肩、窄袖、窄身、束胸以及腰身造型趋于模糊的褙子和襦袄等弱化女性基本特征的服装形制,显示了“程朱理学”中“灭人欲”的主旨思想。这些新旧哲学思想相互接纳、融合、渗透,从不同层面影响着中国古代女性服饰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二、古代男权社会影响下女性服饰的审美取向
“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纲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汉)班昭等撰:《蒙养书集成(二)·女诫》,梁汝成、章维标注,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在女为柔弱、男为刚的古代男权社会,女性服饰审美取向主要受阶级化、道德化、哲学观念和男性个体化审美的影响。其中阶级化、道德化审美具有一定的社会趋向性,它们与哲学观念从阶级和道德层面对女性服饰进行了规范和管理,以巩固封建社会中的男权地位,属于社会范畴的审美。男性个体化审美却从男性生理和心理的角度,重新把握对古代女性服饰装扮的要求,在男权不可侵犯的前提下,又渴望女性在服饰上满足男性自身生理和心理上的欲望。一方面女性要遵从社会制度与道德上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要迎合男性欲望的满足,这两种看似冲突的审美,却在不断的碰撞中对立统一成一体,确定了古代女性服饰审美的大方向。
(一)“尊卑有序”的阶级化审美
封建社会里服饰作为人类情感物化的载体,表达的不仅仅是着装者的喜好,更多的是社会秩序的要求,它受社会制度的制约和限制,体现着社会的进步和制度的可行性。正如唐人白居易所说的那样,“划邪窒欲,致人于格耻,莫尚于礼”,“惩恶抑淫,致人劝惧,莫先于刑”*(唐)白居易:《白香山集·刑礼道论》,转引自任喜荣:《“伦理法”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基于刑事法律范畴的分析》,《比较研究》2004年第3期。,以礼约束和禁锢女性的思想,以刑惩戒违背社会规则的行为,礼、刑成为古代维护阶级化审美的重要手段。等级制度下产生的衣冠制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服饰以形制、色彩、图案、质地等视觉化元素形象地将贵胄与布衣、纨绔与儒士明确地区分开来,各级冠服不得僭越,士农工商也各有规制,从而达到“辨等威”的等级化服饰目的。女性服饰的阶级性划分主要依附于男性的身份与地位,并随着男性地位的提高而发生相应地改变。各个朝代的贵族女装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不同的地位、身份、穿着场合、从事的活动等对服饰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汉初曾规定,百姓一律不得穿杂彩的衣服,只能穿本色的麻布。又如,明朝命妇与平民女子的服饰虽然基本形制为衫、袄、褙子、比甲、裙子等,但普通女子多以紫花粗布为衣,不许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绿色、桃红等间色,不许用大红、鸦青与正黄色,以免混同于皇家服色。*华梅:《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第91页。这种服饰不同于古代时装的时尚性和潮流性,它存在于社会制度中,并带有很深的阶级性,是对身份和地位的认可,因此也是众多女性向往的服饰装扮之一。
(二)“德言容功”的道德化审美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男性审美取向影响很大,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礼”自始至终作为主线贯穿其中,“宗法血亲”“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一种固化的习惯与规程。这种规程又对女性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要求,即所谓的“德言容功”。《礼记·昏义》曰:“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日……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郑玄注曰:“妇德,贞顺也;妇言,辞令也;妇容,婉娩也;妇功,丝麻也。”*《礼记》,崔高维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虽然“妇德”占据首位,但是占据第三位的“妇容”也不容小觑,因为第一印象是外在的“妇容”,通过妇容辨其“妇言”、了解其“妇行”,再通过“妇行”确定“妇德”。而“妇德”中的“贞顺”强调的是女性的贞洁与顺从,体现在服饰中则是一种严谨、内敛的伦理美学。飘逸、柔顺、宽博的整体服装不需要过多的结构线来体现女性胸、腰、臀的凹凸有致,多余的面料在锦带的束缚下,形成自由流畅的褶裥,体现的是一种随遇而安的审美境界;曳地的长裙与压住裙身的环佩,行走时形成行云流水的步态与步摇的轻微震颤,表达的是女性的沉稳与贤淑。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线装经典》编委会:《论语》,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9页。,一方面表明的是圣人的思想态度,一方面传递出男性对女性美的关注。男性在个体化的审美中将女性之容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社会审美中更为看重的却是美貌以外的附庸与顺从。*高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女性形象审美嬗变》,《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这种行为、思想意义上的顺从,表现在服饰上就是一种形神藏拙与中和的着装之美,即神态上的温婉含蓄和行为上“怨而不怼”的审美定位,而所谓的“伦理美学”实际上就是对男尊女卑社会基调的认可。女为阴,男为阳,“阴阳变化,各得其宜”,方能“上下顺通,奏为肤功”,反之则“阴升阳伏,桀失其室”。*(商)姬昌:《周易全书》,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187页。
(三)“形神兼备”哲学思想影响下的审美
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对自然的敬畏是古代哲学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人又必须立足于群体之中,“尊尊亲亲”的人伦和谐与外界的社交关系交缠成整个生存环境。在自然和群体关系的影响下,“礼”“道”“玄学”等迎合时代发展的朴素哲学思想与“乐”的美感享受,通过实用理性的理智感而纳入制度,形成秩序,使人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活境界。*苑涛、章亚昕:《中国服饰文化与角色心态》,《齐鲁学刊》1991年第5期。即人的欲望在规定的框架内不僭越,并通过服饰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启示和引导人的精神世界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与服饰不再只是简单生理上的需求关系,而是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哲学思想和人文情怀,宽展的服装形制带有较多的回旋余地,低调隐性的服饰格调体现的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夫妻之间的“仁义礼智信”的伦常。通过点、线、面、体、色、纹样、面料及配饰等,来达致古人哲学观所渴望达到的“知礼”“尊礼”“知耻”“重伦理”“辨等威”等观念要求。*宋金英、王婧:《齐国服饰文化特征探悉》,《丝绸》2011年第3期。
不同时代对女性美的要求不同,或含蓄,或华贵,或清丽,或柔弱,服饰则通过款式构成、色彩、面料等元素与女性自身的气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从迎合时代审美的角度出发,通过服饰的装扮,完成外在“形”与“神”的和谐统一。这种外在“形”与内在“神”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和男性的审美观念。《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再如对薛宝钗的描述:“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清)曹雪芹:《红楼梦》,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21、64页。这虽是小说中的描写,但也能看出不同“形神”之间的巧妙搭配,外在“形”在服饰的装扮下,将内在“神”充分地体现出来,形成风格迥异的两种审美。
三、结 语
影响古代女性服饰文化的因素有很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是基于男权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化规章制度,这种制度从各个层面维护着男性在社会上的权利和地位,并将女性地位变得无足轻重。但这种对女性的压榨往往被表象化的社会现象所掩盖,多数研究者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身心残害时,却忽视了男权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因此,在古代封建制社会,无论政治如何开明,经济如何发达,哲学思想如何高深,甚至政权更迭,不同民族文化的渗入以及特定环境下的男性个性化的审美取向,改变的也只是不同时期特定的艺术形态和审美定位,而古代女性作为私有财产和附属物而不被尊重的境况却并未改变。在此基础上,将生存逻辑和情感逻辑统一于艺术审美逻辑的古代女性,从根本上不可能与具有平等民主意识的现代女性相提并论,那种以维护男权利益的女性审美取向所形成的严格划一的封建服饰构架,漠视和压抑了女性体现自我、彰显个性的服饰审美需求。这正是中国古代女性服饰之所以会产生、发展与嬗变的重要原因和规律之一。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