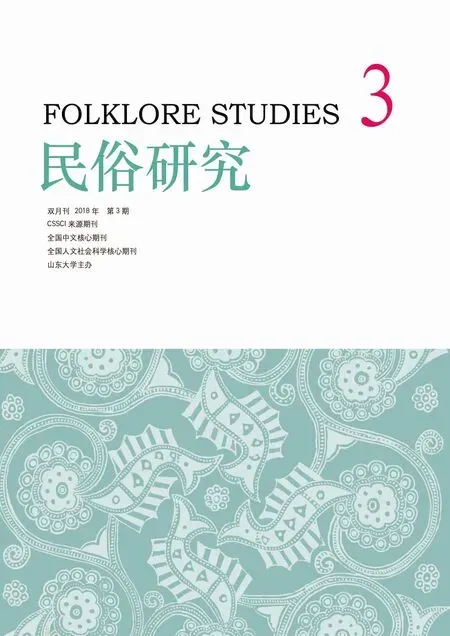乡村剧团与社会动员
——以1944年河北阜平县高街《穷人乐》的编演为中心
韩朝建
中国共产党将戏剧作为革命手段及社会动员的方式,从苏区时期已得到广泛实践,并确立了革命戏剧的基本生产机制,如剧本预审、预演、改造旧戏、培养戏剧人才等。*黄擎:《红色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吁求与“十七年”戏曲改革》,《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5期;王永华:《苏区戏剧与中共意识形态教育的政治互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郑紫苑:《苏区戏剧教育功能:大众化与化大众》,《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抗战时期华北、华中、西北等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普遍重视演剧在社会动员中的巨大作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徐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廷军:《戏剧与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王欣媛:《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戏剧宣传与动员》,《盐城工学院学报(社科版)》第29卷第2期;王飞:《论曲艺在抗战中的宣传动员作用——以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陇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其中部分成果专门探讨了社会动员的发生机制,尤其突出的是中共积极改造利用华北乡村传统的秧歌剧、山西梆子、京剧等旧剧形式,对旧剧的内容、组织者等进行“消毒”,植入革命内容和政治符号,以重构戏剧的教化功能。*崔一楠、李群山:《“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李军全:《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王冬:《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秧歌剧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王宁娜:《被历史改造的民间文艺——论延安新秧歌剧运动》,《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Chang-tai Hung,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pp.222-234.韩晓莉则结合社会的维度,探讨了山西乡村的旧戏班被改造成革命剧团,旧艺人被改造成“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过程,她由此认为改造后的戏剧沦为政治教育和革命宣传的舆论工具,无论是演剧还是看戏都不再是乡村社会的自发行为。*韩晓莉:《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3期。
总体来看,既有的研究多从文艺理论、政策措施的角度,自上而下探讨中共对戏剧的改造利用,而乡村剧团作为沟通官方与乡村大众的桥梁,其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考察阜平高街村剧团编演《穷人乐》的过程*关于《穷人乐》的研究成果有周维东:《被真人真事改写的历史——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程凯:《“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人间思想》第5辑,人间出版社,2016年,第99-133页。,探讨该剧团的性质、人员构成、与专业剧社的互动、与观众的关系等问题,换言之,就是谁来动员、谁被动员、如何动员,以及这种动员过程与既有的乡村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希望对理解乡村剧团与社会动员的关系有所助益。
一、阜平高街村的干部、模范与村剧团
高街村《穷人乐》的创作应置于剧变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高街村位于大沙河南岸,与阜平县城隔河相望,是通往五台山的要道。1937年年底,八路军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次年初在阜平县城第一完小的礼堂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抗日临时政权即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为了争取贫苦农民的支持及社会动员,边区政府先是实行减租减息,引入“永佃权”;随后废除国民政府时期的编村制度,在乡村实行选举,建立了救国会、工会、农会、合作社、青年团、妇女团、儿童团等机构。新的乡村组织的权力及合法性来源于晋察冀边区政府,因此,其领袖即新的乡村精英必然积极配合政策需要,并为边区政府的乡村动员提供了组织渠道。《穷人乐》的两大主题即穷人“翻身”与“组织起来”,反映的正是这一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对不同人的意义不同,所以我们需要考虑社会结构。
村庄旧有的权力架构被取代了,最明显的是地主的角色被边缘化。晋察冀时期,高街村大部分土地名义上仍然属于五台山台麓寺,该寺是康熙年间敕建的喇嘛庙,台麓寺喇嘛首领的地位仅次于五台山菩萨顶大喇嘛,因此民间俗称之为“二喇嘛”。1938年尽管二喇嘛当选为晋察冀边区议员,但他却无力维持旧的乡村秩序。在晋察冀二五减租的政策下,高街村佃农们不仅少交租粮,免除了租草、粮料、杏核、核桃、花椒、栗子等负担,而且享有“永佃权”。“要入农会,农会才给做主,要不入农会,农会可不管”,高街村的农会就设在原来喇嘛收租的柜房里。*黄金涛整理:《八路军抗战文艺作品整理与研究(话剧卷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7-168页。农会使得喇嘛地主失去了对佃户的控制,佃户拒绝交租的现象增多,例如以1939年边区大水灾为契机,据说许多佃户“无法交纳租子”*戴烨:《五台山和尚喇嘛负担问题的解决》,《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1年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324-326页。。1940年年底日军大扫荡时,台麓寺被焚烧一空,边区政府及五台各界去慰问时,庙里的一个老喇嘛表达了改过自新、配合政府的立场,县农会主任则表示敦促会员交租,第二天,在五台山的反投降群众大会上,果然有不少农会会员背着租子来交租。*台山:《五台山下蒙汉民族的亲密团结》,见《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1年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83-84页。
随着地主势力的消退,旧的庄头被新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取代。之前寺院地主收租需要庄头催收,庄头多是父子相继,其经济状况优于一般佃户。*福田喜次:《山西省五台山の寺领地について》,《满铁调查月报》,第22卷第4号(1942年)。根据笔者的访谈,高街村庄头齐家是全村唯一供奉祖先图的人家,这也是其地位的体现。*受访者:李逢泉,受访时间:2017年9月17日。李逢泉称此祖先图为“灵牌”。边区成立后,庄头被取消,新式机构的首领即村干部成为新的村落精英。这些干部多有打工或做生意的经历,所以他们比一般种田的佃户见识广、能力强,例如《穷人乐》中的主角、合作社主任陈福全即是。陈福全大约生于1901年,19岁租种过地主的坡地,25岁当了长工,曾短暂跑过一次“口外”,并曾因遭水灾而卖了6岁的女儿。边区成立后,他由长工变成有产者,并被选为工会干部,曾领导雇工,向地主作斗争,可谓是“翻身”的代表。
陈福全最主要的事迹是办理村民自愿入股的合作社。根据报道,高街村合作社成立于1940年,头几年经营不善,1944年2月陈福全当选合作社主任后,清算糊涂账,分派红利,扩充股份;到区合作社借款买地瓜救济灾户,又资助部分村民卖豆腐、作运销;另外还收买废铁,统一订制农具,低价卖给村民;借出春耕籽粮,保障生产。除了调剂物资,合作社最重要的功能是组织全村的劳动力。入社的男劳力统一分派工作并算“工”,谓之“拨工”,每10天用实物或现金清算一次;入社的女劳力主要是做军鞋,由合作社低价供给原料,统购统销。*周钧:《阜平合作英雄陈福全》,见《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82-184页。《穷人乐》第7-14场反映的就是合作社组织村民集体劳动的场景。此外,合作社兼具许多社会职能,例如优待抗战家属(优抗)、教育、卫生、文化活动等。在优抗方面,抗属买东西、籽种、农具有优惠,抗属的积肥、刨荞麦有社员帮忙。在教育方面,在四四儿童节购买纸笔奖励模范儿童,鼓励群众上民校学习认字。在卫生方面,社员每天需打扫房院、街道,每户都要建厕所和猪圈以积攒肥料。文化方面,陈福全是高街村剧团的团长,创作出了《穷人乐》等多部作品。当然,在领导合作社的过程中,陈福全自己也受益了。1944年他家多打了六、七大石粮食,增加现金收入3000元,由贫农上升为中农;同时因为办合作社成绩显著,他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合作英雄,获得边区领导接见。*周钧:《阜平合作英雄陈福全》,见《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上),第185页。
积极响应边区号召,贡献突出者往往获得劳动英雄、合作英雄、拥军模范等荣誉称号,这在乡村是很大的荣耀。在高街村,这样的人物除了村干部陈福全,还有拥军的李盛兰。他出生于1899年,“无房产,无土地,耕种租佃”。1927年三月初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他的母亲和两个女儿在土崖下刨树根当柴烧,发现了藏在瓦罐里的古铜钱,总共约800斤。他没有将古钱卖给民国阜平县政府、博物馆等试图低价收购的机关,却于1943-1944年间无偿把古钱献给晋察冀边区政府。军区代司令程子华为此专门设宴款待他,程子华在邀请信中尊称他为“先生”,并赞扬他捐钱资助抗战的慷慨之举。*1944《穷人乐》剧本已提到献古钱一事,而据《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48页)载,1943年程子华始任军区副政治委员,1943-1945年在军区主要领导聂荣臻、肖克赴延安期间先后任军区代政治委员、代司令员,据此推测献古钱应该发生在1943-1944年间。此事在1944年被抗敌剧社编成快板《李盛兰献古钱》,其中有段描述他进军区的情形:“军区把我请了去/首长们和和气气/亲亲热热拉着我的手/打问了孩子大人的身体/跟我说了不少家长里短/国内国外的大问题/给了我不少帮助和教育/招待的好饭食强/因我不动荤/特给摆素席/首长们陪着我吃饭/照顾的好实在没说的/临走时给了我匹大骡子/诚心实意让我牵回去/我牵着骡子刚要走/首长打敬礼!/一个同志高举照相机/“卡登”一声把我照在里/我老汉心眼里“合碰”、“合碰”真是欢喜/牵着驴子我离开军区/边走边笑我挺高兴/骡子都没舍得骑/心里思摸着/村里要是知道这个消息/干部迎接在区里/乡亲们拍着巴掌待鼓励/这真是件光荣事/谁会看不起。”*车毅:《李盛兰献古钱》,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1946年,第13-14页。干部迎接、乡亲鼓掌,让他觉得“谁会看不起”,可见献古钱提升了他在乡村的社会地位。
高街村还有其他几位政治觉悟性比较高的干部也与《穷人乐》有密切关系。李盛兰堂弟李英兰是阜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李英兰的父亲李老七在根据地成立之后领导演戏,宣传减租,“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在《穷人乐》中他带领佃户向喇嘛抗议加租,甚至要拉上喇嘛到城隍庙去盟誓,是觉悟农民的代表。*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27页。另外排戏的关键人物李又章,1944年从高街村调到阜平二区(治所在高街)青年部任职,他与抗敌剧社、区干部、村干部一起拟定演剧的主题、内容及编排,安排剧社进村后的住宿、找人等所有的细节。第一次村里演出被批评后,他率先反思自己没有走群众路线的缺点,可见其政治敏锐性相当高。
新崛起的干部、模范构成了高街村剧团的骨干。尽管本地有年节闹红火的风俗,村民会扭秧歌、唱小曲,也有人会打快板,但从下段引文中“团员中没有一个会搞旧玩意儿,也没演出过旧东西”以及缺乏乐器人才判断,高街村以前不存在旧剧团。高街剧团是在晋察冀根据地成立后才出现的,曾演过减租的宣传剧,并于1940或1941年重建。*程凯:《“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人间思想》第5辑,第107页。1944年12月《穷人乐》大获成功后,负责排演的文艺干部张非简述了该村剧团的历史:*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3页。
高街村剧团成立至今约四年,配合中心任务自编自演经常活动,专业剧社曾陆续帮助过,但外来剧本演出并不多。团长陈福全,副团长抗联组织部王朝金(女),正式团员三十余人。村各部门干部参加者约一半以上,青妇、青壮年、儿童比例差不多,不识字的很少,平均初小二年级的程度。……在艺术上,团员中没有一个会搞旧玩意儿,也没有演出过旧东西,对演出活报剧、小调剧、秧歌舞形式很喜欢,并能自己搞,就是缺乏编剧与乐器人才。现因与冬运结合,学习空气很浓,每次排戏之前都有人在学算盘,或识字读报。此外,在各方面,可经常得到区宣教委员会的帮助。
从村剧团的构成来看,一半以上是村干部,另一半则是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人和儿童,实际上囊括了村里最具有政治觉悟、最容易接受文宣影响的群体。从剧团的活动内容看,他们接受过专业剧社、区宣教委员会的指导,演出也主要是配合政策进行,成员参加冬学看报等。高街村剧团作为村里的宣教机构,它以干部、模范等新的村落精英为主导,承担着乡村社会动员的任务。
新的社会结构中,除了少数的干部、英雄、模范之外,还有作为社会动员对象的普通村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高街资料中的村民多是新式组织之下的村民,内容多是他们被组织起来后发生的积极、正面的变化。例如1945年大生产运动的总结报告显示,高街村通过合作社社员之间的相互“拨工”、“返工”,减少了原来普遍的私人雇佣行为,并且使病患户、受灾户、军属家庭得到一些救助。*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实业处编:《1945大生产运动参考材料》(1946年1月30日油印本),第辛8页。《穷人乐》表演的重点之一也在于军属、光棍、寡妇等特殊家庭如何通过参加合作社解决生活困难。除了将普通村民组织起来,合作社还积极改造“懒汉懒婆”等边缘群体,例如有一户好吃懒做,但曾经杀过羊,于是合作社帮助他开肉铺,同时为了克服他好吃的毛病,干部和他同吃住。*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实业处编:《1945大生产运动参考材料》,第辛8页。有些边缘人往往被冠以贬意的绰号,例如“懒婆”池占贞、“肮脏鬼”安国花被妇女组组长拉进做鞋组,学会一技之长,成功改善了生活。*周钧:《阜平合作英雄陈福全》,见《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1945年卷上),第184页。《穷人乐》中也有好吃懒做的“万年穷”曾去合作社贷粮当口粮,被大家嘲笑,最后一场他却背着粮食来交公粮。当然,《穷人乐》考虑到当事人的面子,多用绰号影射的方式表达,如果需要出场也往往由其他人代演,目的是希望通过演剧改造这个群体,例如“懒汉”张风旗就是看了戏以后,才参加拨工组的。*曼睛:《晋冀区一年来的乡艺运动》,见《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可以说,资料中的普通村民,都是在社会动员的大背景下呈现的标签化的形象。
资料的文宣性质显而易见,只报成绩不报缺点的偏颇,以及明显配合政策(如“改造懒汉懒婆”运动)的报道风格让读者有理由怀疑其夸大事实的可能。不过,文宣本身是社会改造的一种途径与方式,具体来说是晋察冀根据地以及村落精英阶层试图宣扬新式机构的有效性及新秩序的合理性,他们描述的群众热切参与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乡村秩序图景,其目标受众更多是那些有待被改造的村民。高街村剧团作为新的乡村组织,其政治性质、人员构成、节目创作等都应置于新的社会结构的脉络下进行考察。从“翻身”到“组织起来”的《穷人乐》叙事,正是这一新的乡村社会结构自我表达、自我巩固的需要,这是演剧能够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社会背景。
二、专业剧社下乡与村剧团的改造
1944年《穷人乐》创作的直接契机是抗敌剧社与高街村剧团两种文艺团体的互动。抗敌剧社原本是1937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宣传队的别名,演员都是宣传员。初期上演的都是大后方流传过来的剧目,虽然1939年剧社社员开始自己编一些活报剧与话剧,但样板色彩较重,并没有紧密结合乡村实际生活。1942年毛泽东发表延安文艺讲话,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领域迅速开展下乡体验生活及“群众路线”的整风。*韩塞:《回忆抗敌剧社与晋察冀边区戏剧运动》,见《抗敌剧社实录》,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9-120页。蔡子谔:《简论晋察冀群众文艺运动的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柳敏和、关翠霞:《试析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乡村文艺运动的经验》,《党史博采》2012年10月。此后,到农村“深入生活”逐渐成为抗敌剧社的基本创作方法,其作品也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1944年初,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英雄模范代表会议结束后,剧社派出一批创作人员,分头到一些英模的家乡去生活、采访和创作,同时更加重视辅导农村剧团的活动。*胡可:《实践中学习的十年》,见《抗敌剧社实录》,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2-77页。尽管抗敌剧社主导了《穷人乐》作品的创作,但在当时突出“群众路线”政治氛围下,所有报道都在强调高街村剧团自发的政治觉悟,《穷人乐》是村剧团基于“真人真事”的集体创作,抗敌剧社只是一个时常犯“形式主义”错误而需要被农民教育的辅助角色。*程凯:《“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人间思想》第5辑,人间出版社,2016年,第99-133页。事实上,这出戏剧是两个剧团互动下的产物,它固然“教育”了专业的抗敌剧社,但同时也“教育”并改造了村剧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
抗敌剧社总共来了高街四次。1944年10月中旬,抗敌剧社副社长汪洋带领剧社成员张非、林韦(女)、车毅(女)、华江(女)等人第一次来到高街村。*高明乡主编:《老区阜平红故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称一共来了7人,而张非的回忆文章称是5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2页。此行的直接契机就是当时区里召开宣教会议,要高街村演两个节目,并藉此“指导乡艺创作,培养训练乡艺干部”。抗敌剧社的最初意见是排一个现成的剧目《问路》,再帮村里现编一个,如果编不成,就演另一个现成的《兄妹开荒》,主题是抗战前后的生活对比。抗敌剧社的张非、区宣教干部谷惠、区青年部干部李又章,以及高街合作社主任陈福全、高街滩委会副主任(农会主任)兼剧团指导周福德等几个人在河滩的打谷场上商讨戏剧的内容,这时周福德提出演个《穷人乐》,得到大家赞同。
抗敌剧社几位年轻人初来乍到,他们首先接触的是剧团干部(同时也是村干部),搜集资料也局限在几个干部身上,包括合作社英雄陈福全、农会主任周福德、区干部李又章,以及儿童拨工组组长、妇女做鞋组长等人。到高街的当天晚上,剧社和村干部陈福全、周福德、李又章等人谈到深夜,主要是关于合作社的具体运作。至于抗战前喇嘛剥削的情形,几位干部都语焉不详,因为彼时周福德是做小生意的,陈福全当长工,李有章出身中农而且年纪小,所以他们只能描述喇嘛入村时作威作福的场景,而无法描述剥削的细节。*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5-7页;又侯金镜《在帮助〈穷人乐〉排演中教育了我们自己》,《晋察冀日报》,1947年增刊第7期,侯金镜的论述似是引自张非的总结,但根据张非的原文,第一天晚上讨论者有吕福才而无李又章。由于缺乏剥削资料,剧社的张非等人决定将战前受剥削的部分作为背景简单交代一下,让虚构的佃农马如龙用一段快板带过,重点则放在合作社的“乐”上。张非很快拟好了剧本结构,同时把《穷人乐》改名为《高街合作社》并加注“又名《穷人乐》”。*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6-8页。
在抗敌剧社与村剧团在谋划《穷人乐》编演的同时,抗敌剧社的林韦、车毅、华江等三位专业女演员和高街合作社的妇女率先创作了独幕剧《高街做鞋组》。*汪洋、林韦:《培养我们成长的抗敌剧社》,《抗敌剧社实录》,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92页。高街军鞋质量据说是阜平县第一名,妇女做鞋有了些许收入,提高了家庭地位,也改善了婆媳、夫妻关系。*汪洋、林韦:《培养我们成长的抗敌剧社》,《抗敌剧社实录》,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92页。在高街陈福全与妇救会主任的支持下,林韦与妇女们座谈后,写了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一个剧本底稿,并由妇救会主任出演被改造的懒婆。妇女们提出她们平时高兴时就唱,林韦于是写了赞颂高街鞋的一首歌,由张非谱曲。这首歌成为《高街做鞋组》的一个高潮,后来“流行在每个妇女的口中”。*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30页;苏叔阳、石侠编撰:《燃烧的汪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页。2017年笔者在高街访谈时,仍有年老妇女可以唱出这首歌。该剧除在本村演出以外,也进城演出过,也与《穷人乐》同时演出过。与此同时,车毅还将本村拥军模范李盛兰的事迹编成快板《李省兰献古钱》。这些戏剧的故事和演员虽然来自高街村,但无论是剧本还是歌曲,都由专业的抗敌剧社创作。
只有专业剧社才能将高街村的“真人真事”赋以时代主旋律,从而创作出符合社会动员需要的剧本,以及训练出能够进行社会动员的村剧团。开始排演《穷人乐》过程中,高街村的干部、演员必须学习如何“真实地”呈现自己的劳动、生活甚至情感。在台词方面,演员们学习如何在舞台上说话,台词由演员现编,或由旁边的干部周德福、陈福全口授。在过程方面,比如排演春天饥饿的情节,本来应该说话动作没有力气才对,演员却很愉快的说着合作社如何好,如何解决困难的话。“因为事实上现在吃饱了,他不愿再回到过去的样子,又因为对演戏看作是闹红火,像不像也不太注意”,所以,张非他们提醒演员不要忘记当时当地的情形。在动作方面,演员一开始动作很僵硬,不知道如何“拉架势”,张非就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生活”。在舞蹈方面,尤其在表现打蝗虫、挑稻蚕等集体劳动场面时,干部李又章等改造了劳动动作的节拍,配上锣鼓,使之具备舞蹈的感觉。在歌曲方面,采用村民平时就会的《七月小调》等,再修改一下歌词。从这些表现看,“真人演真事”的模式并非是对过去的简单呈现,而是包括对干部和演员的改造及训练。
整部戏两天就排练好了,但是村剧团的演出仍然暴露了太多的问题。第一次演出就在高街本村,主要的观众就是本村村民及阜平二分区的部分干部。在抗敌剧社的张非看来,村剧团的演员们太过于“混乱”和“随便”了:
村剧团从来没有排演过这样长、人这样多的戏。许多演员都是第一次上台,并不清楚舞台位置。妇女不愿化妆,特别不愿化妆老娘娘,因为是真人演真事,大家都说“就这样吧,不用化妆了”,所以只有几个老头化妆了。第一场本来该穿破衣服饥饿的样子,大多数都没有带破衣服(服装道具都是自己用什么带什么)。这说明了当第一次演出时,演员在认识上还存在着“闹红火”、“玩一玩”的观念,对于如何更真实的表现生活认识不足,因此有的在台上笑场、忘词,跟排戏一样。
由于村剧团还是“闹红火”、“玩一玩”的观念,所以张非从专业的角度,认为化妆、道具都不符合要求;他们在舞台上说的话常常主次不分,易于混乱,再加上笑场、忘词,极大地破坏了整个戏的感情和效果;他们随意走来走去也使得场面很凌乱,破坏了舞台画面的构图。*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15页。
艺术上的失败也就罢了,更大的问题是表演的内容受到非议,并随即演变成政治问题。原本演佃户马如龙的演员在台上说一段快板,简单叙述抗战前遭受喇嘛苛打和加租增佃,被迫折变牲口,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等悲惨生活。有村民认为老头老婆、懒汉懒婆适合说快板,而正经人物不适合说快板,而且认为没有把喇嘛责罚佃户的细节演出来。有村民说:“没有阴天,就没有晴天!你们年轻不知道,你爷爷他们受喇嘛的苛打可厉害呢!”尽管如此,剧团从艺术角度考虑,并没采纳这些意见。*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17页。原本是技术性的处理,随后演变成了阶级立场的问题。他们被举报不尊重佃农的意见,所以李又章不得不专门写个报告,并反省说:“我的出身是中农,又没经受过喇嘛或地主的剥削,闹剧团过去不十分尊重群众的意见,群众几次提出要加上喇嘛剥削一场,始终没有采纳,抗战前村里群众绝大多数是佃农,只有两三家是中农,还怕演了那段没人看。”接着在北岳区三专区专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他们被批评“民主精神还不十分够”,“群众的立场还不坚定”。看到文艺座谈会将此事上升到阶级立场的问题,负责编剧的张非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后来在文中也做了自我检讨:“我是小资产阶级学生出身,没有受过什么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懂得一点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在革命队伍里工作了,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对于农民的减租等斗争亲身体验很少,因此对于群众非常关心的‘喇嘛逼租’的一场戏,轻轻地取消之后并不以为怪。”形势至此,加上喇嘛一场戏就变成了政治任务了。
文艺座谈会后,李又章带着这项“政治任务”回到了村里,随后的11月20日,剧社的汪洋、张非等也第二次来到高街。他们需要设法把喇嘛逼租的情节演出来,首先采用的是第一次的结构,即佃户无法交租,庄头建议变卖家产儿女,然后是喇嘛坚持增租,百姓跪请等。张非觉得这个结构平淡而又苦于无法改进,于是要求本村出身的李又章负责排演。李又章吸收了部分村民的意见,增强了“逼典”时的戏剧性,例如喇嘛逼租要一句比一句紧:“你不是还有一口猪吗?”“猪早就折变了顶饥荒了。”“你的一头驴呢?”“唉!这不是那头卖驴的钱呀!”“我给你出个好主意,把你那个闺女聘了吧!”这样一改,观众反映“喇嘛演的像”,“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差!”据说还有人落泪的。由于村民接受,所以这一关算是通过了。随后,在县群英会又演出了一次,边区领导胡锡奎及其他很多人,建议把边区政府成立后如何减租减息、组织村选、带领佃户“翻身”的过程加进去。另外,由于面对的观众超出本村范围,剧里的许多名词、人物、事件都要加以解释。如此一改,整个剧本长度增加一倍不止。
抗敌剧社张非等人觉得既然边区领导认可了这部戏,就应该把《穷人乐》的“萌芽状态”再提高一步,改编成歌剧,由专业剧社自己演。张非等人第三次来到高街后,他们带着拟好的结构提纲,念一段情节就请村干部陈福全和周福德给编一段对话,由于进展极为缓慢,于是剧社就希望先把歌剧剧本写好,再让干部帮忙改成“老乡话”。改写剧本时,他们打算把高街群众的苦乐都集中在一个家庭、一个人物身上,或者把其他合作社的特点集中在陈福全身上。就在这时,他们听说了一件事,原来另外一个专业剧社“群众剧社”捷足先登,把他们曾经演出的《穷人乐》改编成了《陈永福合作社》,增加了很多自己设想的故事情节,结果引发了很大争议,被批评失去真实性。于是抗敌剧社自己写歌剧剧本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由于《穷人乐》需要大幅增加内容,抗敌剧社决定当务之急是先帮助高街村剧团排演,于是他们在副社长汪洋带领下第四次来到高街。为了补充材料,他们在村里找了几个亲身体会过喇嘛剥削、卖过儿女的老头,当谈到卖女儿时女儿不愿去,用绳子捆到驴背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哭了;当谈到喇嘛凶狠的样子“我就是为了要吃肉,吃了肉啃了骨,啃了骨头汤儿也要喝了”,所有人都很愤怒。这次他们发现不仅是喇嘛这场戏,原来其他各场也有了新的启发。例如他们最缺乏资料的是“民主大选举”,忽然有一天听到村干部周福德、吕福才聊天,谈起那年放羊的、打铁的、拐子、瞎子都去参加选举,妇女们没名字,写公民榜的时候都坐在一个大院子里起名字,许多老太太都起了小姑娘的名字,大家笑了一整天。*侯金镜:《在帮助〈穷人乐〉排演中教育了我们自己》,《晋察冀日报》1947年增刊第7期。此类鲜活的细节给剧社同仁很大启发,于是很快所有剧本情节都备齐了。
经过抗敌剧社与高街村剧团的几次修改,《穷人乐》剧本最终定型为14出,分别为:(1)加租增佃,卖儿卖女;(2)中央军南退,八路军北上;(3)减租参军;(4)军民合作拉荒滩;(5)民主大选举;(6)反扫荡;(7)贷粮救灾,组织起来;(8)春耕;(9)陈福全拨工组;(10)儿童拨工组;(11)打蝗虫;(12)战斗生产结合;(13)挑稻蚕;(14)穷人乐。其中(1)-(6)主题是“翻身”,(7)-(14)主题是“组织起来”。在表现形式上,《穷人乐》以话剧为主并糅合了多种艺术形式,当时阜平县的一个文艺座谈会指出《穷人乐》“在形式上是一个创造,有歌有快板,有话剧也有舞蹈,‘大杂烩’的方式”,“各种形式‘一合摊’,不拘形式,又跳又唱又说又扭”。*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19页。
为了改变高街村剧团在舞台上的“混乱”和“随便”,张非等人要求:“要按剧本排演,上台不许多说一句,也不许少说一句,更不许乱说。这次要用布景演出,不许乱走,叫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叫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不可以随便。”他们一句一句地读剧本给演员们听,发现演员根本记不住,于是有人提议边排练边记词,可是又有了新问题,张非回顾说“我读一句词他们跟着学一句。有几个也就撇起京腔来了,有的是光为记词忘了动作,有的是光记住位置忘记台词。”*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21页。最后排的人、演的人都急了,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不能用专业剧团的排演方法去要求村剧团,不能用剧本台词来限制演员,又认为第一场之所以难排,是因为演员们没有亲身体验过喇嘛的剥削,演自己不了解的生活比什么都难。*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21-22页。于是当天晚上他们请两个老演员细细地讲被卖的女孩“二荣子”该怎么哭,她的母亲该说些什么动人心的话,并强调说“这一格截戏要把人拿住才行”。演员逐渐进入情境,果然在最后一次排练里,他们不再笑场了。
有必要评估一下高街村剧团和抗敌剧社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村剧团的“混乱”与“随便”保留了下来,反复挣扎在“群众路线”与专业标准之间的抗敌剧社不得不接受村民演戏的一些特点,例如“群众极端尊重事实,特别是生产问题在季节上不能混乱”;“群众很喜欢歌唱,他们把自己学会的歌子只要能用上的都用到戏里”;“群众对上场门与下场门记得很死,不能改变,他们说一改就乱了”;“陈福全因为去参加边区群英大会,由区干部谷惠来演,但是和大家在一起很不调和,很不自然。老乡说他说的是‘干部话’,不是‘庄户话’”等。从这些特征来看,村剧团仍保留明显的“村”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专业剧社的指导下,演员们逐渐学会“回到生活”,将他们已经忘却的甚至是不了解的生活重新拼接,他们进入了情境以至于最后不再笑场。周维东敏锐地指出,《穷人乐》的排演有“塑造”演员的功能,他们由此学会释放情感、嫁接情感,从而实现自我教育并训练成为“革命群众”。*周维东:《被真人真事改写的历史——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经过训练的干部演员能够说出来一些很有水平的台词,例如第二场,周福德说:“农会就扎在喇嘛的柜房里”,李又章说:“周福德咱们磕头罚跪可也在那个屋里呵!”周福德说:“咱们翻身也在那屋里!”如果没有村剧团的这些演技,是不可能“把人拿住”的。经过这番训练,高街剧团才有能力编创多部戏剧,成为颇有影响的先进村剧团。
三、《穷人乐》的演出与社会动员
第一次表演《穷人乐》是在高街村,观众除了二区各村干部外,绝大多数是高街村及附近的村民。观众们对干部上台很惊讶,对表演自己生活的内容也很意外,于是纷纷评头品足。看到演自己的事的时候,他们就不由得笑起来了:“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差”。在“锄草”的那一场,演员没有注意,锄得很乱,一个老太太就在台下说:“唉!那不把苗锄瞎了吗?”观众看到“打蝗虫”时说:“就是这样打。”有几个人不注意乱打,观众在台下就说:“把苗踩坏啦!”张非评论说,这个戏演了一个钟头,观众仿佛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了。*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15-16页。可见“真人演真事”的表演,调动了村民的切身经历,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感。在《穷人乐》之前,很多村民抵触演戏,这次演出之后,很多人要求上台“乐一下”。有外村的干部们说:“这个好闹,咱们回去也演个《穷人乐》!”有些平常不喜演剧的人也说:“要不要咱们也乐一乐呀!”据说高街村长金凤圆以前不关心村剧团,这回也主动参加了演出。*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11页。
显然,第一次被搬上舞台的《穷人乐》面临村民的两种反应。一方面,他们是观众,普遍将《穷人乐》与普通社火表演等同看待,视为“乐一乐”、“闹一闹”,看戏时的情绪十分欢快。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有待被动员的群众,“真人演真事”的直白表演让村民有些惊讶,至少对部分村民而言,他们感到需要进行某种表态:*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16-17页。
许多贷粮户说:“这个戏是实事,今年合作社和往年不一样,真救了咱们。”“陈付全办合作社就是不一样。”一个贷黄豆磨豆腐救活了一家的老太太无限感激地说:“上大园村社主任反映,这比陈付全作一个生产总结报告还详细哩。”妇女们做鞋更有劲了,三百双军鞋的任务谁也不发愁,早早地就到合作社门口等着开集买东西。
表态的观众主要是从合作社受益的群体,包括贷粮户、贷黄豆磨豆腐的老太太、买材料做鞋的妇女等。这些观众看完了戏,很敏锐的意识到这是合作社“陈福全的生产总结报告”,所以他们表达的不仅是看戏的感受,而且还是对合作社的态度。村剧团和观众的关系,其实也是干部尤其是合作社和群众的关系。
第一次修改(即增加了喇嘛逼租的情节)后演了两场。首先是在阜平二区的高街村,这次的表演也是配合二区正在召开的群英会。至于观众,应该和上一次差不多,即主要是高街村人、二区干部与劳动英雄。这次表演内容与上次相比主是把喇嘛逼租加进去了,虽然经过一些艺术加工,观众纷纷反映:“喇嘛演得像”,“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差”。接着又在县群英会演了一次,观戏的各区劳动英雄都觉得“不带劲”,在边区领导胡锡奎的提议下,增加了“翻身”为主题的几场戏。
第二次修改(补充生动的细节)后,终于到了1944年12月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大会在阜平县家北村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参会者是来自晋察冀边区数十个县的劳动英雄及各单位的干部。该戏连演4场,其受欢迎程度远超预期。第一场喇嘛逼租的部分尤其引发了观众共鸣,英雄模范们看到剧中人物痛苦时都哭了,都说抗战前高街人受的苦,都是大家所受的苦,也是代表大家说了话。*韩塞:《回忆抗敌剧社与晋察冀边区戏剧运动》,《抗敌剧社实录》,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亲身受到压迫的英雄哭得最痛,忻县的一位劳动英雄噙着泪花说:“早先世道就是这样,我小时,连个屋子也摸不着,在毛野地还不如一个狗哩!”繁峙劳动英雄耿金旺说“我当了十八年长工,有一回给东家摘杨叶,从十来丈高的树上摔下来,吐了半盆血,‘算盘珠儿’跌歪了,那时没有吃的,差些没死了。”不禁噗噗地落下泪来。但当演到“减租参军”、“组织起来”以至“穷人乐”时,都止不住高兴地大笑起来。*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27页。劳动英雄们不仅发表感慨,而且多表态要学习高街剧团。垅华县的英雄集体写作了一篇《看了〈穷人乐〉以后》,投稿到大会办的刊物《大会生活》第3期,表达了回去要把村剧团办起来的决心,干部也表态回去参加演戏,练练讲话。*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28页。
这次表演是整个高街村剧团最辉煌的时刻,他们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村剧团都不曾得到的荣誉。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与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了演员,首长们亲自陪他们吃酒,新华园澡堂请他们洗澡。边区首长如胡锡奎、宋劭文主任、于力副议长、抗联王主任都发表讲话鼓励,抗敌剧社社长汪洋也感谢高街剧团帮助文艺干部整风。*张非、汪洋:《〈穷人乐〉的创作及演出》,张非:《偏套集》,三乐堂编印,2008年,第30-31页。随即中共晋察冀分局作出了表彰、推广高街村《穷人乐》的决定,认为《穷人乐》实践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它将创作过程和演出过程相结合,表现本村群众的斗争生活,代表了群众文艺路线的新方向与新方法,从而要求各级机关、宣教部门、文艺团体认真学习推广。*《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1944年12曰23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中),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008页。紧接着,《晋察冀日报》也发表了长篇社论推广“真人演真事”的创作方法。*《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1945年4曰2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汇编》(中),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010-2013页。此外,边区政府还将《穷人乐》剧本编入文艺丛刊第一册出版,并赠送高街村剧团幕布一块。*崔少宏:《抗战乡村剧团的历史见证——阜平高街村剧团的一件幕布》,《文物春秋》2001年第6期。
从边区群英会演出回来后,不仅干部们深受鼓舞,其他村民也认为是莫大的光荣,于是又有十多人要求加入剧团。高街剧团在此后一年间,密集推出了许多新作品,例如元宵节时几位老年妇女创作的《拉小车》受到观众及文艺干部的好评。*曼睛:《晋冀区一年来的乡艺运动》,《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高街村剧团的戏剧创作与表演成为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曼睛:《晋冀区一年来的乡艺运动》,《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28-329页。
阜平高街《穷人乐》演出后,村剧团已成了群众自己的文娱组织,成了高街推动与指导各种工作的有力武器。在正月进行拥军时,他们演出了优待抗属剧,表现了本村优抗模范刘如琴和邢门荣,该剧演出后,群众纷纷议论说:“咱们可是向人家学哩,也得争取个模范上上戏”,之后,群众自动给抗属打柴七千斤。在大生产运动开始的时候,村剧团演出《全家忙》和《耕二余一》,不仅推动了本村的大生产,而且连懒汉张风旗看了戏以后,也自动参加拨工组,积极的生产。在春天天旱不雨时,他们及时演出了《不能靠天吃饭》,打破了群众靠天吃饭的思想,提高了群众向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全村组织了大拨工,不多几天三百八十多亩岗地全部完成了播种。在“七大”宣传时,他们演出了《幸福是谁给的》一剧,群众看了普遍的开展了回忆运动,都一致的说:“要不是八路军和共产党,咱们凭什么有今天的生活呢?”“跟着毛主席吧!没有差。”日寇投降的消息传到该村时,合作英雄陈福全马上集合了团员到副村进行宣传,一早上演了两个街头剧,饭也没顾的吃又到十五里以外的龙门、沙地一带进行宣传,使我们抗战胜利的消息很快的让二区群众知道了。他们不仅演完剧即算完事,而且团员还在实际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如在防旱备荒中演剧之后第二天就挑水播种,群众见了,也跟着干起来。
高街村剧团与以前不同的是,它“已成了群众自己的文娱组织”,这句话实际上有两种意思,首先是剧团的群众基础在扩大,越来越多的村民被吸纳进这一“先进组织”。这些村民不仅是剧团演员,同时还“在实际工作中起模范作用”,例如在防旱备荒演出后带头挑水播种。其次,演剧已然成为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因为村民不仅是戏剧的观众,同时又是政策宣传的对象;村民观戏不仅是一项娱乐活动,同时也是参与一项政治活动。演剧之后,往往伴随着实际的乡村动员,例如给抗属砍柴、参加拨工组、进行“回忆运动”、防旱备荒等。不难理解,在表演后,“观众”立即转为“群众”,往往都自发的以语言或行动表示对政策的拥护。
演剧能够用于社会动员,从观众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它是一种施加规范的方法。它直白地宣传“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积极响应政策者是“先进分子”,否则即是“落后群众”。这种标杆对观众而言是一种道德示范,尤其是带有强烈影射色彩的“真人真事”的表演,将“地主”、“懒汉懒婆”等体制异类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是一种舆论压力与政治压力。这种情况不仅在高街村,在晋察冀其它村也常见,例如平山县柴庄村即是。该村剧团配合优抚工作演出了《炕头会》,以假名的方式揭露了个别村民的“蜕化现象”,说某村民娶了媳妇,有了几亩地,以为革命成功了,工作越来越不努力,村长派他家一顿饭,他自己吃扁食,给八路军赶杂面,剧中要求该村民“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改善的好光景。”连演四次,结果被影射的村民找到剧团认错并表态,优抚工作有了大转变,据说五位落后的群众,四位被这幕剧改造了。*曼睛:《晋冀区一年来的乡艺运动》,《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29-330页。这些转变的案例说明《穷人乐》开创的“真人演真事”的模式模糊了演剧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使得观众无论自觉与否都必须参与到社会动员中来,从而达到规范异质因素、强化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高街村剧团的成功刺激了晋察冀边区乡村剧团和和社会动员的发展。一年之间,“晋冀区的乡艺运动已成了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各县共出现了1381个乡村剧团。这些剧团全年不断地演出,尤其在集市、庙会的场合还有各剧团联合公演。*曼睛:《晋冀区一年来的乡艺运动》,《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25-331页。当时阜平全县200多个行政村都建起了文艺宣传队,“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敲起脸盆都能唱几支抗战歌曲,演一折抗战小戏,村戏活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高明乡主编:《老区阜平红故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2页。乡村剧团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社会动员,例如,河北容城县五区王路村借鉴了《穷人乐》的模式后,将本村劳动英雄金木山的事迹编成了十余场的长剧,村干部亲自排演,老乡们看了戏,都说“戏上都敢演,咱们怎么不找石二阎王(戏中之地主)算算账去?”村干部稍微组织了一下,就有四十多位骨干,带动了二百多号人,浩浩荡荡奔到地主所在的郑村,口号喊得震天响,非叫地主把放高利贷押的红契文书交出来不可,甚至戏中金木山被地主抢去的大车和工具都要回来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报道说得十分精辟:“未完的戏,到这里才闭幕”。*胡苏:《〈穷人乐〉方向在容城的实践与发展》,《平原杂志》1947年第6期。从另一个方面说,这出戏刚刚开始,因为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以“翻身”为武器,将矛头直指地主,显然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农村土地改革打下了群众基础。*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60-365页。
四、结 语
高街村《穷人乐》的个案显示,晋察冀根据地的乡村剧团与社会动员的关系可以从社会结构、演员、观众等三个层面理解:
首先,晋察冀根据地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是乡村剧团发挥社会动员功能的基本背景。村剧团作为新的乡村组织的一种,其成立初衷就是配合政府的宣教工作;它的成员包括各级村干部及青年积极分子,他们需要经常阅读报刊,熟悉时政;它的工作重心是通过演剧配合政策宣传、发动群众、促进各项工作。《穷人乐》受到的表彰无疑强化了村剧团及其成员在村里的政治地位。
其次,乡村剧团囿于文化水平、政治觉悟等诸多短板,它需要被改造和提升。被赋予重要政治任务的村剧团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文艺干部和村干部,不能理解普通群众的感受,缺乏民主作风与群众路线;剧团成员把演戏当成娱乐,认为是“闹红火”、“乐一乐”;剧团演员不会演“自己不了解的生活”等。这些都是村剧团在编演《穷人乐》的过程中努力克服的问题,演员们在排练中接受了改造,政治觉悟和自主编演戏剧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第三,乡村剧团对观众(群众)的影响需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下考察。看戏本是乡村的娱乐方式,但同时也有其政治功能。戏剧观演调动了观众“苦难的”生活经验,俨然就是一种集体的“诉苦”;村民观看“翻身”与“组织起来”,无疑是接受既有社会秩序合理化的宣传;同时,他们也受到戏剧宣扬的价值标准和舆论压力的影响,而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政治表态,并参与到具体的动员行动中。
乡村剧团对于根据地政权、村落精英、普通村民有不同的意义:根据地政权需要培训乡村剧团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村落精英需要演剧以合理化新的乡村秩序并表达政治忠诚,普通村民则通过看戏获得娱乐并成为社群的一部分。尽管村落精英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并不垄断对戏剧的理解和表达。与其说乡村剧团是某个群体专属的工具,毋宁说它为新时代的国家-社会互动搭建了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