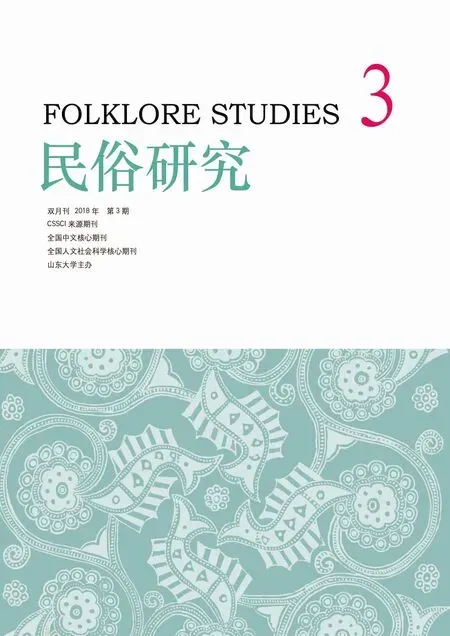多元螺旋式世俗化、价值重建与文化自觉
——德国巴伐利亚阿柏村天主教徒的实践
谭同学
一、引 言
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宗教总是充满了变化,基督宗教的变化则更是“格外剧烈”*Cannell Fenella,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当代著名神学家汉斯·昆曾将其变化划分为六大范式:“早期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观模式;教父时期的希腊-拜占庭模式;中世纪时期的罗马公教模式;宗教改革时期的福音派新教模式;启蒙时期的现代模式;当今正酝酿中的后启蒙、后现代模式。”*[德]汉斯·昆:《基督教往何处去》,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614页。作为天主教中的“开明主义者”,他力推后启蒙、后现代模式,主张天主教与新教乃至伊斯兰教、佛教、儒教等对话。*[德]汉斯·昆:《基督教往何处去》,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625页。至于对话的原则,他则主张细辨各宗教中的精华,以追求更高的真理。*[德]汉斯·昆:《基督教往何处去》,刘小枫主编:《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628-1629页。因与保守派思想针锋相对,梵蒂冈教廷于1979年底宣布取消了汉斯·昆的天主教神学家及授课资格,至今未恢复。
其实,对基督宗教而言,更具冲击力的无疑还是现代人“自我”的发现,以及“上帝死了”*[德]尼采:《上帝死了》,戚仁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页。“重估一切价值”*[德]尼采:《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页。之类的言论。如在韦伯看来,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宗教世俗化过程。宗教变为私人之事,人将被淹没在世俗化的理性“铁笼”之中。*[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II: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西美尔也感叹,世俗化后的货币成了“世界的世俗之神”*[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人与宗教的关系不再是“充满生命的当代形式反对毫无生命的旧形式的斗争,而是生命反对本身形式和形式原则的斗争”*[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年,第25页。。此后,马尔库塞更尖锐地批判道,世俗化消灭了作为主体的“自我”,使人变成了“单面人”。*[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7页。而拯救“单面人”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流浪汉、局外人、不同种族与肤色的被迫害者、失业者等边缘群体身上*[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33-234页。,因为只有他们才具有“大拒绝”的精神。*[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与之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社会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关键问题还在于“沟通”*[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100页。,并主张通过“协商民主”辩论,以合理的理据,克服价值差异、达成共识。*[德]哈贝马斯:《三种规范性民主模型》,[美]本哈比主编:《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专注于世俗化研究的当代哲学家泰勒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即使对于最虔诚的教徒来说,宗教信仰也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信仰上帝不再是理所当然的”。*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究其缘由,这与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加]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2-33页。,也即“人本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70.不无关系。对泰勒而言,天主教与其他宗教乃至无神论间的对话,对于世俗化过程中的价值重建十分重要。*Charles Taylor, Western Secularity. in Craig Calhoun etc. ed. Rethinking Secular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1.但作为天主教徒的他格外强调,对话应以“开放的自我(porous self)”面向、皈依或重新皈依宗教(尤其是天主教)。*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768. 关于泰勒以上思想的中文述评,可参看郑戈:《世俗时代的诸神对话》,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夏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吕绍勋:《世俗化理论与查尔斯·泰勒的新视野》,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与此略有不同,费孝通曾尝试将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平等、包容的理念,应用于包括宗教在内的不同文化对话,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原则。*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6页。
可以说,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对话,已成为当代基督宗教面临最重要的议题之一。*Cannell Fenella, 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5.在实践中,这即涉及到如何吸引信徒的问题。在这方面,不得不提及“宗教市场论”:在信徒、教职人员、宗教活动之间,存在类似于市场经济的消费者、供给者和产品的关系,在宗教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宗教“产品”“供给者”的经营状况是影响“消费者”多寡的决定性力量。*罗杰尔·芬克、罗德尼·斯达克:《信仰的法则》,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45页。“宗教市场论”为透视宗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性维度。不过,它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建设性批评,如不宜将神职人员和信徒看作纯粹理性的“经济人”*Michael J. Sandel, Religious Liberty: Freedom of Choice or Freedom of Conscience. in Rajeev Bhargava ed. Secularism and its Critic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5;卢云峰:《超越基督宗教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范丽珠:《现代宗教是理性选择的吗》,《社会》2008年第6期。,“消费者”本身的社会和心态基础亦是其接受某种宗教产品的重要原因。*谭同学:《在上帝与祖先之间》,《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
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阿柏村田野工作所得资料,对以上论题所涉及的宗教世俗化背景下的价值重建,以及不同宗教(教派)间的竞争与对话机制略作探讨。*2010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2014年4月下旬,笔者曾两次访问该村(人口约1000),在该村做了访谈,参与了农场劳动和复活节宗教仪式。访谈年轻人用英语,访谈年长者则依靠德英或德汉翻译。2014年2-11月,笔者曾与一位出生并成长于该村、工作于伦敦的报道人,有过数次正式访谈和大量日常交流。
二、房名、长子继承制与现代性自我兴起
阿柏村位于巴伐利亚州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脉中段北麓,与奥地利接壤。它虽属山区,交通却很便利,处于德国慕尼黑与奥地利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三座重要城市的中间地带,村内有火车站,乘火车或汽车均只约需一个半小时即可到这三城。在语言和宗教上,阿柏村人与奥地利大部分及瑞士少部分地区居民一样(前文所述汉斯·昆即出生、成长于阿尔卑斯山脉西段北麓的瑞士卢塞因),说同一种有别于标准德语的方言,信奉天主教。以至于笔者在与阿柏村居民聊天时数次碰到如下情况:问对方是德国还是奥地利人(现在欧盟框架下,过境无需特别手续,故为常见现象),其回答有时是“德国人”但同时特别强调为“巴伐利亚人”,有时直接就说是“巴伐利亚人”;有几次听居民间聊天,问他们是否在说德语,其回答是“我们在说巴伐利亚语”。此外,从餐桌礼仪到宗教习惯,阿柏村人都常强调自己与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北方德国人不同。
阿柏村人的地方传统和宗教认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德国统一前,16世纪初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即发生过著名的路德宗教改革运动,而巴伐利亚公国则仍是天主教核心区域之一,在国家认同上也不属于德意志。19世纪初,拿破仑进攻德意志时,巴伐利亚公国与由天主教主导的法国站在一边。拿破仑战败后,巴伐利亚并入德意志,但关系仍较松散。此后,奥地利与德意志发生过几次战争并占领慕尼黑,巴伐利亚农民被迫起义反抗并捍卫慕尼黑。再加上19世纪末首相俾斯麦推出诸多国家化政策,以及强调德意志国家意识的文艺运动影响,巴伐利亚人才真正在国家认同上接受了德意志,与奥地利、瑞士相区别开来。不过,其宗教、语言及地方传统仍留有鲜明的特征,与奥地利、瑞士接壤地区同出一辙。尤其以宗教而论,它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极为传统的区域之一。2005年4月至2013年2月期间担任教皇的本笃十六世,即出生在阿柏村咫尺之处。
在阿柏村及周边乡村地方传统中,房名制是一项重要的亲属制度。人们看重继嗣关系,但并不以男性或女性血缘关系为标志,而是房名。从字面说,房名就是人们所居房子的名字,如“容克”“索瓦”等,通常刻在房子大门或大厅的墙壁上,旁人一见即知是“容克家”“索瓦家”。不过,实际上它并不简单是指称某栋房子。如容克家即使有很多栋房子,但都属同一个房名,兄弟分家后若有能力另辟住处,也仍沿袭此房名。而无子者,则可以将房名传给无血缘关系者。在笔者重点调查的索瓦家,其房名原主人姓弗里德里希。在现主人祖上五代时,因为无子,让长女婿上门继承了家产。这位女婿姓梅耶,此后该家后代即姓梅耶(而非如汉文化中那样继承弗里德里希的姓氏),但该家的房名则仍必须是索瓦。在村内或熟知当地房名制度的人中间,相互称呼,均用房名代替姓氏标识身份,如索瓦·彼特、索瓦·詹妮,使姓氏常为人所忘记。人们判断某家是兴旺还是败落,标准亦是房名是否得以存续,而根本不关心姓氏、即血缘是否延续。若非家道中落、万不得已,居民不会变卖房名下的农场。若取消房名,则不仅是“绝后”,而且也是“灭祖”。直到高度现代化的当下,阿柏村中95%以上的人口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约半数人口连年居住在外,甚至有的已变成他国公民。但是,除因政府公益建设被征收土地外,人们仍绝不变卖在阿柏村的农场(只提供租赁),更不会更改房名。
与房名制紧密相关的还有长子继承制。它在阿柏村的确切起源时间及缘由,当下居民已难说得清楚。不过,其功能则十分清晰,可以避免同一房名下的财产在代际更迭和继承中被分散、碎片化。当然,它很显然带来了兄弟之间的不平等。未获得继承权的兄弟不得不外出谋生,甚至就在兄长的农场中当雇工,以换取几乎仅够糊口水平的工资。这使得他们很难结婚,或者即使结婚也难找到条件好的对象并抚育后代(除非女方无兄弟且为长女,从而可获得岳父家的继承权)。以索瓦家安德鲁为例,他在八兄弟中排第二,原本没有继承权。但因老大于20岁时病逝,安德鲁遂成为索瓦家的继承人。一个弟弟患癫痫,1941年被纳粹政府强制收到精神病院,后被送至并死于残疾人集中营。另5个弟弟在1942-1944年间被征入伍,三人战死,两人战后回到老家为安德鲁做雇工,均终身未娶。安德鲁有四女一子,儿子名为彼特。彼特于1970年末与詹妮结婚,后育有五个子女,分别为海登、海勒、埃米莉(女)、海曼、索菲娅(女)。
在国家走向统一和社会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德国联邦及巴伐利亚州的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了很大变化。1896年,《德国民法典》得以出台。次年,德国制定了专门的《不动产登记法》与民法典相配套。根据《不动产登记法》,警察局对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人口及户主不动产信息进行登记*财产登记在户主名下,权属变更(含继承)需经过司法手续,并报警察局登记方生效。,只认可姓名而不登记房名。而且,法律还承认所有子女都享有继承权,但对农场,则原则上支持由一个儿子继承。之后的法律虽不乏变化,但此原则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二战后,正式法律不再支持长子继承制,转而强调个体权利。可直到当下,在阿柏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关注家产在警察局的户主信息有无变更,仍认为它是房名的主人,而不管姓名(政府则不关心房名)。之所以关心房名的主人在警察局的登记信息,是因为这会涉及到他们在与人协商一些重大事情时(如大宗农产品交易、房屋租赁需户主签字),需要弄清楚一个家庭中的“父”与“子”,谁才是最后定盘的谈判对象。至于继承权则更是如此,没有弟弟或姐妹会依据正式法律,通过起诉的方式与长子争继承权。这不仅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律师都会考虑调和制定法和习惯法,而且因为此类行为在地方社会中将被认为在道德上有违诚实和本分。与此类似,阿柏村居民在上学、就医以及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使用的都是姓名,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用姓氏加名字(如梅耶·彼特),而用房名加名字(如索瓦·彼特)。
当然,地方传统在现代家庭生活中并非就没有遇到反思。尤其是在1970年代及其后出生、世纪之交成年的年轻一代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已变得十分普遍。尽管户主为男性,在家庭重大决策中,妻子的意见同样也重要。不少年轻人表示,就夫妻关系而言,作为户主的丈夫只是对外的法人代表,并没有特权。甚至,在有的家庭中,所有财产都平均登记在夫妻两个人的姓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如离婚则颇为复杂。想要保持房名下住房和农场完整延续的一方,需做出各种努力与另一方交涉(如用其他财产或现金作为补偿),可达到此目的。在代际关系中,由于年轻一代“自我”意识兴起,也不乏冲突的例子。
2010年4月初的一天,笔者在索瓦家便碰到一场微小的父子冲突。该家长子海登因已远到伦敦工作,主动表示放弃继承权(但尚未办理司法手续)。次子海勒参加一个乐队,常在欧洲各国游历,也表示对继承权无兴趣。三子海曼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此时担任镇政府非全职农地评估员*当地政府对每块农地的质量每年进行一次跟踪登记、初评,三年一次复评,五年一次总评估、确定其未来五年的质量档次。农地质量档次是政府进行农业补贴和经营税收的依据之一。,有继承家业的想法。由此,家人早已有了将来由海曼作户主的预期。海曼想将住宅三楼一处空闲的地方改造成自己与未婚妻的卧室,并建一座楼梯直通室外,不用经过其他人共用的大厅和楼梯走道,相对独立、私密。父亲彼特原则上同意此想法,但在工程师上门现场策划改造方案时,他撇开海曼直接与之商定了很多设计细节。海曼对这些设计细节很不满意,次日早餐时与父亲发生了争论。海曼认为,房间是给他与未婚妻用的,应由他们设计。但彼特提及了谁才有权利改变房子的问题,暗示他才是户主,即使他老了,潜在的户主也应该是长子海登,轮不到海曼说话。无奈之余,海曼干脆暂缓房间改造。2013年,索瓦全家在律师见证下明确了海曼的继承权(但警察局的户主登记尚未更改)。*父母和海曼为示补偿海登,变卖了家里在某镇上的一栋商品房,以供海登作为在伦敦购买套间的首付。2014年4月,笔者再次到索瓦家时,海曼正在亲自动手按照自己的方案改造房间。
与索瓦家相比,邻居容克家的冲突则显得比较严重。容克家只有一子(现已50多岁),另有三女。父亲对儿子很不满意,认为他既不安心经营农场,也无其他一技之长。父亲又尤其认为儿子找女友不切实际,数任女朋友都是城里人,且属难以沟通之辈,最终还被这些女友都“甩”掉不要,以致至今未婚(但有一非婚生子)。父亲常拿村中几个光棍的例子警告儿子,一味强调自我性格、好玩,可能最后一事无成,并劝他按照传统标准找个农村姑娘。儿子不仅不听劝告,反而认为父亲严重干涉了其自我独立及私生活。甚至,他将自己诸事不顺的人生经历,怪罪于父亲迟迟不肯到警察局更改户主名字,以至他跟人打交道时得不到足够的尊重。父亲则表示,如果儿子还不找回天主教徒和农村人应有的本分,他完全可能将房名和家产让女婿或孙子继承。2014年4月笔者再到阿柏村时,容克家的父子矛盾仍未有丝毫改变。该家父亲已70多岁,但仍是户主。
从以上案例中不难看出,虽然随着“自我”意识兴起,阿柏村居民的个人自主性有了提高,但在房名与财产继承问题上,地方社会及天主教传统仍有着很强的力量。
三、启蒙后的宗教选择、代际更迭与对话
在西欧,人们通常所说的启蒙运动已是久远的事情。但对阿尔卑斯山脉天主教核心区域而言,人们对天主教开始相对理性反思,却直到战后在对二战及理性主义灾难的反思中,才真正兴起。从思想层面,如前文提及的汉斯·昆乃是从1960年代初举行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之后,才积极宣传其天主教变革及其与不同宗教(教派)对话的思想。阿柏村居民对二战的反思并非直接来自“梵二”后天主教内部的思想革新,但却殊途同归地走向了关注生命、个体权利,以及反思教会组织的政治、经济权力。
以索瓦家为例,彼特三个叔叔死于战争。但据说,他们都属于被迫入伍,家人也都十分不愿意他们参军。这三人横死他乡,让彼特一家长期不忍提及这一残酷的事实。至于其残疾叔叔被纳粹政府送至集中营处死的做法,则更是令人发指。彼特的妻子詹妮对战争也深有痛感,她父亲于1945年初被应征入伍,数月后为苏军所俘,此后一直被关押和在西伯利亚接受劳动改造,直至1951年方被释放回国。战争与强迫劳动使得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终身未能痊愈。2010年4月,这位老人言及战争时仍是愤慨不已。而詹妮则表示,天主教会本应反对战争,并且可以采取有力行动,但却没有。甚至,在1933年后,很多教会还与纳粹有合作,这是最不应该的。
不过,彼特与詹妮这一代虽然对天主教与二战有反思,并且已不再认为天主教可以立于世俗政治权力之上,却并不认为它应像基督新教那样与政治脱钩。相反,他们认为天主教应当成为世俗政治的道德基础。由此,在政治派别与天主教关系的综合考虑下,彼特“很自然地”选择了“基督教社会联盟”(也称保守党)。在1990年代,彼特还曾担任保守党阿柏村委员会的会计职务。
无论是在镇、村级的政治事务中,还是在宗教事务中,男性都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教堂神职人员中,男性更是控制了所有重要职位,少数女教徒作为志愿者只能从事一些辅助工作。彼特和詹妮这样的教徒,虽然在家庭生活上已完全认可了男女平等,却并不觉得应该对公共生活中男性主导的局面提出尖锐批评。2010年,梵蒂冈个别主教因鸡奸男童等不良行为引发了广泛批评。彼特和詹妮当然也认为这些主教不对,甚至也赞同由此而引发的关于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讨论。但是,他们并不愿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的看法。
言及父母这种实际上已理性开明化,但在正式场合表达观点时却显得保守的宗教行为特点,海登认为可能与他们成长的经历有关。他们生于1950年代初,虽然对二战反思已开始,但阿柏村农业机械化和社会现代化是1960年代末才开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进入城市及第二、三产业工作是1970年代之后的事情。这使得他们在宗教上既不反对新的变化,但又认为保守传统其实也很“自然而然”。例如,他们完全不反对子女们婚前同居,却常会提起当年谈恋爱时,即使在订婚之后,詹妮偶尔白天到彼特家的农场来帮忙干活,晚上仍必须回娘家。他们并不认为传统的做法就是压制人性,相反认为那时有那时的浪漫。同理,在彼特和詹妮看来,某著名天主教神职人员系其母亲未婚先孕所生,是一个有道德瑕疵的天主教徒,很不适合担任神职(而在其子女看来则并无问题)。
彼特和詹妮甚至还在住宅旁,自建了一座占地十几平方米的小教堂。该教堂从建房到内部设置,全部都是他们亲手做的。其中,基督、天使神像由詹妮用木头刻就,墙上各种天使画也是她的杰作。笔者问及制作过程,詹妮说花了很长时间才精心雕刻和描绘出来。她非常相信基督神像能代表基督,保佑人的平安、幸福。2013年,海登在伦敦买房后,詹妮给他“乔迁新居”的重要礼物之一便是一尊木雕的基督神像。
在重要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彼特和詹妮都会到阿柏村中心教堂去参加祷告等活动,其他时节则常到半山腰的一座小教堂祷告。以笔者于2010年和2014年参加的两次复活节为例,詹妮牵头负责早早准备了各种捐献给教堂的食物以及蜡烛等东西。复活节当天,彼特、詹妮及部分家人早上五点开车出发,五点半至七点半参与神职人员在中心教堂举行的仪式,仪式结束时分食一点饼干和红酒(代表基督的肉与血);然后,詹妮给彼特的父亲及叔伯墓地点上一盏防风的蜡烛;最后回到家里,年轻人在住宅周围搜寻詹妮藏好的糖果,再祷告开始早餐。在阿柏村,复活节重要程度超过圣诞节,半数以上的人即使在外地生活也会回到该村参与中心教堂的仪式。中心教堂的坐席上刻了各家的房名。据说,在1980年代因为参加的人员太多,常出现一家十来口人拥挤在五六个座位上的情况。在当下,因部分外出人口和年轻人并不参加,坐席才显得宽松起来,以至于不少坐席是空的。不过,各家都会保证至少有代表参加。否则,自家房名下坐席空无一人,会被认为不太好。
与村中不少中老年人一样,彼特和詹妮夫妇与阿伯村中心教堂的神职人员有比较密切的来往。除了日常来往之外,通常他们每年还会在家里至少举行一次宴会,邀请神职人员前往参加。当天,神职人员除了在索瓦家享受丰盛的菜肴之外,也会为其家人做一些相关的仪式,如宣讲圣经、祷告和唱诗等。作为阿柏村一个重要的家庭聚会习惯,彼特和詹妮会要求子女及其他准家庭成员(如未婚儿媳、女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参加。通常,它也被视作一个天主教家庭和谐美满的标志。
可正是在以上诸方面,阿柏村年轻的一辈与中老年人有了重要区别。他们之间的对话,虽有诸多可通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分歧乃至冲突。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年轻一辈所关注的着重点不在家庭生活,而在政治和宗教管理事务上。以索瓦家为例,彼特和詹妮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属于保守党。他们都公开赞成要求镇、村级的政党组织中,女性应平等得到担任政治职务的机会,又尤其旗帜鲜明地反对禁止神职人员结婚和禁止女性担任主教的规定。在正式政治选择中,海登、海勒因常年在外而成了无党派,基本上不参与阿柏村的政治选举,但对保守党某些不足之处则持批评态度。海曼在政治观点上与基督教民主同盟(简称“民主党”)大体一致,相对于保守党而言开放很多(他还知道汉斯·昆的神学观点)。2012年,海曼辞掉了镇政府非全职农地评估员的职务,开始专心经营自家农场。言及缘由,海曼说一方面是工资并不高却要花不少时间,另一方面是那些保守党主导的政府事务太烦人。至于埃米莉和索菲娅,则选择了自1980年代以来长期作为巴伐利亚州议会反对党的绿党,对保守党许多政策都持批评态度。2014年4月某天,当说到三位死于二战的堂爷爷时,海曼和埃米莉都与母亲詹妮不一样。他们认为,将三人送上战场,以及纳粹政府用集中营谋杀残疾人的原因不是天主教会没有反对战争,而是政治缺乏理性、整个社会很疯狂。
年轻一辈对天主教保守派的反思,不仅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也直接影响到了家庭和私人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海登还是其他兄弟姐妹,都跟村中很多年轻人一样,基本不上教堂做礼拜,在餐饮之前的祷告仪式也均被放弃。即使在复活节,他们也未必去教堂。笔者两次访问该村时,索菲娅以及海曼的未婚妻在家,但未去教堂参加仪式,埃米莉也只参加了一次。而其理由并不复杂,只是觉得仪式并不那么重要,同时“想多睡一会儿”。埃米莉和索菲娅在找工作时,也都受到了这种倾向的影响。埃米莉工作于一家社会福利院,而索菲娅则在一家农业合作社上班。她们认为,这些工作能体现爱心而又相对自由,不像传统天主教徒那样死板。在婚姻这件人生大事上,最小的索菲娅于2014年5月最先结婚。其丈夫是邻镇某村居民(六个兄弟中的老大),但他做了一名护林员。在宗教观点上,他也属于天主教中的开明派。在这一点上,海曼的未婚妻也很相似。
至于埃米莉的未婚夫赫伯特,则对天主教保守派持更激进的反对态度。赫伯特认为,人类确实需要宗教,其中包括天主教,但人人都有靠自己理解、掌握神圣真理的能力。相反,所有神职人员都是在卖弄具体的宗教知识,而离真理本身却很远。所有神职人员、宗教场所和仪式,都是用有形的赝品遮蔽了真理,将信徒与真理隔离了起来。2014年4月在一次与笔者的交流中,赫伯特指责了大量的神职人员腐败现象,然后说:“为供养这么多神职人员、盖这么多教堂,花这么多钱!还有这么多腐败!(这些钱)为什么不能用来支持改善人们的医疗、教育和养老呢?”就此而言,赫伯特颇像是个“宗教无政府主义者”。不过,赫伯特反复强调自己毫无疑问是个天主教徒,而且其虔诚程度比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彼特与詹妮部分赞同赫伯特对神职人员腐败的批判,却完全不认可其宗教主张。这使得近年他们在邀请阿柏村中心教堂神职人员到家做客时,遇到了尴尬。为显示一个天主教家庭的和谐美满,他们很希望赫伯特能参加聚会,但却又担心他与神职人员产生冲突。于是,詹妮不得不事先反复叮嘱赫伯特,除了与对方打招呼之外就少说点话,装作性格内向。
四、后现代的价值重估、重建与文化自觉
较之于父母辈,阿柏村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已变得更强。他们不仅对天主教保守派有更深入、系统的反思,甚至对战后成长起来的父母辈的宗教态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思。这颇有理性启蒙后“价值重估”的味道。不过,当他们面对其他宗教(教派),尤其是后现代思潮时,却也逐步意识到,一味反思一切传统价值并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
以海登为例,他到伦敦之后在宗教体验方面可谓很不适应。虽然伦敦有多元宗教文化,但太多基督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注重宗教价值,让他觉得生活失去了价值坐标。海登所碰到的,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少有按宗教节律庆祝各种节日。即使政府安排了放假,他们也不知其原本的宗教含义,而笼统地称之为“银行假日”(bank holiday)。以至于,连擅长用节日做活动的商家,也只能把圣诞节做得热闹一点,其他宗教节日则相当冷清,连复活节都无太大起色。身边的基督教朋友不如阿尔卑斯山区天主教徒重视婚姻的神圣性,对海登也颇有刺激。此外,海登还曾碰到几个新教徒朋友,其住宅乃由教堂改造而成。海登问朋友道:“住在教堂里,墓地就在窗外,你住得心安、舒服吗?”对方告诉他:“怕什么呢?有基督帮忙看着墓地呢。”可是,在海登看来,教堂被改作商品房用来赚取利润,说明基督早就被赶跑、没有了寄寓之所。
无独有偶,2014年4月在阿柏村邻镇、海登一位高中同学的生日聚会上,几个人跟笔者提起,美国摩门教徒不如巴伐利亚天主教徒讲诚信、重朋友。其中一位叫拉法尔的提到他几年前去纽约的经历。某天在吃晚饭时,一个摩门教徒以“美国人特有的直爽”跟他作自我介绍,攀兄弟关系,最后拉法尔帮对方付了晚餐费用。可在次日午餐再见面时,这位美国“牛仔”不但忘了拉法尔的名字,而且连请他喝杯咖啡的意思都没有。拉法尔表示,他永远都不会再跟美国人交朋友,这些摩门教“牛仔”基本上没什么情谊可讲。当然,也有旁人认为拉法尔的观点过于偏激,只是偶然碰上了一个不靠谱的美国“牛仔”。但他们却也同样认为,天主教徒的确更诚实,更适合做朋友,而一旦与完全不认可这套价值的人打交道时,会产生障碍。
诚然,年轻人并不常将天主教与新教、摩门教拿来作比较。但在其对天主教的正面表述中,同样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解构一切宏大话语,以及极度强调个体快感的后启蒙、后现代主义,心存忧虑。
以擅长音乐的海勒为例,他原本在一所著名大学攻读哲学本科,能够熟练阅读古希腊、古罗马哲学著作原文。但当他读到后现代哲学之后,放弃了继续读哲学并做哲学研究的想法。因为,海勒认为后现代主义瓦解了古希腊、古罗马及古典哲学的“同一性”哲学基础,再没什么唯一永恒的真理值得追究下去。于是,在大学毕业后,海勒与几个有音乐特长的朋友组建了一个乐队。他们开始从酒吧演奏艰难起步,经过几年逐步发展到常年在欧洲大陆国家巡回演出,甚至还偶尔演至美国、中国、日本等地。海勒认为,好的音乐说起来很玄妙,但并不在其知识和技巧,而是要有灵魂。他所在的乐队以巴伐利亚乡村音乐为基础,融入了天主教和乡村人的乐观、淳厚情感,使之成为音乐的灵魂。海勒认为,这样的音乐方能让人真正舒展情绪、打动心灵。而与之相反,当下很多音乐都只是刺激人的肉体反应,如借助于现代音响,用狂躁的音调和高低重音,或者再加上歇斯底里的叫喊、哭叫、尖叫,让人心跳加快、神经兴奋。但是,这样音乐没有灵魂,听者在肉体兴奋结束后即是疲惫和心灵空虚。
海登、海曼虽然不如海勒擅长音乐,但也算音乐爱好者,分别有小号、手风琴作为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海勒这套关于音乐的说法,他们高度认可。2010年4月某晚,海登、海曼在自家厨房里给笔者演奏了许多乐曲。在中间休息时,海曼用手风琴猛拉了几下,然后说:“这就是歇斯底里的,没有灵魂的。你瞧,如果这样的话,连手风琴都受不了,会被拉坏的。”
传统价值被重估,而且被弄得支离破碎之后,必然面临新的价值体系如何重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连“宗教无政府主义者”赫伯特也认为,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宗教仍有其价值。在与笔者的一次聊天中,赫伯特谈到了在德国部分地方出现的、个别极端分子组成的“光头党”。这些“光头”大多数是失业的年轻人,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敌视、排斥外国人和非基督宗教徒,有时甚至会攻击他们。在赫伯特看来,这些“光头党”的问题不是心中有没有上帝,或者有没有其他什么神灵的“异端”,他们就是纳粹分子,根本上没有人性,就像野兽。说到这里,赫伯特再次强调,他反对保守腐败的教会组织和神职人员,但不反对人们信仰宗教。宗教或许可以让一些无所顾忌干坏事的人有所收敛,让社会有一个起码的道德底线。
对于阿柏村年轻的天主教徒而言,虽然在父母辈眼中就像是新教徒甚至无神论者,但当他们真正碰到有人对天主教人生、家庭价值的稳定感质疑甚至冲击时,却仍有很明显的挫败感和深受震动。在婚姻问题上,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从以下两个案例中,可见一斑。
海登数年前曾与汉娜女士谈恋爱,两人在事业上相互帮助、相得益彰,并于2010年订婚。2012年,两人决定结婚,并确定了婚期。彼特与詹妮十分高兴地开始为长子,同时也是第一次为子女筹备婚礼。他们与阿柏村中心教堂的神职人员取得联系,确定了婚礼的初步准备工作,同时还知会了各方亲友。但很让人意外,婚礼最后却不得不被取消。直接原因则是汉娜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心理准备,而且对将来何时能决定结婚也完全没有预期。谈及此事,詹妮倒没有责怪汉娜。她认为,女方需要多考虑、甚至另作选择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在他们通知教堂及亲友之前就做出此决定的话,则不至于如此尴尬。同时,詹妮也强调,阿柏村人对婚姻是慎重的,所以无论如何这次风波还是一件大事。海登本人更是因此倍受打击,与汉娜发生过争吵。不过,海登认为,从理性的角度看,或许对于中法混血、长在伦敦且经历了父母离异而由单身母亲养大的汉娜来说,无论是国家、宗教还是婚姻都不坚固,由此可能确实有理由怀疑婚姻的长远预期。但是,对于深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海登来说,既已做出结婚承诺,很难接受如此突变。两人随即分手,成了普通朋友。索瓦家所有人都因此意识到一个切身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价值坐标,人如何能过上有长远预期的生活?
索菲娅的婚礼也遇到过一个小插曲。其婚期为2014年5月中旬,彼特、詹妮与子女们共同商定,给这个首先结婚的女儿把婚礼场面办大一点,计划邀请200个左右亲友参加。可在3月,索菲娅的准婆婆与公公因家庭琐事闹矛盾。这位年逾五十的妇女认为与丈夫数十年积累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而六个儿子也不能体谅她的处境,毅然与丈夫分居并要求离婚。此举引起不少亲友非议,有人批评她,即使要闹离婚也应该等儿子、儿媳的婚礼结束之后再说。于是,她暂时压制了离婚的要求,但仍与丈夫保持着分居。彼特和詹妮认为,到这个年龄、这个节骨眼上闹离婚,无疑是不懂得做人,同时有违天主教传统及地方社会日常伦理。可是,按照天主教婚俗,又无论如何不能不让她参加婚礼。为了避免让更多亲友前来参加婚礼时知晓这件尴尬的事情,彼特和詹妮跟子女们商议后决定,慎重控制婚礼规模,只邀请有血缘关系的至亲、共30人左右参加婚礼。
五、结 论
在阿柏村天主教徒代际间,以及和其他宗教(教派)的互动、对话中,无疑清晰呈现出了现代性“自我”意识兴起,以及宗教世俗化的趋向。但它并非单一直线趋向“上帝死了”,而是在总体世俗化的倾向下有诸多回旋,宗教传统以新的方式在诸多领域仍在不经意地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教徒与非教徒均有了多样化的选择。也即,它呈现出了一种多元的、螺旋式前进的特征。年轻一代的天主教徒对教会组织与神职人员的经济与政治权力有了更多的反思,并且在宗教仪式上也有了多种世俗化的选择。可是,当这些具有了“自我”反思精神的天主教徒碰到了重估、解构一切传统价值的理性主义与后现代思潮之后,却发现仅有启蒙式理性反思还远远不够,要把生活过好还得进行价值重建。否则,宗教世俗化后的现代人可能真有陷入理性“铁笼”,为货币和肉体享受所奴役的危险。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主张“自我”个体“快感享用”*[法]福柯:《性经验史》,徐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并不能解决宗教世俗化时代价值多元、碎片化的问题。相反,它只能导致价值更为碎片化,“快感”之后是虚无。
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重估、解构一切传统价值,虽然在思想上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重估、解构之后,如何重建价值。在此问题上,由于有了“自我”反思精神,价值重建绝不意味着简单回到原教旨主义、本质主义的天主教保守派传统,而要在基督宗教不同教派以及与其他宗教、无神论者的对话中,找准新的价值坐标。这个过程当然也难以一蹴而就,即使在亲友间要取得共识,也需要大量的建设性对话,甚至妥协性包容。不过,拯救价值“失范”的希望,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寄托在本宗教和文化内部的边缘群体身上。就此而言,马尔库塞对于理性压制人性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但以“大拒绝”的态度作为重建价值坐标的原则,则显得消极而偏激。
在多元宗教(教派)对话中,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谁具有启蒙“他者”的资格。在实践中,无论是作为个体“自我”的教徒,还是作为整体“自我”的宗教(教派),都容易倾向于去启蒙“他者”*Ragini Sen etc, Secularism and Religion in Multi-faith Societies. Cham etc.: Springer 2014, p.14.,让“他者”接受“自我”的宗教思想。因此,在多元并存的格局下,客观上便出现了宗教(教派)竞争的问题。它们之间除了竞争说明“自我”宗教思想更具有神圣性、合理性之外,在实践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竞争信徒数量。在这一点上,“宗教市场论”无疑富有洞见。它呈现出了不同宗教(教派)在竞争中争取更多信徒的动态机制。至少就结构主义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而言,“宗教市场论”创造性地关注到了能动性的一面。宗教“产品”“供给者”,尤其是神职人员的能动性,得以在多元竞争的框架中显现出来。
不过,从阿柏村天主教徒的生活实践来看,神职人员似乎也并非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动性经营宗教,相反他们也身处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结构当中。作为天主教保守派传统核心区域的神职人员,很显然有诸多历史“包袱”要处理,以至于对当代教徒,尤其是年轻教徒的宗教观念变化,难以及时做出有效回应。对于普通教徒而言也如此,出生、成长于此宗教(教派)之下是一个历史事实,在此后的人生中要重新做出选择,就意味着要面对各种社会关系纽带重建。例如,对父母眼中的“宗教无政府主义者”和已经像新教徒的年轻天主教徒而言,便面临着如何与父母及其他长辈相处的问题。由此,确实不宜将神职人员、普通教徒理解成纯粹理性的“经济人”,对宗教“产品”进行“自由选择”。
即使在“宗教市场”中,普通教徒也不仅是宗教“产品”的“顾客”。事实上,一旦他们接受了某种宗教(教派)之后,其所作所为即使并非主动传教,在客观上也必定具有“供给者”的社会作用。“他者”会将其所作所为,当作判断该宗教(教派)“产品”是否值得信赖的依据。例如,尽管美国的天主教、摩门教实际上十分保守而缺乏世俗化*Roger Finke, An Unsecular America. in Steve Bruce ed. Religion and Moderniz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p.164.,但一个普通的纽约摩门教徒和巴伐利亚乡村天主教徒的日常交往行为,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后者判断摩门教、甚至美国人不可信的依据。在阿柏村天主教徒内部也如此,“宗教无政府主义者”会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宣传“自我”的宗教主张,以劝说其他亲友接受“宗教无政府主义”。这足以表明,普通教徒除了是某种宗教“产品”的“消费者”之外,在客观上同时也会变成它的“经营者”。此外,阿柏村天主教徒外出之后,在与其他宗教(教派)打交道的过程中,还重新认识到了“自我”宗教(教派)的特点。在宗教主张上,一些年轻天主教徒原本以为与老一辈已彻底不同。但是,在与“他者”接触后,他们发现在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其实与老一辈仍有诸多共同的价值底线。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凌诺斯基将宗教放置到人的生活中去理解*[英]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58-259页。,以及格尔茨把宗教作为文化体系看待的思路*[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仍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作为文化现象,宗教富有变化而非本质主义,其多元世俗化过程及不同宗教(教派)的对话,也与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及政治权力关系密切。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后,不同宗教(教派)在与“他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将“他者”误判为“不洁”或“危险”的异端。*[英]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就此而论,汉斯·昆强调宗教向“后启蒙”“后现代”模式转型,主张天主教与其他宗教(教派)对话,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和建设性意义。不过,其细辨各宗教中的精华,以追求更高的真理的主张,在宗教文化对话和价值重建中却显得有些过于乐观。宗教(教派)既深深植根于各种结构,同时在价值重估、解构之后,却又高度依赖于宗教徒个体能动性。在此基础上,如果非要固执地找出更高的“真理”,极可能会造成新的冲突,即使在亲友间也如此。
同理,哈贝马斯肯定不同(价值)体系间的沟通、对话无疑也有建设性的一面。但其通过民主辩论、协商,用最“合理”的论据说服“他者”,消除不“合理”的异见的主张,则显属一厢情愿。至于泰勒试图从宗教世俗化的趋向中直接逆向皈依天主教,主张让教徒以天主教价值为前提与其他宗教(教派)、乃至无神论对话,以求共识,则不仅有违宗教多元世俗化的事实,也不符合多元文化平等共处的原则。正如有批评者已指出,这是一种充满“秘密欲望”的、“时代错误的”的“浪漫主义”*Colin Jager, This Detail, This History: Charles Taylor’s Romanticism. in Michael Warner etc. ed. Varieties of Secularism in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92.,而世俗化的弊病也并不能简单成为复活某种单一宗教的充分理由*Steve Bruce, God is Dead: Secularization in the West.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241.。
其实,汉斯·昆、哈贝马斯和泰勒在强调通过对话处理宗教差别,都忽略了求“同”未必非要彻底去“异”的事实。在对话中一味求“同”或者“更高的真理”,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有损不同宗教(教派)文化间的和谐。由此,在对话中强调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原则相结合,仍有其必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并非无需反思地简单沉迷于“自我”之“美”,或盲目崇拜“他者”之“美”,而是要有“文化自觉”。即人们对“自我”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只有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加强对话,才能够求同存异、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