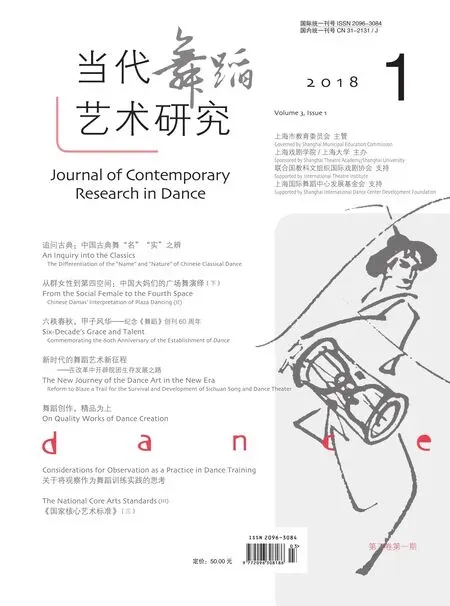中国古典舞“名”“实”之思—在“中国古典舞‘名’‘实’之辨”博士论坛上的发言
吕艺生
主持人让我做总结发言①,我还是借机谈一点个人对古典舞问题的思考。
一、讨论中国古典舞的两个维度:国家的高度和国际的广度
所谓国家高度,即“古典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创时,是有一种国家意志在其中的,文化古国再建新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古典舞蹈,这就是欧阳予倩那代人的初心。当时年轻的舞蹈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它已是一种客观存在,既是学科存在,也是舞种存在。否定、更名都是不可能的,无论喜欢或不喜欢,它都存在。我以为,舞蹈理论、舞蹈评论的任务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将它存在的合理性说清楚、讲明白。“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这是当代中国人在舞蹈方面的两大创造,中国舞蹈界要以文化自信的精神和意识,用人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将这个中国舞蹈故事讲好。比如说,它为什么会受到芭蕾舞的影响,甚至在训练中会直接使用擦地、旁腿转?这个历史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中国古典舞”创建初期的国际封锁、冷战的对立,使得中国人不知世界舞蹈发生了什么。现在门户开放了,国家崛起了,需要再重新认识它,尊重它,爱护它,还要解释它,修正它,充实添补它。
之所以要注重国际的广度,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获得世界上各种舞蹈参照,因而更知道“中国古典舞”存在的独立价值,也更能看清楚它所存在的不足或不合理之处,比如那些芭蕾的影响是否应当剔除了。在原来没有古代舞蹈遗存的情况下,舞蹈家们创作了一些“仿”作,这应当怎样定位?特别是看到中国古代乐舞竟然在异国尚有遗存,它们是否已到了“还乡”的时候了?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事实上,创建“中国古典舞”的前辈,早已看到它的不纯,因而才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创造了“中国古典舞身韵课”“汉唐古典舞”。而现在年轻一代教师在“中国古典舞”课堂上,也悄然地开始化减芭蕾舞的痕迹,其美学思考也正在认识中,“中国古典舞”已经暗地在纯正化。只是目前发生的变化还不够成熟,因而也没有全面公开展示。这都是中国开放后有了国际性比较后的自然变化。
二、中国古典舞的“名”与“实”要一致,不仅要正名,还不能继续关门滥用
“名实之辨”,其实主要的意义在于如何使它更“名正言顺”。我认为更名是不可能的,更了名人们就不知言之何物了。但“中国古典舞”之名亦如“中国民族民间舞”一样,其名不可滥用,尤其是舞蹈理论界。我们实在太习惯“闭门论剑”了。在国门未开之时,关上门说什么大家都不在意,“名可名,非常名”,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说的“民间舞”“古典舞”并非真正的古典舞和民间舞,它们常常涵指一切这一群体中的训练、创作等,但当对不清楚我们的一贯做法的人来说,当他们看到将今人用此风格动作进行的个人创作也称作“古典舞”时,他们无论如何弄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古典舞,对舞蹈历史一点不了解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也会产生迷惑。
20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开过一个民族舞蹈保护会议,我们把舞蹈学校的“民间舞”课和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舞蹈节目,展示给外国人看。有五位外国专家对“中国民间舞”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把明明是当代人编排的作品称作“民间舞”,特别是当他们看过花鼓灯艺人冯国佩的表演后,更坚定了自己的怀疑。局外人的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经过几代教育工作者的努力,特别是到了高度、黄奕华这一代,终于把真正属于民间的舞蹈集成为《沉香》(现已做到了“《沉香》之四”),才让人们在舞台上看到了相对真实的“民族民间舞”。在教学上,填补了真实的传统这一块,使民族民间舞系也名正言顺了,“民族民间舞”的名称也实至名归了。当然对于一些已经非常习惯原已形成的“民间舞”舞台艺术和教学状态的人来说,不知表演这个干什么,甚至不把这种内容看作教材,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实际上,原来舞蹈教育中那种所谓“元素”提炼法、“元素”性教材,也只不过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规范也好、科学性也好,应当还有更多的方法。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系教师带领学生到乡下向民间艺人(尽管可能已是“二代老艺人”,第一代艺人大多已经过世了)学习原样民间舞,并将它们搬上舞台,让观众看到了相对原汁原味的民间舞,也使真正的传统融汇在学生身上,使后代保存下真正传统的舞蹈基因,这意义多么重大啊!从“民间舞”教学来说,这一举措至少使教材丰富了,教学方法也多样了。
“中国古典舞”是否也应这样考虑填补这一空白呢?
三、中国古典舞建设要珍惜中国古代舞在世界上的遗存
中国古代舞蹈特别是宫廷雅乐舞,因种种历史原因在国内未能流传下来,倒是周边国家保存下来一些。在汉文化圈中,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分别在唐、宋时代派遣正式留学生(唐朝时日本派遣来华访问留学者称为遣唐使)来华学去了相当数量的宴乐舞与祭祀舞蹈,这都是有史料记载的。例如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中国史料中有记载,他所带的学子在唐代学了为数可观的乐舞,他本人甚至被唐朝廷授予官职。高丽(当时朝鲜半岛的统治政权)在宋朝时学的是祭祀乐舞和宴乐舞蹈,如果不是日本在侵略中国东北前先侵占了朝鲜,结束了朝鲜的宫廷统治,这些乐舞也会像日本那样继续传承于宫廷之中。日本在天皇的支持下形成了中国唐乐舞的保存载体。因而,现在只有日、韩保存着一些货真价实的中国古代乐舞及在其影响下的本土宫廷乐舞,因此使他们在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获得成功。
面对这种情况,具有强烈民族传统意识的专家肯定会产生能否让唐宋乐舞返回故土的意念。戏曲界的欧阳予倩和李少春,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董锡玖、王克芬、江东都有过对其考察和学习的经历;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也曾邀请过日韩专家来校传授古乐舞,台湾老一代舞蹈家刘凤学先生曾专程赴日韩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创作。近十年来,中国舞蹈学者刘青弋与日韩古典乐舞专家合作,先是在杭州师范大学开始了关于“亚洲‘非遗’中的中国宫廷舞蹈代表作”的研究、传习和课程建设,现又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了“东亚传统宫廷乐舞国际研究会”,开展了“海外唐乐舞的遗存研究”和“海外唐乐舞回家”的工作,以及唐乐舞传习及其课程建设。这是一项具有伟大意义的“乐舞还乡工程”。试想,“中国古典舞”如能增添“古代舞蹈”这一内容,岂不是也如“民间舞”《沉香》一样,使“古典舞”的内涵更为丰满且真实,从而也与职业舞蹈家依此风格进行的个人创作区别开来。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岂不也多了真实的研究对象,届时,中国古典舞的“名”与“实”也不必如此辨析了。
事实上,让中国唐宋乐舞还乡的意愿,如果说在原来冷战时代和国内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办不成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时机已成熟,甚至日本和韩国友人也有此愿望。有了这样的条件,如果我们这代人仍抓不住机会,认识不到此一问题的重要性,那我们将有愧于祖先,有愧于中华舞蹈文化,更有愧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承受不了这历史之重,谁能担起这样的罪责!
不错,有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会认为那么简单的东西能上台表演吗?能成为古典舞教材吗?这也与“民间舞”《沉香》一样,如果我们的观念仅以现成的教材与成果为唯一标准的话,那它可能根本无价值可谈,然而,它的价值绝不比出土文物差,因为它们是活在人体上的,具有鲜活性。
珍惜历史,珍惜活的古代舞吧!我相信无论是学术还是实践,它们都有巨大的价值!
四、不能把职业舞蹈家的创作随意称作“古典舞”,“仿古”就不是“古”,不要贩卖历史的谎言
在当代“中国古典舞”实践中,有一些成功的“创作”,我们轻易地把它们一律称为“古典舞”,那是关上门自说自话时形成的习惯。如今改革开放了,就不能太随意,那会对外国人造成误导,也会使年轻后代产生迷茫。
在改革开放初期,陕西歌舞剧院编创了一台唐乐舞,他们恰当地称为《仿唐乐舞》,一个“仿”字了得,证明了他们的艺术态度的严肃和认真。后来,孙颖先生的遗作《踏歌》,本是为电视连续剧《唐明皇》创作的插舞,应当说概念也算是比较清楚。后来“桃李杯”舞蹈比赛和其他各种比赛中,特别是在院校比赛是以学科划分的,必须把古典舞、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标舞清楚地分类,这样的分类如果比表演没有问题,但一到比创作的作品,也一律称“古典舞”就使概念模糊了。原来这些比赛是内部的自说自话,无人问津,一旦对外公开就会产生许多误解,引起矛盾,到头来“名”与“实”越发混乱,连舞蹈圈自己都搞糊涂了,以至于今天只好为其进行“名实之辨”了。
孙颖先生本不是要创建什么“汉唐舞”,他是想改变“古典舞”的训练与创作之传统不纯正的问题,并想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清理,而历史上材料最丰满、最具情感化的就是汉晋时代,于是他开始创作舞剧《铜雀伎》,后又创作了《踏歌》《七槃舞》等。后来为区别于它们和原有“古典舞”的不同,称之为“汉唐舞”,从此以讹传讹,成了一种带有朝代性的“汉唐舞”,熟悉他的舞蹈界朋友知道这是他的创造,不知者却被绕到古代舞中去了。此次刘青弋的作品《德寿宫舞姿》,算是最有历史依据的、严格按照史存舞谱进行研究的作品。但她称其为“舞姿”,并说明这个作品是对宋代舞谱中的术语进行的破译和复现研究,作为作品并非为舞蹈的历史原本,从而明确否认这个作品是古典舞。刘凤学的某些作品也有这种舞谱根据,但她也不称其为古代原始形态之作,而是她个人的“仿作”。
对于从事“古典舞”教学或“古典舞”创作的实践者们来说,或许没有时间思考那么多,只是按常规进行教学与创作就是了,但是对于理论家、评论家们来说却不能太随意,不能跟随实践者滥用概念,那会误导观众,误导“老外”,也会误导中国的年轻一代。几十年来,“古典舞”领域发生的这类事例已经不少,如把根据敦煌绘画雕塑创造出来的舞蹈说成是“敦煌舞”,让人以为那是唐代遗传的舞蹈,这也是一种误导。敦煌艺术石窟中的绘画,虽有某种现实中表现的根据,但其“三道弯”的基本形态主要还是美术家的创造,在其他任何古籍中和绘画中,并没有刻意描绘这种“三道弯”的,如果唐代舞蹈有这种动态特点的话,那决不可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我们知道,“三道弯”的基本形态最初出现在甘肃舞蹈家创作的舞剧《丝路花雨》中,又由高金荣教授编制出一整套训练,都是他们根据壁画、雕塑进行的创造,不能误认为是一种古代现成的舞蹈种类。在一些人看来,无论是谁都可以把某一墓葬的壁画或秦砖汉瓦中的舞蹈形态连接起来,像编考级组合那样随便串连一下,就成为一种假造的古代舞。古典舞不能再乱中加乱了!
由各种误解到误导,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让流传在外的唐宋乐舞还乡之必要。这些被严肃地保存下来的舞蹈,至少更偏于真实的历史。虽然古典舞的问题,没有必要去追讨什么历史责任,但对于理论工作者、学术探讨者和在座的舞蹈博士们来说,却不能随波逐流,不能再蹈覆辙,而要以一种自强自信的民族意识,以一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待古典舞问题的“名”与“实”。这样,才能把真正属于我们的中国舞蹈故事讲好,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