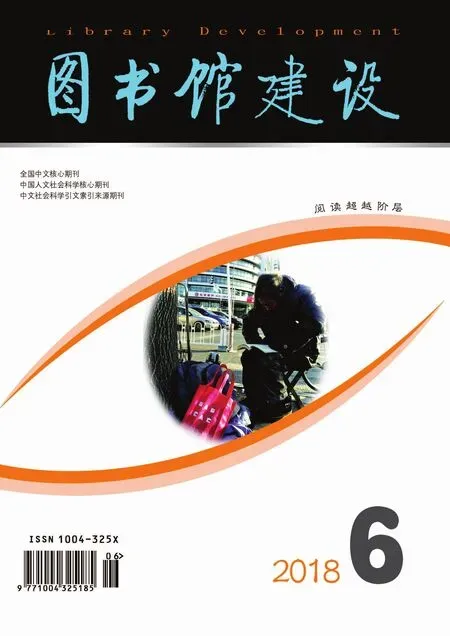1840年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成就述论*
陈彬强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福建 泉州 362000)
1 引 言
“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中后期,通常指1840年之前中国与世界各国通过海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交往的通道,涉及港口、贸易、管理、外交、航海技术、文化传播、民俗交流等诸多方面。1840年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学”经过不断完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门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1]。早在我国先民劈波斩浪、开辟海外交通的漫长岁月中,即已留下灿若星河的文献资料。但这些文献记载显然还停留在“记录”阶段,主要功能是搜集、记录、保存“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见闻,未能从中发现有系统性稽考源流、辨识讹误的著述,因而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整理和研究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徐继畲、魏源等为代表的封建知识分子,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开始将眼光投向西方,研究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外夷”的域外诸国,探寻他们成为世界强国的原因,为清政府寻找“制夷”方略。例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都是在探索“制夷”良策。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探索都和“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学”开始形成并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2]13。这一时期是中国人因应西方入侵而被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林则徐诸人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奠基人。而称得上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进行系统性地整理研究并取得令人称道的成果,则是直到清末的丁谦、沈增植诸人才真正开始。本文拟就1840年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成就做一梳理、审视和总结,以期全面呈现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做出的基础性贡献。
2 清末民初的起步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人视野的逐步打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海外,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逐渐发展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自1840年以来直到民国初年的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学”形成的重要时代,许多清末学者都实质性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学术建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逐步取得令人称道的成果,而其中成果最丰硕、影响最大的当数丁谦和沈曾植。
丁谦(1843—1919年),字益甫,同治四年(1865年)举人。丁谦一生博学多才,工于骈文、散文,一生著述甚丰,著有《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元马可博罗游记补注》等多部史地著作。《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对后世的学术有较大影响,它系统考证了我国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许多重要地理问题,历来被学界称为“天下之奇作”[3]。《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分上、下两集,共69卷,上集考证了《汉书》《后汉书》《宋史》《元史》《明史》等17种正史中的地理志和外国传,下集考证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异域录》等13种域外地理著作[4]。丁谦一方面承袭“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对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和各种地理著作进行系统的考订、校勘、释义,订误了不少地名、人名和航线,贡献颇多。例如,对婆罗岛的考证,丁谦认为其始载于《梁书》,《隋书》亦作“婆利”,《唐书》则作“婆罗”,《宋史》作“渤泥”,《明史》作“渤尼”,都是据音译而作,无固定用法之故[5]162。至于史书所言“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6],乃是因为古代航海技术落后,航海活动皆循岸而行,不敢直跨大洋,因此从中国到婆罗岛的航线须沿交趾洋靠海岸一侧南下,经马来半岛转向东行才能到达[5]162。其考证结果与现代学者的观点相符[7],足见丁谦洞察力之敏锐和考证之精详。另一方面,丁谦也注意反思传统史学的不足,尽量搜集、利用域外史地的各种文献资料,扩大研究视野,力图摆脱时代的局限。例如,在对“安息”的考证上,他运用世界史知识正本清源,指出前人将“安息”考订为“亚细亚”是错误的,“安息”实为古波斯地,国名源自其国王“阿赛西”名号的转音,其王世代以“阿赛西”第几为号,汉人误认王名为国名,称为安息[8]188。丁谦的考证严谨周密,结果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时人所叹服。北大学者陈汉章评价称是书“以实事求是之学课士,多所成就”,其考证水平之高“并非诸儒所可及”[8]5-7,可见其影响之大。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精于中国传统学术。他是我国首位对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进行系统校注整理的学者,著有《佛国记注》《诸蕃志注》《岛夷志略广证》等书。沈曾植在校注过程中非常注重对版本的校勘,通过比勘各文献记载来源的异同,纠正讹误,力求接近事实真相。例如,他将《佛国记》与《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书对勘,指出“竺刹斯罗”即《大唐西域记》的“怛叉始罗”,“希连河”即《水经注》“希连禅”;在《诸蕃志注》中,他考订出“三佛齐国”即《唐书》“室利佛逝”,“篷丰”即《岛夷志略》彭坑,“弼琶即《新唐书》《酉阳杂俎》“拨拨力国”,“弼斯 国”即“巴索拉”等[9]。据统计,沈曾植根据《岛夷志略》《诸蕃志》《佛国记》《太平寰宇记》《宋史》《职方外纪》《异域录》等考订出的域外地名达近百条,为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做了很多筚路蓝缕的工作,对后学的影响极为深远[10]。
丁谦和沈曾植在继承魏源、徐继畲等人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经典史籍予以校勘、考证、注释,在实践中还创新了“揆地望、度情形、审方向、察远近、核时日、考道途、辨同异、阙疑似”8种文献考证方法[11],提升了辨误能力,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学术理论方法,使“海上丝绸之路学”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问。不过,由于丁、沈二人不通外文,也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在某些考证上难免犯错,最典型的如丁谦认为现代的欧洲人种出自亚洲,系亚洲人分南北两路迁入欧洲所传[5]58-71,以现有常识来看,当然是错误的。但瑕不掩瑜,他们的努力开拓为将“海上丝绸之路学”剥离传统经史之学,引入全新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诸多贡献,也为后学树立了典范,可以说代表了清末民初“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研究的最高成就。
3 民国年间的辉煌阶段
民国年间,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欧美学术成果加速进入中国,“西风东渐”成为一时之盛,中国的传统学术受到巨大冲击,“西学”的影响则日益深化,有些学者踏上了欧美留学之路,开始尝试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解答“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这一阶段,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整理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以冯承钧(1887—1946年)、张星(1888—1951年)、向达(1900—1966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都曾留学或访学于欧美,既受中国传统学术熏陶,又懂外文、通“西学”,他们将西方最新的学术成果应用于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了许多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宝贵成果。
3.1 翻译考订外国文献
冯承钧在留欧期间与沙畹、伯希和等精于中外交通史研究的汉学家均有来往,深受西方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回国后翻译了大量中外交通史名著,如沙畹的《西突厥史料》、沙海昂译注的《马可波罗行纪》、伯希和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等共计40种[2]34,其中许多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关。冯承钧在翻译西方文献过程中,不仅参考了通行的多个版本,且善于旁征博引,使用大量中文文献予以比证,指出不少原作者的错误,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例如,他在转译沙海昂法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纪》过程中,不仅参考、比对了地学本、颇节本、剌木学本、玉尔-科迭本、拜内戴托本等多个不同版本的优劣,还大量引用了《元史》《辍耕录》《文献通考》,以及《伊本·白图泰游记》《波斯行纪》《使臣行纪》等多种中西文献,予以互相比对,考订各种史实,澄清了马可·波罗与《元史》所载元枢密副使孛罗系同一人等多个沿袭已久的错误说法[12]。冯承钧的译本文质相间,注释博洽,考订审慎,在读者当中的影响也最大,是学术界公认的最佳中译本。
另一位早年留欧学者张星,其1930年编纂出版的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书翻译、辑录的外国文献达42种之多,如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教皇约汉柯拉的《大可汗国记》、麦锡克的《拔都他印度及中国游记》、刚德赛克齐的《海敦纪行》等,还有相关的通报、地图、考古报告书,很多均属张星首次辑录、译介[13],有些迄今未见新译本,仍是研究人员必备的参考资料。张星在汇编过程中,运用“中西史料比勘法”,对所辑录的文献均予以校注考释,既有以中文记载证西文之误,也有以西文记载证汉籍之失,更多的是以中西文献互为补充,从而使其搜考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应用价值。
3.2 编纂汇录中国文献
此项工作以张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为最,基本上摸清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家底。该书辑录的中文文献达274种,“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者,无不爬罗剔抉”[14]。不仅全面摘录了中国古代的正史、野史、游记、文集、笔记,甚至将矿石、动植物的记载也录入书中。张星认为这些见载于中国古书的异域事物,亦足以证明古代中西方海陆交通之繁盛,可见其所辑资料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除此之外,向达的《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图书叙录》,岑仲勉的《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王庸的《宋明间关于亚洲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许道龄的《南洋书目选录》,所载资料很多都是已佚古地理书的叙录,也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15]。
3.3 校注整理古代典籍
冯、张、向诸人均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在校注、整理中国古代典籍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国外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用西方实证研究方法来解决相关学术问题,使文献整理工作突破了中国传统考据之学的局限,为“海上丝绸之路学”的现代学术建构奠定了基础。冯承钧在校注《瀛涯胜览》《海录》《星槎胜览》《诸蕃志》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运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须广采东西考订学家研究之成绩,否则终不免管窥蠡测之病”[16],因此,对众多人名、地名、物产的考释,都尽量做到博采众长、小心求证,力求纠误勘讹,恢复全书原貌。例如,他在校注《瀛涯胜览》“古里国”的“狠奴儿”中指出:“旧考作Cananore,对音未合,今从伯希和说以对更北之Honavar(Honore)”[17]。现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狠奴儿即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卡利卡特向北199里的Honavar,今名霍瓦那[18],冯承钧采信伯希和的观点是正确的。另一部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文献校注整理成果是张维华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他以中文史料为主,辅以西文载籍为比证,运用“溯源、辑补、比证”的研究方法,对《明史》中的“佛郎机传”“吕宋传”“和兰传”和“意大利亚传”进行系统的考订汇释、比对校勘,澄清了学术界的许多疑点,被誉为“是中国与西方殖民者早期交往史的开山之作”[19]。
3.4 挖掘搜考海内外文献
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新发现是这一时期取得的另一项重要成就。其中,以向达、阎宗临等人从海外寻访、抄录回的文献最为难得。1935年,根据北平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达成的互换馆员协议,向达赴英、德、法等地寻访古籍,共抄回几百万字珍贵的文献史料,其中就有《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本珍贵的记录航路航向的针路簿。《顺风相送》是目前证明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等岛屿的文献资料,是最有信服力的历史证据。另一本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献《身见录》,则是阎宗临从梵蒂冈图书馆中抄录回来的。《身见录》成书于1721年,系樊守义奉康熙之命,随同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循海路出使罗马教廷期间,根据其留欧见闻撰写而成,书稿从未刻印,深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中。1937年阎宗临在梵蒂冈图书馆中发现了这部手稿,并于1941年公开发表《身见录校注》,使这部极为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得以走进国人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国内各地也相继发现了不少有关郑和的文献史料。袁嘉谷、李士宣、郑鹤声、萨士武、张星等学者分别在云南昆阳、福建长乐和泉州、江苏南京各地发现了《马哈只墓碑》《郑和家谱》《娄东刘家港天妃石刻通番事迹记》《天妃灵应之记碑》《郑和行香碑》《静海寺郑和残碑》等深藏在民间的碑刻、家谱文献,为研究郑和的先祖、家世、信仰,以及郑和下西洋事件提供了极珍贵的史料证据。
尽管民国年间国运危机四伏,但众多从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中国学者仍坚持克服困难,竭尽所能地搜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为子孙后代保留下一份宝贵的文献遗产。在中西学术交融的大环境下,不少学者走出国门,将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典文献译介到中国。他们已逐渐走出中国传统文献考据法的局限,以中外史料合璧互证,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献中找到与中国文献史料相对应的记载,并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加以考订汇释、比对校勘,取得了中外瞩目的成就,为“海上丝绸之路学”向现代学术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停滞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中国史学的主流位置,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则处于边缘地位,在学术界较少发声,整体处于停滞阶段。但仍有一批学者努力坚持,默默奉献,他们在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的某些领域取得了持续性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4.1 编纂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这项工作的发起人是向达,他在1960年代就积极筹划《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文献整理工作,拟将除正史以外的中外交通史著述都加以整理、出版。丛书原计划出版41种,但因“文革”爆发而中止,丛书也只出版了向达整理、校注的《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3种。直到改革开放后,谢方继续主持该项工作,才得以继续完成向达未竟的事业。2000年《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重印时,已形成16册28种的规模[20]。这套文献之前大部分都未经过整理、校勘,有的甚至从未刊印过,还有一些有关西域南海的古地理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仅存的一些片段散见于各类书之中,也被校编者辑录出来,整理成书。得益于向达当年的大力倡导和亲身实践,这套丛书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必读文献,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4.2 搜集整理相关考古文献
1949年之前,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发掘和研究极为薄弱。建国以后,考古发现有了很大进步,如在广州发现了宋代《重修天庆观记》碑刻[21],在扬州发现了元代两块拉丁文碑刻和4块用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写的伊斯兰教碑刻[22],这些石刻文献都相继得到了整理和研究。而发现石刻数量最多、价值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数福建泉州。有赖于泉州地方史研究专家吴文良的毕生搜藏和保护,使得大量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石刻得以从战火中幸存下来,成为20世纪中叶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957年,在郑振铎、夏鼐等人的关心、指导下,吴文良将其收藏的石刻以文物照片、文字辑录、补充说明、专题论述相结合的方式予以稽考汇释,以《泉州宗教石刻》为名正式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轰动。吴文良所辑录的石刻文献达200多种,种类非常丰富,共包含5大类:一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伊斯兰教石刻,这类石刻保存数量较多,大约有90种;二是用蒙古文、叙利亚文、拉丁文、八思巴文书写的基督教石刻,都有十字架、天使和莲花等图案,约20多种;三是用汉字书写的摩尼教石刻,碑碣中刻有华盖、火焰、莲花、十字架等图案,这一类石刻极其珍稀罕见,仅存寥寥数种;四是用泰米尔文字书写的印度教石刻,此类石刻最多,达100多种;五是与宗教无关,但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九日山祈风石刻、元代大使奉使波斯墓碑石刻,以及元将亦黑迷失在泉州所立的一百二十大寺看经碑记等十几种[23]。
1958年,苏联科学院编纂出版《世界通史》,请求中国提供100幅图片,其中就有15幅是吴文良提供的[24]。这些碑刻大多是宋元时期外国蕃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泉州定居留下的宗教遗迹,为研究当时中国与亚欧非诸国的海外交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5 改革开放后的全面繁荣阶段
1978年至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领域百花齐放,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也走上了快速发展阶段,很多年轻学者相继加入,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各自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而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也随之进入全面繁荣时期,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显著提高,大大超越前人。
5.1 中文文献的挖掘出新
5.1.1 大量秘藏的档案文献得到公开
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权威部门所藏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布、整理、编辑和出版,大批官方文书,如诏、诰、起居注、实录、敕书、谕旨、奏本、题本、揭帖、奏折等得以陆续“解密”,极大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学”的一手文献资源。近年来出版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档案文献主要有《清代中琉关系档案》《清代琉球史料汇编:宫中档朱批奏折》《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粤澳公牍录存》等,将明清时期中国政府与琉球、东南亚的关系,以及妈祖和澳门问题的所有档案文献基本上都辑录出来,促进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5.1.2 民间文献的发掘整理全面铺开
以前不受史家重视的谱牒资料、针路簿、碑刻铭文、地图资料等民间文献,也纷纷进入文献搜集、整理范围,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陈佳荣、朱鉴秋主编的《渡海方程辑注》和《中国历代海路针经》,将我国古代航海针路的文献资料都辑录出来,集航海针路之大成,有不少针路簿系首次发现,极其珍贵[25];朱鉴秋编著的《中外交通古地图集》、蝠池书院编制的《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收录了大量反映古代中外交通的舆图、航海图、海防图及其他古地图,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26];郑振满、丁荷生主编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对福建地区的宗教碑刻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收集和整理,发现了不少涉海碑刻[27],为古代海路上的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文献证据。
5.1.3 域外汉籍的寻访取得巨大成效
同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日本与中国的海上交通历史悠久,朝鲜、越南也都有海路与中国通贡,过去他们以收藏中国的汉文典籍为荣,也留存了大量本国文人用汉文字书写的著作。但当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很少收藏这些国家的典籍,使得现在的国内学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只能通过转引相关论著的文字片段为据,于学术研究极为不利[28]。随着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得以走出国门,寻访域外汉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近年来出版的东亚地区域外汉籍主要有《日本汉文史籍丛刊》《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燕行录全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等,以影印居多,文献种类丰富,既有官方文书,也涉及家谱、诗文集、日记、碑文等民间文献,大多系国内首见,其中包含了大量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史料。
欧美地区的图书馆历史上也搜集、保存了不少汉籍,也是海外访书的重要对象。台湾学者方豪就曾多次走访梵蒂冈图书馆,在台湾影印刊布了一些梵蒂冈藏汉籍[29]。近年来,中国学者赴欧洲访书,整理出版了一些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汉籍,如《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等,为我们了解欧洲汉籍的馆藏分布、研究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5.2 外文文献的译注整理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此前较少接触的外文原始文献,开始逐渐走进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且不再局限于英、法、日等少数几个语种,还有韩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有些学者将其中一些重要文献翻译成中文,并用中文文献加以考释校注,确保了史料的可靠性,有效补充了我国文献史料之阙。此项工作,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内容最为丰富。该套译丛收录、翻译了古代阿拉伯、突厥、波斯和欧洲等地作家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以及一些中外关系史研究名著,从1982年开始至今,共出版了20余种。其中有不少涉及海上丝绸之路,如《中国漫记》《道里邦国志》《东印度航海记》《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大帝国史》《道里邦国志》《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国帝国概述》等,均为第一手资料,很多系首次全文译介到国内。该套译丛还收录了《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和《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两部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文献史料汇编。前一部书搜集了8~18世纪阿拉伯人、波斯人与突厥人有关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的大量原始文献史料,并有许多重要的考订[30];后一部书则从90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辑录了有关远东的记载,时间跨度为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4世纪,所搜集的文献相当广泛和全面[31]。这套译丛的出版,拓展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史料来源,而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引用了大量中文文献史料对原著作了精详的考释,使得该套译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迄今仍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
5.3 专题文献的搜集编纂
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特点是散而繁杂,经过千百年积淀,相关文献记载可谓浩如烟海,郑和、妈祖等重要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专题文献,更是散见于各种古籍、档案、文物及民间传说故事中,非常驳杂,搜集、整理工作十分艰巨。近些年来,由于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资金投入,以及研究队伍的持续壮大,使得该项工作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由莆田学院牵头组织编纂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排印本)和《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影印本),已基本将古今中外关于妈祖的小说、戏曲、史志、经书、诗、碑文、档案,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论著辑录完毕[32-33],堪称目前最完备的妈祖文献,其中部分文献尚属首次面世,弥足珍贵。而由郑鹤声、郑一钧主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自1980年出版后,即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是郑和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2005年,原编者之一郑一均先生在原书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中外相关文献史料,出版了增编本,使之成为郑和下西洋资料最权威的汇编本,也是郑和航海乃至明代海外交通史料的集大成者。此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海疆文献初编》和《中国海疆文献续编》影印了100多种历代以来有关海防、海军、海运等海疆史料的珍稀古籍,《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及其续编、《中国南海诸群岛文献汇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文古籍中的马来西亚资料汇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中国边境史料通编》等,也均是各自专题领域的重要文献整理成果,为研究人员查找、利用相关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
5.4 二、三次文献的开发利用
相较于影印出版和资料汇编,目录、提要、索引、综述等二、三次文献的开发进度要慢一些,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尚没有出版过针对整个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书目提要,但某一具体领域或某个学科的专题文献目录提要则较丰富,如《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清代档案中的海难史料目录》《中国涉海图书目录提要》《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等。此外,已整理出版的沿海各省地方文献及域外汉籍的书目提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寻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线索,如《浙江文献总目》《江苏地方文献书目》《山东文献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续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福建文献书目》《海南文献总目》《海南地方文献书目提要》《广东文献综录》《广东文献书目知见录》《台湾文献书目解题》《东洋文库汉籍丛书分类目录》《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录》《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等,从中按图索骥,或可挖掘出一些尚未公开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史料。索引编制的成果较少,仅见有《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海南文献资料索引》等少数几种。综述性的图书主要有梁二平、郭湘玮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文献导读》、龚缨晏主编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等,对于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来源、种类,及其相关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热点和趋势均有重要价值,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入门的必备参考书。
6 余 论
综观百余年来的成果,不难发现,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研究,整体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历程。以丁谦、沈曾植为代表的清末学者尽管已经“开眼看世界”,开始关注西方,但仍没有走出经史之学的窠臼,其文献整理主要还是遵循诠经读史、文献考据的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再加上不通外文,对现代知识所知有限,也无法接触国外学术动态,因此,在考据结果上经常会犯一些常识性错误,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通过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考证,来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从而将“海上丝绸之路学”引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应该加以肯定。而到了民国年间,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现代“新学”也因“西风东渐”而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这一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开始接受现代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训练,掌握了基本的科学知识,文献整理工作开始摆脱传统学术束缚,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新材料的叠加效应,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学”进入一个繁荣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有些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受到国外同行的广泛赞誉。解放初期,“海上丝绸之路学”整体处于边缘位置,相关文献整理研究成果较少。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得到彻底解放。近年来,各种学术思潮碰撞交融,中外交流日益频繁,研究方法层出不穷,文献史料推陈出新,研究队伍发展壮大,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学”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而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远迈前人,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
尽管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基础性工作,目前也只能算是良好的开端,未来仍需凝聚各方力量,开展跨学科、跨地域、跨机构的多方合作,达成共识、共同推进。图书馆作为文献收藏和管理机构,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前形势下,可以考虑从3个方面入手,积极参与该项工作:一是利用图书馆馆藏优势,加强谱牒、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谱牒资料,各馆近年来都加强了收藏,这座珍贵的文献宝库,亟待挖掘。例如,南宋末年担任泉州市舶司达三十年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其“导元倾宋”致使宋军海战失利而走向覆灭,是宋元政权更迭时期的重要人物,但《宋史》并未为其立传,相关事迹语焉不详。而福建永春《蒲氏族谱》和广东《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对其生平事迹均有详述,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可极大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类似的谱牒文献还很多,现大多藏于各图书馆而鲜为人知,需尽快予以发掘和整理出版,以资利用;二是针对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特点,大力开发二、三次文献。此项工作是目前文献整理的一大弱点,远远落后于陆上丝绸之路,急待加强。图书馆可根据研究团队和馆藏文献特色,编写《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献目录索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目录提要》《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叙录》等二、三次文献。通过将零散、繁杂的文献进行有序化爬梳整理,使读者既可以获得对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整体认识,也可以根据目录、提要和索引按图索骥,快速找到自己所需的文章,大大节约文献检索时间。三是联合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数据库。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没有一个专门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资源数据库,于学术研究极为不利。而图书馆拥有资源和人才、设备优势,完全可以承担这项基础工作。笔者建议由国家图书馆牵头,各省级馆参与,按照各自馆藏特色分工建设,将现有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合并上传,而尚未电子化的纸质文献则予以全文数字化后上传至文献资源库;同时,建立联合文献目录库,方便用户检索。此外,还可通过与博物馆、档案馆等部门合作,将各自特色的文献、文物和档案资源予以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和有机整合,实现数字化共建共享,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学”研究走上快速发展道路。
今后,随着频繁中外交流带来的“文献大发现”,以及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工作还将继续保持快步前进。我们期待更多、更新的文献整理成果面世,也期待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数据库能够尽快开发、投入使用,以形成强有力支撑,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持续繁荣发展。
[1]龚缨晏.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2]龚缨晏.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3]赵 荣,杨正泰.中国地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
[4]徐兴海.丁谦的历史地理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81-84.
[5]丁 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2册[M].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6]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五,列传第八十三[M]//《二十五史》编委会.二十五史:卷5,南史、北史、隋书.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1043.
[7]陈佳荣,谢 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0.
[8]丁 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1册[M].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9]许全胜.沈曾植与早期中外史地研究[C]//耿, 朴灿奎,李宗勋,等.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66-78.
[10]苏继.岛夷志略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4.
[11]丁 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4册[M].影印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48.
[12]波 罗.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
[13]修采波.张星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J].史学史研究,2000(3):96-104.
[14]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3:5.
[15]修采波,俞晓辉.向达对整理中外关系史料的贡献[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56-64.
[16]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2291.
[17]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5:26.
[18]万 明.郑和七下西洋——马欢笔下的“那没黎洋”[J].南洋问题研究,2015(1):79-89.
[19]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历史研究,1996(1):110-124.
[20]孙文颖.中国经典古籍的文本价值挖掘——谈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编辑出版[J].出版广角,2012(1):32-33.
[21]戴裔煊.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公元十一世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往来贸易关系以及关于三佛齐和注辇国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J].学术研究,1962(2):63-76.
[22]耿鉴庭.扬州城根里的元代拉丁文墓碑 [J].考古,1963(8):449-451.
[23]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3-4.
[24]马丁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吴文良[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1):54-58.
[25]姚 芸.以出版情怀共同打造国家精品项目——《中国历代海路针经》组稿及编辑出版实践[J].出版发行研究,2017(6):100-103.
[26]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M].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13:前言.
[27]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前言.
[28]许林平,孙 晓.近三十年来域外汉籍整理概况述略[M]//胡振宇.形象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1-242.
[29]荣新江.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M]//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西初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139-144.
[30]Ferrand G.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M].耿,穆根来,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中译者序.
[31]Coedè s G.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M].耿,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3.
[32]刘福铸.妈祖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展望[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5):21-26.
[33]孙 晓《.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述评[J].莆田学院学报,201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