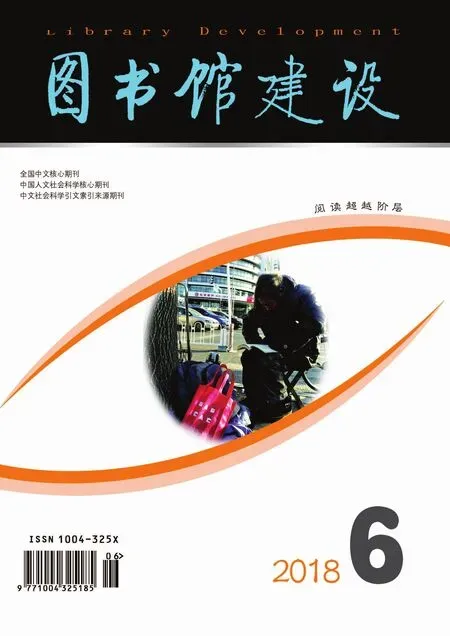论20世纪初日本在华所建四大图书馆的文化侵略功能*
王一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文献资料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7)
1 引 言
日本的对华侵略,在军事和经济之外,从来没有忽略旨在同化或奴化中国人民、削弱其民族精神、消弭其反抗斗志以便对占领地进行完全殖民统治的文化侵略。作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文化教育机构,图书馆在对华文化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日本所重视。从在日租界设立居留民团,又于东北建立“满洲国”到蚕食华北,日本政府将在华创办图书馆作为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20世纪初的天津日本图书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图书馆,还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无不是在日本政府觊觎中国和朝鲜等国家而推行“日本大陆政策”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中,“满铁”图书馆更是“满铁”总裁后滕新平提出的“文装的武备”殖民侵略思想的直接产物。随着日本军事侵略的逐步升级,在馆藏、读者服务、社会活动方面,这四大图书馆的文化侵略功能愈加显著。
2 日本在华建立图书馆的历史背景
2.1 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侵华的根源
起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持续了14年的侵华战争,是日本政府贯彻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所谓日本大陆政策,又称大陆经略政策,即日本谋划的自朝鲜、中国台湾到中国东北、蒙古、中国华北、中国全境的分步骤侵略,进而吞并整个亚洲,继而称霸世界的侵略政策。作为19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基本国策,日本大陆政策的出笼,既与日本“以忠信、勇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武士道’”[1]历史传统有关,更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近代化资本主义道路、军国主义急剧膨胀而迫切对外扩张企图雄踞亚洲之首乃至立于世界之巅的必然结果。
1895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这其实是日本实施日本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战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澎湖列岛和台湾。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也为继续有效推进日本大陆政策,日本与俄国开战。战后,双方签订《朴茨茅次和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中国“南满”地区的租借权[2]。之后,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以便日后将爪牙伸向中国关内,日本相继在“南满”地区设立关东都督府、“满铁”、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侵略机构[3],开始了对中国东北民众殖民统治、奴化教育、思想渗透的文化侵略行为。
2.2 “文装的武备”论是贯彻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武器
表面上看,“满铁”是一家企业经营会社,实质上则是日本国家机关、政府的代行机构,是法学意义上的殖民会社。简言之,它是为了执行日本大陆政策而特别设立的代行日本政府统治“南满”的殖民机构。“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是“文装的武备”论的始作俑者,他认为殖民统治不应局限于经济,还应该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只有这样,日本的大陆政策才能贯彻到满洲民众的生活中”[4]。所谓“文装的武备”,其内涵是“以文事的措施,以备他日侵略之用”[5]。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也就是“揭王道之名以行霸道之实”[6]。
“文装的武备”实施范围无外乎宗教、卫生、教育、文化领域。仅就“文化”而言,“满铁”将其触角伸及文化事业各个领域——出版、科研、社会团体、博物馆及图书馆。从1907年“满铁”建立第一个图书阅览场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其在附属地沿线一共建有31个规模不等的图书馆。无论是在开始时为在华日本人提供参考资料服务、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还是后来自觉承担起宣传日本文化、宣扬“大东亚共荣”和“五族(即汉族、日本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协和”的责任,再到全面抗战后成为为侵略军提供精神慰藉的服务场所、为战事提供文献资料的情报基地,“满铁”图书馆其实一直都在践行“文装的武备”的殖民思想。
2.3 “对支文化事业”的实质是文化侵略
1923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此为标志正式开始推行在华文化事业,决定在北京设立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文化图书馆;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华文化事业所使用的资金有两个来源,一是应该退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二是日本在英美的抵制下未能成功接收德国在山东的铁路和矿产等方面多项权利而蛮横无理地向中国强索的所谓“赔款”。也就是说,他们用中国人的钱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他们的文化事业。之所以说该文化事业是“他们的”,在于他们打着中日“合作”的旗号、宣称该文化事业由双方共同完成,却在资金使用、人员配备、具体计划等方方面面将所有权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终使中国人认识到“对支文化事业”的真实目的是“伸张其国家行政权于中国领土,以肆其文化侵略,而怀柔中国人”[7]。
1936年5月,在日本制造挑起“华北事变”后,为应和蚕食华北的大计方针,日本外务省发布“对支文化事业”新规事业(又称“新计划”)。它“是日本为了配合即将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在文化事业上所做的方向性的调整”,其目的是使“对支文化事业”尽快摆脱“为学术而学术”的禁锢,而将其强行拉入政治和侵略的轨道;其内容是“中日之间,不必专事研究陈腐学问,或做考古学的研究,应先实行为中日两国国民亲善之工作。……实行有国际文化色彩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在中国各地新设日本文化图书馆,积极介绍日本文化”[8]。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相继建立。
日本大陆政策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基本国策,根本目标是扩张和侵略。在此背景下,代行政府殖民统治的“满铁”应运而生。而为了贯彻“文装的武备”“满洲”殖民思想,附属于“满铁”的“满铁”图书馆成立。“对支文化事业”是日本大陆政策指挥棒下的文化渗透方式之一,其“新计划”更是作为所谓“亲善”的工具,由此设立的北京、上海两家近代科学图书馆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政治的因素而无法保持文化的纯粹。这样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图书馆除了具备一般的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的效用外,更多了一份文化侵略的功能。
3 图书馆的隶属关系与人员构成
3.1 直隶政府决定了图书馆的非民间性
日本在中国建立的四大图书馆中,只有天津日本图书馆自称是“自治团体”。事实上,该图书馆的确由生活在天津的10余位日本侨民联合发起,于1905年8月7日成立。表面上看,它属于民间组织,但实则与日本政府关系非同一般。第一,从日本政府的主观意愿来说,欲使日租界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基地,故而必须注意对租界的管控,而对租界内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团体和组织也都务使“尽在掌握中”。第二,从图书馆常设委员、评议员构成看,“官员”不乏其人,其中官员评议员有16人之多,占评议员总人数的24.6%。第三,天津日本图书馆初建时,馆址设在天津闸口日本俱乐部,而这个俱乐部是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的主持下成立的。第四,1907年8月,“大日本租界局”改为“居留民团”,天津日本图书馆划归其管理与经营,而居留民团直接听命于日本总领事。这一切都显示了该图书馆的日本官方背景,暴露了其与日本政府非同寻常的关系,也决定了它参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必然性。
如前如述,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是日本政府“对支文化事业”新计划的产物,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直接管辖。正如居留民团实则参与天津日本图书馆的馆务——包括直接参与修订《天津日本图书馆规程》《天津日本图书馆事务章程》《天津日本图书馆图书阅览细则》[9],两家近代科学图书馆本身也没有多少权力,文化事业部不仅在资金方面严格按照《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的规定拨付,且严苛限制使用范围,更插手馆务工作,规定“图书馆馆长、总务主任、司书、庶务、会计主任的任免必须经外务大臣的批准,图书馆助理、特聘人员的任免必须经总领事批准”①。而图书馆规程、经营方针的制定、修订等必须由外务大臣批准;图书馆出版物必须经过外务大臣及北京、上海日本总领事审核;图书馆事务报告书、成绩报告书、运营状况必须定期提交给总领事等[10]。同样地,“满铁”图书馆的管理规章也非由图书馆自身制定,随着从“阅览场”过渡到“简易图书馆”又发展到“图书馆”,《图书阅览场规程》《简易图书馆规程》《大连图书馆规则》等均由“满铁”会社制定。
日本在华建立图书馆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收藏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产业、殖民、地方志、官方档案、军事材料等在内的一切关于中国的书籍、资料和情报,以便于其对中国的了解、认识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为蚕食、侵吞中国做文献上的准备。因此,图书馆的任务是“用所藏图书,配合当时的形势发挥其作用”[11]。由此便不难理解“满铁”图书馆的隶属关系——1906年,“满铁”成立;1907年,“满铁”图书室筹建,隶属“满铁”调查部;1908年12月,调查部更名调查课。顾名思义,调查部(课)是“满铁”所辖下的专门收集情报的调查机关,“从日俄战争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十年间,满铁调查部凭借从各方面收集到的大量情报资料,为日本有关方面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方向和依据”[12]。显然,“满铁”图书馆存在的价值,一是为调查部(课)进行情报资料调查提供文献保障;二是为调查部(课)收集提交的6 000多份调查报告、出版发行的数千种图书资料和杂志[8]进行专业的整理、分类和保存。
3.2 图书馆决策者官员占比高
无论是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评议员,还是“满铁”图书馆最早的创始人,抑或是各图书馆的馆长,官员占比很高,而图书馆专业出身的微乎其微。除了神田城太郎(1920.2—1925.3)、佐竹义继(1926.3—1926.5)、柿沼介(1926.5—1940.4)在加入“满铁”图书馆出任馆长之前,分别在京都大学图书馆、京都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东京日比谷图书馆从事过图书馆专业工作以外,大多数馆长从未与图书馆打过交道。“满铁”图书馆筹建者冈松参太郎有两重身份,一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法学博士,一是“满铁”调查部(课)理事。事实上,“满铁”调查部(课)这样的含有国家智库性质的组织就是由他参与建立的。“满铁”图书馆既然隶属调查部(课),那么,调查部(课)官员兼任图书馆馆长似乎天经地义。先后担任(或兼任)“满铁”图书馆馆长的调查课官员有岛田孝三郎(1918.1—1919.7)、唯根伊兴(1919.7—1920.2)、水谷国一(1940.4—1941.3)、菊地池(1941.3—1942.2)、北川胜夫(1942.2—1945.8)等。
天津日本图书馆最初馆务由常设委员(1943年1月29日改为图书馆委员)和评议员负责,不设专职馆长。不少常设委员和评议员身份显赫。常设委员主要有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官员奥田竹松、“大日本租界局”首任理事西村虎太郎等;主要评议员有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伊集院彦君、小幡酉吉。另外,至少还有两名情报官员担任评议员,一位是日本间谍特务机构内阁情报系统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之一的阪西利八郎;一位是“日本老牌经济特务”[13]吉田新七郎。
大量特殊身份的官员存在于图书馆事务中,势必会强化对图书馆的思想控制,打破作为文化单位的图书馆的正常发展规律。出于维护本国政府利益的本能,官员们也会自觉地将图书馆视为文化侵略的辅助工具。
3.3 管理者的行为和思想倾向左右着图书馆的走向
由于职责所在,官员们总是习惯地竭力执行政府的决策,其行为难免利己(国)排他(国)。例如,从法学专业性上说,“满铁”图书馆筹建者冈松参太郎堪称“法学大家”,撰写过《注释民法理由》《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论》等法学著作,“在日本民法学史上留下重大贡献”[14]。但他同时又利用法学专长配合时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参与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不仅“提供台湾旧惯调查事业及台湾旧惯立法法理论基础”,而且“致力将台湾的旧惯一种‘前近代’的法律,改编入西欧法体系”[15]。天津日本图书馆的评议员伊集院、小幡酉吉凭借其天津总领事的身份,以自己对所驻国的了解,竭力找寻为本国谋取更多利益的机会,而罔顾所驻国利益。前者于1903年4月代表日本政府与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强迫清政府对之前日本非法扩占的中国土地予以承认;后者于驻华大使参赞任内,在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协助公使日置益频向中国施加压力。
在图书馆决策和管理人中,不乏对中国深怀偏见之人。天津日本图书馆首任常设委员之一的奥田竹松曾经撰文《我观清国人》,对大和民族怀有强烈的优越感,反过来对中国人极其厌恶,认为中国人只有个人主义而缺乏国家观念,甚至将中国人列为“利之念炽盛之人种”“对利害计算极敏锐之人种”“胆怯懦弱之人种”,最终得出“固陋保守,难以改易”的结论[16]。常设委员、评议员、馆长们多有反华倾向,因而积极支持或配合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首任馆长上崎孝之助原是东京朝日经济部次长,与图书馆从来没有过关系,只因为对日本侵华“持积极意见”[17]而被推送上馆长之位。
“九一八”和“七七”事变的爆发可谓一面照妖镜,它将侵略者或支持侵略者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满铁”图书馆奉天馆馆长卫藤利夫是“五族协和”思想的积极拥护者,他为“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图书馆一改读书消遣的文化场所而变为“王道思想的讨论场、国家哲学的大熔炉”兴奋不已,而把“满洲国”的建立视为“宏伟的事业”,积极建议关东军司令把以日俄战争为题材、宣扬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说《肉弹》(樱井忠温著)的英文、法文译本赠送给驻沈阳的上层外国人,为的是给他们“进行一次有效的历史启蒙”[18],从而为日本挑起战争辩护。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长山室三良在“七七”事变后,撰文将事变之所以发生栽赃到中国人的身上:“考其根因,实由中国未能了解日本之真意,提携未克实现有以致之。”[19]
决策和管理者们如此行为和思想无不与日本侵华政策同步,由他们掌管的图书馆自然不会只是“知识的海洋”那么简单,参与文化侵略并为军事侵略服务随着战争的升级而成为图书馆的主业。
4 为文化侵略提供服务的馆藏建设
4.1 服务对象的不同对馆藏的影响
文献是图书馆的物质基础,因此,藏书被认为是图书馆的五大要素之一。无论日本在华创办图书馆潜藏何种居心,藏书建设总是各类图书馆的基本工作。从藏书本身来说,它们虽然多半并不具有侵略属性,但这不妨碍被怀揣侵略目的的人刻意利用。换言之,馆藏文献的作用因人而异,知识的载体也可以被用来当作工具或武器。这在日本在华创办的四大图书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相对来说,天津日本图书馆、“满铁”图书馆建立较早,服务对象分别以在华日本侨民、“满铁”会社成员为主。天津日本图书馆由于经费的限制,馆藏以接受捐赠为主,这使馆方难以确立文献资源建设方针,难以确定文献收藏原则、范围、重点,难以实施购藏标准,而只能停留在捐赠者捐赠什么、图书馆就收藏什么的随意性、被动性、低层次馆藏水平上。既然该馆服务对象着眼于日本侨民,而乐意捐赠藏书的也是日本人,故馆藏以日文书刊为主。来自在华与日本各地的机构与个人所捐赠的书刊的内容,当然与捐赠者的思想倾向、一己私好与个人趣味有关,他们的反华情绪对所捐书刊的品种当然有直接影响。在这些日文馆藏中,意识形态意味比较浓重。这主要是军国主义意识是当时日本的思想主流,日本大量的出版物要么是此类宣传品,要么其中挟带此类意识,要么为此做外围与基础服务。这类书刊的大量入藏,无疑强化了在华日本侨民的军国主义思想,加剧了他们对中国的敌对态度。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官吏、军人读者急速增加,馆藏中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随之增多。“根据有关居留民团事务年报历年阅览图书各类的统计,有关中国的图书大都占据第二位,甚至有的年份还占据第一位”[20]。由馆藏的变化可以发现,天津日本图书馆为文化侵略服务的程度是逐渐增强的。
“满铁”图书馆从在大连设立图书室开始就被定位于为“满铁”会社成员提供业务参考、调查研究的场所[21],因此馆藏侧重文献的收集,主要内容包括东北地区民俗风情、地形地貌、矿产资源等,涉及铁道、矿山、港湾、产业、教育、卫生、工学、文学、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方方面面,以日、汉、英3种语言为主。随着“满铁”图书馆的不断扩张,图书馆遍布东北铁路沿线,除了大连,奉天、铁岭、开源、四平、公主岭、长春、本溪、抚顺、沙河口等地均设有图书馆。为了方便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为了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以便日后占领和殖民统治,“满铁”对各个图书馆的馆藏进行了功能分区。例如,最大、最主要的“满铁”大连图书馆侧重“收集普通图书,同时收集官方的档案以及军事机密材料”;奉天图书馆“主要收集古籍珍、善本和中国各地的重要方志”;长春图书馆“以收集东北地方文献为主”;哈尔滨图书馆“重点收集有关满蒙的俄文文献资料以及有关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文献,特别是关于远东地区的文献”[22],等等。
天津日本图书馆和“满铁”图书馆都有为特殊人群提供专门馆藏的服务。所谓“特殊人群”,主要指政府官员、高级军人、“满铁”的上层职员、关东厅和关东军机关的要员等。他们都持有“特殊阅览证”。这种阅览证不仅需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批准,还要经过图书馆的审查核准,因此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得到的。以“满铁”图书馆为例,持有特殊阅览证的特殊人群可以进入图书馆专设的“满蒙”“殖民”“交通”3个内部参考阅览室[23]。这样的“特殊服务”,无论是阅览者的“特殊”,还是馆藏的“特殊”,都已超出单纯的学术范围,而与侵略紧密相连。
4.2 为特殊目的而进行的馆藏建设
在以侵华为目标的日本大陆政策背景下建立图书馆,其目的性显而易见。抗战爆发前,“满铁”图书馆为了配合“满铁”对“南满洲”进行殖民统治,规定其自身的任务是“广泛搜集古今中外图书资料,供给‘会社’业务的参考”[24]。因此,该馆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地质资源、风土人情,特别是东北的地方志、地图以及政府机构出版的一般不经售的重要调查资料是垂涎三尺”[25]。不限东北地区的“地方志”是“满铁”图书馆的重点馆藏之一,它从“图书室”时期便开始注重搜集,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搜集到中国各省通志、府县志700部”[26]。1923年2月,该馆获专款用于采购地方志、地图、图绘、稿册、非公开发售的油印本县志、村志等[27]。经过十几年持续不断的搜购,仅“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方志,1940年时便已高达2 300余部[28],数量惊人。如此不遗巨细地对于地方志的搜求,只为了对中国各地进行深入毛细血管的彻底研究。天津日本图书馆也自诩对中国县志的收集是其馆藏的“一大特色”。他们很早开始搜集以河北省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各省的地方志,而以河北省地方志的收集最见成效。
为积极介绍日本文化而设立的北京、上海两家近代科学图书馆,其运营当然以此为中心,所明确的目的也是“向中国学者、学生等人士介绍日本自然科学发达程度、最新发明发现、人文科学及其他日本事情”[10]。既然图书馆标明“科学”二字,那么,馆藏必然偏向科学类,又以自然科学为主,涵盖医学、产业、工农业等,占比达70%,“人文科学书籍占百分之三十”[29]。既然以介绍日本先进文明为目的,馆藏中的日文书刊自然占据主流。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开馆之初,“以三万五千元日金向日订购各种科学书籍四五千种”[29]。在平时的馆藏建设中,日本权威学者的著作、有关日本历史产业文学等方面的最新著述、日本新闻报纸杂志、日本人述及关于中国的中国学论著、日译欧美书籍等都是重点搜购的目标[10]。“七七”事变后,图书馆“为应其势所趋,复多备有日本语学书及辞典等之副本,以供其需要”[30]。在日文馆藏方面,“满铁”图书馆同样重视有加。据不完全统计,仅“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日文图书资料就高达94 115种、179 416册,其中杂志1 906种、22 017册,报纸104种[23]。
对于日本在华建立的图书馆来说,在藏书的语种方面,中文和日文各有用处,广泛搜集中文古籍线装书,乃出于对中国珍贵典籍的占有目的;将中国地方志列为所欲竭力搜求的馆藏,其动机更是不言自明。因为地方志含有一区一地极为丰富的信息,是情报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地方志收集的意义不只可为经济文化侵略提供帮助,甚至可为军事侵略提供直接帮助;文化渗透少不了植入本国语言和文化,日文书籍便承载了这一使命。总之,这四大图书馆的馆藏建设超越了公共图书馆以提供正当的学术研究和健康的精神食粮为己任的一般属性,而多了一份辅助文化侵略的功能。
5 图书馆参与文化侵略的主要活动
5.1 举办日语学校进行日语教学
文化侵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侵略者在被占领国推行己国语言。作为社会教育机构之一的日本在华建立的图书馆,有意识参与传播和宣传本国语言的方式,一是将日本书刊作为馆藏建设的重点;一是推行日语教育、开设日语学校。在开办日语学校方面,四大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
1942年11月,天津日本图书馆开始在雇佣的华人职员中实行日语教学试验。在获取一定经验后,于1943年7月开办日语讲习课,按照受教者日语掌握的程度,分为初等部、中等部,每周进行两次教学[31]。1938年6月,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针对中国普通民众举办日语学习班。学习班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次年4月改为图书馆附属日语学校,也设初、中级两个班,教员由本馆日本职员担任,教材以日本东亚学校主编的《日本语读本》为主[32]。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更将日语教育作为图书馆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方式是[19]:(1)设立日语学校。它在东城、西城、北城开设了3间日语学校,所用教材是自己组织人员编写的《日文模范教科书》6卷、《日文补充读本》6卷。学校以短期培训班为主,学习期限3到6个月不等。(2)举办日语讲座。“七七”事变后,北京的日伪电台有专门的日语教学节目。该馆不但在阅览室里专门配备收音机供阅览者收听,而且还在节目结束后进行补充教学讲座。1937年11月,图书馆特别聘请大学教授、文化学者开设日语基础讲座。(3)开设师范科。为培养更多的日语教员,该馆开设师范科,招收有一定日文基础的中国学生入学,学习期限6个月。(4)举办日语研究会。这是该馆“把日语教育提升到专业学校级别”的措施之一,招生对象是日语程度达到一定高度的人。该会每周举办1次,时间90分钟,3个月为1期。
如此热衷推广日本语,其目的当然并非如日本人自己所说的“用博日华亲善之好转,……且为一般学术及现代文化之要素”[30],而是企图将日本文化强行输入以便同化、奴役中国人。
5.2 举办展览和演讲宣传“圣战”
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日关系陷入冰点。为给中国人民群情激昂的反日情绪降温,减少日本侵华的阻力,四大图书馆通过举办展览和演讲,以及制造舆论的方式为日军侵略行为辩护,竭力宣传“圣战”,美化“中日亲善”。
“满铁”图书馆的展览从来都紧跟侵略形势。“九一八”事变前,他们为配合日本占领东北和内蒙,举办“满蒙研究资料展览会”(1926.11)、“支那民族研究资料展览会”(1930.10);事变后,则举办了反映关东军占领热河的“热河文献图绘展览会”(1933.5)、展示日军侵略华北的“华北文献展览会”(1935)等。天津日本图书馆也不例外,1938年10月21日和25日,广州、武汉先后被日军攻陷后,该馆不但用“午后休馆”的方式加以庆祝,而且还于11月10日至13日,连续举办了4天图书展览,其主题的关键词为:“支那事变”“中国情况”“日本精神”“国民精神的唤起”[33]。选择这个时候举办这样的展览,其用心显而易见。不仅如此,在“日俄战争”结束35周年的1940年,该馆选择在3月10日“陆军纪念日”那天又举办了一场展览,陈列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相关图书120部,以及印章、书画、图片、明信片等100多件实物[34],全然不顾东北人民因该战争而遭受的深重灾难。
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举办的展览主要有:1940年12月14—27日的“近代日本文学展览会”。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举办的展览主要有:1938年12月10—15日的“日本中小学生儿童书画展览会”和“日本生活风景写真展览会”,1942年12月6—11日的“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展览会”,以及“日本艺术写真展览会”“北支蒙疆全貌展览会”等,不但大力弘扬日本文化,而且为战争添粉抹彩。
口头与文字鼓动当然也都是宣传的有效方式。天津日本图书馆筹划的天津读书会在3年时间里举办过30场演讲,演讲者的身份有些是日本军政界头面人物,演讲的内容有政治目光下的世界大势与格局,有对皇道精神的宣传,有日本必胜、在华日本人负有重大使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鼓动,有如何进行大东亚建设的讲解等。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满铁”图书馆则利用馆办期刊《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书香》进行“日本文化”和“圣战”宣传。《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刊》上刊登的《日本语与日本精神》对日本文化极尽赞美之辞。《书香》第26号发表的《满洲图书馆的使命》、第33号发表的《时局与图书馆》、第39号发表的《满洲事变与图书馆》等文章直言图书馆和图书馆创办的刊物要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工具,要负有向中国人民宣扬“王道”思想的使命,“要从时局相密切的立场出发”[35]。“九一八”后,《书香》更专辟“事变”专栏,刊登《满洲事变与世界正体》等一系列文章,以及军部书信等,毫无愧怍地为侵略战争代言。
5.3 直接为军事侵略提供服务
5.3.1 为侵略者提供地图服务
地图无疑是军事侵略中必不可少的情报资料。“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图书馆向“满铁”会社提供了从中国抢夺的中国陆军测量局制作的五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会社将其复印了2 000份,分发到各省[22]。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这些地图发挥了很大作用。“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亲口说过一个“故事”:“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政府所在地临时迁往锦州,日本军队仍然紧追不舍。一个夜晚,一位关东军青年参谋来到奉天图书馆,查找中国出版的辽西地图,该馆平日积累的中国东北各地地方志派上了用场[36]。
5.3.2 为侵略者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
曾经有3个日本特务深夜赶到“满铁”奉天图书馆要求查阅有关“黑龙江洲教育制度”的资料,馆长卫藤利夫竭尽全力提供帮助,不但暖气彻夜不断,电灯整夜不灭,而且一直亲自陪伴。“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图书馆以大连图书馆为中心,由24个图书馆共同参与,编制了《全满二十四图书馆共通满洲关系和汉书件名目录》,免费赠送给关东军等机构,为他们查阅资料提供方便。卫藤利夫不无得意地夸耀说:“你所要查找的题目,比如说矿山,或者大豆……只要用电报把书号传送去,下一次列车无论停靠何处,都可以拿到书。”[37]除此之外,各个图书馆还从本馆藏书中选出与战事有关的图书,编成“时局文库”专供关东军用于情报分析。
5.3.3 为侵略者提供精神慰藉
“满铁”图书馆一直都有以书籍作为精神慰藉产品的传统,其慰藉的对象当然是长期离乡背井的军人。早在1918年9月,“满铁”图书馆便建立过“战时巡回书库”用以慰问西伯利亚派遣军。“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2月19日,“满铁”图书馆发出募集图书杂志倡议,其目的如《阵中文库宗旨》所言,是为了对前线的战士进行精神慰安。短短半年时间,“满铁”所属各图书馆共收到捐赠书刊12万册。经过军部的审查筛选,最后确定将109 800多册组成“阵中文库”送往前线[22]。天津日本图书馆也在抗战期间组织过“巡回文库”活动,军队是他们的“巡回”目的地之一。“七七”事变爆发,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即刻启动“前线慰问文库”,精心挑选文学类、时局类、娱乐类、实用类等图书送往前线,用来“满足皇军诸将士战斗闲暇之余阅读,以了解有关支那的基本知识,增进对本邦历史、文化等的再认识”②。
5.3.4 参与整理军队掠夺的图书
1937年下半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在日军特务部的直接安排下,由15名委员组成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和“占领地区学术资料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对华东沦陷区日军掠夺来的珍贵古籍、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进行接收和保存。其后,“满铁”图书馆派出6名图书馆员和调查员于1938年7月和8月到南京对接收图书进行整理,其中包括“满铁”大连图书馆书目部主任大佐三四五和馆员青木实。而天津日本图书馆则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军掠夺的文献资料进行接收和整理。为此,他们在天津防卫司令部的安排下于1942年12月组织成立“军队管理图书整理委员会”,对太平洋战争前英国工部局图书馆约13 000册图书、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上的天津俱乐部图书室约9 000册图书、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上海东方图书馆约22 000册图书以及来自所谓“敌性仓库”的287册图书进行甄别处理[38]。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图书馆已经由辅助文化侵略转化为直接为军事侵略服务。
6 结 语
日本在华建立的图书馆,其主要任务是用图书馆所藏图书资料发挥情报参考作用。早期,它表现在大量购藏汉籍、典籍和地方文献,为日本政府了解中国形态地貌、物产资源提供文献支持 ;后期,随着军事侵略的进一步扩张,图书馆一来以其占据大量图书资料的优势自然成为情报中心,二来图书馆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对侵略者提供信息情报服务。除此之外,图书馆除了收藏中国文献外,也大量引进宣传日本文化、展示其先进文明发展成果的日文图书资料,目的自然是为了文化渗透。为配合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图书馆还积极开办日语短期培训班,从而使其又变身为军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基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图书馆举办“阵中文库”等活动,送书上前线以满足侵略军的所谓精神需求从而达到“慰藉”目的。由此可见,在战争环境下,原本单纯的只是用来提供给人们精神食粮的图书馆也被日本侵略者利用而赋予侵略功能,使其沦为文化侵略的工具。
注 释:
①来源于日本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关系杂件(经费关系 第二卷)”中的《馆命令书》。
②来源于日本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寄赠图书报告(昭和十三年八月)》。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15:23.
[2]何 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3]易显石“.九·一八”事变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60.
[4]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G].成都:巴蜀书社, 2014:82.
[5]张素玢.台湾的日本农业移民(1905-1945):以官营移民为中心[M].台北“:国史馆”, 2001:409.
[6]吕芳上.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1:和战抉择[M].台北“:国史馆”,2015:29.
[7]教育界反对日本文化侵略之宣言[J].中华教育界,1925,15(2):3.
[8]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M].北京:昆仑出版社, 2015:213.
[9]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立日本图书馆规程[G]//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现行法规汇编.[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926:172.
[10]石 嘉.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的文化侵略:以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23-31.
[11]杨力生.满铁大连图书馆[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大连文史资料:第1辑.大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11.
[12]谢环环.满铁的“大脑”——满铁调查部[J].百科知识,2016(18): 55.
[13]孙立民,辛公显.天津日租界概况[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天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132.
[14]田口正树.冈松参太郎与日本统治下之台湾旧惯调查[C].小林贵典, 译.//“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基础法学中心.法文化研究(二):历史与创新.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6:80.
[15]吴豪人.冈松参太郎论——殖民地法学者的近代性认识[C]//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贺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战斗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贺论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4:512.
[16]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68-375.
[17]山根幸夫.东方文化事业的历史[M].东京:汲古书院, 2005:175.
[18]王中忱.走读记:中国与日本之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86-187.
[19]王 燕.抗战时期的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J].兰台世界, 2016:87-91.
[20]万鲁建.天津日本图书馆述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06(5):76.
[21]冷绣锦.“满铁”图书馆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31.
[22]李 娜, 王玉芹.满铁图书馆的职能及其在东北的侵略活动[J].日本学论坛, 2008(3):66.
[23]程宪宇.满铁大连图书馆史略[C]//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2006:15-17.
[24]杨力生, 王泯虬.日寇侵略东北时期伪满铁大连图书馆史料[J].图书馆学研究, 1982(6):105.
[25]张海齐.伪满铁图书馆的图书搜集方式及其危害[J].图书馆学研究, 1983(6):129.
[26]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9.
[27]李晓菲“.满铁图书馆”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J].图书馆建设,1998(1):74.
[28]韩俊英“.大谷文库”藏书初探[J].日本研究, 1994(2):92.
[29]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平设科学图书馆[N].大公报, 1936-11-01.
[30]日本语讲习会[J].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2):186.
[31]天津日本图书馆.华人佣人日语讲习实施[G]//天津居留民团.昭和十八年事务报告书.[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 1943:76.
[32]石 嘉.抗战时期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以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 2015(1):223.
[33]天津日本图书馆.特记事项-日记杂抄[G]//天津居留民团.昭和十三年民团事务报告书.[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 1938:150.
[34]天津日本图书馆.日露战役资料展览会[G]//(日)天津居留民团.昭和十五年民团事务报告书.[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940:559.
[35]“满铁”大连图书馆.满铁图书馆的使命[J].书香, 第26号.
[36]卫藤利夫.满洲事变与图书馆[J].书香, 第39号.
[37]王中忱.满铁图书馆遗事[J].博览群书, 2005(6):48-50.
[38]天津日本图书馆.军管理图书整理[G]//天津居留民团.昭和十八年事务报告书.[出版地不详]:[出版社不详],194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