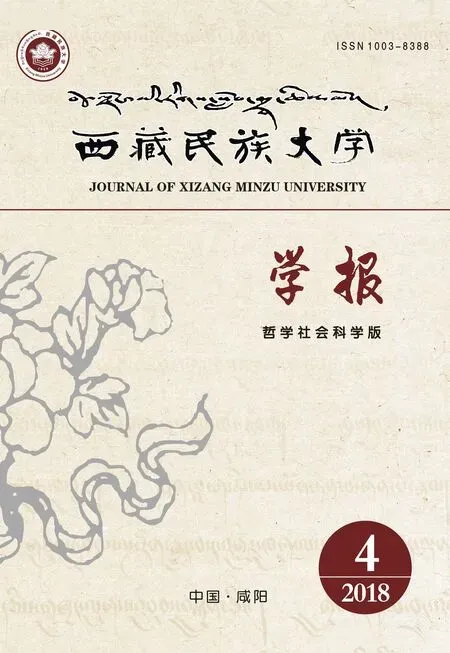从四川石渠洛须照阿拉姆石刻藏文题记看唐代吐蕃与党项的关系
陆 离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江苏南京 210097)
关于唐代党项部族与吐蕃的关系,先后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探讨①,本文主要利用近年发现的四川石渠洛须吐蕃时期藏文石刻题记结合其他史料记载对唐代吐蕃与党项部族的关系再进行一些考辨,略抒己见。
一、关于四川石渠洛须藏文石刻题记中出现的弥药王(me nyag khri rgyal)
近年发现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石刻藏文题记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在位时期(755-797)雕凿的佛教摩崖石刻题记,其内容先后由瑞士学者艾米·海勒、夏吾卡先等进行了录文和释读,现将之转录如下:
“菩萨赞普赤松德赞之世,积大功德,拓展圣冕之权势,远播四境十方,弘扬佛法,设立译场,所译大乘经典渊博宏富,如弥药王等得入解脱之道者,逾百千人。广建寺庙,向差役属民划归农田,佛法永存,大乘四道永固。(1)/btsan po byang cub sems dpav khri srong lde btsan gyi skuvi ring la(2)bsod nam che/dbu rmog btsan de/phyogs bcur mthav skyes nas(3)sbad cing dar ma theg pa chen po mdov sde mang mo zhig gtan la bab par bsgur to(4)me nyag–khri rgyal la stsogs pa brgya stong prag du ma zhig thar par zhug so(5)-ra gtsug lag khang rgyas par brt⁃sigste/rkyen vbangs du rje zhing la(6)-ldan par phul/dam pavi chos nam du yang myi-ig par(7)theg pa chen po bzhe ste brtan par bzhigs so//”②
赤松德赞当时大力兴佛,以佛教为国教,推行寺院属民制度和三户养僧制,一所寺院划拨100户属民供养,一个僧人由 3 户属民供养[1](P202-203),故被称为菩萨(byang cub sems pa),弥药王等也受到感染,皈依佛门。所谓“广建寺庙,向差役属民划归农田”,即指吐蕃在弥药王居住区域石渠等地也建立佛教寺院并推行寺院属民制度和三户养僧制,并给寺院划拨土地以供养寺院。
谢继胜先生认为刻文中的弥药王又可以译为弥药座主,这是目前有关弥药(me nyag)的最早记载。谢继胜先生还指出16世纪成书的藏族史籍《贤者喜宴》记载:“(弥药)东为汉地,南为南诏,西为吐蕃,北为霍尔,在此诸国中心为弥药之国土。(De yang shar ni rgya nag lho na vjang nub nab na bod byang hor gyis bcad pa dbus ni mi nyag gi rgyal khams te)”③,可以印证石渠一带就是唐代弥药的领地。
弥药(me nyag,也写作mi nyag)是藏文史籍对党项部族的专称,该部族很早就与吐蕃发生了关系。《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时期:“是时自东方汉地(rgya)及木雅(mi nyag)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dkar povi rgya gar)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sog po)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hor)、回纥(yu gur)取得了法律(khrims)及事业之楷模。如是,松赞干布遂统治四方,将边地之全部受用财富悉聚于(松赞干布)权势之下。”[1](P30)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另一部藏族史学名著《西藏王统记》。[2](P47)木雅即弥药,该部族的工艺及历法同汉地一样处于较为先进的地位,一起输入吐蕃,对吐蕃产生了重要影响。《贤者喜宴》还记载松赞干布当时娶弥药王(mi nyag gi rgyal po)之女茹雍妃洁莫尊(ru yongs bzav rgyal btsun)为王妃④,而吐蕃王朝势力扩张,周边部族纷纷归附:
“东方之咱米兴米(rtsa mi shing mi)、南方之洛(klo)与门(mon)、西方之香雄(zhang zhung)及突厥(gru gu)、北方之霍尔(hor)及回鹘(yu gur)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治半个世界。”⑤
据学界研究,咱米(rtsa mi)是弥药(mi nyag)的别称,同书又称松赞干布去世后,吐蕃大相噶尔对松赞干布所致的悼词云:“弥药杂米(mi nyag tsa mi)赞普,闻你名而五体投地,道你名者赐予奖赏。”[1](P89)弥药杂米赞普即与吐蕃通婚的弥药王。
另外该书还提到松赞干布时在康区(khams)以弥药人为工头建造压女魔右手掌的隆塘准玛寺(Klong thang sgron ma),以弥药人为工头,又在弥药热甫岗地区(mi nyag rab sgang,今甘孜道孚、乾宁、雅江一带)建造雍佐热甫嘎神殿(yong rdsogs rab dgavi lha kang),松赞干布的弥药妃子也建有寺院逻娑卡查寺(lha sa mkhan brag)[1](P73-74)。
这个松赞干布时期的弥药王(mi nyag gi rgyal po)或弥药杂米(mi nyag tsa mi)赞普与四川石渠洛须照阿拉姆石刻藏文题记中的弥药王(me nyag khri rgyal)应该存在一定关系,后者应为前者的后裔。khri rgyal中khri为万或座之意,rgyal po为首领、王之意,则me nyag khri rgyal可以译为弥药座主(王)或弥药王,其领地的具体位置应该就在今四川石渠一带,下辖若干部落。
林冠群先生对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及藏文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考察后认为对于地方势力,吐蕃史官以rgyal phran(含义为小王)一词来称呼,其统治者王号为rje,用以区隔外邦君主rgyal po,以及吐蕃君主的btsan po,rje在位阶上乃低于后二者[3](P40)。敦煌文书及《贤者喜宴》记载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汗国可汗就被称为rje,松赞干布在位时期的弥药王(mi nyag gi rgyal po)或弥药杂米(mi nyag tsa mi)赞普属于尚未被吐蕃征服的外邦君主。而四川石渠洛须照阿拉姆石刻藏文题记中的弥药王及其属民在赤松德赞时期已经被吐蕃吞并,成为吐蕃的附庸和属民,弥药王的地位应当相当于或略低于吐蕃小王(rje)。另外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1185号中也出现了弥药(me nyag),P.t.1185《军需调拨文书》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上峰来函,弭药纳部落卓局之死/sphring yig gcig kyang dngos kyis skri zhing skur ba lags//me nyag sna ldivi vtso mgyogs gum/”“退浑追兵长官本为囊依担任,甥吐浑王子下令:‘派追兵长官贡达僧拉来代替囊依,’/va zha ded dpon du da red gnang yi bdus pha las dbon va zha rje bkas gthade//gnang yi sk⁃yin bar//ded dpon du da kong dav seng lag/thong shig ces byung nas/”“尚论子侄能效劳王差者很多,与谁替换,要向甥退浑王衙门或内长官尚绮立心儿中一人启禀。/zhang blon gyi bu tsha vam rjes blas kyi rn⁃go thog pha ni mang ste/gang dang rje ba/dbon gyi pho brang vam/nang rje po zhang khri sum rje vam gcigi thog du zhes/”“阵亡费收齐后发给。安抚论与……向对方使者寄出,/gum skyin ni gzhi nas vthus ste/gtong bar vtsal/bde blon por dang/……po nya dang//vphar rol la/spring du/……”[4](P232-233,310)
关于该文书的年代,王尧、陈践先生认为是吐蕃大相噶尔家族专政时期,即在唐高宗及武后时期,但是文书出现有安抚论(bde blon,德论),该官职的设置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主持德论盟会(bde blon vdun sa),负责总管该地区军政事务,所以P.t.1185《军需调拨文书》应该是中唐时期文书⑥。文书记载甥吐浑王子(dbon va zha rje)就是吐蕃统治下青海地区的吐谷浑王国可汗,他与安抚论等吐蕃官员一起负责当地军政事务,内长官尚绮立心儿(nang rje po zhang khri sum rje)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吐蕃宰相大论,兼任河陇地区最高长官东道节度使,该人在822年前后参加了唐蕃会盟,列名吐蕃僧相钵阐布之后。
弭药纳部落卓局(me nyag sna ldivi vtso mgyogs)当为弭药纳部落(me nyag sna ldivi,ldi可能是sde之误)成员,该部落成员当时驻扎于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弭药纳部落正是吐蕃统治下的党项部落,被吐蕃征服后部落成员随吐蕃军队驻扎在这一地区服役,参与吐蕃同北方回鹘、唐朝军队作战等军事行动。与四川石渠洛须吐蕃赤松德赞时期藏文石刻题记一样,该文书记载的弭药纳部落同样也属于关于弥(弭)药(me nyag)的最早记载,填补了关于唐代弭药部族在青海地区分布的史料空白。弭药纳部落应当来自青藏高原东北部,与石渠洛须石刻题记的弥药王(me nyag_khri rgyal)之间应该有着较密切关系,有可能是弥药王所管辖之部落。在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吐蕃官员呈请状》等中将河陇地区党项为主的羌部族称为dor po,该词包括范围应该比弥药宽,晚唐五代敦煌汉文文书中则称dor po为羌,同样指党项等羌部族⑦,而藏语dor po可能是党项首领姓氏拓拔的音译。
二、汉文史料中的婢药和弥罗国
汉文史籍对隋唐时期党项部族的分布迁徙也有很多记载。《隋书·党项羌传》云:
“(党项)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5](P1845)
《旧唐书》卷二二一《党项羌传》则记载的更为具体详细:
“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6](5290)
党项羌南部与舂桑、迷桑杂处,据今人考证,舂桑、迷桑地当在今青海、四川交界处,即今果洛、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7](P3)。“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6](P5290)
《隋书》卷八三《附国传》记载在附国东北往往有羌部族存在,“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峡,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5](P1895)
舂桑、迷桑居地与《旧唐书》卷二二一《党项羌传》记载相符,在党项之南。“婢药”即“弥药”,其余皆羌部落名,其地在今青海东南和四川西北一带。
《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向唐朝求婚未获许可,开始进讨吐谷浑、党项、白兰等部族:“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8](P6072)松赞干布去世后,大相噶尔专政,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唐朝西域十八州,占据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调露二年(680),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接[6](P5224)。党项拓拔、野利等部被迫内徙于今宁夏、甘肃东部及陕西北部一带,故地皆陷于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弥药。”[8](P6214)吐蕃占有今四川木里、康定、理县、松潘以西,及甘肃迭部、夏河以西、以南,青海湖东南部广大地区的党项部落居地,基本确定了对被征服党项的统治区域⑧。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同样也记载:“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于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兰等诸羌,自龙朔以后,并为吐蕃所破而臣属焉。”[6](P5292)这个雪山据考证为今青海省境南部的大积石山。
由以上史料可知在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居住在青海、甘肃、四川地区的各党项部族被吐蕃征服后,被统一称为弥药,而在此之前隋朝的官方记载中弥药(婢药)和党项是分开的。具体来说隋代弥药(婢药)在党项之南,大致分布在今青海东南和四川西北一带,当时依附于吐谷浑或附国,较之党项各部族离吐蕃更近,其活动地域与今天四川石渠洛须照阿拉姆石刻所在地也比较接近⑨,实力与白兰、舂桑、迷桑、当迷等相当,并不是很强大,应该像两唐书所记党项各部族一样,人马在万余骑至千余骑之间。故此笔者认为,松赞干布时期嫁女给吐蕃赞普的弥药王(mi nyag gi rgyal po)或弥药杂米(mi nyag tsa mi)赞普可能就是《隋书》卷八三《附国传》中记载的婢药(弥药)部族首领,吐蕃崛起后不久附国随即消失,实际为前者吞并,曾经依附附国的婢药(弥药)则与吐蕃保持友好关系,开始依附吐蕃,与之通婚和亲。
后来随着吐蕃的不断向北扩张,与吐蕃关系密切的婢药主动归附吐蕃,而青海、甘肃和四川地区的白兰、春桑、党项等羌部则被吐蕃逐一派兵征服,族源与婢药(弥药)相同的党项部族则被吐蕃统一改称弥药。婢药首领由于归附吐蕃时间很早,与吐蕃联姻,关系密切所以受到优待,在赤松德赞时期仍然保留有弥药王的称号,定居于今四川石渠洛须一带,其人数或仍然保持原有规模。对于原来在其北面活动,后来被吐蕃征服的各党项部族,弥药王则并无管辖之权,而且在敦煌藏文文书中随吐蕃进入河陇地区的党项部族也并不称为弥药,而称为dor po,与《新唐书》卷卷二二一《党项传》记载有所不同,《新唐书》卷《党项传》所记为唐初吐蕃吞并党项地区时将党项都改称弥药,而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尚论传记》等中则记载中唐以后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地区,将随吐蕃进入该地定居的党项部族称为dor po,当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对于党项部族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赞普赤松德赞大力扶植扶植佛教,迎请天竺、汉地僧人入蕃传法,建立起吐蕃本土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第一批吐蕃人剃度出家,佛教被吐蕃确立为国教,在国内广泛传播,弥药王也皈依佛门,在其辖地摩崖上刻石造像,虔心礼佛。前面提到《贤者喜宴》所记松赞干布时期即在弥药地区建造寺院,还有弥药人担任工头具体负责修建,赞普的弥药王妃也曾修建寺院,从洛须照阿拉姆石刻藏文题记来看在赤松德赞时期弥药地区建有寺院是确定无疑的。成书于元代的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记载,赤祖德赞时期全国有30所重要寺院,据考证其中龙塘计登卓玛(glong thang vjig rten sgron ma)在金沙江左岸丹玛(vdan ma)地区,亦即石渠一带,梅尔雪赛金格威耐(mer shod seng ge dben gnas)位于今甘孜德格(sde dge)一带,也就是弥药王及其部众居住区域⑩,而藏文史籍《第吾宗教源流(rgya bod kyi chos vbyung tgyas pa)》也有同样记载,但将赤祖德赞时期(815-836年)的重要寺院龙塘计登卓玛(glong thang vjig rten sgron ma)记为glong thang vjig rten sgrol ma,sgron应该是sgrol的异写[9](P357)。《第吾宗教源流》(rgya bod kyi chos vbyung tgyas pa)还记载龙塘卓玛寺(glong thang sgrol ma lha khang)也是松赞干布所建镇边四寺之一⑪,该寺院就是前引《贤者喜宴》所载松赞干布时期弥药人担任工头在康地负责修建的隆塘准玛寺(Klong thang sgron ma),此寺也应该就是赤祖德赞时期的重要寺院龙塘计登卓玛,由弥药人担任工头修建该寺正说明当时石渠一带是弥药人居住地区,也可印证石渠洛须藏文石刻题记中确实出现了弥药王,虽然后来拍摄的照片中这几个词已经漫漶不清了。
定居在今四川石渠地区的弥药王在赤松德赞时期地位较高,受到优待,由于吐蕃在779年建立起本土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寺院桑耶寺,以佛教为国教,大力兴佛,所以石渠洛须藏文石刻题记年代可以进一步确定为779-797年之间。而《拉达克王统记》和生活在中尼边境地区的夏尔巴人历史文献还记载,古代康藏高原氏族董(ldong)族人由藏南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约如(g.yo ru)迁至多康六岗一带繁衍生息,某些支系在塞莫岗(zal mo sgang)谷底的弥药日芒(mi nyag ri mang)与木雅(弥药)融合而成董木雅(ldong mi nyag),也称弥药巴(mi nyag pa,即弥药人)[⑫。塞莫岗在今四川石渠、邓柯、德格和白玉等县境,正与石渠地区的弥药王辖地重合,所以弥药王当时应该受到吐蕃及其所统领部众的监控,吐蕃的这一做法在河陇西域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可汗、龙王、于阗王等投附吐蕃的邦国首领身上都曾使用,党项首领也当不例外。
而吐蕃统治下的党项部族首领拓拔氏曾被镇压。《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记载南诏王致韦皋帛书(时间在793年)云:
“吐蕃阴毒野心,辄怀博噬,……往退浑王为吐蕃所害,孤遗受欺;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拔首领,并蒙诛刈;仆固志忠,身亦丧亡。”[8](P6273)
随着吐蕃的不断扩张,征服青藏高原各部族,党项部族中势力最强的拓拔部族一部分内徙归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党项大酋拓拔赤辞在贞观初年的内附[8](P6215)。另外还有部分成员没有内徙而归顺吐蕃成为吐蕃属民,留在原居地的拓拔部族首领应该是对吐蕃的统治不满有所抵抗,所以遭到了诛杀,此事影响很大,在敦煌文书S.1438v《书仪》残卷中记载,795年沙州地区玉关驿户反抗吐蕃统治起义时就自称拓拔王子[10](P137)。这些个被诛杀的拓拔首领可能也包括定居在今四川石渠一带的弥药王,弥药王亦即《隋书》卷83《附国传》中记载的婢药(弥药)部族首领,归附吐蕃较早,对吐蕃比较忠心,关系密切,但如果其姓为拓拔,在793年之前也有可能被诛杀,793年也是赤松德赞在位期间。而被吐蕃诛杀的拓拔首领也应该包括在弥药王领地以北地区居住、活动在今甘南、青海及四川西北一带的党项部族首领。在赤松德赞之后目前尚未再见到关于弥药王的记载。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对于唐前期内徙至此的一些党项部族又进行拉拢怀柔。《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则记载:“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缘,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四十年。”[8](P6217)吐蕃则竭力拉拢当时居住在唐蕃边境庆州地区的党项破丑氏、野利氏、把利氏等内徙党项部族,赐予王号,并与之联姻,给予不亚于石渠一带地区弥药王的宠遇,以使之成为与唐朝争衡的助力。所以吐蕃对于弥药(党项)各部族策略并不相同,而且因时而异,或残酷镇压,或给予优宠,一切皆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
唐初阎立本所绘《西域图》中在附国嘉良夷之旁记录一国名为“弥罗国”,元人戴表元文字表述为:
“一王皮韬小髻,余发垂双髻如缕,皮裘玄鞾解衽交手按膝。一奴布绦,余发独垂辫,朱裘玄鞾者,吐谷浑之南,白兰之北,弥罗国也。”⑬
据汤开建先生考证弥罗国应在今四川阿坝、若尔盖一带⑭。汤先生认为弥罗即弥药的异译,弥罗国王就是藏史记载的与松赞干布通婚的弥药王。弥药又可以译为弥诺,当然也可以译为弥罗,二者古音相通。戴表元所记唐初弥罗国地望在吐谷浑之南,白兰之北,与《隋书·附国传》所记当时婢药部族活动的地域相合,而且戴表元文字表述中还有“党项之西千碉国也”⑬,说明在《西域图》中党项与弥罗国并不是同一国,所以,如果戴表元所记不误,这个弥罗国当是初唐时期活动在四川西北地区党项以南的弥药,亦即《隋书》卷83《附国传》所记在党项之南离吐蕃较近的婢药。只是两唐书《党项传》的作者记载吐蕃命名党项为弭(婢)药,没有再单独列出弭(婢)药族名,说明他们认为在唐代二者已经是一个部族,婢药姓氏当为两唐书《党项传》所列党项八种姓氏之某一种。当时附国还没有灭亡,弥罗国仍然依附附国,吐蕃灭附国之后,弥罗国就转而依附于吐蕃,其首领当然有可能就是藏史记载的与松赞干布通婚的弥药王,亦即石渠洛须石刻题记中出现的弥药王的先祖。
汤先生还认为由弥罗国王辨发的记载可以证明此国王是来自鲜卑的党项拓拔氏,而非羌人⑮,但是实际上辨发即为羌人之俗。《新唐书》卷216《吐蕃传》就记载吐蕃本为西羌之属,“衣率毡韦,……妇人辫发而萦之。”[8](P60720敦煌文书P.4638《大番敦煌郡莫高窟阴氏修功德记》记载,吐蕃占领敦煌后,当地居民“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11](P239)S.6161+S.3329《张氏功德记》记载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父祖在吐蕃占领时期“形遵辫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12](P400)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则将头发编成两条辫子,让僧人分别坐在上面,以示尊崇[1](P259),而且近年公布的开元二十五年立石之《拓拔守寂墓志》明确记载隋代党项名王拓拔木弥本系羌族[7](P16),所以弥罗国即婢药、弥药,应为西羌部族,而非鲜卑。
另外弥药在西夏政权中一直作为党项人或西夏人的称号,西夏人追述祖先来源的诗歌说道:“黑头石城漠水边,赭面父冢白高河,居此长弥药之国。”[13](P51)这应该与婢药部族在吐蕃建国初期即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在吐蕃王朝一直受到优宠礼遇,保持王号,后来吐蕃又将所征服的党项部族全部改称弥(弭)药,吐蕃文化典制对西夏建国影响很大有关。据《夏尔巴先祖世系》一书记载,今天分布在中尼边境的夏尔巴人迁自多康六岗中的塞莫岗(zal mo sgang)谷底的弥药日芒(mi nyag ri mang),其祖先形成于该地,故而自称弥药巴(mi nyag pa),即《拉达克王统记》等藏文文献记载的董木雅(ldong mi nyag)⑯。另外在今四川甘孜州道孚、木里、乾宁、雅江一带,即今雅砻江中游以东地带,藏语文献称之为木雅热岗(mi nyag rab sgang),该地区的居民被认为是党项羌未北徙而留居下的原始居民,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党项部族南徙与之共同生活,遂融合于其中[14](P372-373)。夏尔巴人及其祖先弥药巴、木雅热岗地区的木雅(弥药)遗民与唐代定居在甘孜石渠一带的弥药王及其部众无疑存在着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居住于青藏高原东北地区与吐蕃方位较接近的婢(弥)药部族最先归附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通婚联姻,故一直受到优待,在赤松德赞时期仍然保持着弥药王的称号,统领所部,定居在今四川甘孜石渠一带,并与当地的来自吐蕃本部的部族进行了融合,赤松德赞时期弥药王也皈依佛教,吐蕃在该地区修建寺院,实行寺院属民制度和三户养僧制度弘扬佛教。而汉文史籍记载活动在婢药以北与之族源相同的党项各部族被吐蕃征服后都被改称弥药,但这些部族并未划归婢药首领弥药王管辖,而是分而制之,吐蕃对这些党项部族或镇压或怀柔,都是根据自己利益分别制定不同策略。甘孜石渠洛须照阿拉姆石刻藏文题记记载了8世纪后期吐蕃统治下今川西北地区的党项部族活动以及吐蕃对其的统治情况,填补了史料空白,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注 释]
①主要论著有:张云,《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初探》,张云,《论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张云,《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张云,《党项名义及族源考证》,收入氏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229-313,420-436页;张云,《吐蕃、党项关系杂议》,《西夏学》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0-194页;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②故宫博物院,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第29页。该录文参考了瑞士学者A.Heller于1997年发表的录文(A.Heller,“Eighth-and Ninth-Century Temples&Rock Carvings of Eastern Tibet”,In Tibetan Art:Towards a Definition of Style.Jane Casey Singer and Philip Denwood,eds.London: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1997:86-103,296-297);另外2012年夏吾卡先对该石刻也发表了录文及译文,在其提供的照片上me nyag(弥药)二字已经漫漶不清,参见夏吾卡先,《石渠吐蕃摩崖刻文的整理与研究》,《藏学学刊》第12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本文录文、译文系根据二者录文、译文而转录。
③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480页。
④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63页;又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著,《西藏王统记》,第94页。
⑤《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53,93页;但是时间应该在唐龙朔年间吐蕃进占西域及攻略突厥以后,当时的吐蕃赞普为芒松芒赞。
⑥参见陆离,《敦煌藏文P.t.1185号〈军需调拨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西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49-56页。
⑦岩尾一史,《ドルポ考-チッベト帝国支配下の非チッベト人集团》,《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ⅩⅩⅪ,2016年,第1-20页。
⑧张云,《吐蕃与党项政治关系初探》,氏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第234页。
⑨据《隋书》卷83《附国传》记载今石渠一带是隋唐时期附国故地,参见石硕,《附国与吐蕃》,氏著《青藏高原东缘的古代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0-298页。
⑩札巴孟兰洛卓著,王尧、陈践译,《奈巴教法史——古谭花蔓》,《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第117页;Helga Uebach.On Dharma-colleges and their teachers in the nineth-century Tibet⁃an empire,In Paulo Daffina(ed.),Indo-Sinica-Tibetica:Studi in Onore di Lucian Petech.Rome 1990:Bardi Editore.p.404.
⑪夏吾卡先,《石渠吐蕃摩崖刻文的整理与研究》,《藏学学刊》第12辑,第19页;弟吾贤者著,许德存译,《弟吾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⑫陈乃文《夏尔巴人源流探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石泰安著,耿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6页;张云《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氏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第305-306,309页;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第375-376页。
⑬(元)戴表元《剡溪文集》卷4《唐画〈西域图记〉》,四部丛刊景明本。
⑭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参见汤开建,《阎立本〈西域图〉在宋元著作中的著录及其史料价值》,《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17页。
⑮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⑯陈乃文,《夏尔巴人源流探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张云,《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氏著《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第305-306,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