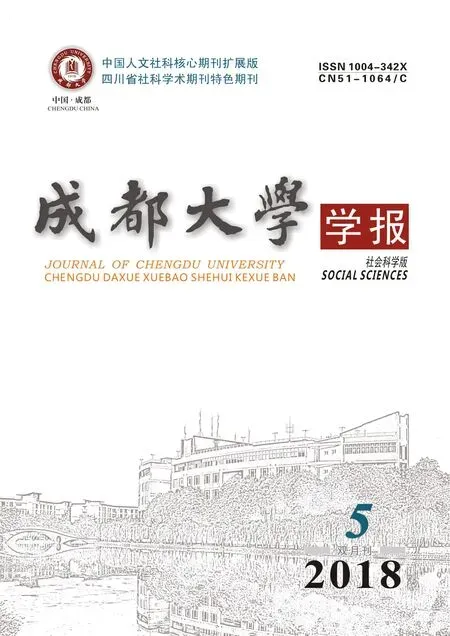清代成都会馆与成都社会发展
袁 月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一、清代成都会馆建立的背景
明末清初,连年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造成了整个四川地区人口的锐减和经济的萧条,大小城镇遭到严重破坏,曾经富庶的天府之国一时之间满目疮痍、饿殍遍地,省城成都也不例外。据资料记载,“明末清初,从崇祯七年(1634年)到康熙前期(1662-1680年)的四十余年间,四川地区连续遭受严重战乱,成都全城毁于战火,官民死亡流离。清顺治初年,成都城有5-6年断了人烟,四川省治也一度被迫迁往阆中。”“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无一寸。”[1]人口的大幅锐减,造成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大萧条,给当地幸存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四川地区的人口锐减同时也危及着清政府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维护西南地区的社会安稳,为此,清政府多次下诏组织移民入川,并前后持续了近百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根据四川民少地多而下诏:“凡流寓愿垦居住者,给地亩为永业,准令五年起科”,“(移民)为力是视,俱发树臼以为界,强有力者得数十丈不只”[2]。在政府移民政策的引导下,数以万计的移民从湖北、湖南、陕西、福建、广东等地前来,在这些移民入川的人口中,以湖广人最多,因此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又被称为“湖广填四川”。据清嘉庆《四川通志》所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四川人口,仅有2/10为原有的土著,其余8/10皆为移民及其后代。在成都, 据《成都通览》第二卷记载,“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在这些外省移民中,各原籍所占比例为:“湖广籍25%,河南、山东籍5%,陕西籍10%, 云贵籍15%,江西籍15%,安徽籍5%,广东籍5%,广西籍5%,福建、山西、甘肃籍各占5%。成都的移民以湖北、湖南为首南方诸省达到80%。”[3]在这场持续了约一百多年的移民运动中, 前后入川的人口大约有一百多万。移民入川在充实了西南地区的同时也带来了各自家乡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 加上清政府实施的一系列鼓励恢复生产的政策,四川地区的经济迅速恢复, 各种文化的交融也使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二、成都会馆的建立
大量的移民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来到陌生的四川地区开始新的生活,既需要适应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异,又要面临着生活的压力,以及与当地土著和其他省移民之间的矛盾。在缺乏认同感和信任感的情况下,也为了能在陌生的地方更好地生存下去,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内聚的集体组织互相帮助,共同抵御外来势力带来的侵扰,而对故土的共同眷念和共同信仰,使一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民间互助组织——会馆在巴蜀大地涌现。这些会馆各自祠祀着故土的神灵,保持着原籍的文化习俗,成为同籍人集会和延伸故土情结的集聚地。在清代四川,各地的会馆大部分都是各省移民建立的同乡会馆,这些会馆数量多、分布广、建筑精巧,堪称全国之最。这些会馆多数建于康雍乾嘉时期,正是大规模移民入川的时期。进入清嘉庆年间,移民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会馆也逐渐成为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会馆“迎神麻、聚嘉会、襄义举、笃乡情”[4]。各类会馆也各具特色,逐渐成为四川移民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动荡,人们的乡土观念逐渐淡化,对于会馆的情感依托已经不复当初,会馆的职能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削弱。民国初期,同乡会开始逐步取代会馆,加之政府功能的加强、民族意识的蓬勃兴起、社团组织的出现等多种因素,会馆逐渐走向衰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成都作为四川首府,是四川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大量的移民聚居,因此在城内形成了众多形态各异、各有特色的地方会馆和公所(公所是从事商业的人们为了保护同籍客居商人的利益而自发组织起来的,起初是同行人聚会的地方,后来与会馆的界限逐渐模糊)。据傅崇矩的《成都通览》统计,成都城内共有17家会馆,包括“贵州会馆(贵州馆街)、河南会馆(布后街)、广东会馆(糠市街)、河南会馆(磨子街)、泾县会馆(中东大街)、广西会馆(三道会馆街)、浙江会馆(三道会馆街)、湖广会馆(总府街)、福建会馆(总府街)、山西会馆(中市街)、陕西会馆(陕西街)、吉水会馆(北打金街)、江西会馆(棉花街)、川北会馆(卧龙街)、石阳会馆(棉花街)、云南会馆等”[5],其中最大的是福建会馆和浙江会馆,最小的是位于布后街的河南会馆。此外,城内还有黔南公所、西江公所、燕鲁公所、黄陂公所、两湖公所、酱园公所、四十炉公所、陕甘公所、安徽公所、泰来公所、西东大街公所、川东公所、酒坊公所、两广公所共14个公所。
三、成都会馆与成都社会发展
会馆的出现,除了维护同乡的利益,弘扬了乡土文化之外,还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并且有了赈灾济贫、资助教育等方面的社会职能,为四川地区社会生活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成都是一个工商业城市,与省内的其他移民会馆有所不同,成都的会馆除了是移民性质外,还兼具工商业性质,是成都社会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
(一)会馆与成都城市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长期的战乱破坏,使成都城内的手工业尽废,其中蜀锦制造业和出版业遭到严重破坏。康熙、雍正年间,浙江工师沿长江而上,将织造工艺重新带回成都。到乾隆、嘉庆年间,成都蜀锦织造业就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织造花样和品种繁多。在城区东南有大量的织机机房和织工,其中以浙江人马正泰、马天裕两家规模最大、质量最好,产品远销省内外。乾隆年间,一批江西书商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开设书铺,贩卖江浙刻本的经学、史学、丛书类书籍,深受成都学子的喜爱。尔后,江西商人又陆续在成都开办印刷业店铺,工匠技艺高超,刊刻版式字体新颖,深受民众喜爱。
从清初开始,一些陕西、广东、湖北、安徽、福建、浙江等地的商贾先后入川经商,长途往返贩运茶、盐、蜀锦、粮食等商品,后来逐渐在成都建立商号,由原本的行商转变为坐贾。傅崇矩《成都通览》中“商铺街道类览”里有绸缎帮、茶叶帮、药材帮、银号帮等51种行帮,这些行帮大部分被各省移民所垄断。商帮、行帮最初是为了对抗土著和他籍商人而形成的,后来同乡同行的商业越来越多,就建立起会馆,以保护本籍商人的利益。在成都,山西人财力雄厚,在城内经营票号,有“蔚丰长、蔚丰厚、协同庆”等著名票号;陕西人擅长经营,在典当、盐茶、棉纺织业等许多四川的大商业行业中形成垄断,发展成陕西帮,成都城内的当铺大部分是陕西人所经营,嘉庆《华阳国志》载“秦人寓蜀者多业此”;药店则大部分是由江西、浙江人所经营,江西籍药商陈光发创设有“同仁堂”药店,浙江籍药商建有“上全堂”“上金汤”药店,店内名药众多,声名长久不衰。
在清代成都的各类手工业商业中都有移民的身影,会馆是他们维系乡情和从事商业活动的纽带。移民通过会馆建立起一种有组织的商业团体,或者在某一行成建立垄断,或者维系着在各行业之间的平衡关系。这种有稳定组织形式的商业团体(会馆)既能维护着移民本身在成都的经济利益,也能较少地受到社会环境变动的影响,保持工商业活动的持久与稳定,带动着成都社会经济逐渐繁荣。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的会馆起初大部分属于移民会馆的范畴,即其功能主要在于团聚同乡,如成都最早的会馆——陕西会馆,但成都毕竟是清代四川的首府,历来是一个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来成都的各省移民也大多从事工商业活动,其身份基本属于工商业者,久而久之,活跃在成都的各省移民商人除了在各自的会馆中加深乡谊,还开始交流商业信息,从事商业洽谈,会馆也通过同乡联谊活动来带动商业运作,满足商业活动,承担起保护移民商业利益的功能。会馆逐渐由移民会馆转向移民、行业双重性质的会馆。这也是成都的会馆不同于川内其他移民会馆之处。
(二)会馆与成都的城市建设
会馆在建立之初一般都位于城内偏僻之处,并没有街道和商铺。随着会馆的逐渐增多,会馆内聚会、祭祀、戏剧等活动的逐渐展开,以及会馆移民商业活动的开展,周围原本荒芜的街道人流量增多,众多小摊贩也聚集在这里,修起了街房和店铺,依靠会馆做起了买卖,街道逐渐繁荣起来,而原本没有名字的荒郊野路也逐渐有了名字。成都城内很多道路都与会馆有着密切的联系。成都城内,由会馆而得名的街巷就有三道会馆街、陕西街、云南会馆街、江南馆街、湖广馆街、贵州馆街、燕鲁公所街等七处;江西商人多数经营棉花生意,设立会馆后便有了棉花街;因杭州西湖附近有小天竺山,因此浙江会馆人称小天竺庙,门前街道也由此得名。移民的商业活动还带动了更多的道路和集市、场镇形成,商号、店、铺、坊一应俱全,经营规模大小不一。当时成都的主要商业街区有很多都是以其商业贸易种类命名,如总府街是皮裘市场,骡马市街是骡马交易市场,铜丝街是铜丝加工和销售的场所,江西商人聚集的棉花街棉絮店铺林立。有了道路和贸易,原本衰败的成都社会又重现生机。
(三)会馆与成都移民文化
各省会馆在成都城内纷纷建立,会馆的功能开始正式发挥。本着以“笃乡情”为目的的各省会馆,在建筑时融入了本土特色,展现了本土文化。同时,各省会馆定期举行的各类娱乐活动,不仅吸引着本籍移民,更吸引着外籍移民,久而久之,成都的移民文化便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形式。
1.会馆建筑
会馆是一个省份文化的象征。各省会馆在建筑时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本土文化特色。从建筑结构上来说,由于会馆本身承担着“迎神麻、聚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的责任,因此,会馆在沿南北中轴线从南向北依次有山门、戏楼、正厅、正殿等一系列建筑,是一个以院落为基本单元的建筑组合群体。
成都的各省会馆,一般都遵循着对称严谨的原则,主要建筑包括:设在南北中轴线上的戏楼、正厅、前殿、正殿,以及设在两侧的厢楼、厢房。戏楼设置在会馆入口处,是供人们娱乐的场所,各省的戏剧表演和节日庆典往往在戏楼举行;戏楼正对正殿,正殿是同乡人团聚议事的场所,正殿或正殿后往往还供奉着故土所信奉的神灵。戏楼正对正殿的布局,也表示着各类演出活动的主旨是敬神娱神,反映着中国文化尊天敬神的传统。戏楼和正殿之间的院落是供群众看戏时所用,厢房和厢楼则是设置在两侧的用来休息住宿之所。各个空间之间往往有侧门相通,便于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各省会馆虽然在空间布局上大体相似,但在结构上却各具特色。江西会馆的独到之处在于,在中殿后还搭建有一个小戏台,进行不对外的、仅供本省人士观看的小型演出。广东会馆为了防火,在建筑外围砌了封火墙,成为广东会馆的标志,在省内只此一处。在建筑风格上,各省风格各具特色。陕西会馆古朴端庄,具有北方特色;位于今天洛带古镇的江西会馆,朴素灵秀,格调更像精美的民居;广东会馆的南华宫,有着南派建筑细腻精致的风格……。在建筑装饰上,各省会馆在会馆内部的栏杆、门窗、屋脊等处上进行雕刻、泥塑、绘画等诸多装饰,这些装饰有些反映了移民生活,有些反映了巴蜀大地的人文风貌,装饰的厚重与否,既是会馆财力的反映,也是商人文化特质和精神追求的表现。江西会馆的装饰朴素而精致,在色彩上大部分是黑或红,少有其他色彩,反映江西人质朴的生活。广东会馆的屋顶脊上有大量的木雕,刻画大量的飞禽走兽和民间传说。湖广会馆的装饰色彩浓厚,殿内房梁上,有大量的云纹和花草、人物的装饰。
成都的各省会馆独具特色的空间布局,不同的建筑风格,加上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是各地建筑文化和四川固有建筑相交融的表现。形态各异的各省会馆是各省移民智慧的结晶,既是清代成都移民社会最直观的反映,也为成都的建筑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成都的建筑有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至今,仍有不少会馆遗址留存,这为我们研究清代西南建筑和成都移民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会馆文化
各省会馆在各自的大殿上祀奉着各自的祖神,作为会馆的象征之一。清代湖广之地是指湖北湖南,两地水资源丰富,当地人们信仰大禹,因此湖广会馆内祀奉着大禹,湖广会馆也被称为“禹王宫”;福建临海,当地人信奉妈祖,称之为天后,福建会馆便祀奉天后,也被称为“天后宫”;广东籍移民信奉南华老祖,又被称为“南华宫”……。此外还有各行各业的商人,在会馆或公所内祀奉各自行业的祖神。
除此之外,各省会馆还留有大量楹联、诗歌,以及修建会馆的序文等。这些文学艺术,记述了各省会馆建造的历史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成都的移民文化。广东会馆在中殿檐柱上的楹联“庙堂经过劫灰年,宝相依然,重振曹溪钟鼓;华简俱成桑梓地,乡音无改,新增天府华裳”,既反映了广东客家人移民入川,又反映了他们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建设四川的美丽愿景。湖广会馆禹王宫大门石柱上的楹联“传子即传贤,天下为公同尧舜;治国先治水,山川永奠重湖湘”,既表明了湖广人对于他们所信奉的禹王的敬仰和推崇,又与会馆建筑的称谓相对应。江西会馆万寿宫的大门楹联“日出东山看洛带楼台四面桃花映绿水闻鸡犬吠牛马喧恰似武陵胜地;客来南海兴江西会馆八方贤达化青菜喜花果密稻麦香这里依稀蓬莱仙家”,既表示了对会馆所在地洛带风景的赞美,也暗含了对故乡的深深思念。
会馆凝聚着不同省份的祠祀文化,使各地不同的信仰在巴蜀大地集中展示;会馆内的楹联和诗歌既是移民历史的象征,也是移民在成都对美好未来的寄托。不同的文化在成都交融碰撞,使成都成为中国古代城市中少有的各省文化的集中展示地,成都文化也因此有别于国内其他城市,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由于移民而形成的多重文化相结合的文化。
3.会馆戏剧
戏楼和大殿是会馆必不可少的建筑。戏楼也称乐楼,是戏剧表演和接诶庆典之所。大殿肃穆庄重,乐楼灵巧花哨。各省会馆建立后,会馆乐楼成了表演戏曲最主要的地方,乐楼唱戏既娱乐观众,又有着酬神的目的。会馆举行的演出,往往不收门票,戏班开场也不限时间,城内众人皆可免费随时观看。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律法之下,妇女本不能与男人一起看戏,必须单设一桌,但在成都的各省会馆,男女同桌看戏则是一种普遍现象。会馆戏楼的演出既展示了地方文化,又促进了各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起初,各省会馆只演出本土的戏曲,如陕西会馆只演出秦腔,江南会馆演出黄梅戏,广东会馆演出粤剧,但随着移民生活的不断交汇融合,乐楼逐渐出现“两合班”“三合班”等形式的班组演出,各省戏剧交替演出,你方唱罢我登场,川剧就是在这时形成的一种新剧种。川剧由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构成,因此又有“五腔同台”“五腔一体”之称。五腔中,昆腔来源于江苏昆曲,高腔来源于江西弋阳腔,胡琴来源于徽调,弹戏则来源于陕西梆子,灯调是四川本土腔调。清代成都是四川的文化中心,城内的各省会馆戏班演出众多,不同声腔的戏班可以同台献艺。文化的繁荣和市民精神需求的不断增长,使不同腔调同台演出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不仅娱乐了大众,也使各声腔戏班的艺人之间互相学习,创造新的腔调和剧种。在这种日益频繁的相互交往中,各种南腔北调与巴蜀歌舞相结合,语言、习俗等方面也逐渐趋向统一,逐渐以成都话为标准,融合五种不同的腔调,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剧种——川剧,并广为流传。这种融合了各地不同文化色彩的川剧文化,也成为今天四川文化的代表之一,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
移民成都的各省移民通过会馆为阵地,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将传统的原籍地文化带入新的入籍地,通过会馆建筑、祠祀、戏剧表演等形式,既将原生地的文化代代相传下去,又使得各种原籍文化在展示过程中发生交流,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都文化本身就是这种由各地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具有不同人文底蕴的移民文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深厚。
四、结语
会馆是清代成都的时代反映,它起初是各省移民为了交流乡情而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清代成都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随着移民生活交流的日渐增多与深入,会馆逐渐成为各省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媒介,成都社会也在会馆的交流间逐渐繁荣。虽然时代的变化使会馆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但会馆始终是清代成都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