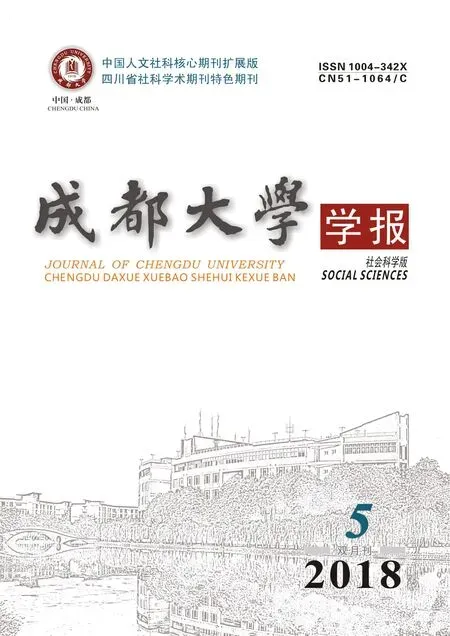论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
程碧英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君子文化源于先秦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君子文化集中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集聚的精神力量,受到了历代思想家的广泛推崇。从汉至清,董仲舒、孔颖达、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梁启超等都对经典文献中的君子文化进行了考辨诠释。后来学者进一步继承发挥,张岱年、余英时、楼宇烈、葛荣晋、刘述先、杨国荣、陈俊明、赵敏俐、王宏亮、任福申、李长泰等从哲学、文献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角度对君子文化进行了广泛研究和学术审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光明日报》陆续推出钱念孙、王小锡、刘宝莅、杨朝明、朱万曙、蒋国保、何善蒙、王钧林、卢风、张述存、孙钦香等学者的“君子文化”主题文章,并就君子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进行了充分辨证。同时,浙江大学、安徽省社科院、江苏省社科院、湖南省等分别成立了君子文化研究中心,目前已举办三届全国性君子文化论坛。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历经岁月沉淀而又常说常新的君子文化如何顺应时代需求焕发生机,如何进入现代公共文化视野,如何实现文化正能量的价值引领,需要我们结合历史语境与现代语义分析君子文化的语义生成,充分挖掘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以进一步明确君子文化价值定位,实现君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君子文化的语义生成
“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李飞跃《“君子”义绎》一文指出,“君子”一词“源起甚早,贯通古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中起着重要作用,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1]。具体说来,“君子”最早见于《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其后多见于儒家经典。考察君子词义的历史演变,余英时认为,“‘君子'之逐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自然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在孔子以前早已开始, 但却完成在孔子手里。"[2]就“君子”词义何以如此变化的缘由,萧公权指出,“君子旧义是‘就位以修德’,新意为‘修德以取位’,孔子推陈出新,提出新的君子人格,反映了孔子改革社会文化及政治的信念,即‘为救周政尚文之弊’。”[3]
自此以后,君子词义逐渐稳定,这为“君子文化”这一概念的形成奠定了语义基础。笔者认为,“君子文化”是一个集体概念,是以“君子”语义元素为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众家文化所长而成。从历史语境与现代语义角度分析,君子文化是众多文化元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广义文化范畴,经由历史发展,涵盖了由“君子”语义所生成的众多文化概念,如君子理想、君子德行、君子精神、君子修养、君子品格、君子作风、君子治国理念、君子人文教育等,既关涉君子语义生成的文化渊源,也包含君子文化演变的历史经验。
二、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
挖掘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自然离不开对《论语》的关注。在《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频次高达一百零七次,从首章《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到末章《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4],可谓相互呼应,贯穿始终。“君子”的高频次出现不是偶然,而是真实表达了孔子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教育讲学的使命。冯友兰认为,孔子是教育家,“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之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所以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5]可以说,从周游列国的失意中归来的孔子,培养君子以改变“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成为了他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对“作为典范的君子”进行过如此评述,“个人修身必然包含对家庭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积极参与,不仅仅是为他人服务,而且是利用这些场合唤起同情和关怀,以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完善”[6],所以,“对孔子来说,君子是一个质的术语,表明一个不断致力于个人发展的人,其成长过程通过修身和社会政治领导能力展现的。”[7]
综上我们不难理解,当孔子将兴办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集中在读书人群体如何实现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时,读书人自然成为了实践君子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君子文化语义所指正逐渐由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转化为读书人这一大众群体。自此以后,君子文化涵养了一代代读书人心忧天下的人生情怀和责任担当。走入现代生活,君子文化丰富的时代内涵得以凸显。
(一)家国情怀
君子文化与家国情怀的语境表达,在《论语·宪问》篇中有如此记载,子路问老师如何成为君子,孔子通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层层推进的方式回答了子路的提问,我们也豁然开朗于孔子对君子责任的建构。《礼记·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顺序,也正是读书人家国情怀的充分表达。
可以说,家国情怀是自古以来读书人心忧天下的情感表达,也是读书人实现自我的实践力量。当孔子孜孜以求追寻“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时,弟子曾子不由感叹读书人任重道远,《论语·泰伯》篇记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孟子道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感慨;屈原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范仲淹展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张载明确“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苏轼提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的警戒;郑板桥抒怀“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担当;左宗棠书写“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情怀。
在生活中,我们常把“做君子”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甚至人生目标。这其中所表达的词义内涵,自然有着属于我们当代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这无疑也是家国情怀的现代表达。于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换》一文中指出,“当谈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化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坐标系,即我们是站在当下去激活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基因,而并非让传统文化全面统辖当下,我们不走复古的路,我们也不会泥古不化。”[8]因此,当家国情怀成为群体文化追求时,现实语境便变得鲜活可期。
当君子文化走出历史语境对话现实生活,家国情怀便超越宗族谱系而走入现代人的精神空间,文化的力量由此变得温润而非支离破碎。因此,家国情怀表达的是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与天下百姓同衷共济,与时代脉搏紧密相依。君子文化家国情怀的表达,既高扬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更是“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的责任书写。
(二)道德遵循
陆建德《文学中的伦理:可贵的细节》一文中指出,“伦理是发展变化的,深深嵌陷在一定的历史过程、社会场域中,不能用绝对的、静止的观念来看待。”[9]对于君子文化而言,在表达伦理观念语义上也的确如此。如上文所言,君子文化的语义表达除了关乎社会责任与人生使命的宏观叙述外,随着汉以后君子文化词义的逐渐稳定,君子文化在伦理道德、人格修为等语义领域的表达也逐渐稳固。
其一,以仁存心。孔子训导弟子,尤其强调“仁”德的重要。《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关于“仁”,《论语·阳货》篇记载弟子子张就此请教老师,孔子如此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进而言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还提出“仁者不忧”“为仁由己”“天下归仁”等话题,皆说明“仁”这一道德遵循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获得的强大的社会价值。
到了孟子那里更是提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10]故此,“仁者爱人”流行于后世,也被当作道德遵循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视野。
其二,义以为质。孔子讲“义”在《论语》中多见。《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朱熹《四书集注》言:“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而行之必有节文,出之必以退逊,成之必在诚实,乃君子之道也。”[11]除此外,《论语》中还提出“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见得思义”等命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义”就是自身行为规范,而“仁”是与他人形成的社会关系。
在其后的文化发展中,便有“舍身取义”“从容就义”“大义凛然”“多情多义”“仗义执言”等说,“义”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道德责任。涂可国《儒家之“义”的责任道德意蕴》一文中指出,“儒学所阐发的责任伦理既包含意图伦理或义务伦理又包含结果伦理,但它又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功利主义。”[12]
其三,博文约礼。在中国古代社会,礼是作为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而加以存在,其背后是强大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在后来的礼制文化发展中,“礼义廉耻”“礼贤下士”“以礼相待”“知书达礼”“彬彬有礼”“让礼一寸,得礼一尺”等说无疑丰富了其内涵。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礼文化进入人们生活视野的是关于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的遵守,实现礼仪文化的传承和仪式感的延伸。
因此,历代君子通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积淀有完备的知识储备和完善的道德遵循,刚毅进取、坦荡中和,自然成为了历代人们追慕的道德典范和人格范式。这对我们当前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着力点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同时,君子文化也是促进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对传统君子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君子文化教育机制,为国民素质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和家风家教家训传承提供范式参考,为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建设等提供可操作之法,亦可为加强和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三)人格力量
当君子文化走过历史演变,回归到现实社会语境中时,我们不难理解君子文化成为了高尚的人格力量的代名词。李翔海在《生生和谐——重读孔子》一书中指出,“儒家的‘君子’人格在传统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与官吏选拔制度,成为整个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人格典范。与此同时,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及知识精英阶层的影响,君子人格还进而成为全社会景仰、信从的人格规范。”[13]裘士京、孔读云在《论语君子观及其现代启示》中指出:“《论语》中的君子是孔子对周代贵族所崇尚的君子人格的重新阐释和再次规定,是历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14]这些说法是有见地的。如今,置身新的时代,当君子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论及,其词义所指已跨越知识精英阶层而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精神得到倡导,表达的不再是单一维度的道德君子范型,而是立体多维的积极进取的人生存在方式。
因此,遵循“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规律,在高扬仁爱崇礼、诚实守信、公平正义、敬老爱亲、谦逊友善、淡泊宁静等人格力量基础上,积极构建文化认同、转化发展和协同创新机制,按照“大众化、常态化、生活化”原则,通过教育引导、平台传播和实践养成等方式实现君子文化的现代转化和传承发展。
三、结语
君子文化所构建的思想价值体系,不能只是抽象的存在,而应渗透在日常生活与一言一行中。陆建德指出:“心灵接受价值必须是主动积极的,价值或信仰内化以后就变成生命的热量,行为的动力,而不是一种撑门面的标榜。”[15]因此,君子文化的各大范畴既独自存在,又相互关联。理论建构的可贵之处在于,超越支离破碎而浑然一体,走出历史语境而对话现实。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成为君子并非可望不可及,而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公民通过努力都可以承担的社会责任,可以达到的人生境界,从而实现从个体修为到集体人格的成长。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在做好君子文化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君子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随之而来的重要话题。因此,当君子文化以昂扬的姿态进入我们现代生活的道德修为、公共价值、文化实践时,君子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也就得到了最大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