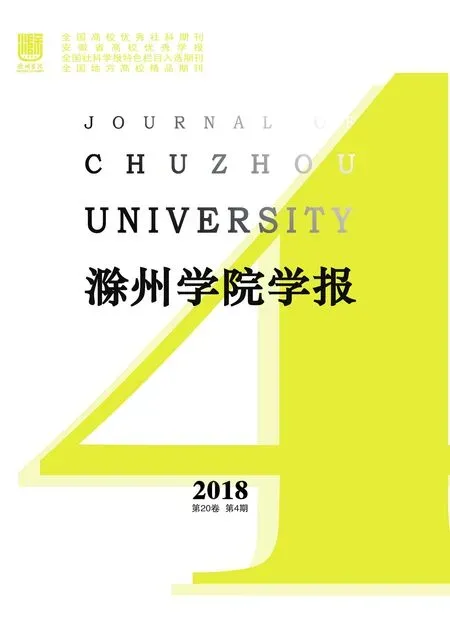中华文明的精神象征:当代诗歌中的杜甫形象
万 冲
被尊为千秋诗圣的杜甫,虽未及时地被同代人辨认出来,却在后代诗人那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如诗人元稹评杜时,称赞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1];宋人评杜时,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将杜诗称为“诗史”;而明人从温柔敦厚的诗教角度将杜甫尊为“诗圣”。自杜甫的经典地位被奠定之后,杜甫被视为士人的精神典范,杜诗则被视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各个时代的诗人赞誉杜甫的现象更是绵延不绝。即便是在曾对传统文化有过大肆否定的20世纪,杜甫依然得到世人的普遍推崇。正如汉学家洪业所言,“鼓吹流血革命的极左分子和捍卫因循现状的右派人士都乐意引用杜甫,保守的文学研究者承认杜甫的知识广博,偶像破坏者以及白话文的拥护者也一致向杜甫致敬。”[2]不同政治立场和文化观念的人皆对杜甫推崇备至,将杜甫视为无可挑剔的精神典范,这足以说明杜甫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
在当代,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在诗歌中表达对杜甫的赞扬和称颂。据学者张松建研究统计表明,以咏杜为题材的诗歌已达14篇之多[3],至于出现杜甫形象的文学作品更是不计其数。诗人西渡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现象,“杜诗的诗史性质和精湛的叙事技巧,为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提供了经典性的榜样。”[4]当代诗人纷纷尊崇杜甫的现象引人深思:拥有丰富精神面相和饱满精神能量的杜甫,到底是哪个方面引发了当代诗人的极度推崇呢?尝试思考这个问题,或许有助于揭示杜甫的当代价值,为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提供一份可贵的精神启示。
一、以“仁心”为基础的家国天下情怀
在当代诗人中,首先书写杜甫的是诗人西川。在80年代末的一次周游全国、认领中华民族文脉的长途旅行中,他将杜甫视为如黄河般博大浩瀚的诗人,激情充沛地抒发了对杜甫的热爱:
杜 甫
你的深仁大爱容纳下了
那么多的太阳和雨水;那么多的悲苦
被你最终转化为歌吟
无数个秋天指向今夜
我终于爱上了眼前褪色的
街道和松林
在两条大河之间,在你曾经歇息的
乡村客栈,我终于听到了
一种声音:磅礴,结实又沉稳
有如茁壮的牡丹迟开于长安
在一个晦暗的时代
你是唯一的灵魂
美丽的山河必须信赖
你的清瘦,这易于毁灭的文明
必须经过你的触摸然后得以保存
你有近乎愚蠢的勇气
倾听内心倾斜的烛火
你甚至从未听说过济慈和叶芝
秋风,吹亮了山巅的明月
乌鸦,撞开了你的门扉
皇帝的车马隆隆驰过
继之而来的是饥饿和土匪
但伟大的艺术不是刀枪
它出于善,趋向于纯粹
千万间广厦遮住了地平线
是你建造了它们,以便怀念那些
流浪途中的妇女和男人
而拯救是徒劳,你比我们更清楚
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5]
在这首诗歌中,西川对杜甫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将杜甫认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汉语的灵魂。与西川的咏杜诗歌遥相呼应,当代诗人黄灿然和西渡也相继写下了歌颂杜甫的诗篇。如黄灿然的《杜甫》:
杜 甫
他多么渺小,相对于他的诗歌;
他的生平捉襟见肘,像他的生活。
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褴褛的形象,
叫无忧者发愁,叫痛苦者坚强。
上天要他高尚,所以让他平凡;
他的日子像白米,每粒都是艰难。
汉语的灵魂要寻找适当的载体,
这个流亡者正是它安稳的家园。
历史跟他相比,只是一段插曲;
战争若知道他,定会停止干戈。
痛苦,也要在他身上寻找深度。
上天赋予他不起眼的躯壳,
装着山川,风物,丧乱和爱,
让他一个人活出一个时代。[6]
再如西渡的《杜甫》(节选):
一个女人的死撕掉了帝国的假面。
而我废弃了圣人的理想,不再做梦,
人们也不需要有人用真话揭破
他们酣睡的大梦,所以我离开。
……
我对自己说:你要靠着内心
仅有的这点光亮,熬过这黑暗的
日子。
……
无边的空间,永无尽头的
流亡。山的那边,是山;路的尽头
是路;泥泞的尽头,是泥泞;黑暗
之外,是更深的黑暗。
……
在春天,竹子的生长被暴力扣住,
在石臼的囚牢里,它盘绕了一圈
又一圈,终于顶开重压,迎来了光。
于是宇宙有了一个新的开始。[7]
这三首具有代表性的咏杜诗歌,虽然艺术手法各异,但诗歌主题却有共同的出发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层:1.虽然杜甫困于日常生活之中,却在诗歌写作中创造出平淡中的壮美、平凡中的伟大。2.在离乱的战争生活中,杜甫虽饱受由残暴的时代和政治引发的苦楚,却凭借深仁大爱,葆有对帝国秩序、山河岁月、风物人情的热爱与赞美。3.杜甫的化苦难为艺术的精神追求,仁民爱物的精神风范,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和汉语的灵魂,给后人带来无尽的精神启发。4.杜甫宽广的精神襟怀和深沉人格境界,创造了充满深厚情感的艺术境界,超越了历史、政治和现实苦难,为中华民族的劫难和天下人民的苦难带来了拯救。
概而言之,当代诗人为杜甫绘制了一幅如许的精神肖像:日常生活的平凡者,时代苦难的承受者,祖国山河的讴歌者,中华民族灵魂的体现者。当代诗人纷纷将杜甫认领为日常生活中的圣者,以贴近他们构想中的中华民族精神传统,这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内涵是什么,杜甫形象背后的深层意蕴又是什么,这的确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只有更深入地理解我们的传统和我们自身的精神境遇,才能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更好地继承传统。
在当代诗人心目中,“深仁大爱”被尊为杜甫的核心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的形成可追溯至杜甫的家教环境。据学者闻一多考证,杜甫自幼就熟读儒家的经典典籍,家族中的人也多笃行仁义、践行德行的义士[8]。杜甫从小就在圣言和行为两方面深受儒家精神传统的濡染,更以一生的诗歌写作和精神实践,对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仁爱思想做了独特的继承与发扬。正如宋人黄彻赞叹的,“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真得孟子所存矣。”[9]作为诗人的杜甫,继承了圣哲孟子的原心与真精神。
孟子的核心精神是“恻隐之心为仁”的人性思想。“仁”被孟子视为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准和尺度。正如孟子说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恻隐之心是人性觉醒的萌芽,更要发展为普遍广大的博爱之心,以达成人性的完成。正如孟子所推崇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孟子倡导的“仁”精神中,以亲子之爱为基础的情感,必须社会化为安邦治国、拯救社会人民的普遍精神使命。这种基于亲子之爱而成于家国天下情怀的仁爱精神,便有了如宗教般超越的神圣意义,成为生命的最后实在和最高本体。
深受儒家精神传统濡染,常常以圣贤为精神追求的杜甫,在诗歌中表达了对“仁者”人格境界的赞美:“位下曷足伤, 所贵者圣贤”(《陈拾遗故宅》);杜甫诗中表现的情感,也由爱亲人而自然而然地推及天下万民。最为人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完满地体现了杜甫的仁者情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由自己个人的苦难真切地感受到天下人的苦难,更发自肺腑地希望以己之苦难承担天下人的苦难,牺牲一己之幸福而成就天下人的幸福,以令天下人免受忍饥挨饿的苦难。杜甫以博大深厚的仁义之心和天下情怀,在诗歌中创造了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抒情的艺术境界,令中华民族的劫难和穷苦老百姓的苦难在其中得以安顿与救赎,将孟子倡导的“仁者”精神发展到了极致与圆满的境界。以至于千百年之后,四川诗人肖开愚向杜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向杜甫致敬》
可是只有你
——自他们想往的古代
发出的哀告符合
怜悯的要求,如果北风、斜树、小雨
构成冬天的窗景,一个老人
无法修好他的取暖器。
哦,让孩子们回到教室,
画图,他们创造一个
替代这个世界的世界。[10]
杜甫这种出于内在仁心而推及天下黎民的胸襟,以牺牲自己以拯救万民的情怀,被当代诗人认领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特征。与西方基督教构建一个拯救的彼岸天堂不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则强调在日常生活之中感受到正常的人伦之美善,并在这种人伦之美善中培养高尚、宽广的胸襟与光明伟岸的人格。如熊十力所言,“中国思想的特性,中国民族之特性,即为无宗教思想。《诗经》所咏歌,皆人生日用之常与男女室家农桑劳作之事。”[11]以仁心为基础,中国传统士大夫诗人形成了以日常人伦为出发点,以家国天下情怀为归宿的心理结构和价值体系。他们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和天下黎明百姓的幸福苦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诗歌创作之中,则形成了“家——国——天下”的意义感知链条,能将个人的情感投射到广阔的国家和天下领域,在个人的悲欢离合之中而兴发历史兴亡之叹。杜甫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诗人中最为典型最伟大的代表。正如章祖程所说:“诗自《三百篇》《楚辞》以降,作者不知几人,求其关国家之盛衰,系风教之得失,惟杜子美以天宝兴感,为得使人忠爱遗意。”[12]
从生活经历来看,杜甫跨越了盛唐、中唐两个时间段,经历了自“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地方叛乱等暴力冲突持续不断的苦难生活。杜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困苦而自怨自艾,而是突破个人的狭小限阈,见证了“安史之乱”前后生活的沧桑巨变,从个人生活的悲喜中洞悉了历史时代的兴衰沉浮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记录那个大变动时代的杜诗,才堪称为集大成的诗史。杜甫把灵魂对现实的反应如实地记录下来,深深地铭刻着普通老百姓的苦难和朝政的凋敝与荒芜,并在这些记录和呈现中,表达了对时代的感受、体认与批判,对百姓苦难的同情、对历史的见证,又在这种记录和见证之中表现了浓厚的悲悯情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深切的伦理关怀和道德吁请。杜甫不仅是唐王朝和个人命运的目击者,还是时代和人民苦难的见证者,更是完整人性的体现者。也正因为杜甫博大的胸襟和强大的记录抒情功能,对更广大的宇宙秩序的祈愿,所有的穷苦人、孤苦无依者、欲哭无泪者,才在杜甫诗歌铭刻般的记录与发自肺腑的悲悯中找到了安顿与救赎的可能。
与传统诗人在家国天下体系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不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诗人,追求个性解放,高扬自我价值,使自我从“家—国—天下”的体系之中冲决而出,令自我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价值个体,成为一个崭新的抒情基点,催生了现代抒情诗歌的诞生。在近百年的诗歌写作中,诗人常常以自我情感的独白作为合理与正当的创作依据。虽然在4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诗人将个人情感与民族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50—70年代,诗人将个人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在对山河的歌颂中歌颂祖国。但这种个人与家国的联系,均出于战争的特殊境遇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缺少儒家那种从内部的仁爱之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牢固的情感体系和价值观念。以至于那个独特的自我,一有机会就会从家国体系之中脱离出来,例如80年代的诗歌写作,自我启蒙便成为诗歌写作中重要的激发点,而在90年代强调的个人化写作中,更是将自我的价值赋予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自我价值和个人感情固然是诗歌创作中重要的根基和出发点,但过于沉溺于个人情感,则易陷入小情小调之中,与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生活失去紧密的联系,诗人的胸怀和人生境界也变得狭小逼仄。在当代,这种沉溺于自我个体价值的写作模式,难以和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不能对苦难的社会现实做出应有的变现与承担,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和伦理危机。
虽然就整体局势而言,杜甫所处的政局混乱、国家贫弱、百姓积苦的中唐时代,与和平稳定、国富民强、经济繁荣的当前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当前时代也面临着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随着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深入,虽然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些社会问题。一方面,金钱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纷纷以消费标榜自己的成功,人文价值遭受严重的失落与冷遇,仿佛进入到了一个消费时代。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也日益出现了诸如贫富悬殊扩大、房价飞涨、下层老百姓生活艰辛等社会问题,而新世纪接连发生的地震、海啸等一系列自然灾害事件,也增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下层百姓的劫难。当代诗人陷入到“贫乏时代,诗人何为”的道德伦理困境之中,如何继承诗歌合为时而作的传统,对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表达深刻的同情与悲悯,成为摆在当代诗人面前亟需解决的道德困境和诗艺难题。面对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如果只以旁观者的心态来书写,就仅仅释放了自己的道德焦虑,而不能对民众的苦难有所承担。正是在这种精神困境之中,拥有以仁心为本的家国天下情怀的杜甫,以一个在野知识分子身份去关怀人间疾苦,以仁人之心为基础,由对亲人的感念推广到对普天下百姓的大爱,通过精湛的诗歌技艺,将广阔的现实转换为浓厚深沉的抒情境界,为当代诗人树立了应对“贫乏时代,诗人何为”困境的绝好典范。正是基于杜甫的表率作用,诗人肖开愚对杜甫有过深情的告白,“他不是抱一个在边缘的态度,而是担当大义,以主流自任。他唯一的事情就是做自己的本职工作。”[13]虽处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的杜甫,用敢于担当大义的精神立场和写作实践启示当代诗人,诗人身份具有介入事件和历史之中的正义性,诗人的责任在于,以独立的身份对苦难作出忠实地记录,用浓厚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来见证时代的兴衰与抚慰人民的苦难,从而体现人性的尊严与人格的伟大。
三、精神贫乏时代的心性追求
如果说,杜甫将亲子之爱的仁爱之心,扩大为仁民爱物的深厚情感和家国天下情怀,是从外在人伦关系角度来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那么,杜甫仁爱精神的另一个面向,则是从内在的人格培养和人性完成角度来实现生命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诗歌通常作为社会成员和特殊灵魂个体的情感表达,但中国诗人鲜少能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家国天下的价值体系对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结构影响重大,但在乱多治少的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给士大夫和诗人提供太多机会,供其既能实现个人价值,又能实现美善的社会理想。大部分时候,诗人往往在乱世退居山林,追求自我价值的完成。连孔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杜甫是中国诗歌历史上少有的有心性和能力将二者统合起来的诗人,他虽然身处乱世,却依然追求自我价值与社会政治理想同步实现。与李白、王维等诗人在浪漫的仙境或空寂的山水田园之间实现个体的价值不同,杜甫完全执著于人间,关注于现实,不求个体的解脱,不寻来世的拯救,而是将个人生活的悲欢与天下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起来,在表达个人情感时承担着社会责任,在表现个人与时代生活的苦难时,又保持着心忧天下的广阔胸襟和美善的心性。正是以仁爱之心和家国天下情怀为依托,杜甫虽然一辈子都身处逆境,却依然对生活充满了无限赞美之情,将艰辛的处境和现实之恶最后落实到赞美。正如叶燮所言,“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秉持“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移”执着性情的杜甫,顽强地追求着人格的伟大与心性的圆满。杜甫将人道情感视为一种本体追求,强调从内心来自觉建立一种完美的主体人格,令这种主体人格在历史与现实的磨砺之中成形,而又成为超越现实与历史而具有独立价值的意义本体。对杜甫这种博大的主体人格,诗人西渡有着饱含深情的赞颂,“杜甫在中国诗人中最能显示人格的深沉博大。”[14]杜甫的精神修为和艺术实践,无疑给当代诗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成为他们渴望企及的精神高度。
在当今这个物质丰富而精神相对贫乏的时代,人们普遍感觉为什么而活的人生意义被悬置,人们难以找到坚定的精神依托,群体陷入一种精神虚无之中,又在无止境的嬉戏之中抵抗精神的空虚。西方的文化价值也日益对国人的精神产生重要影响,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文化认同日益遭受严重的危机。当代诗人的精神和人格难以统合整一,常常以反讽的抒情面目出现。执着地将价值立足于个体心性,保持了人性完整的杜甫,无疑给予了当代诗人莫大的精神鼓舞,成为他们崇高的精神路标。哲学学者劳思光指出,“价值根源之归宿不外乎人的主体性、非人格化之天、外在的权威主义或者利益等数种”[15]在一个价值混乱的转型时代里,当价值无所依傍时,杜甫以反身而诚的方式,将价值追求从外在事功转向内在心性,追求自身人格的的提升与完善,并将之视为个体生命存身的依据和根本的价值根源,最终达致了人格全美与人性全善的境界。这便是杜甫在当代诗人那里被推崇备至的原因。正如当代诗人廖伟棠所言,“杜甫的确是楷模,他通过他的写作告知我们:诗歌不是无意义的,存在也不是无意义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明示。”[16]杜甫在诗歌写作中坚持的完整心性,不仅成为抵抗暴力、苦难和死亡的工具,也是混乱时代个体生存的意义依据,是精神贫乏时代的价值根源。这给当代诗人提供了无尽的精神启发,成为当代诗人效法与追慕的榜样。如当代诗人西渡表达的:“我对自己说:你要靠着内心/仅有的这点光亮,熬过这黑暗的日子/终于顶开重压,迎来了光。”内在的心性,恒为个体生命存身的依据,是熬过黑暗、迎来希望的本质力量。以西渡为代表的当代诗人,不再是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现实的二元对立中,获得将自我圣化的崇高感,以求得一劳永逸的自我陶醉感;而在于对时代生活的承担之中,以广宽的胸怀容纳现实的苦难,并将其转化为赞美来磨砺自己的心性,最终内化为诚心正意的修炼心性的行为,追求自我人格的提升与完备。
四、结语
在论及当代人与本民族精神传统的关系时,美国诗歌评论家有一番颇为精彩的妙言,“在创造过去的形象中,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17]。杜甫在当代诗歌中被不断重写的意义就在于此。当代诗人从自己的精神处境出发,将杜甫认领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汉语灵魂的体现者,尝试将杜甫作为伟大的精神资源,来应对“贫乏时代,诗人何为”的精神困境和诗艺难题。杜甫发自仁爱之心的家国天下情怀,在精神贫乏时代的心性追求,无疑为当代诗人提供了一个精神榜样与诗艺典范,令诗人从狭小的个人情绪中挣脱出来,寻求个人情怀与历史境遇的深刻关联,在价值失序的年代,执着于自身的心性追求。正如当代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所说的,当代诗歌应该“在真切的个人生活和具体的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之间达成同步展示,既烛照个体生命最幽微的角落,又折射出历史的症候”[18],这是当代诗人从自身的精神境遇出发,对杜甫的精神品格和诗歌技艺做出的实际而有效的继承。
历史学家汤因比有言,“在恰好生在这不幸年代的人们心中,相应地出现了心理分裂现象。人们失去了方向,盲目地蜂拥到各条小路上去,以寻求逃避。较伟大的心灵超然物外,更伟大的心灵则试图将人生变成某种比我们所经历的尘世生活要更高级的东西,并把新的精神进步播撒在大地之上”[19]。在当代诗人心目中,在心灵中对苦难现实进行了转化,体现了人性的壮美与完善的杜甫,无疑属于拥有更高级心灵的伟大者行列,在心灵需要指引的精神贫乏时代,杜甫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召唤着新时代的诗人加入到向伟大心灵进发的队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