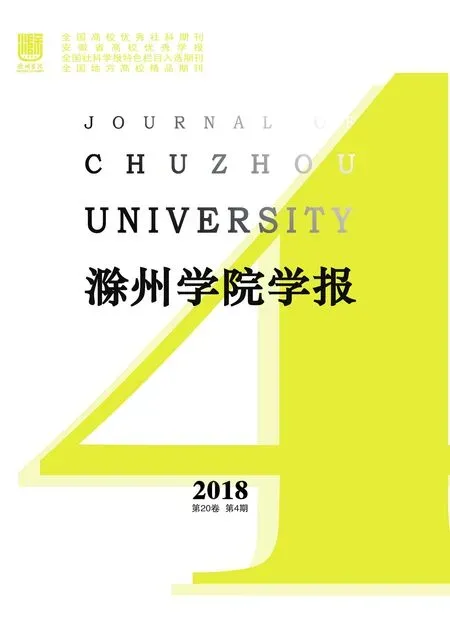论庄子的“相知”与“不相知”:由鱼乐之辩说起
蔡广进,李大华
我们能否理解超出自我的他者?换言之,不同的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必然存在差异,那么彼此之间的理解和相知又何以可能?本文试图借由《庄子秋水》中“鱼乐之辩”寓言的分析,探讨庄子与惠子在知“鱼之乐”问题上的不同致思倾向,并从鱼乐之辩蕴含的问题出发,考察庄子对“相知”与“不相知”关系的看法,以及二者背后隐含的道德意蕴和生活理想。
一、“鱼乐之辩”的两个问题
鱼乐之辩,肇于惠施,止于庄子。《秋水篇》云: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由鱼出游从容以推断其乐,惠子则对庄子安知鱼乐提出疑问。惠子的质疑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安知”在这里是“如何可能知”,惠子的问题是康德式的追问,即“认识如何可能”是认知进行的逻辑前提。可以说,惠子对庄子的辩难基于知识论的立场而言是有效的,①即要求庄子从知识论上对“相知”的可能性予以证明。其次,庄子和鱼属于不同的类,“鱼”在这里可以视为“自我”之外他者的隐喻,因而当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时,乃是以相知的前提为同类方能相知,即此欲知彼只能由“此成为彼”方才可能。
面对惠子的质疑和辩难,庄子的回应是一种“以辩止辩”的方式。一方面他顺着惠子对相知的界定反问道:“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个反问无疑是庄子意图通过指出惠子逻辑的荒谬,以捍卫不同个体之间相知和理解的可能性。而惠子进一步辩护则是对自己相知逻辑的彻底贯彻:“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如此一来,任何超出自我之外的认识和理解都几无可能。
从辩论逻辑角度而言,这场论辩到这似乎已经走向了“死局”。“惠施之问虽层层逼入,已犯明知故问之嫌。庄周之答,非仅层层化解,且引惠施入彀。”[1]34庄子“请循其本”,指出惠子问“汝安知鱼之乐”乃已暗含庄周之知鱼乐,正犹惠施之知庄周耳,既然已知而问我,则以“我知之濠上也”止辩。在此,庄子坚持不同个体间相知和理解的可能性,“苟知我之非鱼,则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鱼然后知鱼也。”[2]330但其对惠子“安知”的问题又作了转化:从“如何能知”转化为“以何种方式知”。②
由此分析观之,知“鱼之乐”事实上隐喻了自我与他者,乃至不同主体之间理解和相知的过程。其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不同个体之间的相知和理解是否可能?其次则是这种相知的可能性应该以何种途径通达,惠子和庄子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进路:前者是强调知识和逻辑的明晰性,主张从客观说理和分析的论辩达至相知,而庄子则强调这种名理辨析的有限性,相知的“真”更重要的是诉诸于气化主体的交互理解而非执着于是非层面的论辩。庄子最后的“诡辩”可视为“以辩止辨”的方式,一方面,“知之濠上”意味着源初的经验,即答案在于所处时空的刹那,存在境域的源初即是鱼乐的理据。另一方面,则是防止惠子关于相知的逻辑预设滑向人与人无法相知的虚无论,从而捍卫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理解和相知的可能性。
二、“相知”之蔽与“不相知”的道德意蕴
从“鱼之乐”或他者之心是否可知的论辩,放到现实的社会领域,便涉及不同个性、民族、肤色、信仰的个体乃至族群间的沟通和理解问题。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便总要与不同的他者打交道,“有人之形,故群于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生存活动源始的就是一种与其他在者一起的“共在”,而这种作为主体本真状态的“共在”先于主客的二分,故海氏在谈及“共在”问题时亦援庄子“鱼乐之辩”为引子,不可不谓之慧解。
在相知的可能性问题上,庄子表现出与儒家相反的致思倾向。在儒家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相知和理解乃是自明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遵循着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立的逻辑前提便是不同个体间的相知。而在庄子看来这种相知的前提恰恰是需要反思的,因为在现实中不同主体间交往的常态是“不相知”,有诸多因素阻碍着彼此的相知和理解。
首先,不同的生存境遇导致的视域差异。譬如《秋水篇》: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河伯之所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在于其生存的地域仅局限于“百川”,因而造成其视域的狭隘与心态上的自大。这种“夜郎自大”的视域局限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自我视之”与“自彼视之”之间总是存在偌大的鸿沟。在《逍遥游》中,大鹏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而在蜩与学鸠看来这种生活目标完全超出其常识的理解:“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蜩与学鸠对大鹏的嘲笑,无疑也折射出不同的生存境遇,从本源上规定了不同个体的生存领会和基本生活观念。从这种生存境遇的根本差异出发,就构成了不同个体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执着于“是非之辨”,从而导致“俱不能不相知”的困境。请看《齐物论》: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在这里,庄子列举了诸种辩论的可能结果。但讨论的双方终究无法达成相知,因为无法达成确定是非的标准。在庄子看来,人本来就有昏昧不明的地方,人的视野本来就容易受到固有观念的遮蔽。所谓的“黮暗”其实就是人的“成心”。“夫域情滞著,执一定偏见者,谓之成心”[2]27,论辩的双方各持一己之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尽管论辩存在胜负,但在庄子看来胜负不等于是非,胜者未必是,负者亦未必非。以往学者多以庄子的观点是“辩无胜”,确切的说应该是“辩无是非”。反而论辩的成心从根本上遮蔽了真正的对话沟通和相知理解的可能性。
在“鱼乐之辩”中,惠子的成心便是执着于客观名理论证,然而在庄子看来,这中对分别之知和“怪说琦辞”的执着终究是“小知”和“小言”。《齐物论》曰;“大知闲闲,小知间间。”间间,分别也,所谓“小智狭劣之人,性灵偏促,有取有舍。”而庄子所欣赏的乃是“智慧宽大之人,率性虚淡,无是无非。”[2]27惠子究意于“鱼乐之辨”,试图以名理辨析之知廓清世界之真理,实不知“是非之辨实始于知(案:名理辨析之知)之一字”[3]148,遂至“逐万物而不返”而“弱于德”,从而丧却大道和生命之真意。
尽管庄子得出“人俱不能相知”的结论,肯定人拥有的仅是“自知”。然庄子并非否认相知和理解的可能性,而是“他看准的是一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即人们在认知过程中难以排除自己的主观性与立场的偏颇,或许是看到这个问题是一个认知的顽疾,才要把话说得偏激一点。”[4]183换言之,庄子的关怀乃是人生问题,其哀叹于世人钩心逞智,游意于是非之辨而失却生命之真意。庄子对话的对象不仅是惠子,事实上也是对儒墨争鸣的反思:“儒墨小言,滞于竞辩,徒有词费,无益教方。”[2]27论辩的沟通方式不仅无助于人们对彼此的相知与理解,反而导致是非之争而走向冲突与分裂,即所谓“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里的“耳目鼻口”,显然就是《应帝王》中致死浑沌的“七窍”。而“道术裂”和“浑沌死”无疑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诸子百家学说之间是非之辨引发的意识形态上纷争正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其次,庄子虽不否认相知的可能性,但他更强调人本身在生存境域和视域上的有限性,事实上这也是对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反思和补充。儒家强调人作为“类”的相同性,《孟子·告子章句上》中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从人类生理上的共同性落到道德领域,就是推己及人的正当性。在儒者看来,己所不欲就不能施加给他人,但反之——己之所欲是否就可施于他人?这就是庄子“不相知”的反思所在,即反对将自己的思想信仰强加于他人,即使是为己之所“欲”的。《齐物论》云“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即是谓以我之个人偏好,晓喻无此偏好之他人,“非人所必明,而强明之。”[5]84俗谚谓“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庄子更加关注的是人作为个体精神生命存在的特殊性,哪怕是否快乐的情感体验都因人而异,《至乐》中曰“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我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以之为诚乐矣,又俗之大苦也。”
在庄子看来,那种将人视为“类”的理解背后都存有一个未经检验的“预设”,即每个人对于幸福和美好生活都有着整齐划一的理解,从而人们都应该过共同的理想生活模式。事实上,今日各种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原教旨主义,亦是在这种“预设”上试图为人类设计一套普遍有效的生活规则和人生蓝图。而庄子提出质疑的是,人难道仅是一种“类”的存在?是否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身上参差不齐的自然天性?种种“主义”之争乃至宗教间的冲突和对立,是否存在绝对的是非标准?人类又是否具备这种认知能力?从这点而言,庄子对于“不相知”的强调无疑具有强烈的解构意识形态的道德意涵。
在《齐物论》关于“梦”的论述中,“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庄子强调人在梦与觉的根本问题上缺乏绝对的认识辨别能力,其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陷入怀疑沮丧的悲观境地,而更像是“苏格拉底式”的唤醒:我们深知面对我们自身的无知(知无知),从而打破对“自我主体”的固执。一般在谈到庄子的“不相知”时,学者大都将其划归到怀疑主义抑或不可知论的阵营,至于“生命关怀”这一重要层面往往落在学人视线之外,多遭忽忘。然庄子实是并未着眼知识论(尽管其触及到知识论问题),而是用心在其人生哲学上。质而言之,庄子意欲唤醒的是一个开放的心灵,使人得以从“黮暗成心”中超拔出来,即从自我中心的狭隘格局中超拔出来。庄子对于“不相知”的强调并非对人与人之间相知可能性的否认,更有其特殊的道德蕴涵,即追求自由与宽容,尊重承认不同个体、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这也是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对话并达至相知的基础。亦可说,庄子的相知乃是以“不相知”为前提的。
三、“以道观之”与相知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人与人的共在构成了人际交往过程中冲突的根源。而人的生存境遇的差异性和自师成心的执着,阻碍了不同个体之间的相知和理解。那么如何超越成心的隔阂,从而达成不同个体之间的理解和相知呢?
在谈及是非之辨时,庄子曾指出:“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质而言之,“自我观之”与“自彼观之”代表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而“我”和“彼”则是对话的不同基点。而在庄子看来,这个对话的基点本身是有限的,因此消弭相知隔阂的关键就在于从“自我观之”转化到“以道观之”的层面,即以“道通为一”的视域审视、看待世界。具体而言,“以道观之”意味着要充分意识到自身于“道”的渺小和有限。《秋水》中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道”的绝对视域是对“物”“差”等相对视域的超越,这意味着在人际交往中,是非,贵贱,大小的主观判断都要“悬置”起来。而作为承载主观判断的“语言”也因而是有限的,故在庄子而言,交往过程中的对话和理解不能止于语言(形式)层面的相知,语义的理解和精神境界的理解间要保持一致。
在日常生活中,人类皆是依赖语言相互沟通,但效果却往往并不理想。回到鱼乐之辩,庄子说“鱼乐”本是感受的自然显露,首先本未诉诸于“知识”的普遍性勉强他人同意,信念与知识的不同在于背后的命题态度,而惠子却执着于语言的真实根据,忽略人与万物之间的相知并非定要依靠语言的介质才可抵达理解和相知的真实。换言之,所谓“真”的成立,并非一定要依赖说理论证才有合法性,惠子对庄子的“真”的怀疑无疑是站在分析的知识论立场,但“拿出证据来”不过是自然科学真理观的“傲慢”③。事实上从柏拉图的知识三条件论,到盖提尔和古德曼的因果知识论,始终未能解决知识的普遍定义难题,尤其是道德伦理、美学等人文知识领域,更无法简单诉诸于经验语言层面的论证④。
本文认为,鱼乐之辩的意义并不在于谁之胜负,而是揭示了不同个体的相知过程中,理解要高于说理。毋庸置疑,真实的相知与理解需要说理,但说理的目的并非证明彼此之是非高低,说理乃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与他人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学会尊重他者与我们的不同的生存境遇。陈少明先生在《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中指出,“只要思想以说理的形态出现,即表达我知道而非独断的我相信,讨论或问答就可能进行。”[6]221而以笔者管见,如果从庄子的视角观之,“独断”的表达反而是“我知道”而非“我相信”——“相信”(信念)只是个人或群落的主观心理或意向,而“知道”(知识)则势必要突破信念的私人局限而达至普世性(universal)和公共性,并要求获得他人的普遍承认。历史上,无论是纳粹屠杀犹太人抑或伊斯兰教徒的狂热圣战,这些政治灾难和宗教冲突背后无不是宣称“我知道”而非“我相信”。因此在庄子而言,放弃“我知道”的独断不仅是对人自身有限性的深刻体认,更是人与人之间共处和相知的前提。本文试图揭橥的问题亦应作如是观。
此外,在《人间世》里,庄子表达了对现实中惨烈的人际冲突的生存感受。为了避免在交往过程中陷入是非之争伤害生命,庄子指出了“顺人”的必要性,“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但庄子所谓的“顺”并非无原则的顺从,而是强调在交往的过程中不能随波逐流,要保持自我精神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即《庄子·外物》篇所云:“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天下万物都是“道”的一部分,万物在道的统一秩序下却又不失其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这事实上也包含了个体与群体交往过程中的智慧。因此“以道观之”的前提就是要在共在之中持守自我的精神自由。“顺人”与“不失己”并行不悖,也意味着在“道通为一”中自我与他者的统一,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知”。
[注释]
① 惠子显然又并非如康德那样彻底追问认识发生的根本可能性问题,因为认识的正当性自始就是被默认的,譬如惠子对“这是鱼”的基本事实并无异议,而这个时候认识已经发生。这种对认识何以可能的穷究,极有可能落入黑格尔所谓“在没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游泳”的认识悖论。而惠子发问的不彻底性也为其后庄子对“安知”的论题转化埋下伏笔。
② 庄子对论题的转化,历来饱受“偷换概念”或者“诡辩”的诟病。然而笔者想指出,庄子对于“安知”问题的转化理解,实质上是知识论到生存论之间的转化,用牟宗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从名理到玄理的转化:名理是客观的谈,而玄理则是主观修证的谈,“庄子之心灵固根本不同于惠施,……名理与玄理之间有相当之距离。”要言之,庄子之“知”并非建立在主客二分上的认知性之知,因此“鱼”不是对象却又与主体一体共在,二者一同游于大化之气中而同享法悦,故庄乐鱼亦乐,然又各忘其所乐也。参阅牟宗三:《名家与荀子》,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14页。
③ 庄子对惠子名理论证要求的拒斥,可视为艺术经验的真理要求的“对抗”,即伽达默尔所说的“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科学或名理上的认识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多种方式的一种,不能以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真理概念作为衡量人文艺术经验真理性的标准。参阅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导言部分,第4-8页。
④ 譬如“不能欺负弱小”的道德律令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信奉的,人们在日常中亦常言“我知道不能欺负弱小”。但如果依因果知识论的定义,“不能欺负弱小”并不是可以经验论证的事实。外在知识或自然科学知识强调手段的可重复性与公共性,但诸如道德或者美学知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互冲突的。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