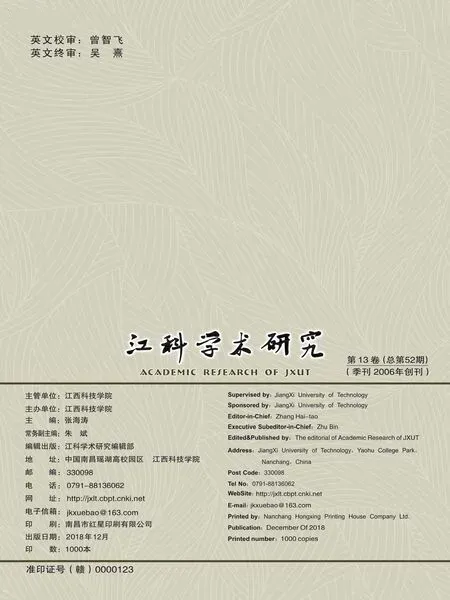齐鲁文化视野下的稼轩爱国词
何凤娇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辛弃疾生活于积弱不振的南宋,为了实现统一祖国、复兴民族的抱负和理想,功业不成转而以词章为武器,而最能代表稼轩“英雄之词”精神的风格就是他的爱国词作。由于其故乡在山东,祖父辛赞在很小的时候就让他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其后又受到道家、兵家、法家等多种文化的多重影响。可以说,齐鲁之地的文化对他一生的个性气质和品格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文化,是历史的缩影。而地域文化会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从而反映出该时代的文化特质。从这个角度上来切入作家的作品,可以站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开拓文学作品研究的新途径。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四部分从儒、道、兵、法四家典型思想上分别阐述稼轩爱国词的爱国情怀,探寻其爱国词在齐鲁大地的文化意蕴。通过对以上各个方面的分析,结合作者的创作本意,更好地感悟作者的内心情感,体会它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能量。
一、稼轩及其爱国词
(一)稼轩的生平
辛弃疾,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完颜亶)天眷三(公元1140年)。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稼轩任镇江知府,时年65岁。两年后被朝廷任命为枢密都承旨,但诏令到铅山,他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开禧三年(1207年)秋天,卒。后赠少师,谥号忠敏。《宋史》记载稼轩“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始筮仕,决以蓍,怀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离》,遂决意南归”[1](P12161)。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21岁的稼轩揭竿起义,投奔耿京。第二年在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的途中擒拿叛徒张安国。25岁时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开始了在南宋的仕宦生涯。乾道四年,他到建康府做通判。期间上书《九议》和《应问》3篇,又将《美芹十论》献给朝廷,详细的论述了形势的变化发展,战术的长处短处,地形的有利有害。淳熙八年(1181)冬,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稼轩开始了10年带湖闲居时光。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他举家移居瓢泉。八年闲居,稼轩的爱国情怀变得更加忧愤深广了,今共得年代可考的词即达180篇。晚年在镇江任职时,又因为言官的弹劾而被罢职,在铅山抱病而亡。
(二)稼轩爱国词形成的文化背景
1.现实因素。南宋积弱不振的局面。靖康巨变造成了北宋覆灭,赵构偏安一隅,淮河以北被金军占领,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金贵族统治者在北方推行民族歧视,对南方则一面多次发动南侵战争,一面又以讲和为条件,强迫南宋称臣纳贡。南宋当朝政权虚弱无能,不断压榨人民,使原本就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沦入更加痛苦的深渊。
2.历史渊源。齐鲁文化,尤其是儒、道、兵、法四家思想的影响。稼轩出生地在历城(今山东济南),距离当时齐都营丘、鲁都曲阜都非常近。在齐鲁文化交叉交流传播影响下,历城就成为了儒学文化的中心地带。其祖父辛赞在孙子很小时就对其进行爱国传统教育。这对稼轩成年后文化品格的养成和定型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从齐鲁文化看稼轩爱国词的文化意蕴
(一)“铁肩担道义”——儒家影响下的爱国忠君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念
在鲁文化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以礼乐为其文化特征。儒家文化诞生于乱世,因而强调心忧天下,兼济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已道出儒家的人生理想。
素有“掉书袋”之称的稼轩曾自誉为孔夫子的学生,其词中也大量用到《论语》、《孟子》中的名篇佳句,表明了其对鲁文化崇拜的虔诚。他青年时代所念所行、他的词作也都带有儒家思想明显的印记。
1.强烈的爱国思想。儒家济世安民的追求使得无数的仁人志士铁肩担道义,更让英雄豪杰们扶大厦于将倾。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这厚重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无疑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而稼轩汲取了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正所谓“位卑不敢忘忧国”,形成了忠贞不贰的“悲歌慷慨”之辞。以《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为例: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2](P22)。
这首词是稼轩在一次登建康赏心亭时,触景生情写下的,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议和派的愤懑不满之情。词的上片开门见山,直接点明主题,抒发了内心感情基调。“闲愁千斛”是形容愁苦极多,表现了词人不在其位而不能抗金所产生的沉重压抑之感。“兴亡”一词,更是为下片抒发无法实现抗金复国的壮志愁苦作了铺垫。稼轩借用了“谢安受谗被疏”和“淝水之战”两个典故来委婉表达自己未被重用的心情。最后两句“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以景结情,对政权的忧虑和爱国的拳拳之心、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深情的关切跃然纸上,是那么炙热而深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稼轩将儒学精神视为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召唤,其词作突出了国家利益的至上性,更为南宋中叶以后兴起的爱国词派奠定了深厚的精神力量。
2.牢固的忠君思想。孔孟儒学体系,是建立在周室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道德伦理原则,是商周时期文化思潮的集大成,并成为历代忠君思想的文化渊源。在《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中,词人写道:“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2](P63)短短几句话用了范增、范蠡的典故规劝内兄范如山以大局为重,希望他能为君王效力。从中可以看出稼轩对忠君原则的认同,但是这种忠君思想毕竟是中央集权下封建专制的产物,我们应该放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来看待。
3.积极的入世情怀。范文正公在《岳阳楼记》中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可见,入世永远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寻。稼轩也不例外,在他的爱国词中,始终渴望以自己昂扬的生命成就一番英雄事业。即便在遭遇贬谪,退居之时,他收复中原的政治理想和愿望也未曾改变过。在词《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中,他写道: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2](P515)。
词的上片以“思亲友”起意,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英雄迟暮的无奈,一个“怅”字写出了词人难觅知音的孤寂,充分体现了词作沉郁的意境。下片“云飞风起”四个字,词人在国势衰微下想起刘邦,写出了无比豁达的心胸和爱国之情。这大开大合之下,稼轩的心境也完成了由悲慨转为沉静。不愧为“真儒”!范开在《稼轩词甲集·稼轩词序》中云:“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3](P172)。
4.欲说还休的故土思乡情结。稼轩的词作书写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漂泊江南的无根者的愁绪,着重表现了心灵的忧伤和精神的苦闷。他的《满江红·点火樱桃》:
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壁。乳燕引雏飞力弱,流莺唤友娇声怯。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 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蝴蝶不传千里梦,子规叫断三更月。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2](P16)。
稼轩用感伤春归、空老岁月、思念家园抒写了“漂泊”者三个层面的悲情。上片惜春,下片怀古思家。“劝人归,归难得”用顶真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情语结束,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云:“稼轩郁勃,故情深”[4](P8)。归乡的愁苦之情,飘摇无定的家园之思萦绕在他众多的词作中。
(二)“充满天地,包裹六极”——道家影响下的达观心态及词学意境
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创始人为老子。后到战国中期,道家内部分化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派别。对于老子道家学派传人宋国人庄周,虽其故里在蒙地(今河南商丘),但在今山东东明县有与庄子密切联系的南华山和庄子后裔聚居的庄寨。这就说明庄子的道家思想成为构筑齐鲁文化的因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稼轩虽然不喜欢道教,但他对道家思想却极为感兴趣,并且尤为推崇庄子。据统计,稼轩词中与庄子相涉者计:词72首,110处。可以说,庄子的文风影响了稼轩的词风,而庄子的思想更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哲学。
1.宠辱不惊的达观心态。庄周《秋水》一篇,主旨在论大小齐一,得失有分。稼轩就以篇名命名他所住的正房,并作两首[哨遍]词。“世间喜愠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表明自己虽三进三退,也应该如浮云般顺其自然。而在《临江仙·钟鼎山林都是梦》,一句“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2](P209)又将庄子“安时而顺处”的达观表现的淋漓极致了。因而,当他晚年被再度起用时,尽管仍以国事为忧,但对于个人的穷达却看得很淡了。
2.“变温婉,成悲凉”的词学意境。清人周济在《宋四家词选序论》中云:“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4](P20)这与庄子“漆园之哀怨”上是有很多共鸣的。可以说,用庄子而转至为悲,稼轩的这一倾向还是很明显的。以词《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为例:
细把君诗说。怅余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千尺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2](P240)。
上片用《庄子天运》中皇帝张《咸池》之乐一事来写叔高之诗,比喻新颖,想象奇特,既富诗情,亦有画意。紧接着下片转至国事主题,腐败的政治,腐朽的士族,这些都没有打倒词人那颗搏动的爱国心:“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中原未复,国之不国,愁绪竟是如此强烈,半夜悲风四起,吹得那檐间的铁片犹如上阵的铁骑般铮铮而鸣。幻觉是如此酣畅,但结果却是“南共北,正分裂”,如此惨痛。此词虽为送别之作,但仍有悲壮之情。然其运笔之妙,则在于“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3]。故而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六五七》称其“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5](P166)。
(三)“大声镗鞳,,小声铿鍧”——兵家影响下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
中国的兵家文化发源于齐,同时源远流长的兵家文化也使代代齐鲁英雄血脉相连。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就是出自于齐姜子牙的《六韬》,其后的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管子》等也都出于此。而齐国深厚的军事文化也被后世代代吸收、代代承袭。
在宋代,由于“国势”特殊,齐国兵家文化收到朝廷特别的关注。而深受齐国兵家文化熏陶的稼轩,则将兵家之韬略全部倾注于奏疏及词中,将尚功意识化为他反复吟咏的“主旋律”。
1.熟练的战术思想。稼轩在其《美芹十论》和《九议》中酣畅淋漓地化用兵书术语,他的战术思想中贯穿着齐国兵家谋略。《美芹十论》开篇即为“审视第一”,而《管子》中有《形势》、《形势解》、《势》三篇论述了管仲对“势”的见解。在词《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下阕中,“一编书是帝王师。小试去征西。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2](P73)稼轩又用张良佐汉的故事抨击统治者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例证了分析形势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些奏疏和词作集中体现了稼轩政治家、军事家的卓越见识,读来让人为之振奋。
2.浴血奋战、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齐地人民群体的一个文化特征,就是骁勇善战、奋发有为。东汉末的黄巾起义,隋末唐末的农民大起义,北宋梁山泊聚众起义,无一例外都出自于齐地。稼轩对齐文化的接受和依恋,除了在反金时揭竿而起外,更多地将这浴血奋战、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寄托在篇什之中。以《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为例: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2](P548)。
此词是稼轩任镇江知府时所作,登楼的目的正是为了“望神州”,那个早已沦陷了的中原地区。词的上片写景,情景交融,渗透了词人无限的感慨;下片进一步抒发其渴望建立功绩的万丈豪情。“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是衔接“千古兴亡多少事?”而来,赞美了孙权在此地建立的功业。“万”是虚数,极言其多,一个字点明了孙权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畏强敌,自强不息,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终使其国势强盛。而末句“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是说人生在世应该像孙权那样奋发有为。从这里可以看出,稼轩那烈士暮年,壮士不已的精神已跃然纸上,强烈的战斗意志让人敬佩不止。
3.军事意象下的英雄情怀。唐五代词和柳永、苏轼词所创立的意象群不同,稼轩词的意象已不再主要来自闺房酒馆和自然山水,其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充满了血性男儿的阳刚美和崇高美,带来了词意象群的一次转折。而稼轩一生都渴望祖国收复失地,战争军事意象就成了体现他英雄情怀的最佳展示平台。以一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为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2](P242)!
词中将曾几何时鏖战的情景铺陈开来,连用“长剑”、“吹角”、“快马”、“弓弦”四个军事意象来展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愿望,颇有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之气。其词壮阔宏大,字字句句中透着建功立业的责任感。遥想姜尚东征,该也是此等气魄吧。一句“可怜白发生!”将在高潮的词境急转直下,将词人由梦境拉回现实。面对理想的灰飞烟灭,词人的内心澎湃激荡却又无可奈何,在苍劲悲凉中留给人们无穷的感慨和思考。
宋末谢枋得评价此词云:“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6](P165),拿稼轩与岳飞这一民族英雄比肩,更加突出了其“豪杰”的英雄情怀。清纪昀也说“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7]。这都点出了齐国兵家英雄气概对稼轩词气势的影响。
(四)“要与管仲做同社”——法家影响下的革新观和民族战争观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而法家学派变法革新的主张也深得改革者的提倡。在政治上,他们提倡用法治来代替西周的礼制;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强兵富国,奖励耕战。稼轩在南归后,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与措施,充分体现了具有法家倾向的军事思想。
1.力行改革,反对“和戎偃武”的革新观。稼轩在福建任安抚使时,谓“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今幸连稔,令宗室及军人入仓请米,出即粜之,候秋价贱,以备安钱籴二万石,则有备无患矣”[1](P12164)又“欲造万铠,招强壮,补军额,严训练”[1](P12164)。为了保证军队指挥的统一,稼轩冲破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创立了“飞虎军”,体现了其反潮流的精神。在这一点上,稼轩比他的前辈岳飞来的要勇敢些。
2.“以战去战”的战争观。稼轩承袭了《商子》中“以战去战”的观点,认为应该坚持抗战,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在《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一词中,他写道: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2](P526)?
“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一连用了昭君出塞、陈皇后被贬、戴为归国三个典故来暗讽宋室对敌人妥协的政策,接着写“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用李陵和荆轲来表达用武力来驱逐侵扰着的信念。
一生中,稼轩提出了众多革新观和战争观,但却从求未得到“主战派”的重视,一声浩叹“谁共我,醉明月?”更表现了末路英雄的悲哀,读来让人更觉悲凉。
综上所述,辛稼轩是一位事功型、行动型的儒士,属于个性刚毅的热血男儿。他又是一位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人物,这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又见诸于他的作为与行动。由于稼轩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了其出生地齐鲁文化的熏陶,又恰逢南宋这样风云变幻激荡的年代,因而稼轩的爱国词中就体现着较为突出的儒、道、兵、法思想。从地域文化的维度对稼轩爱国词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进一步透视其人其词的个性特色。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稼轩爱国词中那激昂的主旋律依然亘古不变,引导着我们唱出时代精神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