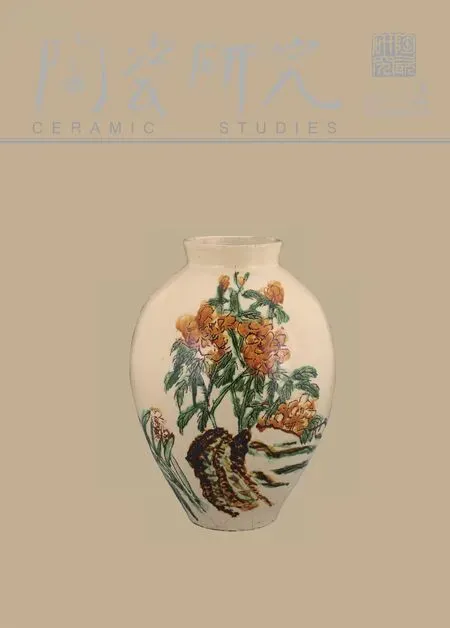契物与文化
——辽代陶瓷造型演变与游牧文化变迁
赵聪寐 王鑫
(1.内蒙古师范大学工艺美术学院,呼和浩特市,010000 2.内蒙古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通辽,028000)
1 引言
辽是由游牧民族契丹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辽代陶瓷是中国古代陶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契丹在建国前是没有制瓷历史的,辽代制瓷业是辽建国后向中原农耕文化学习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的,并最终构建了包括契丹形式、中原形式、融合形式的辽代特色陶瓷造型体系。中原形式的陶瓷器大都仿造中原固有产品造型烧制。契丹形式的陶瓷器多是仿照契丹族传统皮制、木制、或先源民族鲜卑族陶器的造型而烧造。融合形式的陶瓷器多是在契丹与中原王朝、当时西方国家接触过程中,在本民族文化与多元文化接触与碰撞中,对外族各种材质器物中某些形式特征进行仿效,并与本民族造型要素相互杂糅、融汇而形成。
器物是文化的物化符号,辽代陶瓷属于器物设计范畴,就分类而言,属物质文化。而物质文化是文化结构中最表层的部分,受制于并体现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辽代陶瓷造型的演变是辽代民族交融、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科学技术等多方面在陶瓷上的集中投射,是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产物。
2 游牧文化变迁的肇始期与陶瓷造型的产生
2.1 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肇始期——辽早期
辽代游牧文化的变迁始于辽朝早期。辽朝早期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和历史坐标,本文借鉴现有辽史及辽代陶瓷关于历史分期的研究成果,将辽朝早期规定为辽太祖至景宗时期(916-983 年)。虽然在辽建国前以契丹为主要的游牧民族其活动范围也曾出现过农耕文化活动,却只是零星的,所占比重极少。至直契丹迭剌部夷离堇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为使契丹部落转变为具有强大实力的民族国家,辽朝统治者开始接受先进的汉民族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学习和趋向于中原农耕文化,就此农耕文化在辽朝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辽代游牧文化开始有了变迁的征兆。
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分析,辽朝早期辽代游牧文化原生态系统包括的几个层面诸如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价值观念都在不同程度的发生变化。首先,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为文化变迁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辽朝建立之初,其领土所辖主要为契丹腹地即古代松漠地区。辽太祖阿保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向外扩张。神册元年(916 年),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①;神册三年(918 年),又“派兵攻西南诸部”;神册四年(919 年)“进击乌古部”;天赞三年(924 年)阿保机亲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②,至此基本控制西北部草原地区。天赞四年(925 年)阿保机举兵东征渤海;天显元年(926 年),渤海所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地俱入契丹;同年二月,东北东部“高丽、涉貊、铁骊、棘韬来贡”③,契丹对长城以北的整合基本完成。在辽太祖之后,辽太宗南下获得幽云,灭后晋。至此,辽朝地理区域扩展到幅员万里,自然环境更为丰富多样,为辽朝社会发展奠定了最基本的疆域格局。
经济生产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辽代经济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游牧经济是契丹辽朝早期的主要经济形式。辽代在拓展疆域的同时,将大量多民族百姓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因各民族群众受原有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在辽境内依然本能地从事着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使早期辽境内存在着游牧、狩猎、渔猎和农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农耕经济在原有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迅速提升,但畜牧业仍是契丹人社会经济生活所需的最主要来源。为了稳定和巩固政权,辽朝统治者对新纳入辽的区域并没有照搬原有由游牧经济占主导的草原地区的统治方式,而是考虑到多种复杂因素,制定了“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开始推行南北“双轨制”的政治体制。
辽境内农耕经济得到发展致使契丹本土开始出现聚落,并以中原地区的模式构筑城市,这是辽代原初游牧文化变迁的重要标识。契丹人的聚落组织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普通的民居方式及组织形态,在辽朝建立前就已经存在。受唐代羁縻制度的影响,其聚落组织由地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关系。至辽初,聚落组织开始膨胀和发展,农耕人口开始增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外来的汉族及渤海人。关于农业人口的聚落,其最高组织形式是“头下军州”,实际上是辽代王臣贵族的私城。城市的出现是农耕文化与定居生活的产物。辽朝城市主要受中原城市建筑的影响,但也有契丹民族特色。辽初的城市建筑规模较小,数量不多,受“因俗而治”的政治影响,契丹等游牧部落人口与汉族等农业人口在城市聚落的居住范围上形成分治的局面,但依然初步确立了辽代城市的基本体系。在草原帝国,城市的出现为农业、手工业、商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与契机。
随着辽朝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契丹人传统萨满教形态、内容、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萨满教作为辽代契丹人的传统信仰,其传统形态内容和政治整合功能在契丹建国初期的政治观念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为适应君主集权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将萨满教的某些内容与形式做了一定的改造。一方面利用萨满教树立皇帝的权威,将天赋王权的精神文化内涵比附在萨满教上,使其成为强化皇权统治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契丹萨满活动被融入辽代国家礼制之中,成为国家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这是契丹游牧文化制度和形态的变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变化的一种体现。
2.2 辽早期——陶瓷造型的产生
对应辽代游牧文化变迁肇始的历史大环境,辽早期是辽代陶瓷生产的初创期。在辽朝建立之前,契丹民族是没有制瓷业的,但早期契丹人有使用陶器的历史。辽朝建立初,农耕经济在辽境内的规模逐渐扩大,农业经济圈、半农半牧经济圈、城镇经济圈初具雏形。陶瓷器是农耕定居生活的信物,在接受中原先进制瓷技术的前提下,辽代制瓷业开始出现并快速发展,辽代陶瓷造型及造型体系随之产生,并表现或反映出辽代早期的某些时代特色和游牧文化特征。
这一时期辽代陶瓷生产从无到有,最初以生产陶器为主,随后釉陶器和瓷器的数量增多。主要品种以白釉器最多,绿釉器、白釉绿彩器次之,大约辽早期的末期出现茶叶末釉和酱釉器,其中酱釉器较少,白釉涂朱彩描金和白釉黑花器数量极少。陶瓷器的种类与造型主要有单孔式鸡冠壶、矮身提梁式鸡冠壶、长颈类壶/瓶、盘口穿带壶、盘口束颈壶、穿带扁壶、盘口长颈注壶、高足杯、碗、盘、盏托、盆等。从造型的形式与风格来看,有反映辽代游牧生活特点的契丹形式的陶瓷造型,其典型器有上述的单孔式鸡冠壶、长颈类壶/瓶、穿带扁壶等,且数量较多,是当时最为常见的陶瓷造型。从其造型的来源分析,契丹形式的陶瓷造型主要承袭了契丹民族或上溯先源民族(鲜卑族)的陶器造型或契丹本民族固有器型,具有浓郁的契丹游牧文化特征。还有一些陶瓷器造型与中原地区陶瓷产品别无二样,几乎是对中原地区北方民窑部分陶瓷造型的完全模仿。这类器物可视为中原形式,如上述提及的碗、盘、盏托、有柄执壶等,但此时这类常于居室内使用的陶瓷器物的数量相对却很少。另外,还有一些陶瓷器造型形式既有契丹民族特征又具有一定的中原遗风或其他外来文化因素,可以说是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属于融合形式的陶瓷器。典型器物主要有矮身提梁式鸡冠壶、盘口穿带瓶、折肩罐等。这三种形式与风格的产品造型构成了辽代陶瓷的基本造型体系。
总体而言,辽代早期制瓷业产生,制瓷工艺的发展处于一个承上启下、开一代新风的时期。辽代陶瓷造型体系基本形成,造型与装饰的基本情况反映出契丹原初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半农半牧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与融合,也反映出辽代游牧文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自我调试与基本态度。
3 游牧文化变迁的转型期与陶瓷造型的改变
3.1 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转型期——辽中期
辽代中期,即辽圣宗到兴宗时期(984-1055 年),辽朝进入鼎盛时期,多元文化在辽境并存,其中以中原汉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在辽境乃至中国北方得到广泛传播,契丹等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游牧文化结构从此发生了转型。可以说,辽中期是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转型期。
此时,辽朝统治阶层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继续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和完善各方面的统治。对内,政体上加快和完善“二元制”政治体制的发展。正式推行科举考试,重用有治国经验的汉族官员,四时捺钵形成定制。军事上,军事机构逐渐完备,隶属关系明确,军备严整、纲纪确立。经济上,劝农桑、轻徭役、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文化上,推崇儒学、编修佛经、佛教极为盛行。对外,以战争求和平,辽圣宗东向征讨女真、高丽,南征北宋。辽与高丽之间的战争,以高丽方割让高丽故土、与宋绝交、尊奉契丹为上国而告终。辽与北宋之间的战争,以辽宋澶渊之盟的签订、辽每年获得高额岁币而告终。这为辽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外部环境。至此,辽朝达到鼎盛,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其中农耕经济与农耕文化所作的贡献较大。
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辽中期在辽境内农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的形成。学术界认为历史上的长城是农业民族防止游牧民族侵扰的防御线,其实长城因南北两侧地理景观、气候水文的差异,成为农业文化类型与游牧文化类型的分界线。长城以北是以内蒙古高原为主的中温带半干旱区,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年降水量少于400 毫米,植被主要是草原和稀树林,北方各少数民族活动于此,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是传统放牧区。而长城以南是以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为主的暖温带半湿润区,以暖温带季风气候为主,年降水量大于400 毫米,植被主要是森林,汉族世居于此,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是传统农业区。辽中期,辽境内已逐渐形成了与牧业文化圈并行的鲜明的农业文化圈。居于多寒多风的北方大漠之间的契丹族、奚族等其他游牧民族,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④的游居生活;而长城以南,环境气候多雨多暑,居于此地的汉民族(包括渤海在内的汉人),过着“耕稼以食,桑林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⑤的定居生活。从宏观的地理位置观察,辽朝农业文化圈主要分布在原渤海国地区,隶属辽东京道;还有幽云十六州地区,这里位于长城以南,原是中原人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被辽占领后隶属辽南京道和西京道。这些地区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原无异。同时辽境内的农业区域不断扩大,已超越长城的界限,不断向草原深处和契丹腹地深入。
另外,此时在农业文化圈和牧业文化圈之间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半农半牧文化圈。因游牧经济无法满足牧人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与农耕经济的贸易交换或在游牧区出现少量农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出现。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互动虽然随着历史发展与时间推移,双方的主体有所改变,但是互动的原因具有重复性即经济互补的需要,强势文化的传播,而且两种文化的互动形成了特有的历史发展逻辑。辽代中期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形成了半农半牧文化圈。辽朝在战争中获得的农业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部分契丹人被迁入农业地区,他们放弃了传统的游牧业改为从事农业,与汉人、渤海人、奚人共同开垦荒地。农牧交错地带处于农业文化圈与牧业文化圈之间,是农业文化圈挤压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生计方式,它既不同于汉族的传统农耕文化,也不同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传统游牧文化,在半农半牧区根据地理环境发展农业和牧业。辽中期形成的半农半牧地区主要有三处。一处位于契丹发源地的潢河和土河流域,属上京道和中京道辖区。这一地域地势平坦,有河谷、草原、丘陵与山地,草原和山地被开辟为牧场,河谷与平地被开垦为农田,农牧兼营使得农田与牧场交错辉映,从而创造了辽代较有特色的“插花地”。另一处是位于胪朐河流域的西北部地区,属辽上京道管辖。还有一处位于黑龙江北部,属于辽东京道辖区。
“草原区域城市贸易文化圈的建立是传统游牧业变迁的又一重要标志”⑥。文化学者通常把建立城市视为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辽中期,辽朝城市体系在早期基础上发展完善,特别是经过辽太宗、圣宗时期的增设和调整,草原区域城市群迅速膨胀,辽腹地的城市设置基本完成,其他地区的城市比以前大大增多,形成了以“五京”为中心的完整的城市体系和全国性的市场网络。从辽朝国内商业整体发展情况看,商业网点遍布全国,从五京到州县、从斡鲁朵与捺钵之地到各个部族都可见规模大小不等的贸易中心或市场。以辽中京道城市群为例,它们是辽代草原地区商业最繁荣的城市群。在中京道所建城市中,最重要的首推中京大定府,其城市建筑布局与结构主要学习北宋汴京,“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⑦,其中“市肆”便是商业贸易的场所。大定府规模宏大,幅员三十里,城分内外,外城是商业区和居民区,即所谓的坊和市。这反映出辽代向先进农耕文化学习的与时俱进性及商业活动已经初具规模。另外,辽中京所属州县商业活动以大定府为依托,互为补充,有固定的商业市场,吸引各地商贾。商贸的发展促进草原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其手工制品具有牧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双重特色。辽代陶瓷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手工艺产品。
辽代南北地区的差异、农牧业与手工业发展的不平衡、辽中期民众剩余产品的丰富、以及全国范围内交通网的建立、铸币的广泛使用、商人群体的活跃、游牧民族商业观念的建立等都促使辽代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与繁荣,成为辽代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城市商贸活动以地理环境为重要依托,在城市群的扩展中逐渐形成了城镇商贸文化圈,成为辽代游牧文化变迁转型期的重要表现。
3.2 辽中期——陶瓷造型的改变
在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转型期,顺应辽代社会发展趋势与辽人对制瓷业的要求,辽产陶瓷进入生产的发展期,陶瓷造型设计也随之发生改变,出现了许多新的造型。这是辽中期境内农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城镇贸易文化圈及牧业文化圈相互依赖与互动、各种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与融合的产物。
因商业活动的普及,各类消费人群的需求被重视,辽中期白釉、绿釉、茶叶末釉等品种的数量都在大量增加,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黄釉陶器和黑釉瓷器,但陶器较为少见。辽代原初游牧文化虽处在变迁的转型期,但游牧经济与文化仍占微弱的主导地位,反映在辽代陶瓷造型上则为契丹形式的陶瓷器在发生变化,但品种与数量不减。辽早期的典型器如穿带扁壶、盘口束颈壶在此时已消失或少见。源于契丹传统器物的穿孔类鸡冠壶,其造型较辽早期发生了改变。单孔式鸡冠壶依然存在但数量相对减少;双孔式鸡冠壶出现并逐渐趋于定型,壶体造型由圆鼓饱满变为扁身瘦长,冠峰处多呈“凹”形,并出现壶盖。盘口长颈注壶从早期的无柄向有柄演进,鸡腿瓶的数量也开始增多,盘口长颈瓶出土数量虽不多,但它与鸡腿瓶、双孔式鸡冠壶都是辽中期契丹形式陶瓷产品的典型器物。从其造型设计与制作情况看,此时契丹游牧文化因素仍在发展并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因辽中期农耕经济与文化在辽朝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中所占比例几乎与游牧经济与文化相当,所以反映在辽代陶瓷的种类与造型设计上是中原形式的陶瓷器种类明显增多。各种造型的碗、盘、碟、罐、盏、盏托、盆、瓶等器物同时出现,且与中原地区的传统造型无太多差异。同时壶、碗、杯、盏托等数量大增并成套出土,野炊的粗制食物减少,室内的精致烹调增加。这些小型饮食器受到使用者的欢迎反映出辽代当时食品及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说明农耕生活及饮食方式对辽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因辽中期半农半牧文化圈的形成及外来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辽代陶瓷融合形式的陶瓷器继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提梁类鸡冠壶明显增多,一般下腹内收,器腹由圆鼓变扁长,器身因此从早期的矮身发展为高体。凤首瓶吸收唐、西域、契丹等文化因素,将生动形象的凤首与器形巧妙结合,成为融合形式的典型器。
总体而言,陶瓷造型丰富多彩是辽代中期的明显特征。辽代陶瓷造型体系中三种形式的陶瓷器反映出辽代制瓷业及所属手工业对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回应。
4 游牧文化变迁的确认期与陶瓷造型的汉化
4.1 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确认期——辽晚期
辽晚期,游牧生计方式、民间习俗、观念信仰已被调整和重构,农耕经济与农耕文化成为主体,辽代传统游牧文化模式发生巨大变迁。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了中期辽朝社会发展的主要面貌具备了封建时代的基本特征,并进入辽代发展的鼎盛时期。至辽晚期即道宗到天祚帝时期(1056-1125 年),辽统治集团内部虽然矛盾重重,辽境内人民反抗接连不断,但辽代的封建化进程依然没有停滞,“汉制”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属于上层制度文化的捺钵制度、因俗而治原则及相关制度继续推行并完备。汉族官员深受契丹贵族的信任,其政治地位提高,形成与契丹贵族同掌国政的局面。在国家经济结构中,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已经丧失,原始游牧经济圈不断被挤压、缩小。辽人特别是契丹人,其思想观念的汉化程度较深,传统民俗文化中大量吸收中原汉文化,佛教已经完全代替契丹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成为辽朝的国教。总之,这一时期辽代游牧文化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基本上奠定了辽境内民族、经济、文化分布格局,因此本文认为辽晚期是辽代传统游牧文化变迁的确认期。
佛教在辽朝的传播与盛行对契丹和辽朝的汉化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它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给予契丹辽朝社会以深刻的影响,使辽人特别是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信仰格局、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纵观辽代佛教发展,真正从信佛到崇佛再到佞佛发生在辽中后期,特别是道宗、天祚帝两朝。辽境内寺庙佛塔林立;佛像、法器、装饰品众多;僧侣人口冗滥;佛教文化与契丹游牧文化相互作用发生变异,从而形成崇佛习俗;佛寺成为社会文化中心;佛学成为契丹王朝的精神支柱等。辽晚期契丹人形成了一个以佛教寺庙为核心的信仰圈。契丹民族已经改变了“重武轻文”的固有民族思想,传统的尚武精神、游牧民族的英雄气概被大大削弱,由强健英武渐变为文弱涣散。可见佛教解构并重构了契丹人的传统思维与观念。另外,辽代晚期的崇佛佞佛不仅使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信仰发生强烈震荡,而且僧侣人口众多与寺庙林立改变了辽朝原初的游牧文化生态格局,促使部分契丹族及其他游牧民族从游牧到定居,也促进了城镇建设及城镇经济文化圈的形成,打破了草原原有的空间格局,进一步扩展了定居生活方式及农耕经济的比重,对游牧文化变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辽中期形成的牧业文化圈、农业文化圈、半农半牧文化圈及城镇文化圈在辽晚期仍然在互动之中继续发展;此时游牧经济及文化区域明显缩小,其他三种经济与文化已占相当的比重,四者之间相互关联。辽代牧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成分在变迁中此消彼长,辽晚期农耕文化最终改变了辽代原初游牧文化的内部结构,成为辽境内的主体文化,辽代传统游牧文化的变迁基本完成。辽境内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传统游牧是一种自然经济,与草原形成一种特殊地缘关系,它有封闭的一面,又具有与外界联系的要求。汉族移民与农业生产在辽境内持续拓展,使传统游牧经济随之发生变化;游牧文化在与农耕文化的接触、碰撞中,不断适应、调试、裂变出四种文化类型。契丹辽朝传统经济结构的改变与新经济形态最终的形成,使辽代各族民众拥有多种生计方式;四种文化圈的发展与最终定型,也使传统牧业观念发生巨变,并使新思想观念最终获得确立。
4.2 辽晚期——陶瓷造型的汉化
辽代晚期,游牧经济与游牧文化式微,四大文化圈互动频繁,农业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以汉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农耕文化已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与认可。对应辽代封建化汉化进程与辽代原初游牧文化变迁基本完成的时代发展趋势与特征,此时辽代制瓷业进入繁荣期,陶瓷器生产与发展较之辽中期又有明显转变,陶瓷造型设计的形态与风格演变更趋向汉化。
从辽代陶瓷整体生产情况看,这一时期可谓是辽产陶瓷的繁荣期。辽代制瓷技术在学习中原的基础上继续提升,烧制工艺的掌握与运用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窑场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例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沙布尔台诸窑、辽阳冮官屯窑在此期间创烧,而契丹腹地最重要的赤峰缸瓦窑、辽南京地区最大的龙泉务窑在此期间都进入鼎盛阶段。辽晚期的陶瓷造型与装饰丰富多姿,生产的产品种类不仅囊括辽早中期的所有品种,还大量烧造三彩器。
从陶瓷造型来看,这一时期辽代陶瓷造型体系依然完备,契丹、中原、融合三种形式与风格的陶瓷器依然并行发展,但三者的演变情况有明显的差别。该时期陶瓷造型设计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趋势是:契丹民族形式的陶瓷种类与造型急剧减少;中原传统形式的器物增多,且造型趋于简化;融合形式的器物种类与造型在该时期有所更替,有新器物出现。辽晚期契丹传统游牧文化式微,在辽早中期一直流行的契丹形式典型器物在此时有不少已经消失,例如最具契丹民族传统特色的穿孔类鸡冠壶(单孔与双孔)都已经不见了。此时的典型器物只有鸡腿瓶、长颈瓶、长颈注壶等,其造型虽为契丹形式,但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造型趋简并有一定的汉文化因素融入其中,契丹固有民族风格较前两个时期已经大大折扣。与传统游牧文化相反,辽晚期农业发展的稳步增长,手工业、商业的繁荣,辽人汉化程度加深,这些社会因素使陶瓷器中中原形式的器物更受欢迎,流通范围最广,其品种与数量变得更加丰富,即使同一类产品都演化出多种造型样式。该时期中原形式典型器物除前两个时期的注壶、盘、碗、盏托、渣斗等;还新增钵、葫芦形瓶、高座笔洗、砚台等器物。其中传统注壶中出现了例如鸳鸯形注壶、人鱼形注壶、内管壶等各种特殊造型的新器物。另外,围棋子、埙、瓷塑玩具也明显增多。文化在传播与接触中必然会相互影响,其影响的表现形式多样,辽代陶瓷中的融合形式是契丹文化与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接触、涵化、融汇在陶瓷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严格意义上讲,一切因文化传播与接触而产生的表现形式均为融合形式,融合形式自身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融合元素的组配情况可知融合的程度,反映文化变迁的历程,辽代陶瓷造型亦如此。辽晚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此消彼长使融合形式陶瓷造型中农耕汉文因素明显多于契丹传统文化因素,但两者的结合已经非常自然,并具有辽代陶瓷自身的风格与时代特征。流行于前两个时期的提梁式鸡冠壶、凤首瓶到辽晚期,其造型逐渐简化,器身拉长,中心下移,出现圈足,汉化趋势明显。该时期又出现了海棠花式长盘、方盘、龙柄洗等新的融合形式典型器物,其中以三彩装饰效果的海棠花式长盘最为突出,成为晚期辽代陶瓷器的代表。
从上述三种形式陶瓷产品的种类、造型样式来看,中原形式已占据绝对优势,契丹与融合形式陶瓷产品的造型设计中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外来文化因素,特别是中原文化因素。至此,辽代陶瓷造型体系整体趋向汉化,但其具体类别中仍有契丹民族文化因素。契丹文化因素与外来文化因素的融汇历程从融合形式的陶瓷造型中可见一斑。辽代陶瓷造型体系中契丹、中原、融合三种造型形式与风格,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反映出辽代游牧文化变迁的过程;陶瓷造型最终趋向汉化,反映出辽代原初游牧文化变迁在这一时期内的基本完结。
5 结语
辽代陶瓷独具民族个性与时代特征的造型体系,产生于辽代特殊的自然、社会与人文环境之中。辽代陶瓷属于辽代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的物质载体。因此,简单理解辽代游牧文化与陶瓷造型两者是决定与被决定、隐性与显性的关系。辽代游牧文化的变迁必然导致陶瓷造型的演变,而陶瓷造型演变的轨迹亦折射出游牧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元]脱脱等.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北京:中华书局. 1974:11.
② [元]脱脱等.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北京:中华书局. 1974:19-20.
③[元]脱脱等.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北京:中华书局. 1974:22.
④[元]脱脱等. 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74:685.
⑤[元]脱脱等.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北京:中华书局. 1974:373.
⑥邢莉等. 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129.
⑦[元]脱脱等. 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74: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