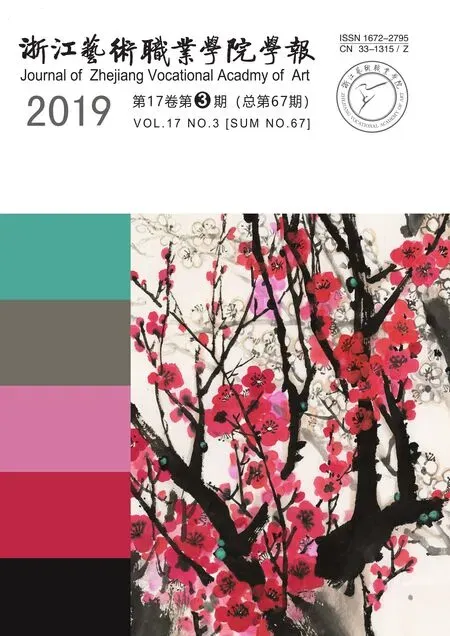中国电影叙事中的绿林文化探究∗
方坚铭 宋晶晶
一、文化模式与电影选择
电影这种影视文化的产生,离开不了与诸多文化领域的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尤其是社会学与文学。它作为一种影视文化,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以往的艺术表达方式相区别,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特点的文化创作。如果把艺术创作纳入社会生产中就是一种文化生产,而电影就是通过声音和画面传播的媒介,这种影视文化的生产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文学生产,其根本就在于它对市场的把控度。
行为交往理论家哈贝马斯曾提出:“以往,文学样式从素材中产生,现今,则作为具有专利的文化工业公开的生产秘密而得以描述,其产品经由大众传媒播散开来,从而在消费者的意识中制造出市民私人性的表象。”[1]在这里,他将文学内容与传播媒介分离开,并将其产品化,认为这种传播是一种被现代文化消费者的倾向选择,“因为市场规律已经深入作品之中,成为创作的内在法则。在消费文化的广阔领域,不再只是作品的传播和选择、作品的装饰和设计,甚至还包括作品的生产都是按照一定的销售策略在进行。大众文化这一可疑名称之由来就在于,它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以促进销售,而不是将广大公众导向一种实质未受过损害的文化”。[1]哈贝马斯把电影文化彻底规划到市场文化范围内,认为这是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产品的选择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一个历史的积淀过程。具体来说,留存至今的每一种文化样式必然是经过无数个历史选择所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样式不论在任何历史阶段都能激荡起人们心中的共鸣,就像一种闭环的循环选择一样,或者说是一种圆形叙事模式。
如果我们想要对其深层原因一探究竟,不妨引入社会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就会发现在每种文化样式下面潜藏着种族记忆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了每种文化样式的被选择过程,因为“原始意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见到这种形象。我们再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一项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2]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积淀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着多种原型结构,比如归—去—来的离合模式、修齐治平儒家政治理想的文人化品格、崇尚正义与公平的侠盗情结等等,这些模式存在于文学叙事的深层结构中,被运用于各种文化媒介,电影亦不例外。但是相比离合模式和文人品格的叙事模式,铲奸除恶的侠盗模式因为受众的原因更容易受到欢迎,也就是说,从受众层面分析,前两种模式因为涉及的文化内涵较深,虽然同属于受众的选择范围,但从接受角度看,并没有后面一种模式接地气。换句话来说,侠盗模式产生于民间,是一种通俗文化模式,来自人们对于社会的最直接的生存需求,能够契合人们的“爽报”心理,所以从古至今,这种文化模式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喜爱与追捧。如此一来,在受到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电影文化产生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效益便毫无悬念地会将矛头指向这种占有广大市场优势的文化模式。
二、心理期待与绿林情结
正如上文所说,电影文化的生产摆脱不了受到市场选择的影响,就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背景来说,由于新式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而电影文化作为在现代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大众文化中的一种,必然会受到来自文化生产领域内的转型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以受众为市场对象、以大众的文化消费为目的而进行的文化产品生产。这种文化产品的生产从取材到成型都必须符合大众的消费口味,满足大众的娱乐需求,所以在这种市场导向的影响下,带有广大受众心理基础的绿林文化便成了不二选择,这种绿林文化植根于集体无意识之中,不过,它是如何影响受众选择的呢?下面笔者将结合受众的心理期待从绿林文化的释义、文化特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一)受众心理期待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社会受众是它的传播对象,所以了解受众心理期待对于传播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受众心理期待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内推力。因为受众是传播媒介存在的基础,受众的知识水平、人生阅历、个人习惯等因素都决定着传播事业的受欢迎与否,不仅如此,受到特定时代因素的影响,受众还直接参与到了当代电影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受众的心理期待,简单来说,就是对传播内容的预先期待,是受众在接收文化传播过程中作为接收传播内容的主体,因为自身的社会阅历、心理暗示、知识储备等原因,在接收新内容之前会提前形成一个预先结构,这种结构的形成会对新内容的接收产生影响,格里维奇等人曾经将受众心理划分为五个方面,即认知需要、情感需要、个人整合需要、社会整合需要、缓解压力需要。考虑到撰述的需要,这里笔者将把这种心理期待整合划分为情节期待、人物期待、逆反期待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在笔者看来,影视作品同样是一种文本叙事,同文字记录不同的是,它们会借助生动形象的画面和声音技巧将受众带入模拟的仿真环境中,以期把受众带入叙事情景中,让受众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只有这样,受众的接受效果才会达到最理想化的程度。然而,在这之前,受众对电影叙事情节的认同与否是一个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受众内在地认同了故事情节,才会有进一步的代入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情节代入感首先必须得契合受众的情节期待,而这种情节期待正好与受众的个人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只有两者统一,才能让受众生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任何叙事过程都离不开人物这个行动因素,受众在解读故事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人物的行动轨迹来感知叙事的节奏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不免会对涉及的人物形象产生某种期待,比如希望该人物应该如何如何,又希望其他人怎样怎样,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人物形象的心理补偿,希区柯克在论述这方面时就有说道:“电影关键在于迫使受众把自己置于作品人物的位置,因为说到底,人们只对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才会真正感兴趣。”[3]也就是说,受众的这种人物形象期待关键是要和自身有共鸣之处,并且能够弥补自身在生活中无法满足的事情。只有这样,人物形象才能走进受众心底,也才能让受众对整个叙事情节产生兴趣。
受众在接受电影叙事的时候存在一种对“未知”的猎奇心理,如果一种叙事程序毫无波澜、完全不能脱离受众的预期设定,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叙事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获取受众的注意力,相应的,最后的受众反应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为这种叙事缺乏了能吸引受众的基本因素,即叙事高潮。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电影叙事想要让受众保持“在线”的状态,必须运用能够满足受众猎奇心理的叙事手法,这种手法不是完全脱离受众的日常生活,相反,它必须紧贴受众,让观众既觉得熟悉又无法完全掌控,我们可以运用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来达到此效果,这种陌生化手法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就是将日常生活进行“变形”,让受众产生一种“陌生感”,以此来突破常规,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二)绿林文化释义
公元前21年,也就是西汉末年,身为大司马的王莽夺取了汉王朝政权,并设国号为“新”,社会动荡不定,当时荆州一带又自然灾害严重,饿殍满地,赤地千里,人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法解脱。为了寻找解决之道,以王匡为代表的数百名民众反抗起了王莽政权,此次起义声势浩大,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于是王莽派遣两万精兵前去镇压,结果以起义兵失败退回“绿林”而告终。这则历史故事记载于《后汉书·刘玄传》中,这里的“绿林”在现代意义上就是山林之意,所以当时也称起义军为“绿林军”。后来这种称谓开始由特指转移向泛指,也就是说,如果你去翻看相关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很多其他延伸出来的称谓,这些称谓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性质的,从词意的正负义上分析,第一类属于贬义,这通常是从国家制度维护者的立场出发,他们会将其定义为绿林大盗、绿林强盗之类;而第二类则是从人民群众出发,他们的称谓一般都具有褒义性质,比如绿林豪杰、绿林好汉、绿林豪客等之类,从这个层面上看,由此形成的这批“绿林人士”拥有广大的民众支持,因为这一批人士代表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不满与反抗。在长达五千年之久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无数个朝代在其中更替变换,就像一种历史规律一般,这种更替也会伴随着无数个起义反抗,尤其是当政权的腐败危及人民自身的生存条件无法保障的时候,来自底层民众的反抗则更为激烈,而这种起义如果得不到预期结果,进已无门、退而无路的时候,起义军的一个惯常选择就是“归隐山林”。他们在山林中安营扎寨,凭着反抗强权、为民为己谋利的精神支撑,常常做出一些仗义豪举,这样就形成了与国家制度相互抗衡的一股力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笔者以为,绿林文化形成于民间对于政治压迫的反抗,因为长期处于在野的状态,又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也决定了其文化表达方式常常以一种通俗的形式出现,就像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一样,而绿林文化就属于“小传统”中的一种,又因为绿林文化中的侠义精神正满足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需要,所以人们对于绿林文化的推崇说是一种选择,更毋宁说是一种精神补偿。
(三)绿林文化特质
绿林文化产生于民间,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大众口味,这是由它自身所具备的特质决定的,联系上文笔者所论述的绿林文化产生背景,我们可以发现,绿林文化最鲜明的一个特质就是对于强权的反抗。
“强权”政治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当政权结构出现破损的时候才会显现,如果从信任的角度来说,一个政权的稳定离不开社会及其子民对其的信任,这种信任就是人们把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政治权利等都交到现有政权中,就像风险投资一样,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自己能从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比如基本的生存保障、个人发展独立的诉求、与他人交往的和谐稳定的环境等,如果这样的信任遭受到破坏,比如说在封建君主统治时期的古代中国,因为君主的至高权利导致下层人民的利益被一层又一层地损害,日积月累,这种社会信任也会随着日益加剧的剥削而削减,于是,为了争取自身的正当利益,重新建立自身与社会的这种信任关系,人们会选择暂且脱离现有国家制度的束缚,就群体内建立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信任网络,这种网络关系和以血缘为链接的宗族网络有根本不同之处,因为它具有明确的行动指南,网络之内的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束缚,或者可以说,这个网络内的人际界限十分明确,这种特点的好处在于网络组织可以迅速发展壮大,而且不限制地域、民族、性别之间的差异,因为共同目标的确立,使得这种网络组织拥有接近于宗教似的忠诚,又因为关乎无政权人民的切身利益,所以往往能一呼百应。因此,这种具有“蝴蝶效应”的民间信任网络组织的建立足以形成与强权政治相抗衡的力量。
绿林文化的第二个特质是英雄豪杰的人格魅力,不论是从现实社会现象中,还是在所有有关绿林文化的文本记录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绿林文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代表符号,那就是“绿林好汉”,如果缺少了对绿林好汉人物个性的探讨,那么整个绿林文化将会失去最直接的行动要素。从社会活动上来说,绿林文化的实践意义远胜于其理论文化意义,而其中的绿林好汉则充当了必不可少的行动者的角色,因为只有这一行动人物登场,才会使得因为特定目标而建立的绿林组织有实现的基础。总体来说,在绿林好汉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特属绿林人物的性格特点:首先,侠肝义胆是大部分绿林好汉都具备的人格品质,这种侠义,体现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敢果断上,也体现在劫富济贫的忠义仁厚上。在古代社会,因为缺乏基本的权利保护屏障,下层人民的利益一旦受损,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妥善处理,当他们对政权失去希望时,就会将目光投放在那些维护社会正义的侠义之士身上,这种寄托既带有渴望被拯救的期盼,也带有对这些“编外人员”的歆羡;其次,自强不息是绿林好汉身上所透露出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绿林组织从小规模不断壮大的精神支撑。因为他们所要面临的正好是社会不平衡的一面,而抗争的对方又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势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一组织内,一批人倒下,总会有另一批人接替,一次活动的失败还会有其他活动的登场。这种不怕牺牲、不怕失败的自强不息精神是获得群众信任的有利因素,就像一种誓言一般,绿林好汉以其自身的实践活动证明了自身;最后,俗世习气是绿林好汉的典型人物特点,这也是为什么绿林好汉最容易获得群众支持的一个原因之一,毕竟绿林好汉一般都是来自群众中,带有群众习以为常的秉气习性,他们对群众极其熟悉,知道对方的喜怒哀乐、急重缓轻,所以更能接地气地贴近群众的生活里面。
因果报应的现实关照,是绿林文化的第三个特质,这其实是由他们的现实目标决定的,绿林组织的每一次行动都具有很迅速的现实回应性,这些行动往往是根据现实中最急迫的问题而发起,因为是直接的冲突斗争而不是协商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得到结果。从现实层面分析,绿林组织脱离了对现实制度的依靠,对于绿林人士来说,更愿相信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这也是他们当初选择“绿林”的原因之一,不像封建君主制度所强调的那套“天人合一”的理论,他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往往是惩恶扬善,扰乱社会公平正义的就应该受到惩罚,反之则应该受到褒奖。他们的惩罚不需要等待层层制度程序的审批,而是当下就能获得心理解脱,所以在他们眼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摈弃了世俗的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平正义、因缘善果才是他们所信奉的真理。所以,面对社会生活中的丑恶,哪怕对方是位高权重的政治角色,他们也能“敢为人先”、为社会除恶,这种雷厉风行的处事风格满足了群众的“爽报”心理,也是群众对于因果报应的现实期待的实现。
三、电影化的“文本”叙事
前面主要讨论了绿林文化及电影受众的心理期待问题,笔者试图从上面的论述中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所在,显然,通过上面的讨论,这两者之间联系已经呼之欲出。也就是说,当下绿林文化的大量影视化改编正好是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根据对受众心理期待的市场分析,发现绿林文化的特质正好可以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不论是绿林文化中对强权的反抗,还是绿林好汉的侠肝义胆,抑或是照应现实的因果报应,这些经过影视化的处理,使得受众忍不住将自身代入其中,希望在里面能得到某种现实补偿。究其原因,人们为何会在一部影视作品上花费时间金钱,从纯粹的消费角度考虑,这离开不了受众的“娱乐心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生活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相应的各种竞争压力也随之加大,处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的观众需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地方,毫无疑问,电影便是其中一种方式。所以,电影创作是如何完成这一“社会期待”的,便是笔者接下来所要论述的问题。
电影创作离不开对于剧本的选择,这是电影故事的蓝图,但是有了好的剧本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后面还需要对这个剧本进行电影化的加工,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只会是空有好的剧本而无法生产出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这种对剧本的电影加工和其他文学加工有所不同,因为这需要运用到很多技巧性的元素来进行画面的拍摄和完成一系列连续性的动作。就表达绿林文化的影视作品来说,从剧本选择到影视化作品的完成,因为电影化的叙事方式,最终决定了它的受众取向和规模,因为这种叙事的转变正好是剧本从“文学性”走向“消费性”的过程。
以“绿林文化”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最多的算是“水浒”系列,《水浒传》这一部文学经典承载了太多人们对英雄豪杰的虚幻想象,故而但凡作品中有其故事来源者如宋江、武松、林冲等皆被改编成独立影视作品,早期作品中较为出色者算是1957年上映的由吴回导演、程刚编剧的《智取生辰纲》,再到1972年由武侠宗师张彻拍摄的《水浒传》和1975年拍摄的《荡寇志》,而后,在影片市场中反响较大的算是1993年上映的《水浒传之英雄本色》,近年来虽也有类似作品出现,但却以翻拍前作为主,自出新意者寥寥无几。如若从文本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由于考虑到大众对水浒故事的熟悉程度,此类作品往往会在对叙事背景进行简单介绍的前提下,编剧会截取文学文本中的一个桥段进行渲染铺设,如1957年版的《智取生辰纲》便是以晁盖、吴用、阮氏三雄等八人为主要英雄人物,影片节选的是“水浒”故事中大名府留守梁中书,为讨好权臣蔡京,敛民脂作生辰纲献京,在黄泥冈,生辰纲却被晁盖、吴用等人用计夺取的经过,在影视作品中,保护与劫取生辰纲便成为故事的焦点所在,对人物的渲染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超越了文学作品中对社会背景的强调,因为影片中叙事的需要,社会背景已经成为一种从侧面烘托英雄的手段。这种手法同样也能在后面的作品中看出来,如1972年版的《水浒传》就是以燕青、李逵、卢俊义等人为主要叙事人物,同样截取的是水浒中吴用智赚玉麒麟的一个桥段,即晁盖被史文恭射死,梁山拉拢卢俊义入伙,之后斩杀史文恭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片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改编更甚于前者《智取生辰纲》,因为在1972年版的影片《水浒传》中,英雄人物是其主要叙事焦点。此外,由影片所展现出来的“侠义”精神似乎已经开始向市场靠拢,更符合人们“爽报”的现实心理期待,加上片子本身影星云集,所以一上映就“吸粉”无数。
除了从水浒故事中取材改编的影视作品外,其他以“绿林”题材为主题并贴近现代大众生活状态的改编作品中,《让子弹飞》算是其中杰出代表。该剧本来源是马识途写作的《盗官记》,原作像是从民间口头流传记录下来的话本小说,作品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呈现了一种当下讲故事的氛围环境,其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讽刺时弊的意味,但是这种手法是以笑写泪、以喜写悲,其叙事风格正好可以借用鲁迅评价清代吴敬梓撰写的讽刺小说《儒林外传》的一句话:“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从小说内容分类来说,《盗官记》同《水浒传》一样,同处于“绿林文化”一类,其基本故事框架都是以时代混乱、官商勾结、百姓民不聊生为背景,再以绿林英雄出场拯救人民于水火为故事发展线索,由此形成绿林豪杰和官商勾结相互对峙的两方阵营。最后故事以双方都被镇压为结局。这种悲喜掺半的结局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对于绿林豪杰来说,这种结局似乎都是注定的,要么解散、要么被收编,总之不再像昔日那般“威风八面”。
从叙事角度来说,电影叙事与被改编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最大的不同应该在于对于声音和运动的掌控上,小说文本主要是以静态的叙事方式将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阅读小说文本的读者需要借助“脑补”才能形成完整的画面感,这样的文本叙事有个好处,那就是“千人千面”,也就是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效果。在电影叙事中,根据对剧本基调的确定会选择适当的音乐,不同的背景音乐会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触体验,从而也会改变对影片的观赏效果。另外,在电影叙事中,通过对场景的转换、摄影镜头的选择也会对故事进展产生影响。
以上是笔者通过案例分析的手法论述了电影化的叙事方式对于文学文本的改编和整合。现代表现绿林文化的电影,大部分都是经过对原著文本的电影化改编才最终显露于荧屏,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作品外,其他还有如《智取威虎山》《英雄本色》《天下无匪》等等,这种电影化叙事,是对原作的二度创作,因为叙事风格的差异,所以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四、结 语
电影是一门艺术创作,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社会受众就是它的市场,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文学创作已经转变为文化“生产”,而文化生产是为了文化消费,把文学“产品化”,其目的终究是想得到文化传播的最佳效果,这就离不开对受众的心理期待进行揣摩,然后进行“文本”选择。绿林文化以其自身对大众生活的贴近性而拥有坚实而广泛的受众基础,其文化特质与受众心理期待刚好契合,不论是它的反抗精神,还是它的“行侠仗义”,总之,它满足了人们对现实缺憾的心理弥补,并且通过电影化的叙事方式,绿林文化以生动鲜明的画面感和“声”临其境的音响调试让受众完成了“未尝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