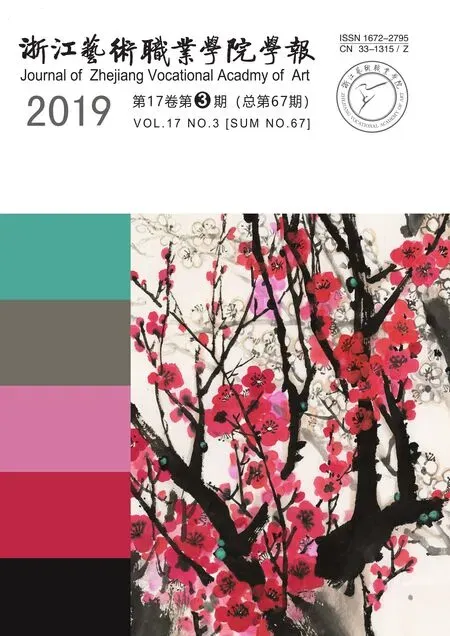关于“康熙十四律”的研究综述
谢鹏飞
“十四律”最早记载于《律吕正义》一书中,据《清史稿·乐志》所云:“帝重违臣下请,五十二年,遂诏修律吕诸书,于蒙养斋立馆,求海内畅晓乐律者。”[1]1713年康熙皇帝主持海内外学者编撰律吕书目,即《律吕正义》。这一饱含中外知律之士智慧的乐学大典,既有经学家们对于传统的律学的继承,又有传教士对“十四律”的生成所注入的西方音乐理论元素。
“十四律”的问世对清朝音乐理论的构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现存的清代及民国时期文献来看,许多文人雅士也将《律吕正义》中“十四律”理论纳入其各自的乐律学著作中,如王坦《琴旨》、毕华珍《律吕元音》、戴喣《音分古义》等都以《律吕正义》为参照,何梦瑶《赓和录》则直接摘抄《律吕正义》中关于十四律的论述。[2]民国时期,“正史”类文献《清史稿·乐志》,政书《清续文献通考》中论及乐律的部分均以“十四律”作为理论基础。由此可知,“十四律”理论不仅在清代正史类《乐志》中占主导地位,并指导着清代民间文人雅士撰写乐律学专著。
正因“十四律”在清代律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有其独特的内涵与历史价值,引发了后世学者对“十四律”研究的重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民国以来先后有十余位学者发表了各自关于“十四律”的学术见解。
笔者将各家关于“十四律”的研究综合起来基本可归纳为“‘十四律’的理论来源”“‘十四律’的律制归属”“‘十四律’管与弦的音高关系”以及“‘十四律’的实践与评价”等方面对近百年“十四律”的研究成果展开综述。
一、“十四律”的理论来源
“十四律”作为一个不同于以往十二律五声二变的律制结构,其理论来源尚不明确,是传统的延续?还是外来音乐体系的融合?这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当今学者们对于十四律理论来源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传统理论的延续”“西学中源”以及“民间来源”三种观点。
(一)传统理论的延续
主张“十四律”来源于传统理论的学者主要有赵玉卿、漆明镜等。漆明镜在《试从〈御制律吕正义〉议“康熙十四律”》[3]一文中指出:“《律吕正义》中详列了由三分损益生律法得出的古尺和今尺十二律的详细数据。凡涉及生律数据,无不与三分损益律相同。”以《律吕正义》中所罗列的数据与三分损益律的数据相对照,两组数据相吻合,故漆明镜主张“十四律”是依照前人所阐述的“三分损益律”这一传统理论所制定的。
赵玉卿在《也论“康熙十四律”》[4]一文中解释道:“康熙十四律所讲的‘和黄钟,为半太簇之半律’的说法,与朱载堉《律吕精义》有关。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认为‘大吕半律合黄钟’中提到的‘略差不远’,从古代乐律理论和实践上来看,朱载堉所认为的‘略差不远’应该是在大吕和太簇两律之间。”由此可看出,朱载堉使用管径实验说明了黄钟与半黄钟不相合,赵玉卿所主张的“黄钟相合半太簇”也正是这一实验结果的延续,故赵玉卿所认为“康熙十四律”理论是来源于前朝朱载堉所用的“管径理论”。
(二)“西学中源”论
翁攀峰《关于“康熙十四律”思想来源的初步探讨》[5]中从“西学中源”的角度对十四律源流作了考究,认为“康熙十四律”是在清朝统治者喜好西学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律学与西方音乐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对此,翁攀峰分析道:“《律吕节要》为传教士为康熙编写的几部音乐教材之一,在此背景下,康熙下令编撰的《律吕正义》一书,完全有可能受到《律吕节要》的影响。”翁攀峰列举了两部著作在内容上的异同,论道:“内容上看《律吕节要》围绕管弦音协和与不协和音程以及其发声原理展开论述,提出‘气冲于箫类之管中,搏于箫管中之裹皮而声响……气入于管内,于管裹皮,冲触而有数者’。”此段与《律吕正义》所记载“凡管生声入气,自吹口入于管内,往来冲触至管底,口边气出乃成音”。从两本论著的对比可看出《律吕正义》中的以管生声的物理方法与《律吕节要》中的记述相吻合。
有关于“十四律西学中源”这一观点的阐述,翁攀峰在别文《西乐与传统律学结合之作——“康熙十四律”思想来源新解》[6]中称康熙所理解的“隔八相生”理论是西方乐理体系的八度的概念,而非三分损益下的传统律学三分损益法中的“隔八相生”之法。翁攀峰引用大学士张玉书《张文贞文集》中关于“隔八相生”的论述,即“七音高下,至第八声复还其始,所谓隔八相生之法”。以此来论述“隔八相生”的乐学概念在这一时期的转变,反映了西方乐理体系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不仅在官撰律书中显现,民间文人雅士论“律”时也将此理论的转变囊括其中,更加印证了“十四律”并不单单是我国传统律制的延伸,而是多轨发展的产物。
(三)民间音乐实践
李来璋先生在《康熙与十四律》[7]一文中提到其对“南昆”过场曲牌“翻七调”的测音实验,测验结果表明其间的音程关系都处于浮动状态,并不拘泥于某一律制,如“大二度关系在纯律七平均律及十二律间浮动;小二度在四分之三音与小全音间上下浮动”。李先生从测音结果反映出的数理逻辑关系,判定这是一种“浮动性的复合律制”,并认为这在清代以前的音乐实践中就已经存在,十四律只是康熙皇帝在为这一复合律制做尝试。
二、“十四律”的律制归属
关于“十四律”中的律制归属问题,各学者们众说纷纭,较具代表性的是以“十四平均律”“变律”“三分损益律”“十三律”以及“律管体积”等方面作为切入点,对“十四律”的律制归属作了分析阐释。
(一)“十四律”为“十四平均律”
有关“十四平均律”的主张最早出现在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这一著作中,著作中指出“清制十四平均律”,依“四率密律”算式而成,首次提出了“十四平均律”的概念。陈万鼐在《清史乐志之研究》第二节《清制十四律理论的推测》[8]87-91一章节中认为“四率密律”不单指清制十四平均律的基本算法,早在明朝朱载堉就使用的定律的方法。陈万鼐以刘锦藻在《清续文献通考》中所首提的十四平均律理论为假设,对“十四律”音分值进行平均计算并罗列,基本算法为将原本十二平均律中的八度内总音分1200 音分除以14,得到“十四平均律”。每一半音的音分值为85.7143,音分继而随律递增而递增,即黄钟至大吕为85.7143,大吕至太簇为85.7143,推得黄钟至太簇为171.4285 音分,十四律中的各律吕均按此规律来排列。
围绕这一观点,有学者支持“十四平均律”,亦有反对者。支持者如:李来璋在《康熙与十四律》[7]一文中所列的“十四管律与十二弦律七声示意图”中的管乐十四律之七声音分值一列中的音分为“十四平均律”音分值,将“十四律”阐述为“十四平均律”,正与陈万鼐先生在《清史乐志之研究》一书“十四平均律”所列的各律吕音分数据相同。
但有学者并未认同“十四平均律”,对“十四平均律”这一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郑荣达在《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9]一文的撰写过程中对陈万鼐的“十四平均律”理论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通过计算得出的十四平均律数与三分损益弦度律作了音程差的比较,其中误差在20 音分以上的就有6 个,听众是无法接受的”。郑荣达从音分引发的听觉效果来论述“十四平均律”并不适用于音乐实践,因此认为“十四平均律”的理论是不存在的。
漆明镜在《试从〈御制律吕正义〉议“康熙十四律”》[3]一文也对“十四平均律”无法认同。漆明镜述道:“《清朝续文献通考》中说康熙十四律是用‘四率密律’计算出的‘十四平均律’,而《律吕正义》原文中并未出现‘四率密律’的字样。”以此来判定刘锦藻“十四平均律”的理论来源并非来自《律吕正义》中“十四律”理论,而是其主观臆断。
(二)“十四律”为“三分损益十四律”(正律加变律)
郑荣达《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9]一文中论及“十四律”律制归属的问题时则认为“正律加变律”是“十四律”制成的关键。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上,郑荣达提到:“他(康熙)将多出来的两个变律,直接插入到原管律的十二律中,将变律林钟在管律上改名林钟,原林钟改名夷则,后续律名都移后一律命名;又将变律黄钟,插入到管律的半律黄钟前,易名半大吕,成为所谓的十四管律。”故郑荣达认为十四律依旧是按照“三分损益法”为“十四律”的律制归属,多得的两律则是三分损益十二律中仲吕所生变黄钟(三分损益法中,仲吕不能再生黄钟,因此故称为变黄钟),变黄钟则下生变林钟,将变黄钟与变林钟两变律加至三分损益所生的十二律正律中构成十四律。
(三)“十四律”为“复合律制”
李来璋在《康熙与十四律》[7]一文中提到:“十四律是一种带有某种浮动性质的复合律制,不是平均律;其乐学形态上的七声(音)关系属下徵调音阶(新音阶)七声间并非等音程关系。”即十四律是民间乐学影响下所产生的律制体系且是带有浮动性的,游离于各律制之间。
(四)“十四律”为“体积律”
陈万鼐在《清史乐志之研究》[8]108-127一书中第六节《清制十四律的检讨》一章节中谈到“用原律管的体积去推求音分值与频率都是非常可靠的,利用此种方法而得出的律制故可称之为‘体积律’”。陈万鼐首次以“管体积”为角度阐释十四律的律制归属,其生律流程是依《律吕正义》中《定黄钟纵长体积面幂周径》中的“四率比例法”求得黄钟管的管径面积与管体体积;继而参照《律吕正义》中《黄钟加分减分比例同形得声应十二律吕》中的“四率比例法”,以黄钟管的体积与管长为基础,推算出各加分减分管的管长、管径与体积。
另外,胡企平在《中国传统律管通论》[10]一书中与翁攀峰在《关于“康熙十四律”的思想来源的初步探讨》[5]一文皆依照《律吕正义》中的各管数值算法,对“体积律”这一概念加以诠释与解读。
(五)“十三律”而非“十四律”
翁攀峰在《黄钟正律与谁合》[11]一文中有依照律管频率值与音分值来考究黄钟正律与何律可以达到全半相合。翁攀峰将正黄钟、半大吕、半太簇的古今管长、管径进行换算,继而用声学公式计算频率,最后算出音分值这一系列步骤,得出大吕半律的音分值为1199.599,故黄钟正律与大吕半律近乎完全接近一个八度,两者音差只有微乎其微的0.401音分。而算得半太簇的音分值为1278.588,与1200音分相隔78.588 音差是人耳完全能够辨别出的。故翁攀峰提出:若用未经过管口校正的律管来制律,“康熙十四律”应该是“十三律”,而不是“十四律”。
三、“十四律”管与弦的音高关系
《律吕正义》中论述“十四律”管弦取“分”(即各乐器的生声的长度比)原则的不同主要集中于上编卷二《明管律弦度五声二变取分不同》一节中,原文阐述了十四律体系下的弦律是依照三分损益法所生得黄钟与半黄钟相合且兼有全分半分的十二律,与“十四律”管律“俱为全分”的取分法并不一致。学者们根据管弦取分原则的不同,所衍生出的音高之间的关系各执所辞,主要观点有管弦取分不同而音高相同与同径管作管口校正后管弦音高相合。
(一)“管弦”同声
郑荣达在文章《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中对“十四律”下的管弦取分与音高关系所作的阐述中论道:“康熙御制的是十四律还是十二律,其实跟管律的管口校正原本没有什么可关联的。自古以来,无论什么律制,都存在有弦律与管律在长度上的差异问题。”[9]基于对《律吕正义》中管弦取分结果的对比,郑荣达所秉持的弦律和管律关系只是取分的不同,音高则是没变的,以此来论证“管弦同声说”。
(二)管口校正后的“管弦”不同声
漆明镜在《试从御制律吕正义议“康熙十四律”》[3]一文中指出:“弦律与管律所对应的声名从第一个音就不相同,可见采用预先设定的弦律音高来补足同径管管口校正值,十四律中的管律律名与实际音高不相符合,其只有排序的意义的声名,并非唱名,实际音高应以弦律所得音高为准。”漆明镜正是利用同径管的管口校正来使管律与弦律在音高上达成一致。
利用“管口校正”来考量管弦取分的音高关系,赵玉卿在《也论“康熙十四律”》[4]一文论及管弦音高关系时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康熙十四律是用律管定弦,在五声二变中的每一声,管律都比弦度高三律,如果将律管的管口校正考虑进来,律管本身再加上管端突出的空气柱,其音高会与弦度相合”。赵玉卿利用管口校正的原理考究管律与弦律的起音,以此来说明管律弦度如何达到相合。
四、“康熙十四律”造管测音试验
有学者对“十四律”律管进行测音试验以及声学计算,以管径物理实验来更深层地剖析“十四律”管律的内涵,旨在利用科学的测音实验来对文献中记载的乐学进行例证。这其中包括陈万鼐、胡企平等学者。
陈万鼐在《清史乐志之研究》[8]172-191一书第五节《清制十四律的研究》中展示了利用日本功学社专利品“调律仪”来进行测音实验。陈万鼐将试验结果分为下列三种表式:一为同径管十二律分表;二为同形管十四律及同径管十二律总表;三为同形管十四律比较表。在第一表式中,陈万鼐仅针对十二支正律律管进行了测音实验,并未对半大吕半太簇进行测音,故表中半黄钟音分值1099.2822音分,半大吕与半太簇并未罗列,所以,无法判断黄钟正律与何律相合。
胡企平在《中国传统管律文化通论》[10]有记载他分别找了三位吹律者,分别为“蔡吹”“李吹”“陈吹”,并选用紫竹制与黄铜制康熙1 ∶1 正黄钟同径管与异径管进行测音分析。从测音数据来看,无论是紫竹律管,还是黄铜律管,三位吹律者的数据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清康熙阳律1 ∶1 黄钟同径开管测音分析表(紫竹律管)”为例,蔡吹半黄钟的音分值为962 音分,半太簇为1142 音分;李吹半黄钟的音分值为940 音分,半太簇为1099音分;陈吹半黄钟的音分值为954 音分,半太簇为1148 音分。故就测音数据而言:按照康熙本意,他为了使管律与弦律律种相谐,采用三分损益法为基础。在管律同径倍半问题上,他采取了同径9 ∶4,即黄钟与半太簇为倍半。但从验声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吹律者的数据能达到倍半相生。
五、“康熙十四律”的实践与评价
乐律有无实践以及是否能够实践,是评价律制价值的重要标准。关于“十四律”在乐器上的实践,有学者对“十四律”律制抱有怀疑态度,继而对“十四律”的实践活动并不乐观,更有学者认为“十四律”根本无实践。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从乐谱中考究出“十四律”的因素,认为“十四律”不仅有实践,且在宫廷与民间中广为流传。
(一)“十四律”无实践意义
王光祈先生在著作《中国音乐史》中论清朝律吕一章节中有述:“由此所构成之乐制,亦当然凌乱无序;在音乐上,无何等重要价值。”[12]对清朝律制在音乐上的实践采取了怀疑的态度,认为清朝的乐制用在音乐上是无价值的。但王光祈在否定清朝乐志在音乐上价值的同时,也给予清朝乐志较为理性的评价,即“逊清乐制,实不能以其无甚价值而遂置诸不论之列也”。以此来告诫后世学者们对于清朝律制应当给予重视,不可让其演现成我国律制发展的“断层”。
杨荫浏先生在其学术生涯自始自终对十四律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一著作中道出:“明清两代出现了很多乐律著作,其共同之点,是脱离物质,逃避现实,贩卖神秘主义,说得玄而又虚,而豪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最不幸的是出现了康熙皇帝那样的最高统治者,他插手乐律的问题,用复古思想来欺骗人民,巩固其统治。”此段评价,正是杨荫浏先生对十四律的价值取向所做出的抨击。关于十四律的音乐实践方面杨荫浏先生也认为“这种纯粹出于个人空想的律制,其本身是絮乱无序,与人民的音乐实践毫无关系”[13]。继而对“十四律”全盘否定。
台湾学者陈万鼐在《清史乐志之研究》一书中论及康熙十四律时提到:“十四律是康熙皇帝要求花样翻新,以打破传统的乐志,达到皇帝裁定音乐权威的目的。事实上,是干扰乐志,制造乐律的混乱。”[8]87-91陈万鼐对十四律的评价与杨荫浏观点类似,皆认为“十四律”是康熙皇帝巩固王权的政治活动中的一部分。对“十四律”实践的评价则认为有“干扰乐志”之嫌,并不具备实践意义。
金文达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书以清朝宫廷音乐的实践为角度对“十四律”的实践作出了评价,其认为“他(康熙)研究出的结果,竟将十二律改成十四律;在实际演奏用的乐器上,音高杂乱无章。清宫廷在音乐实践方面没做过值得称赞的贡献”[14]。也否认了“十四律”的实践意义。
不难看出,这几位学者对于“十四律”的实践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是基于他们对于“十四律”的根本态度所决定的。
(二)“十四律”在钟磬管弦上存在实践
当代的学者对于清朝流传乐谱进一步分析与研究后,发现十四律在琴谱以及器乐合奏谱中存在着实践。赵玉卿在《也论“康熙十四律”》[4]中论述十四律实践时,提到“十四律”在《诗经乐谱》上的应用。《诗经乐谱》是清乾隆时期所撰,其中钟磬等乐器的使用,以及乐谱提要中出现“援古证今”“一字一音”“琴瑟止用六弦”的记录,都无疑显示出这是一份带有宫廷雅乐性质的乐谱。赵玉卿根据《诗经乐谱》中的原文所列出乐器的立调以及音阶排列组合中,钟磬一栏中下羽位对应的是倍夷则,若按照三分损益相生而成的十二律来看,下羽位对应的应该是倍南吕,而非倍夷则。由于十四律“皆为全分”的律吕排列关系,“十四律”较三分损益十二律对应的律下了一律,故钟磬一栏是按照“十四律”的律吕关系来排列。赵玉卿虽证明了十四律的实践,但对此并不认可,认为“十四律”是同径管管口校正而生出,钟磬只是人工制作的固定声高乐器,不存在管口校正的问题,在实际的演奏中势必会出现清浊两列律制间的“碰撞”。
针对赵玉卿所述的“十四律”下乐器演奏中律吕“碰撞”以至于音高不相和的问题,吴志武在文章《康熙十四律乐器实践——以〈诗经乐谱〉为例》[15]中解答了“十四律”下的乐器组合律吕间的“碰撞”问题。吴志武以管律弦律两者不同取分下的音高关系为核心,对《诗经乐谱》中的乐队组合中的各类乐器的律制的数理范畴以及乐学轨范等方面分别作了论述,从而得出“十四律”下乐器是在实践中不断地磨合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一个过程。管乐器都以“十四律”的理论主体构架下制造,以三分损益法的弦乐器通过改弦移柱或紧慢处理,以实现十四律的目的。
除了上文所论及的乐队合奏谱《诗经乐谱》运用了“十四律”的律制来实践以外,吴志武在《康熙十四律影响下的两种琴谱——律音汇考与琴谱谐声》[16]一文中记述了运用“康熙十四律”的琴谱。吴志武在文中列举了运用“十四律”的琴谱有《律音汇考》《琴谱谐声》《琴学初津》三本,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律音汇考》《琴谱谐声》两本琴谱,并以两本乐谱琴论的律吕排列、定弦以及与其他乐谱中收入的同名曲谱作乐学与徽分上的对比等作考证,均显示出与《律吕正义》中的“十四律”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吴志武在两文中都涉及了“十四律”在乐器实践上的可行性,证明了清朝流传琴谱中的琴律并不局限于纯律和三分损益律,并对“十四律”的理论价值以及实用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评道:“《律音汇考》与《琴谱谐声》大大丰富了康熙十四律在古琴上的使用,也为康熙十四律在民间的运用与推广做出了贡献。”即表明了十四律并不只是在宫廷音乐中使用,也并未像明世子《律吕精义》中的“十二平均律”那样束之高阁。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十四律”得到了广泛的实践。
结 语
自民国至今,有关“十四律”的研究取得的成果颇丰,但仍然存在较多的盲点,如“十四律”为何在清末以后的音乐实践中销声匿迹;新时期下依据数值排列的“体积律”是否经得起乐学的推敲,还是只针对相关文献中记载的支言片语所进行的进一步解读;“十四律”影响下的乐谱是否能够演奏出不同于以往十二律的音响效果?其中种种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
诸学者对十四律的讨论,笔者认为其意义不仅仅是生律途径以及律制轨范的探讨,其更深层的含义是触及到此“律”如何作为“万事根本”,继而作为加强皇权的手段。这其中涉及前朝律制在当时保留多寡、外来音乐理论如何参杂进传统律制中、此律制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效应以及统治者在制律时的心理特征等方面,“十四律”就变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且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