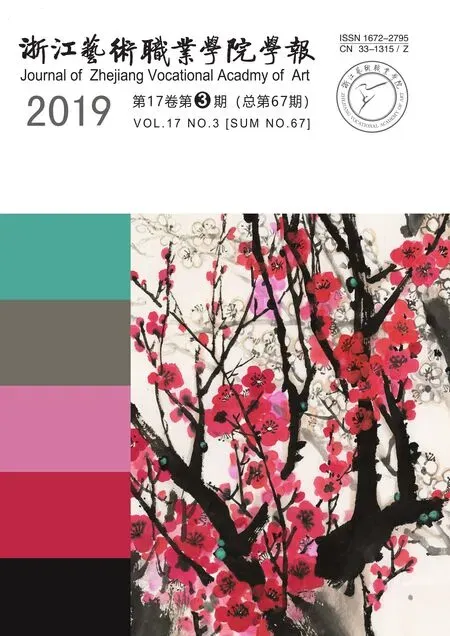图像的范式及运用
——对中国美术作品视觉阐释的反思
易善炳
图像是直观的历史,但是直观的背后不是直接,而是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形式的图像被发现,其势必会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关联。然部分学者对古代美术作品的研究夸大了图像的外延,而不注重美术作品的实质,过度地用图像学方法去解读和阐释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势必会造成对美术作品的误读,最终导致美术作品研究的非理性。
一、洋为中用——图像学是“舶来品”
图像学是目前中国美术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美术作品研究方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术学者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艺术学者采用这样的方法研究美术作品,形成这种局面,是好是坏,从当前来讲,无从对其进行定论。既然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作品,在学界就形成一种“趋之若鹜”的局面。面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这似乎是一种研究的新突破,但能否所有的中国美术作品都适合此研究方法,这里不仅让人产生疑问。
现在不妨先厘清“图像学”。“图像学”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图像学”最早的记载是1593年切萨雷·理帕在罗马出版的《图像学》(《Iconolo⁃gia》)一书中,然他在这本专著中论述到案例并未涉及图像的本身,而是对具有象征主题的作品进行了从文字上的描述,但是与图像无关。由此,可以看出理帕只是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对图像的知识进行阐释,没有对图像学的知识进行深入探讨,其实质是图像志的汇编。而后,德国学者阿比·瓦尔堡在1912年罗马国际艺术史会议上首次提出“图像学方法”,他主张要把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放在其所属时代进行研究,也就是原作品的“历史环境”。随后,潘诺夫斯基(阿比·瓦尔堡的学生)在1939年出版专著《图像学研究》对图像学作了系统的定义,从而标志着现代图像学的诞生。在潘著中,他把阿比·瓦尔堡的图像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并对图像学作了三个层面的阐释,即“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①前图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Primary or natural subject matter:(A)factual,(B)expressional,constituting the world of artistic motifs.Details on:Erwin Panofsky.Studies in I⁃conology: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M].Oxford:westview Press,1972,pp,14.、图像学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 in the narrower sense of the word)②图像学分析(Iconographical analysis in the narrower sense of the word):Secondary or conventional subject matter,constituting the world of images,stories and allegories.Details on:Erwin Panofsky.Studies in Iconology: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M].Ox⁃ford:westview Press,1972,pp,14.、图像学阐释(Icon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in a deeper sense)③图像学阐释(Icon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in a deeper sense):Intrinsic meaning or content,constituting the world of‘sym⁃bolical’values.Details on:Erwin Panofsky.Studies in Iconology: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M].Oxford:westview Press,1972,pp,14.”[1],由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来看,他的图像学理论对美术作品的解读主要是从目的到表象再到文化象征的阐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作品中所反映出的视觉图像。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要考虑到创作的社会效应?这一点很难讲清楚,谁也不可能跨越历史和时间去了解过去艺术家创作的构想和目的。对古代绘画创作的了解也只能停留在画面定格的瞬间和历史文献的记载,往往这些信息并不是太确切,因为有些信息是人为因素,干扰了公众对传统美术作品的认知。
潘著中的理论关注的是美术作品的本身,而对作品的深层次只谈到美术作品的象征(symbolical)的含义,这只是对美术作品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文化学解读,并没有触及美术创作的本身,因此,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是一种泛文化研究,给美术作品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但这并非是研究美术作品就要使用图像学的方法。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H·Gombrich)在前人图像学的基础上对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进行修正,其目的是要摆脱先前图像学研究的不足(对美术作品解读的单一性),力图把对美术作品的研究中心转移到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之上。他的担心是有必要的,更多的西方艺术学者参与到图像学对美术作品的解读的研究之中,甚至一度扩展到对中国美术作品的形象阐释上,也让中国部分研究绘画的学者耳目一新。
从图像志(Iconography)到图像学(Iconology),前后历经四百多年的历史,其间有大量的学者或多或少地在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科学技术的限制,图像学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其不能适应当时的文化成长环境,也得不到当时科学技术的支持,所以并没有出现井喷式的发展。而真正得到发展的时机,是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社会文化发展为图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最明显的变化是公众开始关注摄影、电影等新媒体技术,并把这种技术逐渐融入艺术审美文化发展之中,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公众开始从博物馆、美术馆中解放出来,逐渐转移到通过相应的媒介手段,随时随地都可以欣赏到美术作品,这种便捷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法和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沃尔夫林打破传统研究艺术史的方法,采用方法论的实际应用来理解美术作品,再用形式分析方法对美术作品风格问题从宏观到微观进行分析,其独特的视角打破了既定的规则,在美术作品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与沃尔夫林的艺术理论截然不同④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研究乃是艺术史的一个枝干,主要并不针对形式(form),而在于探讨美术作品的主题(subject matter)或含义(meaning)。因此,让我们一面分别主题以及含义的不同,一面定义形式”。详细请参见:潘诺夫斯基.造型艺术的意义(视觉艺术的含义)[M].李元春,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31.,潘著转变公众先前对传统美术作品的认知,打破了形式分析的观察方法。但潘著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公众对一定美术作品内容的理解,必须要具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或者对特定艺术题材的作品有一定的认识,不然也很难达到对美术作品深层次的认知。
中国的图像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德国著名乐器学家和音乐图像学家维尔纳·巴赫曼访华,将音乐图像学介绍到中国,图像学才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1987年,傅志强翻译出版潘诺夫斯基的《视觉艺术的含义》和林夕、李本正和范景中共同译注贡布里希的著作《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而后图像学相关书籍被不断地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学院学报《新美术》和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世界美术》先后将世界图像学研究的新成果及专著介绍到国内,并对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给中国美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目前,对西方图像学引介国内具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有范景中、曹意强、常宁生等。
图像学在引入我国之始,在术语概念上也不尽相同,也没有公认的标准。傅志强在译注中把图像学(Iconology)一词译为“圣象学”、把“图像志”译为“肖像学”,显然与公众所认识的图像学是有差距的,但是他的译法是有其合理之处。“图像志[ Iconography]一词源于希腊文中的εικονογραφιαε。在现代用法中,图像志指对美术作品内容的描述和阐释,所以,图像志的历史属于人类思想的历史。”[2],西方早期的图像志确实与早期宗教艺术有关,讨论最多的地方也是相关宗教绘画创作的内容,把“图像学”译为“圣象学”也不为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西方的绘画多为人物画,它占据了西方画史的主流。从研究西方人物画史就可以得知西方绘画的发展脉络,这样看来,把“图像志”译为“肖像学”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后来,在中国艺术研究中有了一个公认的名词——“图像学”,较为笼统地取代了相关图像学研究名称。随着西方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介入,中国绘画研究面临一个问题,即把西方图像学理论进行本土化,使它适应中国美术作品的研究。
从目前中国知网收录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论证图像学作为方法论的问题。二、论证西方图像学对中国绘画研究的适应性问题。三、用图像学方法对中国美术作品进行解读的问题。其中问题主要集中在利用西方图像学知识对中国美术作品进行解读。从上述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开始接受西方的图像学研究美术的做法,是一种“洋为中用”的表现,但令人“尴尬”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即如何使用好这个“舶来品”的问题,在利用西方图像学研究中国美术作品时,如何保持一个“度”的问题。针对此问题,锻炼先生认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图像理论”[3],然建立一种研究方法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同时也需要学者自律和慎独个人的学术研究。
二、目前图像学在中国美术作品研究中的现状与表现
图像学在中国美术研究中呈现出良好的局面,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图像学视为其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基础,并呈上升的趋势。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主要原因是相关美术图像学研究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还没有一种新研究方法能够代替目前的图像学研究。因此,图像学研究方法成为中国美术研究方法中的显学,很多学者都开始采用图像学的方式来研究古代美术作品。
用图像学方法做研究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可供“读”的美术作品。通过美术作品的视觉形象才能逐渐地展开深入研究,但这种研究通常要涉及美术作品的深层次含义,即作品的文化含义及社会功能意义。这是一部分国内研究者对图像学的理解。然通过查阅西方的文献资料发现,学者对于美术作品的图像研究较为成熟,有先后顺序,即“图像志”到“图像学”。
为了厘清这个发展的过程,可以参考波兰学者亚洛斯托基《图像志》一文,其对西方美术研究中涉及“图像志”的问题论证的较为清楚,在其文章中描述到西方图像志研究已经有500年左右的历史,其为后来西方的图像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学者使用图像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艺术品仅仅只有30 多年的历史,与西方相比,在时间上就有很大的差距,用30 多年的时间补足500 多年的知识,时间尤为仓促,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其中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够弥补时间的不足,而潘洛夫斯基在著作《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导言中讲到,美术作品的主题、意义与形式的问题,并试图定义主题和作品含义与形式之关系,其在下文中接着用“当一个熟人向你打招呼通过挥舞他的帽子”[4],你会作出反应来论证图像的视觉效应,显然在其著作《图像学研究》中的事例不是美术作品,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活中的事例,但是从中可以得出,西方的图像学研究不限于美术作品,它包括一切可视、可感的视觉形象,然在中国的图像学研究中,起初部分学者就开始设限,自觉地把它定义在美术作品之上,这就产生了中国式的图像学,而忽略了图像学的社会学意义。
对目前图像学在中国美术作品研究中的现状与表现,可以从国内举行的相关图像学学术会议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从会议论文的内容来看,其主要还是针对古代美术作品的文化阐释进行展开的,没有过多地涉及美术作品本身的讨论,参会的大部分学者只是对古代美术作品的文化学意义作了一般意义上的阐释。从知网收录学者发的论文来看,论文数量逐年增多,相关美术图像学研究主要涉及古代美术作品,对古代美术作品解读的篇幅呈上升趋势。另外涉及图像学本身考证的论文相对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块的知识是由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在研究,很多学者把方向转移到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上面,对中国古代美术作品进行文化阐释。它是考证美术作品的一种方式,可以丰富美术作品的外延,但是有些国内学者过度地去解读美术作品,脱离了艺术的本质。
从中国艺术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艺术至少要经历“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四个时期①本文论述中的中国绘画发展分期参照邓昶著《中国画学全史》,在其著作中将中国美术从总体上分为四个时期,即“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实用时期”是指夏商周秦之前的美术;“礼教时期”是指夏商周到汉朝时期的美术;“宗教化时期”是指魏晋到宋朝之前的美术;“文学化时期”是指宋朝以后的美术。。从中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艺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其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存在差异。目前中国图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不管什么样的美术作品都可以用图像对其进行解读,显然违背不同时期美术作品的初衷,最终导致研究古代美术作品的弊病。其实,出现上述现象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图像学方法使用上,曾也引起西方学者焦虑,霍斯特·布雷德坎普在《被忽视的传统?——作为图像学的艺术史》一文中论述到,德国和奥地利的学者想彻底排除艺术史,建立一门图像学。“或许是因为这种发展在现代学者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图像学过去的含义现在正处于被遗忘的危险之中。”[5]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在使用图像学方法上,也是存在着对原本图像学概念的理解偏差问题。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图像学缺少西方图像学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图像志研究阶段。因此,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于古代美术作品形式的解读上,而不是西方真正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对图像学方法的理解不全面。
从美术作品与图像学产生关系来看,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西方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图像人类学:图像学纲要》(《Bild-Anthropologie:Entwürfe fur eine Bildwissen⁃schaft》)载:“倘若潘诺夫斯基没有以图像学的方法去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寓意画的话,艺术史本来可以成为一门图像学的”。[6]从中可以看到,图像学的范围较之艺术史的范围要小,图像学隶属于艺术史,潘洛夫斯基把图像学当成一种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寓意画的一种方法,也没有想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图像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早期历史中也有见证。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图文互证”的现象,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载:“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7]在历史研究中适当地运用图像是一种有益的增补,但在著作《通志》中并未见图像。近代学者郑振铎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跋》中认为“从自然环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到建筑、艺术、日常用品、衣冠制度,都是非图不明的。有了图,可以少作多少的说明。少了图,便使读者有茫然之感”[8],说明图像作为一种视觉表达形式,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除了上述学者观点之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王充在《论衡》中认为“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见列人之面,孰与观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劝者,不见言行也。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9]显然,王充的观点是反对图像、图像描绘较之文字记载是不可靠的。由此可以看出,对图像的理解,国内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学者对认识它存在偏差。
三、图像学在中国美术作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一种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有其自身的属性决定的,图像学适用于美术作品研究最早是由图像志发展转变而来。中国图像学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先开始的是译介西方的图像学专著及论文,后来国内的艺术学者开始着手用西方的图像学研究中国美术。能够采用新方法并把它运用到美术作品的实际研究当中,对中国美术史研究来讲,具有积极意义。从整个研究情况来看,目前国内较多的学者围绕中国绘画作图像学研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推动了图像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进程,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一些隐性的问题也在凸显出来,这不得不引起学界对图像学方法研究和应用进行反思。
(一)对图像学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反思
图像学方法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这样才能够显示出它的价值所在。在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研究的过程中,运用适当的方法,才能够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西方艺术史家潘洛夫斯基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美术作品时就运用图像学的方法,其只就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作品进行图像学解读。国内学者曹意强先生在《图像与语言的转向——后形式主义、图像学与符号学》中认为:“新艺术史家对艺术史的理论假说、方法和目的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在这个批评范围内,阿尔珀斯和其他一些学者觉得,潘诺夫斯基的方法是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也最适合于文艺复兴艺术研究的方法。”[10]由此可见,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当初只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但后来的学者对他的理论进行拓展延伸,以至于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图像学体系。然对比西方绘画研究,中国绘画在使用图像学方法上要对其适用性保持慎重的态度,而不能够把所有的中国古代绘画用这种方法进行解读。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研究的不同在于作品形式和主题与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接受范围,主要是地理环境、民族、历史、风俗等原因。所以,美术作品的审美接受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但是有时这个范围并不受地缘的影响,也存在跨地域或者跨国度的审美现象,这是西方审美文化对其他民族审美文化的影响所致。
中国古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存在着地域的差异。从范围上来分,可以沿着中国七大水系①七大水系,珠江水系、长江水系、黄河水系、淮河水系、辽河水系、海河水系、松花江水系。进行划分,但每个水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艺术都具有个性特征和相互关联性。从考古发现的土陶到后来发现的绢本、纸本美术作品,都存在这样的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黄河水系沿岸的艺术文化,黄河上游、中游、下游都形成了不同的土陶文化艺术,在造型、纹饰等方面都存在地域上的差异。用图像学的方法来考证黄河沿岸不同区域的土陶艺术,就要把它们进行合理的分类,把它放置到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去理解。如果以偏概全去应用图像学的方法,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研究效果,进而会起反作用。在古代美术作品中,中国南北的绘画风格存在差异,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不妨从一个大的知识背景进行入手,可能会找到更多的实证,它对解读古代美术作品大有裨益。仅仅局限作品本身进行研究,可能会进入研究的误区,但前提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作品的实际范围。例如中央美术学院黄小峰先生在《丝线与家国理想:传宋人王居正〈纺车图〉的考察》研究中,认为历史上画家创作《纺车图》与“世掌丝纶”有一定的关联,寓意吉祥。在该文中,黄先生对王居正的《纺车图》进行了历史梳理,对相关《纺车图》的图像也做了详细的阐释,但从整体上看来,在阐释方面做得有点过度。行文中第二部分讲到“画错的纺车”,从图画场景表面上来看,纺车似乎是有问题。[11]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王居正的绘画风格为“精密有余,而气韵不足”[12],古语中“精密”最早见于王符《潜夫论》载:“非聪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13]此中“精密”可作“精致细密”解释。另宋代是理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绘画中注重理学精神,在宋代的一些美术作品能够达到高度的写实。然作为北宋画坛一名享有名气的人物画家,应该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不然与郭若虚记载王居正的绘画风格“精密”是不相符的,除非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现存的《纺车图》是王居正原作《纺车图》的一幅摹本,是临摹者画错的。从图像学进行考证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犯这样错误的也不是孤例,细心的研究者可以从中国古代绘画研究中找到较多类似的案例。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都适合使用图像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否则美术史将会变成图像史研究。那么,哪些作品适合图像学方法进行研究呢?这是学者要考虑的问题。现代的美术作品最多地要考虑视觉审美效应,但是作品如果只满足公众的视觉审美,那么作品的价值可能会被削弱。美术作品最为重要的是其思想性和能够反映时代的特征,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木刻宣传画,作品形式虽然简单,但是它们的主题相当突出,在救亡运动中就较好地发挥了它们的社会功能意义。艺术家在创作这些作品时,它并不是满足于审美的需要,而是带有宣传的目的,这类作品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其功能意义较为明显,如早期的艺术作品主要发现在一些遗址中,显然它们并不是先人要刻意留给我们的艺术品,所谓的艺术作品在当时它的使用价值要大于审美价值,然回过头去审视这些器物时,艺术家、美学家就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来看待,这是因为它们能够启发学者对先前历史的思考,透过它们也可以找到相关古代艺术审美的证据。后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艺术开始走向独立,以实现自身的美学价值。艺术家开始撰文来传达个人对美术的看法,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种说法:(1)基于实用的美术。例如早期的彩陶艺术。(2)宣传艺术为政治服务,主要通过标榜道德、炫耀威德等样式的作品出现,例如《历代帝王图》《职贡图》《步辇图》等。(3)宣传艺术为审美服务,例如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山水画应该要实现“畅神”的目的。以此来看,中国早期的艺术作品研究不能以偏概全地用图像学的方法进行解读,其他方面的文化因素也需要考量。
(二)不同题材作品中的图像学研究问题
在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由早期的器物美术到后来的绢本再到纸本绘画,它们所追求的目的不尽相同,但不管美术是倾向于实用或者审美,其都带有一定的社会目的性。要对这些艺术使用图像学方法进行研究有点不现实。下面将从宗教题材绘画、宫廷绘画、文人画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中国早期的宗教题材绘画主要集中在佛教艺术之中,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它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那么是否能够像潘洛夫斯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寓意画一样,采用图像学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题材的美术作品多采用象征、隐喻的形式法则来含蓄地表达宗教的内容。潘洛夫斯基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寓意画作品采用图像学的方法进行考证,是有针对性的题材和作品内容,这为潘洛夫斯基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中国的宗教题材的绘画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但是佛教是在皇帝支持下信奉的,所以它较之西方的基督教艺术显得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众多的皇帝都支持佛教的发展,每个时期大型的佛寺、石窟、雕塑修建是其重要的证据。在今天的佛教艺术研究中,研究者大部分从图像学和文化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而不是从美术的角度进行分析,其主要原因是佛教艺术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佛教文化属性,有它自身的文化倾向,用图像学的方法对佛教艺术进行探讨,或者比从美术的视角探讨更符合佛教艺术的特点。中国古代宗教题材的艺术受到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较大。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冈石窟中出现了皇帝的肖像、在敦煌莫高窟中出现了供养人的肖像。从中可以看出,宗教的题材艺术样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走向世俗化。
除了宗教题材的作品之外,宫廷绘画和文人画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可以使用图像学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产出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宫廷绘画和文人画研究过程中使用图像学方法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宫廷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背后是王权政治的支持,作品往往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目的,对其从图像学角度进行考证,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例如《韩熙载夜宴图》,它是五代时期顾闳中的一幅经典人物美术作品,但是其不是一幅普通的人物美术作品,主要原因是韩熙载不被皇帝李煜信任,为了监视韩熙载,叫画家偷偷潜入韩府,画家把所见所闻如实画下,显然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作品自身的意义。另外一类作品是文人画题材,该类作品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有些是约定成俗的题材形式,本身具有符号化的意义,如“四君子”“岁寒三友”这样的题材,在文人画中反复被摹写或创作。有些作品是表现作者率直的个性,例如宋代画家梁楷画的《泼墨仙人图》。有些作品是寄托文人关心世事的情怀,例如清代画家郑燮画竹,在《衙斋听竹图》上题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似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14]用图像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显然可以把一些内涵问题探讨清楚,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是,倘若不把上述的作品从图像学的方法考证,而是采用文化学的视角来探究,应该也是可行的。但有些学者仅仅抓住图像学方法不放,而冠以图像学研究方法的名号,其从实际上看来,它与图像学的关系并不大,因为这些绘画题材在画家落笔之前,公众对画家所选的题材已经从文化的视角给它们赋予了美好的文化含义。画家创作这类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
四、结 语
从上述来看,图像学已经成为一种研究古代美术作品的重要方法,是中国艺术学界公认的。但在有些问题上还是值得研究者去思考。西方的图像学方法引入到中国,其主要的目的是为寻找研究中国艺术的新突破,为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提供新视角,为深入研究某一种艺术风格提供帮助。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国内美术史图像学研究,其主要集中在宗教艺术领域和个别作品个案研究之中,然令研究者不得不警醒的是,当前国内的图像学研究方法适用范围混乱,有些学者看到美术作品就想用图像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毕竟中国的美术史不是图像史,简单地罗列、堆砌事实,肤浅地分析,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学术研究。其实不妨反过来看西方图像学发展的轨迹,它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迷茫期和过渡期,当图像学方法成熟、被学界认可时,研究者才开始对美术作品进行探索式的研究。当然,退一步来讲,图像学的方法完善,到回归理性,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研究者采用西方图像学方法对古代美术作品进行研究,处在一个活跃期,有些问题也在日益凸显。图像学方法被运用,是否正确,后人会对其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