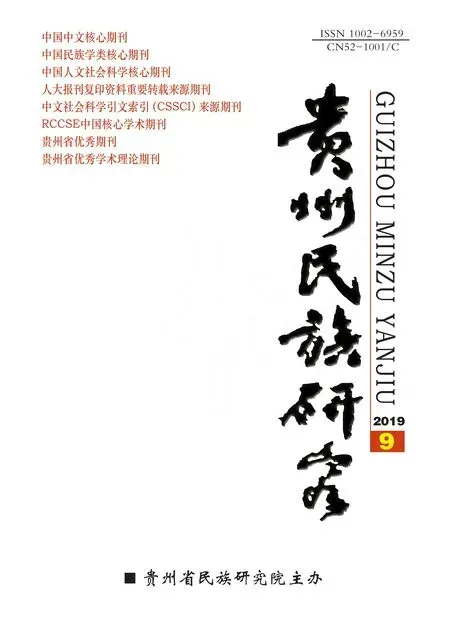民族地区传统习惯法的多样性及其长期保留的原因
杜 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习惯法产生于史前时代,是史前时代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维护社会秩序的法规。早期的成文法以习惯法为基础。习惯法与习惯不同,一般的生活习惯与公共秩序无关,而习惯法则具有法律的效力。习惯法一般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二是具有制裁和约束的功能,三是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赋予法律的效力。习惯法通常是先由氏族或部落议事会根据社会习惯约定而成。习惯法并无专门的司法机构,对违法者施法,通常是由氏族部落首领、巫师或村社头人主持。
制定法是由国家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公布的法律。早期的制定法在习惯法的基础上形成。一般认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魏国。公元前425年,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在战国七雄中率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李悝总结春秋以来各国的立法经验,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秦汉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前朝法律的基础上增加或删节,形成本朝法典。乾隆五年完成并颁行天下的《大清律例》以《大明律》为蓝本,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保留丰富多彩、类型多样的习惯法。习惯法为什么在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能够长期保留?为什么中央王朝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法典,但允许边疆民族地区的习惯法长期存在?本文简要分析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习惯法的多样性,探讨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并就习惯法长期在边疆民族地区保留的原因略作探讨,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习惯法的多样性与边疆治理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成文法典,但由于古代边疆民族地区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无法实行直接的统治,因而采用间接的“因俗而治”的方法。正是这种“因俗而治”的方式,使边疆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得以长期生存和发展。
在“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指引下,地方官员一般不强迫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采用中央政府的制定法,允许各民族采用本民族原有的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并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直至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民族地区仍然采用传统的习惯法来维持本民族的社会秩序。
中国边疆民族传统的习惯法十分丰富,种类多样,本文仅介绍刑事审判习惯法和村社头人推选习惯法。
(一)刑事审判习惯法
1.神判法
神判的方式有:捞油汤、发誓、热铁神判、动物神判、猎头、潜水、食物神判、抽签等。例如,捞油汤是将一锅油或水烧至沸点,然后投以鸡蛋或其他东西,让被告赤手伸入油锅内把鸡蛋捞起,如果手没有烫伤,则认为是无罪,如果手被烫伤,则认为是有罪[1]。
热铁神判是用烧红的金属(一般为铁质)放在手掌上或用脚踩。如西藏僜人是在被告的手上垫一层茅草,由巫师将烧红的铁块放于茅草上,未烧伤则为无罪,反之则有罪。有些民族不是用铁块,而是用石头。如四川凉山彝族由毕摩将烧红的石块分别放在原告、被告的手掌上,未被烙伤者为理直,烧伤者为理屈[1]。
2.赔偿法
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族地区直至上世纪50年代仍实行自古留传的习惯法。如偿命法规定,男人的命为全命,偿命价200匹马或1000只羊(或100峰骆驼);杀死女人偿半命。伤人致残,也须偿付命价。若伤瞎两只眼睛,偿全命价;伤瞎一只眼睛,偿半命价;伤残他人两只手,偿全命价;伤残一只手,偿半命价。但在某些场合杀人可不受罚,如在抓盗窃犯时,盗窃犯因反抗而被杀死,不偿命价。抓获盗窃犯可以不经过审判抽打20—60鞭,如在抽打60鞭内死去,也不偿还命价。如果“妻子杀害丈夫,必须处以死刑,不能用偿还命价的方式来拯救她,除非其亲属宽恕她。……如丈夫杀死妻子,则可交半个命价以免受刑罚。”[2]
哈萨克族的财产法规定:对盗窃者实行“九罚”,即罚九头牲畜,一般分为三种:一是“大九”,罚以骆驼为首的9头牲畜,即一峰骆驼,怀有马驹的母马两匹,3—4岁的马4匹;二是“中九”,罚以马为首的9头牲畜,即5岁马一匹,3岁马2匹,2岁牛2头,羊4只;三是“小九”,罚以牛为首的9头牲畜,即牛1头,2岁牛2头,羊3只,羊羔3 只[2]。
(二)村社头人推选习惯法
西南部分民族地区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实行村社头人推选的习惯法,主要有神选制、推选制和竞选制三种。
1.神选制
某些村寨的布朗族村社头人的产生方式,采用神选制。
村寨头人“召曼”是通过抽签的方式选出的,亦即由寨神“再曼”来决定的。其方法是凡村社成年男子,都有权利到佛寺参加抽签选举。届时,事先准备好九根竹签,其中有一根写着“当选召曼”的字样,将竹签投入铜罐中,由布占向佛祷告说:“现在我们全寨来抽签选召曼,你在高处看得清,谁管寨子最合适让谁当选。”祷告完毕,就由参加人依次摸签,谁摸到“当选召曼”签就当选。当选者手执竹签到大佛爷面前,大佛爷向他滴水、拴线,群众击象脚鼓、敲铓锣、跳舞表示祝贺[3]。
另有一些村寨在选举村寨头人时,推举出办事公道,善于辞令等条件具备的候选人,提交全寨,经其他各个氏族同意后,再筛选出3人为候选人,到佛寺去抽签。在3块竹片上分别写上候选人的名字,装入一个铜锅里,请不是与候选人同一氏族的人来,摇动铜锅,随便抽出一块竹片,名字是谁的,谁当选。选出的召曼如不称职,或当年庄稼不好,可以改选[3]。
2.推选制
基诺族大多数村寨都有两个长老——“卓巴”和“卓生”,他们由村寨内最古老的两个氏族中推选。其唯一的条件就是年长,而并非勇武多才。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仍采用推选制。卓巴、卓生基本上仍属于基诺族村寨的人民公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领导者[4]。
怒族在50年代前,还保留氏族组织和氏族制度,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头人,头人的产生是共同推选,条件是作战勇敢、能干、公道的人。推选不分贫富,老年、青年都可以。氏族头人没有一定的任期,一般是选出后到死为止,才再选别人。也有年老辞职的,要送一头牛给新头人。头人如作战不力,办事不公,可以撤换[5]。
独龙族大多数社会组织以村寨为单位。一个或两个(户数少地区相连)村寨有一个头人。头人都是推选的,一般是能说会道,办事公正的人。头人没有特殊的权利,不能父子继承[6。
3.竞选制
直至20世纪50年代,海南岛的黎族还保留斗牛竞选习俗。头人年迈后就向村寨公众宣布退位,宣布之后的5日内由新头人接替。寨民得悉头人退位后,便在寨子附近宽平的山坡上,开辟一块直径约500米的圆圈,用木椿围成六角形的圆圈。让青壮年男子入内把牛杀死。如果某人斗牛失败,另一个继上,依次轮番上阵,直至把牛杀死。杀死牛者当选,继任为头人。牛伤不死,不能继任,原来的头人还得留任。新头人产生的当天晚上,全村寨的人举行庆祝会,一连3天,燃火炬纵情歌唱,狂欢跳舞,开怀饮酒,直到第4日,新头人才就职[7]。
鄂伦春族射箭竞选佐领。黑龙江省呼玛县鄂伦春族,过去选拔佐领时,事先由“莫昆达”(氏族长)们举行联席会议商量确定,以“乌力楞”为单位派出候选人,在会场上设一靶场,在众人观看和监督下,于一定距离射箭五发,连中五箭者当选[3]。
拉祜族投玉米粒竞选头人。拉祜族村寨的头人称“卡些”。每个村寨皆有卡些,由群众选举产生。选举过程是,首先召集寨内户主会,提出三个正直、会说话、富裕、能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候选人,然后投玉米粒,以玉米粒多者当选。“卡些”任期无严格规定,办事公正、负责、为群众拥护者可当一辈子,否则,群众可随时罢免[8]。
瑶族酿酒和狩猎竞选头人。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瑶山的瑶族实行目老制,各寨头人称“目老”。候选人的条件是识字,有能力,能说会道,办事公正,为人正直,会祭鬼神。竞选时,当众酿制白酒于若干竹筒内,把候选人的名字随便写在任何一个竹筒上,规定两天或三天为期限,推举数名公正的人当众揭开竹筒,品尝甜白酒,酒味最醇的三人当选,一人任寨老,一人任寨主,一人任龙师,各司其职。另一种方法是,每户的家长都是候选人,事先大家同一日酿制甜白酒,到上一届寨老家中,互相品尝酒味,谁的酒味醇,谁当选[3]。
二、当代习惯法与制定法的整合
部分边疆民族地区直至改革开放后,仍采用习惯法与制定法相结合的方法处理刑事案件和婚姻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与国家法律往往发生冲突,但有些地方则采取尊重当事人选择的方式解决。例如,青海藏族在20世纪50年代前普遍流行偿命价的习俗。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实行国家制定法。但改革开放后,该地区要求用本民族的习惯法处理刑事犯罪。杀人或伤人以赔命价的方式处理。少则几千元,多则万余元。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上世纪80年代命价为5000元。它是按身体不同部位的价值折算,即四肢各1000元,头脑1000元。不少地区的藏族当发生人命案后,大多不愿意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审判,而愿意沿用习惯法赔偿命价私下了结。在他们看来,罪犯即使判死刑,也不是严重的处罚。人的灵魂是不灭的,生死是可以轮回的,人死了还可转生。所以他们并不希望罪犯被判死刑或重刑,这对受害者没有任何好处。即使罪犯被判了重刑,还是照样索取命价,不能少给分文。一般都以马、牛、羊或贵重物品折算。有的甚至还向公检法机关提出不要捕办的要求。对此,司法人员十分为难。如果完全以习惯法办事,显然与刑法基本原则不符。当赔了命价之后,被害人亲属感到泄了愤,消了恨,从此就前嫌尽释,重归于好。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两个县发生草原纠纷,酿成流血事件,当地牧民群众也提出用赔命价的办法解决,叫政府部门不要过问。为保障各族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应处理好国家法律与习惯法的关系,既要加强法制教育,又要根据现实灵活处理好各种刑事案件[9]。
婚姻家庭习惯法至今仍在不少民族中存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云南永宁纳西族摩梭人的阿注(阿肖)婚。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摩梭人仍盛行古老的男不娶、女不嫁的阿注(又作“阿肖”或“阿夏”,意为“朋友”或“情侣”)婚姻,其核心是走访婚制,因此,目前学术界多称之为“走访婚”,即建立性关系的男女双方,彼此称“阿注”,而不叫“夫妻”。男女结合自愿,解除自由,具有非契约性、非义务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其显著特点有六个:一是行族外婚制,禁近亲结婚。二是暮合晨离,各居母方。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的家庭,男不娶、女不嫁,晚上男方到女方家过夜,次日清晨回到自己家中,过着暮来晨往的婚姻生活。三是结合自愿,离异自由;四是年轻更换频繁,中年趋于稳定。五是感情为先,贫富为次;六是子女归女方,以母系为姓[10]。
摩梭人的阿注(阿夏)分三类:一是临时阿注,即同居不到一年的称为“临时阿注”。二是短期的,即同居一到三年的为“短期阿注”。三是长期的,同居三年以上的称“长期阿注”。大多数男女,在一段时间内,既有一个长期的或短期的阿注,同时又有一至数个(多至8个)临时的阿注。只有长期阿注而无临时阿注的人属于少数。女人的阿注比男人的多,通常多一倍以上。无论男女,在一生的婚姻生活中,一般都有阿注六七人至数10人,甚至百余人。尤其是年轻貌美的女子,阿注更多,多达100人以上的不少。少数女子的阿注多达200人。在摩梭人的观念中,以结交阿注多为荣,认为一生中阿注多的人才是有出息的人。阿注少的人大多是各方面的条件都较差的人。他们有一句俗话说:“乌鸦守死狗,没出息。”摩梭人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没有嫉妒,没有仇恨,若干男子同时与一个女人发生关系不会引起冲突,随时解除同居关系也不会引起对方不满[10]。
摩梭人的这种婚姻制度一直较为完整地保留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后提倡一夫一妻制度,但相当多的人仍实行阿注婚制。60年代,当时政府要求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效果不好。文化大革命前有位领导曾到泸沽湖畔督阵,限期改变走婚习俗,实行一夫一妻制,结果人走令废,男阿注依然夜入晨出,照“走”不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摩梭人被迫实行一夫一妻。改革开放以来,又恢复阿注婚,其原因一方面他们认为这种婚姻形式好,较自由,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独特的婚俗可以吸引外来游客,阿注婚成为摩梭人的重要文化资源[3]。
收继婚(转房制)是普遍存在习惯法。上世纪50年代前,普米族除了实行同辈收继婚习俗外,还有移配习俗,即使收继者与被收继者之间年龄相差很多。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说,清代维西县的巴苴,又名西番(即普米族),“……兄弟死,嫂及弟妇归于一人”。近人徐珂在《清稗类钞·婚姻》中记载,清代云南维西某户有四子皆已婚配。“不幸某年长子死,某年四子之妻又死。”以长媳配四子,年龄相差太大,于是采取叔嫂移配的办法,使长媳配二子,二媳配三子,三媳配四子,这样“一转移间,年皆相若”。此事被县官发现,认为有伤风化,欲治其罪。县吏告之,“此间习俗如是,愿无拂其意。”县官只好作罢。
以上一些案例,都是习惯法与制定法相互调和、整合的结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历代中原王朝“因俗而治”的治边方式为民族地区的习惯法长期保留提供了条件,也是使中国2000多年保持统一的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管理民族问题的制度是逐步一体化的过程。最早的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册封制度,其管理方式是完全自治(间接统治)。其次是形成于汉、盛于唐宋的羁縻制,其管理方式是半自治(半间接统治)。再次是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其管理方式也是属于半自治(半间接统治),最后是始于明末终于民国的改土归流。无论是间接统治还是半间接统治,主要采用“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因此,“因俗而治”是使民族地区习惯法得以长期保留的原因之一。
第二,习惯法与制定法的相互整合、相互补充是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有利于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整合性是中华主流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千年来,中华主流文化通过不断的整合,把各民族、各地区异质的、矛盾的元素或群体,以及本土与外来、旧与新的元素,通过改革、创新、协调、融汇等方式,整合成为一个相互适应、联系紧密、均衡和谐的有机整体。新旧文化的整合对于面积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在民国时代,在新疆各地实行郡县制,不少县的县长都由哈萨克族部落首领担任,因而不少人一身两职,既是某县的县长,又是某部落的部落首领。法文化也一样,在边疆地区的城镇,一般实行国家的制定法,在乡村多采用传统的习惯法。或者在某些方面采用制定法,在某些方面采用习惯法。总之两者相互整合,相辅相成,使制定法与习惯法不相冲突,和谐相处,使习惯法成为制定法的补充。由于历代王朝尊重边疆各民族的意愿,不强迫他们完全采用制定法,获得边疆民族的拥护和认同。
第三,中华主流文化包容性较强、排他性较弱,也是使部分民族地区长期保留习惯法的原因之一。一般情况下,虔诚的一神教信徒排他性较强,多神教信徒包容性较强。中国的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都属于多神教。儒家文化也具有宗教的性质,崇拜的圣人众多,也具有多神教的性质。另外,只信仰一种宗教的人往往排他性较强,信仰多种宗教的人往往包容性较强。西方人大多只信仰一种宗教,而中国人往往既信佛教,又信道教。正如罗素所说:“我们从犹太那里学到了不宽容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一种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样的正统的教义,规定没有人可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不相容。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并行不悖。”[11]中华文化包容性极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中华文化包容各种宗教,也包容不同的法文化,包容与制定法完全不同的习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