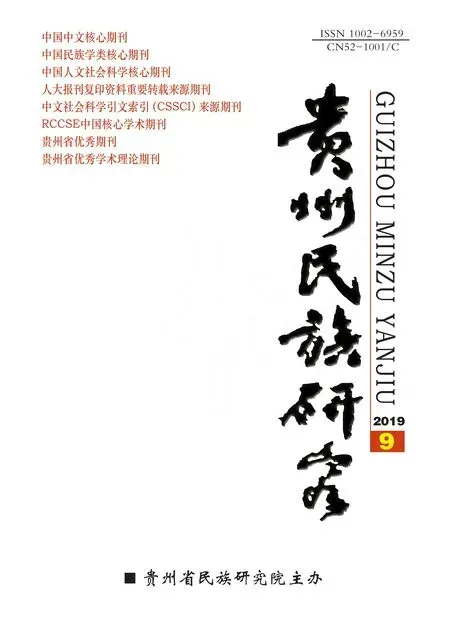历史、当下与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
平维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新表述,也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在宏观层面的重大部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被官方正式提出以来,其话语表述经历了“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塑于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进程中,确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实践中。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方式,是在晚清的王朝帝国衰败之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而在中国兴起的一种书写历史的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虽是在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基础上的延伸,但它更为注重超越狭隘民族性的共同体意识视角,以此限制族群民族主义的肆意泛滥。之前,笔者已有文章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做过论述,[1]此篇则着重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继承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民族虽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它并非是建构在想象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历史发展脉络”等要素的批判性继承。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延续性发展的内在禀赋,也是中华民族融汇发展的动力机制。赵汀阳认为,中国是一个“配天”的神性概念,它包含着家喻户晓的三层共识:中国文明强劲的连续性、中国文明光谱的兼容性、中国文明的非宗教性,这一内含天下的中国得以形成的动力结构则是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模式”[2]。中华民族正是形成于这一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吸附力的“旋涡模式”之中,它的形成轨迹截然不同于西方打破“神性”的宗教共同体之后实现“人性”的民族共同体的再造。
展开民族形成的历史画卷,就会发现民族从来不是一个最终结果,而是一个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中的动态过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对于族类群体的认知也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华夷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绝对分野,“有教则无族类之分”[3]是对古代族类关系认知的最好概括。中国古代的族类观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了种族、宗教、地域和国家的“文化族类观”,在天下体系的同心圆结构中,只要接受中华文明的礼俗文化和典章制度就能构成了文明体的一部分[4]。天下体系是一个秉持“无外”[5]原则的古代世界政治秩序构想,“兼容他者”是天下体系的应有之义,“协和万邦”是“无外”原则在具体施政方面的体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自在阶段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基于对“天下观”“大一统”“族类观”等文化理念的践行而实现的。郝时远先生在对古代“族”和族类思想进行详细系统地研究之后,提出“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蛮夷戎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动能”[6]。这种由边缘到中心的“涡旋”模式与由中心到边缘的“雪球”模式共同发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自在阶段的不断发展壮大。
(二)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批判性继承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使用频率较高且极为混乱的概念。涂尔干根据社会分工的高低程度把社会结构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社会结构类型[7]。帕森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将社会结构视为由不同基本功能、多层面的子系统组成的“总体社会系统”。柯林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将社会结构解释为“互动仪式链”[8]。在总结了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杜玉华提出社会结构是由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而每一个系统又都有特定的内在结构[9]。笔者基本赞同杜玉华教授的观点,并以此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及作为社会结构一部分的民族结构。
社会结构是生发于自然地理结构基础之上的各组成要素的有机结合,任何社会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基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这块“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10]的自然地理空间,内部地理生态要素多样一体、紧密相连,自成一个结构完备的体系。自然地理结构的完备性决定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这一超稳定结构体的形成除得益于地理结构的完备互补之外,也得益于中国传统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的互动整合,即社会上层的大一统官僚机构、社会中层的士族缙绅和社会下层的宗法家族组织之间大致实现了良性整合[11]。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国同构式”社会,国家是宗法家族在政治伦理上的延伸,天下则是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体[1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这一“家国同构式”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的迭代追求,故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中,我们依然可以听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传扬。
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形成于这种“家国同构式”的社会结构体中,批判性地继承了家国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包容开合的“家的模式”,以“大家庭”模式包容各个民族,以“一家亲”模式包容两岸同胞,以“根脉”模式包容华人华侨[13]。这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叙事模式也反映在当代的影视作品和歌曲传唱中,“五十六个民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都是这种模式在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中华民族以“家的模式”叙说着共同体的亲和性,“中华儿女”“两岸同胞”“兄弟民族”等语词都承载着中国语境中民族关系的紧密性。
(三)对中国传统历史脉络的批判性继承
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世界公认的事实,是何种力量或者机制推动促成了这一文明连续系统,苏秉琦先生用“满天星斗”说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该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世界文明的起源。但在追溯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发现唯有中华文明从古至今连续不绝,而可以与之媲美的譬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远期文明,抑或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近代帝国,都已经或消弭在历史长河中、或裂解为众多民族国家。尤其是近代由王朝国家(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大多数王朝帝国的一体化历史被改写,唯有中国依然坚持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脉络。
许倬云先生认为,中国一脉相承的“大一统”历史脉络的形成除得益于相当聚合的地形之外,市场性农业经济(包括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区间互赖和王朝政治中的文官体系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4]。葛兆光认为,中国的近代民族国家是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的,它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的意识,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15]。这种前后相继的“大一统”历史脉络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并非似“新清史”般简单武断地以“族群”视野来否认中国历史的完整性。
中国的历代中央王朝,无论是汉族皇帝登基大宝、南面称孤,还是少数民族领袖入主中原、建极绥猷,他们都以建立合乎礼制的“大一统”政权为政治任务。秦汉帝国首度实现中国历史的“一统”,这一时期形成的复杂而高效的政治体系、交通体系、经济体系和学术体系,为之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历史奠定了基础。因此,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将秦朝视为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16]。
隋唐帝国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再度一统,并将古代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推向了极致,无论是人口、版图、经济、文化都实现了对秦汉帝国时期的超越。明清帝国实现由“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华丽转身,尤其是在有清一代中国真正走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批判性地继承了“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使“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由古代发展趋势变为现实存在的事实。
二、立足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还有着充分的现代基础和制度保障。国家内部多民族共生所生成的形象与外部环境的持续互动,共同构成了多民族视角下的完整国家形象[17]。从现代性的角度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立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发展的现代文化基础”等多重现代基础。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政治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具有独立主权意义的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18]。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重新铸就了现代转型后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结束了中国自晚清以后“列强侵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分裂动荡局面。中华民族作为重塑中华的重要载体,也是建立中华现代国家、跻身世界政治舞台的基石。晚清之后的中国在“屈辱、迷茫、割据、危机、灾难”的境地中挣扎前行,也正是经历近代以来这些磨难的洗礼,中华民族彻底从历史上“自在”状态走向了“自觉”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华民族的现代主权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抵抗外侮、保家卫国”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之路。在这一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保障。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并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序言。这标志着国家从根本法的角度肯定了“中华民族”整体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城市民族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等法律和工作条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为处理民族事务、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法律保障。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体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在政治逻辑上是一致的、共通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一政治体系下进行的,它是嵌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部分,也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战后一片狼藉的经济基础上开始进行艰苦卓绝的经济恢复工作。罗荣渠先生在分析了新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在建国之后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这三个阶段是前后相承、一脉相继的发展史,期间虽经历重大挫折与困难,但在调整与改革之后,中国经济焕发出了盎然生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被彻底激发出来,创造了多项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1978-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3%;从改革开放之初3679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90.03万亿元;国内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20]。在经济方面取得的的卓越成就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增强了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实现了“人员、物资、科技、管理”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增强了边疆与内地各族群众在经济上的交流与往来,促进了国内民族关系在经济方面的整合。此外,国家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等重要举措,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增强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随着现代中国的交通运输业、通讯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地理空间的隔绝作用渐趋减弱,通过时间“拯救”空间越来越成为现实。以我国“高铁”发展为例,“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建设,日益将中国“织成”紧密相连的巨网,这些传输着中国经济资源的“大动脉”,也进一步强化了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交通基础。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方针,大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是认同产生的重要来源,文化的传承需要教育事业的支撑。
现代国民教育是实现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影响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因素。盖尔纳在研究民族主义与高层次文化社会的关系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大多人来说,个人的可雇用性、尊严、安全感和自尊取决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在其中受教育的文化范围,也就是他们在道德和职业方面赖以生存的范围。”[22]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价值的有效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国民教育的接受程度。现代国民教育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传授过程,也是“培养国民认同、提高政治能力、健全政治人格”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是文化兴国和族际关系整合的必由之路,也是培养“多元一体格局”下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必由之路。
随着现代科技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教学、电视教学、广播教学等各种形式的远程教学方式开始应用到教育领域中来。这些新形式的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教育推广的地理限制,即使远在边境地区的边民也能够享受到丰富的现代教育内容。“慕课”的开发和推广,更为我国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现在的慕课学习受众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线城市和发达城市,学习人数已超过7000万人次[23]。现代教育在传播知识内容的同时,也传播着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民族地区群众的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国各族群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领域的基础学术概念,它的内容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24]。这里探讨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结构,而是表现在民族方面的社会结构,或称民族结构。对于中国的民族结构,费孝通先生具有经典的论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分别从“中华民族的地理生态结构”“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5]这一论断提出之后,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研究中华民族结构的核心理论”和“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26]。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结构。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尊重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已经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多元一体运动而形成今日“多元融汇一体,一体包容多元”的民族格局,这是中国进行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宝贵历史财富,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结构支撑。
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既是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措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政策的改革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现代社会结构变得更具“开放性”和“流动性”。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做出了“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重要指示[27],为建立民族互嵌式社区旨在打破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实现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现代转型,建设一种相互嵌入的多民族社会结构指明了方向。这种互嵌的多民族社会结构有助于打破相对板块化的传统民族居住格局,推动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面向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面向未来层面,包含着三层建设性意义,即表现在民族层面的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展、表现在国家层面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现在国际层面的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三个层面。
(一)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总体部署,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主旋律[28]。民族与国家作为共同体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并非天然存在结构性张力,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以规范化的体制机制整合国家内部民族,通过族际政治整合制度化是可以有效地解决二者之间的张力[29]。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血脉相通,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既是对“民族与国家”的继承,也是对“民族与国家”的超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大团结,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时代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地抑制“两种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进而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民族团结事业既确定了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又奠定了我国民族政策体系的主要脉络,还塑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3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是对其关系的凝练表述。
当今国际局势日益复杂,一些反华势力利用民族分裂分子搅扰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大局,鼓动疆独、藏独、港独、台独不时兴风作浪。在这种形势下,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引导全国各族群众“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3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屈辱和磨难中渡过了黑暗的近代历史,辉煌的中华文明几度被殖民列强洗劫,中华民族也曾数次遭遇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团结奋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凝聚全国各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从深层意识层面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功能目标、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32]。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一人一族之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各族群众“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共同团结奋斗数十年甚或上百年方能完成的大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33]。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和伟大梦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凝聚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的力量,以“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主题,努力实现全国各族群众共同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充分动员各族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奋斗目标。
(三)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
近些年来,国际局势变得日益复杂,欧洲难民问题、民族民粹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欧美债务危机、国际霸权主义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外势力干涉我国内政的问题依旧严重,多种迹象表明,近期发生在香港的暴力犯罪事件就有着西方反华势力的干涉与策动。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我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应有之义。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在转型期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杨洁勉研究员认为,美国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使大国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更是引起了一系列的国际贸易摩擦[34]。种种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应对全球事务时开始表现得力不从心,其对国际社会的统治力也逐步减弱,近代以来形成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尤其是伴随着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向深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中国唯有不断增强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努力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以更为“开放、包容、自信”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应对云谲波诡、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的底气。在内在逻辑层面,“表现在民族层面的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表现在国家层面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现在国际层面的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这三者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只有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够从容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思想的主旋律,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在宏观层面的重大部署。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塑于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进程中,确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着“继承历史、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的三层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立体饱满”的学术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一项“系统完整”的建设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应当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共同体的锻造、政治-法律共同体的建构、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塑、精神-文化共同体的模铸、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构”[35]等多重维度进行考量。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我国更为从容镇定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