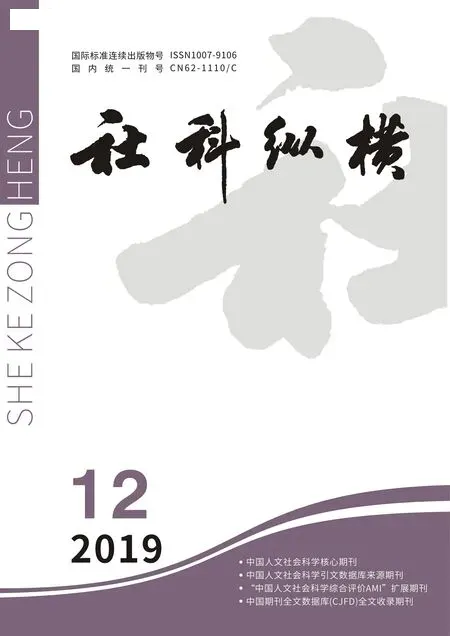晋宋之际文臣傅隆述略
安朝辉
(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陕西 安康 725000)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地傅氏家族虽然不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家族享有盛名,还是涌现了傅嘏、傅玄、傅咸、傅袛、傅亮等重要人物,在政治、军事、学术、文学等方面有所建树。傅隆(公元369—公元451)是晋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中成员之一,《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谓“北地灵州人”[1](P1550)(一说北地泥阳人),高祖即傅咸,曾祖即傅晞,族弟又为刘宋重臣傅亮。傅隆生活于晋宋之际,其生平事迹主要载于《宋书》、《南史》等,此人以能吏、学者闻名于世,而当代学术界少有关注①。兹探讨傅隆为人特征、政治业绩及学术成果,希望能够拓展北地傅氏家族人物研究,祈请方家指正。
一、笃实沉静,为人谨重谦恭
北地傅氏家族汉代至西晋生活于北方,西晋永嘉时期天下板荡,部分傅氏族人为了避乱迁徙至南方,《晋书·傅咸传》(卷四十七)记载傅隆曾祖傅晞,“亦有才思,为(会稽郡)上虞令,甚有政绩。”[2](P1330)东晋王朝主弱臣强,尤其是后期政治局势多变,司马道子专权、孙恩与卢循起义、桓玄篡位,直至刘裕崛起而代晋,天下动荡、分裂,傅隆正是处于这一时期。《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云:“父祖早亡。隆少孤,又无近属,单贫有学行,不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参军……复为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及东归,便有终焉之志。”[1](P1550)。这则材料透露出以下几点信息。其一,从家庭情况来看,傅隆因父祖早亡而孤苦不幸,“无近属”意谓本族势单力薄,从小缺乏可以依靠之人,这种家庭环境有助于形成坚强、刚毅、独立性强等性格。第二,从其为人特征来看,傅隆虽然孤贫而有才学,有品行,恬静而不喜欢交游。“终焉之志”表明,在晋末乱世中,其性情淡泊,不慕功名富贵,倾向于退隐。第三,从早年仕宦来看,傅隆不同于东晋众多少年得志者,“年四十”说明出仕较晚,历经生活的磨难,其心智较为成熟,待人处事不乏沉稳、谨慎。
我们将傅隆与其族弟傅亮略作比较,以辨析二人行事异同。《南史·傅隆传》(卷十五)云:“(隆)累迁尚书左丞。以族弟亮为仆射,缌服不得相临,徙太子率更令。”[3](P444)傅隆与傅亮为关系较远的族亲,不过按照朝廷规定,仍然不宜在同一部门任职,故傅隆改为“太子率更令”。两人之间也有所来往,如《宋书·蔡廓传》(卷五十七)所载“征为吏部尚书,(蔡)廓因北地傅隆问(傅)亮”[1](P1572),可惜这样的资料很少。傅亮年轻时已经步入仕宦之途,曹道衡、沈玉成认为傅亮初仕“年已二十四五”[4](P253)。晋宋之际傅亮辅佐高祖刘裕,撰写策加“九锡”文、草拟晋帝禅位诏书,在晋宋禅代中立下大功,为开国元勋之一。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陶彭泽集题词》论道“傅亮攘袂劝进(刘裕),三尺童子咸羞称之”[5](P160),讥刺傅亮身为晋臣而丧失节操的行为。刘宋王朝建立后,傅亮又参与废黜少帝刘义符、拥立文帝刘义隆活动,担任中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封为建城县公、始兴郡公,后来由于功高震主、擅自杀戮而被诛杀,家属流放边远之地。《南史·傅亮传》(卷十五)云:“亮之方贵,兄(傅)迪每深诫焉,而不能从”[3](P443)傅迪常劝诫要知晓政治进退,而傅亮并未听从其兄之言,可见其功名心强,急躁冒进而不知退隐。傅隆在晋宋禅代中所作所为虽然未见史料记载,其政治态度当与族弟傅亮相似,拥护禅代,并与刘宋政权积极合作。宋文帝元嘉时期,傅隆得以自我保全进而受到提拔、重用,高寿而终,不仅仅在于他和傅亮并非近亲属而少受牵连,而且由于他沉静内敛,处事谨重、稳妥,终未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记载,宋文帝就所撰《礼论》征询傅隆的意见,傅氏上表云“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又云“而复猥充博采之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默,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1](P1551-1552)。傅隆上表中用语固然有套式化特征,表达臣子对皇帝的敬畏、钦佩、感恩之意,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其人持重、谦和、老成的一面,平日与同僚、朋友相处也当如此。至于傅隆所上呈“五十二事”现已不详,大致数量多而内容详实、中肯,仍然体现其严谨求实的态度与作风。
二、为官称职,博得天下声名
晋宋之际,傅隆中年出仕,曾任给事中、尚书左丞、县令、司徒右长史、御史中丞、太守、太常等职,虽然不像族弟傅亮那样官位显赫、封为公爵,而其仕途尚算顺利。傅隆德才兼备,不论是任朝官或地方官,基本能够履行职责,也获得美誉。如《南史·傅隆传》(卷十五)云“有能名”[3](P444),唐代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二)亦谓“傅隆长于为政”[6](P436),清代乾隆年间所修《大清一统志》(卷六十)还将傅隆列入“名宦”之类[7]。以下略论傅隆为官政绩,以凸显其在晋宋时期的政治才能。
傅隆曾经担任“御史中丞”,此为御史台长官,负责纠察百官,又参治刑狱,位高权重,我们重点论析傅氏“御史中丞”履职情况。傅隆的先祖傅玄、傅咸在西晋时期就任“御史中丞”一职,颇有声名,尤其是高祖傅咸,《晋书·傅咸传》(卷四十七)称其“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2](P1323),傅咸《御史中丞箴》写道“鹰扬虎视,肃清违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赫赫有国,可无忠贞,忧责有在,绳必以直”[8](P1761),强调“御史中丞”的职责所在,“肃清违慢”“绳必以直”既用以自勉,也告诫他人。傅玄、傅咸二祖立身行事当对傅隆有所启发、激励,这体现了北地傅氏家风对后人的影响。《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记载元嘉初,“(隆)迁御史中丞,当官而行,甚得司直之体。”[1](P1550),傅隆任职尽心尽责,“甚得司直之体”是给予充分肯定。《宋书·王昙首传》(卷六十三)云:“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尝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虎幡,银字棨。’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上特无所问,更立科条。”[1](P1679)元嘉年间皇帝车驾深夜出宫城之门,守门官吏因为缺少“白虎幡”“银字棨”符信而不肯开门,有司奏免御史中丞傅隆等。其实主管长官傅隆是遵照旧制而行,本身并无过错,当然元嘉初也有无符信而开门情形,最终皇帝并未问罪,而是重新确立“科条”,完备宫廷门阙制度。由此可知傅隆根据制度而行事,并非一味遵从皇帝旨意,其做事能够秉承原则。又据《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记载,“(元嘉五年)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1](P1774)。宋文帝元嘉五年,御史中丞傅隆履行个人职责,奏劾名士谢灵运,谢氏因为游宴无度、有违朝廷礼制而被罢官,影响了本人的生活轨迹。《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将此事暂系于同年“十二月”[9](P3803-3804),实际上具体月份难以考订。晋宋时期,供职“御史中丞”的某些人并不称职,受到社会非议乃至被罢官。《宋书·蔡廓传》(卷五十七)云:“世子左卫率谢灵运辄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纠免官。”[1](P1570)晋末刘裕当政时期,谢灵运多次“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却因为未能纠察而被免官,可谓前车之鉴。又《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云:“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1](P1902)刘宋时著名文人颜延之担任御史中丞却“无所举奏”,显然有失职之嫌,受到舆论指责。相比较而言,傅隆刚正忠贞,恪尽职守,政绩卓著,有益于当朝吏治。又《宋书·蔡廓传》(卷五十七)记载傅隆的好友蔡廓,“高祖以廓刚直,不容邪枉,补御史中丞。多所纠奏,百僚震肃”[1](P1570)。蔡廓任职正直、忠贞,勇于惩治邪恶,受到时人好评。傅、蔡二人都曾任“御史中丞”,可谓志同道合,同气相应,相互影响,对整肃官场风气不无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傅隆宦海生涯中也偶有犯错,贻误个人的政治前程。《宋书·傅隆传》载道:“(元嘉时期)征拜左民尚书,坐正直受节假,对人未至,委出,白衣领职。”[1](P1551)傅隆因为渎职而罢官,《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一)将此事归于“台省部”中“谴责”一类[10](P5438-5439)。平心而论,“白衣领职”原因颇为复杂,这样瑕疵无损于傅隆的良好形象,傅隆仕宦历程中,应该说政绩是主要的。
三、勤勉好学,精通“三礼”
东晋南朝社会动乱变幻,玄学、佛学、道教兴盛,传统经学则呈现衰微之势,不过就晋宋之际而言,当权者多注意兴儒重学,为强化政权而服务。东晋帝王多有崇儒的倾向,如《晋书·孝武帝纪》记载康宁三年“帝讲《孝经》”“帝释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颜回配”[2](P227),孝武帝注重解析儒家经典、祭祀儒家先贤。刘宋王朝建立,宋武帝、宋文帝等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大力推崇儒学、兴办学校、征辟儒士,如宋武帝策试州郡秀才与孝廉、下诏加强儒学教育,宋文帝则是涉猎经史、崇儒尚文,据《南史·宋本纪》记载,“(元嘉十五年)立儒学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3](P45)晋宋之际帝王倡导儒学,出身低微的士人除了从军建功外,重儒笃学更是立身扬名的重要途径。傅隆受到这种环境的浸染,从小刻苦好学,研读儒家经典,勤勉不倦。《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谓傅隆“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1](P1552),年老归家后仍然兴致不减,正如《南齐书·虞玩之传》(卷三十四)中玩之上表所云:“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盖以世属休明,服道修身故耳。”[11](P608)虞玩之对此加以称赞,并与元嘉盛世风气相联系,其实这更取决于傅隆勤于修身、好学不倦的特征。《南史·傅隆传》云:“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3](P444)东晋南朝“三礼”成为显学,傅隆特别推崇,《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所引其论《礼论》云,“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1](P1551),他还撰写礼学有关专著。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载:“宋光禄大夫傅隆议二卷。《祭法》五卷,亡。”[12](P923)又《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还记载:“傅隆《礼仪》一卷。”[13](P1432)可惜傅隆的著作在隋唐时期已经散佚严重,而当今杳然无存。由此可见,傅隆笃志好学,长于著述,彰显学者的风范。
傅隆精通礼学,还将其运用于从政实践,卓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敢于对前人礼学方面的成说提出质疑,这种学术方面大胆批判的精神值得肯定。刘宋元嘉年间,傅隆任太常,论“诸王舞伎”事宜,驳诘西晋杜预有关说法。《宋书·乐志》(卷十九)引用傅隆之语云:“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1](P547)西晋杜预号称“左传癖”,其《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释本,在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堪称经典著作之一。傅隆批评杜预注《左传》中诸侯“佾舞”人数之说,认为杜预所云“三十六人”有误,并根据服虔注《传》说法,引经据典,提议应该按照古例人数的要求配给刘宋朝廷诸王“舞伎”,以四十八人为准,而非“三十六人”。傅隆熟知经典,能够认真辨析旧说,他的见解不无道理。苏轼《东坡志林》(卷七)、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明代卓尔康《春秋辩义》(卷二)等引用傅隆之论,可见后人重视傅隆这种说法。二是基于“礼”“法”兼顾的原则剖析、处理当时重大的法律案件,活用有关礼学理论,以适应复杂社会现实的需要。《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记载元嘉年间傅隆任司徒左长史时所遇疑难案件,会稽剡县民黄初妻子赵氏殴打儿媳王氏致死,赵氏有儿子黄载而黄载又有儿子黄称,后遇到朝廷大赦,依据法令迁徙赵氏二千里之外,在如何处理赵氏母子、祖孙之间关系方面出现争议,关于此案裁决也有不同说法。傅隆议道:“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沉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理固然也。”[1](P1550-1551)傅氏将朝廷律令与礼法、人情结合起来考虑,法根据理、情因素予以调节,凶手与死者儿子毕竟为祖孙关系,二者之间仇恨不能比照常人处理,故认为若果赵氏适用流刑,赵氏儿子乃至孙子都可以跟随,实际暗示没有必要流徙赵氏。又《宋书·临川武烈王道规传附刘义庆传》(卷五十一)所载,临川王刘义庆也议论这桩奇案,认为“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1](P1476),其看法与傅隆相似。宋代郑克《折狱龟鉴》(卷四)收载了傅隆所议这个案例,当代学者霍存福论道:“傅隆对该案所涉及的‘情理’‘事理’‘通情’等核心概念及‘孙无仇祖之义’‘孙祖之义不得绝’等原理讲得非常透彻。”[14](P107)霍存福赞同傅隆之言,实际为后世这类特殊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的范例。
傅隆儒学方面的成就得到时人称许,在晋宋之际经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宋书·傅隆传》(卷五十五)“史论”云:“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1](P1553)晋宋之际裴松之著有《三国志注》、《宋元嘉起居注》、《集注丧服经传》等,何承天有《礼论》、《分明士礼》、《孝经注》等,雷次宗则有《毛诗义》、《略注丧服经传》等,《宋书》“史臣”将傅隆与上述三位硕儒相提并论,应该说相当看重傅隆的学术成就。傅隆事迹对后人颇有影响。清代傅山《傅史》评傅隆:“盖元嘉中通儒。”[15](P222)甚至清代李汝珍小说《镜花缘》(第五十二回)中引用傅隆元嘉时上表论《礼论》之语,并云“至注礼各家……宋有光禄大夫傅隆”[16](P258),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异邦谈论傅隆的礼学,从另一面反映明清之人对傅隆的接受。
四、结语
傅隆是晋宋时期北地傅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集能吏、学者于一身,在当时颇有知名度,其人特征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归纳。第一,受到特殊社会环境、家庭出身等多种因素影响,为人谨重、沉静、谦恭,不喜交游,在晋宋之际纷乱时世中得以保全自我而善终,这与其族弟傅亮位高权重、不知隐退而被诛有所不同。第二,为官刚直不阿、尽职尽责,担任朝官、地方官颇为称职,尤以任职“御史中丞”为突出,展示其理政方面的能力。第三,一生笃志儒学,勤勉博学,以学者著称,尤其精通“三礼”,重视著述事业,重视经世致用,收效良好。总之,傅隆堪称晋宋之际一位名臣,其在东晋南朝经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可惜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其少有关注。傅隆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北地傅氏家族人物探究,也可以拓宽晋宋之际文化名人研究视域,因而具有其学术价值。
注释:
①就著作而言,《中华历史大辞典》(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德弟著《先秦至隋唐五代藏书家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罗康泰著《甘肃人物辞典》(甘肃民族出版社,2006年)等提及傅隆。霍昇平《灵州傅氏试探》(《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柳春新《论汉晋之际的北地傅氏家族》(《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彭浩晟等《论南朝司法之伦理性》(《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论文论及傅隆。当今学界对傅隆的探析显得简略、零散,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