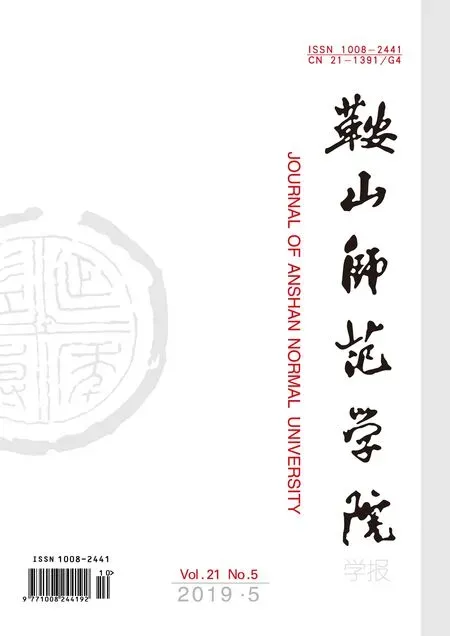明清朝鲜使团“下马宴”和“上马宴”考释
张士尊
(鞍山师范学院 国学研究中心,辽宁 鞍山 114007)
明清时期,朝鲜使团入境以后,根据当时的外交礼仪,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给予“筵宴”招待,其中有些是随意性的,如皇帝赐宴;有些则是规定性的,比如“下马宴”和“上马宴”。就后者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和惯例,从明朝到清朝,实行了五百多年,其自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本文参考有关的中国文献和朝鲜汉文文献,对“下马宴”和“上马宴”做些梳理,以有助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明朝时期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所谓“下马宴”,是指朝廷专为迎接朝鲜使团所举行的宴会,有接风洗尘的意思。相对于此,“上马宴”是指朝廷专为送别朝鲜使团所举行的宴会,有一路顺风的寓意。但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无论“下马宴”还是“上马宴”,都是朝鲜人的说法,在明清会典中并没有相同的词汇,而且在朝鲜人所说的“下马宴”和“上马宴”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据裴三益《朝天录》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作者作为陈谢使前往北京,渡鸭绿江之前,义州地方官在义州官署为其举行“下马宴”,几天后又在鸭绿江边点军亭为其举行“上马宴”[1]。这里所提到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就是广义的“下马宴”和“上马宴”,而我们所要研究的则是狭义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明朝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始于何时,很难确定,其原因主要在于嘉靖之前存世的朝鲜汉文使行录较少,但我们仍然能从有限的记载中发现某些迹象,如权近的《奉使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权近奉命出使金陵,在金陵曾有《奉天殿朝见后赐宴于会同馆》诗:“□□金门辟,千官玉佩齐。轩墀仙仗集,宫殿瑞云低。帝泽论肌洽,伶才夺眼迷。赐宴那避酒,兀兀醉如泥。”另有《初八日进谢赐宴仍辞》诗:“晓随群□入金门,咫尺天威望至尊。风送炉烟香满殿,云移仙仗日临轩。公堂赐宴恩难谢,禁陛辞归语更温[2]。”诗中有几点与后来“下马宴”和“上马宴”相合:一是赐宴的地点在会同馆;二是有乐舞表演;三是公堂赐宴模式化,由此看来,这应是较早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据《大明会典》记载:明朝初年,凡使团到京,皇帝往往在宫中赐宴,洪武二年(1369)改为使团到宫中朝见后,回到会同馆参宴,由礼部主持。永乐以后,凡外国朝贡,钦命宦官与文武大臣或学士等待宴,朝鲜使臣则明文规定由礼部官员待宴[3]。《大明会典》还记载:凡有藩国进贡,按例钦赐筵宴一二次,朝鲜筵宴二次。每次筵宴,礼部要先确定筵宴日期,奏请大臣一员待宴,然后命光禄寺备办酒席,会同馆准备场地,教坊司提供乐舞,鸿胪寺安排通事及鸣赞供事,仪制司为每位赴宴者准备一枝宴花。如果使臣数多,分为两日进行。如果遇到禁屠斋戒等事,推移三四日举行[3]。
很明显,会同馆赐宴之事始于洪武二年(1369),赐宴时各司的职责和分工也应同时形成,但为朝鲜使团二次设宴,即“下马宴”和“上马宴”的规定,可能要晚于这个时间,因为皇帝赐宴对使臣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如果有“下马宴”和“上马宴”之说,肯定会在《朝天录》中有所反映。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月,明朝“更定藩国朝贡仪”[4],对原来的某些规定进行调整,但这次也没有确定“下马宴”和“上马宴”,因为朝鲜使臣李詹建文年间曾两次前往南京,往返路上,他留下很多诗作,包括南京城内的一些活动,但却没有提到赐宴之事,如果有两次赐宴,必定会在其诗作中有所反映[5]。到永乐时期,特别是迁都北京以后,“朝鲜益近”,国王李芳远“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之以加礼,他国莫敢望也[4]。”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下马宴”和“上马宴”制度形成了。
嘉靖以后,《朝天录》对“下马宴”和“上马宴”记载增多,对这些材料略加整理,有利于我们对“下马宴”和“上马宴”整个发展过程的清晰了解。
嘉靖十二年(1533),皇太子诞生,朝鲜政府派遣进贺使团前往北京,苏世让在《阳谷赴京日记》中记载了“下马宴”和“上马宴”的情况:嘉靖十三年(1534)闰二月十三,明朝政府在玉河馆设“下马宴”,押宴官员为太监黄锦和礼部尚书夏言。“押宴太监黄锦,礼部尚书夏言,乘轿入来,即于阶前拱立迎入,精膳司员外郎毛□亦来。序班等引立阶上,行向阙五拜。又进尚书前,行再拜礼后,各就位设宴。备呈杂戏,行七爵,乃罢。又行向阙拜而退。太监先出,尚书次出。”十余天后的闰二月二十六,举行“上马宴”:“赴上马宴于会同馆,夏尚书及太监麦福承命押宴,仪如下马宴[6]。”
嘉靖十六年(1537),朝鲜进贺圣节使到达北京,九月初六,明朝政府为其举行“下马宴”。据丁焕《朝天录》记载,本次“下马宴”由宦官黄锦和礼部尚书严嵩押宴。“是日,光禄寺设行下马宴,臣等与进贺圣节使书状等早诣于会同馆,礼部尚书严嵩先入,余等祗迎于阶下,少顷奉命太监黄锦继入,又出祗迎,即于阶上随尚书之后向阙一拜三叩头。又入大厅,就太监及尚书前再拜讫,各就东西宴桌。优人舆乐呈杂戏于堂,酒行七酌而罢。臣等随尚书复行向阙礼,又就太监尚书前再拜,退阶下,祗送太监出门。”九月二十,赐“上马宴”于会同馆,这次由太监赵政押宴,没有提到礼部官员[7]。
嘉靖十八年(1539),朝鲜奏请使到达北京。十一月初六,明朝政府在会同馆为其举行“下马宴”。据权拨《朝天录》记载:使团一行“凌晨诣阙下,以下马宴往会同馆,千秋使以上马宴亦往,尚书先入,俄尔太监麦福亦入。尚书率臣等西向行望阙礼后与太监南面而立,率下人行再拜礼讫,分东西而坐。众乐并作,杂戏具呈,行宴礼,良久而毕。太监与尚书入馆内少歇,尚书还出,率使以下又行望阙礼,如初仪,与太监南向而立,使以下拜辞,退立庭中。太监先出,尚书继出。”同月二十一,在会同馆举行“上马宴”,仍由太监黄锦、礼部尚书严嵩押宴[8]。
万历二年(1574),朝鲜贺圣节使团前往北京,同年八月十六,明朝政府在会同馆为其举行“下马宴”。据赵宪《朝天日记》记载:这次押宴的官员是礼部尚书万士和,“初坐东廊,提督送茶,俄有光禄少卿来视,设馔,提督迎揖于堂檐下,序班等祗迎送于月台下,将出,郎中等相列立于而揖送,至乘马处(大门内庭中),又三揖以让请入。郎中还至檐下,少卿乃乘马,又举鞭揖出。已而,尚书至,余等以南为首,祗迎于庭中,郎中迎于阶上,尚书下轿,于序班迎处,微揖于郎中揖处而入。又出于庭上,与余等西向一拜三叩头。又一揖,尚书就座于堂中之椅,余等入楹内,再拜就座。(使坐东,书质在西,军官从事坐阶上,奴辈坐下),桌前已设肴馔,俎用生肉,器数甚多而侈,杂戏巧列于前,尚书前有光禄官四人分立,酒至则奉置于前而揖,尚书引手微揖,献馔亦如之。鼓人进于尚书前,三鼓讫,尚书乃执爵。又三鼓,乃举箸。迭奏之戏,不是小儿迷藏之态,则都是夷汉交兵之状,全不是干羽之舞也。九爵毕献,光禄等官齐揖而出,下人各以其器收馔,还于家讫。尚书与余等又下庭中,向阙一拜三叩头,又再拜于尚书而退。尚书之出,祗送如迎仪,但以北为上,郎中共至乘轿处,尚书让而乘,则郎中揖,尚书微揖。”八月二十六,在会同馆举行“上马宴”,押宴官员仍然是礼部尚书万士和。据赵宪《朝天日记》记载:“他外国则只有下马一宴,而我国使臣则别设两宴以慰之,其见宠厚如此。是日尚书自朝参直来,故早到会同。一行人才得入门,而立于祗迎位。拜礼爵数,一如初宴之仪,但舞工之戏,比前日尤有怪者。上古待外宾之礼,想止于舞干,而今焉盛备之时,尚有不经之事,意者天下无道之后,为天子者无德以服远,设为傀儡眩幻之术,枪刀交刺之状,以惑远人,而为远人者,亦有好而瞪视之者,故以皇朝之圣制,亦因而不改,岂非厥典而也哉,只知以此为娱[9]。”
关于此次“下马宴”和“上马宴”,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有类似的记载:“是日行下马宴:朝诣会同馆,尚书未至,余等坐于东廊,馆中门匾曰柔远,尚书高仪所书。大厅有二额,万国来同,声教寺讫。光禄寺少卿来点阅桌馔而去,尚书至,余等排班祗迎,尚书入于厅后,少焉,改穿新服而出,阶之西设设龙亭一座,尚书率余等一拜三叩头,鸿胪寺鸣赞礼,已而,尚书入,面南而立,使先行两拜作揖,余与质正亦入之。尚书皆答揖。尚书坐,使则坐于东,余与质正则坐于西,上通事以下行礼后列坐于东偏。乐作,酒进,呈杂戏,凡七爵而罢。下人入撤,尚书又率余等一拜三叩头于龙亭前,盖谢恩也[10]。”
万历三十二年(1604),有朝鲜使臣对“下马宴”和“上马宴”做过总结:“宴有上下马宴。下马宴于到馆六七日内行,上马宴于临行五六日间行,俱礼部题奉钦依,移文光禄寺,由礼部尚书押宴,行于会同馆。宴之日,尚书出入时,使臣以下俱迎送。先于厅上设阙牌,尚书率行员役行五拜三叩头礼讫,撤阙牌。尚书坐堂,使行以下行两拜作揖礼讫。尚书坐北壁,使臣东壁,书状西壁,一行员役人俱于中□□。”“自壬辰以后,使臣亦本国有难,领宴未安,呈文礼部,具题免宴,移文光禄寺典簿厅,准折银两[11]。”
后金占领辽东以后,朝鲜使团过海前往北京,“下马宴”和“上马宴”照常举行。天启四年(1624),朝鲜奏闻使团到达北京,明朝政府为其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据李民宬《癸亥朝天录》记载:天启四年(1624)二月十一日领“下马宴”,“朝以吉服,诣会同馆。尚书林尧俞押宴,亦吉服入,就阙牌前西向立,两使后余,余后译官等,俱五拜三叩头。尚书就堂中南向立,使臣就前,尚书命免拜,只一揖,各就座。尚书北,两使东,余西,译官等东。阶上进膳进花,呈舞乐耍戏,尚书命阅视馔品,极示优厚,七勺而罢。”二月二十九,领“上马宴”于会同馆,仍然由礼部尚书押宴,“令外郎使之满酌,勺数如前[12]。”
天启三年(1623)朝鲜冬至、圣节兼谢恩使团到达北京,次年正月二十三,明朝政府为之举行“下马宴”,据赵辑《燕行录》记载:“往会同馆参下马宴,以红袍参宴事,禀于提督,则黑衣为之云。通官等图之于黄堂吏,禀于尚书,则以红袍入参云。尚书入门时,郎中等祗迎于中阶东边,吾等祗迎于庭下东边,尚书上堂,西壁下围龙障处行礼,尚书前行,吾在后行,皆布红毯,员役又在后行,行一拜三叩头礼。尚书主壁,吾一行行见堂礼,跪四拜,尚书答拜。尚书主壁坐椅子,尚书插两边劝花,吾插左边劝花,行九酌七味。戏子等着假面入舞,行杂戏幻术,大近于优倡,不欲观。诸床桌饮食,极其丰侈,羊鸭鹅则全体,猪牛肉则割脔。油果五器,实果三器,饼面五器,皆插花。尚书每杯揖而劝之,极其忠厚,天朝之柔远人至矣。罢后,还立西障下,行一拜三叩头如初。尚书还,就北堂,吾欲行辞礼,则尚书答以免拜[13]。”而“上马宴”则因为使臣赵辑等以“虏氛未消,时怀为国至忧,万里遥瞻,再切危邦之惧,恩惕交集,食觉哽咽”为由,题请免宴[13]。
崇祯九年(1636),金育等出使明朝,第二年返回。据其《潜谷朝天日录》记载,由于清朝进攻朝鲜,并迫使其投降,国难之中,没法举行上下马宴,故折银56两免宴。这是朝鲜使团最后一次出使明朝[14]。
作为礼仪制度而言,明代不同时期举行的“下马宴”和“上马宴”有如下几点是共通的:第一,前来押宴的均为礼部尚书,即主管明朝外交活动的最高长官,而且万历之前,还有皇帝身边的大宦官参与押宴(宦官押宴可能始于明初,成化年间就有大太监汪直押宴的记载[15]),可见明朝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第二,仪式中都要拜阙,有的是龙亭,有的是牌位,明确表示宴会为皇帝御赐的特点。第三,因为特殊原因,可以“免宴”,但“免宴”的银两可以带走,这就是所谓的“折宴”。第四,从食品到歌舞,都安排得非常周到,体现主人积极维护双方关系的良苦用心。总的来说,无论是“下马宴”,还是“上马宴”,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儒学的礼制精神。
有明一代,朝鲜使团进入中国,除了在北京会同馆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招待之外,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回还之时,经过重要的行政中心,要“茶饭管待”,允许总兵、三司、府卫正官二三员陪同。比如宣德三年(1428),朝鲜使团回国,路经永平府,由永平府加以宴请[3]。而经过辽东的时候,宴请的机会就更多。如: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进贺使团路经辽阳,由辽东都司掌印郭继宗,三大人鲁倬出面,宴请朝鲜使臣[16]。再如:万历十五年(1587),朝鲜使团出使北京,路经辽阳,“受宴于都司,掌印郭梦徵,二大人刘秉节在座,初出中阶,西向五拜三叩头,次行再拜礼于大人,移坐桌面,众乐交作,始以一人入舞,中以二人,终以五人,皆著假面,持兵器或戈戟,或旗梃,踊跃交锋,如战酣状,又以五人为鞑子舞而罢[17]。”有时,由于特殊原因,朝廷不能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往往变通到辽阳举行。据《明实录》记载:隆庆元年(1567),朝鲜谢恩使团到达北京,但恰巧嘉靖皇帝去世,国丧期间免宴,最后朝廷命辽东都司在辽阳举行[18]。
二、清朝入关前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清朝在入关之前,与朝鲜多有交往,双方使臣往来频繁,设宴款待亦属常事,虽这个时期,也有“下马宴”和“上马宴”之称,但这并不是制度化意义上的“下马宴”和“上马宴”。而制度化的“下马宴”和“上马宴”则要从崇德元年(1636)开始,因为这一年清朝与朝鲜正式确立起宗藩关系。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崇德元年(1636),清朝政府规定:朝鲜国贡使至东京(辽阳东京城),宴请一次;至盛京,礼部宴请一次;在朝鲜馆宴请一次;回至东京,宴请一次,总共宴请4次。
据《昭显沈阳日记》记载:清崇德二年(1637)闰四月十三日,“清人来报我国使行初十日渡江,满月介求见宰臣,问中朝待我使之礼,宰臣援例以答[19]。”就是说,从此,清朝统治者要按照明朝的仪式来接待朝鲜使团,当然也包括“下马宴”和“上马宴”了。
另据《昭显沈阳日记》记载:崇德五年(1639)正月初五,朝鲜“内官朴滉自京来,留于东馆,盖因正朝问安而来也。衙门为使臣设下马宴。”正月初六,“衙门为使臣设上马宴[20]。”当时,朝鲜在沈阳共有三馆,一是朝鲜馆,由朝鲜国王世子和人质们居住;二是东馆,一般由朝鲜使臣居住;三是北馆,朝鲜使臣和其他人员经常光顾这里。从崇德四年(1639)的情况看,使团当时落脚在东馆无疑,举行“下马宴”和“上马宴”的地方可能在礼部,也可能在东馆。
三、清朝入关后的“下马宴”和“上马宴”
清朝入关以后,完全沿袭明朝的制度,特别在处理与朝鲜关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顺治初年,朝鲜国王往往派遣与清朝有密切关系的王子出使,如麟坪大君李渲就曾出使北京,为此清朝政府于顺治元年(1644)特别规定:“朝鲜王弟来朝,差礼部司官、光禄寺官往山海关迎接,燕一次。遣侍郎往三河县迎接,燕一次。到京日,遣尚书在馆燕一次。朝见毕,赐恩燕一次,在部燕二次,在馆燕二次。回日,饯送筵燕,与来时同。”同年规定:“凡朝鲜差来正副使至山海关,驻防官陪燕一次。到京朝见后,在部燕一次,回日燕一次。饯送筵燕,与来时同。其领时宪书赍咨官,在部燕一次。”顺治八年(1651)规定:“朝鲜进年贡及来京庆贺正副使,在部燕一次,在会同馆燕一次。”朝鲜贡使朝见后,在礼部筵宴,以礼部尚书主持。正使副使各1人,书状官1人,大通官3人,押物官24人,得赏从人30名,无赏从人300名。共设45席,乳酒1瓶,烧黄酒13瓶,茶18桶,蒙古羊13只。当天,仍在会同馆筵燕,礼部尚书主持,共设40席,羊、茶酒,照部燕例送馆。其领时宪书赍咨官役,在精膳司筵燕,以精膳司郎官主持,赍咨官1人,小通事1名,并主燕司官各1席,得赏从人15名1席,共设4席。茶1桶,黄酒1瓶,蒙古羊1只[21]。《大清会典事例》最后修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说明如上记载“下马宴”和“上马宴”这种仪式,在顺治初年被重新强调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虽然如此,清代的“下马宴”和“上马宴”与明代还是有些区别,特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仪式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顺治六年(1649),朝鲜谢恩使团到达北京,五月十七,清朝政府在礼部为朝鲜使团设“下马宴”,“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眶,此人早有重望,曾在皇明之朝为礼部尚书,见时事日非,辞职归家,清人闻有名望,招致任用云。”五月二十六,举行“上马宴[22]”。这里只提到由汉尚书曹某主持“下马宴”,但“下马宴”和“上马宴”具体仪式如何,却只字未提。
康熙二年(1663),朝鲜陈慰使团到达北京,七月二十五,清朝政府通知要为其举行“下马宴”,朝鲜使臣认为自己是“以进香入来,受宴未安”,但礼部认为:“此言虽好,丧事既已完敛,别无拘丧之事。”无奈,朝鲜使臣正使以下30人,穿着黑团领衣服,前往礼部。礼部尚书祈车白,到院子里迎接,率使臣等一行员役,向阙三跪九叩头,然后进入大厅入席。先是喝茶,然后上装满食品的银盘,作者形容食品之丰盛是“积成如堆”。再上茶,很快撤下。又上一盘牛肉,一盘羊肉,用纯金酒杯,装蒙古烧酒,极劝数巡以后离席,回到院中,再向阙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回馆。“八月初五,由礼部侍郎布颜主持,在玉河馆设上马宴[23]。这里记述得比较详细,“下马宴”的主持者是礼部尚书,地点在礼部;“上马宴”的主持者是礼部侍郎,地点在玉河馆。
康熙七年(1668),朝鲜使团到达北京,但迟迟未行下马宴,行期没法确定,在朝鲜使臣屡屡催问下,最后举行“下马宴”:使臣们穿上朝服,前往礼部,汉尚书郝惟讷押宴。首先向北行拜阙礼,然后入席。尚书西向坐,使臣们南向旁坐,员役在臣等之后重行,行茶后进馔,献酒三杯后,又起就阶上拜后相揖,罢归。”四天后举行“上马宴”,礼部侍郎至馆舍举行“上马宴”,使臣等“出中门外,揖入就西庭,北向叩拜,引至中堂分宾主而坐,礼官坐东,臣等坐西,员役堂上坐臣等后,其余坐庭西,以地窄,故宴毕就庭又北向叩拜,揖送至中门外而还[24]。”
从诸多《燕行录》的记载来看,清朝延续了明朝“下马宴”和“上马宴”的传统,但也些区别,如明朝无论“下马宴”和“上马宴”都在会同馆举行,而清朝“下马宴”在礼部举行,而“上马宴”则在使团驻地馆舍举行。筵宴的主席,俗称押宴,明朝一般是由礼部尚书和礼部侍郎担任,但多数情况下宦官也要参与,但清朝比较固定,“下马宴”一般由礼部尚书主持,有时用礼部侍郎,但这样的情况很少,而“上马宴”一般都由礼部侍郎主持。但是,有时也有特例,据权以镇《癸巳燕行日记》记载:雍正二年(1724),在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押宴者竟然是所谓“十二王”,朝鲜使臣在这里提到的十二王,就是雍正皇帝的十二弟履郡王允祹,当时负责礼部事务。午门赏赐以后,朝鲜使臣前往礼部参“下马宴”,“王主壁东向坐,使臣坐其右南向。通官侍立王左,我行员役坐使臣后,受馔,宾主相距不数尺,宴床极丰侈,器皆叠。”宴罢回馆,当行“上马宴”,应该由礼部侍郎主持,但使团居住的院子里水深数尺,而且大雨下个不停,结果侍郎没有来,但筵席照给不误[25]。
参宴的朝鲜使团成员在礼部举行的“下马宴”一般是30人,即使团中的翻译和官员。乾隆五十八年(1793),朝鲜使团前往礼部参“下马宴”,共有三使及从人57人[26]。嘉庆五年(1800),在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据朴齐仁《燕槎录》记载:“西壁下又列盛桌,无虑七八十桌,皆为正官从人而设者。”这就是说,参加筵宴的不但有使臣,而且从人也参与了[27]。七八十桌,超过了《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45桌的规模。关于宴会的规模,可能后来也做过某些调整,据金景善《燕辕直指》谈到此事:“三十正官之外,自前无赐桌之规,始自去年各房军官亦得一桌,是别礼云”[28],看来与嘉庆初年已经有所不同。
此外,清代与明代在礼部举行的“下马宴”上也存在差别。礼部“下马宴”要有望阙礼、见堂礼、宴礼、谢恩礼、别堂礼。望阙礼要在入座前举行,也就是先给皇帝叩头。代替御座的有所谓的“龙亭”,关于“龙亭”的样子,嘉庆初年朴齐仁在《燕槎录》中有所记载:“厅中设虚位,以云纹帐置高床,覆以黄袱,列以烛台,香炉,即行礼处也。”没有“龙亭”,就设皇帝牌位,如果没有牌位,就向北方行礼。尚书在前,使臣在后,面向阙位站好,在赞礼官的口号声中行三跪九叩头礼,注意,明朝望阙礼是一跪三叩头。行完望阙礼后,要行见堂礼,见堂礼就是使臣向押宴官礼部尚书或侍郎行礼,规范见堂礼是一跪三叩头,但“上马宴”免见堂礼。宴礼的流程大略是入座、行茶、上菜、行茶、上馔、上羊肉、进酒、撤膳。礼制文化对座次很讲究,就“下马宴”而言,一般情况尚书或侍郎座位在东,郎官等座位在其后,使臣座位在西,面向尚书或侍郎,其他官员的座位在其后,仆人座位在庭中,也就是院子里。入座以后,行茶一杯。然后是上菜馔。无论“下马宴”还是“上马宴”,菜肴都是非常丰盛的,以致有的使臣在描写其丰盛程度时直接把其称为“盛桌”。据徐文重《燕行日录》记载:康熙三十年(1691)为朝鲜冬至使团举行“下马宴”,“行茶后进床,银碟四十三,叠架以设,既退,进银盘,盛烹羊肉,手自割啖,退后,以金杯进烧酒,一巡后又进煮酒一巡[29]。”再如金舜协《燕行录》记载:雍正七年(1729)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物品之盛,未有加于此也。器上加器,其上又加之,无非奢味珍馐,一盘之器四十余矣[30]。”另据朴齐仁《燕槎录》记载:嘉庆五年(1800)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桌上“尽是果羔糖锡之属,猪羊鱼鸭之炙,以全脚全肩盛之于俞锡之器,一桌所列合计五六十器,可谓盛桌[31]。”一般情况下是“酒三行”结束筵宴。离开桌子以后的首要事情是再行望阙礼,仍然是三拜九叩头,以表谢恩。然后是谢堂礼,此礼有时可免,这要看押宴官的态度。最后使团离开礼部,返回其驻地。
在设宴的过程中,有个程序在清代《燕行录》记载中比较少见,那就是在明代筵宴时必不可少的艺术表演。据《燕行录》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礼部为朝鲜使臣举行“下马宴”,其中有“乐作,酒进,呈杂戏,凡七爵而撤[32]”的描述。这种描述在《燕行录》中少有出现,是清朝方面取消了这个程序,还是朝鲜使臣认为清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根本不屑于记载此事,可能是后者。
任何一种规定,行之年久,都有向形式化发展的趋向,为外交使团举行的“筵宴”也是如此。最初,使团刚到北京,礼部即为其举行“下马宴”,一朔,即一个月后,礼部再为其举行“上马宴”,基本符合“下马宴”和“上马宴”设置的初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团到达北京以后迟迟不举行“下马宴”,直到要离京前才做这件事情,数天后,再举行“上马宴”使团就离京了,故礼部通知举行“下马宴”实际成为批准使团离京的一种信号,这种做法,已经背离了举行“下马宴”的初衷。从现存文献看,这种情况可能在康熙初年就已出现。经过一段时间,“下马宴”往往安排在离京前午门受赏后举行,即上午到午门受赏,午间到礼部参“下马宴”,晚上,有时是午后在使团住处举行“上马宴”,也就是说,“下马宴”与“上马宴”在同一天举行。最早“下马宴”和“上马宴”同一天举行的记载出现在赵荣福的《燕行录》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使团驻在智化寺,六月初五到午门领赏,然后到礼部行“下马宴”。这次由礼部侍郎王顼蛉押宴。“侍郎率吾辈北向行三跪九叩头礼,侍郎定坐,吾辈又向侍郎前行一跪三叩头礼。遂设宴,宴罢,侍郎又率吾辈北向行一跪三叩头礼,后遂罢归智化寺。”“午后,侍郎到智化寺,又行上马宴,吾辈鞠躬祗迎于门内,侍郎答揖,仍设宴如上马宴仪,侍郎罢归,吾辈又祗送于门内[33]。”后来又有“下马宴”和“上马宴”分开进行的例子,但这样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情况是把两宴合并到一天举行。
朝鲜使团出使中国,例有上下马宴,但有时出现特殊情况,不能举行筵宴,就得“免宴”。康熙四十年(1701),朝鲜告卜使团到达北京,当明朝礼部官员与其商议领赏赐宴等事的时候,朝鲜使团明确表示不能参宴。结果,午门领赏以后,“日已晌午,礼部官自礼部赍宴具而来,盖礼部虽已免宴,自前例有入送之规故也。使臣使译舌言于士杰,曰礼部既许免宴,则今虽入送,与上马宴有间,不可行跪叩礼云。则士杰终以为不然,必使使臣行礼而后已[34]。”乾隆五十一年(1786),朝鲜告卜使到达北京,“使行例有上下马宴,而今以丧事奉使,言于礼部停免[35]。”嘉庆三年(1798),朝鲜使团到达北京,恰巧赶上太上皇乾隆皇帝逝世,国家大丧,自然“免宴”,但却采取了变通办法,由内务府施赏鹿5首、熊1首、山猪3首、獐3首、野鸡20首、大生鲜3尾,小生鲜20尾,鹿古鹿尾各10尾等[36]。
一般来说,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筵宴,特别在礼部举行“下马宴”,参加者只有朝鲜使团的成员,但有时也有例外,如与琉球使团一起赴礼部参加“下马宴”等。乾隆五十八年(1719),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团到达北京,次年正月二十四,前往礼部接受“上马宴”(估计这里的上是下之误),关于这次筵宴,朝鲜使臣李在学曾记述说:前往礼部参宴的有朝鲜正使、副使、书状官,以及从人57人。礼部押宴官是礼部侍郎多永武,宴会内容和仪式与其他年份的“下马宴”和“上马宴”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座的还有琉球使团[37]。道光十二年(1832),朝鲜冬至兼谢恩使团到达北京,次年二月初一到礼部领“下马宴”。这次押宴官是礼部侍郎文庆。“侍郎主壁而坐,我三使坐西向东,诸译坐三使之后,琉球使坐东向西。既定行杯,先骆茶,次以酒者,再凡三行才毕[38]。”这次同样有琉球使团参宴。尽管如此,翻阅各种《朝天录》和《燕行录》,与朝鲜使团共同参“下马宴”的只有琉球使团,而且次数很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马宴”“上马宴”都属于国宴性质,其场所和仪式当是非常严肃的,但是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的“下马宴”“上马宴”却出现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抢宴”就是其中之一。“抢宴”,是笔者给下的定义,就是指宴会中哄抢食品和菜肴的现象。“抢宴”的最早记录出现在金昌业的《燕行日记》中。据金氏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作者因为出去游玩,未能参加,等到他回到住处的时候,使臣们刚从礼部返回,他就询问“下马宴”的情形,有位军官告诉他说:“宴床才入,未及下箸,马头辈各持囊袋而进,竞攫饮食。胡人恐失其器,相争做一战场,寒心。上马宴亦如此云。柳凤山、金中和亦不知其如此,而以未能预饬恨之[39]。”马头辈是朝鲜使团中的仆人,地位较低,把“下马宴”和“上马宴”剩下食品赏给他们食用,可能要早于这个时间。据金舜协《燕行录》记载:雍正七年(1729)举行“下马宴”,“酒三巡,遂撤床,而给从人辈。其各所带马头等,抽出腰间之大囊,无论鸡果馔肉,争先掬之,纷扰殊甚,其势不可禁遏[30]。”这种情况,虽然有伤大雅,但毕竟是清朝政府同意的行为,但到嘉庆年间,北京街头的光棍们参加到“抢宴”的人群之中,就使筵宴更不成样子。据朴齐仁《燕槎录》记载:嘉庆五年(1800)七月,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行酒未毕,忽见一队黑汉,扑地揽入,获取馔羞,自相践踏,鞭扑狼藉,势极危怖,不得下箸,传还酒杯,旋即起身出来。”晚上在会同馆举行“上马宴”时出现同样的情况,“才到炕前,又有群汉突拨入来,竞相攫取而去,纷拿杂还之状,一如俄间,诸译从官处亦各有桌,而炕前起扰尤为甚焉。”为此,朴齐仁感叹道:这种行径,“非是宴好之美意,而还贻一场困扰,上国宴宾之节,若是骇恶,甚可叹也[27]。”据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道光十三年(1833)二月,当礼部为朝鲜使团举行“下马宴”的时候,“忽有无数光棍,突入攫拿,势甚危迫。盖从前宴毕撤桌,饷我国诸隶,诸隶之必先争攫,即起恶习也。彼人见而效之,今则我隶更不敢着手,可谓法自弊也[40]。”另据李遇俊《梦游燕行录》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八,前往礼部参“下马宴”,使臣刚刚到桌前,“群胡纷集,以手攫取,破碎器皿。”而“所谓礼部大人,袖手在旁,略不禁止”,故作者感叹说:“待客之礼,不胜骇然”[41]。据江时永《輶轩续录》记载:咸丰四年(1854)二月,礼部为朝鲜冬至使团举行“下马宴”,“方把杯欲饮之际,自庭下忽地扰扰,渐入厅内,盘桌器皿砰訇相搏,如军行鸣军之声,势头危怕,盖是彼人之争攫宴桌而然。礼部侍郎及通官辈虽在座而不少忌惮,亦不为之禁止,可见彼中纪纲亦甚解弛也。尝闻我国从行驿卒,亦多助恶云。故今番则别般操刺,无一人敢上,而彼自如此,奈何,遂与诸使通为起身,到庭下设位处,行拜叩礼而还馆[42]。”
作为礼仪制度,“下马宴”“上马宴”实行了五个多世纪,从明朝到清朝,其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没有大的变化,可见明清与朝鲜之间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