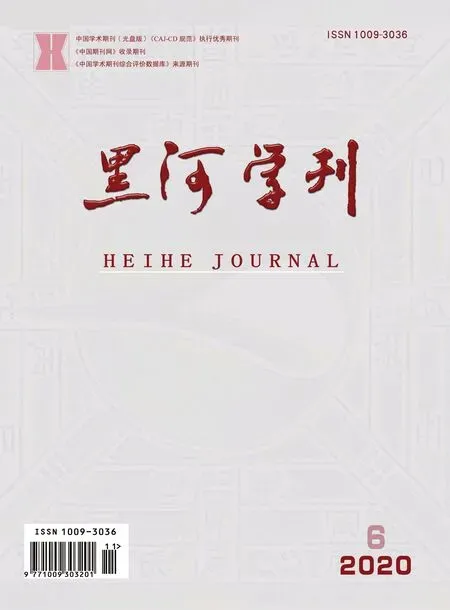《云谣集》若干字句新探
王亚楠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7)
《云谣集》作为最早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敦煌文学作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世纪初,陈人之和颜延亮两位先生将《云谣集》的相关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出版了《云谣集研究汇录》[1]一书。由该书可知,文字的校勘、注释一直是学界对《云谣集》关注的重点。且自从《云谣集》被发现以来,有关其校订本多达十八个,可见先贤们在此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尽管如此,集中部分字词的文字形态及意义,依然众说林立,尚无定论。
本文仍以《云谣集》为考察对象,主要通过文本内证并结合其他史料文献,对其中部分存有争议的字句进行辨证,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己之见,以期对《云谣集》的相关研究有所补益。
一、《凤归云》的字句探析
(一)“拟塞雁行”问题
学界对《凤归云》第一首“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句中的“拟”字究竟当作何字,持论不一。唐圭璋先生的《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和任半塘先生的《云谣集杂曲子》,均将本句校录为“月下愁听砧杵起”,认为“拟”当作“起”,下句校为“塞雁南行”[1]60,龙沐勲先生也在《云谣集杂曲子》中疑“拟”当作“起”字[1]21。但孙其芳在其《云谣集杂曲子校注》中认为,应作“凝塞雁行”[2]85。
引全词来看: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飏。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阇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2]85
整首词为思妇对征夫的思念之情。若为“凝”字,那么这句就是对事实地客观描写,即思妇是在庭院里听到远处的捣衣声并凝视大雁南飞的场景。但下片中,“倚牖”“添香”两个词是对思妇的动作描写,加上思妇又“孤眠鸾帐里”。因此可推测思妇此时应身处闺房,而用“凝”字便与思妇身处房中的境况不相符。且“月下”一词点明时间应是晚上,在晚上凝视大雁,是不合常理的。而“月下”与“拟塞雁”是一个整句的前后两分句,应当有内在的情感及意义关联。若为“凝”字,则建立不起两者的关联。但为“拟”字,则能够建立起由耳之所闻引起的心之所想的连带性。
但若为“拟”字,本句即为思妇在闺房内听到捣衣声,由此联想到大雁南归的场景。前句是实写,写思妇实际听到了远处的砧杵声;后句乃虚写,写思妇自己的想象:北方的大雁都已南归,征戍的良人何时才能还家。这不仅深化了思妇内心的愁绪,使本词的望夫主题得以升华。而且由实入虚,由声牵情,捕捉住女主人公心理意绪的波动变化,使词作情感的生成流转合情亦合理。因此,此字为“拟”更符合全词内容。
此外,在《云谣集》三十首词中,共出现三次“拟”字,分别是:《浣溪沙》:“拟笑千花羞不坼,懒芳菲。”[3]49、《洞仙歌》中的:“少年夫婿,向绿窗下左偎右倚,拟铺鸳被,把人尤泥。”[3]48以及《倾盃乐》中的:“拟貌舞凤飞鸾,对粧台重整娇姿面”[3]50。这三句中同样也使用了“拟”字。《浣溪沙》下包含两首词,孙其芳先生在其《云谣集杂曲子校注》中提到,“这两首均咏歌妓,或为一人一时之作。”[2]86可见这句描写地是,以花之娇媚来喻女子的动人姿态,一个“拟”字传神地描绘出歌妓笑靥如花之态;《洞仙歌》这句主要写女子和年轻丈夫在窗下亲昵拥抱,撒娇软缠,拟上床欢乐之态。同样,《倾盃乐》主要描写女子回忆自己还未出嫁时,在闺中闲居,拿针线描绣凤鸾的场景。全词主要表达了女子由于受媒人的苦言诱骗以及父母之命,嫁给了一心只求功名利禄丈夫后的孤独心情,这里的“拟”字主要为女子描摹凤鸾的样子进行绣花,同時“拟”字则暗示出女子的手艺精湛,刺绣栩栩如生。
综上,在同卷中多次出现“拟”字,且都作“效仿、模拟”之义,可以确定其与“效仿、模拟”这一义项的确有非常固定的联系,即用到“拟”字时,几乎表达的就是“模仿”之义,而反过来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在表达“模仿”这一义项时,《云谣集》中贯用“拟”字。因此,《凤归云》中的“拟塞雁行”之句,应当是表示想要仿效某种事物这一心理活动的意思,那么依据《云谣集》的用语习惯,此处用“拟”是合理的。
(二) 关于《凤归云》曲牌下“闺”、“怨”二字问题
《云谣集杂曲子》是一部敦煌曲子辞总集。在集中所使用的曲牌名中,除《内家娇》外,其余十二种曲牌名均见于崔令钦的《教坊记》。《凤归云》是《云谣集杂曲子》中唯一带题目的曲子词。就其题目,学界亦有不同意见。唐圭章先生在《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中,将本首题目校订为《凤归云徧》,且将《凤归云》第二首前的“怨”字删去。任二北先生在其《云谣集杂曲子》中,将题目校订为《凤归云·闺怨》。任先生指出:“《凤归云》调名下,原卷有一字,似‘闺’而非。王集即谓原卷实系‘闺’字,便不必再强改为‘街’、‘徧’等字。次首之第一字上,原卷有‘又怨’二字。朱孝臧本已校,谓‘巴黎本’的‘怨’字在调名‘又’字之下,王重民亦认为,按伦敦本‘怨’字亦在调名‘又’字之下,便不必再强调为曲辞之第一字。此分明为相联之‘闺怨’二字,此乃二辞共有之题目,被手书误将二字拆开,分属二辞调名之下。应还原如上式,而定二辞为联章。唐乐曲调名,从无缀‘徧’字者,罗书作‘《凤归云徧》’,不可从。”[1]97
现引四首曲子如下: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鴈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飏。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阇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3]85
渌窗独坐,修得为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止凭三尺,勇战奸愚。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公卿回故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3]48
幸因今日,得睹娇娥。眉如初月,目引横波。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朱含碎玉,云髻婆娑。东邻有女,相料实难过。罗衣掩袂,行步逶迤。逢人问语羞无力,态娇多。锦衣公子见,垂鞭立马,肠断知么?[3]48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合,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娉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3]48
首先,四首在内容上具有连贯性。因为征夫“去便无消息”,所以思妇才在闺房中进行“金钗卜”,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卦卦皆虚”,因此女子才想要“传书”给丈夫。后两首也叙写女子在寻找替自己传书人的过程中被锦衣公子爱慕,但最终女子还是表明自己的坚贞之情。第一首中的“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第二首中的“岂知红脸,泪滴如珠”和第四首中的“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都是直接表达出来思妇对征夫的想念与忠贞不渝。其三虽然是以男子视角来描写的,但“罗衣掩袂,行步逶迤”一句叙述的亦是女子在着急地寻找替自己传书人的匆忙情景。组诗的出现是在某一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一个连续创作,其所要表现的情感趋向基本一致、逐层深入[4]12。通过这四首曲子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首呼应式的联章,虽叙写的内容不一,但整体从感情的表达上来看,四首都具有一致性。
从主题层面上看,表面上前两首所表达的主题是“闺怨”,后两首却无明显闺怨之情。但实际上,后两首是对前两首的补充和扩展,正是由“闺怨”所引申出来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四首曲子的主旨都是表达了女子对征夫的思念与忠贞,前两首正面描写,后两首侧面描写。四首诗分别从正、侧两个维度将女子的思恋之情与坚贞之意呈现得更加饱满。
更具体而言,上述《凤归云》四首,各两首为一联章。前两首都表现出“闺怨”这一主题,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第一首中,通过“愁听”“孤眠”“魂梦”“垂血泪”和“添香”等词呈现思妇在闺房中的一系列动作。妻子对月念远,倚窗垂泪,盼望着征人早归,表现出与征夫的久别之苦,重在抒发对其深切的相思之情。而后一首重在表现思妇内心的哀怨之情:丈夫只顾战场杀敌,却不知为妻者孤寂思念之苦,是为一怨;久久不归,却不知为妻者卜卦不利的惊惧忐忑之痛,是为一怨;为家国功名,却未意识为妻者对色衰爱弛的忧虑感伤,是为一怨。三怨接连而出,使幽怨之情较前一首更为深入。第一首以“闺”字为题,既点明“闺房”为词作所展现的核心空间,同时借此空间又预示出词中抒情主人公乃为女子,而所流露的亦是女性内心私密复杂的情愫。第二首以“怨”为题,则更契合词作的情绪基调,同时也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一联章中两首词作表现重点的变化。而将两首词的题目即“闺”与“怨”合而视之,又能清晰地呈现出身处闺房的思妇内心情感随着时间推移,由思念而入幽怨的情感变化过程。这是《凤归云徧》或《凤归云·闺怨》的题目形式所不能充分发挥的功效。因此可以认为,《凤归云》为曲牌名,而“闺”是上篇的题目,“怨”是下篇之题,“又” 字意为承接上首《凤归云》这一曲名。
二、关于《破阵子》第二首的字句解说
《破阵子》在《云谣集》中共四首,其中第二首中的“雪落亭梅愁地”一句争议较大。关键在于学界对“亭”字究竟当作何字,看法不一。在影印本《英藏敦煌文献》中,此字的偏旁模糊难辨,但作为另一组成部分的“亭”字则比较清晰,因此,学者们对“亭”的真实字形进行辨析考证,主要形成了“庭”“渟”“停”三种观点。
今引全曲如下:
日暖风轻佳景。流莺似问人。正是越溪花捧艳。独隔千山与万津。单于迷虏尘。雪落亭梅愁地。香檀枉注歌唇。拦径萋萋芳草绿。红脸可知珠泪频。鱼笺岂易呈。[3]49
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歌词总编》中认为“亭”当作“庭”,并将“亭梅”校正为“梅庭”。笔者认为此说不妥。一则,上文已述影印本《英藏敦煌文献》中,此字可明确辨认的部件为“亭”字,那么原字应当包含此部件。而任半塘先生认为的“庭”字,从字形上看已完全与残留的字部不相吻合。二则,若此处表达的是庭院的意思,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庭”字,使用“亭”字部的其它文字,反而不合逻辑。如在《破阵子》第四首中,“春去春来庭树老,早晚王师归却还。免交心怨天。”[3]49一句以及《内家娇》第二首中的“搔头重慵憽不插,只把同心,千遍捻弄,来往中庭。”[1]214和《抛球乐》第二首的“无端略入后园看,羞煞庭中数树花。”[1]217都使用了“庭”字来表达“庭院”之意,从此可知,在《云谣集》中没有将“庭院”之意的“庭”字,写成“亭”字部件之字的例子。因此,任半塘先生校正的“梅庭”二字是不太合适的。
潘重规先生在敦煌《云谣集》新书中,校“停”字为“渟”,又云:“读‘停’为‘亭’或‘庭’,皆可通。言满地落梅如雪,甚愁人也。”[1]206“渟”字在《康熙字典》的解释如下:“渟”,《集韵》《韵会》《正韵》“从音庭”;《埤苍》“渟,水止也”;《史记·李斯传》“决渟水致之海”。[5]633
若为“渟”字,“雪落渟梅愁地”一句在文中的意思即为:初春的梅花如雪花一样飘落下来,落到了溪水边。这一句看似与上文中的“正是越溪花捧艳”暗合,但却与下文“香檀枉注歌唇”几句不搭。整首曲子是在描写闺中女子思夫的情景,上片描写美好的初春景色,下片通过描写女子因思念落泪而导致妆容尽失的场景,以此表明女子的思念之情。因此,若为“渟”字,则“雪落”一句依然为初春景物的描写,而与下片以人物为表现中心的谋篇布局相冲突,似乎不妥。
唐圭璋先生在其《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中将本句校订为“雪落亭梅愁地”,认为“停”字为“亭”之误。[1]70“亭”字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如下:《说文》“民所安定也”;《释名》“停也,道路所舍,人停集也”;《风俗通》“亭留也,行旅宿会之所也”;《东观汉记》“卫为桂阳太守,凿山通路列亭置邮”等。[5]89若为“亭”字,本句的即是描写雪花飘落,亭子旁的梅花等景物,那么此句便为环境描写,但下文却笔锋一转开始描写女子的妆容,意脉的断裂及突兀感与上文对潘重规先生“渟”字之解的相同。显然,若作“亭”字理解,同样不妥。
王重民先生在其校辑的《云谣集杂曲子》中,将本句校为“雪落停梅愁地”。[1]89“停”字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释为:《集韵》《韵会》《正韵》“从音廷,行中止也”;《释名》“停,定也,定于所在也”[5]110。若为“停”字,“雪落停梅愁地”此句就暗含一定的文化韵味。据周汛、高春明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一书中《面饰篇》一节可知:古老的妆粉主要有两种成份,一种是以米粉研碎后加入香料而成;另一种是将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化铅而成,所以又叫“铅华”,也有称“铅粉”的。其色泽洁白,质地细腻,深受妇女喜爱[6]118。可见,此句中的“雪”也可能含有其他意义。同样,出于同卷中的《凤归云》 第三首中又有:“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3]48一句,其中的“雪”字亦为此种内涵。再如同卷的《内家娇》中“轻轻傅粉,深深长画眉渌,雪散胸前。”前者是对女子形貌的描摹,后者则是对女子化妆过程的叙述。显然,两处出现的“雪”字,并非实指雪花,而是代指白如雪般的铅粉。
而“停梅”中的“梅”字,也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梅花,它亦可指唐代女子所画的一种妆容。《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中提到,唐代妇女使用花钿较为普遍。从形象资料看,最为简单的花钿只是一个小小的圆点,复杂的则以金箔片、黑光纸、鱼鳃骨以及云母片等材质剪成各种花朵之状,其中尤以梅花为多见[6]133。
唐宰相牛僧孺之孙牛峤,曾作《红蔷薇》一诗,其中“若缀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7]7694一句就借用了寿阳公主的典故。据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三记载:“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8]144再有,唐代吴融的《还俗尼(本是歌妓)》中提到:“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得旧身。”[7]7928其中,“梅额”指的便是额头的梅花妆。可见本句中的“梅”也就不是其字面含义,在这里亦可指是唐代女子所用于妆容的一种形状为梅花样式的花钿。纵观整首词,其感情基调为哀怨,通过描写女子舒展不开的眉头来表达出其内心的忧愁。正如唐代诗人李廷璧的《愁诗》所描写的“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7]7695一样,而这正与下文“红脸可知珠泪频”一句相通。且唐代妇女的化妆顺序大致为:“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或染额黄)、贴面靥、描斜红、涂唇脂。”[6]132因此,若将“雪落停梅愁地”一句看作是描写妇女扑粉和贴花钿的过程,与下文的“香檀枉注歌唇”等句衔接地似乎更为流畅,所表达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综上,若根据对整首曲子的理解,本句中用“停”字更为合适。正是初春美景,女子却在化妆时联想到了与自己远隔的丈夫。于是悲从中来,想到此时欣赏自己的那个人却不能陪在身边,打扮得再美丽又能让谁来看呢?至此,眉头紧蹙,描眉的手久久停留在额间。
三、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最早的民间词集,《云谣集》的发现,使得对词的起源、词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民间词与文人词的关系等问题得到进一步研究。且其自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词史研究和唐代文学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在对《云谣集》的刻印、校勘、注释、考证等方面都产生了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对于其具体的字句等方面仍存有许多争议。因此,《云谣集》仍值得我们深入考证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