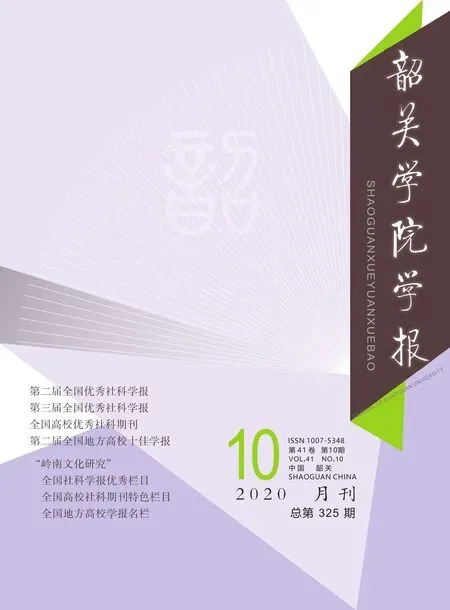学术通讯:《民俗》周刊的一种编辑意识
王焰安
(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韶关 512005)
《民俗》周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辑,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定期刊物,自1928年3月21日创刊到1933年6月13日止,共出版123期。1936年9月15日复刊,再出版2卷各4期,1943年12月停刊。期间,1928年3月21日—1928年9月5日钟敬文任编辑(23/24期止);1928年9月9日—1930年1月容肇祖任编辑(93/94/95期止);1930年1月—1930年5月16日刘万章任编辑(110期 止);1933年3月21日—1933年6月13日容肇祖任编辑(123期止);1936年9月15日—1937年6月30日杨成志任编辑(第1卷第3期止);1942年3月—1943年12月钟敬文任编辑(第2卷3/4期止)。《民俗》周刊的编辑虽经历了多次变化,但《民俗》周刊的“通讯”却没有因为编辑的更换而彻底中断,而是断续地有所沿习,这种断续地有所沿习的“通讯”,尽管不是《民俗》周刊的固定栏目,但却有59期的《民俗》发表了“通讯”,几乎接近《民俗》周刊总期数的一半,甚至还有作者建议考虑“通讯栏之增加”[1],由此我们认为,它体现了《民俗》周刊的一种编辑意识。
《民俗》周刊发表“通讯”,始于第三期,其中,以“通讯”为关键词的有33期,共有46篇通讯;以“通信”“通函”“来信”为关键词的有9期,共有30篇通信;以“关于XX”为关键词的有5期,共有5篇通讯,这里的“关于XX”,是指没有排在“通讯”栏内,特指书信体的文章;还有没有排在“通讯”栏内、且没有“关于”等关键词,仅有书信体形式的有6期,共有6篇文章,这是作者为行文方便而借书信体写作的论文。《民俗》周刊每期“通讯”封数不定,有的是1封,有的是3、5封,最多的有16封。《民俗》周刊的“通讯”,绝大部分与一般意义上的“通讯”不同,多具有学术涵义,因此统称之为“学术通讯”。纵观《民俗》周刊,其所谓的“学术通讯”,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探问投稿发稿的通讯
探问投稿发稿的通讯,在资讯不甚发达的时代,是期刊编辑工作中作者与编辑最常用的交流方式,对于通信中涉及的普遍性问题,期刊通常会以启事等形式进行告知;对于具体的稿件问题,编辑一般则多以私信回复。《民俗》周刊将部分通讯公开发表,目的是借以宣传《民俗》周刊的主张,表达《民俗》周刊的编辑意识。
《民俗》周刊发表的有关探问投稿发稿的通讯,具有这样几种内涵:
一是告知编辑查收稿件。作者投稿后,首先关心的是稿件能否顺利地到达编辑部,所以绝大部分作者会以通讯的形式告知编辑查收稿件,《民俗》周刊告知编辑查收稿件的“通讯”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将信附在投稿稿件里,告知编辑,如:“兹付上‘关于张天师的鸡零狗碎’和‘翁源的过年风俗’二文,请查收。”[2]其二是另外再写一信,告诉编辑,如:“寄顾先生的,有《吴歌乙集》《苏州婚丧》《杨师石故事》(前后两次,前次六节,后次三节)等篇,曾否接收?”[3]“前寄奉稿子一篇,大约题名《中国民间的故事型式研究发端》,想来你已收到了吧?”[4]“几天前,所奉民俗稿件——《蛇郎故事》《狡童》《长青里族谱上的天后》三篇——收到了吗?”[5]“十多天前,寄上《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一文,想已收到付排了。”[1]“顺寄上《百年前之台湾及其土番》一文,待删补白《民俗》周刊,未悉可否?暇乞示复!”[1]
二是征询稿件的需求意向。为了了解期刊的发稿意向,提高发稿的命中率,作者在投稿前,往往会询问期刊的用稿需求意向。《民俗》周刊征询稿件需求意向的“通讯”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投稿前先专门来信询问,如郑玄珠想将自己搜集整理的一百多首歌谣寄给《民俗》,又不知有没有采用的价值,便给钟敬文写信:“久欲将这些东西付与先生处置,但不知你有没有闲情来看,这是一个问题,是否有采取的价值,正是难料。”[6]其二是在相关的信件中顺便询问,如:“倘《民俗》需要此类稿子,自当检出寄来。”[7]“不识可以寄来《民俗》发表否?得便,祈示知。”[7]“我这里颇有些民俗、歌谣、故事的稿子,如果你那里十分需用,可以寄一部分给你。”[1]“倘需稿件亦祈示知,以便奉上。”[1]
三是请求刊发稿件。为了体现自己作品的价值,尽早获得社会的承认,作者往往通过“通讯”,表达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发表,《民俗》周刊有关刊发稿件的“通讯”,具有三种情况:其一是请求刊发稿件,或是希望刊发作者本人的稿件,作者本人的稿件,有的是编辑的约稿,如:“现将旧作《绍兴歌谣》奉上,或可聊以塞责。”[8]“兹即依命将番歌寄上,便希实之民俗。”[9]有的则是作者的自投稿,如“我寄静文伙友的稿子,尚有《宋襄的故事》未发表,恐日久违失,请先生刊出吧!”[3]“《新年号》如能出,这篇《水仙花的故事》,亦可凑趣。”[8]“这信与拙作《贝洛尔的鹅妈妈故事》有关,请在同一期的《民俗》上发表。”[10]“奉上《关于民俗的平常话》二节,希为斧正,实之《民俗》。”[7]“倘有采录的价值,请将这封信在《民俗》上发表,以供嗜欲民俗学的先生们研究。”[11]“《关于民俗》与《为西湖博览会一部分的出品写几句话》两个短论,是弟百忙中给此间的《民俗周刊》作的,《民俗》如有余幅,很可复载一下,因为此间的《周刊》,外边不易见到也。”[11]其二是希望朋友的稿件能够刊发,如:“均正已有《嘉兴谜语》百则寄你”,“也不妨登载一下。”[12]“这是罗香林先生复我的一封信,因其中所说的,多是实际问题,而罗先生又嘱寄刊《民俗》,故特抄正奉上,祈请编入《民俗》通讯栏吧。”[13]其三是请求发表有关学会或征稿信息,如:“寄上敝会征集客家歌谣的启事一通,方便则请代为发表!”[14]“兹特抄本《歌谣》二卷各期要目一纸,希于下期《民俗》择要登载,藉通声气。”[1]“附上《民俗园地》目录,请刊入《民俗》第二期中。”[1]
对于这类通讯,有的编辑进行回复,有的编辑则不进行回复。进行回复的,具有三种情况:有的仅是表示稿件可以采用,如:“先生各篇稿件,均已预备付印,在四十期以前,总可以陆续出现。”[3]有的则体现了编辑的编辑意识,对于郑玄珠的询问,钟敬文复信表示:“你所收录的东西,能寄了来,乃是我们所十二分欢迎的……可以先分期在《民俗》周刊上发表一下。”[6]鼓励郑玄珠以后能“给我们以很多的关于民间文艺风俗的材料”[6],这既是对郑玄珠的答复,更是对所有作者、读者的答复,体现了编辑的一种宣传意识。有的回复则是约稿,这种约稿,或是针对《民俗》的选题需求进行约稿,如:“四十一期以后或可出一次‘槟榔专号’……兄如有文章,也可凑凑高兴。”[3]或是针对通讯者提供的选题进行约稿,如:“你有关于‘张天师的传说’么?暇中可示我一二。”[3]
二、交流民俗活动信息的通讯
《民俗》周刊中的通讯,很多是作者通报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相关信息,具有这样几种内涵:
一是交流民俗学学术活动的信息。主要是指有关民俗学学术组织的信息,发表这种“通讯”,可以促进团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如:“敝会同人……专门研究客家歌谣……现在已经搜得的客歌,约一千余篇。”[14]
二是交流民俗学同人调研活动的信息。主要指民俗学学术同人的调研经过和调研收获与研究动向,发表这种“通讯”,借以引起同人的相互学术关注,如罗香林报告他们的妙峰山调查活动和调查结果:“所得结果,比之四年前顾先生第一次上妙峰山所得的成绩,虽似不及,然其中亦有一二点,为从前调查所未及或未详者,不可谓非民俗学会中的一个好消息也。”[13]杨成志报告他在云南凉山调查的情况和收获:“‘庐鹿’的民间文艺,的确带有初民的气习且富有自然艺术的。他们的诗歌分为六种:新年歌,挽歌,山歌,新婚歌,火把节歌,儿歌。我搜集了百余首且译为中文,这又值得告慰的。”[15]容肇祖报告自己近期的研究动向:“近来著作,都偏向于中国思想史的一方面。”[1]
三是交流民俗学同人的通讯处信息。由于民俗学同人经常变更工作单位,往往会影响同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发表这种“通讯”,可方便同人的交流,如:“南中不少关心北大研究院及先生个人生活的朋友,我特把此信暴白于刊末,算作传布个公共的消息。”[16]江绍原的通讯处,“现在是杭州下板儿巷十五号”[12];白寿彝的通讯处,在“北平海甸前辛庄八号”[17]。
四是交流民俗学书文出版发表的信息。学术信息不通畅,是影响学术发达和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发表这种“通讯”,可为作者读者提供新的信息,其一是通报自己或同人的研究出版信息,如:“弟北来后,出版有在粤时所编辑的关于民间文学书籍两册,一名《歌谣论集》,北新书局印行;一名《马来情歌》,远东图书公司印行。”[8]其二是通报同人的研究出版信息,如:“赵景深先生,是个童话研究家兼汇集家,对于民俗学的兴趣极浓,亦尝愿与不相识的人们通讯,其著述有《中国童话集》《格林童话集》《童话评论》《童话概要》《童话论集》《童话学ABC》《月的话》《民间故事研究》。”[18]江绍原的《现代英吉利谣俗》“经已译完,逐章送登《春潮》《俗物》《一般》……等刊物”[18];谢云声“编成已出的书,有《台湾情歌》《闽歌甲集》二种”[18]。
五是交流民俗学报刊的信息,主要是通报其他报刊发表民俗学方面文章的信息,发表这种“通讯”,以利于同人投稿获取材料。如:“据调孚兄说,前几年,《时事新报》的‘青光’(汪仲贤编辑任内)倒有许多民间故事的记载。”[2]“《新女性》上,最多纪述风俗的论著发表……《妇女杂志》,今年所出的‘生活专号’‘婚姻问题专号’,亦颇多各地妇女状况的记录。”[2]“最近《小说月报》启事,又有自今年起,将兼讨论及民俗学与文学有关系的问题。”[8]“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樊演先生等出版的《俗物》(以裒罗社名义出版),也是以研究民俗学为职志的。”[18]“顾颉刚先生拟于天津《大公报》上辟一《风俗周报》……又闻钟敬文先生近亦在杭州民国日报办一《民俗周刊》。”[18]“《开明》或者能够出一‘民间文艺号’。”[17]“这里有一家杂志,要出版一个‘民间艺术专号’。”[1]“日本民族学会出有一种季刊,已出至二卷四号。”[1]
六是交流民俗学的研究信息。由于同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个人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和条件进行研究,发表这种“通讯”,有利于相同兴趣和话题的同人进行商讨,其一是发布正在写作或已完成写作的研究成果,如赵景深告知:“昨天又作了一篇《挪威民间故事研究》,介绍顾均正的《三公主》,已投《贡献旬刊》,内容述及挪威民间故事与中国故事异同处甚多,并引及宋人小说、元曲、《京语童话》‘小英雄’,拙编《中国童语集》里的‘小白龙’等等。”[4]顾均正告知“现在正在整理一部《世界童话研究》”,“将由开明书店出版”[12]。其二是介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如:“容元胎先生在最近北大《歌谣周刊》所发表之《粤讴及其作者》一文,见地颇精审。”[1]
三、提供民俗学材料的通讯
《民俗》周刊中的通讯,提供了不少的民俗学材料。具有三种内涵:
一是提供自己所发现、所记录的材料。通讯者在从事民俗活动中,或是发现了某些新材料,发表这种“通讯”,对民俗学研究者有所帮助和启发,如张清水分类记录了翁源各种命名形式,求神、佛而生的人名中必有“神”“佛”字,求石、树、路、桥、日、月、水、社坛、观音娘娘护佑过的人名中必有“石”“树”“路”“桥”“日”“月”“水”“社”“观”[19]。叶德均发现二郎神有不同的称呼:“关于二郎神的诞日,《玉匣记》一书内说为六月廿六日,但称为二郎真君。又上海石印的历书亦谓六月廿六日,又称为二郎星君。”[7]钟敬文发现壮人与客家人有相同的丧葬习俗:“《峒溪纤志》,记有壮人亲死,儿子恸哭赴河投钱买水的礼俗,但吾乡也有此同样的俗尚。”[8]瑶族人与东江客家人有些词语发音相同:“吾邑(广东东江一县)的客家人,有些念‘鱼’音作‘牛’的,《粤风》中,明说着瑶人念‘鱼’当‘牛’的话。”[8]赵景深发现泰勒《中国民俗学》中茶树的起源来源于小泉八云的《几个中国鬼》:“最近买了一本小泉八云的《几个中国鬼》……其中茶树的起源和钟鼓寺钟的起源两故事与谭勒《中国民俗学》中所说的相同,也许谭勒的话就是根据小泉八云的原书。”[12]
二是补充自己研究的材料。发表这种“通讯”,利于研究成果的趋于完善,其一是作者文章已经完成,且已投稿,后来又发现了新材料,便以通讯的形式进行补充。如于飞投寄《关于石敢当》后,发现了两条资料,于是以通讯进行补充:“《旧莆田县志》云:‘在城西南隅,今兴化府署是也。庆历四年,知县张纬新中堂,掘地而夸之;得一石,修广各五尺;验之,无刻缕痕,系墨迹。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茶香室续抄》卷十九‘石敢当碑始于唐,云: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记》,兴化军有石敢当碑,注云:‘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兴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厌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家用碑石书曰‘石敢当’三字镇于门,亦此风也。’按此则‘石敢当’三字石刻始于唐。”[20]其二是作者的文章已经发表,后来又发现了新材料,便以通讯的形式进行补充。如张清水在《杂谈端阳古俗》发表后,“兹续得些材料,用特补记于下,以供日后改作拙著之用。”从李时珍《本草纲目》得来的,从《增广验方新编》得来的,从《时疫辩》得来的,共有13条[17]。《博物志》《玉烛宝典》《唐会要》《岁时杂记》《中华古今注》及杜甫《端午日赐衣》诗中,记载有 6 条[18]。
三是补充他人研究的材料。发表这种“通讯”,有利于相互促进与提高,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其一是作者对《民俗》已发表的某一问题或相关同人正在研究的某一问题进行补充或提供相关的材料。如钟敬文发表《啖槟榔的风俗》后,云心以自己家乡祭祖时要说“进榔姜”,揖轿时有专装槟榔的“槟榔古”,做喜事不收贺礼而送两个槟榔相告等,告知存在过啖槟榔的材料[21]。张清水则提供广州、翁源、南洋啖槟榔的材料:广州“在食餐之后,伙伴们每每送上一磕用油或火锅炸过的槟榔来”,“生客甫来,即以槟榔相敬,真是如茶烟般的普通了”[22];翁源日常“设席待客,不论官民,槟榔是少不得的”,闹房时说的四句和民间情歌中,也与槟榔相关联[22];肇庆与广州均有年卅晚上啖槟榔的习俗[23]。魏应麒告知福建漳州槟榔是和解的食品,“裹槟榔和老叶灰吃”,还是婚礼的重要礼物,“婚礼纳彩,槟榔是必要之一种礼物”[24]。赵景深读了容肇祖有关“华光”文章后,提供《南游记》中有关华光的材料:“图后两个鬼大约即千里眼顺风耳,华光中间一眼为‘天眼’,手中所执为‘三角金砖’法宝。”[8]魏应麒读了有关“石敢当”文后,即提供“石敢当”材料:“昨偶翻阅元陶宗仪《辍耕录》,见有‘石敢当’一条,因忆本刊‘神的专号’中邓尔雅先生所著《石敢当》一篇尚未见此,用特录呈清览,想亦先生暨邓先生之所乐闻也。《辍耕录》卷十七说:‘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25]“梁祝故事”专号发表后,郭坚提供五华的梁祝传说材料:英台裙变蝴蝶的传说,百日花深红色的传说,蝇、蚁、狗反魂的传说[5]。张清水的《命名的迷信》发表后,黄有琚提供本地命名材料:“文昌民间也同样以期求男孩为用意,多命他们的女儿名为‘呵舅’和‘舅随’等。”“文昌尚有因为女儿的多病难养,乃依卜筮先生的推算,借别姓为命名的一例。……如‘何养’‘周留’‘何清’‘林书’等。”[11]其二是作者对他人在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材料补充,如:“去年某君曾在《文学周报》上揭载一文,说明江西一带客人男女野合的‘倒青山’风俗,但据我所知,《两般秋雨盦随笔》中,已记载有苗瑶民这种同样的风尚。”[8]张清水见《妙峰山》中有“中伙”的讨论,特提供家乡“中伙”的材料:“婚娶时,新娘的兄弟骑马坐轿去‘送嫁’,至半路止。娶媳妇的,多领新郎去半路相候,届时出酒肉相待。相见时,新郎须拜见妻兄弟。宴饮时,新郎须把盏进酒。——这个婚俗的片断,便叫作‘打中伙’。娶媳妇的如允‘打中伙’时,须预先去帖请女家亲人。”[26]薛澄清“细读书中所编入的各位先生所作的各篇大作,他们都没有提到一部和《天后之研究》似不无有相当之关系……至少亦足备为此项研究的参考书之一——的一部书,所以我此刻喜为之介绍于此……《湄洲屿志略》。”[27]
四、进行民俗学探讨的通讯
学术探讨的通讯,主要是指以学术内容为主的通讯,《民俗》通讯中,涉及了很多的学术问题,无法一一列举,这里主要就其论述稍有系统的问题进行胪列,借此而见一斑。《民俗》通讯探讨的学术问题主要有:
一是关于民间故事的分类。民间故事的分类,在民间文学史上存在着不同的学说,是民间故事学上一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顾均正认为:“对于民间故事的分类问题,我绝对不赞成用型式表,因为相同故事只是偶然的,或是由一个故事转变而来,我们不能说每一个故事都有相同的例子,或每一个故事都有转变”,而主张将民间故事分为童话(含有神异分子的)、传说、故事、寓言、趣话、事物来因故事、地方传说[28],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标准。
二是关于民间故事的重叠。重叠是民间故事常用的结构形式,是儿童和妇女心理的自然表露,但整理发表的重叠故事却不多见。张清水认为,这与民间具有众多重叠故事的事实不相符合,并由此分析重叠的民间故事之所以不多的原因,“是因记录者不大注意和不了解‘重叠故事’之重要的原故”,因为“记录者,多是成年人,已脱离了儿童的生活,对童话中的情节,认为重复、累赘”,把重复的情节删除了,加之记录者又学过古文,以古人的标准要求故事,把“重叠的情节删去或改作了”[29]。
三是关于广州儿歌的问题。刘万章编著出版了《广州儿歌甲集》,读者梁孔滚认为书中存在着一些有关方言注解、俗字俗语注音问题,刘万章据此进行了答复。如词语“捐入”,梁孔滚认为应该是“爬入”,刘万章答复道:“‘爬’是在征途上的工作,‘捐’是差不多要到目的地;也许爬是长的,捐是短的工作,而且‘捐’多数是对准一个洞(即粤语的窿),爬未必有洞。”如方音,梁孔滚认为“最好是有字可表其意的,便写字而附以罗马拼音,没字可写的,则写上拼音的罗马字母而附加注释”。刘万章答复:“何妨再把相近音的字来表现,反正都要注释附音”,“在广州方面,俗字俗成语很多很多,有许多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俗字或俗成语,定要留存”[30]。
四是关于河南谜语的有关问题。白启明先生的《河南谜语》出版后,编辑刘万章约白寿彝先生进行品评,白寿彝谈到《河南谜语》存在的问题,“在一部分谜语之后,有所谓‘附’者,页一五则‘附’中更有‘附’。其实所谓‘附’也系纯粹的谜语。就谜语的立场说,还有什么正和附之分呢?这未免过于牵强了”,“本书不采注音法,只用方块字来记,有时是很使人觉得硬涩之感的。有些字,写不出,也须注音”[31]。
五是关于“轶事”与故事的分别问题。张清水投寄给《民俗》的是“宋湘的故事”,发表时编者改为“宋湘的轶事”。为此,张清水认为:“轶事,太过实在……宋湘虽有其人,但是老百姓们所传关于他的故事太多了,其中不无附会、纠缠、借用之处,真实性,着实很少;我们只把它当做‘传说’看便算了,若把它当做轶事,以为实有其事,可就错了。……故事止于故事,我们万不能确切地当它是轶事看。”[26]
六是关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民间故事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如“所以照我的意思,还是取前一种方法。因为前一种所得的成绩是无限的……用前一种方法研究,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民俗学的智识来做工具的”[32]。民间歌谣,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歌谣的比较,范围并不狭隘,并不偏于局部一方面。其比较起来的结果,应用是很广泛的”[33]。
七是关于民俗学具体问题的商讨。即针对《民俗》所发文章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发表议论。如招北恩在《民俗》第1期的《广东妇女风俗及民歌一斑》中认为“骂玉郎”是广东民歌,谢光汉认为“骂玉郎”既见于《聊斋志异》,也见于广西民间各地,是三大调之一,且词的语气和口吻,也“没有广调的特征”[34]。
这些不同观点和方法的讨论,编者有时附以简短的文字,或表示认同,或提供材料,如编者在谢光汉信后附言,认为“其中没有色彩很浓重的岭南方言之存在”[34],这等于是借此而参与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
五、改善《民俗》编辑出版的通讯
如何编辑出版《民俗》,发挥《民俗》的作用,提高民俗学的地位,热心《民俗》的作者、读者,通过“通讯”的形式,向编辑提出了一些有关编辑内容和编辑形式的建议:
一是有关编辑内容的建议。关于编辑内容的建议,主要有四点:其一增加风俗的内容。《民俗》由《民间文艺》改刊而来,前期沿袭的是发表民间文学作品的思路,这与《民俗》名实不符,因此,有人建议:“《民俗周刊》似乎也该有这类风俗调查的文字发表,不知你与顾傅诸先生以为如何?”[4]其二增加翻译的内容。中国民俗学在初创与发展时期,需要借鉴国外的民俗学理论与实践,因此,应以《民俗》为阵地,宣传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引领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故有人建议:“对于此门学问的理论,应负有迫切宣传之重责……但介绍翻译,似属可能。”[8]“译著些外国民俗学的专著”,“国际民俗学研究之译述”[1]。其三,增加研究份量。增加发表研究内容的份量,是推动民俗学研究,扩大《民俗》影响的有效途径。因此,有人建议:“民俗的研究,是一种纯碎的学术运动……为严肃我们学术研究的营垒起见”[8],“研究的文字和叙述并重”[35],“多发表有研究性的作品”。“今后《民俗》,照愚见所及,应注意于长篇研究作品之登载。”[1]注重“征名家之著作”[1]。“篇首能够冠以一篇带有研究讨论性质的论文、杂录,更佳。”[3]其四增加作品的注音。无论是发表记录的民俗作品还是研究的民俗论文,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字词,为便于准确的理解,有人建议:“歌谣中的方言方音,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详加注释。”[35]
二是有关编辑形式的建议。关于编辑形式的建议,主要有四点:其一是出版专号。专号,是一期或多期集中刊发某一主题的文章,有利于材料和论题的集中展示,往往具有集束的宣传效果。或是直接希望出专号,“继续出许许多多的专号,则《民俗》的身价,自然会提高而为一般人所颂扬了”[3]。如“多出专号”“各种专号之刊行”[1]“倘能在《民俗》出一‘粤讴研究专号’或‘广东民间文学专号’,以发掘吾粤之宝藏者,尤为弟所企求也”[1];或是通过赞扬已出专号,间接希望再出专号,如“尤其是最近所出神与槟榔等专号,材料丰富,论述详备,更使远人读阅之下,不胜高兴”[8]。其二增加文内插图。“《民俗》周刊希望以后多多登各地风俗照片”[36],“珍贵图片之加插(如各地风俗、民俗之照片及民俗学先进之照相,应广为搜求刊出)。”[1]其三是缩短出版周期。《民俗》改为季刊后,出版日期不定,故有人建议:“如稿件许可,可改为月刊否?(自然,至好仍为周刊)。”[1]其四是科学归类栏目。栏目归类,是编辑知识与意识的体现,而“民俗各期文字分类表,似不尽臻于美善,如拙作《绍介鹅姆姆故事》之论文而归入故事栏中,殊觉其未妥也。其他,正复多此。谨以相质,幸垂注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