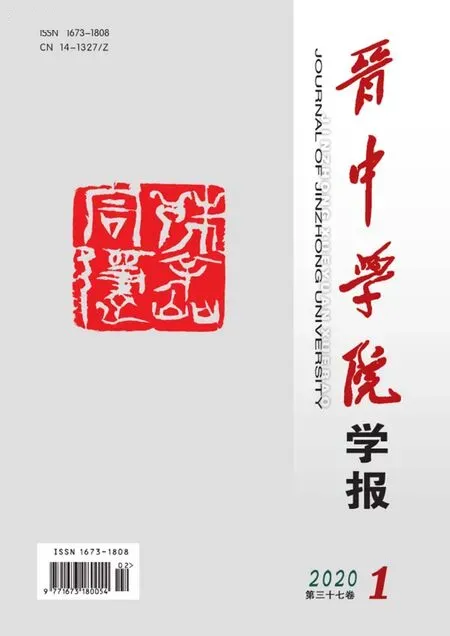当前古体诗歌文体权力的内在诉求
郭 鹏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白话文运动后,古体诗歌并未退出文学舞台。目前,古体诗歌的创作与交流活动都还存在。这种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学文体虽然失去了过去的“贵族”身份,但仍然是人们摅写心志、表达情怀的重要介质。不过,古体诗歌的创作交流虽然较以往兴盛,却无法获得主流文坛的认可;虽然创作群体阵容庞大,但仍无法摆脱在文坛上的“失语”境况,其文体权力也早已让渡于小说、白话散文以及新诗和戏剧等其他文体。文学以摅写人生情感、表达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为核心要素,只要现实生活生动流转,人生情怀也会变动不居。“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34,生活在变化,情感也相应地会氤氲卷舒。诗歌,无论是古体还是新体,自然有其存在并发展的理由。因此,探讨古体诗歌在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处境、问题与未来走势,为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这种古典艺术形式找到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并绾结国人精神性灵与时代变迁的路径,应该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一、关于当前诗歌文体文学性的缺失与文体权力的丧失
皎然在《诗式》中说:“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2]34在古代文学的文体序列中,诗是最具文体权力的。而诗歌这种文体权力的获取,与古代诗歌具有非常强大的文体功能有关。宋人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犹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3]42诗之所以有其文体权力,盖因其本身就具有作为诗的强大的文体功能。古代诗歌的文体功能之强大,几乎可以说,举凡人生际遇,世事感慨,家国命运以及山川草树,迥野风华,均可以诗来表达。刘勰说“物色相召,人谁获安?”[1]294钟嵘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4]1,都阐明了诗歌可以摅写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相应情感。萧纲曾说自己进行文学创作是因为周围世界的各种物象都时时在召唤着自己:“……至于春庭落景,转蕙承风,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架,车渠屡酌,鹦鹉聚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奋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5]353诗人周围世界的丰富多样和变动不居,决定了诗世界同样地负海涵,无所不有。诗歌具有的文体功能,源自人的情感,源自于“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34的情感发生逻辑。
“诗言志”是我们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后来经过不断发展,或是认为诗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认为诗人抒情时应“发乎情,止乎礼义”[6]12-18,或是认为“诗赋欲丽”[7]83,或是认为“诗缘情而绮靡”[8]1……无论倾向于哪一端,诗都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其文体功能在发展中始终都在印证着孔子关于诗的“不学诗,无以言”[9]261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9]270等等一系列关于诗歌功能的训示。而古代文学在深层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表达上,也可以说是诗性的,讲求的是“言近旨远”“近而不浮,远而不尽”“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兴味盎然、饶有意蕴的审美表达效果。即便是史书,也要求做到“微而显”“志而晦”“宛而成章”“尽而不汙”[10]21的由表入里,表里相宣,可以使人思而得之的表达效果。这种传统审美心理的渐次成熟与最终形成十分稳定的审美定势,与诗歌在文体序列中的突出位置和相应的诗性心理弥散至文学思维之中的传统文化风气有关。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确定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9]270的功能性要求,这便确立了古代诗歌的基本摅写方向和创作宗旨。数千年来,诗的文体功能遂成为古代各种文体中功能之最为强大者。正因为具备了强大的文体功能,故而在古代各种文体共同构成的文体秩序中,诗处于金字塔尖,也最具文体权力。
但是,在古典时代结束之后,古体诗虽不乏作家,但诗的文体权力却遽然失落并让渡于其他文体。在新文学的文体序列中,白话小说的地位勃然跻升,成为新的文体秩序中的王者。同样,白话散文、戏剧和白话诗歌的文体权力也跃居于古体诗歌之上,古体诗歌的文体权力全部失落,几乎可以说,已经被放逐到文学苑囿之外,相应地也丧失了被主流文学研究予以观照和分析的权力。
古典文学发展到新文学,文体序列重新排布,新的文体秩序和文学格局没有容留古体诗歌进行后续展示的任何机会,古体诗歌遂在新文学视野中失位、失语、失势。这一方面自然有文体革命和文化救亡的大历史原因,同时,也与古体诗歌的创作者和批评者们自身忽略了对诗歌进行变创以因应时代需求的文体革新机遇有关。古代文学的诗性传统被现实生活冲刷,被时代总体的叙事要求湮灭,诗性从诗歌弥散到其他文体之中去发挥边缘作用,无法再通过整肃的独立文体去聚结力量并发挥诗性作用。我们前文已经述及,目前古体诗歌在创作与批评上存在着自我作故、无视诗性要素、一切以形式格律为评骘矩矱的风气,这种风气使得本来就失位、失语的古体诗歌成为古董玩意儿,难以发挥出曾经具有的文体功能。于是,古体诗歌文体权力的丧失就成为固然。在分析古体诗歌在当前文体秩序中的尴尬处境时,我们必须正视创作与批评活动在文体权力丧失过程中的作用。
以形式格律绳束创作并主宰批评,是凿空诗歌文体功能的最大祸端。诗写得是否符合铁板一块似的形式规则,是不是像古人,成为作者是否“入流”的唯一标准。“复古”意识成为窒碍摅写性灵的森严壁垒,更何况还不是在精神格调上的“复古”,而是在形而下层面的形式“复古”。明代袁宏道曾对当时的“复古”风气进行批评,他在《雪涛阁集序》中说:“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省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于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唱亿合,优人趋从,共谈雅道。吁,诗至此,抑可羞哉!”[11]710袁氏此说,盖指明代前、后七子影响下的“复古”风气,而我们今天的古体诗创作,还不及前、后七子诸人尚有在诗学旨归上对唐人精神的尊仰与瞻顾。人们以形式格律为所有关于诗的思维的中心,以之推导出的所谓批评鉴赏活动,自然会导致袁宏道所说的“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的精神困局。至于“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句比字拟,务为牵合”的以“剿袭为复古”,更是无须细论。模拟害道,格法束才,王夫之也曾予以指责。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中,王夫之指出“(为诗者)把定一题一人一物一事,于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意,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靡,何尝动得一丝纹理”[12]48。这种无视实际,闭门造车,自我作故的一味仿效模拟,便成为古体诗创作的痼疾——诗无法去融入生活,无法发挥哪怕是些微的文体功能,其文体权力的丧失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再扣问其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叶燮所言更得要领。叶燮在其《原诗·外篇》中对“诗道”沦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他所罗列的原因,在今天看来,似乎变本加厉地存在着。叶燮说:
诗之亡也,亡于好名。没世无称,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窃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后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誉之学,得居高而呼者倡誉之,而后从风者群和之,以为得风气。于是风雅笔墨,不求之古人,专求之今人,以为迎合。其为诗也,连卷累帙,不过等之揖让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闻其论,别亦盛言三百篇、言汉、言唐、言宋,而进退是非之,居然当代之诗人,而诗亡矣。诗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夫诗之盛也,敦实学以崇虚名;其衰也,媒虚名以网厚实。于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以交游朋盍为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滥,诗道杂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义,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诗穷而后工”,然则,诗岂救穷者乎!斯二者,好名实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诗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为垄断名利之区!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问之自有之性情可矣![13]53
叶燮从“好名”与“好利”两方面来分析“诗道”云亡的深层原因。“好名”者,得到了“居高而呼”之“倡誉”,于是众人从风而“群和之”。在这种风气之下,诗简直成为一种为人处世的“羔雁筐篚”,成为妆点自身、联结同类的手段,却失去了对风雅精神的承继,论者只在意其是否合于“今人”胃口而不顾其余。联系古体诗当前的景况,邀盛名者以格律为金科,向风而从者亦奉之为圭臬。无人计较风雅精神,不见谁去在意比兴传统。那种“垄断名利之区”的做派,较之叶燮之所论,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创作与批评可以赋予文体生命力,它决定着文体的命运。然而目前,风气浮薄,“利”字横亘其中。创作与批评在“格律唯一”的旗帜下盘结,也攀结成为相互鼓噪无底线掖扬的朋党。真可谓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以交游朋盍为牙市”,其所导致的便是“是非淆而品格滥”。这种无视公允的批评,使得“以友辅仁”和“友朋勿劘”的古训烟消云散,荡然无存。诗至今日,人不知已失却诗性固有的、作为言志抒情,反映社会人生的载体职能,而沦为形式攀比的奇巧玩物。古体诗在目前的文体秩序中失位、失语和失势,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吗?没有良好的批评风气,评论不去关切诗之文学性,而以格律通吃一切的局面必须予以改变。不为其他,就为诗性传统在我们自身文化中的正当性与正统性所决定的诗必须承载本民族精神血脉的历史义务。
二、关于诗性的修复与诗学意旨的重建
诗性的有无,决定着古体诗歌创作的未来。诗性是深情的寄托、真心的流露,是“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14]154的综合意蕴。诗性是蕴含着感情的审美情境,是足以触动读者心弦的情感氛围。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诗之至处,妙在合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13]30诗要有真情,在言语表述上要灵动自然,生动可感。所谓“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就是此意。诗化境界源自诗性的寄寓,它是一种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境界。表述此种境界,常常言语道断,思维路绝,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使人沉浸其中不能释怀的深远而醲郁的况味。而这种艺术况味,便来自于古代诗歌一以贯之的诗性内蕴。我们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要更好地继承古代诗歌流传下来的诗性传统,就必须先去修复这种诗性传统在当下古体诗歌创作领域中的生存面貌。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古体诗歌那种曾经触动我们先辈的声调、韵律不在当下浮躁的文学语境中继续失声,才能使我们的心灵世界不被促迫的时代节奏冲击成碎片,从而诗意地活在当下,诗意地应对周遭变动不居的一切。
修复诗性,应致力于对包括“韵味”“兴趣”“格调”“神韵”“意境”甚至是“诗法”的精准阐释与充分拾取,这样才能在新的文学语境之下将我们固有的诗性传统予以激活。明代的钟惺在《诗归序》中曾说:“诗文气运,不能不代趋而下,而作诗者之意兴,虑无不代求其高。高者,取异之途径耳。夫途径者,不能不异者也,然其变有穷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变无穷也。”[15]355“取异之途径”可变,即使“其变有穷”,而人的精神随外在世界的变化会有所不同,那么,就须因应变化,在变化中延续,在延续中求变。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过“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他看出了文学不断演化前进的内理。刘勰也主张文学创作应“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要求“望今制奇,参古定法”[1]208,作家应果断地根据时代需求调整创作思路。萧统也曾指出,文学的发展与演进须“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16]1,敢于变创成规,才能紧扣时代与人心。因为文学摅写人的精神情感,而在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激流中,与实践直接相关的人的情感也在不断地变化着,那么,与人的情感相匹配的文学形式以及一些形式规则也应不断地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人的精神与情感。这种因应变化而须要调整改变文学形式以适应实践要求的内在逻辑是文学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形式要素必须不断发展改进的深层原因。古代诗歌的格律要求早已稳固,其平仄用韵的依据,即当时的语音体系也早已变改,不再是古代韵书所可表现的。诗歌本身具有音乐美,而其音乐美的表现,须要借助诵读甚至是内心的默读予以显现。诗歌以古韵评骘,却已无法以古韵念诵,无形之间,诗歌的音乐美属性便流失了。目前的古体诗,尤其是古体律诗的创作,既不能以形式格律统治一切,也不能踯躅于对古韵的依从与否而罔顾现实的语韵要求。
诗性的修复应从古代关于诗学的诸多理论中寻找药石,而“意境”理论就不仅仅是可以疗救诗性缺失的良药,同时还是固本培元,增强诗性、延续诗统的灵药。“意境”理论是古代诗学理论的最终成果。王国维即指出其“意境”论具有集成性。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14]143又指出:“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14]160若从“意境”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观照“意境”理论,可以说“兴趣”“神韵”等理论都属“意境”论的范畴,而“意境”理论本身也因此具有了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集成性,成为古代诗学的核心理论。创造出意蕴悠长,使人涵茹不尽的艺术境界是古代诗人最为重要的精神追求。但古人早已明瞭,诗歌意境的有无实际上取决于创作者的诗学——诗性素养。
诗性素养要求我们对古代诗学的成果应深入领会,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属于本民族的诗学意旨。拙文《从“学诗”到“诗学”——中国古代诗学的学理转换与特色生成》(1)对古代诗学的发展与演进的内在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将古代诗学的授受性、实践性特征与本土诗学的特色生成联系起来论述,本土诗学的基本学理对我们当前的诗歌创作是具有适配性的指导意义的。诗学发展到古典时代行将结束时,王国维集合众说,阐说了其“意境”理论。他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指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14]176简言之,“意境”即写景直接明了,读来感到真切自然,同时,因感情真挚深切和文学语言的自然流畅综合形成的情景交融,具有强大艺术感召力和情绪感染力的鲜活、生动的审美情景与氛围。此外,王国维还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4]142。按照王国维这里的表述,因主体内在感情的真切强烈而直接予以抒发所形成的审美场域亦属意境。此外,王国维还继承了传统诗学重视主体人格素养的理论特色,他明言“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4]27。他认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唯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轼方可称之为伟大。可见王国维的意境理论中还包含着源自儒家诗学的理论观点;同时,王国维对语言自然和情趣自然的反复申说以及对“无我之境”的理论钟情又可见他对道家理论资源的吸取。总之,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具有极强的理论集成性。我们这里所说修复我们古体诗歌目前衰苶的诗性,就是从对“意境”塑造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创作角度上讲的,这是古代诗学的核心意旨,只有在新的文学语境中再造这种意旨,修复诗性才有可能。
在修复诗性的基础上,通过提高诗学素养培植开放、包容的诗学态度和审美旨趣是重建诗学意旨的根本途径。诗学素养要求学者必须“通方广恕,好远兼爱”[17]131,必须具有转益多师的诗性胸襟。杜甫广泛汲取前人经验以熔炼自身的诗学风格。后来江西诗论主张“无一字无来处”,讲求通过学力功夫臻于混成境界。他们虽力主师法前人,但从未拒斥因时而变。陆游曾说:“律令合时方帖妥,功夫深处却平夷。”[18]155他对包括音律问题的形式规则持“合时”,即顺应时代要求的态度。同时,陆游延续了江西诗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19]320的意见,又力主以“平夷”出之,而不是自立涯岸。严羽的诗论则既重学力功夫,又重“兴趣”,追求空灵淡远的诗性意趣。明代王世贞一方面与后七子一样,重视参法前人,又强调“神与境合”。其《艺苑卮言》有云:“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班氏《汉书》,西京已还至六朝及韩、柳、欧,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咏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后却,已落第二义矣。”[20]39-40只有学者自身从古代优秀诗歌作品中汲取精神养分,蓄养诗性内心,才能在作诗时有我在,才能不至于勉强应对形式束缚,窒碍主体精神的摅写与表达。
重建诗学意旨也要从培植内心构建意象世界并统摄成为诗歌意境氛围的能力开始。在古人看来,构建意境要有真情,要合理地根据情感摅写的需要安排意象,从而构成意境。要做到情景合一,安排并设计好能充分容纳主体感情的意象群。但是,安排意象群与构建意境能力的取得,一方面靠功夫学力,即熟读涵咏优秀作品以提升自身的艺术构思水准;另一方面,则主要靠对诗法的心领神会和熟练驾驭。从江西诗论倡导诗法精神之后,重视诗法可以说成为古代诗学的主流意见,即使是构建意味深远的诗歌意境,也离不开运用诗法去驾驭摅写活动。清初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曾就诗法问题阐说过意见,他说:“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杂乱无章非诗也。然所谓法者,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矣。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试看天地间水流云住,月到风来,何处著得死法”[21]188。他认为作者不能在创作中一味遵循所谓的诗法,“不以意运法,转以意从法”,而要发挥主体情感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做到“以意运法”,才能把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感受借助诗歌创作予以传达。对诗法理论阐述得最全面的是清代中后期的翁方纲,他明确提出了“诗中有我在也,法中有我以运之也”的观点。在其《诗法论》中,翁方纲提道,“故法非徒法也,法非板法也。且以诗言之,诗之作作于谁哉,则法之用用于谁哉?诗中有我在也,法中有我以运之也”[22]330。“诗中有我”,便不能模拟抄袭;“法中有我以运之也”,便不能被动地遵循形式规则。只有创作者积极地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探索艺术形式容置主体情感的最佳方式,才不会导致“以意从法”“诗中无我”的尴尬。因为看出了创作者运用并驾驭创作规则才能推进创作,促使创作活动臻于艺术形态的完型的实际,翁方纲进而强调属于诗学审美范畴的“神韵”和“格调”也联属于诗法理论。翁方纲的理论意旨,便是以诗法统摄包括形式规则和审美呈现在内的整个创作活动,也就是说,以诗法连贯创作,以创作臻于诗歌艺术特质的审美完型。因此,提升古代的诗学素养,增强运用诗法的能力,才能有助于我们对诗性的体认,从而修复已经夐然难寻的诗性心怀。
从事古体诗歌的创作,是一种体会古代文学意蕴并借以尚友古人,同时融养我们诗性情怀的颇有意义的创作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借助古代诗歌的韵律、节奏和字句来表达我们自己的生活情感与内心志意。“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都是触动我们内在情感的客观物象。黄庭坚曾说:“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23]24确是如此,只有具备了诗性的内心和一定的诗学素养,才能做到以诗人之眼观物,以诗人之舌言情。客观世界中,举凡人生际遇、世态炎凉,嘉会以诗相亲,离群以诗抒愤——诗依托于现实生活,诗性境界只能源于现实。生活越是嚣杂,我们越是劳碌浮躁,就越是需要我们心灵中有一个诗性的空间来栖息我们的灵魂。古代诗歌的形式规则是否能够容纳我们此情此境中的内在情感,是我们谈论诗性和诗学的唯一参照。诗要找回自己已然失落了的诗性言说功能,要摆脱在目前文体秩序中失位、失语和失势的惨淡处境,并在新的文体秩序中宣示自己的存在,重新获取相应的文体权力,就应该根据时代和生活的客观需求,去修复诗性,增强诗学内蕴,重新振作,绍续绵延数千年的诗歌传统。
三、关于创作的拟态适应与文体秩序的规整铺排
从事古体诗歌的创作需要增强传统的诗学素养,需要大量的阅读实践经验,同样离不开大量的创作实践,也就是习作。习作需要模拟,需要在模拟中揣摩,以裨形成自身的风格。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中载:“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孰以为可教也。’诸君笑而然之。”[24]1189谢榛认为,通过对盛唐十四家诗人的深入研读与揣摩,“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便可成就自身的诗学品格。这种学以为诗的思路,就是模拟。西汉扬雄曾说过能读千赋则可作赋的话,古人大抵认为,通过模拟,可以渐次掌握古人“为文之用心”,可以提升自身的诗学品味与创作能力。模拟是手段,成就自身才是目的。何景明“舍筏达岸”[25]576之喻所阐明的就是这个道理。这种通过模拟来掌握创作技巧、提高创作能力的学诗——作诗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文学环境的一种“拟态适应”。通过模拟来提升自身创作能力,目的是适应当下的文学环境,在由模拟而适应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逻辑和创作行为,实际上是古代诗歌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至涣灭的内在原因。对这种类似“拟态适应”表述得比较详细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体性》篇中,刘勰认为作家具有性情方面的“八体”,作家可根据自身的性情特质,选择师法对象,并通过模拟来获得提高,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1]200就是此意。(2)
目前,我们从事古体诗创作可以运用“拟态适应”的理论。先选取适合自己参究模仿的古体诗作,熟读涵咏,以“夺神气”“求声调”“裒精华”,提高诗学素养,获取古代诗歌的诗性内蕴,再根据实践的要求,以变创技巧和形式法则,去“适应”现实。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学诗、作诗时的“拟态适应”方法在古代诗学中一直都在起着作用。叶燮在《原诗·内篇》中说:“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旨归,得其神理。以是为诗,正不伤庸,奇不伤怪,丽不伤浮,博不伤僻,决无剽窃吞剥之病。”[14]18他认为只有以古人的作品涵养自身,才能“会其旨归,得其神理”,获得诗性内蕴。进而叶燮又说:“若舍此两端,而谓作诗别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谓变化生心,变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则死法为定位,活法为虚名。虚名不可以为有,定位不可以为无。不可为无者,初学能言之;不可为有者,作者之匠心变化,不可言也。”[13]21叶燮认为,“初学者”应掌握“死法”,掌握诗歌创作的基本形式规则,但要以“匠心变化”将“死法”用成“活法”,这样才能“会其旨归,得其神理”,才能“变化生新”。叶燮是在古代诗歌创作在清代前期已经表现为自我更新“内力不足”的情形下阐说其见解的。其实,在古代散文领域也有同样的问题,而刘大櫆给出的理论解决方案也与叶燮一样,均是一种类似“拟态适应”的思路。在《论文偶记》中,刘大櫆说:“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然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要在自家于读时微会之”。从可告人的“死法”中超越,超越到细微体察古人之“神”,就是“匠心”,就是创作主体的诗意与诗性。刘大櫆进而指出:“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有迹可循的字句音节去体察古人诗文之“最精处”的“神气”,刘大櫆给出这样一种方法,他说:“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26]316-317。“以此身代古人说话”,就是一种“拟态”,及至烂熟,便得古人“神气”,同时也做到了“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终于成就了自身,这便是“适应”。
清末,黄遵宪所阐说的诗界革新主张,实际上也是一种绍续古诗传统的“拟态适应”策略。在其《人境庐诗草·自序》中,黄遵宪说:“人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于诗。其取材者,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业,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闻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韦、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27]1。黄遵宪从创作技术到诗学宗趣上均提出了自己激活古体诗创作的思路和设想。他认为创作主体内心要有“诗境”,要继承古人的“比兴之法”,还要广参古代优秀作品的“神理”,要揣摩并运用古人“伸缩离合之法”,同时要增强学殖,要掌握古代语料,也要瞻顾现代语境,敢于涵纳新事物、新语汇,如此才能适应当下,并“自立”于诗坛。黄遵宪之论,与梁启超所说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同一旨趣,都是在时代变革的语境下关于古体诗歌创作的一种“拟态适应”的方案。
同样,古体诗歌的创作必须适应新的文学环境,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创作者须要用模拟的方式改变自身,提高适应新的文学环境的能力。所谓模拟者,就是古代诗歌的各种优秀作品。学者通过深入研磨、细心体会,增强诗学素养,修复内心的诗性,进而以诗意观照万物,带着诗性内心去表现世相,运用诗学素养去完成创作——通过“拟态适应”,去绍续诗歌传统并向新的时代致敬——这便是古体诗歌在当前的文学序列中重新获取本应具有的文体权力的内在理路。也唯有如此,才能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建立起更符合我们自身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的文体秩序。
四、结语
一种文学体裁有没有文体权力,关键在于它能否摅写作者真实的内心情怀,同时也与这种文体能否顺应时代变化,顺应人们不断变化的审美期许有关。读者的接受判断最能体现出一个时代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接受期许,也只有读者,才是一种文体有无文体权力的最终评判者。这种权力并不在那些掌握着话语霸权的人手中,也不是这些人评出的什么奖项能够代言的。他们没有担当天下诗统的道义付出,更没有总览人物,代读者立言的胸襟。他们不是“舆论掌门人”,他们没有这种资格。古体诗歌失位、失语、失势的现实与我们绵延数千年的文学传统精神不符,必须予以改变。修复时代的诗性内蕴,增强创作者与批评者的诗学素养,重建符合传统审美精神的诗学意旨,在此基础上去因应变化,顺应时代,通过“拟态适应”重获文体权力,重新规整文体秩序是古代诗歌流传至今的逻辑要求,也是我们不能继续失语于时代文学语境的义务。古体诗不应是古董玩意儿,不应是各类顽主们交相评骘的奇巧物什,它是文学,是一种曾经陶融了我们数千年性情的诗性存在,它不应成为过去,更不应失语于当下,失语于未来。虽然目前它风光不再,虽然它已沉沦为连边缘文体都算不上的书案摆件,但它曾经蕴蓄过的先贤气宇与深层性灵不允许这样的难堪局面延续。“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与自由”[28]309,只要人的精神世界存在,诗性就会长存,古体诗歌就会有着绍续古代诗统并能摅写现实的未来。
注释
(1)《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2)参考拙文《枢中所动,环流无倦——定势:理解〈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重要关捩》,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