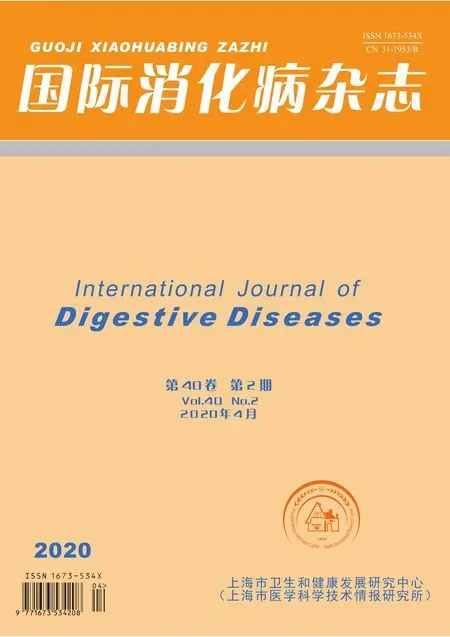肝移植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赵 东 夏 强
肝移植发展的历史曲折而又艰辛,其中既有伟大的胜利,也有惨痛的教训,并且涌现了许多英雄的个人和杰出的团队。从免疫抑制理论的发展到动物模型的创建,从器官保存技术的革新到人体试验的成功,不同学科的齐头并进,攻破了肝移植的多项技术难题。之后器官来源问题的讨论又促进了法律法规的进步,并最终使得这一领域走向成熟。
自1963年Starzl首次将肝移植技术应用于临床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肝移植已成为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唯一的有效方法[1-2]。受益于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开发应用和现代外科技术的创新发展,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肝移植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在国内较大的移植中心,肝移植围手术期患者的病死率已低于5%,受者的术后 1年、5年、10年的生存率已分别达到90%、80%和70%。中国肝移植技术的快速稳定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的医疗技术水平,从而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中国的肝移植技术自2010年起数次走出国门,指导并提升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肝移植水平,为中国的先进医疗技术走向国际,扩大在世界肝移植领域的影响作出了贡献。然而,面对日趋严峻的器官短缺现状以及资源合理分配的要求,如何进一步拓展供肝来源、规范受者选择标准及移植技术标准等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
1 机械灌注技术在肝移植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器官捐献来源。DCD供肝由于热缺血损伤,导致移植后移植物功能延迟(DGF)、原发性无功能(PNF)和胆道并发症的风险较高[3]。DCD供肝的胆道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长期发病、移植物失去功能及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4]。缺血性胆道病变(ITBL)也称为缺血性胆管病,是目前最棘手的胆道并发症。机械灌注(MP)能够提供氧合支持和营养物质,并可冲洗代谢废物,可在热缺血和冷保存(CS)损伤后重新激活肝脏代谢功能,并允许在移植前测定移植物的体外生存能力。CS因其低成本和易于操作,是目前移植中心广泛采用的保存方法。然而,借助科技革命的浪潮,MP技术的应用重获关注。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MP保存方法的应用,但是系统、技术、参数设置和成本的不确定性妨碍了标准化和全球推广。低温机械灌注(HMP)可通过低温环境抑制细胞代谢,并通过保存液或灌注液中的抗氧化物质减轻氧自由基对组织的损伤,同时提供氧合和代谢支持。但有部分研究支持使用常温机械灌注(NMP),通过门静脉和肝动脉提供氧合、营养和代谢支持,从而最大程度地模拟肝脏的生理环境。此外,NMP还可以在移植前动态监测肝脏的功能(胆汁生成、乳酸清除率等),而这在HMP时是无法完成的。亚低温机械灌注(SNP)在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较少,目前仅限于肝移植[5-7]。该方法是一种可在最大限度提高移植物代谢的同时最小化再灌注损伤的新方法,其优势在于既可避免采用NMP的复杂技术和庞大的设备,又可避免HMP对器官的低温损伤和灌注后的复温损伤。然而,对于关键参数如最佳温度、氧合模式、理想灌流、单次和双次灌注、压力和流量设置等还存在争议,至今仍缺乏对理想灌注设置的共识意见。不过,SNP在减轻移植物缺血再灌注损伤方面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发表了关于如何优化参数设置的研究报告。
器官保存技术发展至今,MP再次受到了重视。MP的优势在于其较接近器官的生理状态,可实时动态监测灌注液流速、血管阻力、生物化学指标等参数,以动态评估器官质量。MP的发展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器官保存时间,这可能会深刻影响器官分配政策的制定。MP拓宽了器官保存技术的选择面,但应注意的是,该技术目前仍缺乏高水平的临床证据,因此无法给予循证医学建议。MP是否能在将来取代CS进行器官保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2 肝癌肝移植技术
2.1 术前评估
与胆管癌不同,患有局部肝细胞癌(HCC)的患者可以进行肝移植手术,且复发率低,长期预后较好。Bhoori等[8]的研究表明,如果患者的肝内肿块符合一定的大小和数量,移植术后4年生存率可达75%,无复发生存率可达83%。通常将这些特征归结为Milan标准(即单个肿瘤直径≤5 cm;或2~3个肿瘤,每个直径≤3 cm)。在美国,当患者被诊断为HCC后,如果达到Milan标准,则可在每3个月时获得额外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一直持续到患者获得肝脏,或者持续到患者出现并发症,致肿瘤继续进展恶化。可以得到额外加分是因为这些患者的MELD评分通常较低,在肿瘤恶化并失去移植条件之前,额外加分可增加他们提前获得肝脏的机会。
当患者被列入等待名单后,多数中心选择使用各种形式的局部治疗来减轻肿瘤负荷,从而避免患者在等待过程中出现病情恶化甚至死亡。如果患者的病情进展超出了Milan标准,获得额外的MELD评分能够降低等待名单中患者的死亡率,有研究表明,对超Milan标准患者行肝移植并不影响其生存率[9]。
2.2 术前治疗和随访
无论是否采用新辅助治疗,等待肝移植的HCC患者均需要每3个月进行1次CT扫描或MRI定期成像,以确保肿瘤的稳定性[10]。如果患者出现肿瘤迅速进展则需进行消融治疗,或者从等待名单中移除。肿瘤的快速进展与较差的生物学特性和移植后较差的预后相关。
2.3 非肝硬化HCC的肝移植
非肝硬化HCC主要发生在年轻人群,大多数患者表现为晚期肿瘤。如果条件允许,切除是治疗的主要方法。肝移植主要是在由于肿瘤的特殊解剖位置而不能切除的情况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肝部分切除与较高的肿瘤复发率相关,此时进行抢救性肝移植的效果较好[11]。
3 儿童肝移植
3.1 简介
儿童肝移植技术在过去40年里有了显著发展,目前多数大型儿童移植中心的患者长期存活率超过85%[12]。DCD供肝和活体供肝以及劈离式肝移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器官的来源,降低了患者在等待肝移植过程中的死亡率。目前,等待名单上约有90%的患儿最终成功接受了肝移植[13-14]。通过多学科的团队合作,儿童肝移植受者的护理得到不断优化。围手术期效果良好,临床工作重点已从降低死亡率转向改善免疫抑制方案相关的并发症,如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等。国内儿童肝移植的发展如火如荼,2017年是中国肝移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在这一年内完成了超过400例儿童肝移植手术,使中国完成的儿童肝移植术总例数达到722例,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范围内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例数最多的国家。
3.2 手术适应证的变化
儿童肝移植的适应证有恶性和非恶性两种情况,主要包括:(1)肝外胆汁淤积(如胆道闭锁);(2)肝内胆汁淤积(如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Alagille综合征、硬化性胆管炎);(3)代谢紊乱(如尿素循环缺陷、Wilson′s病、酪氨酸血症、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4)急性肝功能衰竭;(5)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目前中国婴幼儿肝移植的适应证以胆道闭锁为主,占所有儿童肝移植的50%以上,尤其在小于1岁患儿的肝移植中比例较高。大多数胆道闭锁患者可行葛西手术以改善症状,然而,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将进展为终末期肝病(10年内20%~40%),并最终需要进行肝移植[15]。为了便于病变肝脏的切除,在行肝门空肠吻合术时,应尽量减少对肝脏周围组织做不必要的游离,肝门的解剖也应该本着“必要但适可而止”的原则,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术后粘连的形成,从而使肝移植时更容易切除肝脏,使患儿失血更少。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先天性代谢性疾病(如糖原储积症、遗传性高酪氨酸血症、原发性高草酸盐尿症等)的患儿数量逐渐增多,这些疾病通常是影响氨基酸、脂质代谢或线粒体功能的突变的结果。一些代谢性疾病如酪氨酸血症、Wilson′s病或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会导致肝脏发生结构性损伤、终末期肝病或HCC。其他代谢性疾病如尿素循环缺陷会导致全身性代谢紊乱。反复发作的代谢紊乱容易造成患儿神经系统损伤,肝移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损伤发生的频率和风险,但并不能纠正其他器官相关代谢酶的缺乏,因此对于这类患儿行肝移植手术时机的合理把握仍是目前讨论的热点之一。
3.3 术前评估及教育
肝移植前对患儿的评估是在不同学科积极配合下完成的,其内容通常包括是否有肝移植指征,有无替代治疗方案、禁忌证、活动性感染,免疫状态,其他器官功能障碍(如心脏、肺、肾),营养代谢状况,患儿及其父母的心理状态等。适时对患儿及家属进行教育,使其对肝移植的步骤、短期和长期结果以及潜在并发症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对于儿童肝移植的术后管理及随访至关重要。
3.4 免疫抑制
肝移植后应用免疫抑制剂对于降低急性或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风险至关重要。传统上,免疫抑制包括诱导(移植时)和维持方案。2015年器官移植受者科学注册系统(SRTR)年度报告指出,在诱导期,大约80%的中心使用甾体激素,35%的中心使用白细胞介素-2受体拮抗剂[16]。钙调神经蛋白抑制剂是主要的免疫抑制剂,90%的受体使用他克莫司,10%的受体使用环孢素。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长期大剂量使用激素会明显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且不能减少慢性排异反应或降低新发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发病率,因此建议尽可能在术后3个月内停止使用激素。医学界目前尚在探索完全停止使用免疫抑制剂的可能性。这类研究尚处于尝试阶段,具有一定的风险,更稳妥可行的方法是减少免疫抑制剂的剂量,维持最低有效剂量。
3.5 术后感染
在免疫抑制诱导方案下,肝移植受者容易受到感染。因此,任何移植术后患儿的发烧都应该被认真对待,术后第1周或术后早期革兰阴性菌感染较为常见。移植物周围的积液常通过经皮或手术引流来处理。肝实质内脓肿可能是由肝动脉并发症引起的。术后早期真菌感染对一部分患儿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因此他们可能需要再次手术、再次移植。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已在大多数移植中心推广。然而,这些患者因病情反复或较长的住院时间而暴露于多重耐药微生物中,通常为了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而放置了中心静脉置管或动脉导管,这对如何合理使用广谱抗生素提出了特别的挑战。
病毒感染通常是由EB病毒(EBV)、巨细胞病毒(CMV)和单纯疱疹病毒(HSV)引起的。由于这些病毒的感染者并不一定有特异性表现,所以有学者主张常规监测血清病毒水平。血清学阴性患者接受血清学阳性者的供肝后发生病毒感染的风险往往较高。在所有的病原体中,目前研究最透彻的是CMV。预防性使用阿昔洛韦或缬更昔洛韦是常见的术后抗病毒方案。术后EBV感染一直是个突出的问题,它既可以复发,也可以作为原发性感染而发生。EBV感染的临床表现多样,包括肝炎及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等。当检测到EBV感染时,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有助于清除病毒。部分中心也应用更昔洛韦或免疫球蛋白G行抗病毒治疗。
4 预后及未来展望
随着外科技术和免疫抑制方案的改进,大多数移植中心的患儿1年生存率超过90%,5年生存率超过80%。甚至在婴儿和小于10公斤的儿童中,术后生存率已由最初的50%上升至接近高体质量儿童的水平。劈离式肝移植、亲体肝移植和器官分配的优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移植等待名单中患儿的死亡率。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趋向于关注患儿术后的生活质量,而不再是早期存活率[17]。追求手术技术的改进和对移植外科医生的重点培训仍将是儿童肝移植继续蓬勃发展的基石。此外,免疫抑制方案的优化、免疫耐受的策略是基础研究的重点,也是改善儿童肝移植远期预后的关键[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