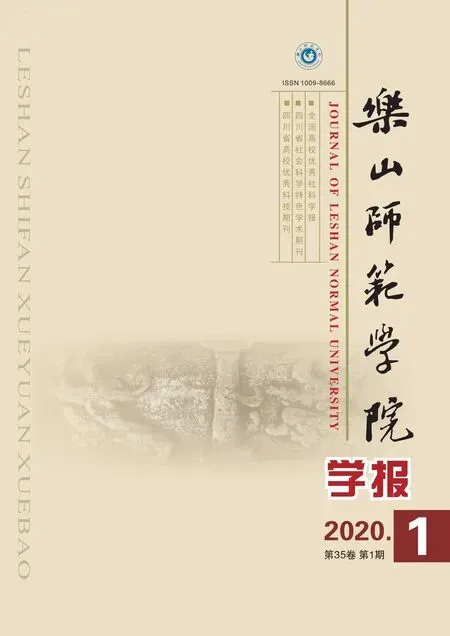“二维码案”定性分析
——以引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视角
唐婷婷
(深圳大学 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
电子支付的发展催生了新型刑事犯罪,典型代表是以替换支付码取财方式的“二维码案”。“二维码案”是指,犯罪行为人趁商户不注意,偷偷替换商户收款二维码,以获取顾客支付商户资金的行为。如犯罪嫌疑人A到商户B的摊位或店铺,趁商户B不注意时,用自己的收款二维码将商户B放置在收银台的收款二维码覆盖,顾客C、D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扫码后将钱支付给了犯罪嫌疑人A,因此商户B未能收到相对应的货款。
此类案件因作案方式新颖,且参入了多方法律关系,因而在司法实务中引起热议,受到了学术届的关注,并引发了诸多形形色色关于“二维码案”判定和定性的观点。然而,各观点在论述定性依据的时候,均忽视了新型支付手段介入后形成的多方法律关系,忽视了支付平台在支付关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为正确判定和定性二维码案件,必须在整合民事关系和刑事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定性二维码案。
一、问题分析
从已判决的案件来看,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的定性在学术界引发的热议并未对司法实务造成过多的影响。司法实务中多认定替换二维码取财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法院也多判定行为人成立盗窃罪。仅在少数案件中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但法院最终亦认定为盗窃罪(如表1)。由此,为有效判定二维码案件,应当分析二维码案件在学术界存在的争议内容和要素。

表1 2017-2018年二维码案件起诉、定性情况①
二、争议分析
(一)争议焦点问题
二维码案件主要在定性方面存在争议,即行为人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盗窃罪还是诈骗罪。虽然盗窃罪和诈骗罪区分的争议由来已久,但是二维码案件在盗窃和诈骗的争议上,又引发了间接盗窃与普通盗窃,普通诈骗、双向诈骗、三角诈骗和新型三角诈骗的争论。如此差异,是因为学者对被害人的确定、侵犯对象的认定均存在不同的观点。
1.被害人的认定
谁是被害人,是区盗窃与诈骗的分水岭。
持诈骗罪观点的学者认为“顾客作为涉案款项的占有人,其失去了涉案款项的占有,因而是被害人。”[1]即根据谁占有财产的处分权来决定受害人。在二维码案件中,顾客作为交易的相对方,在获得货物后,理应支付对应价款。然而,在以二维码方式支付的过程中,顾客并非真正的占有者。因此,不应仅从表面确定谁是财产的真正占有者,而据此确定受害人。
持盗窃罪观点的学者认为,财产权益损失的人就是被害人,故从赃物退还的角度,因顾客已经获取了商品,所以不管是从实际的赃物退还,还是受害人的权利维护方面,均是商户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商户才是真正的受害人。本文赞同此观点。
2.侵犯对象
对于被侵犯对象的认定,存在商品或财产性利益之争。前者认为行为人替换二维码取财的行为是直接对商品的盗窃。实际上,行为人并未获得任何有形商品,而是获得与商品对价的资产。后者认为行为侵犯的是财产性利益,因为被害人丧失的是对应的财产,以及要求顾客再次支付对应款项的民事权利,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属于财产性利益。本文赞同后者的观点。
(二)定性观点评析
被害人、侵犯对象作为关键要素,其差异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定性。即引发了关于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区分热潮。
1.诈骗罪观点
诈骗罪争议中,又分为普通诈骗罪、三角诈骗罪和新型三角诈骗罪三种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不管是普通诈骗罪、三角诈骗罪还是新型三角诈骗罪,其本质均是有人因为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财产。为便于理解,本文仅选取普通诈骗罪和新型三角诈骗罪进行详细分析。
(1)普通诈骗罪
持普通诈骗罪观点的学者认为二维码案件中被害人是商户,行为人通过替换二维码的方式,虚构事实,使店家误认行为人的二维码是自己的二维码,基于该错误认识引导顾客扫描该二维码付款,使顾客处分了本属于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得了财产。因此该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从表面来看,二维码案件似乎符合诈骗的构成要件。但实际上存在以下两点问题:
一是根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诈骗罪成立需要行为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予以欺骗,即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要存在沟通、协商的行为,但是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中,行为人并未与商户或者是顾客之间存在任何的联系,而是在商户不注意的情况下,偷偷替换了二维码。因而商户或者顾客根本无从知晓有行为人的存在,即不能因此认定行为人替换二维码的行为使商户存在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
二是处分的前提是实际占有该款项,即以享有该款项的所有权为前提。二维码案件中,商户并未实际占有还未到达的货款,因此对于并未实际占有的款项,自谈不上处分。质言之,商户并没有处分还未到达自己账户内的货款,商户就不存在处分货款的行为。故本文认为不能将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认定为普通诈骗罪。
(2)新型三角诈骗罪
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二维码案件中,是“被告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自己的财产,进而使被害人遭受损失”[2]。与普通三角诈骗存在差异,普通三角诈骗是由于被骗人处分了受害人的财产,此类案件中是受骗人(顾客)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即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中受骗人和处分人并非同一人,有别于正常的三角诈骗,应认定为新型三角诈骗。实质上,张明楷教授也认为新型三角诈骗与传统三角诈骗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若认定为新型三角诈骗,有利于更好的处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质言之,张明楷教授仍赞同二维码案件属于诈骗罪的范畴,即仍然存在着欺诈行为。
此观点虽然进一步将事实与案件融合,可以帮助理解和分析案件。但实质还是承认二维码案件是诈骗。因而也存在疑问:
一是从处分意思的角度来看。处分意思不要说“要求受骗者具有某种转移的意思,要求受骗者对于将特定财产转移给行为人占有具有认识和意志”[3]。即要求被骗者具有将特定财产转移给行为人占有的认识和意志因素。换言之,在诈骗罪中,受骗者对于被骗转移财产的外在情况要有所认识。但二维码案中,商家并没有发现二维码被更换,因而商家根本不可能认识到顾客所支付的钱款将被转入行为人的账户,更不可能存在将该钱款转移给行为人占有的意思。所以即未对其所转移财产的外形有所认识,也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占有。所以,顾客、商家均不存在诈骗罪中所要求的处分意思,不符合诈骗罪要求的处分行为的要件。
二是从被害人教义学角度来看,被害人教义学由阿梅隆教授提出,其认为在诈骗罪中,当“被害人对行为人实施的‘欺诈行为’产生具体怀疑时应该排除错误。”[4]由此,将诈骗罪判定为互动型犯罪。即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需要辨别的欺诈行为。质言之,诈骗罪需要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行为人是立足在双方已有互动的基础上实施犯罪。二维码案中,行为人没有与被害人、受骗者产生任何互动交流,并不符合从被害人教义学角度认定诈骗罪犯罪模式的要求,因此也不能定性为诈骗罪。
综上,本文认为二维码案件并不符合诈骗罪、三角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首先,替换二维码取财案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并未存在沟通,不存在欺诈事实;其次,被害人也不存在将财产性利益处分给行为人的意识。因此,不能将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定性为诈骗罪。
2.盗窃罪观点
持盗窃罪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人采取秘密手段调换二维码取财,商户作为被害人,根据社会生活经验认定顾客在确认支付时商户即占有了该债权,故行为人以秘密手段窃取商户占有的债权,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盗窃罪。
本文认为,此观点以社会生活经验作为标准,模糊了实际判断的标准,并不能有效论证二维码案件为何应当被认定为盗窃罪。
首先,替换二维码的行为作为取财的先行行为,只是获取货款的方式。因此,不能仅通过替换二维码的先行行为即断定二维码案件符合盗窃的客观要求。
其次,根据一般社会观念以确定商户占有财产性权益,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社会观念本身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反之,亦可根据社会观念认定顾客支付的钱款转移到了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如同淘宝支付一样,并未实时到账。因此,本文认为以此论证二维码案为盗窃,理由不充分,理论上也经不起推敲。
综上,不管是将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认定为诈骗还是盗窃,在定性或论证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定性和论证过程中,都忽略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存在,未考虑第三方支付机构在此类案件中的作用。故本文接下来将立足于整个案件事实,纳入第三方支付机构,综合案件事实和已有理论,分析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的定性。
三、本文定性分析
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产生于新型电子支付,其定性自然脱离不了电子支付手段的分析。因此在定性之前,应当清楚二维码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方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判定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
(一)作案工具解析
二维码是指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图片代码。[5]支付型二维码是交易中常用的二维码,支付型二维码是以二维码为载体由第三方支付机构管控债权债务数据的一种支付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新型支付方式。这种支付方式通过数据变动使债权债务转移,改变了以往现金支付的模式,减少了现金流。
第三方支付机构主要从事资金转移、结算业务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资金转移活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银行”的支付机构,有支付宝、微信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机构生成的支付型二维码分为付款扫码②和收款扫码③。收款二维码是指第三方支付机构代为收取款项,付款二维码是指支付机构代为转移资金款项。不同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不能转换,因此二维码取财案件只能发生在同一第三方支付机构内。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二维码将顾客、商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连接起来,形成了复杂的法律关系。行为人正是利用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资金流动的便捷性获取钱款。
(二)多方法律关系

图1 第三方支付关系、二维码支付流程
根据第三方机构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④,可以确定在二维码支付关系中行为人与支付机构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即在二维码案件中,商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是委托收款关系;顾客与第三方支付机构是委托付款关系。以支付宝为例,其确定了商户和顾客收、付款二维码的法律关系。支付宝服务协议规定了代付⑤和代收⑥两种概念,将代收行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从支付宝账户转付至银行账户中,另一种是从支付宝账户转付至支付宝账户。
根据资金流向,确定支付机构是受托人,商户是委托人,委托的事项是收取钱款(如图1)。行为人替换二维码的行为,直接破坏了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商户、顾客之间正常的委托合同关系。
(三)第三方支付机构
如上所述,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二维码案件中作为被委托方,是支付关系中的关键,也是二维码取财型案件定性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被纳入案件予以分析,以有效确定被害人和行为侵犯的对象,最终合理地判定二维码案件。
根据第三方支付机构与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付款人和收款人之间的资金关系建立在付款人与付款机构的委托合同之上,付款人扫描第三方支付机构生成的二维码进行支付,付款人凭付款指令发起付款程序,以此产生付款人与付款机构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到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中,顾客通过电子终端,直接向支付服务商发出支付指令,支付服务商在其资金数据中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质言之,“在第三方支付中,付款人发出付款指令后,支付机构须具体执行代付事务,完成资金移转”[6],即第三方支付机构根据支付指令,在付款人和收款人双方的“钱包”中进行计算机数据程序操作变动数据,实现付款人资金转移、收款人获取资金的目的,完成债权债务关系的变动。因此,在替换二维码取财的案件中,商户当面将商品交付顾客后,通过扫描商户二维码的方式完成了支付对价的义务。然而,事实上,顾客是扫描了行为人的二维码,导致第三方支付机构依据错误信息,将货款转移至行为人账户,商户由此失去了商品的价款。在此过程中,顾客在获得商品并扫码支付后,货款即转移至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了交易。实际上,顾客支付了对价获得了货物,不存在着民事或者刑事意义上的损失,也不能向行为人主张退赃。因此,商户才是真正的被害人。
根据委托合同关系,当委托人完成了被委托的事项时,从实际意义上可以认定为被委托人在观念上控制了被委托的事项。对应到二维码取财型案件中,当付款人完成了付款行为后,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被委托方在接收相应的资金转移请求时,在第三方支付机构未进行资金数据变动的短暂瞬间,可以认定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占有了相应的资金,与此对应作为委托方的收款人依附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在相应的瞬间即占有了该资金。换言之,在付款人完成支付指令后,资金指令到达了第三方支付机构时,行为人替换二维码的行为,直接改变了二维码数据,使债权转移产生错误,导致第三方机构根据错误的信息进行支付。即第三方支付机构依据行为人的二维码数据,将相应的资金划入了行为人的账户。正如行为人趁付款方疏忽时替换银行卡(号),使资金转移到行为人银行卡的行为。虽然银行卡和二维码的制作过程涉及到不同的技术手段,但偷换银行卡(号)和调换二维码行为无本质差异,均采取调换收款关键信息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非法占有他人钱款。只是替换银行卡(号)获得的财产来源于银行。二维码案中行为人获得的财产来源于第三方支付,将二维码作为犯罪的工具,误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将顾客指定的消费款划拨至行为人账户,以获取钱款。
此外,“二维码支付的本质属性是资金在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内的流动。商户和顾客对支付机构享有债权,而支付机构实际占有并管理着账户内资金”⑦。换言之,在第三方机构内部的资金是由第三方机构实际控制的,用户可以在其余额限度内“使用”,但是无法直接获取现金。实际上,在第三方机构钱包内的资金数额,本质上是随时可申请的财产支付请求权。因此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实际上侵犯的是财产性权益。
(四)最终定性
综上所述,替换二维码取财型案件应当考虑商户、顾客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委托关系,因为在介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后,商户和第三方平台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使得商户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短暂控制被转移资金时,即占有了该财产性权益。因此,结合第三方支付机构,全面分析法律关系后,可以得出,二维码案件是行为人以非欺诈方式非法占有商户财产性权益的行为。正因为忽视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存在,才引发了盗窃与诈骗区分的热议。假使不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情况,行为人的行为要么是直接针对顾客,要么是商户,就不会出现被害人是商户还是顾客的争议,更不会出现对其行为是诈骗还是盗窃的争论。因此,二维码案件实质上,是行为人利用二维码技术措施违反商户意志非法占有顾客已经支付转移给商家委托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取的债权的行为,该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故应当被认定为盗窃罪。
在信息网络时代,犯罪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当前的网络犯罪绝大部分都属于传统犯罪的网络化,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变换犯罪方式并不会使犯罪的实质发生变化。正如二维码案件,尽管犯罪手段中惨杂着信息技术,实际上侵害的也是传统财产法益。所以,对于类似介入信息技术的犯罪行为,应结合案件的全部情况分析法律关系,从本质上去认定犯罪行为。
注 释:
①案件信息来源:http://www.pkulaw.cn。
②付款扫码是指付款人通过移动终端识读收款人展示的条码完成支付的行为。
③收款扫码则是指收款人通过识读付款人移动终端展示的条码完成支付的行为。
④《支付宝服务协议》第3条表述“支付宝服务是支付宝向您提供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受您委托代您收款或付款的资金转移服务”。
⑤代付是指“自款项从您指定账户(非支付宝账户)出账之时起至支付宝根据您或有权方给出的指令将上述款项的全部或部分入账到第三方的银行账户或支付宝账户之时止的整个过程”。
⑥代收则分为两种情况:“(1)自款项从您的账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账户或其他账户, 但不包括支付宝账户)转出之时起至委托本公司根据您或有权方给出的指令将上述款项的全部或部分支付给第三方且第三方收到该款项之时止的整个过程;(2)自您根据本协议委托本公司将您银行卡的资金充值到您的支付宝账户或自您因委托本公司代收相关款项到您的支付宝账户之时起至委托本公司根据您或有权方给出的指令将上述款项的全部或部分支付给第三方之时止的整个过程。”
⑦阮齐林,全国十佳公诉人谈“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案”定性,网名为机器猫大王的作者认为,从二维码支付的本质谈本案定性,二维码支付的本质属性是资金在支付机构账户内的流转。商户和客户对支付机构享有债权。本案的行为人破坏的是商户对支付机构享有的债权。本案的行为手段更符合盗窃罪的特征。载“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https: //mp.weixin.qq.com/s/ 80OmCDjGyIIBjMRjDcRLlg,访问日期:2018 月 6 月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