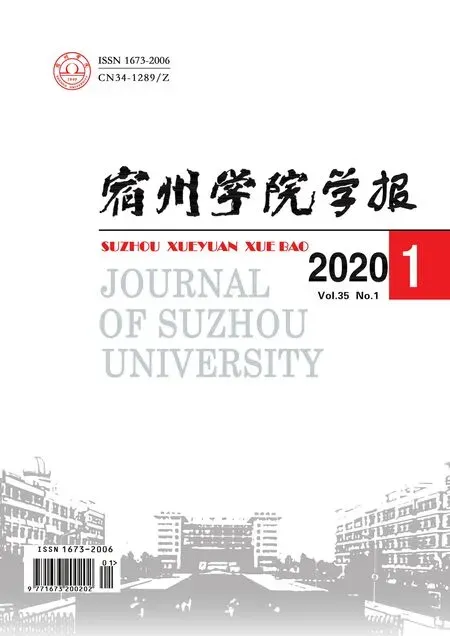泗州戏拉魂腔艺术特色剖析
丁志刚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基础部,安徽合肥,230088
位于安徽省东北部的泗县(古称泗州)是泗州戏拉魂腔的主要流传地段。新中国成立后,拉魂腔正式定名为“泗州戏”,它与柳琴戏、淮海戏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在淮河两岸的皖北、苏北和鲁南相接壤的广大地区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她以美妙的旋律、优美的唱腔唱响淮河两岸。
因为该戏拉魂动魄之处极为使人念想,因此便有了她最初的名称——“拉魂腔”。她有别于其他剧种特别之处在于独有的尾音拖腔翻高和精湛的花腔技巧,感染力极强。淮河两岸地区这里至今还流传着“‘拉魂腔’一来,跑掉了绣鞋,拉魂腔一走,睡倒了十九”[1]的民谚,足见这个剧种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之所以在当地很多老百姓一直叫它“拉魂腔”,因为这种戏曲从音乐伴奏、锣鼓点子到唱腔表演都是十分地让人们“着迷”,只要小锣子一响、琴声一起真的就能够把人们的“魂”给勾了过去。
1 泗州戏拉魂腔唱腔特色
泗州戏拉魂腔的唱腔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它的唱腔不分行当,只分男女。男腔都用大嗓(真声)演唱;女腔的部分花腔、拉腔以及唱腔的高音区用小嗓(假声),其他用大嗓,虽然没有形成行当唱腔,但不同的演员,不同的角色,又有多样的风格特色”[2]。
1.1 “怡心调”
泗州戏拉魂腔的地方特色和音乐唱腔尤其突出。该剧中男腔粗犷、嘹亮;女腔宛转悠扬,并且花腔技巧丰富,无论是男腔还是女腔,都可谓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令人回味无穷。所谓“怡心调”,演唱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创造,自由变化,也就是所说的“怡心调”。它是整剧中的最大特点,一唱起来就把人的魂都拉走了,要求伴奏跟着演唱者走。演唱者基本不受音乐伴奏的束缚和影响,常常是说中夹唱、唱中夹说,演员可以根据自身嗓音条件随意发挥,所以被称为“怡心调”,如谱例1所示。
在这个部分明确写出:“紧拉慢唱”,并且节拍变化比较自由,这就要求伴奏要紧跟演唱者,由于该剧“怡心调”的特点,形成了特有的“即兴性”,并且每个演员都会因自身的嗓音条件、情绪饱和度及艺术素养决定,他们在不同时间地点、不同的剧目中带有不同的“即兴性”演唱。

1.2 “拉腔”
“拉腔”是拉魂腔极具特色的艺术手法,男、女腔均有。一般用在结尾处,但不是每句都有。尤其是女腔用“小嗓子”拉腔,在句尾翻高八度拉腔,并伴有虚词“哎”“嗯”等;而该剧的男腔“拉腔”,是加入衬词拖后腔,也叫“后腔”,一般是在句尾有一个级进音程,常用“安、衣”,“啊、呀”等,如谱例 2所示。

如谱例2所示,男腔所用的衬词为“哪、咳、咳”,男腔的“后腔”虽不如女腔丰富,但也有线条曲折的旋律。
泗州戏“拉魂腔在唱腔的落音处,女腔常用小嗓子(假声)在尾音处‘啊’或‘嗯’字这个音上翻高,拖一个小小的、上翘的尾巴,明快野艳,风情万种,‘拉魂’也常在此处,委婉极致,动人心魄,故有‘拉魂腔’’之称。”[2]
宿州市泗州戏艺术团团长——陈若梅说:“拉魂腔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女的唱腔后面结尾那个音翻高那个‘啊’或‘嗯’字,拉的很长很长的那个长腔,这就是泗州戏的特点。”[3]如谱例3所示。

如谱例3所示,在第三小节的结尾处“哎”字过渡到“嗯”上时,忽然来一个小七度大跳,翻高七度,给观众耳目一新,也就拉住了听众的“魂”,当然这就要求演唱者一定要用小嗓来演唱,这就是泗州戏拉魂腔的独特魅力所在之处。
1.3 “打舌头”
所谓“打舌头”也就是“花舌”。泗州戏“拉魂腔在演唱过程中发出的‘打舌头’是无史料记载的,而这一唱法也是的确存在的,拉魂腔的‘打舌头’音一般是在一句话的结尾处或歌曲间奏处,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加入‘花舌’,且演唱时间长度可以随着演员的感情或现场的气氛来决定,甚至一直到观众的掌声响起时候才停止。‘打舌头’这一技巧,演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入串词中,同时还可以作为呼吸换气的语气词,‘打舌头’这一技巧很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每当‘打舌头’出现,都会得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4]如谱例4所示,在第七小节出的“得儿”就要求演唱者,用“花舌”来演唱,直至本句结束。

2 泗州戏拉魂腔语言特色
语言是戏剧的主要要素,戏剧又是语言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地方戏的特色主要体现在音乐和方言两大要素上。泗州戏拉魂腔属于地方戏,受皖、苏、鲁、豫地区和长江北部、黄淮文化的影响,在“生活的反映”和“反映生活”的双向再造中,以及北方人文气质、民风民俗的熏陶滋养下,逐渐形成了淳朴泼辣、热烈浓郁的淮北方言剧种风格,具有鲜明强烈的“草根”特征,因而拉魂腔又被誉为“淮河岸畔一朵花”。
在戏曲中,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介绍、矛盾冲突的展开与解决、细节的描绘、环境气氛烘托与雕琢等等,都必须通过语言来完成,所以语言是决定这一部戏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而泗州戏拉魂腔的语言基本使用的上全是当地方言,具有口语化,不仅诙谐幽默,最重要的是通俗易懂。泗州戏拉魂腔的语言之所以有独到之处,是与淮河两岸地区劳动人民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思想依托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在泗州戏拉魂腔《绣鞋记》剧中,女主人公生得貌美如花,戏词中有一段巧妙而生动的描写:
“卖布的看见二女子,人要鱼白扯毛蓝;
卖药的看见二女子,人要甘草抓黄莲;
卖饭的看见二女子,稀饭锅里抓把盐;
卖饺子的看见二女子,饺子就对缸里掀;
剃头的看见二女子,我的乖乖,耳朵割掉大半边!”
从泗州戏拉魂腔朴实生动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该剧流传地区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朴实天性和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愿景,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的态度。
另外,泗州戏拉魂腔中的台词大多是采用对话的形式,从这些对话中不仅可以看见活生生的农村生活片断,而且可以看出人们是怎样面对生活,怎样对待不同类型的人,对善良者的同情,对恶者的憎恨和嘲笑等。例如《姜胥搬兵》中的一段,姜胥与薛金莲的对话相当风趣。
姜胥:小莲,你为何捣二哥的乱子?
薛金莲:我怎么捣你的乱子?
姜胥:我跟山贼奋战,眼看就要逮住了,你为啥把他放走?
薛金莲:你逮山贼?为什么你在山贼头里跑?
姜胥:哦……我上山不知路径,特地把他引到山下来,好逮活的!
薛金莲:哟!我看真喽,山贼一枪都把你吓得趴到石头上啦!
姜胥:咳!不是的,是俺杀起了火,俺趴在石头上冰冰肚子的。
这一小段插话,不仅风趣有味,而且把薛金莲的天真烂漫和姜胥的死要面子描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又如《四告》一剧中“黄桂英护法场”的一段,它描写了正在绣花的黄桂英,忽然听丫环禀报自己的未婚夫已被绑赴刑场,马上就要开刀问斩了,这时黄桂英万分惊愕,她唱道:
“插什么花,描什么云?
做什么闺女为什么人?
噹啷啷扳断剪花剪,咯嘣嘣撅断绣花针,
扳断剪花剪、撅断绣花针。”
就在这短短的几句唱词,就把黄桂英当时万分紧张、激动的情感和泼辣、倔强、大胆的性格生动地描写出来。
在泗州戏拉魂腔的许多剧目中都可以看出人们怎样来塑造他们所喜爱、拥护或讨厌、憎恨的人物。他们把自己喜恶的对象描写的栩栩如生,对于不熟悉的,他们也会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塑造,比如拉魂腔舞台上出现的王侯将相、公子王孙之类的人物,都带有几分土气,因为这些人物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形象。虽然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人物与真实的上层人物有所距离,但是这正是泗州戏拉魂腔语言独特魅力所在。
3 泗州戏拉魂腔的表演特色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泗州戏拉魂腔也一样,集唱、念、做、打为一体,合称为“四功”。其中“做、打”两功为形体表演,“唱、念”属于声音的艺术范畴。泗州戏拉魂腔表演除了受淮河两岸地区的生活习惯、习俗风尚影响外,她同时也吸收了流传到这个地区其它剧种的艺术精华,如京剧、越剧等。
3.1 念 白
泗州戏拉魂腔的舞台念白作为与歌唱并列的一种手段,具有独特的表现力,虽然有别于歌唱,但是它又与歌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念白分为两种:一种是韵白,即用官话,多为袍带戏,一般用在戏曲中的官宦、文人、大家小姐等身份角色。例如:泗州戏拉魂腔《白蛇传》选段《断桥》中白娘子唱到:“情郎,我今天水漫金山,全都是为了你这个冤家……”二是道白,在泗州戏拉魂腔的生活戏中一般的角色多用道白,比如底层阶段的农民、丫鬟、仆人等角色,道白是舞台化的皖北地区方言,例如:泗州戏拉魂腔《四换妻》中马孤驴唱到:“常言说老年怕丧子,少年怕丧父母,青年就怕丧同床的,这打光棍的日子是真难熬啊。这山东地界,年年灾荒,街上卖女的,我花了十两文银,买了一名,只是我买的这个老婆长的什么样子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大型泗州戏拉魂腔剧目《槐花飘香》中第三幕,二栓娘唱到:“二栓,我的儿唻,我的儿唻……”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当然,这些戏曲演员为了剧本角色的需要,也会随着角色的出生地、生活地而采用该地方言。
念白的艺术性表现很强,对声音的控制力要求也很严格,即所谓:“千金白,四两唱”的道理。念白的运用规律要注重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符合角色的人物需要,来加以注释;还要掌握念白的节奏,跟着打击乐的伴奏,以烘托不同的节奏气氛;更要注重念白的声音位置与呼吸运用,要以情带声,以声带韵,正所谓“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短而促”[5]。
3.2 “跑 坡”
“由于拉魂腔的源起很随意:每当当地农民干活累了,就自制个土琵琶(也就是柳琴),拨拨唱唱,随口编点小曲,一些容易上口的小曲就在周边流传开来,时间久了,也积累了很多朗朗上口容易被接受的曲目,当每年收成好了,大家凑在一起自娱自乐;收成不好,十年有九年荒的时候,一家人就把全部家当搬上手推车,走街串巷,唱着小曲讨口饭吃,他们把这种形式叫做‘跑坡’”。
如今,这种形式依然存在,只是演唱内容上有所调整,再不是当初的拉魂腔正剧了,演唱者也不仅仅是拉魂腔的艺人,一般都是用皖北地区方言来挨家挨户的唱着小调乞讨,这些小调的歌词内容都是乞讨人自己编撰的,这些曲调很简单,俗称“一捺腔”。如谱例5所示。

因为该曲调每小节时值都是一拍,说唱人手拿两块竹板,身上背着个布袋子(布袋子是为了装乞讨的东西,有的人家不会直接给钱,有时候会给些馒头、大饼或米面之类的东西)。起初这种形式是一些艺人为了生活,以说唱的形式“赶门头”(挨家挨户乞讨),有时候可能会两到三个人一起去“赶门头”,伴奏乐器也出现了木板三弦或者是自制的土琵琶,为了制造热闹的气氛,一人唱,其余人伴奏或是随声附和,一唱一答的形式也经常在“赶门头”中出现。
3.3 “压花场”
泗州戏拉魂腔的表演是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在说唱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来自民间的"花鼓灯"、"旱船舞"等舞蹈表演形式,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并富刚劲泼辣、爽朗质朴的特点。
所谓“压花场”是一种独具一格的表演形式,是泗州戏拉魂腔的表演之根本,分“单压”和“双压”两种。“单压”是一生一旦,也就是一男一女的表演;“双压”是一男两女对舞对唱。“压花场”的表演形式比较简单,由男女演员(小生、小旦)边唱边舞。先由一个花旦伴随音乐节奏上场,做出不同的舞蹈身段,再走出各种不同的步法,接着唱一个“八句子”,然后一小生跟着唱腔舞上场,然后双双起舞。在“压花场”中,男女演员都会特别注重手、眼、腿、腰、步等各个部分的和谐配合,像这样的身段步法,能够叫出名字的就有:提领、顿袖、整鬓、拔鞋、旋风式、撒种式、剪子股、蛇蜕皮、百马大战、浪子踢球、燕子拔泥、鸭子和泥、白鹤亮翅、凤凰单、双展翅、苏秦背剑、怀中抱月等。这些舞姿都是泗州戏拉魂腔艺术家们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独具一格,深受劳动人民喜爱。
3.4 行 当
泗州戏拉魂腔的行当十分有特色,和其他剧种的行当在名称上大不相同。最早时期拉魂腔只有一个人说唱,到明末清初时由说唱阶段发展为两小戏(小生、小旦)、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再后来有了稍微细致一点的行当划分,大致可分为:大生、小生、二头、老旦、花旦、娃娃旦、彩旦、丑旦、奸白脸、老丑、文丑、武丑等。拉魂腔中有一些行当有兼演的习惯,这应该与早期的拉魂腔人力不足有关,例如:大头兼演小头,大生兼演红生等。后来,由于泗州戏拉魂腔正式登上城市舞台,为了进一步适应城市人们的胃口,不断地从其他兄弟剧种中吸取精华,现在其角色行当也就与京剧大致相同了。
4 泗州戏拉魂腔的伴奏特色
拉魂腔的伴奏分为文场伴奏和武场伴奏。文场主要是管弦乐伴奏,武场主要以打击乐为主,合称为“场面”。据泗州戏拂晓剧团团长王怀斌介绍“拉魂腔的伴奏乐器主要有三大件:琵琶、二胡、竹笛,而京剧伴奏乐器由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大件,后来拉魂腔向老大哥京剧学习,才有了武场,才有了锣鼓伴奏。”[6]
4.1 文场伴奏
文场的作用主要是为演唱伴奏和配合表演而用的场景音乐,传统的拉魂腔伴奏乐器主要分为:
弹拨类:土琵琶(柳琴)、扬琴、琵琶、大(中)阮、古筝、小三弦等;
吹管类:竹笛、唢呐、笙、箫、埙等;
弓弦类:二胡为主,其次大胡、板胡、中胡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泗州戏拉魂腔的伴奏乐器也逐渐的加入西洋乐器,比如为了剧目曲风的需要加入大提琴、小提琴、长笛等,如今为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场景需要,增强乐队表现力,还添置了一些传统民族乐器,比如古琴、排箫等。
4.2 武场伴奏
武场的任务是配合演员的念白、身段表演、打斗场面来烘托气氛,以及场次的衔接、“唱、念、做、打”之间的衔接,多用锣鼓统一贯穿。
其武场伴奏与京剧基本相同,但是在音色上却有略有不同,泗州戏拉魂腔主要以铙钹、大锣、板鼓、小锣“四大件”打击乐器构成;色彩乐器由梆子、中国大鼓、小云锣、小镲、定音鼓等构成。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手较充足的情况下,有的还增加了大鼓、小鼓、小钹等,开始打些固定的点子,但没有固定的演奏人员。
4.3 土琵琶(柳琴)主伴奏
泗州戏拉魂腔的主弦乐器——土琵琶(图1)也称柳琴。起初的泗州戏拉魂腔没有固定班设,艺人们走街串巷,怀抱土琵琶,挨门挨户传承拉魂腔,到了20世纪30年代,泗州戏拉魂腔虽然有了简单的班社,虽然乐器增加了梆子,但是土琵琶(柳琴)这一乐器却一直传承至今。

图1 土琵琶(柳琴/柳叶琴)
它的样式如同缩小的琵琶状,粗糙简单,泡桐木做面板,柳木做身,高粱杆做品,通体长约65 cm,两根丝弦,形如柳叶,故又名柳叶琴,只能演奏一个半八度音程,无半音品,不能转调。
土琵琶是泗州戏拉魂腔艺术家们通过长期不断地摸索、实践创造出来的一种弹拨类乐器。后因为它的音域较少,又不太美观,20世纪70年代后改用四根弦。
音色特点:颗粒性极强、富有穿透力、清晰均匀、圆润浑厚。
伴奏技巧:捧、送、闪、托、衬等。
由于泗州戏拉魂腔唱腔的说唱特点,使得土琵琶伴奏起来运用自如,这也是泗州戏拉魂腔伴奏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表现。后来通过改革,多次研制,相继制成了三、四、五、六弦的多种高中音柳琴,现在柳琴除了运用于本剧种伴奏外,还被国内外中西乐队选取用,影响颇大。
5 结 语
泗州戏拉魂腔来自于民间,所谓“风谣歌舞,各附其俗”,她与生俱来的的乡土气息,和她所流传地区的人民生活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她是劳动与艺术的结晶,经过多年的艺术探索,形成自身的艺术特色。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要更加注重她的传承和保护,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就像泗县拂晓泗州戏剧团团长王怀斌说:“从艺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努力培养一批接班人,一直致力于发展泗州戏,弘扬这原汁原味的拉魂腔。”[6]泗州戏拉魂腔也不断地发展创新,推出戏歌、小品、加入流行音乐元素,并学习其他剧种丰富自身,也由原来的城市演出走入基层。
以泗州戏拉魂腔为代表的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地方的象征,反映的是人们的生活现状,它是人类多样化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承载着独特的民族风格情感以及宝贵的时代记忆。“一曲拉魂腔,千里淮河浪”,拉魂腔,这朵散发着皖北地区泥土芬芳的乡野之花,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盛开得更加灿烂辉煌。